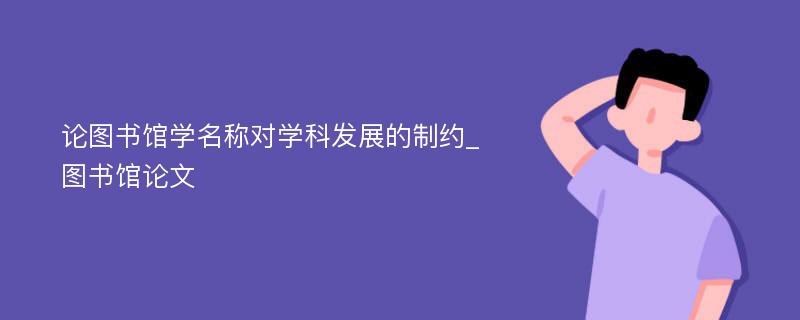
论图书馆学名称对学科发展的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学科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学名称对学科发展的限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科研究对象久论不决,二是教学机构名称屡变。
任何一门学科必须有与其它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独立于科学之林的根基。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1807年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这一名称至今,近200年来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 这种讨论当然是有益的,但一门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讨论竟如此之久,而且仍未见有哪一种主张得到共识,原因何在?在分析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后,笔者认为学科名称的不科学,是使这一讨论不能早日获得圆满结果的主要原因。
根据阐述研究对象时是否遵循“名实相符”的原则,现有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此原则的前提下探讨研究对象,另一类则不受该原则羁绊。
有的论著明确要求在确定研究对象时须“名实相符”。如《图书馆学概论》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必须与学科名称相一致。”[1] 许多学者实际上是遵循着这一原则的,试举要者如下:
——“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1957年)。
——“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李景新:《图书馆学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吗?》,载《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7卷,1935年第2期)。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
——以图书馆整体为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体,不是图书馆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或某一运动形态”(黄宗忠:《略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载《图书情报知识》1985 年第1期)。
——以图书馆活动为研究对象。沈继武在对什么是“图书馆活动”作了一番阐述后,最后将之概括为“泛指古今中外所有图书馆的一切实践活动”(《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载《图书情报知识》1985年第1期)。 郭星寿的《现代图书馆学教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在历数中外各种主张后,也把“图书馆及其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上述观点,说到底都是把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只是着眼点有所区别:“要素说”着重图书馆的内部分析,说明图书馆的最重要部分包括哪几项,并以之为学科研究对象;后几处着重外部包容,即把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都概括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上述诸说虽都做到了名实相符,但所规定的研究对象还是图书馆的表面现象,未能触及到本质。
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构成图书馆的各种“要素”、“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等等,都是图书馆的表面特征。而科学研究的任务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正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现象暴露于事物外表,人的感官可以直接感知;本质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依靠思维才能把握。把握本质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在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尝试中,主要有以下诸说:
——以图书馆的主要矛盾为研究对象。至于什么是图书馆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则有“收藏和利用的矛盾”、“收藏和提供的矛盾”、“管理和利用的矛盾”等不同看法。
——以文献信息交流为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2]。
——以文献信息的开发和利用为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如果没有这个最基本东西的存在,图书馆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的开发和利用[3]。
虽然意见还不甚统一,但已可看出上述诸说正在透过现象向本质逼近(假如说它们还都没有准确揭示本质的话)。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逼近本质的研究对象,还能够与“图书馆学”这一名称名实相符吗?文献的“收藏和利用的矛盾”是否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不是,许多地方存在文献的收藏和利用。“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只适用于图书馆?不是,它适用于任何有文献信息交流的地方。“文献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是否只在图书馆发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如此,研究对象的讨论陷入了两难境地:若要名实相符,只能把图书馆的表面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若要揭示本质,就要突破图书馆的界限,把在图书馆以内和图书馆以外都存在的同本质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看来,学科名称的确阻碍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用机构——‘图书馆’作学科名称就属不妥”[4]。这种“不妥”, 当图书馆在对文献的收藏和利用居垄断地位时,还不明显,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的这种垄断地位将被大大削弱,被有些论者当作学科研究对象的图书馆的表面现象也将发生深刻变革,“不妥”将日渐显著。
如果一门学科连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都不能明确和统一,那么这门学科就不会有严谨的理论,这正是教学单位屡屡更名的根本原因。教学单位原本称为图书馆学系,后由于情报学的加盟而改称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相近或相通,只是情报学的内容不以图书馆为限,因此不能被“图书馆学”涵盖。假如图书馆学有一个反映学科本质的名称,则完全可以把情报学的内容作为本学科向微观和宏观的深化。如情报用户研究就是从图书馆读者研究发展而来的。
继而,“信息”代替了“情报”,各院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又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教学单位的名称中不见了“图书馆学”字样(虽然仍作为专业名称),这是否是因为大家至少在潜意识中感到图书馆学的学科名称限制了学科的发展,遂借行政部门改情报为信息之机,把极具包容力的“信息”一词先拿来“罩”住系名,而把学科的名实问题留待以后再论?如若不然,“信息”代替的只是“情报”,系名改称图书馆学信息学系就可以了,何必把“图书馆学”删去?
80年代初,当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讨论如火如荼之际,就有不少学者提出用“图书馆”这一机构名称来命名一门学科是不科学的,会限制这门学科的发展。目前,规范学科名称又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一级学科的名称——在提出了各种各样一级学科名称的同时,大家无一例外地仍把“图书馆学”作为其下位学科之一,而没有对这个最需要规范的学科名称作一番规范化尝试。其实,考虑到我们多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学科名称下从事的科研和教学的实际内容,只要给这门学科一个科学的、反映其研究对象本质的名称,就完全可以构筑其基础理论,理顺其学科体系。而如果沿用其名,无论是作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还是只作为专业名称,问题都仍将存在。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图书馆学欲图发展,当自正名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