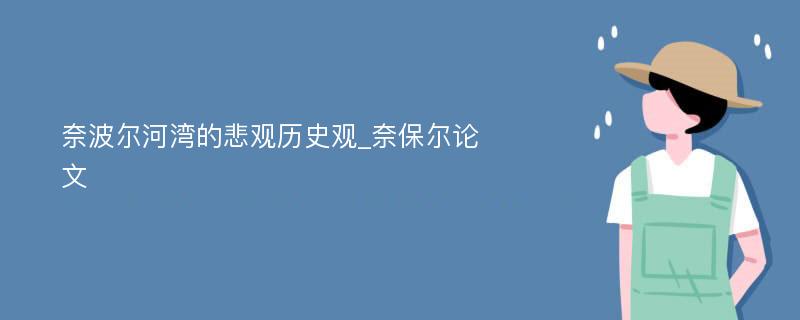
奈保尔《河湾》中的悲观主义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尔论文,河湾论文,历史观论文,悲观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奈保尔(V.S.Naipanl)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其获奖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将富有洞见的叙述与正直的观察结合在一起,驱使我们去了解那被压制的历史存在”。作为一位数十年来始终关注非西方社会人民生存状况的作家,奈保尔是个“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① 他在作品中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讲述着“黑暗世界”的历史。在题为《两个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奈保尔称自己是“凭直觉写作”的作家。② 他这样说显然意在否定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对他的影响,强调自己是位“作为作家的作家而非作为社会人的作家”。③ 不过,这也许是奈保尔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论者无论对其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几乎都会将注意力投向他与当代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奈保尔20世纪70年代的小说创作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奈保尔试图为这个“因变化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做出“另外一种想像性的阐释”,④《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便是这种努力的登峰之作。这部充溢着悲观主义色彩的小说,既深受欧洲文学传统中非洲形象的影响,又源于作者本人对非洲的实地考察,更是作者基于悲观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构建。它用虚构的形式表现非洲后殖民社会生活,属于后殖民话语范畴,而通过解读,我们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向度以及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
《河湾》的故事发生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的非洲,一个正在处于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描写了社会形态的变化对印度族裔非洲人、欧洲人以及当地非洲人生活的影响。故事的主人公兼叙述者萨林姆生长在非洲东海岸,但是他却自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人,因为其祖先来自印度西北部。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萨林姆就离开他所熟悉的社会,到处于后殖民境况下前途未卜的非洲生活。尽管他名义上是穆斯林,但是却缺少像家人那样的宗教意识。当他的朋友纳扎努丁要将自己在非洲中部某个国家的店铺转让给他时,萨林姆欣然应承并历经颠簸驱车来到大河转弯处的城镇。这个地方的状况果然不出所料,新近赢得的独立、军事政变和内战闹得这里民不聊生、一片凋敝。后来镇子渐渐恢复生机,生意也好了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动乱再次降临,萨林姆决定再一次与自己生活的社会脱离。他去英国找到已移居那里的纳扎努丁,与其女儿凯瑞莎订下婚约。然后,萨林姆回到河湾镇结束那里的生意,以便到伦敦重新开始。岂料他不在家期间,极端主义势力以国家信托公司的名义没收了他的店铺。由于有人出卖,萨林姆因非法拥有象牙被捕,但他逃脱了。在小说结尾,萨林姆乘一艘汽船逃离那个城镇,在黑暗中顺河漂流而下,离开那个是非之地。贯穿整部小说的是黑暗的意象,这十分自然地令人想起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呈现的非洲,尽管这两部作品问世的时间相差八十年。
康拉德对奈保尔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直是论者关注的焦点。约翰·特厄姆曾说,《河湾》的标题及其中部非洲背景,立即就能让读者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类似描写。⑤ 佩姬·南丁格尔甚至声称,《黑暗的心》影响到“奈保尔对现实的理解”,其程度“几乎和他自己的观察差不多”。⑥ 潘卡吉·米什拉在为《文学机缘》撰写的引言中指出:“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英语作家中,唯独康拉德似乎有助于奈保尔理解其特殊的处境和困窘:一个殖民流放者的困窘,他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由帝国形成的世界和文学传统中进行写作。”⑦ 奈保尔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康拉德与自己写作生涯的联系。在《康拉德的黑暗》一文中,奈保尔说他在康拉德身上发现了某个人,这个人与那些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不同,是一个“一直在他之前的每个地方”描写那些“作为其文化囚徒”的人;“康拉德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六、七十年前就对我所熟悉的世界进行沉思的人”。⑧
奈保尔主动与康拉德认同,其目的颇为意味深长。有着双重移民身份的奈保尔如同康拉德一样是闯入英国文化中心的外来者,他所受的教育及其阅历告诉他,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从边缘向中心的旅行,其可能性是由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提供的。⑨ 从边缘来到中心,最重要的就是旅行,它不仅可以让他获得创作冲动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必须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这就是说,康拉德对奈保尔影响的重要性,不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作品的结构模式和背景,而在于康拉德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所起的示范作用。诚如奈保尔本人所言,“起步很晚的康拉德,为那些似乎根本就没有起步的人提供了希望”。⑩ 自打十岁那年父亲给他读了康拉德的短篇故事《泻湖》起,康拉德就成了奈保尔效仿的榜样。后来,当以关注“黑暗之地”而闻名的奈保尔将目光投向非洲时,西方世界在康拉德影响下形成的所谓“《黑暗的心》传统”,便成为他理解这个神秘大陆的一条捷径。(11) 而对于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将非洲看作“黑暗大陆”的西方读者来说,奈保尔的非洲表征也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当然,这也正是他试图达到的效果,因为他的作品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12)
如果说萨林姆的非洲腹地之旅类似于马洛进入刚果心脏的旅行,那么他们所遭遇的境况则有本质的不同。《黑暗的心》的背景是殖民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而《河湾》表现的则是处于“去殖民化”进程中的后殖民社会的非洲生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前进数十年之后,《河湾》中所表现的非洲去殖民化进程带来的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殖民统治者带来的欧洲文明被象征着野蛮的丛林所吞噬。诚如故事的叙述者萨林姆所言,非洲人怀着对入侵者深沉的愤怒和“不计后果的破坏欲望”,试图“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殖民时期的塑像和纪念碑”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更令他感到“震惊”和“失望”的是,急流附近昔日“房地产的宝地”已经沦为废墟,重新“变为丛林”,并且“按照非洲惯例变成了公共地界”。(13) 相对于欧洲文明而言,丛林意象意味着一种吞噬文明的力量,它导致“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契约的破坏”、“偷窃、腐败和种族主义的骚动”。(14) 与丛林为伍的非洲人是这种毁灭性力量的行为主体。他们要么“迷恋现代的东西”,要么断然拒绝不熟悉的事物(第5页)。生活在被丛林环抱的“隐蔽的村庄”里(第65页),对他们而言,那是“真实、安全的世界,有森林和障碍重重的河道防护,外人无法闯入”(第9页)。此外,他们还受到祖先在天之灵的保护。这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非洲传统抵御外来文明的力量。可是奈保尔的非洲表征告诉人们的却是:非洲人在现代世界无法保持其传统的价值观,曾经被殖民的个体和文化非但拒绝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且模仿殖民者的生活和文化。应该说,这是对后殖民社会本质与历史的一种误解。作为一个后殖民文本,《河湾》从来也没有展示过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摆脱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给非洲人带来的不是美好生活的希望,而是战火频仍、混乱无序、血雨腥风的现实。独立之后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在小说开篇,为寻找新生活深入非洲腹地的萨林姆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什么新生活”(第4页)。这实际上已经为整个故事定下了基调。
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一种观点,即殖民秩序的终结似乎为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带来希望与雄心,可是“殖民地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独立就不再是殖民地”。(15) 这就是说,西方殖民权力尚未真正放弃对前殖民地的控制,有论者将“这种持续的西方影响”界定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16) 还有论者指出,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非洲表征暴露出非洲国家的危机,这种危机使得非洲国家无力行使三种重要功能:一是不能制定法律和维持秩序;二是无法保持其合法性;三是不能管理公共事务。简而言之,就是丧失了统治的权力和能力。(17) 在《河湾》的叙述中,现实境况让萨林姆感觉到“人人都可参与混战的独立已经到了尽头”(第77页),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回到殖民时代的过去,即那个所谓“不可思议的和平时期”(第34页)。河湾镇的人民因此得接受他们毫无希望这个事实。现实的情况是,假如他们反抗,情况会变得更糟:他们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因为“世界如其所是”(第3页)。由此奈保尔得出结论,第三世界人民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属于真实可信的人类,他们不能制造炸弹和机器,而只是消费这些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奈保尔看作新殖民主义的代言人。萨义德指出:
奈保尔思想的要点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仅“压下去未解决的”、“真正紧张的形势”,而且还扑灭了抵抗它的最后希望和西方文明最后一点影响。……作为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旅行作家和小说家,奈保尔成功地、生动地说明了一种西方的思想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就能够批评殖民地国家无条件获得的独立。(18)
这种西方的思想立场就是:假定白人/西方殖民者对于黑人/被殖民本者的优越性——以及前者压迫后者的权利,而后者的作用不过就是重申前者的优越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河湾》的叙述中非洲黑人不具有统治自己的能力。
河湾镇所在国家的总统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的独裁者。论者一般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蒙博托。1975年初,奈保尔重访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即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其直接产物是《刚果日记》(1980)和《刚果的新国王:蒙博托与非洲的虚无主义》(1975),前者是一部发行量极小的著作,后者则是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其中许多内容后来成为《河湾》中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奈保尔将《刚果的新国王》一文作为《河湾》的物质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小说获得一种历史感和真实感。《河湾》中的大人物雄心勃勃,想成就一番大业;“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人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困难重重的非洲,创造出一个堪与任何国家媲美的东西!”(第100页)不过这样的东西始终只是停留在话语层面上,如萨林木所言,是用“语言描述的非洲”(第123页)。由于要与过去决裂,大人物需要模仿一种政治生涯,仿效他在西方见到的展示权力的方式,像戴高乐一样向其政敌的妻子致以私人的问候(第188页)。当然,大人物并不真正理解法国政治的理论本质,他模仿的是相异于非洲经验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姿态。同样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人物决定建立“新领地”,办起文理学院,让来自欧洲的教师实施对非洲青年的教育,将他们造就成新型的非洲人。而这些青年原本是一些像费尔迪南一样来自丛林的无知少年,他们认为“非洲以外的世界正日渐衰落,而非洲则正在复兴”(第48页)。新领地有豪华的现代建筑,成为一个崇尚西方价值观的样板。可是作为现代化非洲样板的新领地除了“满足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外(第101页),丝毫也不能让人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耗费巨资兴师动众建立起来的新领地其实“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它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毫无信心。”(第103页)因此,新领地尚未完全建成就衰败不堪,成为整个国家衰败的缩影。
《河湾》中的大人物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就像满怀希望来到新领地工作的因达尔所言,他是了不起的非洲酋长,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是搞现代化的人,也是重新发现了其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他无所不是。他既要回归传统,又是一个要奋勇向前的人,他打算在2000年之前将这个国家建成世界大国。我不知道他是偶然做了这一切,还是因为得人指点。但是这样杂七杂八的方法倒真能奏效,因为他一直在变。他是决心成为老式酋长的军人,而他的母亲却做过宾馆女佣。(第138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萨林姆的叙述中,大人物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真实性:总统的权威是靠随处可见的总统照片展示的,而人民对他的服从则表现为对“非洲圣母像”的崇拜。应该说,总统试图建立的新非洲只不过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理想之地,是“非洲里的欧洲”,与“丛林和村庄的非洲”没有丝毫联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声称拥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却依赖于欧洲顾问。代表欧洲知识分子中理想的“非洲主义者”的雷蒙德一度对总统的观点颇具影响力。他居住在新领地以非洲为研究对象,可是“他之所以将非洲作为自己的题材也许是因为他来到了非洲,因为他是个学者,习惯于研究报纸,并且发现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新报纸。”就是这样一位“对真正的非洲并无多少真正认识和感受的人”,却由于机缘的巧合成为政界要人,享受“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第181—182页)在某种意义上,雷蒙德的作用只不过是作为已被普遍接受的那些自由信条的传话筒,他的失败实际上验证了西方谎言的失败。(19)
《河湾》无疑具有隐喻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意义。作者没有指出河湾镇所在国家的名称,这就是说可以用其代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正处于要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境地。然而这是个法语国家的事实,以及大人物与蒙博托的诸多相似之处,又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扎伊尔联系起来。如果说现实层面的意义使得故事的叙述获得一定程度的真实感和历史感,那么在隐喻层面上,小说则以非洲作为一个场所,象征着世界范围内西方殖民秩序的崩溃及其所带来的后果。
贯穿《河湾》叙述始终的是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河湾镇就是这种交锋的战场。然而,本来就处于弱势的非洲传统在萨林姆的叙述中并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表述。故事中唯一对非洲古老传统感兴趣的人物是惠斯曼斯神父,在他眼里“非洲是个奇妙之地,充满新鲜事物。”(第61页)因为他“对非洲人的遭遇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河湾镇目前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别有一番意义。他认为“他的同胞们建设起来的欧式镇子的毁灭,只是一种暂时的退步。每逢重大事件或新生事物发生、历史进程出现变化,都会出现这样的事。”(第63页)惠斯曼斯神父还预见到“真正的非洲正奄奄一息或即将死亡”(第64页),“欧洲文明将会更稳地在河湾镇扎根。镇子总会从头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第85页)这无疑是对以现代性的最终胜利为标志的“宏大历史进程”的描述。可是,这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父却没能看到美好的未来,在一场叛乱恢复和平之后没几天,就被不知什么人给杀死了。
如果说所谓的“宏大历史进程”意味着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那么非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确终止了这一进程。《河湾》中有一段颇具象征意义的描述:
总是有一簇簇的水葫芦从南方漂流而来,它们绕过河湾,如同漂浮在黑色河面上的黑色岛屿,随着激流浮动。雨水和河流仿佛正在将丛林从大陆腹地扯走,让它顺流而下漂到远方的海洋。可是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它们那高高的淡紫色的花是在几年前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在当地语言中还没有描述它的词语。人们依然将其称作“新东西”或者“河里的新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又一种敌人。水葫芦富有弹性的藤蔓和叶子纠缠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黏附河岸,堵塞河道。它长得很快,人们用现有的工具都来不及消灭它。通往村里的河道必须不断地清理。水葫芦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播撒下种子。(第46页)
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河的意象可以看作是上述“宏大历史进程”的象征。从南方没日没夜漂流而来并在河湾疯狂生长的水葫芦显然喻指民族解放运动所带来的一切,它最大的害处就是阻断了非洲丛林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它们“用古老的丛林的方式禁锢河流两岸的人民”。(20) 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可以说小说中所谓的“宏大历史进程”乃是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是符合社会历史规律的对当代非洲现实的描述。它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对后殖民社会的普遍看法一脉相承。下面是从1973年出版的一部颇具影响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选取的片段,其中表达的思想与《河湾》中的悲观主义历史观几乎毫无二致:
实际上,后革命时期的新事物在许多方面加剧了民族主义。新兴国家与西方在实力上的不均衡不仅没有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溃而改善,而且这种不平衡在某些方面更严重了,同时殖民统治所提供的用来抵消实力不平衡造成直接影响的缓冲被除去后,只能听任没有任何经验的新兴国家自己去抵抗更强大的、更有经验的、已稳定的国家,使民族主义者对“外来干涉”的敏感更加强烈、更加普遍。(21)
从结构上看,《河湾》中描述的旅行从相反方向重复了早期奴隶的旅行。萨林姆从海岸迁徙到内陆谋生,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没有非洲血统的印度人生活在一种不完善的社会中,羡慕那些由大人物赋予特权的新殖民主义者。他前往英国,又重返非洲,最终又逃离非洲前往英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前殖民地居民却要在导致他漂泊无定过流亡生活的国家里寻求避难之所。这其中的反讽,就如同他与耶苇特的私通一样,暗示殖民化所带来的永远无法摆脱的后果。雷蒙德与耶苇特是殖民者的榜样,他们的存在取决于当地人为他们创造的虚假角色。虽然雷蒙德曾经被总统尊为导师,但很快就被忘却了,不光他的著作不能出版,就连其地位也受到动乱的威胁,他的知识最后也如同新领地一样是骗人的把戏。正如雷蒙德对非洲的学术断言迷惑了非洲人一样,耶苇特的性能力也征服了萨林姆,而后者对前者的痴迷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殖民依赖的征候。
作为一部充溢着悲观情绪的小说,《河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萨林姆的存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小说叙述一开始就得到清晰表述,它引导着读者体验萨林姆的悲观主义之旅,从一个轮回的毁灭走向另一个轮回的毁灭。政治秩序在他周围崩溃,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不断迁移。萨林姆所遭遇的所有人和事都表明,奈保尔试图通过其叙述表达如下观点:殖民主义的终结导致了后殖民地国家在历史上的倒退。虽然就像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后殖民社会的某些现实的确不幸被奈保尔所言中,(22) 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河湾》准确地再现了后殖民社会的历史。故事的整个叙述几乎从未正面地、直接地描写民族革命给非洲带来的巨大变化,相反,其关注的焦点是一群生活在非洲的外国人,写的是他们对后殖民境况下非洲的体验和感受。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萨林姆,就连其祖先的“历史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中了解到的”,他对非洲的理解必然也打上西方的烙印。当然,读者也可以将大河的意象看作是人类历史长河的象征,河湾镇所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只不过是暂时的,历史长河在绕过这个弯之后便会朝着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流淌,非洲人民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现代化之路。可是,奈保尔大概不会支持这样的解读,因为在他眼里非洲“毫无希望”可言。(23)
注释:
①爱德华·萨伊德:《智力灾难》,黄灿然译,载《天涯》2002年第1期,第148页。
②③V.S.Naipaul,Literary Occasions,intro.&.ed.by Pankaj Mishra,New York &.Toronto:Alfred A.Knopf,2003,p.182,p.181.
④V.S.Naipaul," The Novelist V.S.Naipaul Talks About His Work to Ronald Bryden," in The Listener 89( March 22,1973) ,p.368.
⑤John Thieme,The Web of Tradition:Uses of Allusion in V.S.Naipaul' s Fiction,London:Dangaroo Press and Hansib Publications,1987,p.179.
⑥Peggy Nightingale,Journey Through Darkness:The Writing of V.S.Naipaul,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7,p.201.
⑦Pankaj Mishra,"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Occasions,p.xiv.
⑧⑩V.S.Naipaul," Conrad' s Darkness," in V.S.Naipaul,New York: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p.211,p.216,p.219,p.207.
⑨V.S.Naipaul,"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38,No.3,January 31,1991.
(11)罗布·尼克森在《伦敦在呼唤:V·S·奈保尔,后殖民官僚文人》中说:《黑暗的心》对20世纪西方的非洲表征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超过任何一个文本。新闻记者、史学家、小说家、人类学家、电影制片人、广告雇员乃至游记作家都从中受益,就连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能明白作为黑暗之心的非洲形象所具有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黑暗的心》传统”。见Rob Nixon,Qxford: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0.
(12)1979年与人会面时,奈保尔曾宣称:“我不是为印度人写作的,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读书。我的著作只有在自由、文明的国度才有可能,在原始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参阅Elizabeth Hardwick," Meeting V.S.Naipaul,"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13,1979) ,p.1.)这一陈述实际上也适用于奈保尔有关非洲的书写。
(13)V.S.Naipaul,A Bend in the Riv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p.27.以下所引《河湾》文字皆出自该版本,只在引文处标明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14)(23)Elizabeth Hardwick," Meeting V.S.Naipaul,"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13,1979) ,p.1.
(15)(17)Pal Ahluwalia,Politics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frican Inflec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52,p.53.
(16)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eds.,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Cambridge:Wheatsheaf,1993,p.3.
(18)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78页。
(19)Fawzia Mustafa,V.S.Naipau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9.
(20)V.S.Naipaul," A New King for the Congo:Mobutu and the Nihilism of Africa" ,in 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New York:Alfred A.Knoof,1980,p.184.
(2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82页。
(22)赵毅衡在《谁能为奈保尔辩护?》一文中写道:“问题在于,现实沿着这本书走得更远:这本书出版的1979年,小说中写到的东非中非,就开始20年动荡:乌干达总统阿明驱赶印裔阿裔人,屠杀30万;然后是索马里内乱不止;此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死亡达107万,400万人流亡;1998年,这场大动乱终于波及刚果。蒙博托的统治,比奈保尔预料的要长,但是至少几十万人死于刚果的内乱,政变与暗杀,余波延续至今未息。”(见2002年8月22日《中国图书商报》)根据国际发展局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统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正在倒退”;“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公民们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前的生活反倒更好些”。Timothy F.Weiss,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p.192.
标签:奈保尔论文; 康拉德论文; 悲观主义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河湾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读书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非洲人论文; 大人物论文; 黑暗的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