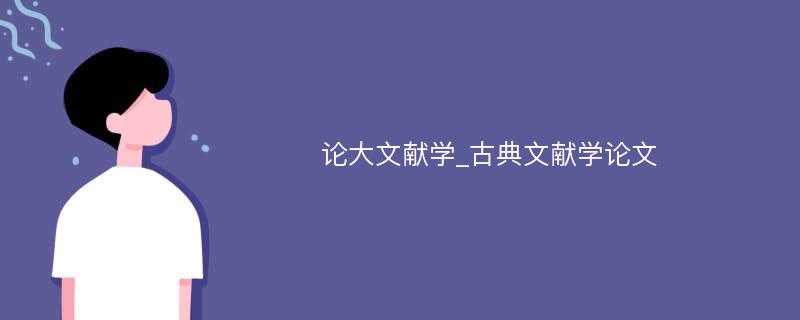
大文献学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学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610(2000)03—0014—03
读了于鸣镝先生的《试论大文献学》[1],如遇知音, 很感亲切。因为,有关“大文献学”,也是笔者多年来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记得1992年曾与倪波先生通信,讨论文献学在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定位问题。我7月去信感叹:“‘大文献学’仍找不到位置。”8月读了倪波回信后又去信说:“文献学处于支离破碎的局面,大文献观念尚未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这是遗憾的事。”1997年,小河同志来采访,又谈起此事,我说:“当今的学术趋势是贯通,是融汇……应该树立起‘大文献’的观念。”[2]1999年春,我与黄镇伟、 涂小马两同志合作编著《文献学纲要》,大家商定按大文献学的思路去写,切磋琢磨,略有心得。如今读了于文,获益良多。于先生诚恳地说:“切望同行们积极参与讨论,赞同也好,反对也好,都有益处。”我自然属于“赞同”的行列,于是撰就此文。拙文对于先生的论文,或补充,或引申,或从不同角度作些修正与发挥,散漫而无系统,故自题为“散论”。
1 为什么要提出“大文献学”这一概念
于先生的论文(以下简称“于文”)两处指出,所以提出“大文献学”,是为了“与传统的‘文献学’相区别。”这使我立即想起袁翰青先生
1964 年发表的《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提到: “有人把documentation也译成‘文献学’。文献学诚然是我国固有的用词, 讨论的内容却着重于考证典籍源流,和现代文献工作的涵义是不同的。至于现代文献工作是范围相当广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为了比较切合实际起见,本文还是用文献工作这一名词。”[3]也就是说, 袁先生之所以提出“现代文献工作”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文献学(即古典文献学)。袁先生所说的“现代文献工作”,其实就是现在常说的“现代文献学”,只不过他当时认为“现代文献学”尚未独立,所以用“现代文献工作”表述之。
当今情况已有所不同,已出版了不少现代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如胡昌平、邱均平的《科技文献学》(1991年版),陈界、张玉刚主编的《新编文献学》(1999年版)等。如今人们见到“文献学”三字,不仅可能理解为古典文献学,也可能理解为现代文献学。笔者以为,“大文献学”的提出,不仅是区别于古典文献学,也区别于现代文献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支学术队伍划疆而治的局面,建立兼容古今的完整的文献体系,促进学科的健全和发展。
2 “大文献学”是近十余年文献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记得1989年春,华东师大罗友松先生寄来他的研究生林申清的硕士学位论文《文献与文献学探要》,邀我参加答辩。我因杂务缠身未能成行,但这篇论文我是认真的阅读了,很受启发。该文详细分析了文献与文献学概念的古今演变和中外异同,并提出:“建立一门能够兼容古今的系统的文献学仍是必要的,其中很多部分是情报学无法替代的。”他所说的“兼容古今的系统的文献学”,实际就是大文献学。倪波主编的《文献学概论》(1990年版)虽以现代文献学为主干,但兼容古今,贯穿着大文献学的观念。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列为一级学科,“文献学”列为二级学科,下属的三级学科是:文献类型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检索学、图书史、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其他学科。虽然这一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已体现出古今兼容的大文献学思路。因此,目前讨论大文献学是有坚实的基础的,也可以说是前阶段探索的深化。
3 我对大文献学的理解
笔者以为,所谓大文献学,有纵、横两方面的意义。纵向看,古今兼容,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机结合;横向看,整体把握,拓展文献学的学术空间。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各自的特点:古典文献学以历代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目录、版本、校雠为三大支柱,以文史哲为主要学科领域。现代文献学以日新月异的多语种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信息技术尤其计算机网络为依托,活动领域遍及各学科,尤其重视科技文献。但两者在许多方面又有共通之处: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知识与信息的载体。其次,它们都研究文献的生产、搜集、整理、传播、利用,有共同的规律可寻。第三,它们的根本任务,都是实现知识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第四,在实际工作中,两支学术队伍也经常优势互补。这些共通之处,是促使它们有机结合的基础和前提。
4 关于文献与编辑出版
关注编辑出版,是文献学拓展学术空间的实例之一。于文将编辑学、出版学纳入大文献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十分赞同,并想谈谈自己的实践体会。
我主要从事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从1986年开始,兼教编辑学课程,并编印了教材《编辑工艺:文献的加工与传播》。1987年,我在《上海出版工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文献学与编辑学本来就是交叉渗透的。以文献学的观点看,编辑出版这门学问,就是研究文献的加工与传播的学问。我过去主要教学生如何查找、利用文献,对文献的生产、加工、传播没有深入研究。因此,我要认真学习编辑出版的理论与方法,边学边教……充实自己文献学的研究内容。”[4]后来, 我在《编辑学·前言》中又说:“编辑学与文献学是近缘学科。用文献学的眼光观察编辑活动,有助于理解的深化。”[5 ]但我强调的是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主张文献学研究者应拓宽学术视野,却无意于把编辑学、出版学列为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这一点,与于文的思路稍有不同。笔者认为,人类的编辑出版活动,出版家要研究,文献学家也要研究,这体现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但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所不同。不能因为文献学家要研究编辑出版活动,就把编辑学、出版学“收编”为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好比音乐家要研究音色、音量、音质,物理学家也要研究音色、音量、音质,但物理学并不因此而将音乐学列为自己的分支学科,只是将“声学”列为分支学科。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出版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自有其合理之处,此处不赘述。
5 以大文献学的思路编著文献学教材的尝试
笔者与黄、涂两同志于今年元月定稿的《文献学纲要》,是按大文献学的思路写的。全书分8章:(1)文献与文献学;(2 )文献的形态;(3)文献的分类;(4)文献的整序与揭示;(5)文献的检索; (6)文献的鉴别与整理;(7)文献的典藏与传播;(8 )计算机与文献的生产和检索。各章力求贯通古今,例如,讲文献学的定义,从古典文献学讲到现代文献学,再讲到大文献学;又如,讲文献载体与文献类型,从甲骨载体、青铜载体、纸质载体讲到磁性载体、光学载体,从图书、报刊讲到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会议文献等等;讲文献典藏,从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讲到现代档案馆、文献情报中心;讲文献检索,从传统的手工检索讲到当前的光盘检索、网络检索。《纲要》能否得到文献学界的认可,尚有待实践的检验。
6 加一“大”字是为了最终删去“大”字
长期以来,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处于分离状态,这与语言学、医学等学科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你是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还是研究普通语言学,都受上位类目“语言学”统辖;不管你研究中医、蒙医、藏医还是西医,都受上位类目“医学”统辖。文献学则不然,古典文献学属“文学”门类,培养的研究生称“文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代文献学大体归“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统辖,而“图书馆学与情报学”80年代属“理学”,90年代属“管理学”(其中“图书馆学”变化更多,60年代至80年代属“文学”,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属“理学”,90年代后期属“管理学”)。这种状况,反映了文献学学科结构的松散和人们对其学科属性的认识飘忽不定。今天在“文献学”前加一“大”字,正是为了构建完整意义的文献学,促进学科的健全和发展。我想,当完整、系统的文献学真正建立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当“文献学”不再被狭义的理解为“古典文献学”或“现代文献学”之后,“大”字便可取消了。这好比“医学”、“语言学”不必冠以“大”字一样。我们正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