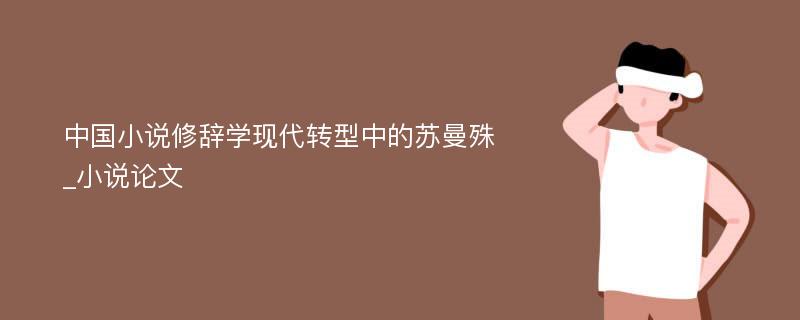
中国小说修辞现代转型中的苏曼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苏曼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话”艺术影响深远,特别是宋元话本中形成的“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①,深深吸引着后世小说家。到了清末民初,在翻译小说影响下,小说家们纷纷突破章回体小说的文本构成方式,摆脱“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变化和突破往往从局部开始,如《绘芳录》、《海上花列传》、《新中国未来记》和《官场现形记》,虽有回目,但已经删去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套语和“下场诗”。1905年,无名氏著的《苦社会》和碧荷馆主人著《黄金世界》不仅程式已经消失,甚至连说话人的存在标志,如“话说”、“且说”等也都不见了。这说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受众审美习惯的变化,章回体小说的一些固定套式已使作家感到累赘,并逐渐被抛弃。”②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捅破章回体这层“窗户纸”的是从事翻译的小说作家。苏曼殊的长篇《断鸿零雁记》和林纾的长篇《剑腥录》均已取消回目直接分章,章回体的“套语”也被完全放弃。一般认为中国“章回小说”体裁形式是由林纾打破的,但从相关材料看,《断鸿零雁记》要早于《剑腥录》。
一 现代小说修辞交流方式的探索者
苏氏小说文本的外部构成,已经完全不同于章回体小说。《断鸿零雁记》近四万字,不仅回目全无,甚至连章回体小说从话本那里继承来的“套语”也完全消失了。《天涯红泪记》未完,只有两章,体式与《断鸿零雁记》相同。其他几篇为短篇,除叙述语言为浅近文言外,其他各方面非常接近现代短篇小说。但应当看到,这种表面形式的最后退场,意味着中国小说的修辞能指已经摆脱了原有修辞能指的存在方式,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形式。苏曼殊在这方面的首创之功不能被埋没。如果这最后的“一层皮”不被扒去,自宋元以来就已形成的“说话人虚拟修辞情境”,仍将如影随形,不断纠缠、干扰甚至阻碍中国现代小说修辞方式的变革。
苏曼殊在他的小说中,寻找着与读者之间新的交流方式。如果我们将小说修辞理解为“同读者进行交流的艺术,也就是史诗或小说的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读者引入他的虚构世界时使用的修辞手段”③ 的话,那么,苏曼殊显然属于在这个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却又为后人所诟病的先行者。
传统章回体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看官”、“且说”等套语模拟“说话”情境来维持。这样的交流是直接的、外在于“故事”的,其交流奠基于平民的日常伦理。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中却设计了一个无名的“读者”,使其与叙述者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叙述者不断提请读者“思之”、“试思”,让读者体验叙述者的无奈和苦衷。这样的修辞交流方式不仅具有典型的过渡性,而且富有独特性,让我们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苏氏的“读者”总是让人联想到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的“看官”,虽然不能说这里的“读者”脱胎于“看官”,但从作者的叙事习惯看,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某种血缘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在小说文本中的存在形式相同。无论是传统的“看官”,还是苏曼殊的“读者”,都需要叙事者跳出“故事”叙述之外,与读者就“故事”的某一情节或场景进行议论或交流;二是交流都渗透着作者的修辞策略——通过情感交流,对读者实施有效的情感控制。就小说叙述本身而言,这样的修辞交流往往会打断故事情节发展的流畅,而情节的完整流畅对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小说中,为了情节的流畅,作者可以牺牲场景的描写,减少人物对话,放弃大段的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描述,或将心理转化为可见的动作和表情,而唯独不能放弃的是“说话人”所持的具有公共权威的伦理立场和道德观念,并且为此不惜打断叙述的时间流程。在阻断叙述的流畅和完整这一点上,苏曼殊的“读者”与传统的“看官”并无二致。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这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看官”、“诸位”与苏氏的“读者”所诉诸的修辞情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看官”、“诸位”等话语符号中,始终残存着“说话人”虚拟的“说/听”交流模式的因素。在这种模式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中,叙述者始终是主导性的、支配性的,小说的“读者”则完全失去了能动性,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存在于小说交流中。《断鸿零雁记》所诉诸的更多是“写/读”的交流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摆脱了模拟“说话人虚拟修辞”所依赖的“在场”效果,小说的修辞空间不但得到了有效拓展,修辞交流本身也充满了弹性。
其次,二者之间的修辞姿态不同。前面已经说过,“说/听”模式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修辞交流的效果。这一模式决定了叙述者的修辞姿态,只能以“独语”的形式存在;而在《断鸿零雁记》中,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则趋于平等,从而使修辞交流本身获得了“对话”的基础。这时的“读者”已经不同于“看官”、“诸位”——一种被动的、被抽空的语言符号,而是能够有所思,有所想,能够对叙述者的境遇、情感给予理解和同情的“叙述者的读者”,它不是出于一般的“读者”,而是作者心目中进行情感交流的对象。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二者之间修辞交流的内容已经有了本质不同。在话本小说或章回小说的修辞交流中,“说话人”往往以其超越的修辞姿态,充当平民日常伦理的代言人,公共道德的护卫者,从而形成不容置疑的修辞威势。叙述者以“公理”为依托,在“说话”这一敞开的虚拟空间中,谈论和评价故事中的事件、人物。而在《断鸿零雁记》中,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则在一个较为封闭的阅读空间里,进行私人情感的交流。无论是叙述者自叹年幼的孤苦无助,将赴玉人之约时的彷徨无助,以及由身世的“难言之恫”所带来的内心矛盾和“惨戚”之情,还是生而多艰,人生哀苦的慨叹,都是在与“读者”、“读吾书者”之间进行的个体情感的沟通,在向另外一个人,倾诉自己的“弥天幽恨”。
二 现代性体验与诗性修辞
鲁迅谈到苏译拜伦诗歌时曾说过:“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的并不广。”④ 不难看出,鲁迅对苏曼殊凄艳哀婉的情诗有些微词,但不容否认,在当时和五四时期真正产生影响的,恰恰是前者。苏曼殊的诗充满古典气息,意象清新优美,清越拔俗,在一个“古典”完结的时代,在诗词中创辟出了感伤、凄绝的审美境界;加之受拜伦、雪莱的影响,诗中所抒之情,缠绵悱恻,哀伤忧郁,真挚感人。特别是他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特殊身份,以及内心深处情与欲的矛盾状态,使他的诗在情感表达上升华出凄幽哀婉的悲剧之美。这样,苏曼殊诗中所表达的孤独无助、感怀忧伤,不期然的切合了五四落潮后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孤独彷徨、无所依归的心灵状态。可以说,这种心理和情感状态,并不是属于苏曼殊个人的,它是那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苏曼殊敏感的天性,较早地触及了这样一种现代感伤,并通过他的诗和小说,传达给后来者。
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有研究者将当时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归结为四种类型:一是以王韬《韜园文录外编》、《漫游随录》为代表的“惊羡体验”;二是以黄遵宪诗为代表的“感愤体验”;三是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的“回瞥体验”;四是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的“断鸿体验”,此种体验“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代和未来的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的融汇形态。”⑤ 这无疑肯定了苏曼殊的“断鸿体验”在当时的典型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苏曼殊的“断鸿体验”成为了“现代性体验”在文学中的重要表征。这种现代性体验对苏氏小说的修辞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苏曼殊的小说中,人生体验并不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以诗歌的形式表达,或者像《老残游记》那样,只是在某一特殊场景之下,将古典诗情熔铸到小说叙事之中。苏曼殊更多是以做诗的方式在“做”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郁达夫批评他的小说“做作”、不够写实的直接原因。如果说在以前的小说中,诗词的存在有时不免流于点缀,或者作者想通过诗歌这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贵族”,来显示自己的才情,那么,在苏曼殊的小说中,作者以情统文,挥之不去的诗性体验弥贯全篇,这就对苏曼殊小说文本的内部构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以往的小说中,叙述动力往往来源于故事中“事件”本身的发展进程,叙述者通过调动“讲述”和“展示”手法,将故事呈现在文本之中。但是在苏曼殊的小说中,小说的叙述动力更多地是来源于叙述者的情感变化,正是在叙述者的情感变化和体验中,在叙事者的内心活动中,故事获得了更为内在的驱动。
苏曼殊的诗性修辞在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对苏氏小说文本内部构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诗性修辞体现在对自然环境和故事背景的诗性描写中。苏曼殊的小说都由浅近文言写成,这为作者在小说中运用古典诗词手法描写景物,提供了方便,使得“诗”与小说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同时,这也决定了苏氏小说的景物描写简短精切,有画龙点睛之妙。如:“百越有金瓯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无云,山麓葱翠间,红瓦鳞鳞,隐约可辨,盖海云古刹在焉。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故至今日,遥望山岭,云气葱郁;或时闻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凭吊,不堪回首。今吾述刹中宝盖金幢,俱为古物。池流清净,松柏蔚然。住僧数十,威仪齐肃,器钵无声。岁岁经冬传戒,顾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肠峻险,登之殊艰故也。”这些充满古典气息的词句,混迹于一般的叙述语言,给人“如盐入水”之感。这样,在文本的内部构成上,“展示”性描写所占空间有限,“讲述”与“展示”之间充满和谐之美。如果不考虑语体因素,苏曼殊小说中时空关系的处理,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让读者领略到了诗性修辞的独特韵致。
其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词是主导。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文本中都存在大量诗词。这无疑对五四时期大量“抒情小说”出现产生了直接影响。正如王瑶先生所言:“鲁迅小说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鲁迅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抒情体小说的作者,如郁达夫、废名、艾芜、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艺术上也各有特点,但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这个方面,又显示出了共同特色。”⑥ 王瑶先生非常准确地把捉到了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给现代小说带来的影响——使现代小说获得民族特色,这也就是前面我们所强调的,小说修辞与叙述中的情感驱动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古典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联系肯定不是单向度的。王瑶先生强调了鲁迅在这一联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如果从小说所反映的精神气质看,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倪贻德、陶晶孙等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精神气质相近的“族群”,他们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抒情传统的联系中介,显然是苏曼殊,而不是鲁迅。
三 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与现代作家的中介
1924年,王以仁24岁,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发表了小说《神游病者》。小说写了一个青年,孤身在上海教书,生活穷困潦倒,性格孤僻内向,带有明显自闭倾向。这样的生活境遇和性格特点,使他既自恋又自卑。他渴望得到女性的眷顾,但又在自卑和自恋中禁锢自己,饱受精神与肉体的煎熬。他暗恋对面统楼上对镜梳妆的女子,但是没有表达的勇气,一天那女子穿了和他一样的白灰衣服,他就自认为她是故意引诱他,表示“她已经爱了他了”。没有女性的爱,身体得不到满足,“他”只能以苏曼殊的《燕子龛残稿》来慰籍自己的精神。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曼殊的《燕子龛残稿》,它在小说中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事件中存在的一个物品,而是应当被视为那一时代精神苦闷,内心痛苦却又充满浪漫想象的青年人情感和精神符号与标志。《燕子龛诗稿》虽可以慰籍他的精神和灵魂,但不能改变他的穷苦的生活境遇,最终他只能在一种精神的迷幻中,在对生命诗性的召唤中死去。黄仲则、苏曼殊、郁达夫、王以仁,他们仿佛是精神上的“连体婴儿”,以诗性承受生命的痛苦,用诗性来表达对生命的体验。甚至他们的精神痛苦升华为文学意象,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苏曼殊的“断鸿零雁”,郁达夫的“零余者”,王以仁的“孤雁”。不同的是,苏曼殊脱掉“西装”尚有“袈裟”,能够在荒山野寺中找到自己精神的避难所;郁达夫可以“颓废”的方式来减缓和消解自己的精神之痛;而王以仁却真的跟随他的主人公,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平原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与五四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认为:“引‘诗骚’入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由来已久。这种倾向五四以前主要表现在说书人的穿插诗词、骚人墨客的题壁或才子佳人的赠答;而五四作家则把诗词化在故事的自然叙述中,通过小说的整体氛围而不是孤立的引证诗词来体现其抒情特色。”⑦ 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小说文本转换的历史进程。但是有两点必须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在五四小说的抒情特征与“说书人的穿插诗词、骚人墨客的题壁或才子佳人的赠答”之间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小说文本外部构成中的有形的诗词,并非一蹴而就地转化为小说的抒情特色,中间经由刘鹗、林纾、苏曼殊等人长时间的过渡,直到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王以仁等都在这条转化的轨迹上,以不同的形式,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就整体形式而言,古典诗词在小说中的转化,有一个由整首诗经到个别诗句再到个别诗词意象最终消弭于无形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以上诸人的小说中都有明确的痕迹可循。这一进程与中国古典诗词境界不断被“现代性”语境销蚀的进程相一致。中国近、现代小说家,已经无力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对中国传统诗词所表现的美学境界进行整体继承,他们只能从某些诗人的个别诗句中,以近乎“断章取义”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意象,来体验和抚慰文化转型期自己敏感的灵魂和精神所承受的“断裂”之痛。王以仁小说中“他”把袋中的《燕子龛残稿》取出,一页一页的撕下来丢在水面,这一“动作”可以理解为五四小说家们的一个整体性的“姿态”,如果我们以“一页一页的撕下”的方式,来比附现代小说文本转换的过程,肯定没有道理,但却出奇的形象。
其次,还要注意近、现代通俗小说这条线索。文学的发展不可能是单向的,其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如此。表现在小说文本构成的现代转型上,“鸳蝴派”小说走着一条相反的路。他们拒绝古典诗词由外向内的文本转化,并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大量读者。苏曼殊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鼻祖,但在这一点上,后来的“鸳蝴派”言情小说的作者,如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不像苏曼殊,他们更多继承了《花月痕》的传统,他们不练“内功”,只练“外功”,一首两首已经不过瘾,动辄十首八首,一篇小说成了香词艳句的“大串烧”,一旦古典诗词的审美精神和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之中消散,他们作品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所以,周作人在评价苏曼殊小说时说出了这样的话:“曼殊在这派(“鸳鸯蝴蝶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孔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⑧ 虽然周作人对苏曼殊小说的本色是什么语焉不详,但在苏曼殊小说的文本构成中,古典诗词精神的内化及其诗性修辞策略的运用,肯定是其小说“本色”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0页。
② 郭延礼:《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包头:《阴山学刊》,1999年第4期,第25页。
③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④ 鲁迅:《杂忆》,北京:《莽原》,1925年第9期,第25页。
⑤ 王一川:《晚清与文学现代性》,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5页。
⑥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5期,第25页。
⑦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⑧ 周作人:《答芸深先生》,《苏曼殊全集》(卷五),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