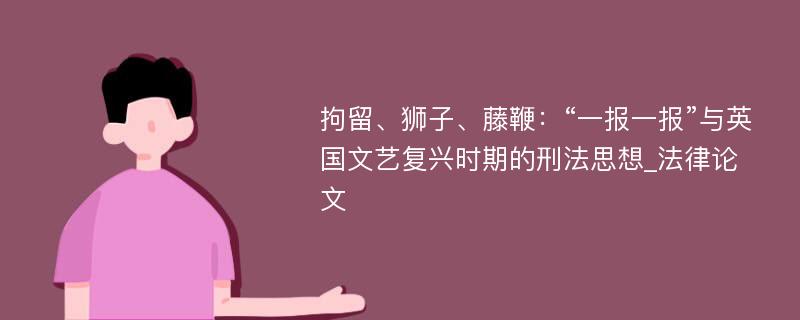
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刑法论文,狮子论文,思想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法治国”是贯穿《一报还一报》全剧的一条主线,如德博拉·舒格(Debora Kulla Shuger)指出,该剧一开场就通过公爵之口表达出作品的主题关乎“政治方面的种种机宜”(1.1.3)。①《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唯一一部以圣经典故为题的作品,“一报还一报”表达的正是基督教上帝惩恶扬善的刑罚思想,象征《旧约》中的律法精神。②早在1307年以前,英国国王在加冕仪式上都必须宣誓遵守“公义与仁慈(的精神)……仁慈地对待他人,以换取仁慈上帝的垂怜”。③此后一直到17世纪,加冕誓言虽然在措辞上稍有变动,却无不强调君王要恪守“法律与正义”,心怀“仁慈”地治理国家。《一报还一报》还特别于1604年12月26日上演,恰逢詹姆士一世登基一周年的第一个圣诞节后。演出地点则是新国王的豪华宫殿,怀特霍尔宫。④从演出时间、地点以及观众来看,《一报还一报》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仪式庆典特征以及政治和宗教的象征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报还一报》的“法”与“治”在剧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维也纳刑法的三种职能
古今中外,为政之道的恩威并施本无可厚非。孔子很早就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以上这段有关为政之道的议论出自《左传》中的《子产论政宽猛》,讲述的是郑国大叔接替子产为执政大夫的故事。郑国这位大夫上任后犯了与《一报还一报》中维也纳公爵同样的错误,为政“不忍猛而宽”,直接导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公爵启用安哲鲁不久就向托马斯神父讲述了他“隐退”的另一真实动机:“我们这儿有的是严峻的法律,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这是少不了的羁勒,可是在这十四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它的爪牙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倘使把藤鞭束置不用,仅仅让它作为吓人的东西,到后来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不会再对它生畏。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从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正像婴孩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纪完全荡然扫地了。”(1.3.19-31)不难看出,公爵选择安哲鲁不仅是为了执政,更是为了执法,是公爵“看中”了他的“一丝不苟”(1.3.50)⑤。不出公爵所料,安哲鲁上任后即大张旗鼓地扫除妓院、暗娼等以整顿法纪。颇有意思的是,郑大夫“宽以济猛”的方略得到了孔子“善哉”的评语,安哲鲁的严格执法却招致20世纪以来众多读者、批评家的非议。
上面一段引文中,公爵使用的三个意象对我们理解维也纳的法律具有启发意义:野马的羁勒、狮子和父亲的藤鞭。从《一报还一报》对法律的表现来看,莎士比亚通过对维也纳法律的描写,大体强调了法律应具有的威慑、惩罚、教化三种主要职能,上述三个意象与该剧宣扬的法律的三种功能大体吻合。如公爵在私下的密谈中向神父坦白的那样,由于多年执法不严,维也纳的法律已经形同虚设。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安哲鲁重申法律的威慑和惩罚功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安哲鲁一上任就恢复了“沉睡”了14年的法律,纠正了公爵执法过于仁慈的弊病,并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公爵对于仁慈的理解。在安哲鲁看来,法官的怜悯之心来自对犯罪者所犯过错的感同身受,暴露了法官本人内心的隐藏之罪;执法者对犯罪者表现出同情,往往会导致包庇罪恶的后果。因此,严格执法就是最大的仁慈:“我在秉公执法的时候,就在大发慈悲。因为我怜悯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人,惩罚了一个人的过失,可以叫他们不敢以身试法。”(2.2.102-6)
在这一点上,安哲鲁的法律主张与中国历史上法家的观点颇为相似:“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⑥而且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安哲鲁这位伪善的代理公爵的法制理念与西方现代刑法思想也不谋而合。现代刑法学的奠基者切萨雷·贝卡里亚便认为:“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而不是执法者的美德;它应该闪耀在法典中,而不是表现在单个的审判中。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惩罚的幻想。”⑦诚然,法律一旦执行不严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法庭也会成为笑柄。因此单从执法精神上看,安哲鲁主张法律应该超然于法官的主观情绪之上,似乎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即使在全剧接近剧终时安哲鲁的伪善道德被公爵揭穿,他仍坚持说:“求殿下立刻把我宣判死刑,那就是莫大的恩典了。”(5.1.365-6)相比之下,公爵倾向于“人治”。他在著名独白中强调,“代上天行惩”的执法者“先应玉洁冰清;持躬唯谨唯慎,孜孜以德自绳”(3.1.481),公爵宣扬执法者本人的道德水平,强调执法者权力来自于上天,他的思想更像是“人治”的体现。
剧中公爵最后的大审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使《一报还一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问题剧”。“司法审判”一场戏(trial scene)最大的问题在于,公爵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集权体现,在一场早已存在预设结果的审判中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在执法中表现的仁慈已经对维也纳法律体系本身构成了威胁和破坏。也正因如此,公爵的“仁慈”行为引起了许多评论者的非议:“维也纳城在公爵复位之后确乎与他隐退之前有所不同了。公爵搞臭了安哲鲁,得到了依莎贝拉,还使臣民们有所畏惧以使他们认真对待他的法律。但公爵做这一切的同时并未改善法律的执行效力。从这方面看,维也纳城在公爵复位之后与他隐退之前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⑧从现代刑法学的角度看,为了达到刑罚的最佳效果,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运用中必须遵循罪刑相适应、刑罚及时性、刑罚必然性等几项基本原则。公爵在刑罚实施中对及时性和必然性原则的破坏以及他的过度仁慈导致了维也纳法律完全失去了预防犯罪的功能。剧作开篇公爵在隐退时就指出自己过度的仁慈使得维也纳法律失效,而公爵在复位后的大审中似乎再一次暴露了他在执法中的弊病。早先,“因为我对于人民的放纵,原是我自己的过失;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1.3.35-9)。而在公爵复位后维也纳的法律体系以及执法原则依然没有本质变化。
除了威慑和惩罚功能以外,《一报还一报》还触及了法律的教化功能。安哲鲁强调法律的威慑和惩罚功能的同时,大臣爱斯卡勒斯不无忧虑地适时提醒这位代理公爵:“可是我们的刀锋虽然要锐利,操刀的时候却不可大意,略伤皮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置人于死命?”(2.1.5-6)⑨法律除了“惩罚”之外,还肩负“纠正”、“教导”的使命。事实上,惩罚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正义、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因此所有法律刑罚的终极理想都是深化一套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进而达到“教化”的目的。然而新上任的安哲鲁偏偏具有清教徒般的严峻与激情,他在追求抽象正义的同时完全背离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援引西塞罗《法律论》以说明“人民的幸福即是最高的法律”。虽然培根并没有强调犯罪者的幸福也是执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但他的确强调执法者“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⑩。而安哲鲁对克劳狄奥的审判过于严厉,其直接恶果就是破坏了刑罚中“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捉襟见肘的刑法体系
现代刑法学告诉我们,残酷的刑罚会造成违背预防犯罪宗旨的有害结果,严酷的法律还会削弱人道精神,促成犯罪。剧中,安哲鲁对克劳狄奥的审判不但没有起到匡扶正义、转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反而将问题的焦点转向了维也纳的法律体系本身,引发人们对法律是否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怀疑:“上天饶恕他,也饶恕我们众人!也有犯罪的人飞黄腾达,也有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也许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2.1.37-40)当事人克劳狄奥对安哲鲁的判决也并非没有异议。克劳狄奥在忏悔过错的同时并没有真正信服法律的公正。相反,他认为安哲鲁严格执法只是为了“博取名誉”而实行的“虐政”,或者是“不熟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掌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1.2.135-9)。由于刑罚相适性的原则受到破坏,执法者和法律体系都受到怀疑。即使按照安哲鲁的逻辑,判处克劳狄奥死刑具有杀一儆百的社会功能,但在剧中绝大多数人的眼中,克劳狄奥罪不至死,安哲鲁将他示众,反而激起更多人们的同情,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严刑审判使得维也纳臣民必须直面一个灰暗的现实,即法律不完全等同于正义,法网恢恢,并非疏而不漏。当安哲鲁处决克劳狄奥的判决传达至狱吏处,后者似乎对这一处决难以置信。与新上任的安哲鲁相比,狱吏具有多年的司法经验。如果说安哲鲁象征了维也纳法律的上层结构,那么狱吏则是该法律体系的下层代表。尽管安哲鲁也坦承,法律并不能保证将所有违法者缉拿归案,但这种可能性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纸上谈兵式的理论假设。相反,狱吏则亲眼目睹过“法官在处决人犯以后,重新追悔他宣判的失当”。(2.2.10-12)
剧中所有的法令都出自安哲鲁一人之口,公爵在临行前赋予了他生杀予夺的大权:“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1.1.44-5)监狱长由此认识到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往往导致法律的滥用。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剧中从没有人对安哲鲁判决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让克劳狄奥、路西奥等人感到震惊的似乎是,安哲鲁竟然对沉睡了多年的法律当起真来。公爵本人也曾经坦然承认,维也纳的法律非常严峻以至于他不忍实施。爱斯卡勒斯多次对克劳狄奥表示过同情,也试图劝说安哲鲁将他从轻发落。但他同时也认为,克劳狄奥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那也是不得不然。慈悲不是姑息,过恶不可纵容。”(2.1.252-4)爱斯卡勒斯的话暗示,安哲鲁的审判虽然严酷,但却合乎维也纳的法律,安哲鲁只是维也纳法律的执行者,处罚克劳狄奥的法律并不是他制定的。安哲鲁对依莎贝拉说:“法律判你兄弟的罪,并不是我。”依莎贝拉只是说安哲鲁的审判“太快了!饶了他吧!饶了他吧!他还没有准备去死呢。”(2.2.85-6)其实依莎贝拉也认为她弟弟克劳狄奥罪不可赦,但她仍然希望安哲鲁能对他施以恩慈:“有着巨人一样的膂力是一件好事,可是把它像一个巨人一样使用出来,却是残暴的行为。”(2.2.110-1)依莎贝拉的求情从侧面说明安哲鲁的判决虽然有违人道的精神,但却合乎法律。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所有人物或多或少都评论过维也纳的法律,但奇怪的是,该剧自始至终都没有具体说明维也纳法律(尤其是安哲鲁处罚克劳狄奥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公爵、安哲鲁,还是依莎贝拉、克劳狄奥等都从未质疑过维也纳法律本身的神圣地位,剧中人物即使心中颇有怨气,也只是针对执法者而已。或者说,他们质疑的是安哲鲁的执法尺度,而不是法律体系本身。有意思的是,剧中只有拉皮条的庞贝对维也纳的残酷法律嗤之以鼻。
爱斯卡勒斯:你要吃饭,就去当乌龟吗?庞贝,你说你这门生意是不是合法的?
庞贝:只要官府允许我们,它就是合法的。……您要是把犯风流罪的一起杀头、绞死,不消十年工夫,您就要无头可杀了。(2.1.200-17)
庞贝的回答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意味深长:维也纳法律的制定者是人,而不是神;法律只是当权者意志的体现。爱斯卡勒斯对庞贝苦口婆心地一番劝诫以后就赦免了他,庞贝则一边谢恩,一边回头向观众说着悄悄话:“可是我听不听你的话,还要看我自己高兴呢,用鞭子抽我!哼!好汉不是拖车马,不怕鞭子不怕打,我还是做我的王八羔子去。”(2.1.225-7)庞贝代表的司法现实与安哲鲁的法律理想似乎相去太远。法律理想何以如此难以实现,庞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法律面对的是人,而庞贝和巴那丁等各色人物很难只用法律进行彻底改造。早在《一报还一报》上演六年前,詹姆士一世就完成了他的政治神学著作《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1598),书中他对加尔文主义者反君主制的观点以及罗马天主教主张教皇至上的观点都进行了驳斥。詹姆士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如圣经和基督教传统揭示的神学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上帝借以维持宇宙自然秩序,世间的法律则应该是君王意志的体现;基督教君王作为上帝的世俗代表,他的权力来自于上帝。(11)詹姆士一世“君权神授”的思想与柏拉图的法律思想非常相似。除了国家统治者必须由哲学家担当,柏拉图政治理论的另一个关键思想就是,他赋予国家立法者以神性地位,“全面控制人类事务的是神”,法律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它应当是神圣的、普遍的、不变的。而庞贝则在寥寥数语间就表达了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法律意识。
三、人法,神法?
公爵除了维护维也纳的法律秩序之外,同时具有教化臣民并确保其灵魂得救的使命。现代读者大可以批评最后一场戏中公爵的“人治”模式,其中自然包含人们对这种权力模式容易导致的权力滥用、贪污舞弊、甚至集权主义等后果的深深忧虑。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一报还一报》中的大团圆结局也许并不会引起观众的太多恐慌。从第三幕戏以后,公爵忙碌于剧中各上场演员之间,俨然成为整部戏的总导演。在最后“司法审判”一场戏中,公爵甚至向依莎贝拉详细交待她上场的具体位置、“台词”、表情等等。依莎贝拉也向玛利安娜转达公爵对后者的“舞台指令”,教导她如何上演一场“御前认夫”的好戏。作为幕后导演,公爵既要瞒天过海地安排克劳狄奥的替身受死,还要给伪善的安哲鲁埋下陷阱,聆听克劳狄奥、玛利安娜的忏悔、考验试探依莎贝拉等等,剧中所有角色无一不在公爵的监控之下。
该剧结尾时,公爵貌似粗暴地安排了克劳狄奥与朱丽叶、安哲鲁与玛利安娜、路西奥与妓女三场婚姻,但是自己对依莎贝拉的求婚并没有得到回应。公爵对安哲鲁以及杀人犯的赦免也有违背正义原则之嫌。他穿梭于所有当事人当中,并坚持所有人都要认“罪”,包括克劳狄奥、朱丽叶、安哲鲁等。可见他被赋予了近乎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圣经《约翰福音》中说神爱世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独子,但就基督教徒而言,信众得到赦免固然是“白白得来”,然而这是建立于耶稣作为“中保”的救赎之功;对于维也纳形形色色的“罪人”(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意义上),他们得到赦免却并非耶稣做了“赎罪祭”,而是公爵教化的结果。公爵身兼“修士”和行政首领的双重身份,在剧中既是匡扶正义的执法者,又是关注臣民灵魂的精神导师。以道德教化而论,《一报还一报》与圣经《马太福音》(7:1-3)和《路加福音》(6:37-42)的主旨颇为接近。耶稣告诫门徒“不可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新约》中的“爱邻如己”可谓执法者的最大诫命。不幸的是,莎士比亚在试图表现公爵的宽容、博爱等基督教君王美德的同时,却使他落下了“执法不严”、“践踏法律”的口实。这里问题的症结是,他在对“法”的处理上将世俗法律和宗教律法混为一谈。该剧的本义应为宣扬基督教中的“仁慈”和“宽容”主题(这从剧本的题目本身也不难看出),但在表现宗教道德意义上的“罪”时,常常与刑事(世俗)法律的“罪”混淆在一起。《一报还一报》的剧情由整顿维也纳的“人法”展开,讲述的却是有关灵魂道德的“神法”。
年轻的未婚夫妇克劳狄奥与朱丽叶两情相悦,只是因为“还有一注嫁奁在她亲友的保管之中”(1.2.126),两人才未向外界正式公布他们的秘密婚约。(12)然而事与愿违,克劳狄奥和朱丽叶“秘密地交欢,却在朱丽叶身上留下了无法遮掩的痕迹”(1.2.131-2)。在第1幕第2场,克劳狄奥被游街示众。路西奥向克劳狄奥询问他所犯之罪。克劳狄奥对自己的行为虽然羞于启齿,却供认不讳:“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会饮鸩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1.2.108-9)狱吏对克劳狄奥罪行的描述最具中立色彩,同时也最为人性化:“唉!他不过好像在睡梦之中犯下了过失,三教九流,年老的年少的,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毛病,偏偏他因此送掉了性命!”(2.2.3-6)依狱吏之见,克劳狄奥所犯之罪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奸罪,而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爱斯卡勒斯是剧中另一个中立、可靠的叙事者,在得知安哲鲁将宣判克劳狄奥死刑时,这位公正、仁慈的辅政大臣也试图劝说安哲鲁从轻发落克劳狄奥:“我知道你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你要想想当你在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你的心愿,或是你自己任性的行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自己也很可能——在你一生中的某一时刻——犯下你现在给他判罪的错误,从而堕入法网。”(2.1.10-16)从文体风格上看,这段话语不免显得重复累赘,仿佛暗示了说话者尴尬、局促不安的心理。其实爱斯卡勒斯想要说的无非是,安哲鲁在相同的情境之下完全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依莎贝拉表达得更为直接:“倘使您和他易地相处,也许您会像他一样失足,可是他决不会像您这样铁面无情。”(2.2.66-8)西奥说得更爽快:“这种罪恶是人人会犯的;……你要是想把它完全消灭,那你除非把吃喝也一起禁止了。”(3.1.347-9)
不难看出,克劳狄奥所犯的罪更接近于宗教之罪(sin),而不是现代刑法意义上的犯罪(crime)。同样,从现代刑法思想看,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是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而不是来自个人的邪念。法律刑法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宗教上的罪与律法涉及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不能用宗教罪孽作为衡量犯罪轻重的标准。从基督教有关“罪”的观念看,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我们看到剧中的“审判者”安哲鲁很快在依莎贝拉出现后也暴露出自己的罪性,从而由审判者堕落为被审判者。安哲鲁其实是利用世俗的法律惩罚克劳狄奥的灵魂犯罪,这也许是安哲鲁或维也纳的刑法违背量刑适当原则的根本原因。
该剧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中,公爵更像是一个“绝对的”君王,王国里的最高立法者,个人的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正因为具有这种合法的、超越法律制度的权力,公爵才可以大赦罪犯以彰显其贤明君主的“仁慈”。维也纳与詹姆士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同样都是绝对君主制的政体。公爵作为维也纳的王权象征,具有国家法度的最终解释权。在这个意义上,维也纳充其量是一个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社会,而不是具有分权思想的法治(rule of law)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公爵可以任意践踏法律,相反,公爵在剧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维也纳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一报还一报》一再向观众昭示,维也纳的法律远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不但存在巨大的诠释空间,而且还留有众多触及不到的角落。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与爱邻如己的悲天悯人情怀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也许我们可以把公爵作为一种基督教理想君王的形象进行解读,只是《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对贤明君主的歌颂呢,还是对神权政治的反讽?这也许是该剧最难以揭开的谜团,也是莎士比亚留给现代读者的一大难题。
注释:
①本文该剧的引文均取自朱生豪的译本,行数标注则以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1997)为准。
②“一报还一报”一语援引的是《旧约》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的观念。《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也用了类似的字眼告诫门徒:“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与《旧约》中的复仇精神不同,耶稣用“爱邻如己”的诫命超越了严峻的律法。
③本文英国国王加冕仪式上的誓言转引自Debora Kuller Shuger,Political Theologies in Shakespeare's England:The Sacred and the State in Measure for Measure(Houndmills:Palgrave,2001)1。
④怀特霍尔宫是詹姆士一世授权修建的大型豪华宫殿,17世纪末毁于大火。伊利戈·琼斯与本·琼森在此举办过极其盛大的假面舞会,且以大肆宣扬詹姆士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权观著称。
⑤“一丝不苟”一词原文为precise。该词词义十分丰富,表示“严谨刻板”、“按章办事”、“恪守教规”等含义。莫里斯·切尼(Maurice Cheney)等评论家认为,precise一词在莎士比亚时代常常用来形容清教徒按照字面含义解释《旧约》的行为。
⑥贺凌虚译著:《商君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1页。
⑦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⑧贝内加:《〈一报还一报〉中的政治-神学心理学》,郭振华译,《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⑨此句原文为Let us be keen,and rather cut a little,/Than fall,and bruise to death.朱生豪译文并没有完全传达出原文cut修剪(树木)的含义。
⑩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4页。
(1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袁瑜琤、苗文龙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12)笔者注意到,该剧不同版本的注释者对剧中克劳狄奥和朱丽叶的婚约(true contract)性质的看法上略有不同。戴维·贝文顿(David Bevington)认为,该婚约有约束力,但双方不得在婚礼以前发生性关系;斯蒂芬·奥格尔(Stephen Orgel)等主编的塘鹅版《莎士比亚全集》认为,他们的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两人已经是合法夫妻;诺顿版认为,婚约是否有约束力取决于文字,如果使用现在时态,那么两人即为合法夫妻,如果使用将来时态,那么这份婚约则表明一种承诺;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RSC)版认为所谓的true contract 是指他们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表达了彼此结为夫妇的意愿,但对婚约本身的合法性语焉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