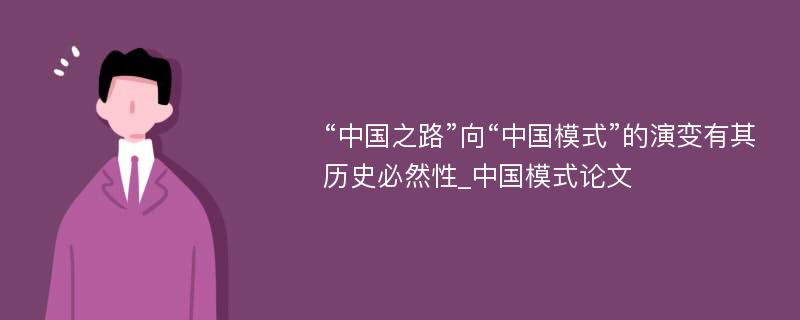
“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的演进具有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必然性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06-03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理论焦点正围绕着“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之争而展开。一些人从国外学术界引进“中国模式”概念,一些人主张“勇探道路、慎言模式”,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了。其实,从语用学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对立只是一个假问题。
人们都知道,“中国道路”是中国人对30年社会主义改革经验的概括总结,而“中国模式”则起源于海外学者对中国30年社会主义改革以及6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实质都是指“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要搞清楚“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之争,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其次要搞清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知道邓小平曾几次提出“中国模式”的问题。1980年5月,他在谈及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对比中明确提出“中国模式”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模式,但“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1988年5月,他讲到“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只用一个模式去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2]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正是这一思想使他产生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
其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世界学术知识界,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具有良知的理论家也都先后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命题。最早是德国人威纳尔·桑巴特在其著作《德意志社会主义》中曾提出问题:“何谓德意志社会主义?”他认为“不应当把它仅作为德意志人的社会主义讲”。他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国族的社会主义,不问其主张之人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而“是一个单独并专门适用于德意志国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为我们时代的德意志国,因为它是按照德国情形而制订的,所以这社会主义好比是一袭按照德意志国身材裁制的衣服,即是定做的,而不是成衣。”在他看来,相对于德意志人的“肉体如风土、人口数量、人种特质等”、“心灵如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和“民族精神如民族伟人的言行、信仰宗教等”,他更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之目标与途径”,即“要把德意志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3]桑巴特所说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是必须按照德意志国度量身定做的思想,“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根本内涵就是要把整个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的目标与途径等寓意,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启迪。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较早提出“中国模式”概念内涵的,大概要算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他最早在1989年第1期《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21卷就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4]他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捉摸不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5]在这里,阿里夫·德里克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第一人则是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6]系统阐述“中国模式”的则是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7]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因此,试点、渐进、非正式,至今中国已经为第三世界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西方人称之为“北京共识”。在雷默之后,“中国模式”的提法开始流行于国际学术界。
只要人们平心静气地看问题,从语义学角度考察,就不难发现“道路”与“模式”在词义上是相通的。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别人看来就是模式,在具体体制和制度的意义上它们具有相近的语义内涵。具体说来,道路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具体手段方法和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恩格斯强调:“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9]他强调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最大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得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体制模式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邓小平明确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而具体制度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模式。由此可见,“模式”与“道路”的基本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模式”主要是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选择,而“道路”则是对于社会具体制度、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之处是两者的具体所指、具体的对象不同,外延范围涵盖有所不同。因此,目前流行这样一种理解是可以讨论的,即所谓“道路”是动态的、而“模式”则是封闭的,这种理解仅仅是停留在现象表面的肤浅看法,不足为据。
最后,从世界舆论来看,中国道路正在向“中国模式”演进,并日益生发出无穷的世界文化意义来。这就是说,13亿人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道路”坚持了30多年,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体制“模式”,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就没有当年毛泽东要搞中国学派、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在现代化建设中,为什么除了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就不能存在另外一种中国模式或东亚模式呢?而且,为什么中国人一提模式就一定是封闭的、不开放的呢?这里除了“文化缺钙”,还有的就是偏见与无知!君不见,欧美模式如果不是开放式的,哪来今天从经济到政治一体化的“欧盟”,哪来美国的“新知识经济”,哪来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呢?“中国模式”如果不是开放的,哪来今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哪来今天的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哪来今天的“低碳经济”问题?问题在于中国道路正在向“中国模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模式”显然还是不成熟的,是具有内在矛盾的,是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的,这是可以分析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况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有世界上对于“中国模式”的肯定或批评的议论,都是可以经过分析为我所用的,只要我们具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足够的辩证分析能力。更何况现在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友好和关注的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发自于内心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显然,“中国模式”不是先验的,而是必须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况且,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须一个科学发展的理论模式的指引。应该清醒意识到他们许多中肯的分析意见是应当值得我们深刻体味和认真汲取的。
远不像“中国模式”论的批评者所言那样,“中国模式”论容易使人封闭、自大,从而自足起来。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道路”的现实发展遇到一系列瓶颈问题,“中国模式”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因此,“中国模式”绝不是现成的,而是一种实践经验的提升和理论建构。实践创新指引理论创新。13亿人走了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也不可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而没有理论模式指引。社会主义作为13亿人的一种共同社会理想,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形成一整套理论模式,从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运动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并进一步成为制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具体制度,虽然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已经和正在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何况中国道路的现实发展正在遭遇瓶颈难题,除了资源、环境、人口因素,还有气候变化、非典流感疾病等诸多因素,这才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这也才有“中国模式”的理想范式应运而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虽然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遭遇到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提出明确的体制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今还在提炼与建构过程之中。各级干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缺失不能不说与此无关。更何况,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的高速发展面临高风险社会时代的降临,从哥本哈根会议上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生态变化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深层次矛盾,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发展,都呈现新的不确定性。后30年中国发展已经不能依据原有的思维模式,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重新构建和重塑。
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考察问题,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模式”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从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人探索创新人类“第三种文明”的思想结晶,是融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结论。从全球现代化运动进程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世界志士仁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理性思索,是关注世界进步发展的人们合力探究锐意丰富创新“现代性”,其中包括从分配、身份、代表性,一直到幸福和尊严的共同愿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是包括越南、古巴、朝鲜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多样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主流理论形态。近来有人著文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但成了“世界村”的一个成员,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央有关领导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走出去,加强与全球马克思主义者互动交流,争取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界的话语权,善于传播中国学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常常是在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状态下得到研究的。[11]其实,如果把“中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那么“中国模式”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的成果(即“出口转内销”的结晶),显然这两者也不应该相互分离、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动力。从这层意思上讲,割裂“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更是不符合现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