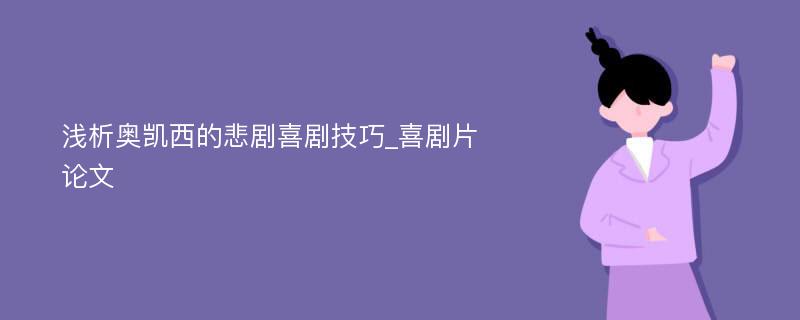
试析奥凯西的悲喜剧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喜剧论文,手法论文,凯西论文,试析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奥凯西是二十世纪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中重要的剧作家,他创作的《枪手的影子》、《朱诺和孔雀》、《犁和星》共同构成了都柏林三部曲。他的戏剧极大地丰富了爱尔兰的民族戏剧,开创了剧坛新风。奥凯西创造性地将传统的悲剧与传统的喜剧叠影重塑成了全新的悲喜剧,即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实质,这是萧伯纳“矛盾修饰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奥凯西创作悲喜剧的原因大致有二:一为其辩证的生活态度,他一向认为有失方有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二为社会对戏剧的要求和需要,观众渴望热烈的场面和诙谐的戏剧语言,对当时舞台上的中产阶级生活已感厌烦。
关键词:爱尔兰戏剧 悲喜剧 奥凯西
继易卜生的问题剧之后,世界剧坛掀起了戏剧革新之风,英国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戏剧复兴。爱尔兰作家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一直史不绝书,对英国戏剧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著名剧作家有王尔德、萧伯纳、叶芝等。他们独树一帜,对戏剧的创作方法,其社会性,思想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兴建的“爱尔兰文学戏剧社”更把一大批杰出的爱尔兰剧作家集于麾下,极大地促进了爱尔兰民族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爱尔兰戏剧运动中三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分别是辛格、奥凯西和罗宾森。他们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不少反映爱尔兰生活的剧本。其中奥凯西的创作最具特色。奥凯西的作品,不论其上演与否,都以其鲜明的个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刻划,诗一般的方言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奥凯西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也是任何一个时期最杰出的爱尔兰问题作家。研究奥凯西的戏剧,可藉以窥得爱尔兰文学之一斑。鉴于国内对爱尔兰文学研究不多,对奥凯西也知之不多,谨撰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就教于文学同仁。
一
奥凯西原名约翰·凯西(John Casey),生于都柏林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幼时贫病交加,全家靠母亲的辛勤操劳过活,这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他作品中对工人阶级和伟大母亲的讴歌即源于此。奥凯西认为“戏剧即生活”,立意通过戏剧直接参与历史的进程。
《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 1923)是他在阿贝剧院上演的第一部作品,反映1920年爱尔兰的游击战争及其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在阿贝剧院连演三个晚上场场爆满。从此,他声誉鹊起。奥凯西在阿贝剧院上演的第二部反映1922年内战时期的剧作《朱诺和孔雀》(Juno and Paycock 1924)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创下了该剧院成立二十年以来连续两周上演同一剧目的记录。其后,阿贝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反映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第三部剧作《犁和星》(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1926),由于《犁和星》中所表明的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看法,在阿贝剧院上演时发生了骚乱,这是继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一剧后的又一次观众闹事事件。观众中的爱国主义者认为奥凯西的剧本诋毁了爱尔兰英雄的名誉。尽管如此,这出戏还是成为阿贝剧院经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奥凯西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战争时期都柏林贫民窟中普通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带有鲜明的反战倾向。战争不仅吞没优秀青年的生命,也给无辜的贫民,包括妇女和婴儿带来了死亡。作品一方面讴歌了爱国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对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作了冷静的反思与评判,有时甚至带有讽刺性。对爱尔兰式的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感伤,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对人们的懒惰、虚荣、冷酷无情以及浑浑噩噩都作了辛辣的嘲讽。
这三部剧作都以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时期(1916-1922)都柏林的一个贫民窟为背景,构成了他的都柏林三部曲,也奠定了他在西方戏剧史上的地位。他的《朱诺和孔雀》被批评界公认为其创作顶峰,于1926年获英国霍桑登奖。在形式上,奥凯西打破旧的悲剧、喜剧严格划分的传统,在悲剧中掺入一点喜剧的场面,使情节产生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感,也使悲剧气氛在对比中得到加强,构成了这三部剧的又一共同特点。
二
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从古希腊开始就已存在,当时的悲剧主要表现人同命运或神的意志作抗争,悲剧人物具有英雄的性格。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旨在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到渲泄与净化;黑格尔以为真正的悲剧应当是性格悲剧,悲剧的原因是主人公的过失;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把“伟人的痛苦与死亡”看作悲剧的本质。在奥凯西笔下,悲剧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它不是《俄狄浦斯王》式的命运悲剧,或《奥赛罗》式的性格悲剧,或《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社会的罪恶,人性的泯灭才是奥凯西悲剧的实质。
首先,是社会的悲剧。奥凯西前期戏剧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来自贫民窟。他们栖身在风烛残年的建筑物里,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肚子使人无法逃避可怕的现实。非人的生活环境营造出悲剧的气氛,而人类的愚蠢则导致了悲剧的直接发生。在《犁》剧中街上的集会上,演讲者正慷慨陈词,鼓动人们“为爱尔兰的独立坐牢!”“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挂彩!”“为爱尔兰的独立牺牲生命!”于是“整个楼的人不是差点儿给打死了吗?年轻的道尔迪的丈夫一条腿给炸掉了;特拉瓦斯太太的儿子…叫一个地雷炸死了;曼宁太太在几个星期以前丢掉了她的儿子,现在可怜的坦克里德夫人的独生儿子也被打得满身窟窿上了西天…”(《朱》剧第二幕)死者成了起义的工具和牺牲品。留下他们的亲人,妻子或母亲,慢慢吞咽战争的苦果,走完苦难的人生。而煽动战争的人们,或者鼓励人们盲目送死的人,如杰瑞一流的工会主席们正拿着一年350英镑的俸禄,远远地离开了贫民窟,过着舒舒服服的体面生活。
“人对人的野蛮行为造成了说不尽的悲哀”。(《朱》剧第三幕),我们悲哀不仅因为战争带来了死亡,吞没了无数青年的生命如马圭尔们,克里西罗们和汤米们,破坏了天伦的夫妇挚爱,母子拳拳,毁灭了美好的人伦。我们悲哀还因为战争扭曲了人的灵魂,扼杀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如《朱》剧中的姜尼,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本是个单纯的青年,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狂热煽动下,他参加了两次战斗,一次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次失去了一条腿。他为共和国流了血,做了贡献,理应是受人尊敬的英雄,生活理应充满掌声和鲜花,可是起义失败了,革命者都受到了追捕,转入地下。他也堕落成了可耻的叛徒,最后被人像狗一样地拉出去毙了。这时,有识之士都沉重地思考起来,为什么这样一个青年会落得这种下场?
当战争就发生在穿着不同制服的爱尔兰人中间,同胞残杀之际,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根深蒂固的仇恨使得军队无法团结一致,使居民不愿互相帮助时,我们感到上帝也无能为力,而只能置他们于不顾了,我们的悲哀变得绝望了。而爱尔兰人自己对周围的悲剧却浑然不觉,依旧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当楼上的坦克里德夫人沉痛地埋葬爱子之时,楼下的博伊尔一家正欢天喜地地举行酒会。当博伊尔太太的爱子也被人打死时,她才理解了坦克里德夫人的心情,于是,她情不自禁地重复坦克里德夫人的话,“…耶稣啊,请拿走我们的石头心肠,…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吧!…让我们也具有你的那种永恒的爱吧!”这个小小的简单的重复,令人震惊而颤栗,多么可怕的冷淡!什么时候博伊尔太太们才能在爱子逝去之前就能理解别人丧子的切肤之痛呢?而我们是否也一样对博伊尔家的悲剧毫无感觉呢?在《犁》剧中,这种冷淡更有了令人痛恨的表现,当爱尔兰公民军正与英军开战之际,贫民窟的人早已把爱国主义抛到脑后,不顾街上的枪林弹雨,参加了抢劫行动,对受伤的爱尔兰战士却坐视不救!因此,这也是人性的悲剧。
作为悲剧,死亡是重要的主题。《枪》剧中的马圭尔、明妮,《朱》剧中坦克里德夫人之子,《犁》剧中克里西罗都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外,《犁》剧中的蓓西为救发疯的娜拉自己却不幸中弹身亡,娜拉的儿子未出世即已死亡,她本人由于过度担忧、惊吓和早产而发了疯,失去了作为人的理智。《朱》剧中的姜尼之死更是耐人寻味。奥凯西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战争的观点:是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毁了这些热血青年和无辜的生命。而恐惧是无所不在的,不过在《枪》剧中稍闪即逝,在《朱》剧中则如利剑出鞘,若非姜尼身陷其中,旁人绝难体会其中之味,在《犁》剧中,则如薄雾弥漫全场。面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人物的担忧,营造出一个若隐若现,至始至终存在的悲剧气氛。
三
然而奥凯西的戏剧并不以人物的死亡作为结束。当情节发展到悲剧的高峰时,却以喜剧收场,而且在情节发展中,既有喜剧场面,也有悲剧场面,即所谓的悲喜剧。悲剧说明的是社会的可悲,人性的可悲,是实质,而喜剧则反映了爱尔兰人的性格和风俗,是表现,是形式。这里悲喜剧手法结合得最完美的当数《朱》剧。《枪》剧未免显得太单薄了些,场景单一,人物远不如《朱》剧丰富和多角度,而《犁》则流露出更多的悲观绝望,冲淡了喜剧效果。
爱尔兰民族热情奔放,真诚爽朗,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的生活也是轰轰烈烈或闹闹轰轰的。这一点在奥凯西的剧中都作了逼真的描绘。如《犁》剧第三幕中的酒馆是一重要场景。酒馆外的街上起义者正在举行集会,台上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台下血脉贲张,群情振奋;酒馆内,路茜正与小伙子和发拉瑟打情骂俏,卖弄风骚,发拉瑟与小伙子还争风吃醋,借酒闹事,酒馆内外恍如两个世界。奥凯西在这里对爱国主义热情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对群众的愚昧和不觉醒作了无情的讽刺。
《朱》剧中的遗产风波也颇具喜剧色彩。当班逊来访时,全家人反应冷淡,当班逊先生提到博伊尔家的亲戚艾里逊先生,博伊尔还无动于衷地表示“希望并没有多少人会为他掉眼泪。”当他得知自己为其遗产继承人,他立刻面色一端,表示马上要“改邪归正”,全家人都对班逊热情有加,他俨然成了幸福使者,财产的化身。玛丽更是急切地、坚决地与昔日恋人分手,投入班逊的怀抱。全家喜气洋洋,简直趾高气扬,他们赊帐买东西,提前消费好日子,连房子也“好象小得盛不下他们了。”(第二幕)然而由于班逊一伙玩弄的文字游戏,遗产一事已属子虚乌有,这时,博伊尔又开始破口大骂了,姜尼差点与父亲动手。但一切已于事无补,玛丽未婚先孕,家中已债台高筑,全家立即陷入了比先前更窘迫的困境。如此大起大落,忽悲忽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悲剧的喜剧化处理表现在另一方面是人物的性格刻划。以《朱》剧为例。
最富喜剧色彩的人物是博伊尔。他一出场就醉了,醉汉的憨态立即引起了观众的哄笑。常常有人将博伊尔与莎士比亚著名的福斯塔夫相比。博伊尔的插科打诨使全剧浑然生辉。借着酒力博伊尔自吹自擂,向来以船长自居。浪荡鬼乔克赛则亦步亦趋。令人联想到唐·吉诃德和他的伙计。朱诺却看透了他,她说:“你用刀叉干活比用铁锹强多了”,常像训孩子似地数落着博伊尔。博伊尔只有唯唯诺诺,毕竟自尊是无法与饥饿相抗衡的,尤其当你吃了上顿没下顿时。赤贫以一种漫画式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捧腹之后,忽然觉得一种恐慌。如果我们境况如此,恐怕要笑不出来了。博伊尔的腿痛也是极具喜剧性的。当他喝酒时,他可以蹦蹦跳跳的。一听说有工作了,他的腿立即痛起来了。当朱诺要他快吃饭,穿上厚布裤准备干活时,他的两条腿都痛得难忍难当起来了。最滑稽的是他明明是个失败者,而且屡试屡败,像战士失去斗志一样,已经丧失了竞争的勇气了,他却不断地声称,“我还有点精神存在着,(我还有点酒劲)”。令人怀疑他醉耶?醒耶?
博伊尔是为我们制造的聪明小丑。他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脆弱,帮助我们以笑为疗法来消除尴尬与难堪。小丑都是好吃懒做的胆小鬼和无赖。他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傻瓜。我们嘲笑他,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沾沾自喜,他奇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便疑心他是我们的变体;他向我们使眼色,我们也很高兴地发现自己也是贪食者、胆小鬼和无赖。这个无赖使我们不再害臊。更有甚者,他还说服我们一起对浪费掉的情感,受挫的雄心,潜在的犯罪当作谵妄而加以嘲笑。因为如果我们是野兽的话,又怎会有精神创伤?更何况,我们已经醉了。
玛丽则是一个女性小丑,她徒慕虚荣,贪图富贵,抛弃了苦恋着她的男友杰瑞,委身于律师查理·班逊,企图跻身于中产阶级。她与杰瑞的拉拉扯扯,与班逊的忸怩作态,作者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最后,她已怀上了班逊的孩子,班逊却不告而别,家里则已被债主们洗劫一空了。
这时杰瑞赶来想与玛丽重修旧好。可当他知道了全部真相之后,他立刻变得语无伦次起来。玛丽看穿了他,“你的人道主义其实跟别人的一样狭隘。”杰瑞悄悄地走了,在玛丽背诵斯特拉夫人道主义诗篇的朗朗声中弃阵而逃了。其讽刺意义不难看出。而玛丽,虽然失了身,坏了名节,又没了家产,可以说跌到了最底层,她却真正地理解了生活,她决心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和孩子,对布满荆棘的前途满怀信心,显示了灵魂获得新生的力量。
就这样,奥凯西借助小丑,以否定来表达肯定,以下降表示上升,以笑声作悲声,以有形的实质上的失败来反映无形的精神上的胜利,小丑们对所有的虔诚都要质疑,他们颠三倒四,似是而非,却聪明机警,以一笑来遮百丑。
这种喜剧式的卑微表现了人的卑下,挫败和孤独,作为喜剧主要表现手法的丑角在西方文化中有悠久的历史。不同于莎士比亚剧中为他人提供娱乐的弄臣,奥凯西剧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丑角,嘲笑的对象是他们自己;不同与塞万提斯笔下置身于社会之外并与之斗争的唐·吉诃德,奥凯西的喜剧人物并无我们所期待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即使是朱诺,“家中的顶梁柱,全靠她把这个家聚在一起”,也想着放松一下,“埋葬哪怕一会儿,那该死的责任和职责”。正如T.S.艾略特所说,“…当无法忍受悲痛、不幸和绝望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出野性的大笑。”小丑们的滑稽动作给全剧增添了亮色,冲淡了悲剧的气氛,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哀。可怕与绝望于大笑中得到了渲泄,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我们获得了严肃悲剧的“净化”和升华。
四
奥凯西之所以采用悲喜剧的手法,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为其生活态度,奥凯西一向认为输家即赢家,有所得必有所失,亦即无所谓完全的失败或胜利,邪恶亦可以是美德,糊涂就是大智,世界观的矛盾反映在戏剧上表现为悲剧的主题与喜剧的形式的矛盾。于是,酗酒,谎话连篇等社会恶习却成了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的良方,玛丽的失身成了美好生活的开始,娜拉因失去理性而得到了最终的解脱,摆脱了所有下层妇女的操劳担忧和丧失亲人的痛苦。其二为社会需要,当时,英国戏剧的聚光灯主要对准乡村别墅,客厅和旅馆卧室,即有产阶级的生活。可以说,英国观众期待戏剧语言,起伏的情节,热烈的场面,但是爱尔兰由于连年内战,人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和饥饿之中,整个爱尔兰普遍存在悲观绝望情绪。这就决定了奥凯西剧作的生活环境充满悲剧性,而占中心的都是喜剧人物,绞架下的幽默冲淡了忧郁的气氛,于是便有了反传统的悲喜剧。
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创新,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喜剧的目的是表现人比真实生活中的“更糟”,而悲剧则表现人“更好”。奥凯西剧中的人物则同时地夸大了人与生活相比的“更糟”与“更好”的方面。在扭曲变形的现实生活中,尊严已经常常受到怀疑,喜剧性的“更糟”也许意味着“更好”,而“更好”也许则是完全绝望的结果。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又一创新。人的心理需要以嘲笑来忍受生存的痛苦、这可能是一个现代的观点,它可以帮助解释用副线的喜剧排挤了作为主线的悲剧,而双线发展的剧情处理则是伊丽沙白时期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现代爱尔兰剧作家,以喜剧式的怀疑描写了悲剧性的英雄主义,他们笔下的小丑不仅亵渎他们的英雄,而且坚持认为小丑应说开头和结尾的话(都有发言权),而可能的爱尔兰英雄通常或在后台英勇牺牲,或盲目送死,当他们上场时,则慨慨陈词,丝毫不知他们是变形的小丑,于是悲剧的主线与喜剧的副线主客串位了。这种结构逆转,也可看作是爱尔兰对主人公发展预见的第三个创新。
奥凯西曾说过……戏剧如果想作为一种艺术存在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观点,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开创新的风格……在生活中,人的心情和举止并不总是,而且也不常常是,前后一致的,在戏剧中却为何偏要如此要求……一颗在手中滚动着的宝石也会闪烁着各种光泽;在喜剧和悲剧环境中活动的人生,在其多面性的统一体中,决不会只是放出许多不同的色彩而已。
从《银杯》开始,奥凯西的戏剧创作转向都柏林贫民窟以外的题材,也开始了现实主义以外的艺术探索。如表现主义的《银杯》(TheSilver Tasse 1928)和《大门内》(Within the Gates 1934),象征主义的《星儿变红了》(The Star Turns Red 1940),半自传的《给我红玫瑰》(Red Roses for Me,1943),奇幻剧《内德神父的鼓》(The Drumsof Father Ned,1955),以及讽刺剧《绿帷幕的后面》(Behind theGreen Curtain 1961)等。这些题材风格各不相同,表现了奥凯西对戏剧艺术的不断追求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