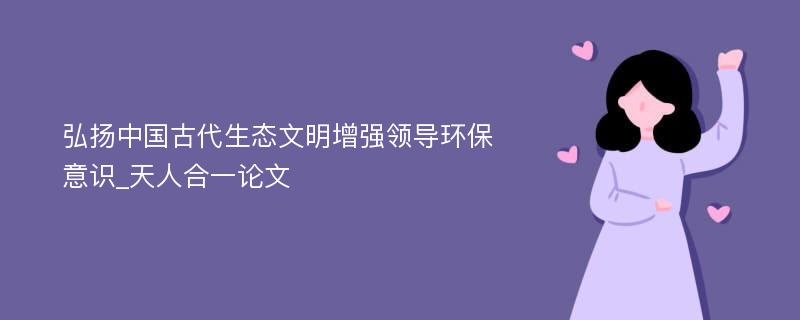
弘扬中国古代生态文明增强领导者环境保护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领导者论文,保护意识论文,生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程度成正比。如果人对自然肆意虐待,毫无爱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调、失衡,势必两败俱伤,社会不仅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最终会毁灭人类自己。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各级领导干部,其环境保护意识的有无和强弱,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一意识的增强,有赖于理智、开明地汲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文明遗产,对于领导干部和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树立,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多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内涵和外延相当宽泛,既有神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又有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本文着重借鉴的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它受到了现代东、西方人的广泛青睐与推崇。
一、中国古代的生态理论
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生态理论,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价值,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至上要义。其精髓主要是:
(一)尊崇自然“好生之德”,效法天地“厚德载物”。我们祖先认为,以“天地为代表的自然界是极其伟大的。首先,是它生成养育了世界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宝典《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繁育万物,使之生生不已,是天地的最高美德。它“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曲成万物而不遣”,其生成之功,惠人之仁,是无与伦比的。《礼记》也认为,正是由于大自然的生生之德,天地间才有“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人类才有了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其次,自然界是最无私的。《周易》云:乾坤“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它造福了天下万物,而又从来不表白居功,真是太伟大了!《礼记》将这种精神概括为“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即对世间万物都一体相待,无所偏佑。再次,自然界具有博大宽容的胸怀,无所不涵容,无所不承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从而使千千万万异质异相的事物和谐相处,实现了多样性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古人才提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厚德载物”,普利万物。
(二)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自然,把万物视为人类的朋友。孟子发展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仁民爱物”。董仲舒也认为,仁爱所及应包括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北宋张载认为人类应兼爱万物。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意谓天地万物有一致的本性,而非我人类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万物的本性,以尽自己的责任。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都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人和万物;人若要成长发展,必须让万物也得以成长发展。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命题:“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天地之体,当作自己的身体,把天地变化的自然本性,当做自己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是多么博爱情怀,何等深刻的生态伦理!
继张载之后,程颢、朱熹等进一步发展了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思想。程颢直接把尊重自然界“生生”规律同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他认为:天地生成万物,万物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意,人类应认识和尊重这个“生理”,以仁爱之心维护万物的生育,便是善德。据此,他明确提出了“物我兼照”的口号。朱熹要求,人皆应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明代王阳明也主张人类要仁爱自然万物。
(三)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系统,强调协调发展。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五行”理论,认为人类如果恣意妄为,就会使“水火木金土”产生恶性变故,殃及动物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以至发生自然灾害,从而使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恶化。“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毒水淹群,漉陂如渔,咎及鳞虫”;“咎及于火,则大旱,必有火灾。摘巢探鷇,咎及羽虫”;“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诛,咎及倮虫”;“咎及于金,……四面张网,焚林严而猎,咎及毛虫”;“咎及于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水、火、木、金、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自然资源,其中任何一种资源的破坏,都会殃及生物,危及人类。汉代《晁错新书》云:“焚林斩木不时,命曰伤地”,意谓违背树木生长规律和时令,滥伐林木,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刘向《别录》云:“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指出山林受到破坏是造成江河洪涝灾害的根源。他们已清楚地看到,无论自然界本身,还是人与自然,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命系统,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会造成系统的失调与失衡,危害自然和人类。所以,程颢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著名口号,要求人与自然一体相待,彼此关照,共生共荣。
(四)把生态的平衡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持续发展相统一,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资源。孟子不仅主张“爱物”,而且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目的是使“鱼鳖不可胜食也”、“林木不可胜用也”,即保障自然资源用之不竭。荀子提出“山林泽梁,以时禁发”,使动植物“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样,自然资源才不会匮乏,百姓才能“有余用”、“有余材”。汉代思想家贾谊强调,欲使资源“蕃多”,人类必须“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淮南子》在提出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的措施后也指出,人类只有有节制地利用资源,才能使“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昌盛繁荣,生机无限。
与当今时代相比,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人口可谓稀少,人均所拥有的资源可谓极其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可谓十分低下。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思想家们却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至上要义,提出如此系统而深刻的环境保护理论,实为人类生态文明之先声。我们相信现代各级领导者可以从中受到很多启迪。
二、“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含义来返观中国古代生态文明的现代价值。
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涵义是,当代的发展要兼顾未来的发展,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发展的前提来看待,二者要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不断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既要造福当代,又要功在后人,利及千秋,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因发眼前财而造子孙孽,不能“提前使用儿孙辈的地球”。这就要求人类从过去那种以征服自然为成功、以无穷无尽地向自然索取为天经地义,转变为关心地球、爱惜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涵义是整体发展。地球是一个整体,资源、人口、环境相互依存,因此必须摈弃传统的社会发展观,用整体战略把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与利益加以整合,变经济单兵独进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进步。
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社会各方面应协调发展。不仅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只是一味满足人的欲望和享乐,而不顾及自然万物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任何社会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即使有所发展,那也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健康的、不持久的。
可持续发展当然也包括要平等发展。除了当代与后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农村与城市之间,都应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外,还要求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待,共生共进。如果人类的现代化是以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为代价,那么自然界的报复就会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社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持续发展。
这种持续性、整体性、协调性、平等性,实际上就是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将“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换句话说,即人与自然统一,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界价值统一,人类生存发展权利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权利统一,生态的持续、经济的持续和社会的持续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它们正是“天人合一”的题中之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依循天地“生生”这一最高的自然和伦理法则,尊重和爱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指导人类自觉肩负起保护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健全生存与发展的责任,履行人类维护整个生存体系内在平衡的崇高义务,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正如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埃及人)所说:“保护环境是我们(指埃及、印度、中国)古代文明的要义。”
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西方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尽管有古希腊“一体三相”的天人和谐观,近代的“物活论”、“理念论”和笛卡尔、黑格尔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因素,以及现代的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自然协同合一的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是天人抗衡、天人交战、天人对敌。他们在功利主义驱使下,片面强调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种强烈的戡役万物、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6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明智的西方生态哲学家、伦理学家开始深入探讨生态危机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从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到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再到最近的畅销书《塞莱斯廷预言》,都明显出现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的趋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越来越受到肯定和重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生态哲学家林恩·瓦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西方的生态危机源于西方人的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把自然界仅视为可供开发的资源。这种观念已经使地球遭受了浩劫。中国文化中关于“人——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值得西方人借鉴,它可以防止人类在自我毁灭的危险道路上走得更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施韦兹对中国的“天人合一”表示由衷的赞许与敬佩,说这种思想“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当今西方世界新创立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文明学,皆与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异口同声,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中汲取营养,因为“天人合一”早就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归宿和最高境界。人类历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几乎与东方文明同时出现,但前三者之所以遭到毁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粗暴地破坏和盲目地使用自然,最终被自己所引发的灾难所吞噬。而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成果所以生生不已,绵延至今,实在是得益于我们先人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既改造自然,又适应自然。
在弘扬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时,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那就是领导者要正确认识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近年来,有人把生态环境恶化单纯归咎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发展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不能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束手无措,任其摆布,不能倒退到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恰恰相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进步尺度,是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标志。虽然科学技术与保护生态环境有矛盾的一方面,前者会给后者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但科技也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人类只有继续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才会更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绝不能为保护环境而反对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因为那样只能两俱无成。
但是,人类不应该由于掌握了科学技术而忘乎所以,对大自然随心所欲,滥施淫威,索取无度,永不餍足;不应该奉行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主义,肆无忌惮地破坏人类生存的条件。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人对自然界的依存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人当然不能甘于做自然界的奴仆,但也不是自然界的暴君,而是与万物同为自然界的儿子。人虽然为万物之灵,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控御自然,但是人并非天然地具有剥夺其他生命的权力。他们只能认识自然规律而不能粗暴地改变自然界运动法则,只能利用自然而不能无限度地损害自然。科学越发达,经济越发展,人类就越要牢记这一真理。
金景芳先生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原始社会,人还不能将自己与周围自然界分开,因而不存在“天”人关系问题;第二阶段,人与自然已能分开,但常把“天”人格化、神化,“天”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神与人的关系。第三阶段,人们心目中的有意志之“天”,主张“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第四阶段,天人对立,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但是以后的事情金先生没有讲。笔者认为:如果人类能理智的把握自己的行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五阶段将是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人类将以更高的认识水平和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对过去进行反思,克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不良倾向。树立有节制地利用资源的观念、把发展限制在自然承受力范围之内的观念、为后人留下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观念,从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一个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体系。人类将努力使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良性互补,弃各自之短,取二者之长,利用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完美和谐,从而步入人类文明的新阶段。这是我们必须达到也能够达到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而且只此一径,别无它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