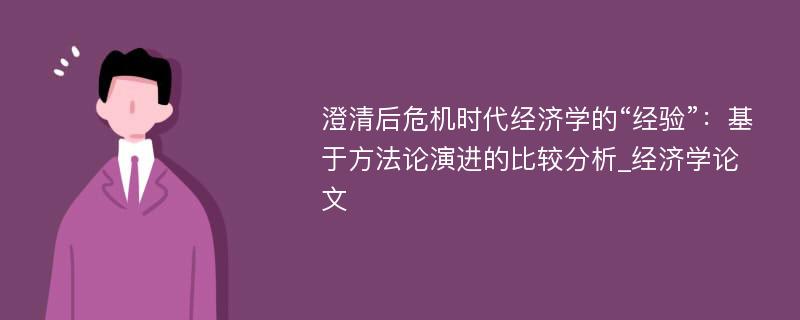
厘清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的“实证”——基于方法论演变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厘清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1929年大萧条后的经济学,哈耶克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说(1933年)中谈到:“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它为何在那么多非经济学家中名誉扫地,让聪明人经常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感觉导致了许多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别人拿它们来戏弄经济学家,我们也用它们来自嘲”(转引自考德维尔,2007,第391—392页)。不幸的是,80多年之后,无论是在分析技术还是计量工具方面均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当代经济学,仍需面对同样的质疑:为什么以证实或预测为核心的当代实证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预测危机?如果将“实证”理解为“用事实来验证”(霍奇逊,2008,第88页),那么经济危机是否意味实证经济学的危机呢?如果是,该如何为主流经济学辩护?如果不是,又该如何看待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在中国,类似的疑问也存在,为何基于实证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无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反主流经济政策却取得了成功(林毅夫,2013,第1095—1108页)?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后危机时代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 然而对于实证的意涵和本质困扰了几代哲学家,这一术语不存在单一的、大家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意义(霍奇逊,2008,第88页)。另外,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就代表着一种坏名声(Delanty,2005;Hands,1998),但实证方法不仅依然是当今经济学的主流,而且经济学领域的实证含义仍经常被等同于哲学的实证主义。①更有甚者,经济学内部也无法就实证方法的标准本身达成一致(博兰,2000,第158—163页)。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界缺乏相关的论述,本文无意且无力从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层面论证实证方法之意涵,而只能从大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学领域不同的实证方法论的演变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如果方法论仅仅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工具箱”(布劳格,1992,第133页),在满足竞赛规则的前提下,哪一种“方法”更适合为后危机时代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提供辩护,那么它就成为判定的适宜标准。由此本文的研究路径是:第一部分考察最早的经济学实证—J.N.凯恩斯实证方法;第二部分分析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问题;第三部分探讨当前主流的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实质与困境;第四部分讨论后危机时代回归凯恩斯实证的必要性;最后是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源头梳理实证经济方法的流变,特别是重新阐述穆勒传统的凯恩斯实证,并探讨其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不同;第二,探讨穆勒传统的凯恩斯实证与当今主流方法论相融合的可能性条件;第三,重新定位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Friedman(1953)的实证方法论(它是当代大部分经济学者读过的唯一方法论著作(Hausman,1992,P.162))。 二、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经济学概念最早由J.N.凯恩斯(J.M.凯恩斯的父亲,下文中的凯恩斯除非特别说明,均指J.N.凯恩斯)提出。在搞清楚其意义为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更早在经济学中讨论过“实证”概念的凯尔恩斯(Cairnes)的观点。在1875年的著作中,凯尔恩斯就将科学分为“假设的”科学和“实证的”科学,其假设的科学相当于穆勒的“演绎”科学(获得推理的知识),“实证”科学相当于穆勒的“实验”科学。由于经济学无法进行实验和完全证实,因此穆勒和凯尔恩斯均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假设或演绎科学。②对此,J.N.凯恩斯认为将经济学称为“假设的”科学不妥,容易给人造成与事实不符的印象。在其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0年)中,J.N.凯恩斯认为,对于“实证”一词,“凯恩斯(应为凯尔恩斯,本文作者注)和其他一些人使用这一字眼时,取与假说这个词相反的意义,但这两个词并没有对应的意思。然而,要找到毫无含糊之意的词是很难的。假说这个词在一些方面看是很好的,有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在某些地方要避免使用这个词,这会被认为有一种与实际这个词相反的意义,而真正对应的这两个词分别是理论和事实”(凯恩斯,2001年,第46页注释2)。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一方面继承了穆勒的演绎科学或凯尔恩斯的假设经济学,即“更依赖于推理而不是观察”,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经济学视为是一门“实证”科学。这样原本意指能进行实验的实证科学称谓引入了“不能进行实验”的经济学,使之成为了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由于约翰·穆勒对这种演绎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最为系统的阐释,因此这种“实证经济学”方法也被称为方法论的穆勒传统。 按照穆勒传统,J.N.凯恩斯将实证经济科学核心特征归结为(凯恩斯,2001,第7—10页):(1)将实证与规范(或理论及其应用)方法区分开来,其中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其目标是建立一致性,它和研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经济学不同;(2)将经济学从一般的社会科学中划分出来,例如经济学只研究人类追逐财富的欲望所产生的后果,从而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特的但非完全独立的分支;(3)由于影响经济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之无法进行实验,经济学不能直接使用归纳法,而应该使用穆勒意义上的先验-演绎法;(4)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它从数量有限的基本假设(如追逐财富的欲望等)中推导出结论,其他散在的、不可靠和不确定的因素被舍弃掉了;(5)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因果规律,而所有的因果律都可称为是假设的(需要使用“假设其余情况均相同”的限制条件),因此经济学只是一门揭示趋势的科学;(6)经验观察可以检验演绎结论并确定其应用的可能性和范围。 事实证明J.N.凯恩斯的实证方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著作第四版(1917年)一直沿用到1930年(熊彼特,1998,第229页注释1),直至众所周知的Robbins(1932)的方法论著作问世。罗宾斯继承了穆勒传统和凯恩斯的实证经济学概念,并将这种经济学定义在稀缺条件下的手段选择上,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定义。这样穆勒传统的凯恩斯实证方法就成了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辩护策略。然而,尽管穆勒传统为建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打下了方法论的基础,但却不断地遭受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攻击。 三、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对穆勒传统的攻击主要来自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然而当前经济学方法论领域普遍忽视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对穆勒传统的攻击,例如Blaug(1992)、Hausman(1992)、汉兹(2009)等知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均未讨论相关内容。因此本部分首先考察孔德的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问题,以便为考察实证主义的后续影响提供基础。 1.孔德的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的应用及问题 针对穆勒传统的“假设”经济学,孔德认为,这种英国的经济思想是“抽象”的、“从概念出发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在他看来,实证科学是确定的知识,它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Delanty,2005,P26)。他还认为,古典经济学家“还犯了把经济现象从整个社会中分裂开来加以研究的错误”,“不恰当地把一个部门从整体中孤立出来,而这个部门却是只能严格地包含在整体之中的”(阿隆,2000,第54—55页,转引自何蓉,2009,第5页)。所以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一个社会学的科学而存在。他建议用动态研究规则取代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研究规则,用历史归纳法取代抽象演绎法。受孔德的影响,英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哈里森、英格拉姆等就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教义使形而上的而非实证的推测成为必要,政治经济科学应该从属于孔德的社会学的科学范围内,这门科学应使用归纳逻辑,进行历史的动态研究,强调跨学科的综合分析(Moore,1999)。不过对穆勒方法论更猛烈的攻击来自于更加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③他们不仅强调归纳法、动态的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而且也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攻击。他们认为,现实中的人受多种动机的驱使,也受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影响,理性经济人是孤立的抽象概念,是片面的,不能代表普遍的人类特点(考德维尔,2007,第43、46页)。经济主体不是只追逐财富的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的人(凯恩斯,2001,第13页)。 对此,穆勒在赞成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和捍卫经验主义的同时,坚持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将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隔离开来的做法。下面从三方面分析穆勒传统对历史学派的反驳。 (1)按照穆勒传统,“孔德的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任何一门知识的进步,要获得科学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只有通过一定范围的专门化才有可能”(凯恩斯,2001,第78页)。科学依靠分析具体现象而获得进步,在研究中总是把构成事物整体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要素分门别类进行处理。由于穆勒时代现代经济学科还没有建立,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仍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范围内,故建立独立的经济科学理论就是其面临的紧迫任务。④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现实中很难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分离开来),经济学只能通过抽象法,从特定的(理想的但不是必然的)真实前提推理出具有解释关系的命题,从而将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从抽象和逻辑意义上隔离开来。“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穆勒,1991,上卷,第8页)。这样政治经济学只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马歇尔认为,“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用现有的资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转引自凯恩斯,2001,第87页)。总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用知识劳动分工的收益支持穆勒传统研究方法的正当性。既然孔德的统一的社会科学不能以其实证主义的预见性、可证实性、持续性或一致性和成果的丰富性(fecundity)等标准证明其成功,也就无法取代政治经济学(Moore,1999)。 (2)“没有演绎法的帮助,将不会导致现代经济科学的产生”(凯恩斯,2001,第132页)。经济学应在基于内省和观察所形成的“显然是正确”的假设(如“经济人”)的基础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行逻辑推理,构建其“真的经验命题”的演绎体系。其结论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论,仅仅在抽象意义上为真。⑤它是一种“主要为演绎、但仍由归纳所辅助和控制的方法”(凯恩斯,2001,第144—145页)。这种综合了归纳和演绎的折中方法被穆勒称为是先验演绎方法(the method a priori)。⑥它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也包含了归纳推理的逻辑,但又非完全的经验现实。这种演绎法相当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豪斯曼,2007,第35页),通过它可建立起来一种对现实中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加以研究的框架(胡明、方敏,2009,2011)。罗宾斯的经济学方法也是如此,如研究稀缺的因果因素(Hausman,1992,chpt.6)。 (3)人的经济行为受到其追求财富的欲望的支配,不仅在构成人类本质的影响因素方面是占据主导优势的,也是无可争辩和不可动摇的。其他影响人类的欲望也存在,也在不同情况下影响着人的经济行为,但这些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凯恩斯,2001,第9页)。因此只有忽视并非重要的、散在的影响因素,而只考虑比较普遍和持久的运行力量,经济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虽然古典学者有时将之视为内省的结果,但它有稳固的经验基础。寻找经济人这一前提的过程需通过不断的归纳比较才最终发现,早期是经验方法的产物,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这种经验方法逐步过渡到公理的方法,并因此过渡到科学的最高概括,而从不颠倒次序(凯恩斯,2001,第120页)。用内省说明的“经济人”的动机在经济领域非常强大,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广泛相符(凯恩斯,2001,第150页)。罗宾斯也认为,“假如不存在有目的的行为,那就可以证明也不存在经济现象”(转引自考德维尔,2007,第227—228页)。因此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来说既必要也合理。 从后来的结果看,凯恩斯的实证方法不仅有效融合了德国和奥地利经济学之间持续数年的“方法论之争”,而且能更加巧妙地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辩护。⑦相反遵从实证主义归纳法的历史学派,虽然能通过融合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为制定政策服务,但其通过现实人的描述无法进行演绎推理,自然也就无法建构他们所期望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他们的努力没有产生一条名副其实的规律”(罗宾斯,2005,第95页)。由于未能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的空前的通货膨胀,又缺乏理论阐述,束手无策,历史学派逐渐丧失了信誉(胡明,2008)。 2.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问题 进入逻辑实证主义时代,哈奇森和萨缪尔森再次在经济学领域倡导实证主义方法。Hutchison(1938)重点强调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认知意义标准和经验检验标准。就前者而言,哈奇森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哲学⑧把经济学命题分为分析—同义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并把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归入分析—同义反复命题。科学研究的是可观察的经验现象,既非分析也非综合的陈述是一种形而上学。哈奇森认为,理性经济人不仅是虚幻的,而且也违背了知识不完全的客观事实。建基于这种不依靠任何事实前提的纯经济理论,是演绎推理的结果,其理论无条件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必然以丧失了经验内容为代价,其命题深陷于限制条件或其他条件不变的体系中,是空洞的定义或同义反复命题;就后者而言,哈奇森承认,虽然纯理论是有用的,但却不能说明关于世界的任何新的事实。经济学按照实证原则的要求,必须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以证实理论与现实经验相符的程度以及由此判断理论的优劣和适用性。 萨缪尔森秉持了一种更加纯粹的或更接近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即他的操作主义(Operationism)方法(主要体现在1938年的《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注释》和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两本书中)。萨缪尔森的“有操作意义的定理”指的是在理想条件下可反驳的经济事实假设,即定理是否具有操作意义决定于它在一定条件下是否具有可反驳性。这种操作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拒绝接受一切本身不是单独地、直接可检验的概括。在其后来转向描述主义方法论(理论是建立在记录陈述之上的归纳)⑨的过程中,他认为,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的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科学解释无非是由方便的或其他实用的考虑所促使的关于经验证据的重新描述(转引自汉兹,2009,第69页)。对可观察的现实通过方程式或其他手段进行较好的描述,是能在世间得到(或期望)的全部“解释”。在萨缪尔森的眼中,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很有用的,但如果它包含着经验错误,就一定要被丢弃,而不能掩盖其不足。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描述不断更替和日臻完善的过程,因此与现象的接近就很重要,假定、理论和结果都应该与现实相符。按照这种归纳式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穆勒传统的演绎的经济科学毫无意义(道,2005,第81页)。“是啊,一想到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有关演绎法和先验推理的力量的夸张要求——由古典作家、1932年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奈特的门徒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提出——我就为自己学科的名声捏着把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时期”(Samuelson,1972,转引自考德维尔,2007,第150页)。⑩ 很明显哈奇森批判经济学中的最大化行为、完美预测等违反现实的假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以及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米切尔对经济理论的批判如出一辙(考德维尔,2007,第241、392页)。如果说历史学派对古典的实证逻辑的攻击必然失败的话,那么哈奇森的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认知意义的标准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另外,哈奇森将纯经济理论称为同义反复,但同义反复并非是错误的,它是建构理论所必需的。当今时代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不识别一个人的形而上学,就难以定义他的研究纲领。另外,形而上学不是同义反复(博兰德,2008,第55页)。 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同样不适用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设。(1)他建构显示性偏好理论的操作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主义(radically behaviorist),不仅前后观点不一致、没有用,而且运用它意味着放弃整个经济学的理论事业(Hausman,1992,P.157)。不仅很少有经济学者照此行事(当然不包括萨缪尔森本人),而且萨缪尔森说的和做的也明显不一致,他的国际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也从公认为明显违背事实的理论假定推论出明显重要的现实世界的结论(Machlup,1978,P.482—483)。(2)他的后期的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不仅过时,而且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与通过揭示深层的、内在的、不能直接观察的因果机制的科学常识观相悖(Hausman,1992,P.157)。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哈奇森和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假设前提的极端经验主义要求导致对诸如“企业是否设法最大化预期利润”的检验(Lester,1946),曾使得上世纪40年代后期产生了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缺乏经验主义的担忧,并最终导致逻辑实证主义退出了经济学的舞台,因为弗里德曼和马克卢普使大多数同行相信:“直接证实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假定既无必要又会使人误入歧途”(布劳格,1992,第133页)。(11) 从上述分析看,虽然两种实证主义存在不同,(12)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即科学就是如实地描述,并将非描述性陈述——在它们不是逻辑——分析陈述的范围内——从知识和科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但是仅有描述或归纳的方法无法建构一门科学。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而从历史学派的现实人出发只能回到孔德的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总之实证主义用以规范经济学的企图并不成功,也无法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方法论辩护。(13) 四、当前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及困境 对于实证主义的失败,逻辑实证主义的后继者——逻辑经验主义,努力消除实证主义对理论的轻视,将科学理论的结构从实证主义的归纳的观点转向假设演绎法(14),以消解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鸿沟。虽然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科学哲学界攻击而衰落(15),但依然是科学哲学的主流和“公认观点”(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当然忽视理论的情况并非完全适用于经济学,至少哈奇森和萨缪尔森没有否定经济理论,只是他们对理论的功能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呼吁经济理论应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另外,尽管弗里德曼和后来的哈奇森、萨缪尔森的实证经济学并不相同,但其实质都在向逻辑经验主义靠拢(16)(考德维尔,2007,第393页),而非将其视为批判经济学的工具(考德维尔,2007,第242页)。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代表性人物马克卢普同萨缪尔森和哈奇森的观点也不相同,但却同他们一样完全拒绝了穆勒传统的演绎法(Hausman,1992,P.159—160)。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基础理论需要做的不过是通过推理出正确的可观察的结论以证明其有效性。这样经济理论的实证重点也就放在结论的证实,而非假设的证实。例如,当前经济学学术论文的标准程式是:引言—模型—经验检验—结论,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趋势。(17)对此布劳格曾慨叹道,“现代经济学家经常满足于证明现代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布劳格,1992,第253页)。 虽然主流经济学实质上遵从的是逻辑经验主义,但是到20世纪70、80年代,当经济学方法论者在批判或捍卫经济理论的经验主义和重建经济学时,更多地依赖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而非逻辑经验主义(Hausman,1992,P.171)。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1)肯定后件在逻辑上没有意义,因为证实无法确认一个命题的正确性,而否定后件在逻辑上却是正确的,因为证伪能够对检验命题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作出判断;(2)通过不断试错的证伪过程,最终能够得到接近于事实真相的理论;(3)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的知识命题才是科学的,证伪则放弃,证实则暂时接受。哈奇森早在1938年就将证伪主义思想引进到经济学(Hutchison,1938)(18),后来的萨缪尔森成为了实质上的波普尔证伪主义者(19),弗里德曼自称是波普尔的信徒(弗里德曼访谈录,载于斯诺登和文,2009,第180页)。因为主流经济学者对不能进行明确预言的理论并不放在心上,他们最终是根据精确预言的成功评价理论的,所以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实际上均认同证伪主义方法论(Blaug,1992,p.xiii)。(20) 这样,主流经济学中的实证实际上指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加证伪主义,这两者构成经济学方法论中“公认观点”最为常用的含义(汉兹,2009,第77页)。但是这种主流的方法论不仅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缺陷,而且也无法为危机时代的主流经济学提供辩护。 就逻辑经验主义而言,其方法论缺陷主要在于不充分决定性、观察带有理论负荷两个方面。所谓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是指“所有可能的观察不足以单独地决定理论”(Quine,1975,P.313转引自汉兹,2009,第108页)。例如,从理论T和辅助假设或某些背景知识H∧C推出结论或预言E,如果E成立,则T和H∧C成立,如果E不成立,并非必然意味着T错误,因为也有可能是H∧C不成立。这意味着理论T的成功不能完全依据经验的检验。在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总是导致最佳社会福利”的结论,如果E成立,例如某时段失业率处于充分就业水平,是否能证明该理论正确呢?因为所有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都存在垄断、外部性、大量的政府干预和私人的勾结等(博兰,2000,第173页)(21),即证伪了辅助性假设或背景知识,所以肯定该理论成立的答案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E不成立,如存在非自然失业,是否能证明该理论错了呢?实际上该理论的提出者Arrow(1967)就曾将新古典价格理论不能解释诸如失业等宏观经济现象视为“羞耻之事”。如果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答案就应该是否定的,但现实中经济学者并没有否定一般均衡理论。这说明,对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说,逻辑经验主义的肯定后件方法并不适用,甚至经济学者更为经常地认为,纯理论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布劳格,2009,第553页)。所谓的理论负荷(theory-ladenness)问题是指所有科学资料都要有理论的指导,没有“脱离理论”的经验。对于经济学来说,理论负荷意味着经济事实是语境依赖的,例如主流经济学中讨论的问题通常是在新古典的语境中,依赖于个体理性与完善市场等条件。正因为如此,经济学者都认识到,一切事实也都渗透着理论(波兰德,2008,第5页)。在这种情况下,逻辑经验主义者就面临着缺乏完备经验基础的纯经济理论(或基本原理)如何得到辩护的问题。 鉴于波普尔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理论负荷和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同时也鉴于两者之间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如理论由数据“不充分地决定”和数据由理论“多元决定”之间并无多少区别(汉兹,2009,第117页)(22),加之主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者并没有否定经济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前文关于经济学中基本假设的经验基础之争等因素,使得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只能以证伪主义而非逻辑经验主义为经济学辩护。但证伪主义方法论也存在以下缺陷(汉兹,2009,第302—311页):(1)波普尔对不充分决定性、理论负荷和科学经验基础的可错性问题采用的约定主义式的回应,既能用于证伪,也能用于确证,从而破坏了用反驳代替证实的整个证伪主义计划(Hausman,1992);(2)证伪主义既具有声名扫地的经验论基础主义的特征(波普尔是一个否定后件式的实证主义者),同时又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3)大胆猜测严格检验的证伪主义方法可以发现错误,却不发现真理;(4)证伪主义同波普尔所赞同的理性原则和情景分析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相协调。这些缺陷意味着证伪主义方法论在捍卫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例如在证伪主义者布劳格看来,一般均衡理论没有且永远也不会有经验性的内容,注定会彻底失败(巴克豪斯主编,2000,167、169页)。对此他特别抱怨道,“现代经济学者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却很少付诸实践”(Blaug,1992,P.111)。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者都没有鼓吹过要严格运用波普尔—萨缪尔森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Boland,1989,P.10),更多对证伪主义的批判还可参见Caldwell(1982,P.236—242)和Hausman(1992,P.188—191)。(23) 下面结合此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最新问题讨论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新挑战。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假设演绎法,预测结果没有出现可通过修改或调整假设来完善理论。但是如果最核心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受到证伪的话,那么是否应该要抛弃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呢?Cheng et al.(2014)研究结果显示:此次经济危机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理性,特别是证券经纪人并不比随机选出、对楼市一窍不通的律师构成的“对照”组能更清醒地认识到房产泡沫的出现和自己所持有房产的价格即将崩盘,前者在楼市中的亏损实际上要大于后者。该文就此表明,经济学假定人是了解一切的“理性”经济人是错误的。对于这种情况,逻辑经验主义仅用“假设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预测的准确性”之类的托词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一则理性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经济主体寻求其自身的物质福利是经济体系运转的原因,而缺乏这一动机的理论就不再是经济学了”(Hausman,1992)。二则,经济学家的经验预测在数量上很少,从来不很具体,也不十分准确,“在预测上是虚弱的”(Rosenberg,1992)(24),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证伪主义采用约定主义(25)的免疫策略,即将其视为是无法检验的理论起点(Popper,1994),但是这种方法论策略也无法为经济学理论提供辩护,因为它必然导致“约定的证伪”(Hausman,1996)。另外,对于市场充分有效性结论的否定,证伪主义采取抛弃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肯定不会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同。 综上,在核心假设和基本结论均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不应该是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对此,Hands(1990)就曾总结道:主流经济学和实证主义无关,因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原理的前提假设、结论或预言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 五、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的实证:回归凯恩斯 综上,无论孔德的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还是逻辑经验主义或证伪主义,均无法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供方法论辩护,也无助于主流经济学应对现实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回归穆勒传统的凯恩斯实证方法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可行选项。 1.穆勒传统可以从经济政策角度捍卫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 按照穆勒传统,不能直接基于“实证”经济学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无论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还是韦伯、罗宾斯等均是如此。作为经济学界首先使用实证与规范之分的经济学者(Blaug,1998,P.371),凯恩斯认为,实证经济学的功能是“观察事实,发现事实后面的真相”,提出关于事实的本来面目的定理(theorems),而不是描述生活的规则和现实生活的实际规范(practical precepts),它是立场中立的(凯恩斯,2001,第8、22页)。为此他特别辨析了经济学与当时流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的关系。他认为,从理性基础出发,政治经济学与自由放任之间并没有实证性的联系。“自由放任是一个现实准则,而不是科学教条,不能把它看作是不可动摇的、最终会受到验证的公理。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古典经济学者均是把它看作一种现实的结论,其效力如何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凯恩斯,2001,第47页)。(26)也就是说,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判断、政策主张和科学研究(是什么)并非完全是一回事(虽然两者相互影响)。但是现代经济学者很少真正地遵守这种方法论的约束(Colander,2005),受弗里德曼方法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把现实规则同经济学规律混同起来,似乎无须加入研究者的判断,直接基于理论就导出政策,特别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值得受到广泛的赞同,对“应该是什么”的回答有赖于“是什么”。(27)对此,科兰德(载于巴克豪斯,2000,第53页)就批评道,这种半正式的理论和半正式的经验性工作,导致了大量的混乱,并形成一种将适用于创立理论的方法论应用于应用政策工作中去的趋势。因此直接基于纯经济理论而主张自由放任政策是错误的(28),是将自称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否定不是对主流经济学原理的否定(胡明、方敏,2009,2011)。 2.穆勒传统捍卫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此次经济危机以来一个知名且重要的争议,即“90%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一个临界值(若高于90%,经济增速就会骤降)”的观点(Reinhart and Rogoff,2010a,2010b),就是明显忽视理论研究造成的后果。不仅这一研究的统计数据的加总计算遭到了指责(Herndon et al.,2013),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债务与GDP之比和经济增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也遭到了质疑。即使两者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也不能说明现实中两者之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要说明这种因果关系,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理论(29),可是目前的经济学并没有建立基于经济主体行为方程的最佳债务水平的理论。从本质上讲,这种研究类似于历史学派的研究方式,缺乏理论推理。仅仅基于经验总结和历史归纳法不仅容易受困于表面现象(通过数据不可能揭示出真正的因果关系),容易犯偶然概括的错误(没有充分意识到理论推理在纠正问题中起到的作用),而且也无法运用已有的知识(包括理论),更不能独立地建构新的理论。 前文谈到,穆勒传统的演绎法或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为建构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通过理想化假设建构经济理论,促进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并最终指导经验研究。这种指导作用可分为:定向,分类,概念化,概括,使思考过程具有准确性,预言事实或识别假设,识别认识上的差距等(埃思里奇,2007,第66页)。如果没有经济理论,这些作用是无法发挥的。(30) 理论研究不仅重要,而且也可分为不同类型,各有其用。例如凯恩斯就将经济理论分为抽象理论和具体理论,其中抽象理论研究的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效用、财富、价值、资本等,它的“方法几乎完全是推理的和假说性的,尽管它最终依赖对事实的观察,但它却出于人为的对事实的简单化处理。其结论在一定意义上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它们自身总是不完备的”,因此还需要具体经济理论进行补充。具体经济理论的法则或者来源于对经验的直接概括,或者来源于演绎方法的应用,主要指的是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手段”(凯恩斯,2001,第89—90页、第106页注释24、第199—200页)。一般来说,抽象理论的目的在于启发和导向,建构分析框架,不强调最终是否运用于实践,故主要使用演绎法;相反,具体理论的构建目的在于指导和运用于实践,强调经验的可证实,更强调运用归纳法。从事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分析的分工,进而采取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旨趣的不同。例如穆勒《论文集》的方法理论就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实践性内容明显不同,前者的“经济人”概念具有核心作用,而后者中这一作用就不值一提了(J.N.凯恩斯,2001,第11页)。这意味着,以可检验性为依据来界定理论不同于以知识价值为依据来界定理论(Simkin,1993,P.16,转引自埃思里奇,2007,第65页)。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抽象理论相当于微观经济学原理,而具体理论则是基于这种原理而建立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如管理经济学、各种具体的市场理论等。前者从理想化的假设开始,如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完全竞争、无交易费用等,通过建构一个纯粹的市场交易机制,从中推理出微观个体最大化行为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命题,由此经济学者能够认识微观经济领域的某种因果联系,形成相对清楚的理论体系。这一原理的功绩在于由其推理出来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其界定的因果关系规律,既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又可作为更加深入和细致研究的基础,或向现实环境过渡的中间环节。但是一旦把经济学原理运用到具体场合时,就必须考虑这一场合中的“干扰条件”(它是复杂现象的本性所固有的,也是建构理想模型所忽略的)。由于“干扰条件”的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经济研究的结论可能存在不一致,因此建构应用经济学理论也就具有多样性。这种分类型或分层次的理论可以更具包容性地捍卫不同目的的经济研究。下面分别从基本经济学原理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讨论穆勒传统在捍卫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有效性。 3.穆勒传统有助于捍卫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科学性。 按照穆勒传统,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可接受标准在于: (1)核心假设(不包括其他条件相同等假设)是真实的或有经验基础的。前文谈到,古典学者的经济人假设(追求财富的动机和行为)是实在的或有经验基础的。对此,瓦伊纳认为,“内省……无论它在今天可能怎样时髦,过去却普遍地被认为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技术,显然不同于直觉或‘固有的观念’”(转引自布劳格,1992,第87页)。Hands(2001)也认为,不管现代理论家如何评价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该理论的创立者(于1870年代)是用实在论的观点看待理论的。因此经济人假设的问题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而在于经济人是否理性(最大化自身利益)。实际上,理性要求仅仅是一种工具性假设,是边际革命时代经济学为了建构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推理体系,特别是运用数学工具所进行的理性化的建构,是一种分析性的工具,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可能性,其本身并非完全吻合于现实。它刻画的是个体应当如何行为(Hausman,1992)。因此不能用严格的经验标准加以证实或证伪。 需要注意的是:一则,弗里德曼的“理论越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的观点,对于经济学原理来说很明显是不正确的,这会导致将经济学原理理解为是无事实根据的推测,如果其核心假设完全没有现实痕迹,那么经济学原理就不能称其为经验科学;二则,无论行为经济学基于多么充足的证据来证明理性经济人的非实在性,也不能证明经济学原理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学不依赖于心理学的成功。例如韦伯就认为,边际效用理论不依靠任何特定的心理学基础,经济学的心理学假设同科学的心理学不是一回事(考德维尔,2007,第133—134页)。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没有前途,或者经济学必然要对行为金融学持怀疑态度,因为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方法和工具融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是一种应用研究。 (2)基本原理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一致性,而非其结论与经验的一致性。经济理论的结论“应通过演绎推理确认”(凯恩斯,2001,第132页)。对它评判,只能根据它的研究成效。一般均衡状态满足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的理论命题仅仅阐述的是一种可能性(趋势)(31),现实中的某些偏离,例如存在着价格刚性,不能证明以充分弹性价格作为假设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错误的。因此按照穆勒传统,此次经济危机不会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地位。弗里德曼“理论的最终检验是看它的预测能力”的观点,是将理论的逻辑混淆为理论对特定情况的应用能力(埃思里奇,2007,第65页)。 4.穆勒传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理论负荷和不充分决定性问题。(32) 穆勒通过19世纪早期苏格兰哲学家Dugald Stewart的著作就已经知道了“不充分决定性论题”(De Marchi,1983,P.174,参见汉兹,2009,第106页),他最早指出了某种带有波普尔证伪主义式的问题,即不管观察到多少数目的白天鹅都不允许做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推论,因为观察到一只黑天鹅就足以驳倒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结论(布劳格,1992,第16页)。杰文斯在他的《科学原理》(1877年)中也讨论了现在称之为迪昂—奎因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Schabas,1990,P.73,转引自汉兹,2009,第106页注释)。凯尔恩斯谈到的归纳方法的“完全不充分性”问题和凯恩斯谈到的“经验方法的局限”问题时,都指出“不要相信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归纳方法”(凯恩斯,2001,第133—134页)。这些古典学者不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在他们的方法中,经济学求助的是“从人类本性基本原则出发的演绎”方法,推导的是有条件成立的趋势性预言,且不依赖于经验结果的验证,从而使经济学原理避免了“不充分决定性”问题。 另外,穆勒传统的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理论负荷问题。穆勒(密尔,2009,第103页)曾说道,“没有其他人能意识到不同事实的相对重要性,也就不能知道要寻找或观察什么样的事实,更不能评估事实的证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据不能靠直接的观察得到确定,也不能从明证中了解,而必须从符号(marks)中引出。”凯恩斯(2001,第185—186页)认为,“经济世界的因果性知识(理论)给我们提供帮助,使我们能够将那些特别被关注的事实与其他更难观察的事实区别开来。”他还特别引用杰文斯的观点认为,科学观察的注意方向应该受到理论预测的引导。因此,为了解释经济现象,熟悉经济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另外韦伯也认同事实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因为所谓的经济事实反映着经济学者自己事先就有的兴趣。这种观点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哲学常识,和波普尔、库恩、奎因等的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的主张相似(考德维尔,2007,第106—109页)。 5.穆勒传统也可为应用经济研究提供辩护,并能够和当今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相融合。 在穆勒传统看来,虽然基本原理不可动摇,但其没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因此需要根据基本原理预测偏离情况,考察不同干扰性因素的作用,考察影响经济现象的其他因素的个别修正作用,建构基于不同条件不同干扰因素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应用理论(这意味着应用经济学必然存在理论负荷问题)。应用经济学理论,即凯恩斯眼中的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必须依赖环境(凯恩斯,2001,第7章)。一方面,由于应用理论隐含在基本原理之中,故不再重视基本原理核心假设是否实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现实,因此需要采用归纳法,检验结论或考察其预测的准确性。(33)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应用经济理论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预示着应用经济学存在不充分决定性问题,但也意味着需要在各种应用理论中,选择预测更准确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应用经济学家要比学科经济学家更重视经验证实”(Eichner,1986,转引自埃思里奇,2007,第65页)的原因,也是穆勒传统能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同逻辑经验主义的假设演绎法相融合的基础。 关于假设演绎法,穆勒在1843年就已说明了假设—演绎模型(布劳格,1992,第6页),J.N.凯恩斯是假设演绎法的真正建立者(道,2005,第94页)。他们在应用经济学领域都接受假设演绎法(34),这样就和逻辑经验主义在应用研究中没有本质的不同。(35)对于应用经济理论来说,其结论在经验上的可检验性仍是科学的最低要求,需要找到最接近于现实的经济理论,否则,经济科学的现实意义就无从谈起。这种检验不仅有助于对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论进行选择,也有利于更科学地制定政策。如果经验的预言失败了,不应该抛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不意味着其他应用经济理论是错误的,而应尝试建构更适合的新的应用经济理论。即使多数经济学者没有预测到此次经济危机,更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强度,也不意味着应用经济学者不应该进行预测或对未来趋势进行判断,相反它会促使经济学构建更具预见性的理论。因此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逻辑经验主义方法仍可提供方法论的指导。(36)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方法论领域常常将弗里德曼归类为工具主义者(汉兹,2009,第256页),或者是实证主义者(Hausman,1992),或者按其自己所称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者,但笔者认为,更合适的称谓应该是J.N.凯恩斯方法论的追随者。首先,弗里德曼1953年的著作是在凯恩斯的实证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文中不仅以凯恩斯的实证与规范二分法开场(37),而且也认为建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从造成经济现象的某些持续的主导力量着手;其次,他像凯恩斯一样区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描述方法和分析方法。弗里德曼1953年的著作主要回应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人假设的经验要求,他对描述主义方法的嘲讽,对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对古典经济学攻击的反驳(认为其将描述方法追求的准确性与分析方法追求的相关性的不同混淆了),同凯恩斯对历史学派相关观点的回应如出一辙;再者,弗里德曼将理论的预测准确性置于优先地位是为了选择可用的理论,而非否定了凯恩斯的实证方法。应用理论的构造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预测,而预测的目的在于确定理论是否可用及如何应用,而非证明理论的对错(这种观点弗里德曼是完全同意的)。(38)虽然他未像J.N.凯恩斯那样区分了抽象理论和具体的理论,但他的理论明显指的是具体理论,而非抽象理论(他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动机)。另外凯恩斯(2001,第149页)认为,在具体理论中构造与实际事实无关的假设有时是有用的,这和弗里德曼的“假设的非实在性”命题不冲突。当然由于他未能区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经济理论,也未能区分假设的不同类型(Musgrave,1981),因而易于造成误解。如果将他的方法论观点置于凯恩斯的应用经济学背景中,他的“理论越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的观点也就不是那么极端(39);最后,弗里德曼关于由实证经济理论得出政策建议的观点,如果放在凯恩斯的具体经济理论的背景下,也并非完全不一致(这一点仍可进一步地分析)。总之,弗里德曼的实证方法与J.N.凯恩斯实证方法的共同点远大于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共同点。 六、结论及启示 总之,相比于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穆勒传统的凯恩斯实证方法不仅有助于建构并捍卫新古典经济学,而且更具包容性,有助于经济学走出后危机时代的困局。其基本原理的肯定前件逻辑(前提的归纳确定)和应用理论中的肯定后件逻辑(结论的归纳证明)一起构成了凯恩斯(2001,第149页)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始于观察并终于观察”的科学范式,从而从终极意义上确保了“实证”经济学的经验基础。这样,具有科学实在论特征的经济学原理揭示了关于经济现象的不精确趋势,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独立发展,而建基其上体现着工具论特征的应用经济学强调更准确预测,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核心依据,确保了经济学的有用性。因此回归凯恩斯实证,仍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应该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当然穆勒传统并没有给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虽然穆勒传统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最好的描述(Hausman,1994,P.205,转引自汉兹,2009,第331页),但它能否为J.M.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提供方法论指导仍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近期争议的几点启示:1.经济学原理是普世的,通行的,不存在只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的作用在于启发和引导,而不是制定政策;2.因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的不同,建基于原理之上的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和服务于制定政策的具体理论可以有所差别;3.中国经济政策成功的奥秘在于制定政策依据的是归纳法(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不是演绎法(本本主义)。 作者衷心感谢刘元春教授、方敏副教授的修改建议和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 ①经济学者很容易将“实证经济学”同实证主义的实证联系起来。参见左大培(校订者的话,第3页,载于米塞斯,2001)、道(2005,第193页)、博兰(2000)。 ②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vus,原意是肯定、清晰、确切的意思。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中使用“实证”一词,主要针对16世纪以来实验的自然科学而言,即科学强调观察、实验,要求知识具有确定性和可证实性,与空洞、荒诞的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穆勒深受孔德的影响,他和他的弟子凯尔恩斯将科学作上述区分有其合理性,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经济学无法进行受控实验。 ③当然德国历史学派并不认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其国内的历史主义哲学的影响(熊彼特,1994,第3卷,第92页)。 ④现代社会科学划分成不同的独立学科不超过一个世纪,大部分其他社会科学的建立晚于经济学(Wallerstein,1996)。 ⑤按照汉兹的观点,在穆勒看来,几何学仅仅是在通过归纳从经验观察中得出公理的范围内才构成知识,这种经验论比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的经验论更强硬(汉兹,2009,第24页注释)。后来穆勒不再将这种研究方法类比于几何学,而是类比于天文学(密尔,2009)。 ⑥经济学关于先验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先验就和约翰·穆勒的先验不同,前者认为的先验不能来自于经验观察,而后者认为这种先验具有经验论属性,但也有理智论的成分,如不认为所有人都按获取财富的动机行事,只是对主要事实的抽象建构(汉兹,2009,第26、48页)。 ⑦从当时经济学的实际进展来看,就像凯恩斯所说,他的著作第一版在1890年出版时,英国的抽象方法和德国的具体方法的争论已渐渐和缓(凯恩斯,2001,第19页注释9),这种融合了归纳和演绎、具体与抽象的实证研究方法已不再少见。例如庞巴维克(1981,第36—38页)在1888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就已试图从经验和抽象两种方法相结合的角度建构他的资本理论。 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真理,它的命题是综合的,且只有在某些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和数学的纯粹形式是分析真理。形而上学,如宗教或唯心主义陈述等所有非经验(非综合)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⑨按照描述主义的观点,科学理论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仅是对以某种记录观察现象的记录语言。记录句构成了科学的最终基础,所有科学陈述要么以其表达,要么通过所谓的对应规则还原为记录句。观察证据可最终确定句子的真值(汉兹,2009,第82—83页)。 ⑩很明显萨缪尔森未能厘清穆勒传统和奈特、奥地利学派在先验方法上的区别。不过,哈奇森并没有批判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实证”,其矛头仅仅针对罗宾斯和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11)弗里德曼观点的评论将在后续部分详谈。马克卢普区分了理论的基本假定及其条件。对于基本假定,如消费者能始终如一地进行偏好排序和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进行独立检验不仅没有必要,甚至令人误入歧途,因为这是一种理性化的建构。即使它是虚妄的,也未必需要抛弃理论,除非有更好的替代理论。对于基本假定的条件,则必须符合可观察的要求(Machlup,1978,P.147—150,参见布劳格,1992,第113页)。 (12)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崭新的数理逻辑作为其分析工具和秩序原则,而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中,逻辑和经验主义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再如孔德的实证主义者的感觉、经验和思想之分析被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语言(借之可以描述感觉、经验和思想)分析所取代,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工具(哈勒,1998,第21—23页)。 (13)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一无是处,其推动经济学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宏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仍功不可没。 (14)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假设演绎法,科学理论从个别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后形成假设(其真理性尚有争议),经演绎推理,形成理论(已非原本的观察)。因为只有科学理论的演绎结果才与它的经验支持相关联,通过将预言陈述和经验比对,判断假设是否为真或可接受(汉兹,2009,第92—95页)。 (15)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萨蒙认为,甚至今天的许多哲学家都把逻辑经验主义视为顽固的且已过时。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混淆了逻辑经验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牛顿-史密斯主编,2006,第290页)。 (16)不论是哈奇森还是萨缪尔森均已从过去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了,例如哈奇森关于可检验性的论述是否涉及假定总体上看相当含糊(布劳格,1992,第101页),萨缪尔森也对“是否仅仅因为已知一项理论的种种假定并不现实而就应当抛弃”的问题闭口不谈(布劳格,1992,第116—117页)。另外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关于“F—曲解”的争论并不存在重大的方法论差异(布劳格,1992,第118页),同样两者关于解释与预测之争也不意味着他们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并没有绝对地排斥解释或预测(道,2005,第72—73页)。 (17)这种研究方法同样推动了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使得应用研究不再关注于假设的实在性,而重点关注结论的可证实性或预测的准确性。 (18)他的思想体现的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三种哲学思想(参见汉兹,2009,第54页)。 (19)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要求是经验性的,自然具有可证伪性。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Samuelson,1964,P.736—740)。 (20)按照汉兹(2009,第301—302页)的解读,证伪主义在经济学界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证伪主义似乎可以满足经济学方法论提供研究规则的要求,即提供了同时具有严格性和简单性的规则——科学理论“必须可以被至少一个经验上的基本陈述证伪,经受住了最严格的检验的理论就能得到最多的支持和最大的偏爱”。 (21)博兰曾经将这种实证经济学的隐秘目的总结为“在于长远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正确,因为既有的研究均在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并讽刺性地指出,20世纪50—60年代多数实证主义者也都是在J.M.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干预的(参见博兰,2000,第173—175页)。 (22)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不受污染的观察,所有的观察都是根据理论的指导进行的观察,理论和观察之间没有“天然的”分别(汉兹,2009,第101页)。 (23)波普尔传统还有两位追随者,即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和博兰的批判理性主义。对于前者,无论是从获取知识的角度还是避免错误的角度其方法论有着明显的缺陷(dramatic flaws),它既是获取知识的劣质工具,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无效的(Hausman,1992,P.203204)。对于后者,博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接受对新古典理论内在的方法论批判”(Boland,1997,P.286,转引自汉兹,2009,第330页)。在此,笔者关注的不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是否应该接受方法论的批判,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解读新古典经济学。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对这两种追随者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评价。 (24)在罗森博格看来,即使经济学“充其量只能做一般化的预测”,但经济学仍没有“足够”的预测力(转引自汉兹,2009,第364页)。 (25)约定主义主张,科学理论就像描述性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是科学家创立的一种约定,可用来组织经验数据。通过约定论既可避免认识过程中的纯主观主义的东西,又能选择出较好的理论。详见博兰(2000,第139—141页)。但约定论并不符合实证主义的主张,即概念应该是真实世界的表象(Gordon,1991,P.610,转引自波兰德,2008,第16页)。 (26)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讨论历史问题,这也是他谈论政策问题的依据。 (27)博兰和多数反对弗里德曼方法论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试图拒绝承认“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二分法,反对规范经济学而只赞成实证经济学(博兰,2000,第153—157页)。另外弗里德曼晚年对其观点不再那么自信了,反而倾向于认为,人们的政治倾向决定其实证观点,而不是实证结论决定政治倾向,因为对他的科学观点提出批评的人,似乎更多地是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受客观判断的驱使(弗里德曼,2004,第297页)。 (28)例如哈奇森就对米塞斯试图用经济学理论维护经济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考德维尔,2007,第240页)。 (29)要建立理论体系,必须要使逻辑演绎的起点建立在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或行为方程之上。无论是历史学派,还是(Reinhart and Rogoff,2010a;2010b)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纯粹的统计指标分析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肤浅的,无法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 (30)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负荷问题的根源所在。 (31)对于趋势预测,哈耶克认为,对于许多社会现象,特别是市场机制,经济学充其量只能做到解释它们的运行原理,而对其进行准确的预测永远无法做到,经济学只能提供模式预测(考德维尔,2007,第405—406页)。 (32)这些特征体现了某种“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则,因此一定程度上说,经济学的穆勒传统和当今所谓的“后实证主义”哲学拥有一定的共同点。 (33)凯恩斯在谈到统计学的作用时说道:“除了绝对地增加经济知识外,其作用还包括检测和修正演绎前提,检查和证明演绎结论,测量干扰项的影响等”(凯恩斯,2001,第226页)。 (34)可能由于Hausman(1992)没有区分抽象理论和具体理论,所以他从演绎法的角度批判了假设演绎法。 (35)Johnson(1986,P.82,转引自埃思里奇,2007,第47页)认为,批评经济学家不是严格地利用数据来证实或检验理论,更多地是针对经济学的学科研究(基本原理),而非学科内各领域的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 (3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学者经常将“empirical”一词译为“实证的”,虽然在这种语境中不算错误,但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经验的”。 (37)按照熊彼特(1998,第229页)的解读,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0年)“能在有关它的种种问题的半个世纪的争论中保持其中心地位,使得直到现今(即弗里德曼写作其方法论著作的时代,本文作者注),学习方法论的学生还不得不选它为指导书。” (38)考虑到弗里德曼“理论不可能被经验事实所证实”的主张,他的证伪不是用来批判理论的真实性,而是用于界定理论的适用范围的观点,至少本文对弗里德曼的实证方法的定位不应该让人感到惊奇。 (39)弗里德曼是在应用经济学背景下谈论“理论假设不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同的理论,当然只能是以“经验预测时哪一个最为成功”为标准,其辅助性假设的“不现实”,不会影响理论的成功。标签: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萨缪尔森论文; 证伪主义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