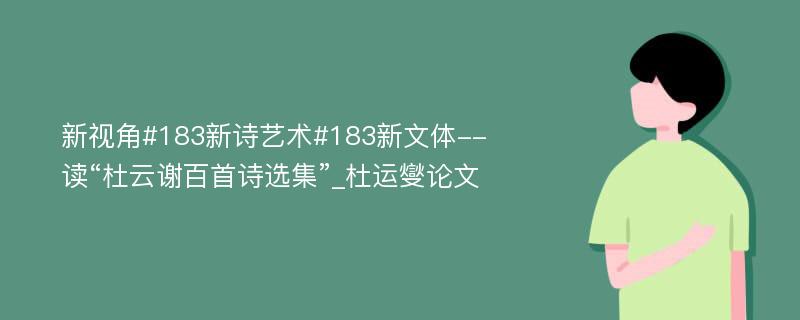
新视角#183;新诗艺#183;新风格——读《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新视角论文,新风格论文,一百首论文,杜运燮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以来,我断断续续地诵读杜运燮的诗作,从40年代的《诗四十首》、80年代的《晚稻集》到1995年的《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我为他的坚持执着的努力和卓然可观的成绩感到骄傲,而且私下也不无欢喜地回忆及早在1947年5月我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里就确认他是40年代新诗现代化运动中的先锋之一。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运燮已经以实绩证明他在现代诗坛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一个以自己独特的追求新真深精的现代风格推动了新诗进程的重要诗人。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运燮的独特的现代风格,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诗艺来抒写旧的题材是其中的一个特点。40年代大家都在歌颂抗战,诉说人民的痛苦,运燮的成名作《滇缅公路》也是歌颂抗战的,但他避开了一般的标语口号的直抒方式,而是把公路放在动态中,把它写活,写它怎样“风一样有力”,“蛇一样轻灵”,写“沉重的胶皮轮不绝滚动着/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这种借物抒情的新视角和把灵性注入事物的新手法打破了几十年来直接呼喊的旧角度和旧方法,也就取得了新效果,创立了新的政治抒情诗。
这种新视角主要是拉开诗人(主体)与对象(客体)的距离,使诗人的想象能超越死的固定的物体而凌空飞腾,然后再以自己所感所思赋予客体,使它获得灵性,生动地呈现出诗人所要传达的信息。这里的关键在于拉开距离要适当,拉得太开了,读者会摸不着头脑,诗人的想象也难以沿着陆地的方式返回客体;如果拉不开距离,就粘在物体上了,诗人的想象就会飞不起来,这首诗就僵死了。《滇缅公路》的成功处正在拉开的距离很适当,作者不断地离开“路”,又不断地回到“路”,把“路”在运动中的使命感,自豪感,艰辛感,它与战士人民的血肉联系写了个淋漓尽致。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方法,而是主客体渗透,导致物我同一的境界,这在带有政治倾向的诗里特别显得重要,否则诗歌艺术就会沦为政治宣传品。
借物抒情、借景抒情历来是诗家的惯用手段,这里也有一个不同视角的问题。运燮有一系列咏物诗,其中有不少称得起是精品,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观点、新诗艺。他喜欢对事物赋予一种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但很少涉及事物的表层描绘。例如他写《山》,不是写山的崇高险峻,而是写它永远有所追求,永远不满足,“植根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的心态,这正可能折射了一位志高意远的艺术追求者的胸怀。正因为“他追求,所以不满足,所以更追求”,“他只好离开必需的,永远寂寞”。这样的视点和写法使无生命的“山”变成了精神活动的象征物,给读者以广大的探索空间,给他们很多的启发。杜运燮诗作往往弦外有音,含有丰富的启发意义,能使读者潜移默化,就在于这种新的视角使人产生新的认识,在思想上引起新的变化,这是他在《学诗札记》中说到的“诗的新能使每个读者变新”的道理。
另一篇佳作《落叶》同样是从一年年地落、又一年年地绿的树叶这一自然界的平凡景象看出不平凡的心灵活动的。作者把树看作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是“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写了又撕掉,撕掉丢掉了又写,又写,/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世界上有的是见落叶而悲秋的诗人,但很少有像运燮这样从落叶看到艺术家追求完美的心情的。
被选入中外多种诗选本的《井》,可看作是借井自比,也可看作是泛写人的性格、表白“他”对生活、对世界态度的力作。诗人表明“他”只是一口小井,“满足于荒凉的寂寞,有孤独才能保持永远澄澈的丰满”,世界只能扰乱他的表面,他将永远保持本色,“静默,清澈,简单而虔诚/绝不逃避,也不兴奋,/微雨来的时候/也苦笑几声。”
这些咏物诗的共同特点是新的观察角度和间接的抒情方式,揭示出心理深度和生活的深刻体验,语言的简洁精炼,意象的新颖准确,使它们经得起一读再读,不愧是杜诗中的佳品。
杜运燮热爱生活,关注现实,他写了一些可称为现代政治抒情诗的作品。《滇缅公路》是这类作品的成名之作,上面已提到。《追物价的人》是我过去一再评论过的另一范例。这首讽刺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的诗,采取了颠倒的写法,把人人痛恨的物价说成是大家追求的红人,巧妙在于从事实的真实说,这句句是反话,而从心理的真实说,则句句是真话。由此形成的一种反讽效果是现代派诗中特有的。运燮运用了现代心理分析手段,把隐藏在追物价者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致逼真的描绘:一则是决不能落后于伟大时代的“英雄”心理;二则是怕物价和人们嘲笑的恐惧心理;三则是唯恐自己追不上的自卑心理;四则是看见人家在飞,自己也必须迎头赶上的逞强心理。这种种心理相互作用,导致了一个荒诞结论:必须拚命追上物价,即使丢掉一切,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心理刻画的深入加强了诗篇讽刺的辛辣。
另外两首作于解放前夕的政治抒情诗,《闪电》和《雷》则表现了更多的期待人民胜利的激情,后者在方式上更直接了当些。但《闪电》仍然是从心理刻画着眼的,说它有“满腔愤慨太激烈,/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由于人们不领会它在半壁天空书写的诗行,因此它“感到责任更重、更急迫,/想在刹那间把千载的黑暗点破,/雨季到了,你必须讲得更多。”这诗作于解放前夕,明眼人一看都会领悟它的政治涵义,明白“闪电”所指,但出之这样的视角和手法,实在是一大创造,至少在我国新诗史上这是罕见的作品。它与当时流行的一般呐喊式的或训谕式的政治诗明显不同,它运用了更多的理性思维和想象力,通过对平凡题材的特殊处理,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取向,让读者在惊喜中得到了教益。
杜运燮在复出后写的《秋》,发表后引起一场关于诗与晦涩的大讨论。其实,这诗并不晦涩,而且同样是别有风味的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作者一如既往,在表达改革开放的喜悦之情时没有直抒明言,而是借相当的事物来暗示和渲染这种情绪:以鸽哨的成熟音调来提示“智慧,感情都成熟的”秋季,以反衬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文革时期);以透明的好酒,醉人的香味来烘托眼前的幸福感;最后以塔吊的长臂上秋阳在扫描丰收的信息指向未来的好日子。不少读者没有理解作者的特殊风格和写法,因而抱怨“摸不着头脑”,其实是明白如话,而且富有诗味的。
以与思情相当的客观事物,曲折而细致地表现思情的发展曲线,是运燮抒情诗的一项特技。40年代作于印度军旅的《月》和《夜》(原名《露营》)就是二个杰出的范例。《月》被安置在清凉明朗的背景中,她超越时间与风景,激起情感的普遍泛滥。接下去四节诗分别烘托四类情景:一对年青人低唱流行的老歌;异邦旅客咀嚼着“低头思故乡”;褴褛的苦力被弃在路旁相对沉默;诗人自己象失了舵的破船,后面已没有家,前面不知有无沙滩,茫茫然中他望着天,分析狗吠的情感。这四种情景都指向孤寂、愁闷和不安,一个从军异国的青年人难免的情怀。为了解脱这种心情,诗人最后说“我们在地上不免狭窄”,要学月亮的女性的文静来欣赏这一片奇怪的波澜。这样烘托暗示的抒情方式,既婉约含蓄,又深沉浑厚,达到了作者所追求的“新真深精”的高标准。
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生活体验的积累,杜运燮的诗在原来突出理性感性结合的同时,显示了加强哲理内涵的倾向。作于复出后的《火》、《只因为》、《占有》、《错误》诸诗分明是这一发展的新产品。与前期的咏物诗相比,它们表现了更多的从生活体验得来的智慧,显示了更多的辩证法观点,更全面的人生领悟。《占有》和《俘虏》都采用古典主义的双行体,以格言式警句写警世的诗歌。有些地方形象的力量相对地减弱了,但语言仍然是精炼有力的。在追求利润高于一切的商业化大潮中,诗人指出“占有”的两重性,“当你占有了一件东西,它同时也就占有了你”。例如,你有了电视,电视反过来就限制了你的视野。“因此当心啊,要选择好对象再占有,/要学会如何占有,不当俘虏当战友”。这对许多热衷于无限度消费的人们应是一记当头棒喝。这类诗很容易变成干巴巴的训诲诗,但诗人有足够的想象力,机智的锋芒和智慧的闪花去赋予它们深度和灵性。《火》是其中杰出的一首。它用三行体的形式歌颂火怎样在各种生命体上把世界燃烧得明丽辉煌,这么美,这么可爱,树,草,花,鸟,鱼,蝴蝶,萤火虫都在燃烧自己作出贡献;他也指出有的人燃烧自己就是为了冒烟以模糊自己,有的人怕自己燃烧,只剩下半死的湿烟,有的人看不见有火,哀叹世界是灰色一片。这里有诗人对生命世界的热烈赞美,也处处表现他对人世心态的深入观察。
杜运燮长有一双慧眼,常能察觉到常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一类情况是他从辩证的观点,洞察到事物的正面、反面和侧面。对于盲人,我们一般只会感到不幸和同情,但他却能看到盲人竟有一种幸福,因为在空虚黑暗的世界中,也就不存在诱惑,也就不会有什么恐怖。这样,盲人也就能赏识手杖的智慧,依赖它敲出一片片乐土,黑暗成了他的光明,他的路。我想,不仅盲人会感谢运燮的鼓舞,连视力正常的人们也会从这里得到一点启示。
我读运燮的诗,每每为他这种洞烛事物隐微的机敏、眼力所感动,他对生活的热爱、世界的关切所导致的对万物的普遍关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一种现代诗中少见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欣悦之情,一种奋发上进的快乐。这与和他齐名的穆旦诗的情调很不相同。穆旦的诗充满苦难、矛盾和抗争,气度肃穆深沉,有时不免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运燮的诗则轻松明朗,光采照人,机警和智慧成为他的底色。有人称之为“顽童和智者”,也许有其道理。这使他在70岁生日之际,写出《最后一个黄金时代》这样鼓舞人的作品。我们读惯了叹惜老衰之苦的诗篇,读到这首诗却突地奋发起来,原来这个黄金时代,时间虽是最后一个,却又比童年、青年、壮年更加宝贵,因为衰老的只是外表,“心/你不想老就不会老/仍然能流出汨汨春水/把你的眼光/灌溉得春意盎然”;何况老年也有它的优势:可以自由设计时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培育出信心的新叶/督促你要善于/种植新的绿色街树”;记忆中虽多创伤,但“中枢仍然清醒,保持乐观,只因为/相信民族的记忆/不会老化和健忘”;一个人自幼到老,还要接受一次写结论末句的难度最大的挑战,以新装备去攀登新高度,迎接值得一搏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
正是怀着这份难得的信心,杜运燮在改革开放的新年代展开了他那闲不住的诗翼。他欢唱爱情,《我们相逢在秋天》,这是一首精纯朴素的情诗。作者运用他熟悉的对照法,以属于季节和年龄上的秋天与心情中的春天相对比,“我们相逢在难忘的秋色里,/却忘了秋天,只谈春天,/连不远的冬景也抹上暖色,/说秋声的主题是红叶的火焰”。连情侣们常去散步的河边、黄昏也成了清晨,“无边的红霞为它喝采/为它画上特大的花环”(《黄昏,散步在河边》)。这时,他的视野更开阔了,转向民族的历史和异邦的故乡。他歌颂古丝路的历史功绩,更赞美新一代的中华儿女以前所未有的活力,用前人梦想不到的色彩和声音,日夜吹奏这庞大的寥寂,叙说着更加迷人的新传奇。1992年3月他重访马来西亚出生地实兆远,写出了一组充满热带风光和椰花蕉香的诗,他欢呼“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在我心中,永远有一尊闪着乳色光芒的雕像”。爱国怀乡的炽烈情绪使他的风格呈现了更多的开朗和亮色,但他并没有放弃冷静的深沉的哲理思考。《小河静静地流》诉说他与老伴常去散步的一条小河如何把他带入沉思,给他新的心灵颤栗和净化。这里的小河实际上是生命之河,那流不尽的不只是水,而是理不尽的智性与感性的变化和继承,是不会衰老的欢乐和月光的温柔,也是那爱雾的哀愁和多义的哲理;小河中流不尽的还有微风的漫游,白云的远航;小河只是静静地流,轻轻地流,执着地抒写着永写不尽的追求。
运燮似乎特别钟情于水,他写西湖,颐和园游泳,写大海。《乐水》一章道出了他爱水的变化多端,在各种境遇下作出反应,象挥洒自如的大手笔写出绝妙的作品;他说乐观是水的性格,它乐观,因此能在逆境中默默地摸索坦途;它乐观,所以才清彻;它乐观,所以才青春常在,因此富有历史感,总是充满信心。这几乎是在宣示诗人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水,历史,都乐观/天天都在提醒/因此,我也乐观”。
杜运燮作为一位现代诗人,从40年代起在诗艺上不断求索,一贯追求新真深精的高标准,他融汇中外优秀诗艺,特别是我国唐诗和西方现代派诗的卓越成就,与40年代的其他诗人共同创建了我喜欢称为中国式现代主义的风格,一种把现实、象征和机智因素结合起来的诗风。它是现代主义的,因为体现了现代人的感性和理性的融汇,吸收了西方现代诗的技法;它又是中国式的,因为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时代脉搏,借鉴了我国古典诗和现代诗的艺术。在同时崛起的一群诗人中,他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在现实、象征、机智的结合上他有出色的表现。他的诗,不论是反映国家大事,抒写个人心情,描绘自然景色,歌颂或讽刺,都表现出对对象的深入观察,对哲理意义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升华,机敏智慧的闪烁,使你感到有所触动,有所领悟,有味道,有情趣。事物在他的笔下,有了灵性,平凡的景象呈现了非凡的意蕴。
运燮在《自画像速写稿(二)》中说:“追求真、新、深、精,爱朴素/向往古今中外精华的结合”,又在《学诗札记(三)》(见香港大公报·文学,1997年11月26日)中进一步说,“后来才渐渐悟到新,才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因为真情实意早在那里,没有新视角,就不会有写诗的激情。“新,就是创新,新颖,有新意,有新解释,就是立意新,题材新,构思新,视觉新,意象新,手法新,形象语言新,有时代的新气息,有诗人自己的独创性,独特风格等等”。这是个很高的标准。验之于他的一部分成功的作品,他是达到了的。特别在立意新,视角新,意象新,手法新诸方面,上文已举过不少例证。
在提出“新”从何来的问题后,运燮回答说:“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都离不开旧的基础,也就是历史传统,民族基因,离不开从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从诗歌历史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从异国异地移植吧,也必须移到本地土壤,与旧的基因杂交,才能存活、生长发展”。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我为什么要称他为杰出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人,因为他的创新虽然吸收了西方奥登、里尔克的优秀诗艺,同时又是结合了他对唐诗宋词的学习和对本国三四十年代的卞之琳、冯至等诗人的借鉴的。运燮讲究练字造句,注意节律整齐,运用远取比和隐喻,追求奇惊的意象等等都是中西诗艺融合的结果。他还警告人不要为新而新,避免过分造作、意象过密,跳跃过速等等毛病。
作为有过几十年创作实践而且有了卓越成就的老诗人,杜运燮总结他的经验说:“我学写诗也有意识地把自己培育成一棵杂交品种的植株。是古典诗词传统与新诗传统,中国诗与外国诗,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广义的)等等的杂交,注意吸收古今中外各种风格名作的优良基因,避免成为‘近亲繁殖’,‘克隆诗’,基因老化的植株”。据我所知,运燮很少发表诗论文章,这里所引的议论实在是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对有志于新诗复兴的人们不啻是金玉良言。
诗人今年已届80高龄,还在兴致勃勃地从事创作,不久前写出了《一个七九老人庆九七》,荣获香港《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合办的迎香港回归诗歌竞赛一等奖;最近又完成了《西南联大赞》,参与了北京大学建校百年纪念活动;去年他和张同道先生合编了《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不久又将推出《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证明他依然“热爱生活,不断求索”,谨以此文祝愿他健康长寿,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