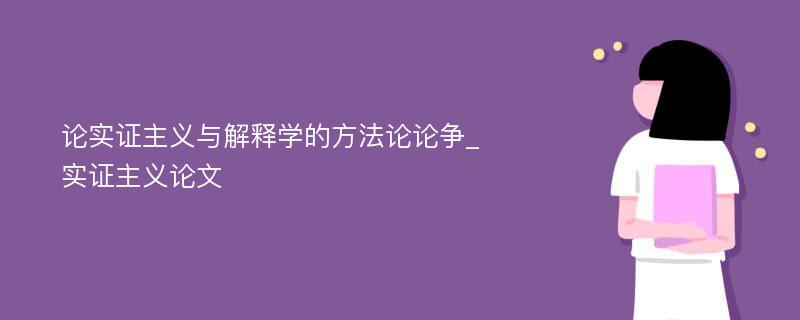
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解释学论文,实证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由来已久,这一争论构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重要事件。虽然实证主义和解释学并非两个各自完全统一的整体,它们各自的内部依然存在不同的取向和声音,不过此种历史的多样性并不妨碍我们关注两者之间最具影响力的主要争论,甚至在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意义上为这些取向勾勒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基本对立(在实际的情况中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完全可能在同一研究者那里彼此交汇,从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混合、妥协乃至变样的状态)。以下我们将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之争、理解(understanding)与因果说明之争,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不难看出,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争论的整体。我们试图通过揭示这一争论整体所包含的主要矛盾与偏见,来寻求一种超越的道路。 一、认识论的主客观二元论 在近现代的意义上,认识论上的主客观二元论无疑滥觞于笛卡尔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笛卡尔所倡导的以科学理性来认识机械的客观世界的主张为后来实证主义所标榜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奠定了基础(尽管笛卡尔的认识论因为诉诸理性的天赋观念而带有先验论和唯心论的色彩①)。而深受笛卡尔二元论思想和经验主义怀疑论倾向影响的康德的哲学人类学则为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认识论立场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尽管如此,试图在这些早期的滥觞中寻找20世纪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认识论争论的具体观点的做法显然并不妥当,然而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在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中依然以各种方式发挥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我们即将探讨的实证主义和解释学在认识论立场上的争论为我们超越主客观二元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正是此种争论为我们揭示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各自所存在的问题和偏见,使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入手去追问事情本身更接近一种怎样的图景。应当肯定的是,解释学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领域中形成对实证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解释学揭露了实证主义的诸多弊病,并针对这些弊端发展出自身独特并颇有教益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认识活动有其不可彻底消除的先入之见(assumption)。海德格尔写道:“任何解释工作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它是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理所当然的’东西被先行给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在我们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被先行给出的东西。”②这一先行给出的先入之见强调了解释(interpretation)所具有的不可彻底消除的前提,这是由人的存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无论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后继者伽达默尔等人如何具体地去理解这里的先入之见③,总之这一论断(它暗示了著名的“解释学的循环”)是对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立场的毁灭性一击,它彻底打破了客观主义无前提的幻觉,使人们得以正视我们自身存在的不可彻底消除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但解释学的立场在有力地击碎了客观主义的梦幻的同时,却矫枉过正地落入主观主义的取向之中。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那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语言本体论充分揭示了他们思想中的人类主义倾向,其思想中的先验论残余则使他们无法看到理解并不是对存在的先验可能性的领会,而是一种排除了任何先验论倾向的由人类的实践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历史性现象。此种历史性与海德格尔等人所谈论的此在存在的历史性无疑有着重大的区别,后者所谓的历史性不过是意指存在的先验可能性是不可穷尽的,存在总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地在场化着。不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学的影响要早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重要发展,就社会学而言,受到狄尔泰等人影响的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即是一例。主观理解的重要性和先入之见的不可彻底排除性这两个重要的解释学立场不同程度地在韦伯的思想中有所呈现。但正如韦伯对价值中立的有条件的主张所表明的,反实证主义的解释学的精髓并没有被他的解释社会学彻底坚持,韦伯对实证主义的部分妥协使其解释社会学失去了方法论争论的典型价值。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更加乐于使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来展开研究,他们的观点不仅更加系统和深入,而且与在理解问题上过分强调行动者的主观动机的韦伯相比,他们的“理解”概念对反思性和对象化的意识层面的拒斥使之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当代社会理论热衷于在无意识层面探讨理解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启发。 强调基于先入之见的主观理解的解释学立场显然与强调绝对客观的方法论立场相对立,但认识本身并无所谓的主观和客观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化,主观与客观不过是理论性的分析建构而已,二元论思维的误区就在于将理论的分析逻辑强加于前理论的现实本身。因此,认识既不是实证主义者所设想的镜像式的客观反映,也不只是解释学者所主张的主观理解的结果。认识总已经是关于某个对象的认识,它的人类学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只能是一种与客观事实相对立的主观虚构,仿佛认识不过只是一种彻底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游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拒绝了此种不可知论的相对主义,他们保留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相对主义倾向,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无法令人满意,其实质只能是自相矛盾地将先验与经验、普遍与特殊奇怪地结合在此在个体的实践中,最终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视角。 我们对世界的社会历史性的阐释总是呈现与对象的一种认识关系(解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对象化的关系无疑是奠基于前对象的理解之上的,因此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对象化的二元状态仅仅是一个派生的现象,因为理解本身就不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④),我们那有限的理性在其有限的视域中为我们传达出对象之所是,作为这一传达之基础的社会历史性的先入之见使我们的认识活动即便在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各种人为的失误之后,也还是一种有限的认识。但社会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并不总是扮演着一种消极的角色,它与现实之间的前对象的关联既会带来我们认知的局限性,同样也可能导致对此种局限性的不断超越,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以更为合理的局限性去取代旧的局限性,使我们的认识更加逼近对象的真实,尽管绝对的真理仅仅只是一个理想⑤。因此有限的认识已然是有所认识,已然以某种社会历史性的方式为我们传达出对象之所是,只不过这一认识与客观主义者所想象的绝对认识相去甚远⑥。 二、事实与价值 实证主义者主张必须严格地区分事实与价值。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家用实证主义方法所收集的经验资料就是社会事实本身,而社会科学家对经验资料的研究和解释也必须排除一切价值观念,以期达到绝对客观的认识。而解释学者对人之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可彻底消除的先入之见的肯定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可能性。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本身就包含在客观和主观的二元争论之中(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我们将看到,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还有其另一面)。简而言之,客观主义立场主张严格地区分事实与价值,而主观主义的立场则反对有所谓的外在于价值的对事实的描述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事实本身就是具有价值因素的,这使之在根本上区别于自然现象,它之所以被纳入客观事实的范畴,就在于其价值因素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而在事实与价值的争论中的价值一方则是专指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而言。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一旦我们的心灵不只是一个消极的镜子或实体——这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甚至客观的知觉也只能来源于估价——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的世界之中,这一价值的世界在一种自主的秩序中安排了实在的内容。”⑦在齐美尔看来,一方面价值具有主观性,它是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对象的判断,是固有地内在于主体的,因而从来就不是物质实体的一个属性;另一方面,齐美尔认为这个主观性仅仅是暂时的,实际上它并不是非常关键,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否定价值是物质对象的属性,一旦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就要让位于一种社会的客观性,此种客观性表明了非自然的主观性的价值对于个人主体而言依然可能是客观的,它能够独立于个体对它的认可而存在⑧。如果我们抛开齐美尔的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倾向,那么齐美尔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尽管是一种非自然的人类文化现象,但除去那个自然的基础不谈(没有自然的基础文化便无从谈起,但文化并不因此而能够被自然所还原),价值可能既不只是一种个人主体的内在性构成,也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个体的所谓自主的集体或结构的因素(或者说客观的主观性因素);价值在分析上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个体的价值同时也就是社会的价值,而后者也不可能独立于行动者们共同的实践活动而被生产或再生产,既没有绝对的个体也没有绝对的社会,二元论所宣扬的彼此对立的个体与社会其实质不过是理论分析的抽象建构罢了。 我们认为,价值是一种奠基于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非二元论的社会历史性的现象。换句话说,它正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局限性本身,说我们不可能不有限地存在,也就等于说我们不可能不采取某种价值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家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并非绝对的事实本身,它总是隐含了某种价值的判断(各种经验资料的收集方法显然已经十分隐蔽地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实证主义方法和解释学方法便是两个彼此对立的大的方面)。它是一种超越了主客观二元论的社会历史性建构,体现了特定认识立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正是特定的价值使此种关系得以可能,尽管这些价值本身也为我们的认识带来了局限性。而作为对此种经验事实的解释的社会科学理论自然也不可能排除价值的存在,它在经验描述的价值取向之上又增加了理论阐释的价值特征,这种双重的建构并非只是来自于某个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价值,也并非只是客观的社会价值的产物,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虚构。 三、理解与规律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把握可用于预测的规律,而是在对象的独特的和历史的具体性中去理解对象⑨。他写道:“无论包含多么普遍的经验,目标也不是去证实和扩展这些普遍的经验以获取有关一个规律的知识,例如人类、民族和国家是如何演进的规律,而是去理解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如何是其所已经成为的样子的——更概括地说,其成为这样是如何发生的。”⑩此种观点明确地将解释学的理论抱负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目标区别开来,解释学所强调的是理解而不是因果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后者所依赖的归纳程序在伽达默尔看来并不能够使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human sciences)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1)。如果人们在伽达默尔的意义上将解释的逻辑前提设定为人的主观意义(或先入之见),那么实证主义者所遵循的归纳程序的确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所信仰的归纳程序其目的在于寻求普遍的因果规律,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目标则是去理解特定的对象如何成其为自身的(就像早期的解释学者所关心的不过是某一个文本具有怎样的含义。有所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反对将他自己的解释学等同于传统的文学和神学的解释学,因为其解释学所关注的是此在的存在——这大大扩展了解释学的空间,使他的解释学不再只是一种精神科学的方法论(12)),它试图把握的是那个使对象成其为该对象的历史性的意义。在伽达默尔的语境中,这个意义所透露出的是此在存在的先验的可能性和存在的不可穷尽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存在的在场化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件,因此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总是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变化着。尽管在此种相对性中伽达默尔依然怀有一种带有先验论色彩的普遍主义的企图(13),但这与实证主义者对普遍规律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 先验论的姿态在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取向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它更多的是被人们所抛弃。这也使得在伽达默尔那里以先验论来搪塞的意义问题在无法接受先验论断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披在主观性之上的先验论外衣使伽达默尔可以堂而皇之地坚持他的“理解”并不需要一种归纳程序的补充,因为先验的可能性自然是无法通过归纳来加以把握的,神秘的事情只能以神秘的方式来处理,于是伽达默尔便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以此在、语言、理性和存在的神秘关系来为他那神秘的“理解”提供神秘的合法性(14)。但当以解释学为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抛弃了先验论的立场之后,他们必须为先验论的缺场提供某种补偿,在这一问题上,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早在伽达默尔之前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案。不过在说明这一点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解释学取向的社会科学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和它的哲学来源一样迷恋于对特殊对象的理解和解释(这无疑是对解释学传统的延续),这使得解释学路径常常只是被用于对所谓的特殊个案的研究,例如一个亚文化群体、一个具有独特风俗的相对封闭的村落,等等。在这些研究中,那些个案所蕴含的意义因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而需要研究者的深度介入,研究者必须融入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氛围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践这一文化(如学会一种语言),才可能深入地理解其对象的意义。无论研究者是在个体的主观赋予的意义上,还是在集体主观性的意义上,抑或是在其他的意义上,来看待这里所谈及的意义,总之这一做法虽然抛弃了先验论的想象,但是其研究结果的高度个案化往往使之更多的只是具有启发性而非推论性的价值。而与之恰成对照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对那些无法被直接经验到的意义赋予不感兴趣,它建基于对那些可以被直接观察和记录的经验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的方法,无论是定性的研究还是定量的研究都强调对归纳程序的贯彻,以期获得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因果法则。然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却落入了客观主义的陷阱,它在变量之间所发现的所谓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无法真正地解释社会现实,它由于无视具有人类学特征的意义的重要性,将原本充满了意义的社会现实歪曲成仿佛是物理学所研究的事物,它把笛卡尔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世界观强加给人类社会(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自然界也并非是一个机械论和决定论的世界(15)),它所信仰的普遍规则实则只是基于简化与还原的社会历史建构(即便是它奉为典范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也同样不能例外(16),不过它通过简化和还原所得到的法则的有效性比它的自然科学榜样要远为逊色)。它没有意识到自身也只不过是诸多立场之中的一种,总已有一些不言而喻的先入之见在它的认识中发挥作用。 在如何解决理解和规律的对立的问题上,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做法(这当然是在抛弃了韦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前提下)。他认为基于理解的解释应当是因果解释,这需要满足两种充分性,即意义的充分性(也就是说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必须是合乎常规的,而不是一些按照习惯性的思维和情感模式难以去理解的特例(17))和因果的充分性(即行动的发生合乎或然性的因果规则(18))。韦伯认为,没有意义充分性的统计的一致性是不能构成社会学概括的,反之,主观可理解的行动的合理过程如果没有因果充分性,则不能构成经验过程的社会学类型(19)。韦伯对理解和归纳的综合,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既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应当是具有因果价值的。我们并不否认独特的个案研究的启发性意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社会科学不应当仅仅停留于此。不可否认的是,韦伯依然主张文化科学的对象是历史的个别事件,其目的是对文化现象的意义从何而来给出一种特殊的因果解释。在韦伯看来,普遍的因果解释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个别事实的因果解释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它充其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20)。此外韦伯对因果规则的或然性的强调也打破了实证主义的决定论的幻觉,社会科学的因果法则必须是可理解的或然性的法则。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或然性法则的效力并不等同于诸如统计物理学的或然性法则的效力,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正如麦金泰尔所指出的:“我们称社会科学的普遍概括是或然性的,丝毫没有说明它们的地位,因为它们不同于统计力学的普遍概括(21)。正如它们不同于牛顿力学和气体定律方程式那类普遍概括一样。”(22)社会科学并不能抛弃归纳的因果诉求,社会科学的知识必须追求属于它自身的那种因果解释力,此种因果解释力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社会历史意义的深入理解而存在,并且必须像任何一种因果解释力一样对自身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保持一种持久的觉醒,否则它就只能沦为一些自以为是的抽象命题的产物,沦为一些不知其所以然的精巧的研究设计的结果,并对社会现实保持一种客观主义式的冷漠与麻木。 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以上研究表明,社会科学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它同样也需要探究因果的法则,这是社会科学知识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有所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充满了意义的人类社会生活,而不是自然科学家所面对的事物和有机体,理解的不可或缺表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实证主义者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现象的做法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种试图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做法只能导致社会科学无视自身对象的特殊性,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知识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捉襟见肘(23)。 实证主义者仅仅满足于研究那些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忽视或无视社会行动中所蕴含的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意义,这些意义是难以甚至无法通过自然科学式的观察和测量来直接获取的,于是实证主义者为我们所描绘的社会世界往往只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数据和指标的表象化的世界,真正赋予这一切以意义的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行动和言谈的外在表象所遮蔽了。解释学提醒我们那个可以被量化和测量的世界其实质不过是一个意义世界的表象,不了解行动的意义我们就无法真正阐明人类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生活,正是复杂而不确定的社会历史性的意义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我们并不打算幼稚地宣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世界是非决定论的而自然世界是决定论的,或社会科学的知识是非决定论的而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决定论的,我们此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即便是自然世界和自然科学也并不遵循决定论的逻辑。我们也不会荒谬地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在于前者适合于主观主义式的理解而后者适合于客观主义式的说明,虽然理解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自然科学,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仅仅是笛卡尔主义的虚构,认识活动并不是绝对的客观和完全的主观之间的非此即彼,理解并不只是主观的,说明也并不只是客观的,我们对于主客观二元论的克服已经展现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认识论思路。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确可以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通过简化和还原的人为操作所得到的那些所谓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法则,比在社会科学中以同样的方式所得到的法则在预测方面要有效得多,但这只是因为人类行动者的反思性和能动性所带来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实践的模糊性问题(24),研究对象对研究本身采取策略的问题,研究结果改变研究对象的问题(25),等等)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使得社会科学家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获取具有相对较高的普遍有效性的知识,这充分表明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即便是排除了决定论幻觉的或然性的规则,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也不同于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这进一步表明,同样是非决定论的世界,同样存在着认识者的社会历史局限性(26),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处境的确有着重大的差异。自然世界的非决定论特征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支持一种具有较高普遍效力的统计规律性,但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则取消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统计规律性的可能性。因此不应当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将社会科学对或然性知识概括能力的不足视为社会科学不成熟的表现,进而贬低社会科学的学科价值,甚至否认社会科学具有理论的意义。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错误。社会世界的现实状况要求社会科学家的归纳研究必须包含理解的态度,基于理解的归纳并不能够获得自然科学知识那种相对较高的普遍有效性(不是绝对的普遍有效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进行相对精确的预测,而是在于尽可能有效地去理解我们自身,它对因果法则的追求正是为了尽可能地提升其理解的效力,当然,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并不止于此。 本文只是从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争论出发探讨了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例如结构主义所关注的实在论问题,批判理论所关注的规范性问题等都没有涉及。但可以指出的是,假定一个无法被经验到的结构实体并不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增加实质性的思想,相反它更可能只是一种无视现实的关系性的形而上学的虚构。福柯、布迪厄等当代理论家在结构问题上都采取了关系的取向,实在论将社会历史性的关系加以绝对化和固定化的做法与现实相去甚远(27)。此外规范性的问题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特指批判意义上的规范性,尽管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理论的描述和解释同样具有价值的立场,只不过更加隐蔽而已),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态度使之放弃了社会科学的批判任务,而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取向则往往导致其对于压迫性的社会力量缺乏有效的反思。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并没有将社会批判作为一个主要的议题,因此,一种批判的精神对于我们的方法论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补充,它表明当我们回答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后,一种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反思所获得的应当怎样的立场将有助于人类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当然我们永远都不能将此种应当加以绝对化,而必须始终对其社会历史性保持一种觉醒,始终保持对它的反思甚至质疑的态度),这无疑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重大差异所在。事实上,批判理论的规范性问题还涉及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前文结合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争论讨论了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最基本的方面。批判理论不仅与解释学一样批评实证主义所宣称的绝对客观和价值中立,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提出了另一种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即那种所谓的纯客观的社会研究的立场并不可取(28)。贝尔特指出,人们对此可能给出两种理由,其中积极的理由即我们前文提到的社会批判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和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而消极的理由则认为,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往往为社会中保守的价值服务,实证主义不仅服务于隐蔽地支配着它的那种保守的价值立场,而且还以排除批判的方式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保守力量(29)。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一切认识都有其不言而喻的先入之见,从而也就有其不可彻底排除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这当然不是自相矛盾地宣称可以获得绝对的客观性,而是体现了一种力求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有限理性的态度。当我们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时候,客观性作为一种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实现的理想总在指引着我们,我们应当不断地去反思自身社会历史性的先入之见,由此将那些危害人们有限理性的因素从我们的思想中最大限度地排除出去,尽管这一过程将永无止境。 注释: ①王太庆:《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载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xv页。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6页;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SCM Press Ltd.,p.192. ③海德格尔的认识论立场无疑是主观主义和先验论的,尽管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主体概念并不意指绝对主体(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主体概念始终持批判的态度),而是意指由存在所决定的有限的主体(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主体主义的接受是十分隐蔽的,他更多吸收了笛卡尔的主体主义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具体观点,这充分地体现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具有先验论色彩的人类主义视角——即便他后期对存在之优先性的突出强调在根本上也没有背离主体主义);而他的存在的先验论所意味的也不是先验的绝对存在,而是先验的可能性的存在(在历史中不断在场化的存在),此种先验论突出地呈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残余。在这些方面,另一位重要的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无疑是十分接近的。 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2页;Heidegger,Being and Time,p.99. ⑤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trans.by A.Goldhammer,Beacon Press,1984,pp.108,113,172. ⑥值得指出的是,认识者与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不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意义上的个人的主观性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或社会的主观性(这一分析性的提法在观念层面也可以表述为社会的客观性或客观的主观性)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社会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认识活动在本体论上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个体与社会这两个分析性的建构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是共属一体的(郑震:《作为存在的身体》,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4页)。 ⑦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trans.by D.Frisby,Rouledge and Kegan Paul Ltd.,p.60. ⑧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pp.63,68. ⑨Gadamer,Truth and Method,trans.by G.Barden and J.Cumming,Sheed and Ward Ltd.,p.6. ⑩Gadamer,Truth and Method,p.6. (11)Gadamer,Truth and Method,p.6. (12)Gadamer,Truth and Method,p.xiii. (13)郑震:《语言与实践》,《社会理论学报》2006年秋季卷。 (14)郑震:《语言与实践》,《社会理论学报》2006年秋季卷。 (15)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pp.104,108,113. (16)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pp.104,107,108,163,172.此种建构性还体现在因果关系的观念本身就具有信念的特征,休谟为我们指出了因果关系的信念是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依赖于前反思的习惯和想象的运作而产生的(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The Clarendon Press,pp.82,91,92,97)。但休谟局限于个人主义的幻觉(Elias,The Symbol Theory,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pp.7~9),从而无法为因果观念的生成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解释。 (17)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Free Press,1964,p.99. (18)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p.99. (19)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p.100. (20)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可以说,我们对韦伯相关主张的借用已经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韦伯自己所设定的范围,尽管我们并不主张一种绝对普遍的因果解释。 (21)这是一种或然性的普遍概括,麦金泰尔认为“它们像所有非或然性的普遍概括一样,也是法则式的概括”(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引者注 (22)麦金泰尔:《德性之后》,第115~116页。 (23)当然自然主义并不一定需要实证主义的立场,例如与实证主义有着重要冲突的实在论便是一例,实在论者甚至试图将自然主义和解释学加以调和(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显然无法取代解释学的方法,自然主义的立场本身并不能够提供解决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问题的方法。 (24)Bourdieu,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trans.by M.Adams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25)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9页。 (26)值得一提的是,在认识者的社会历史局限性方面,社会科学家与其研究对象(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人这一点使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除去研究者的理论立场不谈,社会科学家的确更有可能将自身对研究对象的好恶有意或无意地纳入其对对象的研究中去(因为像人们的政治和道德立场总是关于人的而不是事物的立场,自然科学家当然不会将自己的政治或道德立场运用于对自然现象的说明,但社会科学家却可能在对作为对象的人的解释中实践自身的道德或政治立场,并且可能由于此种立场获得广泛的认可而不被人们所觉察),以致使自身的研究采取理论立场之外的价值立场,当后者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对研究结论的歪曲就更难以被研究者所觉知。而当一种政治的、道德的或民族的立场隐含在研究者的理论立场之中的时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事实上这些危险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27)Bourdieu,Practical Reason:On the Theory of Action,trans.by G.Sapiro,Polity Press,1998,pp.3,4. (28)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第237页。 (29)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第237页。标签:实证主义论文; 解释学论文; 二元论论文; 韦伯论文; 先验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笛卡尔论文; 决定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因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