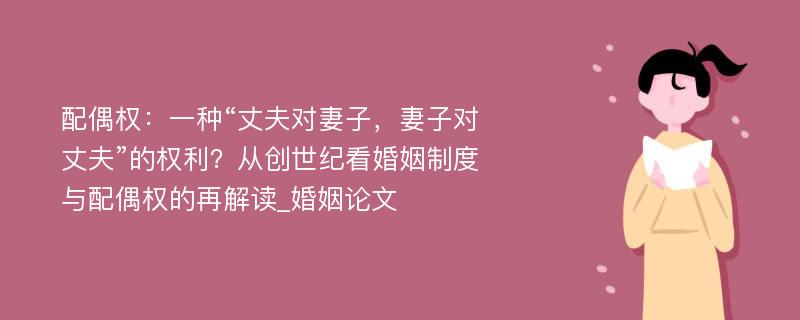
配偶权:一种“夫对妻、妻对夫”的权利?——从发生学视角对婚姻制度和配偶权的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配偶论文,视角论文,权利论文,婚姻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1-0142-06
一、问题的提出及分析视角
以婚姻法的修改前后为背景,配偶权以及与配偶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同居义务、 忠实义务、婚内强奸、第三者插足)一度成为国内法学界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争论焦点 。相关著述虽数量颇丰,但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一个纯粹的法律视角,所探讨的问题均与 立法、司法直接相关,其共有的缺陷则是未能阐明配偶权背后深刻的制度背景——这个 制度背景决不仅仅是指国家制定的婚姻法。如今,关于配偶权的争论已经伴随着新婚姻 法的出台而逐渐冷却,但与配偶权相关的一些前提性思考尚未真正得以澄清。尽管学者 们对于配偶权的界定有众多说法,但一个基本的命题——即配偶权是一种“夫对妻、妻 对夫”的权利——似乎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1](第260-291页)然而,本文首要的 写作意图则恰恰是对这一基本命题提出质疑。
配偶权的确是个法律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早在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产生之 前,作为一种习俗上或伦理上的权利,配偶权早已存在了百万年之久,从发生学意义上 ,配偶权是与婚姻制度相伴而生的。但我并不认为,配偶权萌芽于最初固定地生活在一 起的一对男女之间。因为在我看来,最初固定生活在一起的一对男女并不是婚姻制度的 真正创始人,而最早约定互不侵犯各自占有的性伙伴的那两个男人才是婚姻制度的真正 奠基者。婚姻制度最基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两性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通过婚姻也能 实现),而是为了阻止同性间的相互侵犯,正如财产私有制是为了阻止人与人之间相互 争夺其各自拥有的财产,婚姻也是为了阻止同性之间相互侵犯其各自占有的性伙伴。说 到家,婚姻首先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一种制度,而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关于女人的一种 制度,其次,在较弱的意义上,也是女人与女人之间关于男人的一种制度。如果我的推 测能够成立,那么关于配偶权那个基本命题——即“夫对妻、妻对夫的权利”——就会 首先面临来自发生学上的质疑。
本文对于配偶权的探讨立足于从发生学视角对婚姻制度的重新解读,之所以选择一个 发生学视角,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婚姻 制度被彻底废除的社会:两性之间的感情纽带由于失去了固定的载体会变得很不牢靠, 某些人会因此生活得相当孤独;孩子出生之后得不到很好的抚育,事实上,所有的孩子 只能和他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之中;妇女会恐惧怀孕,在孕期和哺乳期她们无法 期望获得男人的帮助;男人也很苦恼,因为他搞不清楚妇女腹中的胎儿是否真正传递他 的基因;由于没有固定的性伙伴,人们被迫在满足性需求上投入高昂的成本;并且由于 性伙伴的频繁更换,长期处于性亢奋状态的人们会缺少足够的生命能量来维持生计,更 没有旺盛的精力去创造文明;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一个男人指着他心爱的女人说:“ 她是属于我的”,没有一个傻瓜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如果另一个男人和他心爱的女人发 生性关系,他既不能通过诉讼去获得救济,也无法依靠舆论给那个男人施加压力,因为 没有婚姻就没有所谓的“配偶”,也没有所谓的“配偶权”。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最糟 糕的,婚姻制度如果被废除将会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灾难是,性竞争的无序与混乱。人们 会为争夺性伙伴而频繁冲突,甚至相互残杀,整个社会必将难以为继。由此看来,婚姻 首先是一种致力于维护和平秩序的制度,与维护和平相比,婚姻的其他功能(比如更好 地抚育孩子、根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都只能是相对次要的,甚 至是附带性的。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发生学意义上的婚姻就是 起始于限制性竞争的需要。
审视婚姻制度,我选择的切入点是性。尽管,除性以外,婚姻还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 财产、生育、抚养),但几乎没有人否认性是婚姻的关键。在本文的论述中,性被主要 看作是一种“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或一种“关系”。由于性资源既可以被 用来满足性欲,也可以实现生育的目的,因而“生育资源”被当作是性资源的一个组成 部分。当一种资源(对比于人们的欲望)相对稀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会为争夺这种稀 缺资源而发生冲突,为了限制或防范这种冲突,社会就会为这种稀缺资源确立“产权” 。发生学意义上的婚姻就是一种关于性资源的产权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性资源的私有 制。婚姻为性资源划分了界限并确定了归属,从而终结了性资源的混沌状态。婚姻产生 之后,自然形态的性资源就被改头换面为社会形态的“性权利”,而性权利无疑是配偶 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生学意义上的配偶权是一种对性资源的排他占有权,因而配偶 权首先应被理解为“丈夫对其他男性的权利”或“妻子对其他女性的权利”。
二、男权社会的婚姻与配偶权
资源的相对稀缺是确立产权的前提,如果一种资源已经丰富到像阳光、空气那样唾手 可得的程度,确立产权就没有任何意义。[2](第2页)但性资源在人类社会中是否真正存 在稀缺的事实,并非没有半点疑问,卢梭就曾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性资源并不稀缺 。[3](第103-107页)的确,如果男性的全部性机会在全部女性那里能够均匀分配的话, 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女性的全部性潜能大概足以满足男性的性欲总和,(注:毕竟, 男性的性行为是不能持续进行的,在两次性行为之间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不应期,但一般 说来,女性对性行为却大致可以持续接受。)然而,由于人类在性选择上的偏好和挑剔 使得性机会无论在男性那里还是在女性那里都不可能是均匀分配的。某个女子对男性拥 有较强的性吸引力就会获得较多的性机会,当该女子所获得的性机会超过了她的生理或 心理负荷能力的时候,作为许多男性共同追逐的一种性资源,她就会显得相对稀缺。不 仅如此,人类男性拥有巨大的生育潜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单个男子一生可以生育几 千个子女。但女性的生育潜能与男性相比却大受限制,单个女子一生生育20个孩子在试 管婴儿出现之前就是一个现实的最大值,[4](第118-119页)这种情况导致了对于男性而 言女性生育资源的相对稀缺。当资源稀缺的时候,为争夺这种资源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 就是不可避免的。[5](第428页)
与动物不同,人类的性竞争没有被自然律限定在一段短暂的发情期内,人类的性行为 或多或少是不分时刻的,这会导致人类的性竞争远比其他物种更为频繁地发生。[5](第 284-285页)然而,对社会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性竞争通常只发生在男性之间,由于社会中 的大多数权力和财富总是被男性控制着,与女性的性竞争相比,男性的性竞争必然会导 致更多的暴力冲突和利益内耗,也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后果。
如果说婚姻起始于限制性竞争的需要,那么限制男性之间的性竞争就显得格外迫切。 因而有理由推测,婚姻制度的真正创始人必定是两个男人,当性竞争使这两个男人感到 筋疲力尽的时候,并且,当频繁的冲突使他们最终意识到终止冲突才是最佳选择的时候 ,他们就会缔结一份关于互不侵犯性资源的和平契约。这份契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 标志着婚姻制度的最初萌芽,也是人类关于性的制度文明的最早开端。契约为性资源划 分了界限并确定了归属,在这份契约内部,伴随着性资源的混沌状态的终结,自然形态 的性资源就转化为社会形态的性权利。请注意,这就是最早的配偶权,它是一个男人针 对另一个男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在契约内部才是真正有效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缔结互不侵犯性资源的契约,双边契约就会发展为多边契约 ,契约在空间上的拓展和在时间上的延续会使契约最终扩大并固定为规则。按照美国社 会学家科尔曼的解释,规则就是一种多边契约。[6](第300页)当整个社会发展出关于互 不侵犯性资源的规则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就已经初具雏形,此时的配偶权已经 在社会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当一个男人指着他心爱的女人说:“她是属于我的”, 其他男人会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因为根据规则,这个男人已经获得了排他占有这个女人 的权利。权利无非是一种规则化了(即由规则调配并由规则保障)的资源。
男权社会的婚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7](第274-282页)配偶权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 的角色基本上都由男性来承担。在婚姻内部,妻子的地位只相当于丈夫的财产,丈夫的 婚外性行为不被认为是对其配偶的侵权,因为妻子没有垄断丈夫性行为的权利。丈夫在 婚外放纵性欲的阻力并不来自婚姻内部,而是来自于社会,因为丈夫必须对其他丈夫承 担相应的义务。要求一位妻子只能从其丈夫那里获得快感,也就等于要求其他男子不与 这位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推而广之,要求所有的妻子对其丈夫绝对忠诚,就意味着任 何人都享有要求他人不与自己妻子发生性关系的权利,这实际上仍然是为了实现性资源 在男性之间的互不侵犯。由此不难发现,在男权社会里,与丈夫配偶权相对应的,首先 是其他男性不与其妻子发生性关系的义务,其次才是其妻子不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 义务,后者只是保护丈夫配偶权的另一道屏障。换言之,男权社会的配偶权主要不是丈 夫对妻子的权利,而是丈夫对其他男性的权利。
三、现代社会的婚姻与配偶权
动物世界里的性竞争大都发生在雄性动物之间,雌性动物只是被动地接受性竞争中的 优胜者。与动物世界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景象颇为不同,人类女性也会成 为性竞争中的积极参与者,这使人类社会的性竞争与动物世界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 势。与男性的性竞争相比,女性的性竞争较少诉诸暴力冲突,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至 少部分地与此相关——女性性竞争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重视。在一个男性始终占据支 配地位的社会里,女性之间的性竞争还通常会受到鼓励,由于女性参与性竞争的手段通 常只是强化自己的魅力,这在绝大多数男性看来是一种建设性活动。但社会之所以没有 专门发展出一种制度来限制女性之间的性竞争,并不仅仅因为女性的性竞争相对温和,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用以限制男性性竞争的婚姻制度也同样可以起到限制女性性竞争 的效果,婚姻制度对于限制男性和女性的性竞争而言是完全可以一物两用的。
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地位只相当于配偶权的客体,所以,当把婚姻制度看作是一种 关于性资源的产权制度的时候,性资源仅仅是指女性提供给男性的性资源,而男性则是 性资源的所有者。看起来,“产权论”与男权社会中婚姻制度是比较吻合的,但用以解 说现代社会中婚姻就肯定会招致众多非议。女性的权利主体地位已经获得法律的保障和 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一事实大概是反对“产权论”最重要的理由,既然妻子已经不再是丈 夫的财产,婚姻也就无法确立关于性资源的产权,并且,将婚姻理解为性资源的产权制 度还似乎是在坚持对女性的某种歧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男性特权在现代社会的婚姻中的确已经大大弱化甚至不复存在, 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妻子已经成为其自身性资源的所有者,因为即便是现代婚姻也不 承认妻子拥有不受限制的性自由,妻子仍然需要对丈夫保持性行为的忠诚。而男性特权 的弱化或消失也仅仅表明现代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一样失去了自由支配其自身性资源的 权利,即丈夫也不能任意到婚外去寻找肉体的快感。所以,现代婚姻中的男女平等并不 意味着妻子与丈夫一样自由了,而只意味着丈夫与妻子一样不自由了。妻子并没有收回 (至少没有全部收回)她自身的性资源,但她丈夫的性资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却归她所 有了。由此可见,现代婚姻已经演变为一种关于性资源的“双向”产权制度,即男女两 性互为所有者,互为被所有者,换言之,丈夫与妻子互为配偶权的主体,互为配偶权的 客体。请注意,这一结论区别于“互为权利主体,互为义务主体”的说法,正因为存在 这种区别,我仍然不认为配偶权在现代婚姻中已经从根本上演变为“夫对妻、妻对夫” 的权利。此外,还应注意到,尽管在婚姻内部,配偶双方相互拥有对方性资源的产权, 但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拥有控制另一方性资源的绝对自由,换言之,任何一方都有权保 留在某种条件下(比如经期或疾病)拒绝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自由。显然,这是一种受限 制的产权。
婚姻的确在外观上呈现出两性组合的表象,但婚姻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同性之 间的互不侵犯,这种对婚姻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康德在其《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对婚姻 作出的经典阐释。在康德看来,婚姻只是两性之间关于性资源的一种契约关系,是两个 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而产生的结合体”。[8](第95页)康德 对婚姻的理解只对了一半,婚姻的确是两性之间的双边契约,但作为一种制度,它又是 同性之间(既包括男性之间,也包括女性之间)的多边契约。婚姻实现了同性间的互不侵 犯也同时满足了两性间的互助合作,或许前者才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两性之间的合作即 便不依靠婚姻也能做到,但同性之间的互不侵犯却是除了婚姻之外别无选择。婚姻之所 以形成一个两性“结合体”,通俗地说,之所以需要用婚姻这条绳索把两个人捆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谁也难以插足到别人的领地之中。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男女都能在各自的婚 姻中恪守夫道或妇道,那么性竞争就可以被降低到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由此看来,即 便在现代社会中,配偶权也首先是一种丈夫对其他男性、妻子对其他女性的权利,其次 才是一种“夫对妻、妻对夫”的权利。
四、婚姻、配偶权与法律
婚姻,作为两性之间的一种互助合作型的双边契约关系,保障了性资源在两性之间的 一种长期(乃至终身)的交易,交易对象是夫妻自身的性资源;婚姻制度,作为同性之间 的一种互不侵犯型的多边契约关系,则保障了同性之间的另一种交易,交易对象是侵犯 他人性资源的行为控制权。交易会实现互利的结果,每个人把侵犯他人性资源的权利转 让给他人,就会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所有性资源不受侵犯的承诺。交易取代了相互间的 侵犯,交易者就能把消耗于相互侵犯的资源节省下来转而投入于其他建设性活动。可见 ,婚姻制度是自发形成的,其动力来源于交易中的利益。无论是两性之间的双边交易还 是同性之间的多边交易,都能使交易者从中获益。在交易能使交易者获益的情况下,经 过多次往复的博弈就能最终促成这种交易。
婚姻制度正是一种如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它不是哪个天才的头脑刻意 设计出来的,它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同其他几种具有深远意义和持久 效力的制度(如财产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等)一样,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的经 验的产物,它来自于众多社会个体反复博弈不断选择的过程。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 ,婚姻制度本身具有自足性,也就是说,婚姻制度无须借助于外在的强制力量就能得以 存续。婚姻制度的自足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维护婚姻制度的监控机制和惩罚机制内含于制度之中。即便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一 无所知的人们也深谙人类的性欲冲动是何等强烈,控制这一性欲冲动又是何等艰难。无 论国家强制力量多么强大,国家监控成本何等高昂,都难以保证所有人的性行为被有效 控制在制度划定的界限之内。几乎每个饮食男女都是需要防范的对象,但却不能在每个 人的身后随时随地地跟踪上一个警察。婚姻制度的自足性恰恰表明,它不是一种主要靠 警察来维持的制度。在婚姻内部,丈夫盯着妻子,妻子盯着丈夫,无论哪方做出不检点 的举止,对方都要令他(或她)吃点苦头,其惩罚措施的多样化和有效性以及监控措施的 严密程度足以让警察自叹弗如。在婚姻外部,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实际上绝非毫不 相干——的人也往往不会对越轨行为袖手旁观,他们或许不会直面责骂,更不见得大打 出手,但却在背后悄悄编织一种对越轨者极为不利的舆论,这种浩瀚舆论的强大能量常 使许多作奸犯科之徒身败名裂。一旦整个社会行动起来,国家的监控成本就可以降到最 低限度。
(2)婚姻制度已经内化到人们的心灵结构之中。婚姻起始于国家创立之前,这意味着在 国家立法机关尚未把婚姻制度白纸黑字地写在法律文本上的时候,它已经根深蒂固地存 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了,并且这种表现为习俗禁忌和伦理道德的婚姻观念通过某种教化 体制得以世代相传并沿袭至今。一旦外在的婚姻制度内化到人们的心灵之中,就会形成 与性欲冲动截然对立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是内化于人的行为规范、监控机制和奖惩措 施的三位一体,它不仅告诉行为人怎样去做,而且监控行为人的越轨行为并对其施加惩 罚,惩罚表现为心理上的一种羞耻感和负罪感。行为人的道德意识越强,夫妻感情越深 ,这种心理上的惩罚措施就越发有效。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足以 抵制婚外的性诱惑,甚至可以打消一个人企图离婚以另寻新欢的念头。此外,婚姻价值 观的流行还迫使那些不打算接受婚姻道德的人们也必须按照婚姻道德去塑造自己的人格 形象,不加掩饰地暴露出自己放荡不羁的品性必然会招致社会的敌视。因而在婚姻价值 观流行的社会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恪守夫道或妇道的楷模,尽管我们知道,在如此众 多的正人君子之中有些人只是假冒伪劣。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固然增加了人们择偶的难 度,但那些企图在婚外寻找性机会的人们也同样感到难觅知音,因为他(或她)们也搞不 清哪位男子风流哪家女子多情,婚外性行为将因此承担额外的交易风险。
总之,由于婚姻制度原本就不是靠国家强制力量支撑起来的制度,所以有理由相信, 即便国家不复存在,婚姻也不会瓦解消亡。纵然法律成为一张废纸,人们依然会认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制度也主要不是靠法律和国家强制力量来维持的,如果一 对夫妻仅仅靠法律来维持他们的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几乎维持不下去了。如果有人 打算插足别人的婚姻,并且他(或她)仅仅担心法律的惩罚,那么他(或她)就几乎无所畏 惧了。由此看来,法律上是否确立配偶权、是否规定同居义务和忠实义务以及是否惩罚 第三者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关键的问题则是,配偶权是否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习俗、 伦理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之中。无论法律作出哪种规定,都只能表明一种姿态,而不可能 真正构成一种威慑。对于一个违法者来说,预期的惩罚成本是抓获几率与惩罚严厉程度 之乘积,因此,对于一种抓获几率很低的违法行为,法律只有通过提高惩罚严厉程度才 能保证一种威慑效果。[9](第225页)不难想象,由于警察抓获第三者的几率低得可怜, 所以依靠法律来惩罚第三者是十分艰难的,除非,法律把惩罚严厉程度提高到无法想象 的地步。因而,法律惩罚第三者不是一个应当或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够或不能够 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3-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