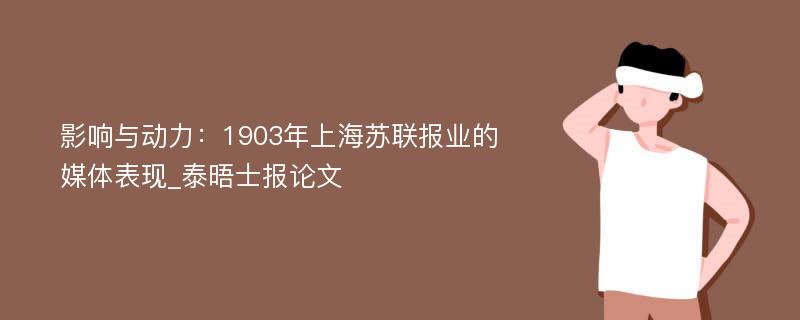
影响与造势:1903年上海苏报案中的媒体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03年上海苏报案,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案件。苏报案从个体案件成为公共事件,再演变为著名事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媒体的广泛报道。一方面,苏报案中的诸多元素契合新闻价值的需求,使得苏报案成为当时媒体议程设置中的重要内容,进而生成为媒体、政治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媒体报道的影响和造势,又夹杂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关注和评判因素,加剧了案件的冲突,推波助澜了苏报案的发展,使得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 或许是由于庭审新闻天然的冲突性和戏剧性,自中国现代报纸诞生之初,有关诉讼的庭审报道就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如1873年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吸引了《申报》前后长达四年的持续关注,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道很快使原来仅限于浙江当地民众和部分官员知晓的案件公诸天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代诸多有关该案的研究,其素材也多来源于《申报》的报道。[1]该案之中,《申报》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披露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前后还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引人称道的是,除了对新闻事实的披露,《申报》的目光已超越一个单纯的案件,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不少报道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2]可以说,《申报》有意或无意中提及的公开审理、陪审团、律师、记者旁听、民众旁听等一系列现代法治概念,展现了当时法治思想的一种萌芽和冲突,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和发酵,无形中成为近代司法转型的催化剂。 一、聚焦苏报案的媒体 相比之下,苏报案发生的1903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得到迅猛发展,涌现出大批形形色色的报纸,国外媒体在华也多有通讯机构或派驻记者。正是他们的介入,使得苏报案能够超越一隅,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内容,成为讨论中国政治、文明,特别是中国司法的一次机遇。 经检索,目前初步发现参与报道苏报案的中外媒体有40多家。中文报纸有《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国民日日报》、《华字日报》、《新民丛报》等;外文报纸除上海本地的《字林西报》、《文汇西报》、《捷报》、《上海泰晤士报》、《益新西报》、《中法新汇报》之外,还有世界各地的外文报纸,如《泰晤士报》关于苏报案报道评论共37篇,《纽约时报》24篇,《洛杉矶时报》11篇,《华盛顿邮报》10篇。[3]甚至连很多中国新闻人不熟悉的《阿尔塔蒙特企业报》(Altamont Enterprise)(美国)、《俄勒冈州晨报》(Morning Oregonian)(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美国)、《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新加坡自由新闻》(Singapore Free Press)(新加坡)、《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澳大利亚)对苏报案都有所报道。中文报纸除大量转引外文报纸的报道外,自己也采写配发了大量新闻,并由于诸多报纸的立场不同,对苏报案的解读和评析也有所不同,但一致的是它们都对苏报案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苏报案的“案中案”——沈荩案,引发的舆论影响就是最典型的佐证。当时英国外交部正在就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苏报案被关押者一事征求国内皇家法院的意见,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倾向于在不实施酷刑的条件下交出被关押者,但《泰晤士报》关于沈荩惨遭酷刑和沈荩案在中国引起的反应等报道引起了英国议员的注意。1903年8月4日和5日,分别有议员在下议院听证会上就苏报案被关押者的移交问题提出询问,这也直接促使英国内阁在8月5日宣布政府拒绝清政府的要求。也正是在报纸舆论一致指责中国政府的声浪中,法国、美国等也在英国表态之后陆续表示拒绝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 有关苏报案的报道中,及时是首要的特点。及时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重要原则。6月29日,也就是租界巡捕开始搜捕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当天,《申报》就发表了《饬查叛党》的新闻,赫然载明朝廷要在上海租界严密查拿爱国学社内“猖狂悖谬,形同叛逆”之“不逞之徒”的密电。苏报案发生的第3天,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发表了《政府与改革党》(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form party)的通讯员文章,主要论述中国保守势力镇压革命党,《苏报》主笔及职员被捕,第一次提及《苏报》。可见,中外报纸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关注了苏报案。 持续性跟踪报道也是苏报案相关报道的重要特点,这也是全面展现事件进展和动态的要求。对于苏报案的跟踪报道,诸多报纸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如《中外日报》在1903年7、8、9三个月转引外文报纸关于苏报案的报道就有近40条。《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8、9两个月期间转引外文报纸关于苏报案的报道就有近30条。《申报》前后共发表《饬查叛党》、《会党成擒》、《会党自首》……《四讯革命党案》、《党魁移禁》等10多篇报道,贯穿整个事件始终,甚至连章、邹二人患病、[4]何时重新开庭[5]等细微消息都给予了关注。《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有20多篇,前后长达数月。《泰晤士报》前后关于苏报案报道评论更是有37篇之多,自1903年5月苏报案尚未发生一直到1904年5月苏报案最终判决形成,时间跨度接近一年,可谓“有始有终”。 二、中文报纸的不同表现 苏报案的中文报道,最大的特点是众口交腾,这也从侧面展示了当时转型社会背景下各种思潮激荡交错的场景。 是时,上海的老牌《申报》完全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对章、邹等人表现出一种讨伐态度,抨击革命党,这在《申报》的诸多报道都有反映。这种表现与当时《申报》主笔黄协埙厌恶西学,思想守旧的立场有直接关系。戊戌政变后,黄协埙完全站在慈禧太后的一边,著文批判“康梁邪说”。等到1903年前后革命风潮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申报》更是大加鞭挞。6月22日刊发的《奴隶说》,指出爱国学社这样“险恶的用心”必然会落得与张献忠、李自成、唐才常等“匪患”一样的下场,“噫!献闯即甚猖狂,不久即膺天讨,唐邓阴谋甫露,已肆市曹,彼何人?斯特庸懦书呆耳,而乃诩诩然曰:驱胡族,灭清人以免二百数十年来为外人之奴隶,试问能乎?不能乎?有不陨首法场步武献闯唐邓诸巨憨者乎?”[6]同时批判留学生们忘恩负义,愧对朝廷的培育之恩,“所可恶者,既受主人豢养之恩,而日以谋叛其主人,图弑其主人为事,则真恶奴贱隶狗流不食其余者矣。”[7] 苏报案发后,除连续报道事件进程外,在清政府以苏报案被关押者是国事犯为由要求引渡时,《申报》也一知半解地认为章、邹等人“与国事犯有殊”,实质上是“忤逆不孝子”。完全从封建纲常的角度来看待案件,自以为是地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定会明辨是非,不会庇护案犯。[8]月初,还特刊发《爱国忠君说》,“今天下有创为爱国社者矣,有结为爱国党者矣,有著为爱国篇爱国论者矣,议论激昂,乍聆听之,一若真赤心为国也者,及徐而考其宗旨,则嚣嚣然,扰扰然,曰我将藉以行革命之事也,我将因上遂易代之谋也,我欲保国土之不凌夷,不得不急图灭清排满也。”[9]指出与章炳麟等人关系密切的爱国学社名为爱国,实为犯上作乱,意图不轨。而对之前引起舆论峰起的沈荩案,《申报》既不报道,亦不评论,更不转载其它报纸的相关内容。从整个时局来看,《申报》倡导的忠君、卫君、爱国论调,与当时日益开化的风气不相符合,黄协埙的一味守旧更是让《申报》声誉倍跌。即便《申报》长篇大论地为政府说话,但旧传统的忠实卫道士最终并没有得到认可,参与案件的武昌试用知府金鼎在向梁鼎芬汇报时,就提到《申报》“素以守旧,为人所恶,故其言亦不足重”。[10]可以想象,《申报》对苏报案最终判决的影响并不大。 另一份中文大报《新闻报》对苏报案的报道可以用戏剧性来形容。苏报案案发前,《新闻报》曾多次发表论说,批判政府,痛陈时局,指出导致革命党人和革命思想趁机而起的原因正是政府的无能与黑暗。苏报案发之时,却又发表《论革命党》,笔锋突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章邹等人,大加嘲笑。沈荩案发后,《新闻报》又回归原先立场,认为政府处置不当,“夫政府之拿获章邹谓之除逆党,政府之拿获沈克减,咸谓之翻旧案,非不可翻,特宽政之上谕煌煌在人耳目,故无论旧案,已许人自新,即未尝许人自新,但使其人实已大改从前之所为,则亦既往不咎,故即康梁回国,亦可不加之罪,而况沈克缄之案乎?”[11]同时对沈荩、章炳麟、邹容表示同情,“乃上海方在办交犯之案,而北京忽插入沈克诚一案,同时并举,于是天下以冤沈者转而冤章邹二人。”[12]但尽管如此,《新闻报》的立场仅限于批判政府,绝不颂扬革命党,分寸把握得当。 《新闻报》言论突然变化,直接原因是一度被官方操纵。苏报案发生后,为争取在舆论上主动,推动案犯的引渡,负责该案的湖广总督端方指示,“《申报》及《中外日报》,能为运动,使之助力尤好。”[13]但最终选择《新闻报》,直接原因是《新闻报》的老板幕后福开森一直被端方所倚重,同时福开森也是上海道台袁树勋与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工部局之间就苏报案交涉的重要斡旋者。《新闻报》主笔金煦生是端方亲信金鼎的弟弟,又是福开森的学生。于是,《新闻报》遂有《论革命党》一文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论革命党》不是一般的报纸论说,而是清政府策划的一个圈套,目的是搜集更多章炳麟、邹容和《苏报》的反清革命言论作为庭审指控的证据。因为当时章炳麟的《馗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中直接明确的“排满”革命言论并不多。《论革命党》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完全以挑衅口吻,点名攻击章、邹等。狱中的章炳麟果然被激怒,一鼓作气写出《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7月6日的《苏报》上,文中遍布“仇满”、“排满”字样,果然中了政府的阴谋。不过,作为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新闻报》最终回归到原先的立场,推测起来,这很大程度上与该报经理汪汉溪奉行的“经济独立,不接受津贴”原则有关。 中文报纸中,对苏报案比较关注的还有《中外日报》、《国民日日报》、《华字日报》等,三者的表现和态度也与前两者不尽相同。 《中外日报》此前与《苏报》就有矛盾,这与它坚持维新的立场有关,而《苏报》则推崇革命。不过,苏报案发之后,《中外日报》并未落井下石,而是持一种局外中立的姿态,既批评政府不应该采取镇压政策,“即如《苏报》与《革命军》,向不见重于社会,不知其名者颇多,即知之者亦无暇一览,西人更未齿及。自此案出,乃人人欲索而观之,日来外埠之来申觅此者甚众,而西人亦争译以去,是不啻国家为之登求售之告白也。”[14]又批评革命党人有诸多缺点,如有宗旨而无方法,有议论而无心志,只会空言革命,流无益之血等,认为革命党没有前途。[15]《国民日日报》在苏报案上持有鲜明的立场,即颂扬革命,塑造章、邹等人的反清英雄形象,同时讽刺清朝政府,指责政府腐败无能。《国民日日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转译外文报纸的内容,前后共有30多篇,大部分都是支持革命党或者有利于革命党的内容,指出苏报案的被关押者是中国推翻野蛮政府的有志之士。“中国有志之士观政府之日非,不利己也,亦摧陷之而靡己,而令野蛮政府仍立于天地间,且推翻政府之热度,日加而愈高,而政府恶其两者相持不下,使吾文明各国不能助志士之力,是吾人之所耻也。”[16]《中外日报》与《国民日日报》表现的差异与报纸主持者的身份差异密切相关。《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国民日日报》名义上是一份外商报纸,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在上海办的报纸,被称为“《苏报》第二”,背后有章士钊、张继、苏曼殊、柳亚子等人参与运作协调。相比上海本地中文报纸都有代表性的态度或观点外,身处香港的《华字日报》则类似于一个公共论坛,守旧保皇、赞扬革命等各种言论都能觅得踪影。 三、外文报纸的一致批评 与中文报纸舆论交错不同,外文报纸几乎是众口一词抨击清政府的所作所为。 他们一是批评清政府保守,认为苏报案与沈荩案都是对改革力量的镇压。《纽约时报》报道沈荩案时就称“沈荩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改革者”,[17]“慈禧太后下令处死沈荩是为了威慑改革者”,[18]《泰晤士报》称苏报案被关押者为“改革者”或者“主张改革的新闻记者”,[19]《纽约时报》称章炳麟等人为“中国的改革者”,[20]或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21]《泰晤士报》借此多次嘲笑清政府,6月6日的评论《针对改革者的行动》(Action Against the Reform Party)中说“这个事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北京和地方政府的糟糕状况。高官对失去东三省和国家的内忧外患漠然置之,但是对一小部分爱国者却高度警觉,这些人的主要罪行不过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和废除满族人的特权。”[22]8月13日的评论《年轻的中国》(Young China)评论说,“苏报案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中国政府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他们使用一半的热情保卫国家的其他权利,中国也不会沦落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23] 二是指责当时中国司法制度落后野蛮,案件审理未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认为慈禧太后仍旧是一个暴君。《字林西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沈荩案完全就是北京官方的野蛮谋杀,是中国司法制度滞后的表现,“审讯没有出示证据,甚至没有说明谁指控、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仅仅是中国式的讯问,以酷刑促使其招供……”[24],判决也不是由主持审讯的法官作出,更没有公开审判,而是报告给皇上,由皇上作出最终的判决。在这背后,显现出“慈禧太后还是那个1898年未经审讯就处决六君子的慈禧太后,还是在1900年参与除掉在华外国人的阴谋并将忠于她的大臣处决时的慈禧太后”,[25]《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也指出,“老太后的令人置信的愚蠢,使得沈克伟(即沈荩)被乱棍打死,引起了满洲人极大的惊恐……”[26],《纽约时报》称慈禧是旧式的篡位者、残暴的君主,是对残酷暴行有特别嗜好的恶妇,是希腊神话中的怪兽鹰身女妖(Harpy)。[27]这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慈禧为“凶恶老妇人”[28]的评价如出一辙。 三是反对移交苏报案的被关押者,声称人权高于主权,中国的落后使得它不配于西方文明国家对等。“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文明的政府,它的腐败臭名昭著,欧洲各国在条约或者待遇上没有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象。我们之所以强调治外法权就是要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仍是野蛮的——这在苏报案中也极其重要。”[29]“为什么在山东、满洲、蒙古和其他地方,中国的主权根本不被当回事,但在租界,中国的主权却成为了忽略正义和公平传统的充足理由?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损害中国政府的尊严和权威成为欧洲各国的关怀对象?”[30]《纽约时报》甚至直接声称,“无论美国驻华公使(注:指康格公使)的个人态度怎么样,但是美国政府不能将这些不幸的人交给慈禧太后,以及她那些可怕的宠臣手里,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命运。”[31] 当然,外文报纸论及的主题还有很多。(1)维护租界言论自由。1903年7月1日,即章太炎被捕的第二天,《字林西报》就刊登了《本地新闻界的自由》(The freedom of native press)的评论,要求公共租界当局保护租界的言论自由不受侵犯。《苏报》馆在未经审讯就被查封后,《字林西报》又刊登《违背公开集会和言论自由的行为》(The prohibition against public meeting and free speech)的评论,指责租界工部局;(2)呼吁各国态度统一。如《泰晤士报》在得知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和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倾向将章炳麟等人移交清朝政府后,立即呼吁各国态度统一,支持英国政府拒绝移交被关押者的立场,“事实上如果法国人民同意吕班先生的态度,或者美国人民支持康格先生。即使是有保留的外交辞令,我们将会感到十分惊讶。相反,我们相信世界上最老的和最年轻的共和国的居民一旦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就会衷心地支持英国政府的行动和意大利公使的理由。毫无疑问,日本政府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方针,当奥地利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会站在起码的正义、民族荣誉和公平的一边。”[32](3)批评所在国政府。在美国政府表态拒绝支持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后,《巴尔的摩太阳报》还是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动作迟缓:“此前,英国和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不同意移交上海的新闻记者给中国政府……如果有任何改革者接受公正审判的担保,就没有理由拒绝移交他们。但是移交他们去送死,受野蛮的酷刑折磨,并不符合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独立的理念。因为这些记者,除了公开他们对政治问题的观点,没有更多的罪行。我们的政府在作决定方面令人奇怪地缓慢——但是迟总比没有好。”[33] 外文报纸的报道立场,毫不掩饰它们的西方文化价值中心,对清朝政府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又极力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认为一旦释放苏报案的被关押者,将会成为清朝政府冲击租界权力的缺口,“不久以前我们提到,中国政府起诉在《苏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真正目的是确保对有问题的报纸的镇压,进而形成一个先例。在租界,中国人被认为受到保护而免于被中国官员起诉,如果道台可以镇压租界里令人讨厌的报纸,那么内地的反动官员就会利用这个先例以加强他们的力量。”[34]即便是后来外方作出让步,同意上海知县汪懋琨作为清政府更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到会审公廨的审判中,列强也强调“公共租界当局希望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不构成先例。”[35]直接言明列强对司法管辖权的坚决态度。 四、中外政府对舆论的关注 外文报纸对苏报案的报道,很大程度是由当时驻华记者和通讯员的立场决定的。 这其中必须提及的两个人,一个是濮兰德,一个是莫理循。前者是《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同时担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向来对清政府态度傲慢。此前就曾经帮助过躲进租界的康有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并一直派船护送康到达香港。莫理循的身份是《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其影响力被称为“一篇报道胜过朝廷的十份奏折”。他是最早向西方报道义和团围困外国公使馆消息的记者,对中国政治上层和远东局势极为了解,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关系极为密切,被西方人称为“北京的莫理循”,直接影响西方国家的对华态度。 苏报案中,两人一南一北,共同反对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在莫理循致濮兰德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濮兰德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毫无必要与其他列强协商苏报案的处理,“我向上帝请求,希望你不要示弱,要迫使英国政府支持你。”[36]对于英国公使萨道义,他直接建言,“我们英国是在上海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应该显示我们的实力,而不应该总是让步。”[37]由此也可见,作为记者的莫理循,其言论和观点都深刻地影响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和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同时他们的报道也引起英国本土官员的关注,这在沈荩案中已有论述。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在苏报案中反对移交被关押者的报道,让支持将被关押者移交清政府的俄国驻华公使大为光火。英国的外交档案记载,“俄国公使在表达了鼓动谋杀不是政治罪的意见后,又因7月29日的电报公开外国代表在苏报案问题上的意见谩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38] 同样,美国政府也非常关注舆论。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一直很关注上海本地公众舆论的反应,随时向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汇报,如在7月9日给康格的信中说:“据我们所知,公众舆论认为与《苏报》有关系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极力反对将他们带出公共租界,因为一旦在租界之外审理,他们非常可能会被草率处决。如果根据清政府的坚决要求,公使团将这些人交给中国当局的话,我估计那会非常麻烦。”[39]7月16日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也提及,“中国政府说被关押者有罪,要求公使指示领事命令工部局将被关押者移交中国政府惩办。人犯关押在工部局监狱。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将被关押者移交给中国政府不经审判即处决。”[40]7月25日给康格的汇报中,古纳又提到了上海本地报纸,特别是《上海泰晤士报》和《捷报》反对引渡的态度十分坚决。[41]沈荩案发生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清政府,美国国内报纸《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也指责美国政府在苏报案中的立场。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决定了最初态度模棱两可的美国政府是不会在一片人道主义谴责声中逆势而行的。 尽管没有证据直接表明中文报纸的报道引起了政府态度和措施的改变,但新闻报道这种现代化的信息流动方式,还是引起了清朝官员的注意。 苏报案发生后,端方就非常重视沪上舆论,要求专门派往上海的探员志赞希、赵竹君、金鼎等人关注上海报纸的言论动向,随时汇报“各报馆议论如何?”[42]并提出“运动”《新闻报》或者《中外日报》的想法。后者则奉命一直监控各报的舆论立场,“……申报持论甚正,新闻亦然,中外报不易化导。”[43]同时“命令律师将《苏报》和《革命军》诸谬说译成英文,登于《字林西报》,俾众咸知其谬”。[44]不久后,端方又秘密联络《新闻报》的幕后老板福开森并转主笔金煦生,要求明确“六犯确系中国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毁谤皇室,妨害国家安宁,与国事犯绝不相同,务将此义著为论说,登诸报端”,认为“该犯已犯众怒,此报一出,众论翕然,不必游移。”[45]对于金煦生在组织舆论上的积极表现,端方也专门发电表示嘉奖,“此事深倚大才,为国出力,拿获逆党,金令世和,竭力相助,均甚感佩。”[46]在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后,金鼎得意地说,“新闻报《论革命党》用讥讽之法,逆党果中计。有闰五月十二日答说一篇亲供,宛然自认。”[47]这也让我们看到,清政府通过媒体,从单方面密切关注走向了策略性利用,进一步加强了与司法外因素的联系。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文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也让普通民众知晓了苏报案的发生,听说了革命排满的改革诉求,扩大了革命影响。“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通过国内外新闻传媒的广泛报道,扩大了影响,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结局是清朝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48]而最直接的层面还是在对本案的司法判决上,被告律师琼斯就指出,“此案东西各国均已知之,现在定案时,各国莫不留意,须请堂上照公法判断,不能凭政府之意。”[49]试图以舆论的影响来制衡审判,防止主审法官恣意枉断。 五、简短的结语 稍加对比就可发现,中外报纸对苏报案的报道与评论是对苏报案的同步建构,影响着苏报案的走向,乃至最后的解决。尽管这个建构与苏报案同时发生,但却有差异,特别是中外报纸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事件价值的取向不同。中文报纸对苏报案新闻价值的关心程度,远远不及苏报案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所有报纸都将偏好从苏报案的原因切入,讨论维新与革命这对政治上的二元对立项,而且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其中,《申报》厌恶新思想,痛恨革命党,表现出守旧的立场,因而常常使用极端的言辞;《新闻报》与《中外日报》不赞成革命,但对革命党态度不尽相同,前者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后者则是怀有一定的同情,《中外日报》甚至希望朝廷能以苏报案为契机,痛下改革决心,推行宪政;香港的《华字日报》身悬大陆之外,吸纳各种意见,表现为一个“意见的综合市场”,对革命持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外文报纸中的苏报案主要是一个新闻事件,其中苏报案反反复复的交涉情况以及西方各国在苏报案上的态度变化是西方媒体报道的焦点。当然,外文报纸也发表许多评论,并且试图影响各国政府、驻京公使、驻沪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在苏报案问题上的立场。“外文报纸也有苏报案问题评论中国政治,但焦点不是维新与革命问题,而是指责中国政府保守,批评中国文化野蛮。”[50] 二是对待事件的态度不同。中文报纸无论坚持什么立场,都是中国人在讨论自己的问题,温和者积极建言,为政府出谋划策,激烈者畅言革命,矛头直指慈禧为首的保守力量。但是外文报纸,不论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还是在国外出版发行,往往表现出肆无忌惮的高傲姿态。对于苏报案,一致地保持着西方人的叙述和想象:苏报案是一起有关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案件,体现了中国保守的政治势力对进步改革力量的镇压,以沈荩案和过往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传教士被杀害)来看,中国政府是一个野蛮政府,中国文化是一种野蛮文化,充满了愚昧、酷刑等落后的因子。据此,外文报纸不仅坚决反对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而且要求对章、邹等人只能轻判。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外报纸对苏报案的建构差异主要与中西方报纸不同的背景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刚刚经历过戊戌维新和庚子之变两件重大变革,保守思想,乃至康梁倡导的维新都日渐渐弱,自1903年起,在拒法运动和抗俄运动之后,革命思想日益高涨,因此,保守、维新还是革命,成为中文报纸竞相争论的热点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于是,苏报案甫一出现,就为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一个契机和舞台,至于与苏报案直接相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如何争回主权、列强是否应该交犯等问题,只有参与苏报案交涉的清政府官员关心,并没有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但外文报纸却认为苏报案实质是中国政治进程中进步势力与保守力量的角逐,是革命者被镇压、新闻记者被迫害的案件。因此,他们毫不掩饰对中国保守势力的厌恶与对苏报案被关押者的同情。加之本案与此前发生的戊戌政变间隔不久,很容易被引申为中国政府对改革力量的再次镇压。加上西方人眼里的“刻板印象”:中国政府野蛮残暴、中国官员顽固保守、中国司法落后残暴等等,都成为外文报纸评论苏报案问题的预设前提。 这些1903年前后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典型的“权利话语”,与当时各国的外交档案、往来电文一起,呈现出苏报案中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 另一个角度,从现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来说,传媒对于司法的报道,必须恪守公正与平衡的态度,并且必须保证不能影响司法裁判的过程与结果。但在当时,这些报道差不多都是具有特定立场的,报纸背后的主持力量决定了新闻的言论倾向,其传播效果对司法的影响没有被媒体考虑在内,有的报道甚至就是为了对司法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和租界没有新闻法律法规有关,与苏报案背后各种力量的角逐有关,更同传媒与司法的天然密切性关系相连。其实,回望现实,当下的影响性司法个案,谁又不是在传媒舆论的包围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