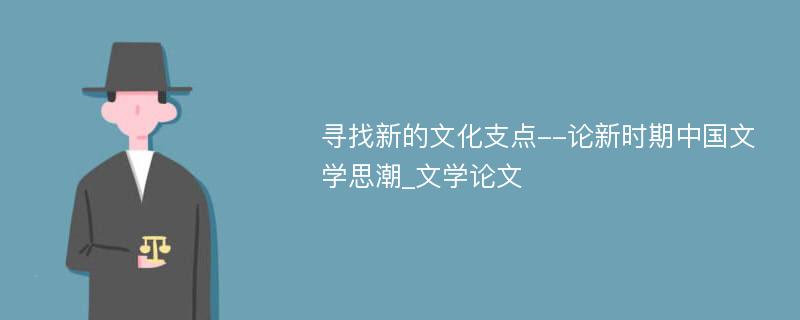
寻找新的文化支点——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支点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丰富多彩。促成思潮起落的原因众多,其中有一点是内在的、重要的:新时期文学穿透了政治的表层,进入到了文化层面,中国文学在用自己的探索,为中国人寻找新的文化支点。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一、社会批判文学思潮
1976年10月之后,中国文学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推倒文学身上左的束缚。不完成这一工作,新的文学便无法迈步。于是,文学开始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四人帮”、对极左政治、文艺倾向进行批判,对建国以来的历程进行反思,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揭露。这是文学在新时期掀起的第一次大的思潮。它既是大陆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力,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思潮是从揭批“四人帮”文艺思想开始的。“四人帮”曾将十七年的文艺诬蔑为“文艺黑线专政”, 又为文艺制定了一整套规定。 1976年之后,文艺界首先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倒了其“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一切强加给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和政治镣铐,批判了其“三突出”创作原则、“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思想,批判其“阴谋文艺”。文艺生产力得到了初步解放。文艺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有一种寒冬过去、春天来临的解放感、喜悦感。大家群情激昂,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要真正繁荣文艺,仅仅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远远不够。中国文艺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其实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与更大范围内的左倾倾向紧密联系着。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左倾错误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1978年5月,中国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口号,向一切禁锢思想的樊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文艺界积极参加了这一场大讨论,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1.推倒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中国文艺从1942年开始,其主要任务便是“为政治服务”,一直演变到文革,“四人帮”利用文艺搞政治阴谋。1979年1月, 上海《戏剧艺术》发表了署名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了质疑。三月,《文艺报》召开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之一讨论。四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随即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文艺界调动一切力量推倒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这场斗争的直接结果是1980年上半年,党中央作出决定,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从政治附庸的地位解放了出来。
2.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光荣传统”的口号。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提倡现实主义。但在文革中,现实主义走向了“假大空”,文艺不能表现人民的真实生活。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为现实主义招魂,呼唤文艺真实地反映现实,表现人民的疾苦。
文学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上展开,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三大思潮都在社会批判层面,共同构成大的社会批判思潮。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刘心武、卢新华先后发表了小说《班主任》、《伤痕》。小说没有停留在对“四人帮”的一般批判上,而是深入揭露了十年动乱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造成的创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内伤”。这些作品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也有人不满意,认为它是“暴露文学”、“缺德文学”,因而在文坛内外爆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讨论中,现实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人们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去面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时候,作家们发现,中国的左倾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早已存在着。于是作家的揭露批判便超出了文革的范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里反思已经走过的路。这就出现了反思文学。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品把反思的触角伸到了大跃进、反右等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之中,生产了巨大反响。
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一部分作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之中,当时的现实是祖国百废待兴。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大声呼唤改革,引来了“改革文学”的热潮。当然,当时的改革大多只在政治思想层面,还未能深入到经济与文化,但在当时却已经产生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二、人道主义文学思潮
文学在对左倾思潮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发现左倾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中国的封建思想有着直接渊源。文学于是穿过了社会政治层面,进入了对文化思想的思考。人们认识到,当祖国在左倾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人都变成了工具、变成了某种观念的奴隶。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最大的问题是,人,没有被当成“人”看待。文学开始借来西方的人道主义,在文本里书写着大写的“人”字。
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并不始于七、八十年代。早在“五四”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猛烈批判了封建文化,并从西方文化中为重构中华文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人。周作人在《新青年》五卷三期上发文认为,所谓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当时的文坛立即刮起了“人”的旋风。以致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论里说,《人的文学》是“当时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重要的宣言”。那是一个呼唤“人”的时代。从拥护德、赛两先生,到文学改革,再到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从诞生起所做的一切都与“人”的呼唤有关。但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始终联在一起的。当民族危机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人道主义的声音自然演变为民族主义的声音。
十七年时期,针对文学的创作中存在的弊端,钱谷融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但遭到不应有的批判。长期以来,人性、人道主义一直成为文学的禁区。八十年代,人道主义的声音再起,接通了五四人道话语的源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批作品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鼓吹以人为目的。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文学作品首先挖掘人物的人性美、人性美。叶文玲的《心香》、张抗抗的《北极光》、刘心武的《如意》、丛维熙的“大墙文学”都写出了感人的心灵,使人受到美的熏陶和震憾。
随着人道主义讨论的深入,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人物的内心,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打破过去那种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的格局,跳出从抽象概念出发的人物塑造方法,使人物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个活生生的个性。方之的《内奸》、苏叔阳的《故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内涵复杂深刻的人物形象。
理论上,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理性到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等几个世纪的人道主义话语,中国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全部温习了一遍,并将西方不同时代的话语混杂地压缩在自己的讨论中。当然,这些讨论也有重点。重点之一是,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人们认为,人性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这当然并不是新鲜的见解,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特殊的含义。1976年之前,在中国的理论中,“人性”往往被等同于“阶级性”。人的“自然性”被排除在人性之外。因而,文革后对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双重强调,便是特定语境里的话语策略。它是中国构词法里“危及存亡”式之偏义复词结构,而不是“悲欢离合”式的平分秋色之联合结构。在既往话语中缺席的人的“自然性”现在堂皇出场,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强调、一种重视。
正是基于对人性复杂性的肯定,理论家刘再复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这一原理认为,“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1〕人,是魔鬼与天使的产儿。 刘再复提出这一理论主张,是希望促进把人作为“根本出发点”。“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美学原理,它首先承认‘文学是人学’这样一个经典性的命题”,希望“促进我们的文艺创作向人性的深层挺进、更辉煌地表现人的魅力。”〔2〕
仅仅指出人的复杂当然并不够,因为人既是有生命的复杂的个体,又是有意识的主体。对个体生命的深入把握,必然导向对主体的能动性的重视。于是,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刘再复接着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的命题。这一命题直接源于康德。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3〕在阐述康德哲学时,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说, 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刘再复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学研究之中。他认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人道主义。他说,文学就是要以人为主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的文学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4 〕“主体性”在中国曾失落于历史的荒草丛中,今天,我们应该在叙事中将它找回并确立,在文学中“恢复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主体性命题把人放在对象中,放在实际中去考察“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5〕,张扬主体的自由。
有意味的是,论者在论述主体自由、无束缚的创造时,却给主体偷偷加进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通过论者的叙述,把从某种意义上对人的要求,或者说社会指令转化为主体性的内在规定。这里有一系列的话语转换。比如,作家有主体性,但主体自由并不意味着创作中的为所欲为,作家的主体是有层次的,其最高层次“是作家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要把爱推到“每一片绿叶”。“只有爱他人时,自身最有价值之东西——自己的良知才能获得实现。”要懂得爱“人民”。因而,主体性的题中之义是必须具有高度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那是“与人世间的苦恼相通的博爱之心,是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精神。”〔6 〕结论出现了这样的逻辑:只有遵照这些“规定”、“使命”,主体才能找到“自由”。
在这样的论述里,“主体”向“人民”靠拢,小“主体”向大“主体”交融。它既有康德理性思辩中道德律令的影子,也有20世纪80年代人文工作者的思考。“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把“五四”时的人道主义话语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把“人”的主题推到了一个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落点”。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以后的文学与文化思考中仍然存在着,但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思潮的人道主义受到了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强烈挑战,再也没有出现过昨日的辉煌。
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人道主义思潮在文革后出现有其历史、现实的必须性,对推进文革后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人道主义思潮是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几个世纪的哲学文化追求。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粉碎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迷梦。
那么,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否还适用?是否还能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新支点?新一代学人和作家在思考着。就在刘再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的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现代主义的描述。〔7 〕其根本用意不在于改写既往的历史,而在于推动正在行进的历史,推进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登陆远不在1985年。新文化运动前夕,早在尼采去世后两年,即1902年,梁启超便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尼采,把他称为“个人主义”。1904年,王国维发表《叔本华与尼采》。1908年,鲁迅在日本发表《文化偏至论》也介绍了尼采。
新文化运动开始,对现代主义的评介、借鉴曾有过几次高潮。“五四”时期,尼采、柏格森、费洛伊德等人的学说都得到过不同程度的介绍和讨论。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不少领袖及中间人物,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都写过评介现代主义的文字。创作上,20年代不仅在创造社的理论的主张和创作里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30年代出现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风等小说创作的新感觉派小说和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
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要么被进行人道主义的误读,要么谦和地以人道主义的同路人身分出现,一直未成为独立而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
历史翻去一页,当我们在“文革”后再次见到现代主义时,它已潜在地具有现代史上不同的地位与姿态。
人们曾喜欢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它们确实有某些相似处。然而,历史并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原处。“文革”后与“五四”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语境。其最大不同表现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的摧残是从肉体到精神的话,那么,“文革”则是直接进入人们内心的摧毁战。当“文革”把人们从虔信引向怀疑时,那坍塌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忠诚和热情,而且是一系列成套的人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和意义崇拜。
这样一个语境,便使“文革”后关于“人”的话语隐藏在一个“确立/消解”的内在紧张之中:刚刚觉醒,便已陷入困惑;刚刚从梦中醒来,却又进入另一个大梦,刚刚还在确立,却已进入焦虑和软弱无力;刚刚感到世界的美好,却已踏入孤独;刚刚看到一个充满信心的未来,却已袭来了荒谬。
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话语欲望首先从艺术形式的变革上表现出来。这不奇怪。国门打开,人们自然要学习西方的艺术手法。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坛出现了“朦胧诗”,引起了一场关于现代派诗歌的讨论。其实,朦胧诗只是在手法上有些现代主义的影子。但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却为国人初步打开了现代主义的视野。80年代初,王蒙连续发表了《春之声》《海的梦》《布礼》等六篇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小说,同样引起了讨论。同一时期,作家高行健写了一本理论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围绕这本书,李陀、冯骥才、刘心武等人利用书信方式讨论现代主义,在文坛的天空放出几只“小风筝”,进一步推进现代主义的讨论。
当然,这些讨论还只限于技巧、形式层面。意识形态上,当时的“现代主义”仍然是反叛封建的人道主义的同路人。
然而,现代主义形式的“引进”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主义的“内容”。这个“内容”又恰恰与“文革”所给予中国人的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相通,提醒给人们一种对文革的新读法,对人生、对世界的新读法。随着对现代主义借鉴的不断深化,八十年代初还只潜藏着的现代主义终于跳出了人道主义同路人的身分,公开打出了与人道主义分庭抗礼的旗帜。
1985年,出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一批作品,以全新的面貌吸引着文坛。作品表现了鲜明的非理性色彩,书写人的孤独感、分裂感、苦闷感。作品里流动着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柏格森的“生命之流”。当人们还在刘索拉等人的作品中兴奋的时候,又突然出了个残雪。她以《苍老的浮云》等一系列作品书写着荒诞。残雪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文革。她的笔下,世界是一个丑、虚无、无意义的世界。她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对世界的解读。批评家发现“在残雪小说构筑的梦境或幻象的世界中生存的是一个孱弱的、恐惧的、孤独的灵魂,处在一种失去了安全感的恐惧中,在丑恶和梦魇的包围中一直走不出来。”〔8〕
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一批作家走着另外一条路。他们的作品《烦恼人生》、《风景》、《一地鸡毛》等,表面上运用写实的手法,但却失却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里的那种精神。他们的作品将情感处于零度,对任何人和事都不作褒贬和判断,这里的“人”也失去了往日的神圣,成了锁碎事物中的忙碌者。
这样一批作品打破了在人道主义叙事中的那个完整、崇高、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形象,颠覆了人道主义叙事中的理性精神,嘲笑了人道主义叙事中对世界的乐观情怀。中国人从世纪初开始追求的作为文化建构的新支点受到了怀疑。
四、“寻根”文学思潮
作为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能否作为中国文化重构的新支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人们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当一部分人在对人道主义进行战略策反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把目前投向了自己的传统,他们希望从传统中找到新文化的生长点。他们认为,文化建设没有自己的“根”不行。他们认为,“五四”使中国文化与传统形成了断裂。于是,他们要“寻根”。
寻根文学思潮也产生于1985年。
韩少功最先用“寻根”来表述他们这一批作家的思考。他在1985年《作家》第4期上撰文指出,“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应穿透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表层。在他看来,“不是地壳而是地壳下的岩浆,更值得作者们注意。”他说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9〕同年7月,阿城在《文艺报》上发文支持韩少功的观点,他说,“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他认为“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10〕
“寻根文学”有一批十分突出的创作实绩。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以及王安忆、郑义、莫言等众多作家的作品。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在寻根文学中颇为引为注目。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对以庄禅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之“根”进行着力挖掘。这一“挖掘”突出表现在王一生这个形象上。王一生的典型特征是呆、痴、淡。他为棋而呆、而痴,其他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淡。在神州大乱之时,他不问世事,痴迷于下棋。他下棋是为了排忧解闷,以求心灵清静和精神自由。他的棋艺高超,“汇禅道于一炉”。这既是他的棋道,也是他的人道。他的性格里表现出一种淡寂、虚静。
阿城对文化之根的挖掘又不止于庄禅。他那“道”的外衣里有着“儒”的筋骨。王一生的性格里,淡泊之中有崇高,虚静之中有壮烈。阿城既喜欢庄禅的超脱旷达,又不回避儒家的进取精神。这二者,被他统一在王一生的生命形态里。
阿城还创作了《遍地风流》系列短篇。这一“系列”里的众多人物干脆脱去了平淡、无为的外衣。那里的马帮首领、骑手和其他汉子们都强悍、豪爽、精干,洋溢着生命的伟力。阿城笔下的人物不都是汉人,人物身上的文化因素也不只是汉文化。阿城的审美世界里包含着并不囿于一子一家的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他在他的故事叙述中进行着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再造。
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着力描写吴越文化圈里的人物故事。李杭育的文化意识里有着强烈的当代感。李杭育善于塑造变革时期的“最后一个”们。他们都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时代前进了,他们却仍然生活在自己封闭的心态里,不愿跨过新旧交替的“楚河汉界”。但作者在表现人物悲剧的同时,又努力挖掘他们身上为吴越文化所重视的人格价值、人格力量。如《最后一个渔佬儿》里的福奎,身上有一种不屈的强者性格,表现出“南方人的生命的元气和强力”。〔11〕这些是能超出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事件而闪耀持久魅力的东西。
民情、风俗和风景的描绘是李杭育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作者象一位丹青能手,往往在作品中大篇幅地描绘葛川江两岸的山水人情,构成一种文化氛围。李杭育笔下的风俗是性格化的,与他的人物相辅相成,共同表现出吴越文化中人格舒展的力与美。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都有些魔幻色彩。《爸爸爸》里的鸡头寨人是刑天的后裔。后裔里有一个丙崽。丙崽从出生就奇怪:两天两夜不吃不喝,第三天才哇地哭出声来。一辈子只会说两句话,一是“爸爸”,一是“×妈妈”。作者在丙崽这个形象里注入了对传统文化的独特思考,使丙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复杂形象,可作多种解读。有论者认为作者用丙崽批判了“民族劣根性”。而他对万物的承受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却又隐藏着鸡头寨人自刑天传宗以来生生不息的奥秘。丙崽将简单与神秘集于一身。他带来了争斗也带来了活力。在这争斗与活力里,演出了刑于后裔们的历史。
“寻根文学”为文学的文化思考开辟了又一条思路。这是一条在二十世纪被反复提出又被反复忽视的思路。寻根文学将它落实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显示了一定的实力。
五、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8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时期。文学往往轻而易举地造成全社会的轰动。9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经济改革的高潮。文学的“轰动效应”失落了。但文学的思考仍然在进行着。更年青的一代从西方引进了“后现代主义”。这一引进,将现代主义思潮已经进行的对人道主义的反叛加强了。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共鸣,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里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国以前的“世界”是统一的,它统一于单一而具有凝聚力的价值观。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统一价值观的破碎。正如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所说:“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乌托帮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2〕当然,中国远未进入后现代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也刚刚开始,但它对传统价值法则的冲击和它带来的新的世界图景,却足以使敏感的作家、批评家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欲望。
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一批作家以与刘索拉们更加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文坛。《褐色鸟群》、《请女人猜谜》、《锦瑟》、《水神》等一批作品破坏叙事时间,制造文本断裂、营造叙事圈套、消解文本与现实的界线,津津有味地玩着文本游戏。批评界认为,他们在通过颠覆文本来颠覆人道主义眼中的社会理想,用游戏文本来游戏人生。
与这批作家形成异曲同工的是王朔。他的文本并不断裂:作品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北京的都市青年。他们是一批“玩主”。作者用他们的故事来书写一种游戏的人生态度。王朔的作品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后现代的文学探索中,还有女性主义文学的身影。它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重要行动。陈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作家探索一种与男性不同的文学叙事,她们大胆书写女性个人的独特经验,张扬女性意识,颠覆男权话语中心,《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一批作品被命名为“女性个人化写作”,受到广泛关注。
如果说创作只是在作品里隐藏着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的话,理论批评则更直接地“拿来”了后现代主义。几年前对中国人来说还相对陌生的名字的,福科、德里达、拉康等等,一下子成了一部分读书人热心讨论的话题。理论批评界向人道主义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人”,在这些理论批评家眼里,“变成了一种虚构之物,一种想象性的实在”。〔13〕人,在现代主义那里已经分裂了,成了孤独、苦闷、荒诞、焦虑的存在。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个分裂的自我在。但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那儿,都被“耗尽了”。后现代主义言说者们逃离“焦虑”与“荒诞”。取代“焦虑感”与“荒诞感”的,是游戏精神。因此批评家乐意捕捉并高度理解先锋文学中的游戏精神。他们指出,先锋作品中“充满了能指和所指符号的无端角逐和游戏活动,它们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乃至相互颠覆,既拆散了文本的内在结构,同时也播撒进而消解了语符的意义。”〔14〕游戏,不仅成为理论批评家的把握对象,更成为批评家的策略,他们或将批评视为与作家玩的智力游戏,或在自己的文字里进行自我颠覆的游戏活动,把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智力游戏。
与游戏精神相并行,理论批评致力于“拆除深度”。深度消失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化的一个标志。后现代创作不追求表达某种思想,因而它不去追求某种深度。它呈现的是一个平面、一次游戏。深度拆除了,文字便剩下了叙述圈套。因而理论批评家对作家们的叙述圈套也津津乐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消解“意义”。后现代主义的言说者们要消解人道主义为这个世界创造的意义。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寻找新的“意义”创造基础。
因而后现代言说者对经济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对大众文化给以了肯定。他们要从这里寻找新文化基因。
六、逃离“后现代”的文学新探索
后现代的一系列新名词因为远离大众而使其言说显得异常艰难,90年代中期,文坛逃离后现代的力量崛起,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一批作家带着他们的《分享艰难》、《大厂》、《车间》等一大批作品迅速崛起。这批作家首先表现了修复故事的努力,他们的叙事不再制造断裂,不再破坏时间,他们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精心构造一个读者愿意读的故事。更主要的是,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投向了艰难中的人生。他们致力于写改革中人们碰到的种种困境,写困境中的人们的奋斗与相濡以沫。他们不再游戏,他们寻找意义。其作品往往都有着一种情感的冲击力。这批作家作品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差不多同时引人注意的是“新都市文学”。张欣、邱华栋、殷慧芬等作家致力于书写经济变革时期的都市人生。这些作品不追求虚幻的理想,它首先面对真实的人生。都市欲望在这些作品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作品书写都市人为满足自己各种欲望而进行的拼搏与挣扎。但这些作品又不同于“后现代”的游戏精神。它们追求着人与人的精神交流、追求一种诗意的人生。张欣的《如戏》、《伴你到黎明》等作品受到人们的称道。
创作里表现出来的文化思考在理论批评里以更加鲜明的形态展现出来。人道主义不能作为中国文化建构的新支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行吗?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把西方话语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把西方之路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后现代主义帮助中国人从“西方中心”里走了出来,也帮助中国人认清了西方话语的盲视。但同时,后现代主义也不能作为中国文化重构的新支点。人们再次把目光从西方移回到传统。于是90年代在学界出现了“国学热”。人们重新研究国学,从国学里寻找资源。一时间,国学大师陈寅恪、章太炎、王国维等等都成了热门话题。京城出现了《学人》、《原学》、《原道》等民间刊物,用较大的篇幅对传统文化进行讨论。
在文学批评界,90年代中期出现了“人文精神”与“后学”的讨论。“人文精神”论者认为,商业大潮中人欲横流,人文精神失落了。他们反对“后现代”的游戏精神,要求重铸人文精神。而“后学”则认为,当前主要的工作还在于对传统话语进行清理。他们认为“人文精神”论者对传统话语中的盲视清理得不够,这样的“人文精神”只能走向传统的误区。他们反对“人文精神”论者对现实的敌视态度。他们认为,人文工作者不能拒绝“今天”。他们消解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认为知识分子在今天首先应该认清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在这样的讨论格局中,一种新的意见正在展开。另一批学者不同意讨论双方的偏激态度,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人文精神”,也不同于“后学”。他们既反对没有解构的建构,也反对没有建构的解构。他们主张在对东西方话语都进行清理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里寻找生长点,建构一种新的“有限理性”。
讨论并没有结束。前面的路还长。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化更新之路走了一个世纪,面临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们不得不进行总结与展望的工作。因而,90年代的任何文学、文化讨论,都不是某些个人的心血来潮。
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仍然是一个问题。
注释:
〔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版。
〔2〕同上。
〔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 期、 1986年第1期。
〔5〕同上。
〔6〕同上。
〔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张钟《残雪的小说世界》,《百家》1989年第5、6期。
〔9〕韩少功《文学有“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0〕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11〕曾镇南《南方的生力与南方的孤独》,《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文版),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
〔13〕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4〕王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当代电影》1991 年第6期。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