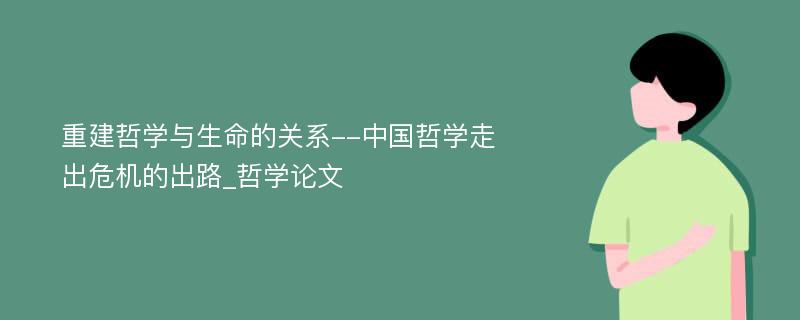
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中国哲学走出危机之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中国论文,途径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似乎人人都在谈哲学的危机。虽然大家对这个“危机”的理解很不相同,但承认“危机”之存在,却是一个共识。要摆脱“危机”,就要首先弄清危机产生的根源。中国哲学的危机,要而言之,其根源在于哲学与生活的严重脱离。因而走出危机的途径,亦在于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
古来哲学与人生、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哲学尤其如此。金岳霖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就是哲学家本人的传记,正恰当地说明了古代哲学的这个特点。中国古代的哲学,虽不可归结为知识,不可归结为人伦日用,但其功能,却在于对知识和人伦日用之反省、了悟及其意义之开显。《论语·子张》云:“君子学以致其道。”程子云:“学以至圣人之道。”(《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古人又强调实践工夫,强调为学不离人伦日用。何谓“不离”?孔子说得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谓之“三不朽”。“艺”,就是六艺,既指儒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亦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科,总之,包括当时落实人生的所有知识技能。什么是“游”?刘宝楠《论语正义》:“游者,不迫遽之意。”朱熹《论语集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故所谓“游”,就是不偏执,无“意、必、固、我”。小程子说:“不可将心滞在知识上。”(《遗书》卷二上)知识、技能、伦常、规范等,皆有所偏,有固定的形式。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犹今语所谓专家。孔子并非否定知识、专家或学有所长,他自己就是一个关于“礼”的专家。在孔子看来,知识、技能、伦常、规范等,皆有偏于形式化的负面作用,因而会蒙蔽人的心灵。儒家讲“解蔽”,道家讲“为道日损”,佛家讲“去执”,皆指此而言。人要有知识技能以求生存;但却必须具有超越社会形式化之蔽的解悟和穿透性的智慧,才能心不滞于知及僵化的形式,从而在现实人生之展开历程中领悟、开显人生之意义,建立人心灵之安宅。因此,“大上立德”,不是在“立功”、“立言”之外别有一抽象的“德”,而是即功业、学问成就而又能超越之,才能达成“德”的落实与完成。《庄子·天下》把古之道术的总体称作“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之学,依儒家理解即“仁智”之学。《孟子·公孙丑上》:“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即此义。此“仁智”之学,即今日所谓哲学。“圣”,《说文》解作“通”。“外王”,即人伦之道。“圣”之“通”,乃将哲学所成就之人格智慧,通贯和透显于人伦日用,日常生活(包括成就此生活之知识技艺)因而绽露出其精神的意义和理想的光辉。因此,哲学家不仅是智者,是有学问的人,而且是贤人,哲学即是他生活、生存之方式。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但却不是他的“职业”。“学而优则仕”,“仕”是中国古时知识分子贯彻其理想的最好形式。仕乃可将其学落实于人伦生活。哲学是“仕”、“贾”、“师”甚至“布衣”者的“业余爱好”或精神追求,而非如今日之谋生手段。哲学家由此则成为人的生活的精神导师。所以,古时所谓哲学,乃在知识之总汇和人伦日用中具体地显现,是以古人称之为切于身心的“为己之学”,而非别有所依、所求的“为人之学”。中西方哲学尽管有差异,在这一点上却有一致之处。
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哲学的状况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是实证科学脱离哲学成为一个个独立的部门,人文社会领域也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其次,社会的分工、学科的分工,使哲学从“业余受好”变成了哲学家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在科学飞速发展,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哲学家不再可能象古代那样统览人类全部的知识成果。这样,作为学院式的哲学,产生了两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从科学知识方面说,继续追踪一般的普遍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概括的哲学,由于不能深入科学自身诸领域而难以为科学家所认同;而由切入具体科学部门所形成的不同哲学学说,则又由于其高度的技术性而难以达到相互沟通,更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从社会的角度看,现代专业的分工,产生了如下吊诡的现象:不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和研究机构,再无法成为哲学家;谋生的需要又使个体的生活领域和心灵空间日益狭窄。这样,一方面,哲学成为专业哲学家的专利,现世的繁忙不再允许世人去“务虚”。王阳明那样带兵打仗的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以磨镜片为生的哲学家不复再生,日常生活失去了往日那种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另一方面,专业的哲学家也不再是贤人、圣者,哲学家对其理论不必身体力行,一个哲学派别,似乎亦只流于“说法”、“宣传口径”上的一致。哲学今天已颓变为仅仅是“说说哲学”而已,完全成为一种与其它行业无差别的、与实践(人生、价值、道德意义的)无关的“职业”。哲学脱离生活,导致了它对人的精神现实解释力量的缺乏。有人说,哲学家成了“孤独的一群”;更具体一点说,那是一个既人不我知,又殆乎互不相知的“一群”。
中国当前的哲学,既存在上述一般的情状,又因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有其特殊性,而其与生活之脱离则尤甚。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哲学的“无家可归”与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
谈到民众意识,我们这里不得不先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现代自“五四”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反传统。民众意识既极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引导,同时,在其现行中,却又极其固执地时时表现着深蕴其中的传统。因此,从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上,毋宁说它又是最为“传统”的。下面所谈,与此点有密切的关系。
从一般的哲学理论方面说,我国确曾有过哲学与日常民众生活紧密结合的时期。解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占据核心的地位。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的一般哲学理论亦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在缺乏外部世界参照的情况下(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兹不赘述),初获解放而当家作主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样态长期地保持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热情中。这使哲学与日常民众生活保有了一种非常态的“和谐”。“文化大革命”把这一点推到了极端:人人都是“政治家”,因而人人也都成了“哲学家”。学哲学,用哲学,农民有了“种田的辩证法”,工人有了“做工的辩证法”。哲学确乎“走”出了哲学家的课堂。但哲学与生活的这种非常态结合,恰恰是哲学的俗化和放弃责任。哲学“虚”而实之;民众生活“实”而虚之,都走上了“不务正业”之歧途。时至今日,一般民众仍习于把哲学工作者轻蔑地称为“搞政治”的人,恰正表现了这种文革的“后遗症”。物极则反。改革开放以来,上述“非常态的结合”已完全走向它的反面。国门开放以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反差,冷却了人们当年那种虚幻的意识形态的理想追求和政治热情,代之而起的是过度的对感性欲望满足的追求。今日民众意识的过分“现实”似乎正是对以往意识形态性的过分“理想”化的矫枉过正。人们不再“务虚”,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在要求“真实”。一方面,“穷怕了”的民众不再象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而是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和感性情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热情逐渐消退之后,传统的那种对人际亲情、温情的寻求又重新在民间意识中显露出来,传统的民间宗教活动,也有蔓延的趋势。一种原创的哲学理论,往往超前于现实;同时,理论形态一旦形成进而占据统治地位,则又会滞后于现实的发展。目前,我国一般的哲学理论,显然由于这种“滞后”作用而无法回应民众意识的变化。这种哲学状况,一方面由于未能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而难以为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所认同,另一方面,又与时下汲汲追求感性满足和人际亲情的民众意识难以协调。因此,这种哲学自然地在现实生活和民众意识的转变中被搁置一旁,受到冷落,失去“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触及灵魂”,引领人的精神生活的权威地位。失却了精神的甚至观念的内涵而仅剩一套单纯的“词语”,它已“无家可归”了。
中国传统哲学是植根于民众意识深层的传统精神之概念表现。单纯从学术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近年来有相当大的进展。多年来以“两军对战”为框架的研究模式逐渐被打破,有助于学者进入传统哲学自身以展现其本有的思想内涵;文化热亦推动了对传统哲学的多角度透视;国学经典著作大量重新校勘整理出版;各种关于传统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严重脱离乃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它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善。问题可以归结到这样一点,即这种脱离的根源在于传统哲学教化意义的丧失。一般说来,任何广义的文化形式,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有某种程度的教化作用。这就是佛家所谓“业力”的作用。身、口、意诸行,莫非“业”而影响心灵、气质。但就文化总体说,任一文化系统皆有一确立人心灵之安宅的教养本原。司其职者,在西方为耶稣教,在中国则为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哲学。耶稣教当然有其作为形上学的学理,但其作为宗教,则主要以一种情感的形式直接贯注于人的心灵生活以为现实人生之皈依。以儒家为主的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思想的形式,其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却要经历种种中介的环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哲学的形上价值理念主要靠官方倡导、儒化的士大夫阶层之治道、文学艺术、学校教育、民间宗教和艺术、宗法家族聚居的组织方式等形式行于民间生活。今日,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以及哲学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已经导致了这些中介环节的丧失,从而失去了传统哲学的研究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联系。“士大夫”阶层和“士林”(知识)阶层,包括作家、艺术家、一般的文艺工作者,所受的基本上是“半西方化”的教育。这个“半”字是指,其所学知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都是西方的;但却很少有人受到西方那种作为价值和教养本原的宗教精神的熏陶。而后者却恰恰是西方文化生命原创性之根。由此而来所形成的政治生活、学校教育,以及作为直接影响人之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便失去了传统价值理念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联系作用。其结果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完全退居学院式的研究领域,成为极少数专业学者所惨淡经营的事情,无法参与文化的总体氛围从而对民众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政治、道德教育也由于其观念上的“无根”而失去其实践的效力和教养的意义。从另一面看,这种“脱离”亦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学理研究与学者自身的生活实践显著脱节。就连一些以当代新儒家自许的学者,也由于不能力行其学说,甚至行为完全与其学说相悖而为人们所诟病。
民众意识乃“传统”之载体。但表现于民众意识中的文化传统,则同时又是一个儒学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面,须于其作为文化理论的哲学思想之阐释、透视、反思、自觉与升华中方能不断超越自身而与时俱新,表现出其原创性的活力。表现于民众生活、习俗、心理中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哲学分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不同层次,在这一点上,学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性质及其关系,却有极不同的理解。近来学界对此有两种与本文有关且颇具代表性的看法,需要略作检讨。其一,认为传统文化可分为自觉或自为文化与自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积淀,表现于传统习俗、经验、常识中的)文化两个层面。在自在文化的层面上,不同民族间不存在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仅在于自为文化与自在文化之间有否“张力”,有否否定的关系。其结论是,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悬置”起来,才能引进现代工业文明,“重建”中国文化(《“内在创造性转化”还是“外在批判性重建”》,《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其二,主张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主要是指活生生地体现于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这个传统,与其它文化传统(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通古今而不变。至于书本上的学说,则只是一种死的材料,死的语言。发扬传统,即在于领会民众生活之道,而不必借助于儒学等死去的语言。引进西方文化也只能是引进西方文化产品,而不能引进其文化传统(《评“儒学复兴”》,《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民众生活及其习俗、心理与传统哲学是不同的两个层面。前一种观点由此区分,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通性”的一面;后一种观点则强调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仅就此而言,都是不错的。近年来谈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这两种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二者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却在于把传统哲学的观念与民众生活及其意识互相对峙起来。毫无疑问,不同民族文化间存在着“通性”因而有融合之可能。但这“通性”并不在于各民族之“自在文化”没有差异性。“自在文化”之作为“文化”亦是人创造的成果,因而正体现着各民族之不同的价值观念及其价值实现方式,不可谓无差异性。毋宁说,表现于民众日常生活之文化,更内在地体现着民族的个性及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在此点上,我们是赞同第二种观点的。文化的核心是其价值观念和价值实现的方式。而在价值层面,其共通性、普遍性却是在具体的历史性和个性化中显现其普遍的有效性。科学无国界,但文化价值观念却不同,把文化的价值观念知性化,与知识层面相混同,这是全盘西化论者以传统可轻易弃置而随意移植的根本理论误区所在。此点在这里不能评论。此处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文化的观念(表现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者)既非知性的形式,则其与民众生活和意识乃有其内在的关联;民众日常生活亦不可脱离其“自为”层面而孤立地看待。
一种文化理念的提出,必须能够体现民众日常生活之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文化的理念亦因其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所体现之传统的反思、自觉、提升而达致其精神的超越,因而又能以其教化之功能而重塑这个传统。儒家哲学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儒家以道存乎人伦日用,百姓皆可知之,行之;但是,“道”虽根于百姓日用之间,却又超乎人伦日用。这个“超乎”,就是儒家所谓“思”、“思诚”的作用。这个“思”,即是一种反思、揭示、阐释和工夫的历程。用孟子的话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孟子·尽心上》),乃是民众日常生活之特征。道存于不自觉的民众生活之状态,乃有习气拘执之蒙蔽。《易·系辞上》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此民众日常生活之“道”的反思、揭示、阐释活动本身,便既是一自觉的过程,亦是一超越,通透日常生活习气间隔而呈显此“道”的创造历程。因此,道虽存于民众日常生活,极平易、切近人心;但同时,就其“思”所达致的天人合一之境(“察乎天地”)而言,则又是一极高远的超越境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这就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义所在。由此看来,传统哲学的学说,原本并非一种“死的语言”、死的形式。当然,语言本身虽“生于真”(“名生于真”,董仲舒语),也可因其僵化和形式化而掩盖那个本“真”。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以一种对历史传统“同情”的不断阐释活动(如六经之阐释),超越语言的外在形式去领悟开显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孟子所谓“论世知人”,“以意逆(迎)志”,李翱所谓的“以心通性命之道”,朱子所谓的“孔门传授心法”,都是此义。而把传统哲学学说视为一种“死”的语言,死的材料,正是忽视了文化的“自为”层面与民众生活之道的上述内在关联所导致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唯名论”态度。这种“唯名论”态度,长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十分严重的。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两军对战”、抽象阶级分析的思想模式,使一部活生生的思想的历史颓变成一种无法为人的心灵生活所亲切体证的抽象概念的堆积。这种思想模式尽管已逐渐被打破,但它所形成的“业力”至今仍在起着作用。由此种思想模式而来的研究结果,当然只能是一套缺乏思想、文化、精神蕴涵的“死的语言”,人们从中无法领受到文化生命的滋养,获得创造的生命之泉。这便使传统哲学的研究失去了对现实民众生活之道的回应、阐释、提升和陶冶作用。体现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是一不自觉的层面,如果失去自觉层面的精神升华,则必由于某种个性习俗之偏执而堕入封闭、保守之途。例如民间传统的天理良心的观念,住往与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观念结合在一起而有制裁的力量。儒家一方面随缘而“神道设教”,使其价值理念可“致曲”地下行于民众生活;同时,又因其心性、天命的观念阐释作用以为前者之自身超越的精神皈依。这种情况,就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如无君子之“文”的阐释超越作用,寄托于百姓之“神”中的传统必然失却其精神的价值而流入迷信之途。体现于民间之仁义忠孝等观念亦应作如是观。目前的一般哲学理论、道德教育都因其不能与传统相切合而无法起到此种君子之“文”的阐释超越作用。传统哲学的研究由于上述“唯名论”态度亦复如是。就连一时盛行于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亦仅仅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缺乏其文化内涵。民众意识失却君子之“文”的这种“无依无靠”导致了民间诸如宗教迷信盛行、族长专制势力抬头等种种传统的颓化现象。以往,我们往往习于将外来文化观念引入中国以后所产生的畸变归诸所谓传统的“劣根性”。其实,这都是由于上述文化之自觉层面与民众意识之断裂所造成的传统之颓变和创造活力的丧失所致。
所谓“哲学的无家可归”和“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是当前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就哲学的危机而言,它表现为哲学理论的“游谈无根”和创造性、建设性的缺失。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当一种所谓哲学已无法回应民众现实的精神生活因而失却其精神和文化内涵时,它所剩有的便仅是一套空洞的言词。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仍需要继续这种“无根”之谈,但实质上它已经被置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处境既产生于对传统过度的破坏性和批判性的态度,而尴尬的愤懑和对这种尴尬的不满嘲弄又助长了这种态度的蔓延。文化的批判创造不能象对待一种物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打碎之后再行制造。文化的发展乃是生命的内在生长,哲学则是这种生命生长的精神头脑。把象“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痛快淋漓的社会革命口号用于哲学与文化,恰恰斩断了哲学自身由之生长的生命之根。哲学的“游谈无根”、形式化、教条化即由此产生。这种形式化、教条化障碍对概念之文化精神内涵的了悟,从而导致了上述文化价值观上的唯名论态度。而对这种形式化、教条化的不满,又正是时下中国哲学界反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的缘起。王树人教授在一次闲谈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说法:“中国社会尚未进入现代,可人们的思想却已进入了后现代。”“思想进入后现代”,非指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而是指当前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和由此导致的“啥都不信”,心无所主;从学理上讲,则指着学术研究上的破坏性、批判性态度。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消解性的思潮。它对于消解抽象、形式化的本体观念和某种教条化的学科、意识形态的霸权,不无积极意义。但依佛家的话说,它“破幻”过之,“显真”则不足。若仅是批判性的“破幻”而无“显真”,则必无建设性和创造性。无建设和创造则无哲学,无文化。美国美田大学唐力权教授的说法令人心惊:“中国当代不存在哲学的危机,而是没有哲学的危机。”“没有哲学”的危机,岂不是更深刻的哲学危机?
“破幻”旨在“显真”。摆脱哲学危机之途,存在于此“显真”的建设性中。危机由哲学与生活之脱离产生;摆脱危机,就必须重建哲学与生活之联系。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不是说要回到古代哲学那种知识总汇和原初形态的合一上去。自我的分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婴儿要长大成人,原初的浑沌不可执持。但正如孟子所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人的成长,以分化为前提;但成人之为成人,亦须在其自觉的层面上保有那个“赤子”的原初浑沌。现代社会以分工分化为前提。人格和精神的整合即存在于贯注诸意识形式(科学、技术、宗教、艺术等)之文化的教养作用中。哲学之意义,正在于消解此诸分化之幻、之执、之蔽,而显此精神、人格整体之“真”实。而此教养的生命之源,则深植于传统之中。切断这个源,哲学将无以回应民众生活,因而自戕其教养、显真之原创性。由此,哲学之切合、回应、反思、升华当下民众生活意识,亦须在传统和民众意识的双向阐释中才能实现。哲学不仅是学理,更是教养。在高度分工分化的现代社会,哲学的理念与民众意识之联系,更需要文学、艺术等文化样式的中介作用。这就不仅需要士林(知识、文化)阶层以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真切“同情”的历史意识以领受传统的生命资源,而且需要在其切实践履中达成一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易·蛊》)之人格挺立,其精神的产品才能切入民众生活意识,从而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实现哲学所应有的价值。
哲学被逼上“无家可归”的境地,从积极的意义看,这种被逼状态正是对某种虚假繁荣和虚情矫饰消解后的真实之显露。一方面,民众意识对“哲学”的厌倦表明了对“真实”追求的觉醒。就连当下盛行的“假冒伪劣”亦具有了某种不同往昔的“赤裸裸”的“真实”性质。另一方面,哲学这种“无家可归也绽露出了“真”正的哲学之“真实”的归着处。哲学与生活虚假联系的消解正召唤着它们的真实的亲和性。这“无家可归”的“山重水复”之地,安知非其“柳暗花明”之机?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