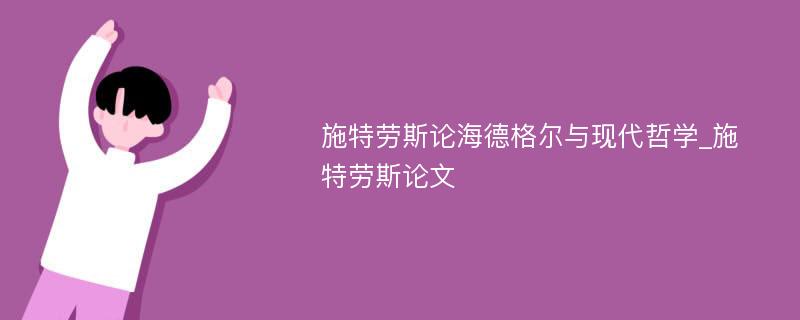
施特劳斯论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施特劳斯论文,海德格尔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6-0127-11 早在十多年前,甘阳先生就指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虽然全书没有一个字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也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任何著作”,这个书名本身却表明了它与海德格尔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某种内在关联①。然而,两者之间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甘阳先生自己也只是借用盖尔斯顿在《康德与历史问题》中的说法简单地予以提示,而且盖尔斯顿对“历史观念”的分析与施特劳斯本人的看法并不吻合②。英文学界也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理查·威克利(Richard Velkley)曾在《理性主义之根: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作为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一文中给予比较全面的阐述③。但若以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字里行间阅读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为标准④,威克利对篇章结构与写作细节的重视还不够,故其解读也并不充分。本文的意图在于,严格以《自然权利与历史》文本本身所提供的线索为依据,将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剖析整合到一起,以展现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尤其是较少为人所注意的现代政治哲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⑤。 一、霍布斯与对整全或永恒的遗忘 海德格尔被施特劳斯看作是激进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不难发现,《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一章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包含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同时,正如甘阳先生所注意到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六章内容两两一组,分别对应着当代、古代和现代,现代与当代又首尾相连,构成一个环形结构。这一环形结构暗示我们,“当代”的问题乃是“现代”问题的发展,而现代的问题只有参照“古代”才能被揭示出来。由此,激进历史主义之错误的根源应该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现代”部分就有所体现。带着这一问题意识,反观《自然权利与历史》第四章的“霍布斯”部分,就会发现,施特劳斯明确地把海德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联系了起来。⑥ 依照施特劳斯的解读,霍布斯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认为传统哲学是失败的,因为传统哲学始终停留于对智慧的寻求,未能真正获得智慧。这也决定了传统哲学无力于彻底摆脱怀疑论的攻击。为了从根本上让怀疑论者无话可说,霍布斯致力于阐发一种绝对可靠的哲学。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数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的范本。数学这门知识似乎表明,只有在那些其本身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建构的主题上,我们才能拥有绝对确定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理解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自然世界中的一切都不是我们创造的,所以自然不可理解,自然科学永远是假说性质的(政治科学由此享有比自然科学更高的地位和尊严)。于是在霍布斯那里,智慧不再像古典派所理解的那样是对自然、对宇宙整全(the whole)的理解,而是人“自由的建构”。而且正因为智慧就是人自由的建构,所以人可以保证智慧的实现。鉴于宇宙不可理解,所以人就没有必要关注宇宙或整全本身,而是应当全神贯注于对人为世界的构建和经营,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有待征服和利用的对象。霍布斯本该对由整全的不可理解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隔绝感到绝望,但是“对于人类所能控制领域内前所未闻的进步的合理预期”,让他全然忘记了人在这样的自然中将会遭受到的恐惧和茫然。在后世思想家看到“人是宇宙中的陌生人”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人是自然的主人”。⑦ 为霍布斯所号召的“有意识的建构”最终促成了海德格尔笔下技术思维主导一切、诸神逃遁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世界变成了一个“座架(Gestell)”,一个生产线和车间,一切事物只在“订造(bestellen)”中,作为预定的产品来与人照面。同时,人自身也被隐藏在技术性思维背后的这股力量逼迫着,成为“座架”的一个部分,失去了与世界之间的本真联系,不再能更为原初地领会人的生存和存在本身。⑧但海德格尔没有看到霍布斯对当代这一危险局面所应负的责任,而是把现代问题的根源追溯到西方形而上学的源头柏拉图那里。因为海德格尔仍然局限在为霍布斯所营造的那种狭隘的现代视野之内而不自知。正如施特劳斯所言,霍布斯之后,“随之而来的数代人所经验到的那一长串的失望尚未能成功地熄灭他和他那最杰出的同时代人所点燃的希望之火”,后代人更未能推倒“他仿佛是为了限制他的视野而竖起的高墙”。变化仅在于,霍布斯那里的“有意识的建构”逐渐为“历史(History)”的无计划的运作所取代。两者都导致了相同的后果,即“通过使人遗忘整全(the whole)或永恒而提高了人和人之‘世界’的地位”。⑨霍布斯主动地忽略原本作为人事之基础和背景的整全,为后来历史主义专注于人事的历史,逐渐淡忘和否定永恒(声称人类思想随历史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无力把握永恒),埋下了祸根。充满了有关此在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或时间性)之精微阐释的海德格尔哲学,被施特劳斯看作是历史主义最后阶段的代表。在海德格尔那里,最高原则本身,“与整全的可能原因或诸原因毫无关系,而是历史(History)神秘莫测的领地。它属于而且只属于人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绝非永恒”。⑩施特劳斯在原文当中并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但这段话显然针对着《存在与时间》里的如下主张: 当然,只有当此在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之领会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可能性存在,才“有”存在。当此在不生存的时候,那时,“独立性”也就不“在”,“自在”也就不“在”。那时,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既不是可领会的,也不是不可领会的。……那时就既不能说存在者存在,也不能说存在者不存在。现在——只要当存在之领会在,并因而对现成性的领会在——当然可以说:那时存在者还得继续存在下去。(11)如果把“存在”换作“真理”,上述观点将意味着,“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唯当此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定律才在,无论什么真理才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12)海德格尔否认永恒真理的存在,因为“除非成功地证明了此在曾永生永世存在并将永生永世存在,否则就不能充分证明有‘永恒真理’”(13)。无论如何,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或真理不再是有待人去认知的、事物的本性或自然的本来面目,而仅仅成了人之本真生存的一种属性,而且并非永恒不变的,甚至根本不存在那种为古典哲学所孜孜以求的、永恒的本性或自然。 二、“历史经验”及其预设 《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一章(“自然权利与历史方法”)既追溯了“历史”如何在霍布斯有意识地忽略整全之后,一步一步成为将人与整全隔开的那道高墙,同时也是对海德格尔生存哲学如何在现代各种思想资源的交汇融合中受孕成形的一种逻辑推演。要全面认识施特劳斯并未言明的后一种意图,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该章的结构。根据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思路,理解作者的意图几乎等同于理清作品的结构(14)。全章共34个自然段,分五个环节。第一环节包括1到5自然段,通过与习俗主义的对照,揭示出历史主义的基本定义:所有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人类理性无力把握永恒之物。第二环节包括6到12自然段,简要回顾历史学派从出现到失败的过程。13到22自然段,构成第三环节,集中分析从历史学派的失败中得到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主义的初步理论化及其内在矛盾。对激进历史主义的讨论构成第四环节,也就是23到29自然段。30自然段至章末,交代施特劳斯本人对海德格尔式激进历史主义的基本评价和应对策略。这五个环节分别包括5、7、10、7、5个自然段,呈严格对称结构。讨论激进历史主义的第四环节与回顾历史学派的第二环节恰相对应。这提示我们两者应该具有某种不容忽略的相似性。在第12段末尾,施特劳斯说,“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要使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结果却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15)。众所周知,对“扎根”和“在家”的向往和迷恋,贯穿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16)且激进历史主义的结果也是虚无主义。可见,历史学派与海德格尔哲学分享着同一种宗旨,即为了使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完全的家园感而反对带有普遍性诉求的“理论(theoria)”,因此在不同的层面上完成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即通往虚无主义的过程。历史学派的失败造就了一种虚无主义情绪,为这种情绪所需要的哲学论证,则是由海德格尔完成的。激进历史主义之所以“激进”,就在于它以纯粹哲学的方式即整全式的思考,以对人类生存的内在一贯的分析,把虚无主义从理论上做实了。“自然权利与历史方法”第三、四环节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考察历史学派的失败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了激进历史主义,也便是搞清楚,哪些思想资源最终成就了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existentialism)。 “历史学派”兴起于18世纪末的德国,主要为了反对卢梭等革命派的普遍主义政治哲学。在历史学派中,首先出现的是以萨维尼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按照施特劳斯的解读,英国保守派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法学派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历史学派在激烈地否定了革命派普遍性的抽象原则之后,原本期待在历史中发现一种具体的、民族性的标准。然而,问题在于,特殊性标准的有效性仍然源自对某种普遍性原则的承认。纯粹历史本身就像古典哲人曾经认为的那样,如同疯子讲的故事,没有任何意义,无法提供任何标准。一个民族的传统并不能仅仅因为它传承久远的历史就自然地享有正当性。假如传统本身就至高无上,那么对传统的损益更化就无从谈起了。“与传统保持一致不会理所当然地比和传统一刀两断更好,追逐‘未来的浪潮’也并不显而易见地比抗拒‘历史潮流’更对。”(17)。历史学派逐渐意识到,否定了普遍性的标准之后,并没有其他类型的标准留下来,“历史”无法享有当然的权威。此时的历史主义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转向古典哲人对于历史的那种常识性态度,并重新思考如何寻求客观标准,要么停留于否定客观标准的虚无主义境地中。历史主义选择了后者,历史学派的失败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后果,被解读为人之为人的一种真实处境,前人据说因为囿于某些错误的形而上学观念,未能发现这种处境。历史主义进而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历史经验”。正是这种“历史经验”成为后来所有历史主义者不言自明的前提,当然也成为促成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思想要素之一。施特劳斯选择在全章的中心位置即第17自然段交代了这种所谓的“历史经验”——“在我们看来,那种被称作‘历史经验’的东西只是在对必然进步的信仰(或者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思想)和对多样性或唯一性的至高价值的信仰(或者所有时代或文明的同等权利)的共同影响下对思想史的概观”,以海德格尔生存哲学为代表的激进历史主义,虽然看起来不再需要那些信仰。但却从来没有考察过,“它所参照的那种‘经验’是否只是那些成问题的信仰的一种结果”(18)。第16自然段详细地给出了历史主义对这个“历史经验”的解读。从此段之前的语境来看,这种解读乃是历史主义经过初步理论化,即吸收了休谟、康德等人对理性的批判之后的成果。而那种从历史学派的失败中直接产生的“经验”,出现在第13自然段。对比两处表述,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区别: (段13)……所有人类思想都依赖于独一无二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背景承继此前多少有些不同的背景而来,对于此前的背景来说,它又是以某种根本不能预料的方式出现的。这就是说,人类思想是由不可预料的经验或决断来奠基的。(19) (段16)人类思想本质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局限性随着历史情景的变化而变化,而某一特定时代的思想所固有的局限性乃是任何人类的努力都无法克服的。……既然人类思想的局限性本质上乃是不可知的,用社会的、经济的和别的条件(亦即用可知的或可加分析的现象)来思考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人类思想的局限性乃是命中注定的。(20) 施特劳斯以此告诉我们,上述“历史经验”作为历史主义者自以为是的重大发现,只不过来自历史学派的失败所造就的那种情绪。激进历史主义者从对整全的理解出发,借助“视域(horizon)”这一概念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所有人类思想都依赖于命运,依赖于某种思想无法掌握也无法预计其如何运作的东西”(21)——依旧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更加“精致”而已。正如文中第17自然段所指出的,激进历史主义由以出发的“历史经验”本身从未经过批判性地考察,也没有哲学论证的支撑,而只是来自两种可疑的预设,即进步信仰和对多样性或唯一性的迷拜。这两种预设的最初形式由历史学派借自18世纪的自然权利论。“对多样性或唯一性的至高价值的信仰”不过是18世纪个性崇拜的一种变体,而进步信仰与历史学派假定存在着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在性质上几乎等同。(22) 三、康德与实践的优先性 历史学派失败前后的历史主义,问题意识有所转变。以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并不否认理论分析能够产生某种标准,以为行动提供指南,他们反对的只是18世纪的自然权利论所宣扬的那种教条化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并打算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标准。最终因为没有找到任何客观标准而陷入虚无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历史学派之后的历史主义则压根否定客观标准的可能性。正是着眼于问题意识上的这种改变,施特劳斯才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一章开头说道:“历史主义原本是在以下信念的庇护下出现在19世纪的:关于永恒的知识或至少是直觉乃是可能的。但它逐渐削弱了在其幼年曾经庇护过它的这种信念。”(23) 要证明客观的标准不可能,其实就是要论证理论依赖于行动,依赖于行动者的历史。后者已经包含在历史学派的失败所导致的“经验”之中——“人类思想是由不可预料的经验或决断来奠基的”(24)。实际发生的历史,总是行动者的历史,说思想的根基立于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之中,无异于说思想本质上依赖于行动者的决断;总是先有行动者的历史,才有思想者的反思,于是,思想依赖于行动,行动生活高于理论生活。海德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最终声称人类思想依赖于命运,也是导向类似的结论。 其实,论证理论对于行动的本质依赖性,毋宁说是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初衷。(25)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试图确立实践对认识的优先性,他一再强调,对现成事物对象化的观看(认识)缘起于寻视着对上手之物的操劳(实践),是后者的一种残缺状态,只有先行越过以操劳为特征的“实践”,作为人另一种存在方式的“认识”活动才能发生。(26)尽管这一努力在《存在与时间》中并不成功,但它至少模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而这种模糊无疑偏向实践一边。海德格尔30年代的校长就职演讲,更加直白地表露了这一点: 但对希腊人来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人们都说:理论是纯粹的“沉思”,这种沉思依附于事物的完整和要求。有人以希腊人为据,认为这种沉思的态度是为沉思而沉思。这种引经据典的做法纯属错误。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单单来自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全部努力,恰恰是把沉思的追问作为一种实现(energeia)、一种“实践存在”、一种人的方式,并且作为唯一最高的方式来理解和贯彻。他们的想法不是要使实践符合 理论,恰恰相反:他们把理论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个“文化财富”,而是民族一国家整体此在的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27) 历史主义不能满足于一种“历史经验”,它的命题要有说服力需要理论依据。历史至多能够证明一种观点战胜或取代了另一种观点,对两种观点以及这个替代本身的合理性,什么也没有说。当历史主义的问题意识不再是寻求一种非普遍主义的恰当标准,而是根本否定任何客观标准本身之后,历史主义得以与批判理性和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趋势合流。由此,康德对理论形而上学和哲学伦理学(自然正确)的否定为激进历史主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思想要素(28)。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处理,显然直接关联着康德的批判哲学。那么,康德有关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立场又是怎么来的,并有何问题呢? 《自然权利与历史》没有专论康德,但为理解康德哲学的基本旨趣留下了线索。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较有启发性的地方有两处,均以注脚的形式出现在“卢梭”部分,一处暗示康德的问题意识来自卢梭(页269注23);一处指出康德对卢梭的解读是成问题的(页260注4)。 在分析《论科学与艺术》时,施特劳斯提到卢梭的一个暂时性的结论:“理论科学并非本来要服务于德性,因此是不好的,要使它变好,就必须使它能够服务于德性”(29)。附在这句话上的脚注提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之所以把道德或行动生活拔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连形而上学都要为它服务,乃是受到卢梭的启发。康德四十岁的时候写道:“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推动知识前进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视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其他劳工还不如。”(30)生活极富规律性的康德,曾因卢梭的新书《爱弥儿》而打破了持续多年的散步习惯。卢梭在《爱弥儿》中通过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从道德的目的出发,证明了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康德后来通过他的理性批判,确立了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除了道德以外没有其它用途。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也有三个类似的命题,即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可以说,康德完成了卢梭的萨瓦牧师所努力追求的东西。萨瓦牧师所给出的形而上学不是基于知性,而是刻在人的心上,康德的结论则是以严格的哲学思辨(对理性的批判)为基础。康德将遵守道德律与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联系起来(人被确立为“自由的道德主体”),显然也受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响。《社会契约论》第八章提到,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过程,也是人从自然人变为道德人的过程,而自然人乃是“次人”,这等于说,没有道德之前,人尚不是人,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31) 然而,从施特劳斯的角度观之,康德对卢梭的理解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爱弥儿》中的萨瓦牧师毕竟不是卢梭本人,把两者等同看待,就像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等同于莎士比亚一样荒谬。更何况,不能认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方案,真正解决了困扰卢梭一生的根本性问题——自然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就在同一本书的开头,卢梭已经宣告“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2)。社会对人来说始终是一种枷锁,真正的自由难以从社会中获得,所以康德心目中“自由的道德主体”违背了卢梭本人的看法。“卢梭至死都认为,即使是正当的社会也是一种形式的束缚”,因此,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那种解决,至多只是一个“能够容忍的近似的解决方法”。所以,“告别社会、权威、限制和责任,或者说返于自然”,对卢梭而言始终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33)。 四、尼采、黑格尔与历史主义的内在矛盾 施特劳斯指出,历史主义自身面临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历史主义声称揭示了所有人类思想的历史性,但历史主义的命题本身恰恰不能是“历史性”的,而是对人类思想之根本局限的一种超越时空的洞见。以海德格尔的深刻和博学,也未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只是掩盖和回避了它(34)。海德格尔之所以能掩盖和回避这一矛盾,还得归功于尼采和黑格尔的工作。 尼采是在对19世纪历史主义的批判中为海德格尔做好准备的。在早期文章《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指责历史主义的理论分析破坏了笼罩在生活或行动周围的“保护层”。真正属人的生活和行动,都要求一种献身精神,要求对某种观念的全身心地信仰。这种信仰只有在一种“绝对主义”的整全视域(horizon)的支撑下才有可能,否则将是肤浅和没有意义的。然而,历史主义通过把所有关于整全的视域都揭示为相对的,破坏了属人生活所必须的“绝对性”。(35)要避免理论对生活的威胁,尼采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回归理论分析的隐微品质,恢复柏拉图式的高贵的谎言,要么否认理论本身的可能性,让理论依附于生活或命运。如果不是尼采本人,也是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选择了第二条路。(36)借用尼采提到的“视域”概念,海德格尔声称,所有的理解和认知都假定了一个参照系,一个整全的视域。对整全的某种程度上的把握,是所有理解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对整全的把握无法被理性地证成,因为它是所有推理得以可能的条件。因此,“存在各种各样地此类整全性的观点,每一种都像其它任何一种同等正当: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理性指导的情况下选择一种观点。选择一种是绝对必要的;中立性或者悬置判断是不可能的”(37)。严格地说,个人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因为每一时代的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整全性视域,而我们总是发现自己早已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并接受了它的“意识形态”。(38)个人的视域是被历史地强加的,被一种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或命运强加的,人类思想最终依赖于命运。 由此,激进历史主义不再声称历史主义命题的客观性。它一方面承认命题的效力是超历史的,另一面却认为其出身是历史性的。历史主义命题的发现被认为是一个历史事件,是人无法解释的,是命运的恩赐。简单地说,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对人类所有思想之历史性的洞察归于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势,“那种形势不仅是历史主义洞见的条件,也是它的源泉”(39):“为了看清所有思想的历史品质,不需要超越历史: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时刻,历史进程中的绝对时刻,所有思想的本质特征变得一目了然的时刻。为使自己免于它自身的裁断,历史主义声称它仅仅是反映了历史现实的特征或忠实于事实;历史主义命题的自相矛盾,不该归咎于历史主义而当归咎于现实”(40)。 假定一个历史中的绝对时刻对激进历史主义来说是本质性的。海德格尔暗中追随着黑格尔的先例。区别在于,黑格尔把绝对时刻看作是关于整全的根本之谜真相大白的时刻,而海德格尔则把绝对时刻规定为“根本之谜的不可解决的品性变得昭然若揭的时刻或者人类心灵的根本错觉被消除的时刻”(41)。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主要“灵感”又是怎么来的且错在哪里呢? 施特劳斯在“伯克”部分最后明确提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诞生,它与伯克的历史转向关系密切。为了反对18世纪自然权利论对理论与实践之根本区别的模糊,抵御理论精神对实践领域的入侵,伯克试图恢复有关理论与实践之正当关系的古老教诲,但由于受到现代以来贬低理性和理论形而上学之思想潮流的影响,伯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更为“自然”的古典思路,其主要表现就是把最高形式的实践即“政治社会的奠定或形成”看作是一个不受反思控制的准自然的过程,进而使得这个过程作为“准自然”之物,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理论性的主题,就像一棵树的长成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主题那样。 政治理论变成对于实践的产物或现实之物的理解,而不再是对应然之物的寻求;政治理论不再是“在理论上是实践性的”(即不在现场的慎议,deliberative at a second remove),而是纯粹理论性的,就像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在传统上被理解为纯理论性的一样。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理论,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其最高主题是人类行动及其产物而非整全……当形而上学像现在这样,把人类活动及其产物视作一切别的存在或过程所趋向的目标,形而上学就成了历史哲学。历史哲学首要地乃是有关人类实践并且从而必定是有关已经完成了的人类实践的理论,亦即沉思;它预先就假定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历史(History),已然完成。(42)不仅如此,为抵制18世纪自然权利论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挑战,伯克在为英国宪法辩护的过程中,把“长久因袭(prescription)”当作判断政体好坏的主要标准,拒绝“参照任何别的更为一般的或先天的正当”(43)。这种对超越性标准的拒绝,等于承认标准即在过程之中,于是,伯克在为传统辩护的同时,无意中成了黑格尔所谓“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主张的先驱。 但伯克终归只是为黑格尔发现“历史(History)”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他本人依旧把历史看作偶然事件的前后相继,没有为历史设置一个“绝对时刻”。黑格尔历史哲学所需要的那种“绝对时刻”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来自卢梭:“良好秩序或合理之物,乃是那些其本身并不以良好秩序或合理之物为目标的力量所产生的结果。此项原理首先是用在行星系,而后又用在了‘需求的体系’亦即经济学上。这一原理之运用于健全政治秩序的产生,乃是对历史之‘发现’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中的一个。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就是将同一个原理运用于对人道的理解,人道被理解为是通过偶然的因果关系获得的。”(44) 施特劳斯在“卢梭”部分详细论述过第二个因素(45)。卢梭通过克服霍布斯理论中的自相矛盾,进一步抽空了“自然状态”中的人性内容,使得自然状态中的人成了“次人”,“所有专属于人性的东西都成了习得的(acquired),或者说最终依赖于人为或习俗”(46)。卢梭于是不得不把人道解释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机械因果关系的结果。由此,“‘历史过程’被视作是在某一个绝对的瞬间达到了顶点:在那个时刻,作为盲目命运产物的人,由于第一次以恰当的方式理解了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何者为对或错,从而成为了自己命运的明辨秋毫的主人”。(47)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在其早期著作《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中,不是将卢梭或伯克,而是把霍布斯看作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驱:“对他(按:霍布斯)来说,人类原始条件的不完美性,或自然状态的不完美性,不是通过考察国家作为完美的共同体这个业已澄清的(即使只是粗略地澄清)的观念而感知认识的。检验的标准,未经事先确立,未经事先论证,而需要自行产生,自行论证。所以,霍布斯没有追随仿效亚里士多德,而是开辟了通向黑格尔的道路”。(48)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似乎对上述观点做出了修正。他认识到霍布斯并没有把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过渡设想为一个机械的过程,这部分地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先于社会的人就已经是理性的存在者,是能够缔结契约的存在者”。于是,对霍布斯来说,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过渡,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而是恰好与社会契约的缔结相对应(49)。 上文曾提到,在海德格尔否定理论客观性的论证中,“视域(horizon)”概念关系重大。“视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种客观事实。早在海德格尔之前,“视域”已经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关键概念。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所谓一切理解都以某种前理解为基础,也是对现象学视域概念的一种具体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对“视域”的重视,都导向了对理论或解释之客观性的否定。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第四章第7自然段,有意识地使用了“视域”概念,却没有落入同样的相对主义。施特劳斯不否认,所有的知识,“都以一个视域、一种知识在其中成为可能的完备的观点为先决条件”(50),所以像海德格尔一样,认为对整全的某种把握,是所有理解的基础。严格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对整全的把握无法被理性地证成,因为它是所有推理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施特劳斯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由此便认定“存在各种各样的此类整全性的观点,每一种都像其它任何一种一样正当”(51),而是指出,各种整全性观点不仅彼此不同,而且相互冲突,因为它们都是对同一个整全的看法。它们的冲突恰恰表明,在所有冲突性的观点之外,存在着一种关于整全的真正的知识。哲学就是要从这些冲突性的观点出发,通过辩证法来接近那种知识。至于能否最终获得这种知识,或者说“哲学是否能够合理地超越讨论或争辩的阶段而进入作出决断的阶段,对此人们并无把握”(52)。但不能因此放弃把握整全的努力,所有对部分的理解都以对整全的理解为基础,放弃对整全的理解,就是任凭所有理解都停留在盲目和黑暗之中。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事业,就是对人的无知的认识(53)。然而,关于无知的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对无知的认识,意味着对界限或必然性(necessity)的认识。把握了界限,就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行动的方向。 简单地说,苏格拉底通过宣称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表明他赞同海德格尔的结论即整全是不可理解(not intelligible)的,但他同时认为,知道整全不可理解,恰恰表明我们对整全已经有所理解(understanding)。因为对于那些绝对不可知的东西,我们根本无可言说。海德格尔像苏格拉底一样,都看到了这个“令人绝望”的事实。海德格尔由此真的绝望了,苏格拉底却并未绝望,他依然“乐观”。海德格尔的失误在于,他想当然地认为,苏格拉底的乐观是“盲目”的,是无视那个存在之“深渊”的结果。就其揭示了哲学事业的“西西弗斯式”的本质来说,施特劳斯认为激进历史主义是有功的,它郑重表明,任何试图建立一种哲学体系的努力都是虚妄的,但它就此而否定哲学,就是“过犹不及”了,并因此证明它自身还停留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之中,对哲学沉思的本来面目并不知情——“历史主义错误地把所有哲人(作为人他们倾向于犯错)不可避免的命运看成是对哲学之意图的驳斥。历史主义至多证明了我们的无知(这一点没有历史主义我们也意识到了),但没有从对我们的无知的洞见而意识到追求知识的紧迫,历史主义表现出令人惋惜或荒唐的自满;这表明,它也是被它所揭穿的诸多教条主义中的一种。”(54) 教条主义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大特征。当霍布斯把智慧限定于理解为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之时,他就排除了智慧在苏格拉底那里因为不完整而具有的疑难品质(zetetic scepticism),让哲学成了一些不容变通、毫无疑问的结论。海德格尔没有摆脱霍布斯以来的教条主义,当他误把“所有哲人不可避免的命运看成是对哲学之意图的驳斥”时,就表明他还在向哲学要求一种实实在在的结论、一种确定无疑的答案、一种教条。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不仅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与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德国哲学巨匠的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它和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如霍布斯、卢梭、埃德蒙·伯克等人的思想之间,也有着虽然曲折却不容忽略的关联。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哲学从霍布斯到海德格尔的过程,也是现代精神从教条主义走向生存主义的过程。按照通俗的理解,教条主义即是罔顾事实空谈理论的倾向,是理论思辨对实践智慧的僭越。为了追求确定的实践效果,霍布斯限制起自己的视野,将智慧限定于“人为的建构”(“人只能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东西”),把对宇宙整全的理解排除在外,从而决定性地奠定了教条主义的基础。为国家确立政体,这样一种本属于伟大领袖的实践事业,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开始成为某种可以脱离政治家的实践智慧,在理论上就能永久解决的问题(55)。伯克为抵制卢梭等人的教条主义(普遍主义),为一种稳健的政治家精神辩护,错误地将政治秩序的产生看作是一个不受反思指导的准自然的过程。黑格尔在卢梭、伯克等人的基础上,把人类实践的整体看作已然终结,从而走到教条主义的顶峰。基尔克果、尼采为反抗黑格尔主义,恢复实践的可能性,把生活或生存本身当成最高的东西,置理论于从属地位,事实上否定了一切客观性,否定了理论本身。(56)海德格尔继承了尼采等人对“理论”或一切客观标准的否定,从“时间性”的角度演绎出了一套生存哲学,赋予历史主义一种存在论层面上的支持。 若从施特劳斯解读的古典哲学来看,教条主义和生存主义是两个错误的极端,“在彼此反对的同时,它们也在关键之处彼此一致——它们都一样地忽视审慎(prudent),‘这一下界的上帝’。没有关于‘上界’的某些知识,没有真正的理论(theoria),我们就无法看清审慎和‘这个下界’”(57)。教条主义认为理论“万能”,故不需要审慎;生存主义认为理论无能,故“盲目”地冒险。海德格尔投奔纳粹无疑是其盲目冒险的集中体现。施特劳斯之所以强调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关键在于严肃地看待他投奔纳粹这一事实,就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冒险透露了现代哲学的根本缺陷,即因失落了“理论”的真谛而无力成全“审慎”这一美德(58)。只有一种适度的、真正的理论才能保证审慎。这种理论既不无原则地贬低理性,也清晰地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就对政治行动的指导来说,这种理论能够提供原则性地指引,却无法给出行动的方案,也不能保证行动的结果,这种理论便是施特劳斯念兹在兹的古典的自然正当学说。 需要补充的是,历史主义脉络中的海德格尔,只是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一个面向。施特劳斯在批评海德格尔激进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我所能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闭上眼睛不读海德格尔”。(59) 收稿日期:2016-03-10 注释: ①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言”,第14页。 ②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第12-14页。从甘阳的转述来看,盖尔斯顿与施特劳斯的最大不同,就是忽略了霍布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章和第八章。 ③Richard Velkley,"On the Roots of Rationalism:Straus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as Response to Heidegger",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0,2008,pp.245-259. ④该译法出自甘阳,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言”,第29页。 ⑤有关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还可参见Rodrigo Chacón,"Reading Strauss from the Start:On the Heideggerian Origi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9(3),July 2010,pp.287-307; James F.Ward,"Political Philosophy & History:The Links Between Strauss & Heidegger",Polity,20(2),Winter 1987,pp.273-395。Steven B.Smith认为施特劳斯的所有著作都指向海德格尔,参见其著作Reading Leo Strauss:Politics,Philosophy,Juda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256; Stanley Rosen则强调,施特劳斯思想的核心是他与海德格尔在哲学之本质问题上的对抗,见其文章"Leo Strauss and the Possiblility of Philosophy",Review of Metaphysics,Vol.53,2000,p.542. ⑥[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9-180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大多据英文版(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有所改动,不再另注。 ⑦[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74-180页。 ⑧[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24-954页;朱清华:《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中“看”的解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⑨[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8-180页。 ⑩[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80页。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这一概括呼应了他在第一章中的以下说法:“最彻底的确立历史主义的努力在以下的断言中达到了顶峰: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还可能有entia[在者],但是不可能有esse[在];也就是说,在没有esse[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entia[在者]”([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3页)。 (11)(12)(1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4、260、261页。 (14)[美]列奥·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施特劳斯致克莱因的信:“不过,我现在毕竟完全读懂了《回忆录》,如果完全读懂这类书与弄懂其结构是一回事的话。” (15)(17)[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9页。 (16)正如巴姆巴赫所见,“政治永远无法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与哲学切断开来,因为哲学对于他而言总是对‘在存在者中间的在家状态’和‘在时间(在时代性的存在历史中)和空间(在某个提供出历史性天命之可能性的故土上)上的扎根状态的某种沉思’。”参见[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除了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认为科耶夫乃现代哲学立场的最佳代表,他对科耶夫的回应,也可以看作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按照科耶夫的预设,无条件的忠实于属人的关注成为哲学理解的唯一源泉(the source):人必须绝对地以地球为家,必须绝对地成为地球的公民,如果不是这个可居住的地球之某一部分的公民的话。按照古典的预设,哲学要求一种对属人关注的根本性疏离,人绝不能绝对地以地球为家,他必须是整全的公民(a citizen of the whole)。”言外之意,现代哲人对家园感的追求以遗忘整全为代价,而哲学的本性正在于把握整全。参见Leo Strauss,"Restatement",Interpretation,Vol.36,Issue 1,Fall 2008,pp.77-78. (18)(19)(20)(21)(23)(24)[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3、20、23、28-29、14、20页。 (2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7页,“历史学派假定有民族精神(folk minds)的存在,亦即他们假定民族或种族群体乃是自然的单位,或者他们假定存在着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或者把这两种假定都融合起来”。 (25)理论对实践生活或生存的依赖性乃后尼采时期德国思想的主题:“表达了一战后德国对于现代文明的典型态度的口号,不是历史VS非历史的自然主义,而是生活或生存VS科学,作为任何一种理论事业的科学”。参见Leo Strauss,"Living Issues of German Postwar Philosophy",in H.Meier,Leo Strauss and 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Probl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16.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中,海德格尔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古典观念(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而且前者高于后者)的独特看法。参见David K.O'Connor,"Leo Strauss's Aristotle and Matin Heidegger's Politics",in Action and Cotemplation:Studies in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ristotle,ed.R.Barlett and S.Collins,Albany:SUNY Press,1999,pp.162-207. (26)[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406页。 (27)[德]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吴增定、林国荣译,“中国现象学网”,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68/c0。可参见权威英译本Heidegger,Martin,"The Self-Assertion of the German Univensity and The Rectorate 1933/34:Facts and Thoughts",Review of Metaphysics,38(3),March 1985,pp.467-502.施特劳斯在给科耶夫的信中,曾提及与此段相关的部分,Leo Strauss,On Tyrann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Including the Strauss-Kojève Correspondence,ed.V.Gourevitch and M.S.Ro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223及编者注释3。 (28)(29)[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9、269页。 (30)[德]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页。 (31)该段对卢梭与康德之间思想关联的分析参照了施特劳斯讲“康德”的课堂录音,Leo Strauss,"Seminar in Kant," spring quarter 1967,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kant-spring-quarter-1967。 (3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 (33)(34)(37)[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60、26、28页。 (35)[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6、91页。 (36)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8页。施特劳斯在第28页注9中说,根据《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的某一段话,可以断定尼采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前提。据笔者判断,施特劳斯所指的这段话应该是:“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的雪崩使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那么生活也会崩溃,变得脆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质疑,生活更高,生活是统治力量。”([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6节专门评论了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提出的观点。 (38)此处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非海德格尔原话。 (39)[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8页。“条件”(condition)与“源泉”(source)之间的区分事关古今之争的关键问题,施特劳斯在批评科耶夫的时候挑明了这一点:“按照古典的预设,理解(understanding)的条件(conditions)与理解的源泉(resources),哲学生存(existence)与永续的条件(某种社会,等等)与哲学洞见的源泉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按照科耶夫的预设,这种区别失去了其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变迁或命运会影响存在(being)并因此影响真理,如果它不是与存在相等同的话。按照科耶夫的预设,无条件的忠实于属人的关注成为哲学理解的唯一源泉(the source):人必须绝对地以地球为家,必须绝对地成为地球的公民,如果不是这个可居住的地球之某一部分的公民的话”(Leo Strauss,"Restatement",Interpretation,Vol.36,Issue 1,Fall 2008,p.77)。 (40)(41)(42)(43)[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0、31、327、326页。 (44)(45)(46)(47)(49)(50)(51)(5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22、278-280、277、280、322、279、126、28、126页。 (48)[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53)[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54)Leo Strauss,"Living Issues of German Postwar Philosophy",in H.Meier,Leo Strauss and 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Probl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33. (55)(57)[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96-198、327-328页。 (56)[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26-327页。关于尼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严厉批评,可参见前引书《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61-67页。 (58)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式生存哲学导言》,丁耘译,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34页。英文有两个版本,"Existentialism","Two Lectures by Leo Strauss",Interpreation,Vol.22,Issue 3,Spring 1995,pp.302-319;"An Introduction to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ed.T.Pangle,Chicago: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1989,pp.27-46.第一个版本更忠实于施特劳斯原稿。 (59)"Existentialism","Two Lectures by Leo Strauss",Interpreation,Vol.22,Issue 3,Spring 1995,pp.305-306.标签:施特劳斯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存在与时间论文; 社会契约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卢梭论文; 爱弥儿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