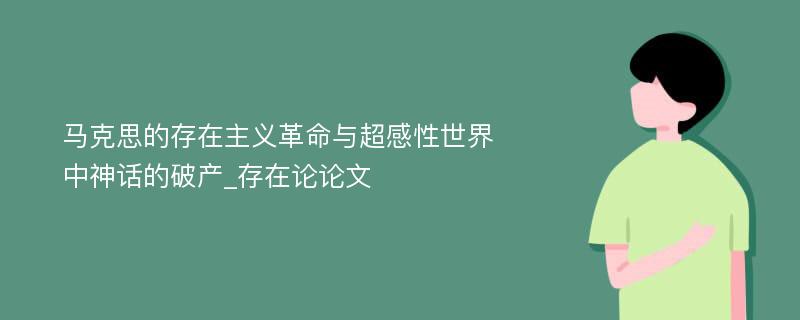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感性论文,神话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是——并且归根到底是——存在论(ontology,或译本体论)性质的。正是这一深刻的存在论革命意味着——并且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然而,这样一场对于整个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存在论革命,却很少得到切近的理解和真实的估价。它往往只是在现成观念的无内容的形式上、甚至只是在纯粹的辞令上被加以理解和讨论。既与的哲学“因素”,诸如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实证科学或革命意志、费尔巴哈或黑格尔,以及它们之间按各种比例配制的混合物,据说就如此这般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此而来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样的争论并非没有成果而且总具有它的“实际意义”,但却依然是表面的。更加重要的是:当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局限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范围之内时,马克思的哲学存在论也就先行地被理解为这种神话学的一部分了。就最终的论断方式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形反过来却印证了由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所引导的基本见解之一,即:除非具有超感性神话性质的现代世界本身实际地发生解体,否则的话,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就不可能真正垮台。
1943年,海德格尔慎重其事并且颇费周章地阐释了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他说,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亦即是被用来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从源头上说,自柏拉图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而与之相应的感性世界则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因此,“‘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就他言,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①。
海德格尔的这一辨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独具只眼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上帝死了”一事,确实与“不信仰上帝”的种种空洞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而是牵扯到我们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来表示的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区分,以及前者为后者所规定、所包含),牵扯到形而上学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超感性世界如何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而成为虚无的。“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Verwesung)。”②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自笛卡尔创制现代形而上学以来,首先体会到超感性世界之本质性崩塌并把它道说出来的是费尔巴哈。这个补充的要点完全不在乎所谓理论优先权的无关紧要的争议,其要点在于:费尔巴哈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首度发难不仅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也同样启发了尼采。如果遗忘了这一点,就会在错估费尔巴哈意义的同时,匆匆地越过马克思,越过马克思曾经开展出存在论深刻变革的整个区域。阿尔都塞指证说,费尔巴哈哲学及其内在矛盾“引起了一个参与了历史并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效果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对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的影响),有些是延迟的(对尼采、现象学、某种现代神学、甚至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新的‘《圣经》注释’哲学的影响)。”③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超感性世界的直接领域就是宗教神学(即宗教反思)。在神学中,上帝的本质正就意味着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意味着这种目标设定从外部规定着并且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费尔巴哈把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观念指认为“异化”。因为在他看来,神学的秘密无非是人本学(即宗教真理);而在宗教的人本学批判中,上帝的本质归根到底乃是“人自己的人的本质”。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还以完全类似的方式批判了哲学即形而上学本身。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思辨哲学、近代哲学乃至整个哲学,都在本质上包含着与宗教神学相同的异化形式,亦即以建立超感性世界作为真正的奠基,通过不断巩固和推进它对于感性世界的优先权和统治权来设定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因此,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哲学和神学虽然形式上有差别,但两者都是完备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在这个主题上,正是费尔巴哈首先使对整个哲学(或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课题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认费尔巴哈的第一项“伟大功绩”就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④
不难理解,为了彻底颠覆整个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费尔巴哈在存在论方面突出地强调了“感性”,并使之与超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样的对立最为充分地体现为“感性”和“绝对精神”的对立,亦即“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感性的事物)与“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思辨的思维)之间的对立。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显现,因此,“感性”同“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止于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的对立。归根到底,绝对精神无非是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于一般哲学之完成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过是在哲学中得到复活的神学之已死的精神,即“幽灵”。就此而言,“超感性世界”既是神学的本质,又是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来说,毋宁更恰当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中的神学本质。
因此之故,费尔巴哈试图在存在论上予以阐释的新原则——感性,初始地来说并且就其一般指向来说,是同先前处于哲学-形而上学中并由之而规定的“感性”相当不同的东西。毋宁说,它一开始就力图表明自身是与超感性世界相对立的东西,因而是与整个哲学的神学本质相对立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感性——它意欲重新领会和设定存在者整体——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就不是一种哲学之内部的对立;毋宁说,它倒更应当被看做是哲学同其“反面”的对立,是哲学同“非哲学”的对立。“因此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的原则。”⑤总而言之,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感性”这个新原则并不是与某种哲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矛盾,而是与一般哲学(作为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矛盾。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质上“就是一般哲学的开端”,那么上述所谓全面的矛盾就表现为:“存在”(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真正对立面并不是“无有”(非存在),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存在”⑥。于是,费尔巴哈试图从根本上超出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并与之形成决定性对立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存在论命题中得到表述:“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
在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神学与哲学——中,真正的感性是被完全扼杀的,正像它在哲学中的那种徒有其表的名称不过意味着它已被先行阉割的命运一样(被理智地抽象化、形式化,或被作为本身没有真理性的环节而加以扬弃等等)。费尔巴哈把事情翻转过来了,他把感性置于王座的地位。“它不仅是人的感觉的本质,而且是自然和肉体实存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按照费舍的一个说明,感觉是迄今为止被轻视的第三等级,他把它提高到一个全面的意义;与此相反,黑格尔却赞美思维,说它失去了视和听。”⑦黑格尔对感性的这种贬抑使我们想起了德谟克利特(他和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几乎是同时代人):这位哲学家兼实证科学家在人类知识的真理性问题上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终于,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便让其心灵的“眼睛”能够更透彻地看清事物的本质。这或许是一则关于哲学—形而上学之命运的寓言——它讲述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在其开端设定超感性世界及其优越性和统治权的,以及这种设定又会以何种方式在近代哲学的完成形式中获得其最终的总结。
于是我们看到,费尔巴哈以非凡的勇气和果敢向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费尔巴哈的存在论纲领就是“感性”:实在性之唯一的和真正的领域就是感性,换言之,只有感性才是实在性——这是一个“可以用我们的鲜血盖图章来担保的真理”。真实的存在仅仅源自感性,因为某物的实存是以感性的方式显现,并因而是为感觉所证明的,它不能通过思维、臆想或单纯表象而得到证明⑧。存在的秘密并不显示给普遍者的思维,而是显示给感性的直观、感觉和爱(情欲);因而真实的存在“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⑨
这确实是一个尝试颠覆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巨大的图谋,然而这个图谋的实施却所得甚微(特别是就其宏伟的抱负而言),整个具有反叛性质的存在论纲领最终几乎全部落空了。于是,试图进一步推动这场颠覆性运动的变革者便开始追问:为什么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对他本人却毫无结果呢?这个检讨性的问题在指认费尔巴哈失败的同时已经把他置放到先驱者的位置上了。重要的是,这个位置是由时代的立场确定的:尽管“与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小多了”,然而,“认为人们能够乘坐一种已死的精神的高头大马越过19世纪的‘唯物主义’却是一种错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理神学的感性化和有限化绝对是我们如今所有人——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处身于其上的时代立场。”⑩
费尔巴哈哲学的最终失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一种状况,即:就其没有离开哲学—形而上学这一基地而言,它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11)。这意味着,费尔巴哈对哲学—形而上学之颠覆性的反叛(“颠倒”),最终是返回到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去了。换句话说,在费尔巴哈那里,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再度主宰了这种神话学之最遥远的对立面。这种情形与海德格尔所述之尼采的命运是十分的类似的:“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12)与此命运相类似恐怕还要包括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等,而这样一种命运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发生在费尔巴哈的失败之际,并且也发生在施蒂纳的失败之际。施蒂纳指证了费尔巴哈的失败,但同时却只是补充了并且极其迅速地再度经历了费尔巴哈的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只是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超感性世界处于外在的对立中,就像施蒂纳以最极端的方式“超出了”精神的历史但却以漫画的方式详尽地再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构思一样。在征讨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初始的步伐中,感性领域的凸显并由之构成与超感性领域的对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困难,即只要感性领域仅仅被领会为超感性领域之极端的对立面,那么,感性领域也就是由它的对立面来规定的了。“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13)事实上,费尔巴哈也一般的懂得这一点,在他看来,现实的人不仅是感性的(感性生活),而且是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作为类本质的类意识)。他甚至在著名的“高卢—日耳曼”公式中把感觉与理智的统一提到了原则高度上。
那么,费尔巴哈所越不过的那个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大略言之,“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正是所涉之道路的未曾真正开启,使得这位哲学家知变却不知变法;而哲学变革在思想方面的要义无非是,归于“道路”并从而辨明之、开启之(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哲学》(14)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只是与超感性世界处于抽象的外部对立中,所以虽然它如此尖锐和极端地抗议并袭击了超感性领域,却并没有形成一条能够使之实质性破裂的道路,相反却仍停顿滞留于同样的神话学怀抱里。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对费尔巴哈“感性”的攻讦时,同样谈到了“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一种想要“跳出意识形态”(即跳出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尝试,谈到了“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15)。因此,“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16)这意思是说,费尔巴哈确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使他最终不得不以实质上是超感性的方式即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谈论感性本身。
这里出现的正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而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正是从这个决定性的区别发端的。体现这种区别之最关乎本质同时也是最为简要的概念表述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和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即“实践”)(17)。它们标识并且确定着关于存在者整体之领会的核心,因而是彻头彻尾的存在论定向,并因而是全部所谓“基础问题”围绕着旋转的枢轴。然而,如此紧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存在论“概念”却往往只是在相当浮泛的表面上、在某些较为遥远的所谓思想领域或理论后果方面被加以讨论,而很少深入到其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基本结构的定向本身之中,也就是说,遗忘或疏远了它们实际上最为切近的存在论主题,并从而使其重大的意义陷于晦暗之中。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起源”抑或“黑格尔主义传统”成为聚讼纷纭的领域,马克思的“实践”纲领遭遇到严重的——从结果方面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歪曲(以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为两个极端的代表)。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各式各样的当代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存在论的根基而言,问题的核心之点涉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涉及这一基本建制之被保留、巩固抑或被瓦解、摧毁。只要意识的内在性未能从根本上被决定性地洞穿,任何反叛的图谋最终都不得不再度复归于——并且还继续从属于——这一基本建制,从而仍然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一部以辅弼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在当代哲学的视域中,这一点已变得颇为清晰了。海德格尔说,自笛卡尔以来,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Subjektivitaet)被规定的;而在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普照之光中,所有意识作为“自身使当前化”(Selbstvergegenwaertigung),都发生在意识的内在性(Immanenz)之中。然而,“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18)
费尔巴哈确实试图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人”出发,这使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19)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意味着在“对象性”的关联中,“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20)。在这个意义上,与主体性的哲学相对立,费尔巴哈试图以作为感性对象的人来拯救真正的感性客体。然而,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却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感觉和单纯的直观。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就像单纯的感觉仍然可以滞留于感觉主体的内部自身一样,单纯的直观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进入——贯穿——对象领域,而只是在表面上做出了一个“跃进”的姿态便立即折返自身。这意味着,意识的内在性,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仍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只是这种内在性或许要被“替换”为感觉和直观的领域,然而在本质上却依然是意识的内在性。这种存在论立场在贯穿对象领域方面的根本无能(从而不得不返回我思的基本建制)突出地表现为:费尔巴哈完全无法克服感性直观中与其意识及感觉相矛盾的东西;“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21)如此这般的分裂情形不仅使得费尔巴哈的感性再度成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俘获物,而且还不得不把与思想—意识本质相关的广大领域实际地让渡给自己的敌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希图挽救感性对象的方式依然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所以他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全部驳难便很快跌落到这种神话学的窠臼中去了。
马克思——至迟自1845年始——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规定所谓“感性”,从而以彻底瓦解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方式重新制定了存在论的基本纲领。这里的核心之点在于: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即实践,不仅是与我思(即“自我意识”)根本不同的东西,而且是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它们只是在表面上区别于“我思”,但在基本建制上却与之一致)根本不同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性的活动”是以颠覆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基本建制本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从来就不是什么“封闭的区域”——仿佛有一个内在的实体之我能从自身中出来并从事某种活动似的;只要如此这般地来设想此等“活动”,无论是意识的活动或其他什么活动,总已先行地从属于意识的内在性建制了;感性的活动(即实践)之所以能贯穿对象领域,是因为它向来就已经在自身之外,也就是说,它向来就已经存在于并深入于对象领域了。“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2)
职是之故,“感性的活动”或“实践”的存在论定向首先就在于洞穿意识的内在性这个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唯当充分把握住这一点,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真正意义方始显现出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变革了的存在论视域中,“现实的个人”才可能被直接领会为感性的活动本身,而所谓对象、现实、感性才可能被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3)这个看起来颇为曲折的命题所要表现的是:在感性活动亦即实践的统摄理解中,正像人的活动先行地寓居于对象领域中一样,对象本身的存在亦先行地涵泳于人的活动领域之中。这样一来,作为基本建制的内在性就被贯穿了:根本就没有一个作为主体自身的封闭的区域(无论它是笛卡尔的“我思”,还是康德的“自我意识”,也无论它是黑格尔的“自我活动”,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身”)。“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的存在论定向中是“出离”自身的,也就是说,是在自身之外的,并且一向已经在外;它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是非主体的“主体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不是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4)。瓦解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是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之最关乎本质的核心之点。离开了这一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就会变得极其有限,它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后果就会变成是纯粹偶然的,而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整个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的真正根基就会依然是讳莫如深的和牢不可破的。
意识的内在性之被击穿所造成的后果是:它彻底地变革了整个哲学存在论,亦即整个地改变存在论设定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然而,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还是不确切的,因为它似乎仅仅是一种“理论的”说法。由于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变革中,传统哲学所谓的“本质性”已被导回到感性活动的领域,所以存在者整体之基本结构的真正改变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并且尤其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形而上学所固有的种种对立,不会仅仅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且仅仅在理论的领域中被真正克服。“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5)一句话,只要现存世界本身未能通过人的感性活动而被彻底革命化,哲学存在论所蕴涵的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就不可能最终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情形也能部分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往往会被再度塞进现代形而上学的体制之内来得到理解和阐释,并因而使其存在论变革的重大意义变得湮没无闻。
然而,以“感性活动”来定向的存在论革命毕竟开启了重新领会存在者整体的极其广大的领域。这里的问题倒并不全在于:较之于“感性对象”,“感性活动”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要广阔到无可比拟;而是在于:这两者在哲学存在论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像前者由于无能击穿意识的内在性而终归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一样,后者由于使得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趋于解体而赢得了烛照存在者整体的全新视域。关于这个视域的最基本的表述体现在下述命题中:“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
这个存在论命题固然是与整个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相对立的,但也本质重要地包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原则区别,因为它把社会—历史的定向置放在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中了。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他根本无能真正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费尔巴哈所谈论的直观实际上大多是——并且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直观,“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这里的核心之点在于,如果要来谈论真正足以瓦解“超感性世界”的感性现实的话,那么正是感性活动构成“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个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哪怕是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而提供出来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即使鲍威尔把“感性”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也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27)。正是由于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完全缺失了社会—历史的定向,所以他毕竟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也就是说,是一位对真正的感性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的形而上学家。
阿尔都塞说得不错,费尔巴哈的本质问题在于,他不可原谅地牺牲了黑格尔的历史和辩证法(由于在黑格尔那里这两者是一回事,所以也可以说是历史或辩证法)(28)。然而问题的真正本质不仅在于这种牺牲,而且尤其在于费尔巴哈存在论根基中的那种主导原则,在于这种原则如何使得历史—辩证法的牺牲对他来说成为不可避免的。与超感性世界相对立的“感性对象”——其反思形式是单纯的直观——从一开始就是与历史或辩证法相抵牾的,或者毋宁说,是处在其最遥远的对立面中。费尔巴哈并不是偶然地与历史—辩证法的巨大成果失之交臂,毋宁说,它直接被看做是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看做是这种神话学的内在本质。因此,“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29)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解释直接论证了费尔巴哈存在论的出发点,即肯定的东西或感觉确定的东西,亦即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然而,即便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遭遇到新一轮的存在论批判时,当“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以一种初拟的、不稳定的形式开始显现出来时,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经表现出与费尔巴哈相当不同的存在论取向了。正是这种取向——力图击穿意识的内在性——使得马克思能够在进一步摧毁超感性世界的同时把黑格尔哲学的巨大成果据为己有:否定性的辩证法,以及历史运动之具有原则高度的表达(30)。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通过接踵而至的存在论革命,不仅以一种真正彻底的方式揭开了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全部伪装,而且以要求对其现实基础的实践改造而宣告了这种神话学的破产。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也就是“意识形态”。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论基础皆把超感性的观念世界设定为具有约束力和建构力的真实的世界,是因为在变革了的存在论视域中超感性世界本身的虚妄性及其本质来历已经被意识到并且被指证出来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纲领是:“……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做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做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31)这就意味着超感性的观念领域作为决定性的原则统治感性世界即“物质世界”,意味着物质世界所具有的“秘密”成为哲学—形而上学家们活动的神话学领域。《神圣家族》中有一节叫做“思辨结构的秘密”,专门讨论这种神话学在其完成了的现代形式中的方法——绝对方法,其关键之点就在于: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32)。
然而,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更为重要——较之于指证其虚妄性远为重要——的一点是,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并不仅仅是虚妄的,它作为“虚假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3)不消说,这个深刻的思想是唯赖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方始成为可能的;同样不消说,正是这个思想超出了对于意识形态之虚假性的单纯的责难和攻击,而为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真正的批判性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影响深远的基础。1962年,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谈到尼采对于20世纪哲学的意义时写道,“我们不仅思考由伪装之神狄奥尼修斯神秘地表现出的伪装的多元性,而且同样思考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自马克思以来被越来越频繁地运用到宗教、哲学和世界观等被人无条件地接受的信念之上。”(34)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真正揭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全部伪装,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在存在论领域中彻底洞穿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从而使得“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的统摄理解中被揭示为“出离”性的;这种出离性直接意味着“人的世界”,正像“人的世界”在这里直接意味着历史过程和社会现实一样(所有这一切统统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只有当如此这般的存在论取向被牢牢地置入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立足点中,才有可能触动和瓦解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真正内核,并且才有可能终止任何一种神话学的批判向另一种神话学的不由自主的回返。且不说费尔巴哈所谓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如何命运般地重新成为超感性的“人”,亦即成为关于“人”的一种神话学,即使是特别无情地敌视超感性世界并以此而闻名的施蒂纳,同样也陷入了这种结局:他最坚决地拒斥人的普遍的“类本质”,他将“我的事情”置于“我这个唯一者”身上;这个唯一者会这样把哲学——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结束掉:他宣称他本身的“无思想”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并因而意味着胜利地进入“肉体生活”。无论这种说法听起来具有多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励了多少反神话的勇士,它本身却依然转变为一种关于“唯一者”的神话。正如马克思所说,施蒂纳事实上只不过是做了一种“思辨鞋跟上的旋踵运动”。在这种情形下,神话学的抨击者们将如何来设想从神话学中解放出来呢?他们试图教会人们如何从头脑里抛弃这些神话,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神话,或者,教会人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神话,以便使当前的现实陷于崩溃(35)。然而很明显,这种设想本身就为意识形态的幻觉所支配,亦即断言超感性的思想或观念统治着人们的现实世界,因而仍彻头彻尾地从属于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
对于马克思来说,“感性活动”的存在论定向是使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开始瓦解的思想前提,而这一瓦解本身所导致的理论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从起源并且也从实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旨就是在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解体过程中,开辟出一条揭示并且切中“社会现实”的道路。正是要求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根本主张,使得马克思的思想看起来又与黑格尔接近起来。因为思辨唯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对“主观思想”的尖锐批判,特别是对从属于主观思想的所谓“外部反思”的严厉拒斥;经由这种批判性的拒斥,黑格尔试图在客观精神的概念领域中达于真正的“现实”(亦即实存与本质的统一),达于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这一点确实是黑格尔较为深刻的地方;就此而言,费尔巴哈比起黑格尔来只是表现出“惊人的贫乏”。然而,在经由历史-辩证法并从而深入于社会现实这个主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类似也只是在相当确定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既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又力陈其辩证法与黑格尔“截然相反”,正如《1844年手稿》指证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一样。洛维特这样写道:“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来说,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恢复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学说。……他之所以针对费尔巴哈捍卫黑格尔,乃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而他之所以攻击黑格尔,乃是因为黑格尔在哲学上把历史的普遍关系神秘化了。”(36)
黑格尔是在什么地方把“历史-辩证法”神秘化的呢?是在现代形而上学之中,在思维的“内部自身”之中,在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之中。从而,马克思对历史-辩证法的非神秘化的领会便是在以上的诸项“之外”,也就是说,这种领会深刻地表现为与现代形而上学——特别是其基本建制——的批判的脱离,表现为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批判的脱离。而这种批判性脱离的必然性实起源于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
①②(12)(13)《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1页,第775页,第771页,第763页。
③(28)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第360页。
④(24)(30)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第324页,第316页,第319-320页。
⑤⑥⑧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页,第63-64页,第154-159页,第167-168页。
⑦⑩(36)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2页,第108页,第127页注①。
(1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14)参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88-607页。
(15)(22)(25)(29)(31)(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8页,第324页,第306页,第15页,第16页注1,第15页。
(16)(17)(19)(20)(21)(23)(26)(27)(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注1,第77-78页,第54页,第77页,第54页,第75-76页,第55页并参看第54页,第72页,第76-79页,第72页。
(18)《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载[北京]《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3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5页。
(3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标签:存在论论文; 神话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家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感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