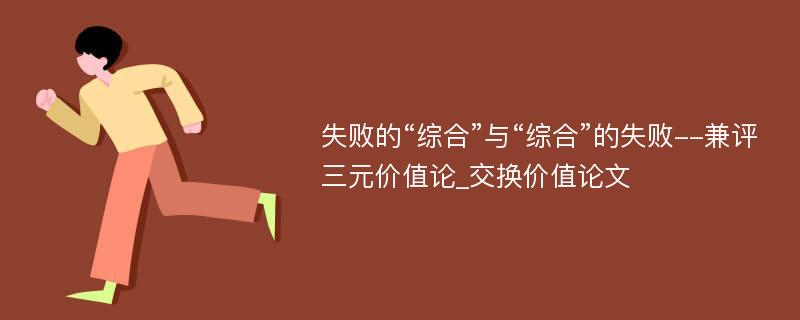
失败的“综合”与“综合”的失败——也评“三元价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丁建中等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隆重推出所谓“三元价值论”,试图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合理成份加以辩证综合”,进而克服其“局限性”(注:丁建中等:《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应该说,论者用心良苦, 所论也不乏真理的“颗粒”。但是从总体上看,“三元价值论”矛盾重重,鲜有实质性突破,在若干方面,甚至还不及传统价值理论已经达到的高度。目前,虽然已经见到一些对其提出批评的文章(注:我仅见到余陶生的《评“三元价值论”》(刊于《经济评论》1996年第2 期)和方军雄等的《从“三元价值论”到“信息价值论”》(刊于《天府新论》1997年第3期)。),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些批评所持的观点, 故不辞浅薄,就价值的质、量和增殖等三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与丁建中先生等商榷。
一、关于价值的实质
纵观经济思想史,所谓“价值”,指的是决定交换价值的那个“东西”。由于“价值并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所以,不同的学派对它有不同的认识。“三元价值论”认为,“所谓价值,从实体上说,就是一般使用价值或抽象使用价值”(注:丁建中等:《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是由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决定的。丁建中先生的这一观点没有错。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使用价值实体,满足需要。这就决定了人们在交换中比较双方产品的着眼点只能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别的什么。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不过“是物质财富的一种代表”(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3页。)。 如果撇开使用价值,商品就没有一个价值的“原子”。马克思也曾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认识到交换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一客观事实, 是效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但是,效用价值论对效用亦即使用价值的认识却是片面的、肤浅的。它或者认为效用是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9页。),或者把效用的“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注:[美]H ·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都没有认识到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本质。丁建中先生虽然看到了效用价值论合理的一面,却没有真正看清它的这一缺陷,因而也就不可能使效用价值论“面貌一新”。
有人认为,“三元价值论”“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因而不能解释“可能出现某一商品的价值量会同使用价值量相背的运动”的现象(注:方军雄等:《从“三元价值论”到“信息价值论”》,《天府新论》1997年第3期。)。的确, “三元价值论”不能解释这种“可能”。但是,它的失误不是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而是把“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实体”混淆了。在丁先生看来,效用是要素的产物(注:丁建中等:《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 产品即“新生成的一定使用价值”(注:丁建中等:《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其实, 产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实体。所谓使用价值实体,它是能够满足人的某些需要的物品或活动。使用价值实体不等于使用价值。比如,同一使用价值实体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即可以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再比如,同一需要也可以由不同的使用价值实体来满足,即不同的使用价值实体可以有相同的使用价值。不仅如此,随着时间、地点等条件的转移,同一使用价值实体的使用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石器曾经是人类重要的生产工具,而现在,至少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已经没有这种使用价值了。由此可见,使用价值实体不等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物品或活动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把使用价值实体与使用价值等量齐观。
区别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实体是认识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基础。目前,还有人以使用价值不同质,因而不可比为由,否定使用价值在交换价值决定中的地位。(注:余陶生:《评“三元价值论”》,《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其实, 这个“经典”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我们知道,任何客观存在都是具体与一般的统一,使用价值怎么能例外呢?如果使用价值没有“一般”,也就不会有“使用价值”这个概念。因为概念作为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或者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是同质与异质的统一。不过,商品一般使用价值与物品一般使用价值不同,它的实质是以要素个别占有为基础的生产交换关系,是物品一般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注:朱健:《“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试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商品生产是建立在要素个别占有基础上的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在交换之前,构成商品使用价值的两个要素被分割在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当中,不能无偿地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交换,商品才能实现“自我”。因此,商品供求关系的实质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既是物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态,又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古典劳动价值论者只注意价值的量,不注重价值的质,无论斯密还是李嘉图,都没有对价值的本质做任何说明。与他们不同,马恩把价值看作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的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恩格斯也认为:“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页。)虽然马恩的认识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发现商品价值亦即商品一般使用价值本质的卓越贡献。
认清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本质,是把效用价值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关键。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本质说明,个别占有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社会物质基础。空气、阳光这些具有很大效用的自然物品之所以没有价值,是因为这些自然物品没有被个别占用,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效用价值论者不理解这一点,只得用稀缺性来解释。事实上,稀缺与个别占有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不是一回事。稀缺并不必然决定某一物品一定有交换价值(注:朱健:《商品一般使用价值及其计量》,《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三元价值论”没有把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实体区别开来,也没有把物品的一般使用价值与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就不可能揭示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本质,从而走出效用价值论的困境。丁建中先生清楚地看到,“‘效用价值论’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在其早期论文中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即任何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一要有用,二是物品的获得花费了劳动(注:丁建中等:《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 试图以效用与劳动的二元论来化解效用价值论的难题。然而,有些自然物,如处女地、天然林木等虽然没有花费劳动,却也有交换价值,这就迫使丁先生最终不得不把劳动撇在一边,在事实上将价值与“效用”看成一回事。所以,在其否定效用价值论的早期论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把价值与效用相提并论的现象。后来,丁先生则干脆与效用价值论者为伍,不再提及效用价值论的这个“缺点”。
二、关于价值的计量
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提出的其它一些价值理论“新说”不同,丁先生的“三元价值论”既谈“质”也说“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非但没有解决价值的尺度问题,相反却钻进迷宫找不到出口,在事实上认定价值量“不可知”。
丁建中先生提出,衡量商品价值不应只是劳动耗费这一尺度,而应是三维尺度,即“商品价值是自然生产力(土地)、物力资本生产力(资本)、劳动资本生产力(劳动)的三元函数。”(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并将其称之为“三维尺度”。这一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三种生产力”的耗费,另一部分是附加价值(注:丁建中等:《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 )。
丁先生认为,“三种生产力”的耗费是通过商品的平均生产成本间接测得的。在丁先生看来,“价值的内在尺度,即抽象生产力”(注:丁建中等:《“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经济问题》 1996年第9期。)。然而,由于“三种生产力”的耗费量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能具体计量,人们只有通过计量具体的土地、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占用或耗费来代替无法计量的“三种生产力”的占用或耗费;又由于“土地、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也不可以直接通约”,人们只得再退一步,“用占用成本来间接衡量‘三种生产力’的耗费量”(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丁先生的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萨伊说的:“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0页。)。这是纯粹的“逆运算”。根据“三元价值论”的观点,“占用成本”是由占用要素的价值决定的,它是占用要素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说到底,它是由占用要素的一般使用价值决定的。所谓“三种生产力”的耗费也就是占用要素一般使用价值的耗费。因此,说“三种生产力”的耗费不可计量,也就等于说占用要素的一般使用价值不可计量,如果占用要素的一般使用价值不可知,那么它的成本就是一笔糊涂帐。一句话,用生产成本计量“三种生产力”的耗费是本末倒置。
至于“附加价值”如何计量,丁先生有两种说法,一说它是“新价值”剔除用于补偿生产费用的价值量后的余额(注:丁建中等:《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 一说它是由成本的平均附加价值率决定的(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前一种说法是“踢皮球”,不可能“踢”出结果。大概丁先生意识到这个漏洞,后来又换了一个说法。然而,这个所谓“平均附加价值率”,据丁先生说,它也是“不确定的”(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可见,无论“三种生产力”的耗费,还是附加价值都莫测高深。所谓“三维尺度论”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效用价值论始终没有解决效用的计量问题,目前计量效用的“希望已经正式被抛弃了”(注:[美]道格拉斯·格林沃德主编,李滔等主编译:《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8页。 )。不过,萨伊认为,决定交换价值的效用是可知的。他说:“就每一个估价行为说,被估价的物品是不变的已知数。”(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8页。 )丁建中先生认为:“‘效用价值论’只从效用(抽象使用价值)谈论价值,撇开了效用的来源,就使价值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丁建中等:《“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经济问题》1996年第9期。 )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至少萨伊曾明确指出:“人们所给与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而物品的用途是“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它是生产创造的(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9页。)。因此,价值即效用“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5页。)。萨伊价值理论的失误,不是撇开效用的来源不谈,而是没有揭示效用的本质,并且在效用计量这个问题上跌进主观的泥潭。萨伊认为:“物品的实际效用”是由人们“估定”的,至于是否准确,“这要看估价者的判断力、知识、习惯的成见以为定。”(注:[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9页。)
丁先生认为,决定价格的是“扬弃了各具体使用价值差别的一般使用价值”(注:丁建中等:《“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经济问题》1996年第9期。)。可是,在论及商品使用价值的计量时, 却又认为“使用价值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计量尺度,不可通约”(注:丁建中等:《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丁建中先生之所以“出尔反尔”, 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对使用价值一般性的认识不彻底,还没有完全与传统认识拜拜;再一是没有发现计量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尺度。商品一般使用价值不是一种物质实态,因而无法直接计量,但可以间接计量,非不能计量。任何客观存在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而凡是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计量。因此,商品一般使用价值不可计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构成商品使用价值的两个要素,即供给与需求不仅统一于生产而且取决于生产,所以,计量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尺度只能到商品生产中去寻找。丁先生也是把生产作为寻找价值尺度的起点的,但是,他没有发现,如果撇开其具体形式,任何生产都是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更没有发现,生产时间既是计量生产一般的天然尺度,也是计量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间接尺度。商品一般使用价值以社会必要生产时间为计量单位。所谓社会必要生产时间,它是由社会需求决定并且反映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供给必要生产时间(注:朱健:《商品一般使用价值及其计量》,《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发现时间是计量价值的尺度, 是劳动价值论者的又一巨大贡献。有人提出,有些商品使用价值很大,交换价值却很小;而有些商品使用价值很小,交换价值却很大(注:余陶生:《评“三元价值论”》,《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 论者之所以“量”出这么一个“价值悖论”,症结在于计量的尺度错了(注:朱健:《商品一般使用价值及其计量》,《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这如同以体积作为“计量”物品重量的尺度,就会得出1 千克棉花比1千克铁“重”的结论一样。
三、关于价值的增殖
丁建中先生非常关注价值增殖问题,然而在价值增殖的条件和源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夹缠不清。
在丁先生看来,“进一步揭示价值增殖的秘密”,“关键是弄清生产力三分力的协同作用”(注:丁建中:《“三元价值论”的实质及意义》,《天府新论》1996年第5期。)。他认为, “‘三种生产力’的协同,一方面使得商品功能放大或增进,一方面使得商品价值增值。”(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即所谓“生产力系统具有放大功能”(注:丁建中等:《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然而事实上, 生产要素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协同的结果,并非一定是商品价值增殖。如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有56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其中英镑、法郎等贬值达50%以上,德国马克分文不值,国家破产事件达历史最高水平(注:参看刘淑兰主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7页。)。研究已经证明,“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是一个扩张和收缩有规律交替的过程(注:参看陈乐一:《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一般考察》,《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 即使在经济扩张时期,也存在一定数量企业因亏损而倒闭的现象。由此可见,“三元价值论”对价值增殖的解释似是而非,并没有挠到问题的痒处。
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存在波动,就存在生产力的扩张和收缩;每一个企业就都面临着盈利或亏损两种可能。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价值才会增殖呢?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产出大于投入这样的高度,只有当产品能够适合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时候,价值才会增殖。
价值增殖必须具备上述两个条件,是由商品一般使用价值的自然性质决定的。从实物形态来说,“增殖”的价值,就是从生产物中扣除各种生产耗费后的剩余。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率为负或为零,那么,在扣除成本后就不可能有剩余,商品的价值也就不可能增殖。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9页。)。因此,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注:《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2页。),是决定社会财富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求在价值决定中无足轻重。没有需求,任何供给都是无效的,也就没有价值。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价值下跌、企业亏损乃至全面经济危机。因此,要实现价值的增殖,产品就必须投消费者所好,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就整个社会来说,价值增殖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一定水平的生产率是价值增殖的基本条件,产品适合社会需求是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说过:“正如骑驴的人用胡萝卜和大棒驱使驴前进一样,市场体系用利润和亏损来引导企业有效率地生产出合意的物品。”(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胡代光等译:《经济学》第14版(上),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只有有效率地生产出合意的物品,企业才能获得利润,商品的价值才能实现增殖。就个别产品而言,适合社会需求更为重要。
价值增殖的两个条件说明,在构成使用价值的物或活动与人的需要的关系中,作为使用价值客体的物或活动,同作为使用价值主体的人,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价值“属于”物品或活动,因而商品一般使用价值增殖的源泉是包括耗费要素在内的占用要素。首先,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占用要素。我们知道,生产率“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因此,从宏观上看,每一经济长周期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科技革命浪潮或重大科技突破提高生产率有关。如启动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长周期的,是“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这两个重要发明在纺织业生产中的应用。从微观上看,技术先进、设备精良、规模适度、管理科学则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较多利润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次,产品是否符合消费需求,也取决于占用要素。产品的质和量取决于占用要素的质和量。比如,没有金钢钻就揽不了瓷器活,只有慧眼独具才能发现潜在市场。在现代,科研能力和企业家才能在开发产品和市场方面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生产不只是耗费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是包括耗费要素在内的占用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丁先生似乎对此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常常把占用要素与耗费要素混为一谈。如,有时认为,“‘三种生产力’的协同”,“使得商品价值增殖”(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有时又认为,“等量的价值消耗对新价值的作用或贡献相等。”(注:丁建中等:《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再如, 把生产成本解释为“对‘三种生产力’的占用或耗费”(注:丁建中等:《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其实,就某一生产过程而言,占用要素一般与耗费要素在量上是不等的。所谓占用要素是指投入某一生产过程的全部要素,即企业的全部资本;而耗费要素则是指生产一定数量某一产品消耗的要素,即产品成本。价值增殖是占用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占用要素必然要求“利益均沾”,即在正常社会生产条件下,等量占用要素取得等量利润。
* * *
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认识到,马克思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解释许多经验事实,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加以“综合”,才能建立起最充分地反映当代经济现实的更加科学的价值理论。如,樊纲先生在数年前也曾进行过包括价值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综合”(注:樊纲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69—209页。),胡义成、鲁品越等先生亦力主“综合”说(注:胡义成:《马恩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反驳》,《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5年第11期;鲁品越:《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对应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要把传统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和“局限性”真正搞清楚,既不把孩子泼掉,也不搞“重复建设”。“综合”的实质是扬长补短,是理论的重塑,必须在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狠下功夫,下狠功夫。我认为,俄罗斯学者戈卢布的一句与此有关的话,值得我们在操刀“综合”前认真思考。他说:“合理内核在两种观点中,而它们中每种观点的发展都是很必要的。”(注:[俄]戈卢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若干方面》,黄德兴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期。 )尽管丁建中等先生一再说明,他们“论及的‘三元价值论’综合了‘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斯密、萨伊提出过的‘三元价值论’的合理因素”(注:丁建中等:《“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经济问题》1996年第9期。 ),然而,从总体上看,它不过是萨伊价值理论的翻版。丁先生的“综合”之所以失败,其根源就是没有把传统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和“局限性”全部吃透,继承和创新都很欠火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