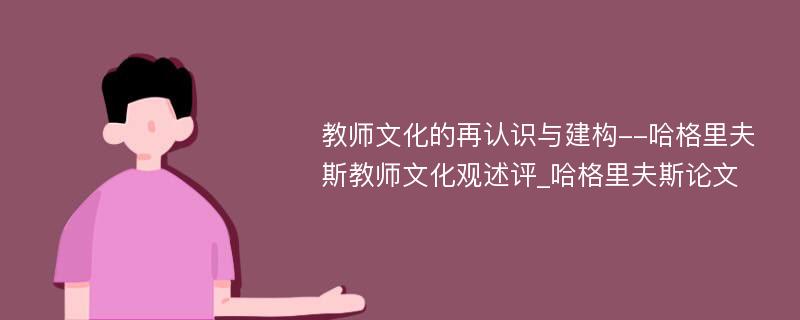
教师文化的重新理解与建构——哈格里夫斯的教师文化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教师论文,文化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A.)是加拿大的著名学者。他的教育思想凝聚着他对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深入洞察和思考。在急剧变化、社会转型的时代里,他强调教育革新要充分关照教师文化的变革。
一、后现代:教师文化的时代背景审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虽然缺少严格界定,但已经可以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全新社会——后现代社会,它正在催生或即将导致教师工作和文化的重大变革。”[1]这是哈格里夫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社会变革及其对教师文化影响的一个基本判断。在后现代概念的理解上,哈格里夫斯不赞成有些学者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与后现代时代(postmodernity)混为一谈。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文学、艺术学、建筑学、哲学等经常使用的术语,它包含着这些领域的特定风格和实践模式等,而后现代时代则体现着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混沌、模糊、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偶然性以及变革等都是描述后现代时代特征的关键词。后现代社会的这些新特征和新变化使得教师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这种挑战体现在教师工作的时间投入必须大大增加。其次,后现代时代的教学对教师的劳动强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后现代时代的多变性使得教师的教学情感正在经受考验。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后现代时期由于人们偏激地强调共识与合作,教师的个性容易迷失,从而使教学职业原本具有的孤独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鉴于教师文化与其日常的职业生活之间的相属关系,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教师文化中来。因此,考察后现代时期的教师文化就必须从教师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充分关照其赖以存在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学校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哈格里夫斯把教师文化放在后现代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其价值、内涵以及未来发展是合理的,也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
二、变革的核心:教师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
在后现代时代,变革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对于处于社会变革中心的学校教育来说,其变革本应更为迅速、深刻。但是,综观近年来的国际教育改革,无论是课程改革和学校结构调整,还是教师专业化改革均鲜有成效,教育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不可否认,教育改革对教师以及教师文化的忽视是造成各种改革项目表面化和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哈格里夫斯对此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鉴于以往的教育改革的弊病,他指出:“全球教育改革越来越被推向通过学校的结构调整、制度完善等来实现变革的轨道,而对教师文化却很少顾及……因此,将来的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化运动应该更加重视教师文化的价值。”[2]为了充分揭示教师文化之于教育革新的重要意义,他强调用一种三维的标准来审视教育变革,指出学校变革不仅在长度上要具有前后连贯性和持续性,而且在宽度上要摆脱视野的局限,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变革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即学校变革不能仅停留在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修修补补,而要致力于学校员工的价值观、教育信念、共同愿景、思维方式等的变革。而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教育变革之成败的决定因素都在于教师文化。
哈格里夫斯的这种重视教师文化的效用和力量的思想是符合文化的本真意义的。史谟勒(Small)曾经指出:“文化是机械的、心灵的和道德的技术之全部整备。在某一时期,人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标。”[3]可见,文化不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表征,而且也可以被用作改造社会的武器。而对于文化价值的承认与接纳构成了哈格里夫斯的教师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此外,他对教师文化价值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反思教育变革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观念上存在的局限必然使教育改革带有现代性(modernity)的痕迹,强调行政干预、人为控制以及对文化的忽视是其突出的特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后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人的思维、观念、情感、态度等因素对改善工作质量的影响,文化因而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哈格里夫斯大声疾呼重视教师文化在教育改革及教师专业化中的核心作用,这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即在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教育变革及其教师专业发展的范式如何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
三、以形式为中心:教师文化内涵的重新解读
解读文化的内涵有多种方式,不少学者如泰勒(Tylor)、克罗孔(Kluchhon)、维斯勒(Wissler)等都主张从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来领略其深刻含义。 对于作为学校亚文化的教师文化的研究,同样有很多学者习惯于从其内容方面来展开。我国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教师文化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包括教师的信念、价值体系、行为模式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了教师文化的统一体[4]。这种从内容方面来进行的教师文化探讨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甚广、界限模糊的概念,所以如果仅从内容方面来探讨,有时很难清晰、透彻地揭示其本质属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考虑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教师文化。哈格里夫斯在这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认为,考察教师文化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教师文化在内容上包括特定范围的教师集体共享的态度、价值、信念、习惯、假设以及行为方式等,教师文化的内容外显于教师的所思、所说和所做。教师文化的形式包括处于特定文化群体中的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和联系方式,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教师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如何。基于教师文化的内容都是通过关系的若干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一认识,他从“形式”的视角展开了其教师文化论,并由此将教师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派别主义文化(balkanization)、自然合作文化(collaborative culture)、人为合作文化(contrived collegiality)。其中,前三种是现状的形式分类,后一种是为了变革而采取的实践形式。对于每一种教师文化,哈格里夫斯都精辟地分析了其成因,并探讨了它对教育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一)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因及其取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劳蒂(Lortie)曾经对教师个人主义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教师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即是指教师羞于与同事合作和不愿意接受同事的批评,教师之间并没有合作共事的要求与习惯[5]。教师在教学中所持的独立成功观以及对其他教师所采取的不干涉主义的态度,虽然有利于教师保护教学隐私和回避外界对教学工作的侵扰,但它也切断了教师从外界获得各种支持和评价的通道,不利于其自身以及其他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教师个人主义文化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和失败,需要消除。而这需要找出导致教师个人主义文化的真正原因。劳蒂、罗森赫兹(Rosenholtz)等学者认为,导致教师个人主义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教师的工作及其环境因素, 如教师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学校的细胞型结构、封闭型的课程教学环境、教学缺少共同认可的权威和共享的教学技术等;2)教师的心理品质存在许多缺陷。比如, 由于教师追求教学的心理报偿,因此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课堂和学生而对同事的工作漠不关心;由于害怕评价和批评,教师具有习惯性防卫的心理;由于很难看到自己工作的明显成效,因而容易产生焦虑、压抑等。
哈格里夫斯对这些研究成果深入地进行了反思。他从教师文化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个人主义仍然顽固地主宰着当前的教师文化?在他看来,这不仅由于人们对教师个人主义文化的归因有误,而且还由于人们在彻底否定个人主义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对个人主义缺少应有的包容。
因此,哈格里夫斯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诠释。他在汲取弗林达斯(Flinders)思想的基础上,将教师个人主义的成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即行政压力、工作环境和教师个性特征,并由此将教师个人主义划分为限制性个人主义、策略性个人主义和选择性个人主义。这种归因比前人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显然更为科学,它揭示出教师个人主义是由组织环境、工作性质、教师职业心理特征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因而变革教师个人主义文化,不是仅靠拆除教师之间的围墙或发展教师心理技能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综合考虑。而且在变革中,必须全面地认识教师个人主义文化的价值,把教师个人主义文化完全理解为消极的文化并大加挞伐是对它的曲解和不公。他引用斯蒂芬·卢克司(Steven Lukes)的话说,个人主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少与人的尊严、自主权、隐私权、自我独立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教师来说,独处有时不仅意味着一种高贵的品质,而且有利于培养后现代教学所需要的核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自主抉择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进行新时期的教师文化建设时,我们对个人主义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既要尽量避免其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缺陷,又要利用发挥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二)自然合作文化与人为合作文化
哈格里夫斯以组织文化和微观政治学的视角,对教师合作文化进行了一番检视,并将教师合作文化区分为自然合作文化和人为合作文化,指出它们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两种文化。
在哈格里夫斯看来,教师合作文化是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成的一种相互开放、信赖、支援性的同事关系,它具有5种特征[5]:1)自发性(spontaneous),即合作关系非外力诱发,而是每个教师自发地形成的;2 )自愿性(voluntary),即合作关系是一起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其实践既非义务也非强制;3)发展取向性(development-oriented),即合作是指向教师专业发展的;4 )超越时空(pervasive across time and space),教师相互交往不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可以充分地进行;5)不可预测(unpredictable),即合作的结果不一定表现为成果,因而不能简单地预期。他肯定李特尔(Little)等人的关于自然合作文化的研究成果,指出合作的中心意图在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整体发展[6]。因为在这种文化下,教师对于教育教学上的失败和不确定性不再采取防卫性态度,而是相互援助,同事共同面对和接受问题,相互进行讨论;同事之间追求在教育价值上有广泛的一致性,但是对于细节上的不一致也保持宽容。正因如此,教师有利于超越个人反思的局限,从同事那里获得更多的专业发展所需要的工具性支持和社会—情感支持,增强了专业自信,更加勇于探索和冒险,这必将大大地促进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7]。同时,同事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教师群体的发展, 有利于整合教育力量来改善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因而,自然合作文化有助于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发展的有机结合。
在构建教师合作文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各种强制性因素的干扰,自然合作文化容易被扭曲为人为合作的文化。所谓的人为合作文化就是指通过一系列正规的特定的官方程序来制定教师合作计划,增加教师间相互讨教的机会。对于这种文化,哈格里夫斯引用柯泊(Cooper)的话一语道破其实质,它是一种接受性文化,是一种对自然合作的安全模仿。其特征也有5个方面:1)行政控制性(administratively regulated),即合作关系不是由教师自发形成而是行政命令催生的;2)强迫性(compulsory),即在很少顾及教师的个性以及所喜好的工作方式的情况下,以强制的方式推行团队教学、同伴指导、集体备课等改革项目;3 )实施取向性(implementation-oriented),即教师合作的目的在于实施行政命令,而不在于促进专业发展;4)特定的时空(fixed in time and space),教师合作的时间和场所等不是由教师们自由决定,而是由行政命令来指定;5)可预测性(predictable),即合作按照特定计划进行,其成果具有较大的人为控制性和可预测性。哈格里夫斯对这种人为合作文化持批判的态度,他通过一些实证研究阐发了几个结论性的观点。其一,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在后现代时代里更是如此。教师工作的情境性决定了我们无法用标准化的方式来推行机械的合作;其二,人为合作文化违背了教师专业主义理念,没有尊重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应该享有的自主判断和自我抉择的权力;其三,实践证明,人为合作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消极后果,即缺乏灵活性和无效性。鉴于人为合作的诸多缺陷,哈格里夫斯指出,人为合作文化必须向自然合作文化过渡,其重要的一个策略是赋权学校和教师,让他们走向合作。
哈格里夫斯对于这两种合作的教师文化的区分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当前正在推行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在其过程中,基于综合课程教学和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要加强教师合作文化建设,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举动,但其前提之一是必须理解合作的真正意义。在这方面,哈格里夫斯关于合作文化的论述当然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在借鉴他的观点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他关于教师合作的论述也存在不足。我们尤其不赞成哈格里夫斯把“自发性”作为教师合作的基本特征,其原因是合作关系不容易自发形成,如果把自发性作为教师合作的基本特征的话,实际上就放弃了我们对培育教师合作的期望和努力了。而事实上,欧美各国近年来采取的“同伴互教”(peer coaching )和“资深教师的辅导”(mentoring)这些合作策略,尽管并非教师自发的,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很好的促进教师发展的方式。因此,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对教师合作文化强烈诉求的情况下,包括校长在内的各级教育管理者不应该持坐等、观望的态度,而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三)派别主义文化及其困惑
从前苏联的解体中,哈格里夫斯深切地体会到了派别主义文化对集体组织的巨大冲击。在他看来,学校中存在的派别主义文化更值得人们警醒和反思。生活在这种文化里,教师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整个学校教师分属若干个团体或派别,每个教师只忠于自己的团体,而与其他团体教师不相往来,甚至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敌视其他团体中的教师。教师的派别主义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1)低渗透性(low permeability)。在派别主义文化里, 合作只发生在每个派别内部,而派别之间则相互隔离和排斥,每个派别都有固定的成员,且这些成员不能同时兼任其他派别的成员;2)高持久性(high permanence)。教师派别团体一旦形成,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成员流动和消逝的现象,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持久性发展趋向;3)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fication)。派别成员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念、自我身份与派别相连;4)政治功能性(political complexion)。各派别发挥着为其成员追求晋升、地位和资源的功能。派别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学校领导在教育管理上过多地强调或习惯于同一年级和相同学科教师之间的横向组合,而忽略了纵向划分的连续性和缺乏宏观的管理理念。
派别主义文化在中学和小学的表现存在着差异。中学由于规模较大,人际关系复杂,加之学科之间的分割现象严重,因而其派别主义文化尤其体现在各学科之间的各行其是和相互竞争等方面。而在小学,教师派别主要是以年级或年段来划分的。但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小学,派别主义文化都客观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对于向来重视个人与个性的西方国家来说尚且如此,对于历来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国家来说,教师派别主义文化则更为普遍和严重。在我国的中小学里,大都存在着各种教师集体组织,如年级组、学科组、集体备课组、合作科研组等,而且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些教师集体组织是令人羡慕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欣慰之余,不难看出这些组织实际上是静态的、僵化的、封闭的,其弊端不仅在于它们限制了全校教师发展共同使命的可能性,制造了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也减少了全校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因此,派别主义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发展,给学校的整体变革带来了困难。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种教师文化给综合课程的实施带来了很多实际困难,是迫切需要加以改革的。但对于如何改革派别主义教师文化,我们始终在谨慎地探索。在我们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消除学科组、年级组等教师集体组织等措施并不现实,而且哈格里夫斯也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这种措施难以在规模较大的中学奏效,我们似乎处于一种两难境地。然而,哈格里夫斯建构的“第五种教师文化”却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四、“流动的马赛克”文化:着眼于后现代教学的教师文化模式建构
哈格里夫斯从后现代时代的视野出发,构建了第五种教师文化模式——“流动的马赛克”(the moving mosaic)。所谓马赛克(mosaic), 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它是指用不同颜色的小块玻璃、石子等材料镶嵌成的图画或图案。如果构成整幅图案的各个部分处于静止的状态,那么不难看出,这些部分之间是存在明显界限的,互不干涉的。这基本上可以用来形容教师之间貌合神离的合作,即表面看起来,各个教师群体组织组成了整个学校的完整画面,而各个教师组织之间却处于不合作状态。但是,如果让马赛克图案的各个组成部分处于动态循环的状态,则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一幅全新的画面,而这正是哈格里夫斯所建构的教师文化新模式。
在他看来,“流动的马赛克”文化是最适合后现代教学需要的理想教师文化模式。在这种教师文化模式下,学校根据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允许若干个教师小组的存在,每个教师小组的活动范围和成员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交叉重叠的。这样各个教师小组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随时可能更新成员和转换职能。从性质上看,它们都是开放的,相互合作和支持的。因此,这些小组凝聚在一起必然会达到一种总体力量大于各部分力量之和的效果,并且使整个学校组织呈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流动性和适应性,具备了彼得·圣洁(Peter Senger)所描述的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的一些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师合作文化可以超越学校界限,扩展到学区、社区乃至于更大的范围。
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教师文化模式?目前,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教师文化本身就具有很明显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和争议性,加之哈格里夫斯对这种教师文化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所以很多学者在评介他的教师文化观时都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种文化模式忽略了。但我们觉得这些都无法遮蔽他对教师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流动的马赛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社会教师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教师,离不开这种文化的支撑。正如埃德加·富兰(Fullan)所言,“生活在混沌边沿意味着要习惯于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蕴涵其中的理由是,任何系统,例如拥挤的蜂房、企业、经济秩序,在混沌的生活状态下,都会‘自我组合’以产生适应性行为……而这种适应性行为的中心就在于在少量严格的规则下,扶持一种经常变化、流动的文化……最终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学习系统”[8]。斯泰西(Stacy)也曾经指出,发展多种文化,建立灵活的结构和学习小组,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去冒险和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