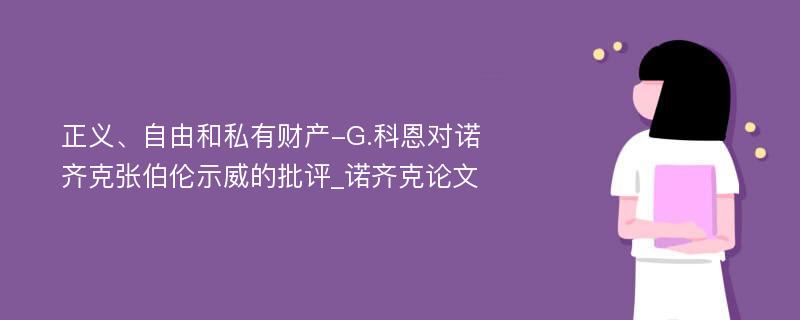
正义、自由与私有财产——G.A.科恩对诺齐克“张伯伦论证”的再次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伯伦论文,正义论文,财产论文,自由论文,诺齐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6-0018-06
“张伯伦论证”是诺齐克在其1987年出版的代表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证,它的提出既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倾向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又对为很多左翼学者信奉的社会主义构成了挑战。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捍卫,牛津大学的科恩教授在其1995年出版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①一书中对“张伯伦论证”做了强有力的反驳。这本书中直接涉及“张伯伦论证”的内容有两章,即第一章“罗伯特·诺齐克和威尔特·张伯伦:模式如何维护自由”和第二章“正义、自由和市场交易”。从这本书的“导言”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章源自他1977年发表在Erkenntnis②第11期的一篇同名论文,而且在收入《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时“几乎没做什么修改”[1],第二章则是他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出版前新写的。③由于这两章的实际写作时间相隔了十几年,而且科恩在这期间对“张伯伦论证”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因而它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深度上都有较大差别,用科恩自己的话来讲,“成为第一章的这篇文章是我在规范的政治哲学中的首次演习。它回避了,有时是特意地,很多关于自由、正义和强迫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而且我还有机会在以后的研究再面对。第二章谈的则是两个在第一章引发的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仔细地考虑了诺齐克的这一表述:‘通过正义的步骤从正义的状态中产生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正义的’,并表明它的表面上的不证自明——而这正是诺齐克利用的,是虚假的。然后我转向自由至上主义对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同化,并揭露了它依赖的是概念诡计”[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章分别代表着科恩认识和批判“张伯伦论证”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他对这一论证的“初次批判”,后者是他对这一论证的“再次批判”。
鉴于国内学者对科恩如何反驳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尚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以及一些学者在说明他的反驳时往往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混同起来使用④,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科恩认识和批判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真实进程,笔者前些时候曾写过一篇专门论述科恩对“张伯伦论证”的初次批判的文章,在这里,笔者将集中论述科恩在第二章对“张伯伦论证”的再次批判。
一
“张伯伦论证”是诺齐克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张伯伦为假设对象而提出的。仔细读一下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提出“张伯伦论证”是基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区分。诺齐克将分配正义原则区分为“历史的正义原则”和“最终状态的正义原则”。依据前者,“一种分配是否是正义的,依赖于它是如何发生的”[3],依据后者,“分配正义是由东西如何分配(谁拥有什么东西)决定的,而其对此的判断则是由某种(或某些)正义分配的结构原则做出的”[4]。接着,他又将历史的正义原则区分为模式化的原则和非模式化的原则。“如果一种分配原则规定分配随着某种自然维度、自然维度的权重总合或自然维度的词典式序列而变化,那么让我们把这种分配原则称为模式化的。”[5]而非模式化的原则则是指每个人通过合法的程序得到他们的持有物。诺齐克本人赞同历史的、非模式化的原则,在他看来,所有其他的分配正义原则,无论是最终状态的原则,还是模式化的原则,都可以被一个“自由如何打乱模式”的例子所驳倒。这个例子就是他的“张伯伦论证”:
我们假设,一种由非资格观念所赞成的分配已得到了实行。我们还假设,它就是你赞成一种分配,并且我们把这种分配称为D1。在这种分配中,也许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份额,也许份额随着某种你珍视的维度而变化。现在我们假设,威尔特·张伯伦是篮球队所极其需要的,具有巨大的票房价值。……他同一个球队签下了如下合同:在每一个主场,每一张售出的门票价格中有25美分归他。……这个赛季开始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去观看他的球队比赛。在他们买票的时候,每次都把门票价格中的25美分单独丢进一个专门的盒子,而盒子上写有张伯伦的名字。他们看他打球感到非常兴奋,对他们来说,门票价格是物有所值。我们假设,在一个赛季,有100万人观看了他的主场比赛,威尔特·张伯伦挣了25万美元,这个数额要比平均收入大很多,甚至比任何一个球员的收入也大很多。他有资格得到这笔收入吗?这种新的分配D2是不正义的吗?如果是不正义的,为什么?至于每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控制他在D1中所持有资金,这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这种(你赞成的)分配,而我们(出于论证的目的)也假定它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愿意在他们的钱中拿出25关分给张伯伦。他们可以把这笔钱花在电影院或糖果店,也可以用来买几份《反调》或《每周评论》杂志。但是他们至少有100万人都把它给了威尔特·张伯伦,以换取观看他的篮球比赛。如果D1是一种正义的分配,而且人们自愿地从D1移动到D2,从他们在 D1得到的份额中转让一些给别人(如果这一份额不是用来花的,那么它有什么用?),那么D2不也是正义的吗?如果人们有资格来处理他们(在D1中)对之拥有资格的资源,那么这不是也包括他们有资格把它给予威尔特·张伯伦,或者同他进行交换?其他任何人能基于正义对此抱怨吗?其他每一个人在D1中已经拥有他的合法份额。在D1中,对于任何人所拥有的东西,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基于正义提出要求。在某些人把某些东西转让给威尔特·张伯伦之后,第三方仍然拥有他们合法的份额,他们的份额并没有变化。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这样一种两个人之间的转让能够引发第三方对所转让的部分提出基于分配正义的合法要求,而在转让之前第三方对这两个人的持有都没有提出任何基于正义的要求?[6]
科恩在第一章就已指出,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从根本上讲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1):“通过正义的步骤从正义的状态中产生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正义的。”[7]这一命题中的“正义的状态”,是指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他们应当拥有的全部持有物,而且只是这些持有物。这一命题中的“正义的步骤”,是指人们的行为不存在非正义,即在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没有人是以暴力或欺骗行事的。诺齐克本人对这一命题的真理性是如此地自信,以至于认为只需对它加以应用,而无需对它做任何论证,就能颠覆包括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内的最终状态的分配原则和模式化的分配原则。科恩在第二章中说,在写作第一章时,“我对这一命题的可信性不太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那种假定的它对平等主义的正义观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没有花费时间对它进行与其相称的审视”[8]。为此,他在第二章中先对诺齐克的这一命题做了更为缜密的分析和批判。
二
在批驳诺齐克的命题(1)之前,科恩先对“人们为何会认为,就像诺齐克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显然认为的那样,(1)是不证自明的,或换句话说,是不容置疑的”[9]做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人们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三种不正确的推论。
第一种推论是:如果我们从正义出发,而且除了正义我们没添加任何东西,特别是没添加任何非正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会得到非正义的结果。科恩说,这种推论可能来自两种通常的想法。第一种想法比较简单,即认为同类事物相加其结果不可能是反同类的事物。这种想法显然不能成立,因为所说的这种不可能实际上总在发生,例如,两个奇数相加结果是偶数,两种可燃的物质混在一起形成一种不可燃的物质。第二种想法虽“不那么简单,但仍粗糙的让人难以接受”[10]。持这种想法的人可以承认两种错误有时会产生一种正确,因为错误和缺陷作为消极的东西可以相互抵消,但他们却坚信两个正确的东西不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东西。换句话说,非正义是一种缺陷,而一种缺陷肯定是来自某种有缺陷的东西,但如果一种新状况只是产生于一种更早的正义的状况和正义的步骤,那它怎能存在缺陷呢?对此,科恩的回答是:“完美的事物的结合确实可以产生不完美的事物。”[11]例如,一桌上好的饭菜与一瓶不相配的好酒,或在一个全然古典风格的庭院花园演奏虽优美却不相宜的乐曲。因此,第二种想法也不能成立。
第二种推论源自对(1)中“正义的步骤”的模棱两可的理解。前边表明,步骤是正义的意指它们不存在非正义。那步骤不存在非正义意指的又是什么?科恩说,它或者如前面所说,是指(a),即它们中不存在非正义;或者是指(b),即它们确保非正义不发生。如果我们接受解释(a),那我们就不能直接从“正义的步骤”的定义推断(1)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还需要表明正义的步骤总能维护正义的状况。如果我们接受解释(b),那么(1)是正确的,但却是没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1)就成了这样的命题:通过(确保非正义不发生的)正义的步骤从正义的状态中产生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正义的。而“如果我们忽略这两种解释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它们之间含糊其辞,那我们就可能错误地认为,(1)既不是没意义的(因为解释(a)),又是正确的(因为解释(b))”[12]。
第三种推论基于对(1)中“正义的状态”的无价值的定义。依据前边的定义,一种状态是正义的,即对一组持有物的持有是正义的,指的只是当且仅当没有人持有就正义而言的他不应该持有的东西,和每个人都持有就正义而言的他应该持有的东西。现在,如果有人认为也可以这样定义“正义的状态”,即只要非正义没有出现在它的产生中,这种状态就是正义的,也就是说,一种状态被视为正义的是如果并且因为产生它的过程是正义的,那依据这样的定义,(1)肯定是正确的,但它依据的却是对“正义的状态”的无价值的定义。因为(1)要令人关注,它就不能依据这样的定义而直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必须许可,一种包含不正当持有物的状态可能源自一个不包含非正义的过程。科恩说,在自由至上主义者中既存在一种通过上述无价值的定义使(1)成为正确的倾向,也存在一种把(1)视为一种令人关注的概念性真理(conceptual truth)的倾向。而要使(1)成为令人关注的概念性真理,即那种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对它的推定的反例的考察而得到检验真理,“它的反例(至少)抽象地讲必须是可能的,而且它必须有可能通过思想的实验室的检验,无论楔子能否在正义的过程和正义的结果之间打入”[13]。
在破除了(1)是不容置疑的先入之见之后,科恩转向对(1)本身的分析批判。
首先,正义加正义可能产生非正义。“正义”这一观念在(1)中被用来指称两种情形:一是状况,特别是持有物的分配(不是分配活动),它们是在某一时刻存在的事情的状况;二是步骤或交易,它们不是事情的状况,而是活动或过程,它们的发生需要时间。由于状况与步骤存在重大的不同,与此相应,它们必须满足的正义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当一种正义加上另一种正义时,发生类似化学反应的反应就完全有可能。举一个与此部分类似的例子:假设,我们可以把健康的人定义为在大多数环境中都健壮有力的,把健康的环境定义为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是健壮有力的。那么,真实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将一个健康的人置于一个健康的环境可能会破坏他的健康,因此,健康加健康也可能产生疾病。而正义加正义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
其次,“正义的步骤”不能保证结果中无非正义。科恩以递进的方式提出了四个反例。[14]
第一个反例:设想“我”正义地持有的一根擀面棍滚出了“我”家的前门,滚下了斜坡,滚进了“你”家开着的门,而“你”并不知此事。“你”简单地错把它当做“你”丢失的,并把它收起来使用。这一例子表明,非正义的状态(不同于非正义的步骤,对此前边已经表明)并不以不道德的行为(wrong doing)为前提,它可能是意外情况所致。就这一例子而言,没有发生任何非正义的步骤,一种正义的状态就转变为一种非正义的状态。不过,这个例子本身构不成对(1)的反驳,因为(1)说的是正义的步骤足以维持正义,而没有说非正义的步骤必然会破坏它。但这个例子表明,人们所采取的步骤不是可将一种分配转变为另一种分配的唯一的东西。假定在步骤的发生中没人以暴力或欺骗行事,那某种伴随发生的意外情况为什么仍有可能产生一种非正义的结果呢?就擀面棍的情况来说,在其向错误方向滚动的时候,正义的步骤也可以在发生,因为完全可以设想,当方向错误的擀面棍滚向“你”家时,我们也许正在自由地用一把小刀交换一把叉子。对此,(1)的辩护者也许会声称,在擀面棍的例子中,新的状态不是“(纯粹)通过正义的步骤”而直接产生的,进而言之,那种意外情况并不源于正义的步骤本身,它不能作为(1)的反例。但这种说法至多是一种皮洛士的胜利(Pyrrhic victory)⑤,因为交易步骤的发生离不开周围伴随发生的情况,以强调“通过”正义的步骤来保护(1)会减弱它维护市场交易的结果的力量,而这恰恰是(1)的政治功能。
第二个反例:“我”很便宜地卖给“你”一颗钻石(或“我”一时心血来潮把它给了“你”),因为我们俩都认为它是玻璃的,这样,“你”持有一颗钻石的状态就出现了,但一旦钻石的真正性质被暴露,而“你”此时还坚持保有它,那没人会认为这种状态是正义的。根据诺齐克论述,只要步骤不存在强迫或欺骗的行为,它们就是正义的,因此,我们的交易中没有非正义的行为。但这一例子表明,主体的无知也可以导致非正义的结果,换句话说,符合诺齐克要求的正义的步骤也会造成破坏正义的情况。
第三个反例:一个保险公司(不是因犯罪)破产了,因而损毁了那些无法知道它的境况将会暴露的人们的生活,人们现在不得不自愿地(在恰如其分的自由至上主义意义上讲的)廉价出售他们的财产给那些机敏但并非不诚实的买家。科恩说,前边讲的擀面棍和钻石的反例虽然对(1)构成了挑战,但实际上还没有驳倒(1),因为诺齐克只需说倘若没有(显著的)偶然情况或(显著的)错误与正义的步骤相伴,正义的步骤就能维护正义。第三个反例则表明,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离开个别的成对的交易主体而放眼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大量的不协调的交易,那因无知而破坏正义的情况就会扩大。这样说来,因为大量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不协调交易的结合,一种正义的状态可以转变为一种非正义的状态。
第四个反例:一个人无意中成了一处饮用水源的独占者,这种状况不是非正义产生的,但它需要矫正。这个反例是诺齐克本人提供的,尽管他不是把它作为反例提出,因为在这个例子出现在他那本书的地方,(1)还没有进入论题。科恩说,诺齐克面对上面的三个反例会加以搪塞,并以略加修改的做法来继续肯定(1),但他显然无法拒绝他自己提供的这个反例。面对这个反例,要么,他依据一种反映最终状态正义原则的理由而拒绝(1),要么,他顽固地强调“通过正义的步骤”而保护(1),但无论哪种情况,(1)作为反对相信最终状态正义理论的人的命题,都会失去它的迷惑力。
简言之,假设我们从一种正义的状态开始,接着发生了一种正义的交易,如果结果中存在任何非正义,那么,按照假设,这种非正义不可能是因为交易本身中的任何非正义,但由此却不能得出结果中不可能存在非正义的结论,“意外的情况,缺少相关的预知,以及预知的组合的过程,都可被合理地看做状态的非正义的制造者”[15]。
第三,“正义的状态”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科恩说,这一问题与前边确定的“正义的状态”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有关,而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是指在对正义的状态的理解上存在不同的维度。为了表明这一点,他先简述了他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第一章第4个注释中谈过的一个正义地生产奴隶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讲的:“A和B在天资和情趣上完全相同。这两个人都是如此地喜爱拥有一个奴隶,以致每个人都愿意冒成为一个奴隶的危险以换取获得一个奴隶的相同机会。于是,他们抛硬币来决定,结果B输了,A给他戴上了镣铐。”[16]科恩说,这个例子给诺齐克出了一个难题。根据前边的定义,“正义的状态”是指每个人都拥有他们应当拥有的全部持有物,而且只是这些持有物。由于诺齐克用“正义”指称一组持有物,因而,正义也就是一个实施正义的权力机构正当实施的东西。但这个奴隶的例子却表明,这种可实施性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他们这种关系的起源无疑是正义的,人们可以认为B对他的主人A没有可实施的申诉,所以,当B要求获得自由时,实施正义的权力机构不愿做出回应是正当的。但尽管如此,人们仍可抵制那种认为A可以合法要求实施他对B的控制的想法。因此,假定B砸开他的镣铐逃跑了,而A要求同一权力机构把他抓回来,那这一权力机构为什么不可采取同其不愿帮助B本人获得自由的同样的态度,说“奴隶制是一种如此贬低人的陋习,以致正义不可能要我们帮你去找到B”。在这一例子中,某人在一次也许是不明智的赌博中惨败。由于他面对的是与他完全对等的对手,所以,诺齐克说的交易的正义性无疑得到实现。但人们仍可认为其结果是不公平的,即使输家不能抱怨它是不公平的,因为输家不能抱怨这一结果是不公平的是基于一种维度,而人们认为这一结果是不公平的是基于另一种维度。科恩说,“这里所做的区分给出了对(1)要持谨慎态度的又一个理由”[17]。因为按照诺齐克的可正当实施的表达,正义的状态具有不同的维度,而这要求对正义的不同的判断,这样一来,(1)的可信性就更值得怀疑了。
三
科恩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一章第八节曾简要论述了诺齐克所说的自由和正义的关系,并讲过“他不能声称,一个其中一些人因害怕饿死而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社会是赞成自由的价值的,但我容许他可以声称,这样的社会是与正义的观念相一致的”这样的话[18]。科恩说,他的这些带有总体性表态的话无疑欠缺精确细致的说明。因为在诺齐克的观念中,自由与正义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尽管诺齐克将他的事例基于自由是站不住脚的,但允许他可以将其基于正义还是显得有些仓促。为此,科恩在第二章又对“张伯伦论证”涉及的自由和正义关系做了深入的探究,并进而揭露了诺齐克之流是如何“玩弄自由的语言把戏”的。[19]
科恩说,一个D1⑥的拥护者对“张伯伦论证”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回应,即提议对张伯伦的收入征税,而税率以及税收所得将由(1)所基于的原则来决定。那么,这个人提议的税收政策会因其无理地限制自由而不被接受吗?这样的征税政策无疑会消除某些自由:它会使张伯伦失去签订这样一种合同——他打篮球并挣得整整25万美元的自由,并使他的球迷失去签订他们每人付25美分而张伯伦获得25万美元这样一种合同的自由。然而,某些自由的消除是能有助于自由本身的,这样说来,在得出向张伯伦这样的人征税就是限制自由或限制它是无理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它使某些自由的消除是否能促进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自由。一个人有多少自由取决于他的选择的数量和性质,而选择既取决于游戏的规则又取决于游戏者的财产。就张伯伦和他的球迷而言,向张伯伦征税显然会减少他的自由,但禁止球迷签订一个张伯伦的收入将不上税的合同则显然不会减少他们的自由,因为这种禁令创造出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否则他们将不会有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付25美分去看张伯伦的比赛而不给予他们社会的一些成员以巨额财富,同时还能重新获得他们支付的通过适当制定的税收政策筹集的社会福利基金的大部分。但尽管如此,一些人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了尊重自由,这种消除某些自由的税收规则能否避免?对此,科恩的回答是,虽然D1的税收规则限制了自由,但它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的税收规则都限制自由,在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赞同的私有财产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流行的税收规则尤其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人都不能声称,同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赞同的规则相比,D1的规则限制了自由。”[20]换句话讲,诺齐克不能说对向张伯伦这样的高收入的人征税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他本人提出的制度(像所有的制度一样)就限制了自由。
科恩接着指出,诺齐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条件的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和对个人自由所有限制的坚定的反对者,然而,“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两种身份,其原因只在于,一个人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第二种人”[21]。为了表明这一点,科恩利用了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如果国家阻止我做某件我想做的事,那它就限制了我的自由”——做了这样的论证:假设“我”想采取一个行动,这一行动需要使用“你”的财产,而从法律上讲“我”使用它是被禁止的。比方说,“我”想在“你”家的后花园支一个帐篷,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地方住,“我”也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我”有一顶帐篷。如果“我”现在试图做“我”想做的这件事,国家就可能为了“你”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如果国家确实干预了,那“我”的自由就遭到了限制。以此类推,对于那些自己不拥有某一财产但想使用它的人们而言,不允许他们使用就都是对他们自由的限制,而且,总有一些人是不拥有它的,因为一个人的私人所有权是以“排斥其他人一切人”为前提的。[22]自由企业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售出和买进的是他们各自拥有的和将要拥有的东西。由此说来,诺齐克之流就不能抱怨社会主义的分配限制了自由,因为他们自己赞同的分配也同样限制自由。
科恩说,他上面的论证是基于“如果国家阻止我做某件我想做的事,那它就限制了我的自由”这一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在这一论证的过程中,他假定,阻止某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使他在这方面不自由。进而言之,“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干涉我的行动,无论我是否有权利采取这些行动,无论我的妨碍者是否有权利干涉我,就此而言,我都是不自由的”[23]。然而,对他的这一论证有一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是基于贯穿自由至上主义者很多论著中的对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它可被称做自由的权利定义),干涉不是使“我”不自由的充分条件,进一步讲,只有当某人阻止“我”做“我”有权利去做的事情时,“我”才是不自由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的一段话使用的就是自由的权利定义:“其他人的行为为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机会设置了限制。这是否使一个人的行为成为不自愿的,取决于这些其他人是否有权利这样做。”[24]
如果有人将这种自由的权利定义与对私有财产的道德认可,即与“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他们自己合法拥有的财产具有一种道德权利”这样一种主张结合起来,那人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自由。[25]从对私有财产的道德认可可以推断,“你”和警察阻止“我”在“你”的土地上搭建帐篷是正当的,而且,因为自由的权利定义,接着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你”和警察并没有因此限制“我”的自由。这样,根据诺齐克所使用的自由权利定义,私有财产不一定限制自由。进而言之,如果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保护与人们的合法权利相一致,它就没有限制自由。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科恩给出了两种回应。
第一种回应依靠对“自由的”和“自由”等术语的日常用法。根据这种用法,阻止某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使他在这方面不自由。由此说来,上述反对意见对自由特征的描述是不能成立的,而其错误就在于,要确定“限制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的行动是否使一个人(就这点而言)不自由,就必须调查导致对机会的那些限制是否是不正当地产生的,例如,当一个被确认是谋杀犯的人被正当地关进监狱,他才成为不自由的。
第二种回应则不依靠对“自由的”和“自由”等术语的日常用法。假定我们拒绝日常的用法并同诺齐克一起说对某人行为的正当干涉并没有限制他的自由,那么,如果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无法证明对私人财产的干涉是错误的是因为它限制了自由。因为人们再不能根据与权利无关的日常语言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私有财产的干涉显然确实减少了自由。根据对自由的权利的定义,在表明人们对他们的私有财产拥有道德权利之前,人们应当避开这种断言。然而,自由至上主义者既倾向使用自由的权利定义,又倾向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私有财产的干涉减少了其所有者的自由。但他们只有基于对自由的与权利无关的说明,才能认为后者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基于这一说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减少了非所有者的自由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而要避免这一结果,他们就得采用对自由概念的权利定义。所以,他们在两个不一致的自由定义之间颠来倒去,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哪一个定义他们更喜欢,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坚持一种事实上站不住脚的主张。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方面想说,对人们使用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些干涉显然限制了自由,另一方面又想说,保护私有财产不会同样限制非所有者的自由,因为所有者有权排除其他人使用他们的财产,而非所有者则因而无权使用它。然而,只有在他们以两种不一致的方式定义自由时,他们才能坚持上述两种说法。
科恩进而指出,退避到对自由的权利定义使诺齐克陷入了一种循环。根据自由的权利定义,当一个人采取他有权采取的行动而没受阻止时,他就是完全自由的。换句话说,根据这种权利的定义,只有在干涉者没有权利去进行干涉时,干涉一个人才是干涉他的自由,因此要知道一个人是否是自由的(在这里自由这一概念是完全从权利意义上讲的),我们就必须知道他的(及其他人的)权利是什么。但诺齐克对人们的权利提供了什么样的描述?他要么根本没提供任何描述,要么提供的是自由方面的描述,就像这样:人们拥有的权利是那些拥有它们将保证他们的自由的权利。因此,诺齐克使自己的命题(1)陷入一种循环。对诺齐克来说,当不存在强制时,就存在正义,这时没有任何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这意味着不存在对自由的限制时就存在正义。但此时自由本身又是根据权利没受到侵犯来定义的,这导致了一种尴尬的循环定义,并且既没表明自由概念也没表明正义概念。
科恩还对诺齐克的自由和正义概念的循环定义如何影响(1)做了进一步的说明。(1)讲的是,“通过正义的步骤从正义的状态中产生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正义的”。要应用(1),我们就必须知道是什么使得步骤是正义的。诺齐克的回答是,当步骤是自愿完成的或不存在强制时,它们就是正义的。然而,当我们接着问什么是自愿完成时,我们被告知,无论一个人的机会受到怎样的限制,只要在对其机会的限制的产生过程中不存在不正义,他的行动都是自愿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循环定义:正义是根据自愿定义的,而自愿则又是根据正义定义的。“以这样的方式谈论问题,我们将既不能把自由,也不能把正义用作评价的标准。”[26]
科恩最后指出,能使诺齐克走出这一循环的“可能的出路是自我所有原则,这一原则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和他自身能力的正当的所有者,因此,也是通过使自己为他人服务而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的正当的所有者”[27]。因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张伯伦拥有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他通过运用这些能力而挣得的收入是不应上税的。但自我所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可张伯伦的例子对其却没提供任何论证。
注释:
①科恩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以往发表的论文的汇集,因为除了导言、第二、第八、第九和第十章是在此书出版前新写的以外,其余七章则源自他1977—1992年期间发表的7篇论文,尽管在此书出版时又对它们做了某些修改和补充。
②Erkenntnis是一种发表分析哲学论文的刊物。
③科恩没给出写作这一章的具体时间,但从《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的“致谢”部分可以推断,它写于1992—1995年之间。
④参见葛四友的论文《柯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应奇主编:《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78页。
⑤前279年,古希腊伊庇鲁斯国(Epirus)的皮洛士王(King Pyrrhus)在大胜罗马军队后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就输了。”为什么打了胜仗还会输呢?原来皮洛士虽然战胜了罗马军队,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和指挥官在那次战斗中阵亡。以后人们便用“Pyrrhic victory”来表示因代价沉重而得不偿失的胜利。
⑥D1的含义见前面引用过的诺齐克关于“张伯伦论证”的论述。
标签:诺齐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