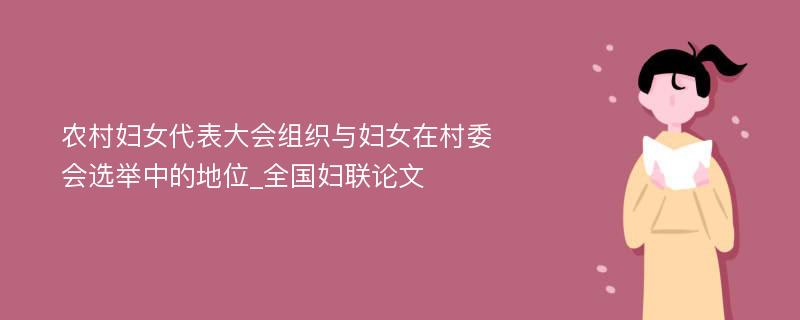
农村村级妇代会组织与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代会论文,村委会论文,村级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6-0112-06
目前农村居主导地位的村级妇女组织是村妇女代表会(下文简称妇代会)。村妇代会是政府供给主导性组织,能够获得国家政策、政府权力结构的支持和关注。由于妇女自身组织的资源匮乏,目前没有其他妇女组织具备了与妇联竞争的力量,在村委会选举中,妇代会在组织妇女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方面最具宣传和组织优势。地方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落实对妇女保护的政策时,多将保护的对象具体锁定为村妇代会主任。同时,妇代会主任在社区工作抛头露面,是乡村“半熟人”社会中的“熟人”,有一定的知名度,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源,是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政治精英。从普遍意义上说,妇代会主任参与村委会竞选,在妇女群体中最具有竞争力。
在当今农村农业女性化的趋势下,妇女在选民中占有一半以上人数,并且是农村常住人口中的多数,在数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与男性村民相比,农村妇女有自己的性别组织,并且置身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中,在组织资源上应该也有一定的优势。但笔者通过对中部两省8县市16个村委会的实地观察和调查,以及19省市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农村妇女以及农村妇代会在乡村公共权利结构中的状况基本上可用“无权无势”来概括。在村委会选举的活动中,妇女地位低落,妇女群体政治参与无力;妇女精英在村治中被边缘化,低层化。全国农村有一定数量的村委会中妇女完全被排斥在外,并且有继续加大的趋势;在有妇女一席之地的村委会中,绝大多数女性成员是“叨陪末座”。
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低落,与一些村妇代会组织虚置或组织作用弱化有直接关联。妇女的组织优势在农村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妇代会自身组织乏力使妇女在选举中难以形成合力,以表达妇女的意愿。
一、村妇代会既无权力也无自主的活动空间
(一)在正式体制中的依附地位
妇联是代表妇女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虽然是社会政治体系的组织要素,但它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而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因此,利益集团以参与和影响决策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方式,而不以执掌政治权力为目的,并且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不过,中国的妇联组织具有双栖的特性,她既是妇女群众组织,同时又被纳入到体制构架之内,属于党群体系中的组织。这种双栖的特性既有利于妇联组织运用同党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开展工作,但如果在总体利益和具体利益关系上处理不好,也有可能使妇联失去可能的活动空间[1](p4-8)。这种体制上的双重属性对农村村妇代会的工作影响甚大,如果协调失当,就会使村妇联陷入既无权又无相对自主活动空间的双重困境之中。农村村妇代会组织的领袖——妇代会主任与村委会中的妇女委员从制度体系上说不是一回事,但在实际运作中,选进村委会的女性委员大多数就是原来的妇代会主任;即便新上任的妇女主任不是妇代会主任,通常也被村双委进行干部调整时任命为妇代会主任以取代原来的主任,村委会的妇女主任开展工作所依靠的组织仍然是妇代会,村委会的妇女主任与妇代会主任虽职务名称不一样,但往往是两块牌子一个人。没有女性成员的村委会,对于落选的妇代会主任,通行的做法是由村双委聘任为非村委会成员的村干部——仍是妇代会主任。因此,普通村民将妇代会主任和村委会的妇女主任通称为“妇联”,在她们看来这两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总而言之,妇代会主任无论进不进村委都被纳入到乡村权利结构之中,
在现行的体制下,农村双委控制了妇代会的经济资源(活动经费)和政治资源(职务任命)。妇代会的活动经费依靠村委会提供,妇代会主任本应由妇女群众选举代表再由妇女代表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妇代会主任基本上是直接由双委任命,选举通常是走过场,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组织拥有的资源越多,“说话的权利”越大,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强,反之亦然。妇代会及其主任在资源配置上居于被动给予的位置,自主工作的空间有限,实际上是处于依附地位。因而,她在村委会中是看“别人的脸色说话”,妇女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双委对妇女的重视程度,以及双委与妇代会主任的关系。而目前农村双委对妇女及妇女工作不重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访谈的多位村妇代会主任大多都谈到自己在村委会中属于最低层的干部,不仅报酬最低,参与决策的份量也轻,人微言轻的感觉很强烈。而选民在谈为什么不选妇女时,很直接地说“村里的妇联也根本起不到啥作用,她本身就在人家大队干部控制之中,支书训起人来挺厉害,她们都不敢吭声”。“妇联主任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哪能代表妇女群众和村民说话,选了也没用。”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村委会选举中,妇代会主任能不能当选,与妇代会主任在村委会中被授权多少成正相关联。妇代会主任如果与双委关系协调不好,权利被双委架空,就很难有所作为,她的当选可能性便很小。选民趋向于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在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下,不会把票投给一个不起作用的候选人。
农村村妇女干部特别是相对年轻的妇女干部经常受到流言蜚语的困扰,主要涉及妇女干部与双委主要领导的关系。这固然是农村落后的文化在起作用,但同时也是妇女干部依附地位的曲折反映。这些流言不仅伤害在岗的妇女干部,实际上也伤害了那些有实力参与村委会选举竞争的女性精英的积极性,有些受访的妇女能力和素质都不错,但她们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懒得听那些闲话。
(二)在乡村权利结构中不痛不痒的角色
妇代会在乡村权利结构中通常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角色。因而,在村委会选举中,也是一个不受重视的角色。如果政策保护工作到位,强调必须有一名妇女进村委会,那么,妇女委员是竞争性最小,也可能是票数最多的一个职务。实际上,这种现象通常与对妇女干部认可度无太大关系,一是保护政策起作用,二是大家对这个职务并不重视,无关紧要,可以慷慨出让。在目前村委会职数减少的情况下,如果选举的组织者对保护政策强调不够或不作强调,那么,最先被排挤出村治机构的可能就是妇女委员。因为她既无权利,掌握的公共资源也有限,工作效能受限。村民在进行利益排序中,妇女委员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
农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在一些地方,乡镇以及村委会的工作重心是收取税费,与此相应,经济以及与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利是村民关注的重点。妇联干部在公共权利分配中,所管的工作大多仍属于“村内”“家内”的事,如计生、调解等工作,与村民最关心的“大事”无多大关系。那些未选妇女的村民,谈到不选妇女的原因时,大家都共同提到是妇女委员“在村委不起作用”。那些投了妇代会主任票的村民,大多数人说选妇联的原因也只是表示“村里的计生工作总是要人做的”。曹村受访的两位选民说得很坦率:“妇联这个工作也就是那样,不疼不痒的。所以我没选。”“我从来都没考虑选妇女,因为大家都是瞄准派系间竞争,想选的人都是与经济财务和权利方面有关系的,妇联这个岗位涉及的只是育龄妇女,与权力、经济不沾边,不属于大家关注的焦点。”有妇女受访者甚至说,选个妇女“还只是干个妇联工作,白占个村委的位置”,妇联的无权无势、在村委会中无关痛痒的角色,群众对她的期望值不高,同时也大大削减了妇女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的积极性,一位在选举中获得不少票但本人在竞选中表现消极的妇女说“进村委也是干个妇联,不管实事,那又何必去干。”
(三)工作角色错位,计生工作成为妇代会主任的主业
农村村级妇代会的主要角色是农村妇女特殊利益的代表。妇代会并不是计划生育工作部门,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使命是“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2](p10-13)。但妇代会因被纳入乡村权利结构之中,其工作受双委及乡镇指派,村妇代会主任普遍兼任计生专干,名曰兼任,实则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主业,妇代会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色已完全混淆。我们在农村调查中,曾访谈过十多位村妇代会主任,当询问妇代会主任的日常工作时,她们除了与其他村干一样包队外,主要是对付频繁的计划生育检查,诸如计划生育工作检查、育龄妇女定期检查、怀孕妇女例行检查等,还有每年的计划生育报表等。在访谈中几乎没有妇代会主任在表述中将如何反映农村妇女的要求、如何代表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作为她们的日常工作,妇女工作处在被忽视甚至完全被遗忘的位置,农村村级妇女组织的目标实际上已发生了转移。在与一般农村妇女群众的交谈中,群众对妇联工作的认识也都将之与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说起妇联的工作也都是计划生育的工作,很少有人主动谈到妇联组织是“我们”(妇女群体)利益的代表。
农村村级妇联组织角色的错位,对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原来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任务艰巨、难度非常大,被看作是农村工作的头等难事的时候,妇代会主任因为兼任计生专干而成为不可缺少的角色,受到乡镇政府以及村双委的重视,故在选举村委会时,妇联的代表受到“组织意图”的重视。1999年以后,一方面是村委会直选,民主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农村计划生育进入制度轨道,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工作难度减轻,形势好转。与此相应的是兼任计生专干的妇联干部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妇代会主任进不进村委不再那么重要,因而,地方政府以及双委在落实保护政策时缺乏功利驱动,有可能只做表面文章而缺乏力度。如果说,以前妇联干部进村委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体制内组织的保护的话,那么,现在妇联干部能否进入村委会,在较大程度上与其群众基础有关。
与组织保护力度的减弱相应,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妇代会干部由于将计生专干作为主业,其群众基础也被削弱。首先,因为计生工作所联系的主要是育龄妇女,使妇代会主任与非育龄妇女以及男性村民的关系相对疏远,故而在选举中,妇联干部往往不被这部分群众认同。在我们的随机访谈中,一位男性村民说:“一般人都不会想到去选妇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妇联不属于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现在不管去问任何人,他们都说不出为什么不选妇女,大家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没有选妇女还有一个原因是,妇联主要是关系到那些育龄妇女,不关我的事,我也不关心这方面的人。”另一位村民则表示“选妇女除了干计生,其他方面起不到啥作用,所以我也没选。”一位老年妇女说,“我家没有年轻人,与妇联也没啥交道。”并明确表示对村里的妇代会主任没啥好印象,不会选她。
其次,计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妇联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调查中,无论是妇联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很多人都谈到妇联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其实真正得罪人的工作是计生工作,群众对计生工作出现问题产生意见,矛头常常直接指向妇联干部。目前农村妇女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对妇联主任意见最大的是计划生育检查收费的问题。农村育龄妇女每年要进行2-4次强制性例行检查,每次检查收费5-10元。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不少妇女谈到,组织进行计生体检的部门只收费,至于妇女群众是否真正参加了检查,则不太关心,有的育龄妇女在外打工,虽没有参加检查,也得照常交费,有的妇女只交费,并不去检查,也没有人催她一定要去检查。因此,计生检查在某种意义是已演变为生财之道,而负责组织妇女去参加体检的村妇联主任便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众人的批评和指责。此外,在有些乡镇,村妇联主任按规定计生罚款可以拿一定比例的回扣,这在群众中影响不好,被指责为“爱占便宜”,甚至更严重的话。妇代会主任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和认同感被削弱,她们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组织作用以及个人当选率都受到明显影响。
二、组织资源利用有限,无势可依
妇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所谓弱“势”,一层含义是她们在资源、机会和利益竞争与分配中的不利态势;另一层含义是她们组织化程度低,形不成势力集团,与主流群体或获益群体无法平等对话。妇女被弱势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所以,妇女弱势地位的改变,一般都采取通过对妇女适度动员也即“运动”的形式,来提升妇女组织化程度,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使原来分散的个人获得一致的行为能力,整合成“压力集团”,以争取在资源、机会和利益的分配中取得平等的资格。
在市场制度之下,分散的个人为满足社会性需求而进行的交易是以互惠为原则,互惠的原则要求交易的个人有交易的资本,资源并不占优势的农村妇女进入市场交易困难重重。作为这种对等互利交易的替代选择——组织,通过将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运用集体的力量对付共同的困难,以降低交易成本,满足组织成员社会性需求。在政治领域,组织是一种中介力量,在国家与分散的个人之间进行沟通,个人意愿通过组织得到正常的表达,换言之,交易双方的筹码是势力与权力。妇联作为农村妇女的利益集团组织,是农村妇女可以依靠的组织“势力”。
农村村委会选举中,实际上也是以组织势力争取权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目前已知的选举制度中,多数投票法则并不是最佳的。这种多数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极不平均,只有利于积极性最高和组织得最好的少数人。我们在调查以及实地观察中看到,在村委会选举中,与农村男性政治精英在竞选中积极活动、拉帮结派相比,一部分村妇联组织由于处于虚置状态,未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缺乏凝聚力,积极组织妇女参与竞选的意识不强,妇女实际上仍处于分散状态,力量被宗族、派系或其他群体所分散。妇女群体参与无力,没有显示群体的力量,同时也未能形成竞选组织,给予参选妇女精英有力的支持。一些参加竞选的妇女精英在竞选中显得孤单无依,因缺乏组织资源的支持而处于不利地位。可以说,那些在选举中妇女被排挤出村治权利结构的村,妇联在组织选举中既不是积极性最高的,也不是组织得最好的竞选力量。妇联在村委会竞选中组织乏力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有组织无活动,形同虚设
村妇联组织的虚置,首先表现在妇女组织不组织妇女开展活动。我们在H县调查时,曾访谈了7位村妇代会主任,只有一位村妇代会主任表示她们曾在“三八”节开过会。在3个调查村,受访的农村妇女群众一般都表示,近几年村妇联从来没有组织过妇女活动。特别是几位中年妇女主动谈起人民公社体制时妇女经常性的集体活动,流露出对过去岁月的向往之情,而对目前妇联有组织无活动的状态十分不满。目前农村家庭经营的经济形式给农村妇联组织开展活动增加了困难,但妇女参与妇女组织活动的意愿仍然相当强烈,她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村治不关心,参与冷漠,但大多数农村妇女对妇女自己组织的活动,则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越是弱势群体,越是对组织有依赖,女性更具有的合群性,与其所处的弱势和边缘地位不无关系。农村妇女潜意识中仍希望通过组织来消解分散性经营所带来的孤独和力不从心的感觉。当我们问到“妇联组织开会你是否愿意去”的问题,受访者都肯定表示愿意参与,有位妇女说:“么样不去,我就是爱开会,可是没得这样的会开。”她的表态得到周围几位妇女的赞同。
妇联组织的“虚置”,也表现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组织妇女投票上。通过选举进行政治民主权利配置的制度在实践操作中,由于缺乏合理的经济激励机制,很容易导致政治冷漠,即很多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其结果就是少数人乘机为非作歹[3](p229)。因此,组织进行适度的动员,使政治资源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是必要的。特别是作为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农村妇女,更需要组织的力量来增加自己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份量。但是,有些地方的村妇代会在组织动员妇女竞选和投票上是不力的。首先是妇联干部个人参与竞选的态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活动与不活动之间犹犹豫豫,对当选与否顾虑很多。其次是缺乏从妇女群体利益角度来看待村委会选举,妇代会作为乡村政治领域里的利益集团,为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应以积极的活动方式来参与和影响决策,妇女组织有责任和义务将妇女代言人推选进村委会。目前村委会“海选”方式的推广,民众意愿越来越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原来有组织保护的妇代会主任的当选,受到她所“代表”的妇女群众的挑战,妇代会主任一方面是自己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动员自己的竞争对手参与竞争,同时还要组织和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投票,支持妇女精英的当选。这对妇代会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妇代会主任所组织的活动就不仅是妇代会主任个人参与竞争的问题,而是妇女组织利益表达的重要活动方式,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当多的妇代会主任并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准备。在目前农村妇女仍受歧视的情况下,妇女精英如果没有组织的“势力”作依托,在没有其他社会资源作为补充的情况下,她们在乡村公共权力的分配中,就可能被忽视、被排斥。对于普通妇女群众而言,组织虚置,分散的个人像一盘散沙,个人孤独无力,只有转而依附于其他各种乡村势力。
由于妇女组织在选举中处于涣散状态,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对投票的效能无法确定,也有可能使妇女精英的得票流失。一位接受访谈的妇女说:“我和我爱人都没选妇女,因为妇女中顶事的人不多,也没啥势力,妇女也不会去为自己拉选票,即使自己想选那个妇女,但别人不一定会选,所以我们投了妇女一票那也是白的,浪费了自己的选票,还不如选个有机会能上去的人。”另一位妇女群众说:“我没有选妇女,因为我觉得别人都不投妇女的票,我自己投一票有什么用?况且会上也没说要选个妇女。”妇女群众在原子化的状态下,由于信息获得的有限,利益要求相对模糊,妇联组织不出面进行组织和动员,信息不能沟通,意愿不能相对达成一致,每一个妇女群众都有可能出于有效性的考虑,而选择不选妇女——因为顾虑她可能上不去。
组织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利益表达的一系列活动来达到的。没有活动,其利益便无法表达。组织长期不开展活动,实际上意味着组织形同虚设,而组织在影响决策的重大活动(诸如选举)中,无声无息,不能通过活动将同类的个人组织起来,组织的作用便令人置疑了。
(二)未能代表妇女的特殊利益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妇女群众对妇联主任认同不高的现象相当普遍。反映在村委会选举中,投妇代会主任票的妇女群众,对妇代会主任的工作表示肯定的不是很多。投票的原因,有的说是上面强调的,有的说是对其她的妇女不了解,选择的余地不大,甚至有人说,投她的票是“让她来丢人”。至于那些不投妇代会主任票的妇女群众,则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妇代会主任的看法。
妇女群众对一些妇代会干部的不信任、不认同,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体制原因带来角色冲突。从逻辑上说,农村基层妇联既代表妇女的特殊利益,又从事党和政府的妇女群众工作,这两者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具体到乡镇、村委的工作,有两种因素妨碍这种一致性的实现:一是性别歧视文化在农村仍然相当严重;二是乡村公共权利也有受“经济人”利益驱动的一面。因而乡村权利结构在进行资源分配时,有可能忽视甚至侵害妇女群众的利益。当妇联干部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与作为村公共权利体系的“公家人”的角色发生冲突时,处于依附地位的妇代会主任选择后者比较容易也对自己有利,故很难坚持“娘家人”的立场,而更倾向于扮演“公家人”的角色。我们在杨村调查时,一位农村妇女在访谈中说:2001年,村委会和乡镇来人到她家收钱,她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顶门户,因为无钱请求延缓,遭到暴力殴打。我们问她为什么不找村妇代会主任帮她说理,她和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回答,“她和他们是一伙的,她能帮你着说话?”(这位妇女后来找到县妇联,在县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她向法院起诉,获得胜诉,乡镇及村委会向她赔理,并赔偿医药费。)在她们眼里,妇代会主任更大程度上是乡村公共权利的代表,妇女群众的利益一旦与体制组织发生冲突,她会选择服从于体制的要求,而放弃她所维护的妇女群众权利的职责。在我们所作的近千份调查问卷中,当问及“如果您觉得村委会干部不公正,您用什么方式表达您的看法”时,只有5.2%的人选择“向妇女主任说”,选择“向村民代表诉说”的反倒有18.7%,可见村民代表较之于妇女主任更能代表妇女群众的利益,反映妇女的呼声。
其二,“公共人”与“经济人”的冲突。尽管国家对农村双委成员的道德要求是做“公共人”,代表公众的利益,村委会实行直选,也是强调治理精英的公众代表性。在实际运作中,村委会所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言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但“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出现及国家权力不断上缩,在很多地方,相对于前两种身份而言,村干部更倾向于成为家庭代言人,为自己谋私利。”[4](p76)村干部一旦成为为自己谋私利的利益群体,作为这个利益群体中的一员,妇女干部考虑私利胜于考虑妇女群体的利益,就会与基层群众的距离拉大。我们在桃村调查时,当地刚遭受大旱灾,政府组织了救灾粮款,但救灾款到群众手中的不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村干部手中都刚添置了手机,群众意见很大。以至于我们在组织座谈时,群众拒绝与妇女干部坐在一起谈话,表示:你要与她谈,我们就不参加。
其三,利益集团关注的是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这是利益集团生存的基础。妇联如果不以实现妇女的特殊利益作为活动的出发点,就会失去组织成员的支持而名存实亡。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选举对选民和竞选者既是一项交易的了结,又是新的交易的开始,竞选者平时为选民的服务,通过选票获得选民的支持,选民对竞选者付出支持和认可,期望选出的领袖能为自己谋取利益。村民能不能将选票投给妇联干部,也要看妇联干部是不是真为维护妇女利益做过实事。中村的一位女选民说:“我没选妇女,我觉得妇联根本就没为我们妇女做过啥事,从来也没代表我们妇女群众说过话,‘三八’节从来也没搞过活动。而且总趁机揩老百姓的油,我怎么会选她?”不能排除说话者可能有个人情绪化的因素,但在一些地方,妇女对妇联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反映相当强烈。我们在桃村、杨村与一般妇女群众座谈,谈到妇女的特殊困难,反映最强烈的一是心理上的被排斥感,感到妇女不受重视,甚至不受基本的尊重,“村干部没哪个把妇女当事”,“根本不耐烦听你说话”;二是生理上的疾苦,目前农村农业女性化,在很多男性外出打工的家庭,妇女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农活,其劳动强度远比以前大,过度操劳落下的妇科疾病给农村妇女带来很大的痛苦。当我们建议向妇代会主任反映这个情况,能不能通过妇联来呼吁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村妇联并不能帮她们什么。桃村、杨村妇女的这种看法,在广泛的调查问卷中也得到了应证。当问及“妇女组织在村民自治中能否起作用”时,有57.3%的人选择了“能,但实际作用不大”,有21.5%的人选择了“不能”。
组织成员参加组织活动,接受组织约束,基本的动力在于从参加组织的过程中得到好处,这种预期能得到满足,组织成员才具有广泛的积极性。农村基层妇联组织如果不能真正代表妇女的特殊利益,不能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不能替妇女说话办事,而成为乡村权利的附属,妇女群众参加组织的积极性就会趋于消沉。妇联干部脱离基层妇女群众,也就无“势”可依,成为乡村权利结构中可有可无的边缘分子,在选举中便有可能被来自上面的力量和来自下层的力量共同抛弃。
收稿日期:2002-08-28
标签:全国妇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