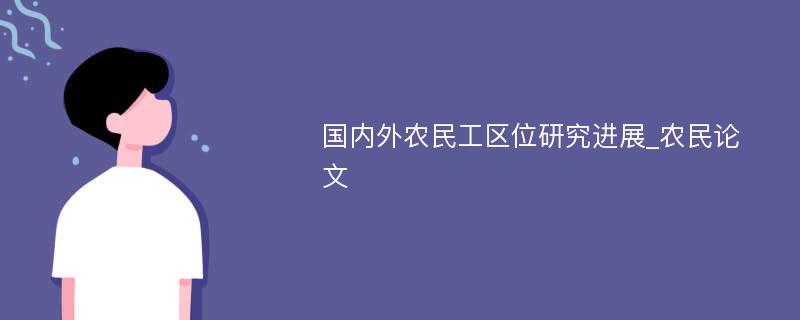
国内外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区位论文,农民工论文,务工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3-13 中图分类号:F3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4)05-0608-0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1]。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而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对于人力资本比较匮乏的农民而言,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增收方式就是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26.1%,而且呈现出增加趋势[2]。农民工外出务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335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3.31%[3]。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4]。近年来,国际上人本主义主导的人文地理学得到加强,行为地理学中行为区位研究受到重视[5]。中国地理学界应顺应国际潮流,加强对农民工务工行为的地理学研究。中国地理学者已开展对农民工务工区位规律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但是,务工区位分布及选择机制等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将从国内和国外2个方面,对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国内研究动态 对中国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情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成果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领域。 1.1 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分析 农民工务工地可分为本地和异地2类,转移方向一般为农村到城市,中西部到东部,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因素。按照空间范围,农民工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其合理性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就地转移是理性选择,通过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异地移民代表了发展方向。大规模候鸟式的农民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6]。事实上,这2种形式均普遍存在,都具有合理性。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7],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比例为62.3%,本乡镇以内的比例为37.7%。有学者将空间类型与农民工就业产业类型相结合,提出了本地农业就业、本地非农就业、外地农业就业、外地非农就业等4种类型的农民工空间行为类型[8]。在转移方向上,劳动力迁移趋于流往最近的城市,趋于大城市,大城市的劳动力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极少迁入小城市。在全国层面转移的地域上,以省内和东部地区为主,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点。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就业地区上,东部地区占农民工总量的66.9%,中部占16.9%,西部占15.9%[3]。采用统计分析和GIS分析的研究表明,1990-2000年流动人口三大地区分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变化高度一致,中国劳动力迁徙具有明显的经济因素驱动效应[9],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10]。 1.2 农民工务工地选择机制分析 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主要是通过关系网络自发外出、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等途径实现的,主要以迁移网络和自发外出为主,打工簇是其主要机制。网络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农户打工区位的选择具有明显的打工簇现象,在自然村尺度上,少数的打工簇集中了多数的打工者,主要基于传统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关系网络在打工簇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种子打工者和潜在打工者在由关系强度决定的博弈中造成了打工簇的形成和扩散[11]。采用SIS模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动态转移的分析表明,其服从传染病模型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能在某一地区成为一种风气,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12]。迁移网络是农民工迁移的最主要的形式,蔡昉等[13]的研究表明,有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有75.4%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从行为地理学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行为包括就业感知、就业决策、就业行为、就业体验4个行为过程,他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8],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本地就业和外地就业的选择。 1.3 农民工务工动因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动因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既有基于务工本人角度及家庭角度的微观研究,又有从产业发展、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谋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促进、寻求发展机会,此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14]。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务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理性的农民将按照个体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自己进城务工或在村务农[15]。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是农民流动的“拉力”[16]。国内更多的研究是引用国外比较成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这些理论如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模型、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双重劳动市场论、新家庭经济学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迁移推拉力理论等,或者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或具体区域的案例研究。 1.4 农民工务工距离与城镇等级分布研究 距离对外出决策和外出务工目的地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代交通运输发达条件下其影响具有复杂性,个人因素对务工距离有重要影响,不同地区由于就业机会不同,务工者对距离有不同的选择。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打工距离整体分散、局部集中,务工人数随距离的变化呈“U”型分布,务工者在务工目的地的分布上具有群聚特征[17]。务工者的期望务工距离和实际务工距离分布相似,同时具有一定惯性,但整体而言仍以本地为主[18],此结论暗示着农民工更希望在本地务工。省份之间的空间距离对省际人口迁移发生概率起着“障碍”作用[19]。距离越远,人口迁移的概率越小,风险厌恶者,往往选择短距离迁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20]。距离因子对迁移者数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迁移者往往集中于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某些城市[17]。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转移加快[21],而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以省际迁移为主,但东部地区主要是近距离迁移,以省内迁移为主[22],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表现出特有的就地城镇化过程[23]。 在务工地城镇等级方面,处于对就业机会和收入的考虑,农民工对务工城市的选择服从“就高原则”。外出农民工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在直辖市务工的占8.8%,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19.4%,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4.8%,在县级市务工占19%,在建制镇务工的占13.8%,在其他地区务工占4.2%[3]。农户对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的选择与打工距离密切相关,家庭代数、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选择的重要因素[24]。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多以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为主。 2 国外研究动态 在国外,和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大致对应的概念是“非永久迁移”(non-permanent migration)、“暂时迁移”(temporary migration),或“循环流动”(circulation)。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从流动空间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从宏观层面对乡城劳动力迁移和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进行了解释。Lewis[25]认为,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隐蔽性失业,在现代城市部门工资高于农业传统部门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现代城市部门。Fei等[26]根据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将劳动力转移划分为3个阶段:等于零阶段;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此外,世界体系理论从全球经济化角度解释人口迁移的动因[27],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劳动力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预期收入理论、双重劳动市场论、新家庭经济学等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Todaro[28]认为,如果城市预期收入现值高于农村且有较高的找到工作的概率,农民就会作出外出流动的决策。双重劳动市场论认为,当地工人主要进入资本密集、高效率的主要部门劳动市场,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主要进入劳动密集、低效率的次要部门劳动市场,形成国际移民[29]。国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新家庭经济学把家庭作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微观主体,迁移决策是由家庭做出的,迁移不仅取决于预期收入之差,而且还取决于相对经济地位[30]。 2.2 移民区位选择研究 2.2.1 移民区位选择过程与选择模型 移民对移民区位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对目的地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在较大的范围内选择重点目的地,然后在重点目的地中选择一个目标目的地。Gustavus等[31]认为迁移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以前居住的地方比较,以确定一套替代目的地。第二阶段是选择一个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考虑作为门槛条件的地方属性。Roseman[32]认为移民目的地选择是以下2个过程的结果:第一,对一生中相关的较大数量的潜在目的地进行分类,第二,在相对较少(通常是一、两个)地方中进行选择,实际的目的地选择是基于地方效用作出的。 已有的空间选择模型可分为2类:离散模型和竞争目的地模型[33]。空间选择模型最初来源于旅行需求研究,后来被应用到移民领域。移民迁移目的地的空间选择实际上是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来自于个人态度和目的地特征的综合。离散模型主要包括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nested logit模型。离散模型主要是基于经济因素的效用比较[34]。竞争目的地模型主要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对备选目的地的心理判断[33],其中信息获取和处理是其核心。 2.2.2 移民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移民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既包括收入、福祉水平等经济因素,同时与语言、宗教、社会网络、教育、基础设施、环境、距离等非经济因素有关。移民选择加拿大Montréal等3个门户城市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福祉水平、历史最悠久和较高的知名度[35]。在解释移民集中居住在一些特定城市中,“组织亲和力的假设”具有较大影响[36],同时,移民的区位选择存在路径依赖,受早期同一民族的重要影响。Massey等[37]使用社会网络理论也做过类似的研究,认为迁移是依赖于社会网络的,而社会网络往往与种族或民族群体相联系。Bauer等[38]认为网络外部性和从众行为对移民区位决策具有显著作用。教育程度高的移民很少和来自同一国家的教育水平低的移民居住在同一地区[36]。人口密度和社会接近在迁移目的地选择上有很强的显著效果。特定地点的各种生活经历对潜在移民确定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移民改变其居住地的动机随着迁移距离有所变化[39]。距离影响移民的效用水平,因为迁移成本和再迁移到一个新国家的信息收集成本直接相关。所以,区位决定和距离是负相关的。 2.3 移民空间结构研究 与移民区位相关的另一些研究是有关移民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测度的研究。一般认为,移民具有空间集中性,或集中在特定城市或城市的特定地区。多数美国关于新近移民区位选择的研究发现,新近移民被吸引到大城市,这些城市早期就有较多移民定居[40]。希腊除了最典型的外来族群代表阿尔巴尼亚裔移民外,其他民族的移民都集中在不同的地区[41]。一些学者对移民中不同组分的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如Atramentova等[42]对Belgorod的婚姻迁移进行研究,证实移民的平均迁移距离在1960年、1985年、1995年3个年份增加,已婚的男性和女性迁移距离也相应增加。在移民分布与影响因素的空间匹配方面,有学者认为,墨西哥年轻人的国际迁移对教育水平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区域内部存在着强烈的空间异质性[43]。在测度移民空间结构方面,David[44]提出用基尼系数来测度移民的空间集中性非常有效,和地理学中的方差和熵等指标相比,具有较大的优越性。Rogers等[45]借鉴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对数线性模型,提出了一个人口从源地到目的地的移民流区域系统空间结构的定义,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3 结论与展望 农民工流动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开展对农民工问题的地理学研究,尤其是开展农民工迁移区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国内外有关农民工务工区位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相应的理论构建较为薄弱,间接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来自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主要是指从农民工微观个体出发,研究务工区位的选择规律。目前,国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务工地选择机制、务工距离分布规律、务工地城镇类型选择、务工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等领域。在务工地选择机制方面,务工簇、传染模型、务工空间行为决策4个过程、社会资本理论给予了较好的解释。在务工距离方面,“U”型分布效应、空间近邻效应、工作机会吸引效应、收入最大化效应给予了较好解释。在务工地城镇类型选择方面,就高原则、收入最大化效应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在务工地选择影响因素方面,涉及农村社区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距离因素、目的地因素等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涉及性别、年龄、学历等,家庭因素涉及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类型、家庭代数等。 第二,国外的间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区位、移民空间结构等永久性迁移移民领域,而对非永久性迁移的区位选择研究十分薄弱。由于目前主流西方国家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类似中国的大规模农民工现象,因此,对非永久性移民的工作地区位研究成果较少,已有成果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研究同样主要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主要研究非永久性流动的形成机制、区域影响及一些具体的区域案例,较少有从地理学和区位角度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人口永久性迁移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相应研究成果较多。由于永久性迁移和非永久迁移在迁移时间、迁移目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用于永久性迁移的理论在运用到临时迁移时存在一定限制。国外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医学领域,其中不少成果为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合作成果,较少有从地理学角度的研究。 中国农民工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农民工问题在当今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一直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未来中国的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地理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农民工区位问题的研究。总的来看,目前对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的学者还较少。地理学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加强解释力较强的微观研究和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研究,在农民工方面也应如此,农民工的流动只有在微观方面给予科学的解释,才能在宏观方面科学地理解这种过程和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农民工务工区位分布、区位选择机制、多阶空间流动规律等。其次,应加强不同区域的案例研究,以丰富务工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中部地区,如河南、安徽等省,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研究成果较少,只有从多方位的案例研究中才能全方位地把握务工区位的规律。再次,目前虽然有了一定数量的案例研究,但在理论方面仍然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在不同的案例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总结出农民工务工区位的一般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应进一步加强模型分析和量化分析,以更精细地揭示农民工务工区位特点和规律。当然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民工的统计工作,因为目前已有的统计数据很少且不系统,仅仅依靠作者的调查,只能获得局部和案例性的数据。标签:农民论文; 地理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移民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