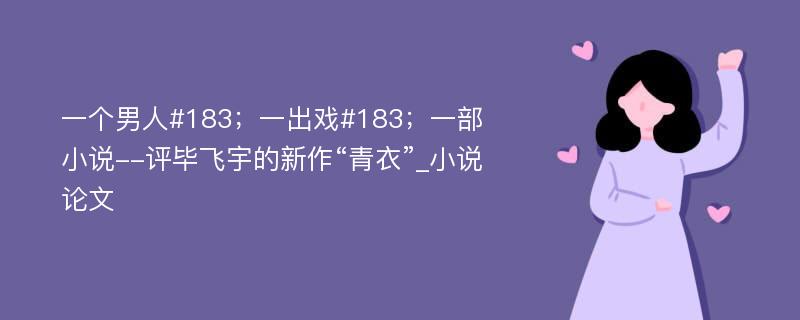
一个人#183;一出戏#183;一部小说——评毕飞宇的中篇新作《青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衣论文,新作论文,一出戏论文,小说论文,毕飞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大多数青年作家急切地成名、急切地说话、急切地向前“赶”的姿态不同,毕飞宇给我的总是一个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形象。他好像特别沉得住气,说话慢吞吞,走路慢吞吞,写小说也是慢吞吞。他的小说产量极低,给人的感觉是不到万不得已就写不出来。他总是在“磨”,总是把每一个小说都“焐”在怀里,舍不得出手,真搞不清他这是自恋呢?还是信心不足亦或有其他毛病?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毕飞宇确实是一个有自己艺术理想的作家,他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明确的“追求”。他不希望自己重复自己,不希望写“没意思”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弄出点动静,留下一点不同凡响的“声音”。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多少有点狂妄和不切实际,因为我们知道恐怕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获成功,更无法保证后一部作品就一定能超越前一部作品。但是对毕飞宇来说,这样的追求却是真诚的,他确实在一直“向上”,一直在追求着自我超越。在不长的创作历史中,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他的小说已经经历了历史的阶段、哲学的阶段、世俗的阶段和审美的阶段等数次艺术转型。我们很难说,他的每一次“转型”都是艺术上的突破,或者都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每一次“转型”都确实体现了对一种新的艺术品位的“追求”。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只有王安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能长期保持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始终如一的艺术“上升”轨迹。而也许是由于数量少的缘故罢,我们发现,毕飞宇似乎也正可以归入这“少数人”的行列,这大概就是他小说写作上的“磨功”与慢性子的正面意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篇小说《青衣》无疑又是一个不错的证明。
《青衣》是毕飞宇于2000年精心打磨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毕飞宇丝毫也不掩饰对它的喜爱与看重,在创作谈里,他不无自得地谈到了这部小说与过去作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我并没有刻意做什么。活到哪儿,你就必然写到哪儿。前提是你不能回避你自己。一个人的作品肯定得像一个什么东西,弄来弄去只能是像自己。”(注:毕飞宇:《〈青衣〉问答》,《小说月报》2000年7期。)在这里,毕飞宇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青衣》是一部具有超越性的作品,但这种超越性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一层意思说《青衣》是一部超越性的作品,但这种超越性以毕飞宇自我风格的张扬为前提。而一旦我们走进《青衣》所营构的那种令人心痛而又伤感的艺术世界,我们也确实不得不认同作家的自信,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部能代表毕飞宇创作新“标高”的小说。
《青衣》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主人公筱燕秋。毕飞宇是一个特别善于把握和发掘人性与人心中最柔弱、最敏感的那部分内容的作家。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心绪与人性的细节经由他的细腻而传神的描写往往会化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泛悲剧的”伤感艺术氛围叩击你的心怀、触碰你的神经,让你心有千千结。《青衣》对筱燕秋的刻划可以说就充分展示了毕飞宇在这方面的才能。在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筱燕秋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又是命运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又是人性的悲剧。而“命运”与“性格”在小说中则又被赋予了丰富、复杂的辩证内涵。诚如作家自己所说的:“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与虚拟的双重世界。筱燕秋的身上最让我着迷的东西其实正是这两样。有一句老话我们听到的次数太多了,曰:性格即命运。这句老话因为被重复的次数太多而差一点骗了我。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这个结论是狰狞的,东方式的。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它决定了汉语作为被动语态的妥协功能。”(注:毕飞宇:《〈青衣〉问答》,《小说月报》2000年7期。)可以说,毕飞宇正是以他的小说“智慧”,以他不动声色的笔墨写活了筱燕秋,也写尽了女人的虚荣与女人的妒忌,写尽了女人内心的曲折与波涛。小说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作家并没有用批判的审视的眼光去表现“人性之恶”,小说没有居高临下,甚至也没有怜悯,而是充满理解与同情,心痛与伤感。自始自终,小说的叙事与精神基调都是与筱燕秋“共振”、“共鸣”着的;“当我动手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我与那个叫筱燕秋的女人已经很熟了。这是真的。在我的身边,筱燕秋无所不在。她心中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我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得到。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变得和筱燕秋一样焦虑了,为了摆脱,我只能耐着性子听她唠叨。然后,把我想对她说的话说完。”(注:毕飞宇:《〈青衣〉问答》,《小说月报》2000年7期。)二十年前心高气傲的著名青衣筱燕秋因《嫦娥》一戏而大红大紫,但因向师傅李雪芬脸上泼了一杯“妒忌”的开水,从此被剥夺了登台的机会。二十年后因烟厂老板的“垂青”,她又重新获得了登台的机会。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拯救,是困扰她二十年心理情绪的释放。她必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拚命地减肥、和老板睡觉、不要命地人流,甚至主动让徒弟春来演A角,在她这里都是必然的、必须的。但,可悲的是她毕竟老了,正如二十年前她没能胜过师傅李雪芬一样,今天她对自己徒弟春来的“妒忌”也仍然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的轮回。她可以连演四场,但究竟不能阻止春来的登场。她在人们对春来的叫好声中崩溃、疯狂可以说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筱燕秋这里,作家把人性的、性格的、命运的、时代的因素熔炼为一个令人怦然心动、黯然神伤的整体艺术氛围,立体地多层面地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与悲剧感。筱燕秋的悲剧无疑是具有放射性的,某种意义上,筱燕秋就是“嫦娥”,就是“李雪芬”,就是“春来”,她们是不同的人,又是同一个人,她们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正是通过“互文”的方式小说赋予了那种人生的疼痛与无奈以普遍性的意义。毕飞宇的小说用笔往往不露痕迹,但切入人性、人心、人情之深、之狠又非一般小说可比,应该说《青衣》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次,《青衣》的魅力还来自于小说艺术上的成熟。毕飞宇是一个对现代小说的叙述技术非常熟稔的作家,但在他的小说中那种“外显”的突兀的“技术”痕迹总是非常少见的。他总是采用一种举重若轻、从容不迫的叙述方式去展开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性格。他声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注:毕飞宇:《〈青衣〉问答》,《小说月报》2000年7期。)在这个问题上,毕飞宇一直有着高度的自信,他认为通过“形式”的努力来引人注目那只是艺术的一个初始阶段,艺术的高级阶段应该是让“简单”和“朴素”自动呈现其艺术力量与艺术魅力,他觉得越是“简单”的越是“朴素”的才越是难以表达的,才是对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真正考验。因为此时没有了“夸张的”“形式”或“技术”的护短,作家只有亮出真功夫才能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说。《青衣》确实是一部“简单”、“朴素”得到家了的小说,是一部艺术形态上多少有点“土气”的小说。在毕飞宇笔下,那些现实的矛盾与历史的纠结、社会的纷乱与家庭的震动……时刻都在发生着冲撞,而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物的内心与精神深处更是充满了波涛汹涌的内在紧张,但这一切在小说中全部都变成了日常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我们看不到人为的设计,看不到剑拔弩张的情节冲突,一切都仿佛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另一方面,《青衣》是一部充满内在力量的小说,这种力量包括情感的、人性的、审美的、思想的等多个层面,但是小说的这种艺术力量又不是通过“煽情性”的语言来实现的,相反,小说的叙述是隐藏的,作家没有主观的视角,而是把视点完全归附在主人公身上,整体上营构的倒是一种朴素、客观的语言效果。小说的主体是筱燕秋20年来的心路历程,是她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但小说却几乎不见正面的直接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剖析,而是把心理刻划完全细节化、意象化、意境化了。比如,小说中筱燕秋重上舞台的复杂心情主要是通过她与丈夫面瓜的性生活折射出来;而她最后的精神崩溃则是通过“雪中唱歌”的意像凸显在小说中的。“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的下面。筱燕秋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同时舞动起手中的竹笛。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簧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的门口突然围上来许多人,突然堵住了许多车。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围上来的人和车就像是被风吹过来的,就像是雪花那样无声地降落下来的。筱燕秋旁若无人,剧场内爆发出又一阵喝彩声。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在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了雪地上,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小说这最后一个意象、最后一个情境无疑是小说的高潮,它通过对于人物精神与心理的“意象性”、“戏剧性”的凸显,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可视性”转换,完成了对主人公的最后塑造,并进而把一种悲剧性的气息渲染成了笼罩性的精神氛围。
当然,说《青衣》是一部体现了毕飞宇艺术理想的成熟作品,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就是完美的。毕飞宇在小说中叙述了大量的戏剧知识,比如青衣与花旦的区别等等,要搞懂这些且叙说清楚十分不易,毕飞宇叙述得如此成功肯定花了不少力气,但也正因为此,这方面的内容就难免给人以卖弄之赚了。“一部戏总是从唱腔戏开始。说唱腔俗称说戏,你先得把预设中一部戏打烂了,变成无数的局部、细节,把一部戏中戏剧人物的一恨、一怒、一喜、一悲、一伤、一哀、一枯、一荣,变成一字、一音、一腔、一调、一颦、一笑、一个回眸、一个亮相、一个水袖,一句话,变成一个又一个说、唱、念、打,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磨合起来,还原成一段念白,一段唱腔。”这样的文字不能说它不美,也不能说它知识含量不丰富,但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总给人以一种卖弄性的“匠气”感觉。另外,作家对老板这个形象的刻划也落俗套了。小说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批判金钱和商业法则,而让筱燕秋去跟老板睡觉,老板可以是一个真正的筱燕秋崇拜者,一个真正的热心艺术者,他不必一定是一个想占有名人肉体的流氓。小说现在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对“老板”一词流行含义的一种简单化认同,是对“老板”的符号化理解。这种认同对于“老板”这个“人”的刻划固然是一种损害,更重要的它还构成了对于筱燕秋这个人物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