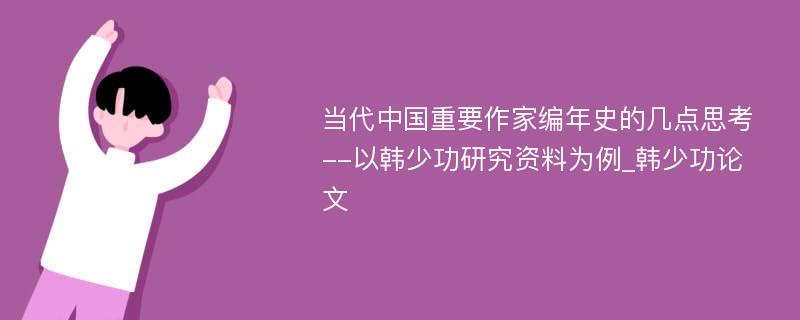
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的几点想法——以《韩少功研究资料》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几点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想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光炜老师在《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中,提出要有计划地推进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有着良好前景的学术倡议。我想结合《韩少功研究资料》(廖述务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中的“韩少功传略”与“韩少功作品目录”,以及编者在此基础上编撰的《韩少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4),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980年代,有些出版社曾经持续不断地出版过一些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集,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一工作因出版业的市场化转型而中断。近年来,天津人民出版社接续了这一传统,先后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王蒙、韩少功、苏童、余华、王安忆、贾平凹、王小波卷,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若以现代作家年谱所达到的高度来看,这套丛书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能给上述作家编撰出较为完善的“年谱”,其文献参考价值和史料积累的意义,可能会比现在提高许多。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资料完备、准确的“作家年谱”,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辑佚、整理工作一直无法展开,当代文学史料的建设与积累,也因此而长期成效不大,若能有计划地推进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则可以突破制约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瓶颈”,使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积累。作为一种传统学术形式,编订“年谱”是积累史料的良方,而“年谱”又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曾高度肯定“年谱”对历史研究的意义。鲁迅也曾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①王瑶在新时期之初,也提出“由年谱入手,钩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设想。②上述看法,都值得我们当代文学史研究者高度重视。
一般来说,成功的“年谱”,在叙述谱主的家世、履历、交友和创作时,要尽可能“详尽细致”,应该在“考订事迹之详”“排定年月之细”上见功力。而《韩少功传略》对作者履历的介绍,则显得过于粗略,编撰者只是求其大概,而未能详考作者履历,只是按照“年度”进行粗略整理,而不是按“年”“月”“日”进行细致排定,以致履历中出现许多重要的“空白”。在“年谱”编撰中,下功夫填补这些“空白”,其文献价值会有明显提升。遗憾的是,作者在“韩少功传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韩少功文学年谱》,虽加入一些新史料,但由于受到编撰思路、年谱的篇幅以及采集资料的范围的限制,对韩少功履历的介绍,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当然,这不是要苛责编撰者,我只是想以此为例,来探讨“年谱”在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方面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韩少功传略》对作家履历的叙述过于粗略,是因为编撰者占有的史料不够,采集资料的范围太小。作家履历需多方搜求、百般考证,方能做到“约悉无遗”。在作家自述、访谈、档案、书信和日记中,甚至在作家的小说和诗文中,都可找到相关的线索。除作家本人的著述外,其周围前后有关人物(亲友、编辑、研究者)庞大而散乱的著述中,也可以搜索到一些有益的线索。因此,要想写好作家“履历”,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各方面的资料,并对其进行披沙拣金、芟汰冗杂、排比归类等精细的考订工作。比如,《韩少功传略》写到:“1979年3月韩少功随团访问中越边境”,而他何时归来,有何见闻与感受,都是语焉不详,如参照韩少功大学同学骆晓戈的《韩少功印象》,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再比如,笔者在撰写《韩少功的编辑生涯与文学创作》时发现,《传略》只提供了韩少功主编《主人翁》《海南纪实》《天涯》的大致年份,而韩少功主编上述刊物时,是与哪些人合作的?他做了什么工作?遇到了哪些波折?这对他的价值观念与文学观念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在“传略”还是在后面编选的资料中,都是其情未详。笔者反复追索发现,张新奇、林刚、蒋子丹、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一凡等,都曾参与《海南纪实》的编辑工作,如果把他们关于《海南纪实》的零散文字吸纳进来,韩少功的这段履历,至少会比现在丰富许多。作者对韩少功主编《天涯》杂志的叙述,虽详而未尽,因为他仅仅参考了韩少功的《我与〈天涯〉》,如参照其合作者蒋子丹的《结束时还忆开始》(《当代作家评论》2003.5)、王雁翎的《〈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10-27)、李少君的《〈天涯〉十年回顾》(《北京文学》2007.8)、《〈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2)等文章,也可以使韩少功的这段履历更清晰些。
其次,年谱对作家履历的介绍,还要尽可能“宏博”。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过:年谱作为一种文体,“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③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年谱,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人看到一个时代,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教育与阅读情况、重要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个人交友等,提供丰富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应该能够以传主的活动为中心,复原当时文坛的复杂的网络结构。作为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韩少功曾引发过多次思想论争和文学论争,联系的作家与学者非常多,纠结着当代文坛复杂的人事关系,它构成了韩少功成长的“具体环境”,对韩少功的思想情感、文学观念乃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自然也应该在年谱中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反映。
比如,在韩少功创作起步时,黄新心、胡锡龙、甘征文、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贝兴亚等文友间的相互激励,老作家李季、严文井以及文学编辑王朝垠对他的提携,这类文人交往行为,就应该成为年谱中的重头戏。再比如,韩少功主编《天涯》以及任海南省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期间,王蒙、莫言、张承志、苏童、李锐、蒋韵、张炜、方方、迟子建、于坚、杨炼、李国文、张贤亮、毕飞宇、黄平、汪晖、李欧梵、李陀、刘禾、南帆、王晓明、温铁军、王绍光、陈嘉映、周国平、赵汀阳、朱学勤、韩德强等人曾来海南讲学。“马桥事件”发生后,也有大量作家卷入其中,史铁生、何志云、汪曾祺、蒋子龙、方方、李锐、蒋韵、何立伟、迟子建、余华、乌热尔图联名上书中国作协,要求为韩少功辩污。韩少功2000年迁入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新居,李陀、刘禾、李锐、方方、蒋韵、贾梦玮等人曾先后来此拜访。此外,韩少功还与许多外籍人士有过交往。在这些交往者的论著与相关的新闻报道中,都留下了零散的相关资料,对其进行整理、考订,可以呈现出韩少功的文坛“交游图”,这不仅有助于认识韩少功的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而且对研究其他作家也会有所助益,倘若年谱编撰能够形成规模,自然也会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深化。
第三,年谱在叙述作家的履历时,要善于“选精择粹”,而不要变成对作家生活起居的繁琐记载。作家年谱不仅仅是资料的汇编,更应该是在深入研究作家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浓缩的精华。因此,要重视“时事”(重要历史事件,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与文学思潮等)对作家的影响,重视能够反映作家思想和艺术观念变化的“关键”史料。应该说,《韩少功传略》基本抓住了作家生平、思想、艺术观念的重大转变,但在“时事”与“作家”关系的挖掘上,还做得远远不够。诸如韩少功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1980年代时而宽松时而紧张的政治文化思潮对韩少功创作的影响,韩少功在“文革”中所受教育与他1990年代以后所坚守的理想主义(注重实践、关注民生)之间的关系,文学思潮对韩少功的影响以及韩少功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都需要在材料上进行深入的挖掘。
第四,《韩少功传略》在体例上也有些混乱无序,没有严格按照年、季、月、旬、日的顺序展开叙述,有不少时间上的大幅度跳跃和事件的提前抑后,这也是对现有史料的占有和分析不够造成的。撰写“年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现有公开出版的资料,都不能填补作家履历的某些“空白”,这就需要耗时费力地访问作家的亲友与知情者,建设和积累新的史料。也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穷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有些史实不能确证,这就需要定论缓作,按统一的规范“存疑”:日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季考订不清的写年。用旬、月、季、年表述的条目,一般要放在该旬、月、季、年的末尾,而不应像“韩少功传略”那样随意。传统的年谱采用这样的体例,是有很大好处的:一方面便于读者翻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后继者补遗拾缺:许多作家年谱,就是在反复补充和修订中日臻完善的,模糊的“年”和“季”逐渐被具体的“月”“旬”“日”取代。依据现有的资料,韩少功的许多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是可以具体到“日”的,而《韩少功文学年谱》却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此外,为便于研究者参阅,年谱在征引资料时,应该注明资料的出处,对有争议的问题,要列出考证的过程,对遍寻而不可得的重要史料,要详细收录。在体例方面,《韩少功文学年谱》相比《韩少功传略》虽有改进,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好的作家年谱,应该具有目录索引的功能。梁启超认为,年谱记载文章的体例,最好是“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④年谱对作品的收目,理应竭泽而渔、巨细靡遗。不可否认,“韩少功作品目录”是迄今为止收目最多的,可惜遗漏和错讹之处太多。已出版的几种“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缺陷。当然,像“作品系年”“作品目录”这类资料性质的工作,要一下做到全部翔实可靠、无所遗漏,是很困难的,但编撰者必须具备求全求真的理想,为后继者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史料的钩沉补遗、考订错讹能够展开。在这套丛书中,文章编目工作做得最好的,当属王蒙卷,也是因为有先期资料整理的良好基础可供参考,可以省却许多考证的功夫。
“韩少功作品目录”的收目,截止于2006年。笔者正在进行《文学报刊与中国当代文学》(资料卷)的编撰工作,随手翻阅手边的一些地方刊物,竟发现几十篇没有收入“作品目录”的“佚文”。湖南是韩少功的故乡,《芙蓉》《湘江文艺》(后更名为《文学月报》《湖南文学》《文学界》)等湘籍刊物,有近水楼台之便,笔者重点检索、翻阅这些刊物,发现没有被收目的作品有:《志愿军指挥员》(《湖南日报》,1979-05-20),《宝塔山下正气篇——记任弼时同志在“抢救”运动中与康生的斗争》(《湘江文艺》1978.4),《调动》(《文艺生活》1980,期次待考),《人人都有记忆》(《湖南群众文艺》,1980.2),《离婚》(《洞庭湖》1980,期次待考),《近邻》(《洞庭湖》1982.1-2),《同志时代》(《芙蓉》1982,期次待考),《美丽的眼睛》(《芙蓉》1996.5),《韩少功致本刊的一封信》(《芙蓉》1999.3),《访法散记》(《湖南文学》1993.3),《烂杆子》(《湖南文学》1995.6),《关于文学》《生活选择了我》《土地》(三篇均见《文学界》2005.5)等,而没有发现的,可能还会有许多。
韩少功发表于其他地方刊物的作品,也有许多没有收目,如:《山路》(《广东文艺》1978.4),《孩子与牛》(原题为《晨笛》,《芳草》1981.1),《反光镜里》(《青年文学》1982.2),《诱惑(之一)》(《文学月报》1986.1),《祝贺〈作家〉创刊三十周年》(《作家》1986.10)《文学散步(三篇)》(《天津文学》1987.11),《美不可译时的烦恼》(《文学角》1988.1)《艰难旅程》(《特区文学》1988.1),《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四川文学》1992.10),《走亲戚》(《福建文学》1993.12),《那年的高墙》(《光明日报》1993-08-07),《余烬》(《上海文学》1995.1),《马桥人物(两题)》(《小说月报》1995.9),《记忆的价值》(《萌芽》1996.2),《我们的残疾》(《鸭绿江》1997.1)《行为方案六号》(《红豆》2002.6)、《山居笔记(下)》(《钟山》2006.5)等。
编制作家年谱时,必须考证文章发表的原始刊物,“韩少功作品目录”的编者,做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其耐心和细致不容否定,但有些出过单行本长篇作品,编者却未标明其原始出处,而注明原始出处,却是年谱编写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原因在于:其一,作品在刊物上发表时,带有更多的原初形态,它们是与诞生时的复杂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编辑们在刊出作品时,往往会考虑是否刊发头条、在什么栏目刊出、是否附加编者按、创作谈和评论文章等问题,从同期刊出的作品、社论乃至广告,等等,可以看出作品刊发时的整体文化氛围,从中更容易发掘出有价值的文学史信息。其二,便于进一步发掘作家的佚文。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刊发于《小说界》1996年第2期,能够把如此重要的作品交给《小说界》,说明韩少功与该刊编辑有着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具有持续性的,笔者顺藤摸瓜,果然在《小说界》上发现一些尚未收入“韩少功作品目录”的作品:如《灵魂的声音》(1992.1),《祝〈小说界〉百期》(1998.6),《山居心情》(2006.3,《山南水北》节选)等。其三,可以避免以讹传讹,确保年谱的文献价值。在“韩少功作品目录”中,有许多文章出处的错误:比如,《战俘》原载《湘江文艺》1979年第1-2期合刊,而非第1期;《飞过蓝天》原载《中国青年》1981年第13期,而非第15期;《暗香》原载《作家》1995年第3期,而非第2期;《论文学的“根”》原载《作家》1985年第4期,而非第6期;《情感的飞行》原载《天涯》2006年第6期,而非第5期。上述错误,显然是简单抄录第二手的文集和研究论著,而没有仔细地核对原始报刊造成的。
此外,“韩少功作品目录”是按照“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及传记”“纪实性散文”“思想性随笔”“文论”“序跋”“对话、访谈及演讲”“杂谈、小品及其他”等不同的文体,对韩少功作品进行分类并按先后顺序编目。编者为考究每篇文章的类别,肯定下过一番功夫,这有助于读者把握韩少功不同文体的创作情况。但这种分类整理,也破坏了不同文体的作品所产生的先后顺序,不符合年谱编写的规范。不如按照传统规范,把不同文体的作品夹杂一处,而在作品篇目后注明文类,以便于研究者把握作家思想与创作发展的轨迹。我们知道,各文体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对于极力倡导“跨文体写作”的韩少功来说尤其如此,要想对其作品进行归类,难免会出现各种混乱。譬如,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部分,编者同时收录了《那晨风,那柳岸》与《火宅》,在“思想性随笔”和“文论”部分,同时收录《感觉跟着什么走?》,在“思想性随笔”与“杂谈、小品及其他”部分,同时收录《民主的高烧与冷冻》,在“思想性随笔”和“文论”部分,同时收录《好“自我”而知其恶》,在“文论”与“对话、访谈及演讲”部分,同时收录《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文学:梦游与苏醒》等。而重复收目,在年谱的编撰中是决不允许的。
指出《韩少功研究资料》的遗漏、错讹和不规范问题,并非否定编撰者的劳绩,而是考虑到作家年谱是在积累史料方面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全集、文集和传记,只有具备了规范而完善的作家年谱,拾遗补缺工作才能展开,资料建设上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韩少功研究资料》的编撰者耗时费力,而未能臻于完备,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可能与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整体滞后有关。迄今为止,高质量的当代作家年谱还很少见,在体例上接近现代作家年谱的,仅有庄汉新的《周立波创作年谱》(《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4),燕绍明的《欧阳山年谱》(《新文学史料》1988.1),吴永平的《姚雪垠创作年谱》(《新文学史料》2003.3),陆志成的《陈登科创作年谱》(《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2),周启祥的《魏巍生平与创作年谱简编》(《河南师大学报》1984.2),艾以的《王西彦年谱》(《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3),盛海耕的《公刘年谱》(《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3,1991.1),曹玉如的《王蒙年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等,其谱主多为跨代作家,而编撰者多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其他许多当代重要的作家,有的也推出了“作家小传”“作品系年”和“作品目录”,但无论在学术质量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无法和现代作家年谱相比。
我同意程光炜先生的看法:可以借鉴现代文学界整理史料的经验和方法,来推进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工作。在近30年中,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先后推出许多大型的史料索引工具书,如:唐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9-1949)》,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封世辉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万一知、苏关鑫的《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和目录汇编》,应国靖的《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王大明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等。上述工具书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建设,因为史料的钩沉辑佚,必须具备相对完善的文学报刊、图书的目录汇编:据我所知,几位在编制现代作家年谱、发掘现代作家佚文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虽然也会漫无目的地到原始报刊中寻找史料,但他们也会依赖各种目录汇编,在目录汇编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后,然后去翻阅原始报刊查找原文。
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在文献辑佚整理工作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作家全集的编撰、作家回忆录和传记的书写、作家年谱的编制,是可以相资相益的,年谱编撰者会从作家全集、作家回忆录和传记中获得重要的史料线索,而作家全集、传记,也会受益于年谱的编撰。不过,通常来讲,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更为看好的是作家年谱,因为年谱是浓缩的精华,其中的史料的线索要比全集和传记丰富,此谓学界流行的“年谱胜于全集”的说法。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否定全集和传记在史料积累方面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正是上述几种史料整理工作的相互配合,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发展,使得现代文学史料的辑佚钩沉工作成为可能,特别是大量作家全集的出版,使得集外佚文发掘蔚然成风,不少“全集”出版后,又推出“补遗”本,而作家的年谱,也总是处于不断地修订之中。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整体水平,就是在这样慢慢地积累中不断提高的。
而当代文学资料的整理工作,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现代文学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工作无论规模、连续性和系统性都不能与现代文学的资料建设相提并论”⑤。由于史料建设的整体滞后,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撰,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首先,最基本的文学报刊目录汇编工作尚未展开。没有完善的文学报刊目录汇编,无论是从事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还是作家年谱的编撰,都是非常困难的。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了“中国期刊网”“维普”“报刊目录索引”“读秀”等电子检索工具,这为资料的整理与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再也不必像1980年代初的资料整理工作者那样,为了某些较为常见的资料,也要东奔西跑、耗时费力。当时信息闭塞,搜集资料艰难,很多资料的整理工作都要依赖作家,由作家提供“作品目录”“研究论文目录”和文章的复印件,为了寻找一篇文章,为了搞清某篇文章的出处,史料工作者们不得不与作家反复地书信往还,效率低下。当时的史料建设,就是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检索,因为“十七年”“文革”与“新时期”的许多地方文学报刊,甚至某些名刊大刊,尚未录入检索系统,许多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还沉睡于布满灰尘的原始报刊中,而得不到挖掘和利用。我们不难发现,《韩少功传略》和“韩少功作品目录”以及《韩少功文学年谱》的撰写,更多依赖的是电子检索系统,收入检索系统的篇目,大多被收目,而没有录入检索系统的文章,则只能付之阙如。可见,尽快进行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目录汇编的编撰工作,是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前不久,听说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重要文学报刊目录汇编”即将竣工,期待着本书能够早日出版。
第二,年谱的编撰往往依赖于作家的全集、选集、评传、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在这些方面,当代文学也明显滞后于与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多已谢世,其创作已进入“完成时”,大多出版了全集,许多作家的书信、日记也随着全集出版而得到广泛地征集与整理。而当代的重要作家,其创作尚处于“正在进行时”,出版的大多是选集,书信、日记尚未进行整理刊布。因此,编撰当代作家年谱,更多依赖的只能是那些残缺不全的、鱼龙混杂的选集文集。以韩少功的文集为例,目前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有《韩少功文库(十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文集中的作品,只标明文章发表的刊物和年份,而具体期次则不详,竟然有大量文章发表的年份被搞错了,也有不少作品的原发刊物被搞错了,这可能是韩少功在编选文集时记忆有误造成的,而后来出版的文集则以讹传讹。笔者依据上述选集到报刊中查阅文章的期次,曾多次误入歧途,劳而无功,深感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之严重。
由于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整体滞后,编制作家年谱时采集资料的范围本来就不大,这就更需要对现有资料进行充分开掘。但遗憾的是,上述韩少功文集中的许多作品,并未进入《韩少功传略》、“韩少功作品目录”与《韩少功文学年谱》,以致出现“年谱不如选集”的奇怪现象。年谱提供的资料线索比作家选集还要少,其参考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梁启超在谈到年谱的起源时曾说:“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⑥连“集内”的资料都没有充分吸纳,怎么能够让读者满意呢?在韩少功“集外”的资料中,目前尚未见到其书信和日记出版,但已经出版的韩少功的两部传记:何言宏、杨霞的《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孔见的《韩少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都披露了不少韩少功的第一手资料,同样也没有被《韩少功传略》和《韩少功文学年谱》充分吸纳。我觉得,编撰作家年谱是一项惠及学界的事业,是不妨大胆地互通有无的,只要尊重同行们的原创性劳动,在征引文献时注明出处就可以了。
第三,缺乏重视史料积累的良好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现代文学年谱的编撰能够取得良好的成绩,得益于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界重视史料积累的良好学术环境,佚文发掘与整理蔚然成风,出现一支人数众多的史料辑佚整理队伍,出现丁景唐、马良春,朱金顺、陈子善、陈梦熊、陈富康、徐迺翔、解志熙、张桂兴等在史料建设上卓有成绩的学者,他们群策群力,在史料发掘中相互支持,经常无私地向同行提供重要佚文的线索;他们相互砥砺,为了某篇文章或某条注释,经常展开激烈的学术争鸣,而健在的作家则纷纷撰写回忆录,支持史料建设。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出版社和刊物的支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出版社和刊物,都为现代文学史料的积累作出了贡献。正是在重视史料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中,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老舍、冰心、胡风、冯雪峰、丁玲、废名、朱自清、沈从文、穆旦、冯至等,都有了较为成熟的年谱,有的还不止一种。由于年谱的编写已成规模,相互对校,共同提高,也就成为可能。现代文学史料的积累,也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了。
在1980年代,当代文学界也曾出现过一个资料建设的高潮,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中文系联手协作,福建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七八个出版社积极参与,先后推出柳青、梁斌、杨沫、杜鹏程、王愿坚、王汶石、刘白羽、魏巍、吴伯箫、秦牧、杨朔、王蒙、茹志鹃、徐迟、徐怀中、胡奇、李准、刘心武、刘绍棠、丛维熙、马拉沁夫、谌容等数十位作家的研究专集,在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惜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出版业的市场化转型,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中断了,而轻视史料建设的学风也在学界弥漫开来。
我觉得,有计划地推进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撰,必须慢慢扭转轻视史料积累的学风,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在作家选择上,应该把上述收入“中国当代文学资料研究丛书”的作家纳入年谱编撰的范围:一是因为当时出版的多数研究专集还不够详尽;二是不少作家在出版了研究专集后,又有了时间长短不一的创作历史,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此外,还有许多在“十七年”间进入写作高峰期或开始文学写作的作家,没有列入上述“研究丛书”中,如吴强、曲波、高晓声、陆文夫、蒋子龙、鲁彦周、莫应丰、陈忠实等,可以纳入年谱整理的范围。再者,我赞同程光炜先生的意见,可以把一些出生于“50后”的作家和少数出生于“60后”的作家纳入年谱范围,他们当时创作资历尚浅,没有被列入“研究丛书”的范围,但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创作后,在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韩少功、莫言、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史铁生、刘震云、阎连科、铁凝、张抗抗、方方、池莉、王小波、苏童、余华、格非等,这些作家现在已经六十岁左右,对其创作历史进行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资料整理方面,我们有必要抓住宝贵的时机,提前着手进行。
由于涉及的作家多,工作量大,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互通有无,才能汇聚较为完备的史料基础:作家应该为史料建设添砖加瓦,1980年代,曾经出现一个现代作家撰写回忆录的浪潮,而1990年代以后谢世的作家,留下较为详尽的回忆录的,可谓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应该有所改变。在积累史料方面,出版社和学术刊物也是责无旁贷的,与其大量刊发那些毫无创意的东拼西凑的学术泡沫与旋生旋灭的文化垃圾,不如脚踏实地为学术与文化的繁荣做些最基础性的工作。在研究生教育中,也要加强史学基础的训练,可以通过撰写作家年谱,提高学生研究历史的能力,培养一批在文献辑佚整理方面学有所长的年轻学者。
今天,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成为历史的,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我们都有责任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一些有益的历史记录,不要让我们或惨痛或美好的历史记忆悄无声息地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因为,只有有计划地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家年谱,才能把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才能像现代文学乃至古典文学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才能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王瑶:《郁达夫生平的发展线索——温儒敏著〈郁达夫年谱〉序》,《王瑶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③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996年版,第438页。
⑤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996年版,第428页。
标签:韩少功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天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