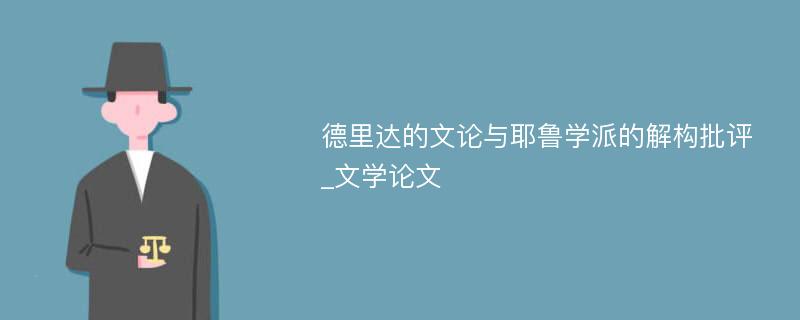
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鲁论文,学派论文,批评论文,德里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构何为?
自从雅克·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结构、符号与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在接下来的20年中,解构主义逐渐成了批评时尚。解构主义理论的身影不仅在《亚姿态》(Sub-stance)和《辨证批评家》(Diacritics)这样的先锋和理论性的期刊上频频亮相,连《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在内的主流学报也对解构主义这一新兴理论表现出了罕见的兴趣和热情。解构主义潮流汹涌,以“拒斥阐释的客观标准”为标志的“耶鲁学派”文学批评应运而生、风行一时。紧接着,以解构主义为对象的阐释性、批评性研究和实际应用甚嚣尘上。先是在法国,随即在英国,解构主义的政治含义受到解读,它与马克思牵扯在一起,被应用到了具体政治问题上。(这从德里达附于《立场》中的访谈录和特里·伊格尔顿的著述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解构主义对神学和宗教所产生的影响等等,也成为重大的学术课题,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其后,解构主义似乎进入了“衰落”期,同时,另一些“后”学兴起(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仿佛掩盖了解构主义的锋芒。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所有“后”学的倡导者,无不公然承认解构主义是他们所倚仗的基本思路。
不管人们喜欢用什么方式和措辞来描述解构主义所经历的这一系列变迁,我们可以肯定两个基本事实:一、解构主义思潮的浮沉大抵可分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描绘出了解构主义的发展走向:书写学(grammatology)—解构批评(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应用解构批评(应用解构思路进行文学或文化批评的理论学说,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二、从第二阶段起,解构主义仅仅成为了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被运用到了解构主义自己乃至由世间万物构成的无所不在的“文本”上。
解构主义是什么?它的效用是否有一个限度和范围?解构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变迁是否说明了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解构主义的学者各持不同的看法。解构学说的重要阐述者V.B.利奇和克里斯多弗·诺里斯均主张解构主义的首要目标及意义在于哲思层面——消除在思想上具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西方形而上学幻象。对于解构主义者后来乐此不疲的阅读实践,他们或称之为一种“简约”过程,(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52.)或谓之曰“并不总与德里达所要求的论辩的严谨性合拍”。(注: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1991,p.91.)乔纳森·卡勒则一方面承认“解构主义”在学者们的笔下一直三位一体,既是一种哲学立场,又是一种政治或学术策略,此外还是一种阅读模式,(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after Structuralism,Routledege & Kegan Paul,London and Henley,1981,p.85.)但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态:“德里达自身对文学作品的探讨,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些重要问题上,但是,这些并不是‘解构’——不是我们一直运用‘解构’一词所表达的意思。解构文学批评将主要受到德里达解读哲学著作的影响。”(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after Structuralism,Routledege & Kegan Paul,London and Henley,1981,p.213.)他似乎主张,就文学而言,德里达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反诘哲学的思维方式给文学观念体系带来的影响。与上述学者不同,G.D.阿特金斯则宣称:“我认为,如果解构主义不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话,它就什么也不是。阅读是我们不间断参与的活动。”(注:G.Douglas Atkins,Reading 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veReading,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Lexington,Kentucky,1983,p.3)
对于同样的问题,解构主义者自己也给出了回答,但又似乎语焉不详,含糊其辞。德里达曾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注:转引自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p.261.)另外,保罗·德曼也写道:“解构的目标永远是揭示假想为单一性的总体中存在有隐藏的连贯和碎裂。”(注: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79,p.24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解构与阅读有关。没有对西方思想史的阅读,没有对结构史的阅读,解构无从谈起。其次,解构是在具体阅读行为中运行的。解构主义相信:“离开阅读就不可能产生可抽象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论点、概念或方法。”(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14.)解构主义与哲学传统针锋相对的焦点亦与此相关:哲学建立在普遍的抽象原则之上,试图企及某种超验的意义、真理或工具性,它与具体的语言行为或对于语言的回应相脱离;而解构主义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再次,解构既是一种阅读行为,又是阅读行为的结果。德里达从列维-斯特劳斯、卢梭、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出发,于细小处进行研读。在他的视线之下,这些西方传统思想代言人的著述就仿佛经过两次绘制的油画,画面表层的油彩逐渐自动脱落,露出全然不同的面貌。这一过程中,“解构”既指德里达“别有用心”又不着痕迹的阅读行动,又指传统思想“自动”崩溃的过程和结果,而最后于“传统”之内、之下显现出的思想仍称作“解构思想”。
然而,解构主义从一种语言观、一种反形而上学演化为一种文学论和批评模式,后又成为一种普适性极强的基本批评手段,这一历程为何会给“解构主义”一词带来诸多歧义?如果这是解构思想前行的必经之路,又说明了什么?要得出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不从德里达的文学论、批评观谈起。
二、德里达的文学论
1.对“什么是文学?”之批判
什么是文学?我们在德里达论马拉美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文学以自身的无限性取消了自身。如果说该文学手册有意说些什么的话(而此刻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它将首先宣布文学根本不——或者几乎不——存在;无论如何,不存在文学的本质,没有文学的真理,不存在文学性存在,也不存在文学的文学性。(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177.)
此外,在《文学行动》收录的访谈中,我们再次看到德里达的宣言:
假定有称作文学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构体,那么,它的开始便是它的终结。(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42.)
文学可能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它永远不是科学、哲学、会话性质的东西。然而,如果不是对所有这些话语开放,如果不是对这些话语的任何一种开放,它也不会成为文学。没有对于意义与指示的中止关系就没有文学。(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p.47-48.)
在德里达看来,文学并不局限于明确界定成里面和外面的形而上概念领域里,文学的王国是一个破坏(非此即彼式)选择、破坏同一性逻辑的王国。文学的力量并不存在于某个地方,它飘忽不定,转瞬即逝;我们只能凭借某种特定的注意力和努力才能感受到它,只能通过某种特定的行为才能确认它的存在。而且,文学的潜能不仅不具备实体,我们甚至不能藉此将文学和其他范畴的写作绝对地区别开来。
从德里达的著述中,我们发现,德里达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论点:没有什么文本完全在哲学概念和对立观念的控制之下,任何文本都可以被读解为“文学的”文本;同样,完全“文学的”文本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语言行为或阐释行为的实施均须依赖哲学范畴和哲学设想。因此,对于德里达而言,“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阅读并没有显著差别。利奇在《解构主义批评:高级导论》中曾指出,德里达的解构论(deconstruction)与海德格尔式的“摧毁”论(destruction)的差别关键在于,后者以存在为文学的领域,而前者以书写或语言为文学的领地,因此,“能指的无序飘动,语法的、修辞的以及指意的语言层的自由嬉戏,杜绝了产生任何最终允诺的可能。”(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84.)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该提问方式表明,它是哲学概念思维的产物,是一句来自哲学思想领域的“引文”。解构主义者解答的第一步,就是解读出这一问题本身所蕴藏的同一性臆想,解读出其中的自相矛盾和自我瓦解的状态。
2.文学作为一种“体制”(institution)
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体制(institution):
文学作为历史性体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体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至去怀疑自然和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体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37.)
语言所具备的“能力”,作为语言或书写而存在的能力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同时可以作为标记重复、反复。于是,它开始与自身有所不同,足以变得典型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典型的可重复性是一种“经济”——这种经济对自身具有形式化作用。它同时也对历史发生形式化效应,浓缩历史。一部乔伊斯的文本同时也是一部几乎无限的历史的浓缩。……有时候,在我看来,文学的“经济”似乎要比其他类型的话语,如历史或哲学话语更为有力。有时候——这是据原则性和语境而定的——文学具有更大的潜力。(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p.42-43)
从德里达的“体制”说,我们可以体会解构主义文学观的若干特点:一、传统哲学式的提问“文学是什么”,要求的是一个从内在属性上对“杂质”加以排除、从外部形态上加以限制的解答,德里达给出的却是一个赋予自由和授权式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中“是”一词所具有的排他性和限定性,在“讲述一切”的开放效应下被抵消。二、“讲述一切”的自由,不仅指社会机制授予讲述者的权力或社会、法律、政治赋予文学的保障,也指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力量。语言的踪迹运动不断将此在因素和缺场因素同时纳入我们的思虑范围,从而既保留了刻在文学话语中的“原创性”,又将“可重复的”一般性引入话语中,这就是文学的“经济”——文学的资源部署策略。德里达说乔伊斯的文本中“绝对独特的签名”和“历史、语言和大百科全书的浓缩”并存,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三、“文学”这种体制既不存在于自然中,也不存在于人脑中,它的形成是由社会运行程序所带来的。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体制存在于力量的关系网中,存在于维系它的法则中;另一方面,它又不在法则的控制之内,不能由寻常的社会—经济—历史的思路所囊括。因此,称文学为一种体制,毋宁说它是一种“没有体制的体制”。(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42.)
可见,从德里达的体制说来看,文学的疆域从传统所认为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拓展开,和语言的边界相互套叠在一起。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扩展为文学和哲学的共性,模糊了文学和哲学范畴的边界,同时,文学和批评、文学和历史、世界、作者、读者的边界也变得无法廓清了。(注:文学文本是完整、独立、自足的,文学是一种与日常语言、科学、哲学有别的特殊语言形式——这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观点,是突破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传记体批评的要点所在。然而,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是与确立文学批评的学科地位、确立批评家的权威地位和身份密切相联的。德里达的文学思想与“学科”视角无关,因此,我们既不宜将他与形式主义批评混为一谈,也不能随意断言他是一种“倒退”。)
德里克·阿特里奇在《文学行动》的前言中这样说道:“……‘哲学’对‘文学’,是德里达在阅读这两种文本时一直耐心抽去的对立关系。此对立关系是一件哲学产物,而且,凭借该对立关系,哲学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也使自己站在了对立面的相反立场。”(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13.)哲学/文学的对立传统,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对立传统在学科上的具体化表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之所以惯于将口语置于优于书写的地位,是因为人们相信言语与意义、真理、主体性无阻碍地相联结。带着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信念反观哲学和文学,哲学显然更符合同一性逻辑,更贴近中心;相反,含混多义的文学也就更接近人们对书写的看法——它是对本原的遗忘和扭曲。惟有在德里达将书写确立为语言存在(包括口语)的前提后,语言与中心的距离失去了恒定的衡量标准,哲学/文学的对立才就此瓦解。
同理,当德里达提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学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对于社会性法则比较含蓄的意识”(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44.)的时候,文学性也与阅读意识融为了一体。这意味着,与其说文学“存在”于文本之中,毋宁说它“产生”于阅读之中。有了“意向关系”的加入,文学成为各种对立范畴相互影响和感应的场地。所以,德里达说,“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做出严格的区别或将两者混为一谈”都会是一件“不妥当”的事。区别的不妥之处在于,“‘好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经验,它是在语言之中的,是在所读文本的范围之内的阅读行为的记录。这一文本永远不允许自己被彻底地‘客观化’。”(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52.)混同之不可行的原因在于,“在称作文学作品的东西之‘内’还有一种‘批评的’要求在起作用”,“文本之‘中’存在着召唤文学阅读、唤起文学传统、体制或历史的特征。这种知性结构包含在主体性中,但这是一种非经验主义的主体性,它与一种主体间的超验的共性联系在一起。”(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44.)
将文学和批评的分界线擦抹模糊的“创造性”(inventiveness),也称作“原创性”(originality);而“复活文学传统、制度或历史的特征”或“知性结构”,也称作“一般性”(generality)或“可重复性”(iterability)。德里达所讲述的文本的原创性和一般性的关系(“经济”),不同于传统文学观里的矛盾而统一、辩证而调和的关系,也不同于艾略特所论述的“传统”和“个人才能”之间的互补关系。德里达说“任何作品的原创性都在于它独特地表现原创性与一般性两个方面,”(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68.)就是对二者矛盾的维系:原创性和一般性会交替作为此在和缺场的因素决定作品的形态,影响作品的接受状况。众所周知,作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传统观念,文学文本的原创性,总是由某些特定要素——内在要素如艺术风格,外在要素如历史、作者或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并且总会充当这些要素的统一表述,因此是可由读者把握的。然而,依据德里达的解构思维,这样的“原创性”无疑是完全自我显现的,是此在世界的产物,因而是虚幻的。德里达宁愿以“双重的、对立的、明显矛盾的”方式来理解文学文本的原创性和一般性:一般性是原创性产生自我差异、在自我差异中发生重复的结果;它既是众多文本在历史中构成的一种状态,也是文本自身的一种构成状况。
德里达对文学的原创性和普遍性关系的阐述,与传统观念所指的多文本共享某些实在属性的意味大不相同。传统认为——正如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体系所指示的一样——世界、作者、读者等因素与作品界限分明,外在于作品;作品通过“模仿”或“反映”前面的要素使自身与其溶解合一。德里达却不这样看。文学(性)非但与读者群“主体间超验的共性”不可分,与批评的疆域不可区分,甚至和历史性等因素也不可分。
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德里达意识到,面对“这样一部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都很久远的文学作品”,“用最有学识、最有见地的方法重新构建它的历史要素是必要的”,而这些历史要素不仅是指“莎士比亚构思的历史性、它在一系列作品中的印迹”,还包括“剧作本身属于历史性的内容”。他得出结沦:“受本身历史充分制约、蕴含历史意义且反映历史主题的文本,格外能够供人们在离它们本来的时间地点十分久远的历史环境中阅读。”(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p.63.)文本融合了包括历史语境、作者构思以及相关文本等在内的历史性因素,不断地携带着这些因素向新的历史语境开放,允许读者对它再语境化,进行新的编排构制,作品的历史因而就在不断的再语境化中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一部文学文本,历史、作者、世界等历史性因素不是外在于它的客体或反映对象,而是它自身构成的成分;而且,反过来说,文学文本的再语境化也是历史形成的重要前提。
所以,德里达依据其解构主义语言观建立的文学观,熔化了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的(也即体现在艾布拉姆斯坐标体系中的)作品、作者、读者和世界的分野。他擦抹了四者之间的严格区别和联系,指出任何单一指向的、有中心倾向的批评读解都有可能陷入谬误。换言之,没有任何一种批评有揭示“真理”的功能。德里达用“书写”、“异延”、“踪迹”等原理描述了语言的构造,用语言“营造”了世界和文学,因此,语言便是存在的前提和领域,而世界是无边无际的文本。在这样的世界中,万事万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自我(批评家、诗人和读者的自我)也都成为语言构造体,即文本。一切语境,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还是神学的,都成为文本间的关系;传统成为互文(intertext)。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的疆域扩张了——它成为文本性(textuality),进入了万物。语言和文学这种相连通、相套叠的关系,利奇表述得最为精彩:
什么是文本?文本即是具有差异性的踪迹串,是飘浮的能指序列,是伴随着最终无法破译的互文(intertext)因素起起落落的受到渗透的符号群,是语法、修辞以及(虚幻的)所指意义进行自由嬉戏的场地。文本的真理是什么?能指在文本表层漫无目的地飘动,意义的播撒,在某种条件下提供了真理:混乱的文本性(textuality)运作过程被有意识地规整化,被控制,被中止。真理在阅读的具体化和个人的愉悦中昭显。真理不是实体,也不是文本的属性。文本从不说出自己的真理,真理总是在别处——在阅读中。阅读生来就是误读。解构运行的目的就在于解开规整和控制播撒的束缚,颂扬误读。(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122.)
3.文学:作为一种行动
文学是一种行动——德里达的这一观点在前面探讨文学作为兼具“原创性”和“一般性”的“体制”时已有所触及。传统上,文学文本通常是作为一种已完成的“人工制品”而为人们所接受的。但在德里达的观念里,文学既是产品,又是一种“行动”——一种既独特、具有创造性,又具有可重复性的行动;其意义和功能可以和签名(signature)、专有名词(proper name)的使用以及日期的签署相类比。
在德里达看来,不论是签名,专有名词的使用还是日期的签署,它们都具有双重特性:它们既是一种动作,又是动作的模仿;既是一种行为,又是一种结果的记录;既是一个事件,又是一种法则。也就是说,三者——签名、专有名词以及日期——均体现了动态的(不稳定的)、不可预知的、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一面,又体现了静态的(稳定的)、可预知的、具有重复性(普遍性)的一面。以签名为例,法律社会中签名的功能具有矛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签名者此时此刻独一无二的确认;另一方面,签名的可重复性、可辨认性及可复制性。签名之所以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和依据得以普遍存在,就在于一个看似矛盾的逻辑——独特性的不可重复性及其同时存在的可重复性。与签名同理,专有名词也是原创性和普遍性共生的例证。
一切文学文本也拥有类似的自相矛盾的特性:一方面,它们拥有产生自我差异的潜能,它们在不断地产生着与其他文本的差异和自我差异,不断的分解组合使它们不断地获得新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分解组合又是一种重复行为,原创性的重复使它们又具有一般性,可为人读解。此外,文学文本和签名、专有名词还共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能超脱自身所对应的人员的缺场而使用下去,继续发生作用。它们表面上是此在,但代表的是缺场的力量。它们表面上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一种行动。所以,德里达之所以称文学是一种“行动”(如书名《文学行动》所示),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替换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法则——如体现在独特/普遍、具体的/理想的、合乎习惯的/法则支配的等对立范畴中的僵化思维——并重新给它们进行了定位。
从德里达对“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质疑,从他对文学作为“体制”、作为“行动”的开放式叙述,可以肯定,他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是对语言问题思考的延伸。没有“异延”、“书写”和“踪迹”等观念存于脑海中,他就不能在思及文学时时刻保持对形而上学思维、对逻各斯中心的警惕。没有解构式语言观和世界观作为他的内在信念和主张,他也不可能就文学做出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又容纳各种矛盾对立方共存的思考。
德里达谈论文学不离开哲学,谈论文学不离开文本以及文本阅读,这在形而上概念体系看来是混乱、无序、难以理解的。然而,依靠着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修补”,德里达建立了自己的语言逻辑和文学逻辑。在这个容许矛盾、欢迎矛盾的思维语境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合理性,一种对此前的语言世界和文学世界既可产生冲击、又可提供补充的新鲜构想:文学、哲学、文本、世界、读者、作者之间的壁垒被拆除,对立的、严格区别的范畴得以相互沟通;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中,无物不是文本;文学作为文本性(textudlity)渗入一切时间和空间;而“异延”、“踪迹”运动作为语言存在的根本,不仅使文本与文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使文本与其派生出的无数他者相区别、相联系;文本既是“产品”又是“行动者”。由此,任何看似单一的文本变得无限多元化了。在这种文学观的指导下,批评通向权威和真理的可能被取消,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体系被“擦抹”(文本、作者、世界和读者无一是真理中心,而且相互的边界无可辨别),一切阅读被视作误读,但阅读的自由又因此获得了充分允许和承诺。
三、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
文学概念置换为“文本性”,是解构思维渗入文学的国度、引发两个解构步骤的结果:一、文学/哲学、文学/批评、现实/虚构等形而上二元对立范畴被消解,文学概念中原本具有的本质属性、特殊含义被“抽空”;二、文学不再是一种特定文类(批评、哲学亦如此),文学领域得到扩展。那么,“文本性”又有多宽多广呢?德里达认为:“没有事物与文本性无关。”(注:转引自G.Douglas Atkins,Reading 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ve Reading,P.23.)另有批评家说:“应当把它理解为一个更贴近于广义书写的概念。”(注:Niall Lucy,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Blackwell,1997,p.109.)的确,当“异延”赋予文学以行动的能力,而文学的“重复”行动将文学与世界、作者、读者的边界擦抹之后,文学和语言已重合在一起。任何有“心灵的语言”发生作用的地方,就有文本性,也就有“文学”的存在。
“文学”的“原创性”和“可重复性”促使文本结构—解构—结构……,赋予文学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我们再不可把文学视为能指传达的所指;同时,面对文学文本,我们再不能依照传统的思维定势,预备揭示其中的真理和美,以组建一篇正确的、共鸣式的批评了。于是,在解构主义语言观和文学观构成的语境下,一个新问题浮现于我们的视野:真理/隐喻、真理/谬误、美/丑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均告消解,批评还能做什么?批评又能是什么形态?
就该问题而言,人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严格遵循传统批评观念和准则的人是悲观者;在他们看来,批评应当是具有知识性的元话语,(注:Niall Lucy,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 duction,Blackwell,1997,p.112.)这种元话语是在某种真理性目标的引导下获取的,因此,“文学越是被认为是异质的,人们对于批评解释和分析文学的力量越缺乏信念”,(注:Niall Lucy,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 duction,Blackwell,1997,p.112.)他们提出了“批评之死”。(注:前面引述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导论》一书,就专门开辟了一章谈当代的“批评之死”。)还有一部分批评家恰恰相反,他们异常乐观;立足于批评的衰落,他们提出以“阅读”取代之,(注:例如,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前言中披露,他带着历史研究的动机着手写这本书,结束时却形成了一套阅读理论。)主张“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一切阐释都是误释”,(注:Paul de Man,J.Hillis Miller,以及Harold Bloom均直接或间接地表述过这一观点。)而且“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栖居在误读和误释的可能性之中”。(注:转引自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p.183.)在他们看来,从来就没有“客观”的阐释,只有或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误读。因为“文学”总是在语境中阅读的,而语境又并非“外在的”东西,因此文学总是由不同方式解读着,而且任何阅读或阐释都不能表达穷尽任何文本的意义。(注:就此观点而言,保罗·德·曼在《抵制理论》一文中的话最具代表性:“当我们提出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要依赖阅读行为时,意思是说……首先,它暗示文学不是透明的信息——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信息和交流方式是明晰地确立了的;其次,而且更有争议的是,它暗示对文本进行语法上的解码会留下一块不可确定的残余地带,其不可确定性不得不,但又不可能为语法手段所解决——不管此语法手段是经过多么广泛地思虑。”见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p.15。)
不言而喻,陷入悲观的是传统批评家,因为传统的批评学科是建立在“真”、“善”、“美”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上,以揭示、追求这些终极目标为己任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辨认出来,后者正是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家的态度和立场。耶鲁学派主将保罗·德曼在解读卢卡契、布朗肖、普莱乃至德里达等人的著作时就不遗余力地证明:“每个批评家总不知不觉地在其公开的文学理论和实际阐释之间表现出不相符”,(注:转引自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p.186.)他似乎胜利超越了有明显中心倾向和超验价值标准的批评,创造了一种开明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他似乎依照解构主义文学论设想出了一幅批评实践图景,内心洋溢着自信。
然而,他们果能如其所愿吗?耶鲁学派的批评实践,能与其解构主义宣言保持立场一致吗?我们的回答是:否。从德里达的语言论到他的文学论,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语言、文学作为“此在”(presence)以及两者在“此在”层面所生发的确定意义的质疑。他借助于“书写”论提出了语言和文学作为“缺场”(absence)的可能,以及一种有关意义多元、不确定的假说。可是,这种宏观的思维构想与具体的文本讨论是不同的。就前者而言,语言既是“书写”的产物,也是“书写”场所和“书写”行为;既是“此在”也是“缺场”;人实际上生活在“书写”当中,不仅不能控制书写,反为书写所支配。而就后者而言,批评者关注的只能是显现出来的“此在”;即便有什么是不曾在批评文字中呈现的话,当它一旦为人所意识到,那它也就成为了具体的、确定的“此在”。因此,德里达对于“缺场”的关怀是不能用具体的文本批评予以实证的。如果批评家坚持把“书写”当作真理中心进行论证、加以确定的话,他恰恰就是违背了德里达倡导的解构精神。德里达对于这一点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德里克·阿特里奇这样转述德里达的话:“解构主义实际上是矛盾的。(它也是不可能的,德里达习惯这么说——而且,它根本不存在。)”(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p.26.)可见,耶鲁学派在批评实践中根本偏离了解构主义立场。他们忘了,依据解构原理,解构主义学说本身也是自相矛盾、充满自我差异的,它也逃脱不了不断自我解构的命运。
耶鲁学派热衷于通过解读“文学”或“批评”文本,论证文本因自相矛盾、自我解构而不可读(unreadable),(注:在阅读中,我们总会发现语言被搁置在隐喻和换喻、修辞和逻辑的拉锯战中,我们因而无法在语法义(字面义)和比喻义之间做出抉择,陷入困境——这是保罗·德·曼在《盲视与洞见》和《阅读的寓言》二书的主题之一。)或者证明文本是早已解体的碎片。(注:“解构不是肢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证明它已经将自身肢解了。”见J.Hillis Miller,"Stevens' 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II",in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Robert Con Davis,Longman,New York & London,1989,pp.416-427。)并且,在耶鲁学派的词典中,批评家是一名创造者,是文本解体过程的参与者和旁观者。(注:“通过这种重新追踪的过程,解构批评家试图从所考察系统找出反逻辑因素,从所考察文本中找出能将文本拆开的线索,或者从整座建筑物中找出松脱的石块,从而将大楼推倒。”见J.Hillis Miller,"Stevens' 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表面上看,这是解构主义的矛盾观、意义不确定论在实证过程中的延续和贯彻,是“解构语言观—解构文学观—解构批评实践”的完成。然而,深入考察下去,我们不难发现,一、解构主义意义不确定论并不等同于“不可读”的结论;二、解构主义所说“解构”实际上就是“结构的结构性”发生作用的过程,是一个无休止的“解构—结构—解构……”的过程,所以,没有只解体而不结构的文本;三、一如解构主义的“书写”论和“异延”论所展示的,解构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即是反对形而上的协调思维、整体思维,欢迎矛盾双方共存于一体。但需要注意的是,解构思维所提倡的“矛盾”或“自相矛盾”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更不是一个超验的概念。它是自我非同一的“事物”或“概念”生生不息地变化、相互转化(即含有“结构性”功能的解构活动)的“成果”,永远处于动态之中,不可实证。因为,实证之,无疑是把矛盾的双方钉死在此在的位置上,同时也把自己拖入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概念化。而这恰恰是解构所要消解的。耶鲁学者执着地坚持对“自我消解”、“矛盾”进行实证工作,无异于堕入了自掘的陷阱。
简言之,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虽以解构的术语装备自己,实则违背了解构哲学和解构逻辑。我们可以对比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批评模式,从中得到具体的认识。
1.意义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与不可阅读性(unreadablity)
从语言观念上来讲,意义不确定论是符号、结构消解的必然产物。正如德里达在《符号、结构和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中所示,一旦我们认识到“结构的结构性”才是结构“原初”的“本质”,我们便会发现符号和结构并非封闭和自我同一的整体,它们只是差异嬉戏的园地。语言的意义由此发生无限的推移和播撒。
从解构策略上来看,意义不确定又是“增补”(supplement)发生作用的结果。增补作为二元对立范畴之间互渗、互动、互换的“原动力”,既能擦抹概念和范畴的整体性和稳固性,又能擦抹二元间的对立关系。受到擦抹的二元,便是意义不定的因素。解构的基本程序,颠倒(二元的次序)——揭示(形而上二元间存在的等级差)——解构与重构(消解对抗,构建新“概念”和新关系),实际上就是以“增补”观念为依据的。为此,利奇才总结说,“解构者的目的就是生产这些不可确定物(undecidables),跟踪它们持之以恒的运作,并将跟踪贯穿整个文本。”(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p.180.)
因此,综上所述,意义不确定性是形而上的整体性和自我同一性观念受到消解、具有暴力色彩的简化性逻辑受到解构以后语言所显现出的意义多元共生、共存的可能性。它是语言“活跃”起来后的状态。
就意义不确定性而言,德里达《柏拉图的药品》(注:《柏拉图的药品》("Plato's Pharmacy")集中展示了德里达的意义不确定说。文章缘起于古希腊语中“药”(pharmakon)一词的多义性,它既指治病救人的药品,也指毒药。见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63-171。)一文的分析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在任何语境下,一个词语不可能一次显现其所有具有差别的意义;二、在任何语境下,语词不可能只完整显现一种意义。也就是说,具体的一次性的阅读语境加诸于语言的自我差异结构上,造成的情况是,文本不可能完全不可读,因为文本的多义不可能全数自我显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因为任何意义都是蕴含矛盾、差异的。意义不确定,就是位于这两极之间的多元状况;意义是“活动”着的,此在和缺场的相互转化维系着它的生命。
意义不确定性既然是动态的,它就是消解权威、促使种种意义产生和消失的力量源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意义不确定性并不消除理解的可能性,它消除的只是形而上的终极性理解。它告诉我们,每种理解都只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注定要在显现之后消亡,要在显现当中孕育“异类”、展示“异类”,所以,从反中心、异质和非真理性这一层面看,每一种理解都是误解,能孕育另外误解的误解。有批评家说,“就是书写的自我差异性和不可确定性,使种种可确定差异的产生成为可能”,(注:Niall Lucy,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 duction,Blackwell,1997,p.117.)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从意义不确定论看不可阅读论,两者相冲突之处一目了然。
保罗·德曼一方面宣称,“语法/修辞这一对要素,当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因为它们绝不排斥对方……”,(注:"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79.p.12.)然而,在对普鲁斯特的分析中,他又赫然把两者对立起来:“在我所说的语法的修辞化和修辞的语法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差异。前者,在犹豫也即在不确定中结束,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使我们在两种阅读方式中做出选择;而后者,却似乎抵达了某种真理,尽管是经由暴露一个错误,即一种虚假的矫饰这种否定性方式达到的。”(注:"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79.p.12.)他把语法/修辞视为对立双方,并完全同时显现,因为,“在符号学中出现修辞语法化的情况下,我们便像在……语法修辞化那种情形一样,在同一种被搁置的无知状态中结束。”(注:"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79.p.12.)保罗·德曼的“不可读”指的是文本中语法/修辞二元对抗给读者造成的无知、无解,其学说自然也是二元对抗思维的成果。显然,这和意义不确定论根本不是一回事。意义不确定性不承认有“二元对抗”,而只承认有变化、运动着的差异;意义不确定性永远体现于表意因素或此在或缺场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转换之中,不可能冻结成二元对抗时相持的静态,因此,“不可阅读”看似强调多元,实则是旧思路的产物,与意义不确定性相悖。
关于“不可阅读”,米勒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在《史蒂文斯的石头和作为治疗的批评》一文中,他认为批评阅读的过程是一个生产失败的过程。读者总是试图把自己的阐释建立在文本内的因素上,然而,他总会发现自己的立论依据将在修辞的自由嬉戏中全盘崩溃。意识/文本(主观/客观)、修辞/逻辑等无疑又是米勒构筑的二元对峙。阅读的结果,说是读者的失败也好,是文本的自我崩溃也好,总之都是二元间爆发战争的结果。可见,米勒和保罗·德曼的批评思路殊途同归。
2.谁是创造者——批评者还是语言?
批评是一种创作活动,其创造性并不比文学低下,这又是解构批评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且,正是这一主张,引发了批评宿将艾布拉姆斯和J.希利斯·米勒间的论战。有他们的论文《解构主义天使》("The Deconstructive Angel")和《传统与差异》("Tradition and Difference")、《作为寄主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Host")为证。依照德里达的文学论,批评是创造这一断言应该是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因为依照广义书写的运作原理,语言本身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产和创造活动。只是问题在于,就批评而言,谁是创造者?是批评家还是语言?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解构主义者说过,批评家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操纵语言的批评创造者。相反,他们倒是经常不厌其烦地解释,语言和文本本身是有创造性的,是无穷尽的,任何人都只不过读出了其中的万一。以耶鲁学派为例,不管耶鲁批评家们如何阐述批评主张、执行批评行动,在他们看来,语言和文本总是“大”于人、“高”于人以致于不可完全把握,读者或批评家注定要受语言和文本的摆布。也正因为如此,在谈及批评者的阅读和批评活动时,他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只能”(can only)这样的句式,以表明人在语言面前的无奈。
可是,批评是批评家随心所欲开展的“创造活动”,这又是解构批评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那么,为什么解构主义者从不曾自我标榜的东西会成为自己的“罪名”呢?分析起来,这恐怕跟解构批评家宣扬的“误读”论有关。其一,听到“误读”,人们总会望文生义,以为这是相对于“正确阅读”的“错误阅读”,殊不知在解构的词典里,“正读”和“正解”并不存在。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一切批评阐释都是误释,因为一切批评阅读和写作的经验都有别于阅读和写作的对象,而且在其叙述成形的过程中也必然有别于自身。也就是说,从差异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误读”是无法避免的。其二,“误读”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这是批评家有意为之、故弄玄虚的结果。事实上,如前所述,“误读”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语言发生踪迹运动,其踪迹痕与我们的无意识及意识展开对话和交流,都由不得我们控制,那么,踪迹痕中的差异、意识和无意识的差异将我们推向误读,也就在我们的力量之外了。
不过,“误读”之说诚然需要澄清以正视听,人们对解构批评的误解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也就是说,解构批评者的确是需要为人们的偏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这里,问题关键出在一些解构批评者的“误读”和“误释”上。
原则上讲,在误读问题上,人们没有选择权,可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误读和误释不应是有心为之的故作之“错”,而应当是文本与人在某一时刻对话的自然书写。然而,不可否认,不少自称解构的批评家就是借着无意识的误读和有意识的“误读”不可分辨、不能证明之机,肆意安排文本的指意,创作“误读”,从而生产出玄而又玄、甚至不知所云的批评文字来。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对这些“创造性”批评的反感,恰好验证了解构主义者的主张——语言有自己的指意之道,不是人可随意摆弄的。那些自以为可以借“误读”的旗号来张扬自己的创造力、掩盖自己的贫乏的人,正好掉进了语言为他设置的陷阱。
3.批评家的角色
耶鲁批评家为自己设计的角色是从事实证工程的角色。他们企图依照“解构主义语言观—解构主义文学论—解构批评实践”的思路,将解构主义进行到底。然而,在设计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忘了解构主义主张的差异和自我差异活动也会发生在解构主义自身体内。差异抵制自我同一(self-identity)、自我此在(self-presence),那么它必会抵制实证,所以,对于解构思维而言,想将“文学论—批评模式”的一致性维持到底,是不可能的。
认识到“证明解构主义”不可能之后,我们便可以安然地进行阅读,完全不必像耶鲁学者那样把“多元”当作一个绝对理念时刻放在心里,殚精竭虑地力图论证它。没有对“多元”意念的暂时中止,就不可能有临时性的结构产生;没有结构,也就没有下一次的解构;没有解构,也就没有多元的产生。对于结构—解构这种相矛盾又相依存的关系,德里达深明其理,因此,他的大量著述也正是在结合了“意义无限的视野”和“文本的临时之锚”之后写出来的。(注: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6,P.lxxvi.)正如斯皮瓦克所说:
解构是一种永久自我解构的运动,异延栖居其中。没有任何文本是完完全全解构性的(fully deconstructing)或者是彻底被解构了的(deconstructed)。然而,批评家暂时搜集形而上的批评资源,进行其自称为某一次的(one)解构行动。(注: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6,P.lxxviii.)
四、结语
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文学论,决定了批评实践与之断裂乃是必然。因为,一则,任何批评实践,必然是由有迹可循的逻辑线索所贯穿的实证活动,而且必然是某种整体观的产物,而解构主义文学论是无法提供这些条件的;再则,解构语言观或文学观体现的自相矛盾可以勉强借形而上学的躯壳、“反形而上”的逻辑和曲折迂回的语言令我们领悟,但它与实证精神的矛盾却难以用实证的语言和文体来表达。因此,与其说解构主义是一种批评理论,不如说它是以批评“批评”为目标的,因为“批评”意味着对意义做出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确认,而这在解构主义看来无疑是藉着自我授权的过程抹杀多种可能性。对于批评实践者而言,解构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就体现在这里。
不过,正如德里达就“结构的结构性”所说的,当作为实体的中心消解之后,中心成为一种功能,在结构的不断形成和消解运动中发生作用。我们的意识活动离不开中心功能,中心功能也是我们抛不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解构主义文学论以后,我们迎来的是“误读”观念对批评学科的“增补”,而不是解构名义下的另一种实证体系、中心体系的建立。一切想把解构主义思想落实在具体实践中、想以批评实践来证明解构思想的合理、合法性的行为是徒劳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解释了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批评的窘境:他们为什么既不能得到以阅读常识和阅读经验为判断标准的普通读者的接受,也不能得到批评界的理解和推而广之。
此时,如果我们把解构主义批评所带出的“结构—解构”问题和解构主义以后兴起的批评模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便会对解构主义的前景获得更深一步的了解:不管是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批评,都是首先针对某种意识形态中心、性别中心的解构,其次是思想再建构。尽管再次构建的过程中也许又会出现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拥有解构思想武器的人们,必然又会将其推向解构,一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前面两代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批判、霍米·巴巴对赛义德的批判一样。正是因为与解构主义哲学保持着既联系又断裂的立场,以“后”自居的批评理论才得以在批评实践领域立足。解构主义或许不会永远是思想界的主流,但它的诞生,就意味着它再不可能全然从舞台上退出。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幕后的声音,将永远对前台的演出提出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