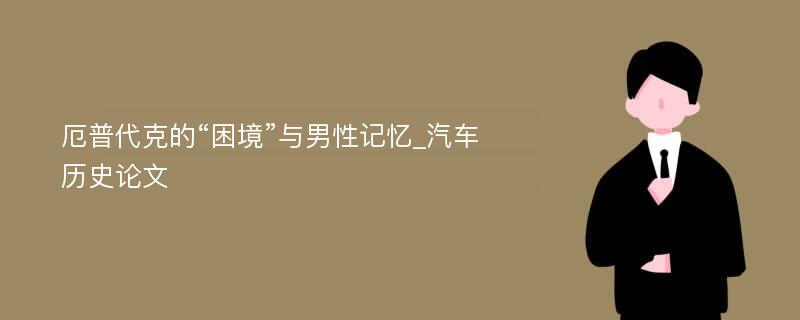
厄普代克的《困境》与男性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男性论文,记忆论文,厄普代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3-0037-06
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困境》(“Unstuck”,1987)的情节简单而生动,叙述的是一夜大雪过后的清晨,新婚不久的马克和妻子的婚姻生活出现了困境,相比之下,两人合作将轮胎卡在路边阴沟里的小汽车从齐腰的雪堆中解脱出来的成功经历给他们带来了近乎“性快感”的愉悦。《困境》是一篇富有幽默感的短篇小说。评论家和学者对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关注得不够,但《纽约时报书评》称这篇小说是关于处在“磨合”期新婚夫妇难以驾驭家庭生活和汽车的幽默。(Robinson:1,44)普列策文学奖获得者艾莉森·卢里在《纽约书评》中赞扬小说对性爱的描写幽默而且含而不露,一直到结尾才抖出“包袱”。(Lurie:3-4)本文认为小说的幽默在于尽管婚姻生活不美满,夫妻两人可以共同努力最终将汽车从雪堆里解救出来而达到和谐。在幽默的过程中作品揭露和描写了男性幻想:叙述者带着男性注视讲述婚姻生活,但出现不和谐时,丈夫可以通过汽车解困的过程,夸大、炫耀男性的自我,以梦幻般的满足弥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用男性的记忆/时间去挤占、吞噬女性的身体/空间。①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迷失在男性的虚幻世界里,并将男性快感强制性地辐射到读者身上——要么男性与马克分享名不副实的阳刚,要么女性渴望这一因男性匮乏而“膨胀”起来的虚幻壮伟。马克似乎要将这一“壮举”与整个社区甚至包括随车路过的男人共同分享,男性话语像无意识一样已被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本文从露丝·伊瑞格瑞的女性批评的角度来揭示这一主题。
米歇尔·福柯曾指出19世纪的特点是着迷于历史,而现今是“空间的时代”(epoch of space),现时的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的结点与历史、时间的延续对立起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Foucault:22)时间与空间的对立还用来比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自从柏拉图以来,女性一直被男性社会当作是身体(空间)的化身,而男性是灵魂(时间超越空间)的象征。(Spelman:109-31)汤姆·米切尔对这一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威廉·布莱克的名言“时间如同男人,空间恰似女人”(Time is a man,space is a woman)将女性看成是被动、摆设的空间,完全剥离了历史、时间的维度。因为语言和文本是男性的一统天下(笔成了阳物的代名词),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1979)一书中设问女性如果不就范男权规训的话,应该以何种方式去书写自己的文本。米切尔提出的方案是运用画笔,即(像简爱一样)用对空间的观察、描绘和叙述的方式来展示女性心里世界,以求得从男权压迫中解放出来。(Mitchell:93,97-98)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评论更多聚焦于女性身体作为空间来研究。如凯瑟琳·柯比将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的建构看成是一段“时间过程”(temporal process),是男性话语(历史)对女性作为文本化的二维空间的书写,她主张将女性主体的形成放置在三维空间的个人(包括身体在内)的体验的框架之中。(Kirby:178)②如果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是时间“雕刻”空间的话,内森·斯托默从针对堕胎的男性话语中归纳出女性身体被“书写”成两种空间形式:(一)女性身体被“降解”为生育器官,(二)女性身体空间被“擦除”(erasure),以张扬胎儿的独立性。(Stormer:111-12)换言之,男性话语像历史话语一样(历史事件是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裁截出来的时间碎片),(Lefebvre:110)对女性身体的空间进行“书写”(书写也是一种空间分割)、“涂抹”和“裁截”。
厄普代克的《困境》揭示了男性历史或记忆(时间)怎样“侵占”女性身体(空间),将其沦为男性话语的“书写”场所。
小说前半部分叙述的是婚姻生活问题,以马克在昨夜做的梦开头,点出了他婚姻生活陷入的困境。在梦里,他想在调色板上调出一种泥土般的灰色,总是不能如愿。这种梦境的灰色调笼罩着他现实生活中的新婚生活:昨夜的房事妻子又一次没有达到高潮。马克是作橱窗装饰工作的艺人,也是爱门面的人。家里的玻璃窗上装饰着他用棉絮做的窗花,窗外也是一片大雪耀目的白色景象:“套上白皑皑‘假发’的屋顶、长着冰凌‘胡须’的屋檐挡风板、像圣诞贺卡上的常青树、挂着冰霜的棒棒糖一样的‘停’字交通牌。”(Updike:62)室内外的“装潢”景色恰好烘托了人物需要掩饰的心情——很明显,夫妻俩想尽量“装潢”昨夜的不快,都想在表面上粉饰一层喜悦。妻子要做一顿早餐,有华夫饼和咸肉,尽管咸肉放在冰箱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说明平时的早餐只是一般对付而已。但今天的早餐像过节一样丰盛,马克认为妻子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冲淡因昨夜的欠缺带来的苦涩。妻子说她做华夫饼是为了让丈夫高兴;虽然烤糊了,马克还是赞不绝口。他本不想喝滚烫的咖啡,但是为了取悦妻子,马克在出门之前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两大口。
夫妻俩如此相敬如宾,想极力掩饰自己不愉快的心情和减轻对方的精神负担,从头到尾闭口不谈昨夜不和谐的回忆。但不等于说对此各自没有内疚或怨言,马克暗暗责怪自己昨夜没让妻子如愿,要不她不至于会拒绝去教堂做礼拜,“如此没有宗教信仰”。对昨夜的记忆犹在,只是他们在别的方面找到了撒怨气的地方。马克抱怨家里没有车库,如果买了牧场上的房子,新车就不必放在露天而减少车的使用寿命。现在的房子因为太大、太旧,缺少隔热保温层,使马克联想到家里“样样东西都缺点什么”,似乎这正是他们新婚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样,妻子也抱怨华夫饼铁锅质量不好,总沾锅,只字不提昨夜夫妻的欠缺。
昨夜大雪过后,早上的市政扫雪车把沿路的积雪扫成了齐腰深的雪堆,把马克停在路边的爱车困在了雪堆里。马克自责昨天晚上没有将车停放好,说明自己的无能;(Updike:65-66);马克似乎将家庭生活的不和谐与停放汽车和自己的无能画上了等号,将“家丑”抖落在外,让人见笑了——他想象街对过的邻居女士在嘲笑他的无能。因此,马克要纠正自己的失误(erase his error),决定将爱车从雪堆里解救出来。这一举动对他来说,一方面可以纠正停车不当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能挽回做丈夫愧疚的面子,省得邻居嘲笑年轻丈夫和年轻车主的无能了。当邻居女士进屋之后,一辆黄色卡车从路边经过,马克倚在铲雪的铁锹上,向坐在卡车后面的几位男士频频招手,他和他们“似乎都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同志”。马克与其他男性作为战友的认同感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的故事是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夺战”。
在将要发生的“争夺战”里,恰恰是男主人公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小说的后半部分讲述的是马克夫妇俩一起将汽车从雪堆里一边驾驶一边推出来的经过,故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主观的叙述视角,描述的整个过程只倾注了马克一人的感受;而妻子没有与丈夫分享叙事视角,她先在车外推车,后来她建议跟丈夫交换位置在驾驶室里开车。不管妻子处于哪个位置,叙述的视角总是向丈夫聚焦。马克推车的全过程反映的是他作为男人的性快感节奏,他自己的“愉悦”触及到了妻子身体内部,以男性的记忆在女性身体的深处书写女性的沉默,用男性历史挤占女性空间、吞噬女性“话语”(herstory)。③
如同小说开头的梦境一样,故事里先后出现了几个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意象,(Freud,1997:233-34)④扣住了小说隐讳的性爱主题。先是象征女性意象的烤华夫饼用的铁锅,妻子抱怨它沾锅,而马克说它应该是自动润滑的(self-greasing)。这一细节似乎暗地导出了缺乏“润滑”是妻子房事不悦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暗示了丈夫需要对妻子有更温馨的呵护和夫妻俩更密切的配合(这似乎正是妻子责怪马克的地方)。这又引出了铲雪用的铁锹这个富有男性意象的器具:当妻子与马克交换位置要丈夫推车时,妻子将铁锹插进土堆里,让铁锹“直直地立起来”(Updike:68)——似乎在比喻他们需要更好地配合、交换更合适的身体位置和姿势,便于丈夫达到激昂亢奋的状态。当然,故事里最重要、最直观的男性意象当属马克的爱车了,小说中关于性爱的暗示都是通过马克开车或推车的过程实现的。⑤当马克在驾驶室开车、妻子在车后推车时,性爱的隐喻开始呈现:马克在一档和倒档之间猛力向前后拉动变速杆,他能感觉到车在雪堆里向前和向后抖动,但只是在雪堆的下坡凹陷处越陷越深;他估计妻子在使劲推车,但马克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尽管透过后视镜马克看到妻子此刻也十分专注、全力投入,她的脸涨得发红,头发也散乱了,对丈夫说“你快行了”(You're closer than you think)。交换位置之后,由妻子驾驶。根据马克的指导,妻子要朝马路的中央开,“要轻轻地向前向后使劲,向前,向后,不要慌。”(rock it back and forth gently,back and forth; don't panic.)就在他们要继续时,马路对面的邻居女士又出现在门厅前,像是要在一边观看,马克甚至感觉到所有邻居都在伏窗围观。马克背着被众人围观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但在妻子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满足,同时也没有让妻子失望:
她把车往后使劲开,到头时,她又给足油向前猛进。这时,他感到了他们在向前推进,真是好样的!他使劲推;他们稍息一会;车又再次一进一退地进行,他使劲地推,以至于下身两边的肌肉绷得都疼痛了。在他们试图掌控的车体惯性当中,马克似乎感觉到他自己的力量触摸到了一种微妙的反应,是一种极深处的女性闪动。(Updike:69)如果这仅仅是马克的快感萌动的前奏,接下来的体验却是因运力良久而集聚的张力以及最后激情爆发的高潮释放,捕捉到了经历男性性爱的“张力—释放”(tension and release)节奏的全过程的那种感受:
车轮又在飞转,在车轮摩出来的雪槽里车在向前挪动,在他推力的支撑下,车体压在他身上的重力似乎即将解脱。“再来一次,”他喊道,他的双腿在颤动……车后轮玩命地飞转,带出的雪沫不断朝他的下半身飞洒,他意识到车轮蹭过了一道边缘。雪堆被突破,已经不必要继续用力了,顺势推车只是出于惬意给他自己增添一丝甜蜜、不可抗拒的动量。他们终于解脱了。(Updike:69)故事在结尾时才提到马克的爱车是一款引擎为八缸的高排量小汽车,跟它相比,在车里的妻子“看起来是那样的瘦小,似乎不可能摆弄这么大的一件东西”。(looked much too small to have managed so big a thing.)马克高呼“太棒了!”他跳到被车轮碾过的雪堆上,飞舞着手里的铁锹。爱车和铁锹并用来张扬男性的“壮伟”,“太棒了”这一褒奖不知是用来称赞妻子浪漫的操持功夫,还是自诩马克“膨胀”起来的男性自我,总之,此时的叙述者在羡慕马克和他的爱车和铁锹。最后,夫妻俩温情脉脉,像是在房事过后交换相互欣赏的心得:他坐到妻子身边,车内开着暖气,很温暖,他还在大喘气,但还是再说了一遍“你太棒了!”她笑着回答说“你也是!”
伊瑞格瑞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将男性性爱视为人类两性性爱的标准,并且这一男性模式,即“张力—释放”的模式,被男性转变为主导人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普遍节奏,为了不断增加其张力的能量而违反自然规律,人类生活因此与自然失去平衡。(Irigaray:20-21,25)⑥按照这一思路,汉森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纳入了男性的生理节奏的轨道之中:经历高速交通、噪音污染和紧张的五天工作日的“张力”之后得到的是周末“释放”的回报。(Hansen:204)厄普代克的作品恰恰也将这一男性性爱模式套用在马克夫妇解救汽车的过程之中,并将看似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赋予普遍性的男性生活节奏和思维模式。在这种叙述的主宰下,女性读者在读马克夫妇的故事时也只能间接想象男性的性爱体验。⑦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就知道这是关于男性的故事,关于马克的故事,而女主人公被称为“他的妻子”或他的“女人”。第三人称主观叙述视角不关注她的感受和内心想法,读者只是通过马克的视角和感受才感觉到她的存在。女性角色被作品边缘化,女性读者也逃不了同样的命运:她们被迫降低自己的阅读品位,默认弗洛伊德论述的“阳物妒嫉”(penis envy)(Freud,1991:114,297-98),在钦佩马克妻子能干的同时,还会欣赏甚至赞誉马克硕大的爱车和长长的铁锹。
女性被边缘化还体现在她的身体空间被男性对历史的记忆所侵占。⑧虽然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的新婚蜜月不尽如人意,但是为了弥补真实生活中的缺失,马克将自己对性爱快感的记忆以隐喻的方式投射到解救汽车的机械过程当中:用汽车比作自己,用汽车突破的雪堆比喻女性身体,用梦幻记忆来替代现实生活。在故事的开头我们就知道激情之夜马克又一次没能让妻子满足,那么推车碾过雪堆所激起的冲动和快感应该主要是他对婚前性生活的记忆,甚至可能是对情窦初开时的更久远的记忆。男人对处女的欲望和恐惧参半体现了一个复杂的心理(Beauvoir:170-71),⑨如果马克从心理上还没有摆脱其恐惧的阴影的话,那么汽车突破雪堆时给他带来的感官上的快感和下身肌肉的疼痛也许是他久远记忆中复杂心理的再现。而且,那种“极深处的女性闪动”和雪沫飞洒、双腿颤动伴随着惬意和甜蜜的感觉不是他现时生活的真实,而是他对历史记忆的凝结。而这男性历史记忆的再现形式是建立在主宰女性身体空间和压制、掩埋、吞噬女性话语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厄普代克的《困境》中所揭示的男性梦幻记忆的根本之所在。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厄普代克对女性是同情的,他的不少长篇小说批判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揭露了在男性幻想中女性是如何沦为他者或商品的,并颠覆了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是欲望的主体和女性是欲望的客体的论述。见Rozette:74,Savu:22-48。
②柯比是在用“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观点批评“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强调除了话语对女性主体(subject)的建构有影响外,个人(individual/person)的体验或经历不容忽视,即女性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似的话语构建成的主体,个体的人不是文本化的“二维空间”,而是真实存在的“三维空间”(178-85)。
③有关女性话语(herstory)和男性历史(history)的讨论,见Ruthven:57-58。
④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认为带长柄的器具如棍子、树干、雨伞等和锋利、细长的武器如刀、剑、匕首和长矛等都象征男性性器;而像盒子、箱子、碗柜一类的容器和房间、船只等都象征女性性器官。
⑤小汽车被认为是男性力量和性的象征。活塞的抽动、踩油门时引擎进发的能量以及车体长条的形状等都给人带来性的“体验”和联想。见Spielrein:209-10; Peirce:230-32。
⑥伊瑞格瑞指出,与男性的张力-释放这一具有“重复、爆炸性”而又违背自然和谐的性特点不同,女性的性与自然和宇宙的韵律相连。像自己的生理特点一样(如身孕有固定的期限,而月经又有不断重复的周期),女性的性有较长的持续性和复杂性,它具有既固定又周而复始的“双重时间性”(dual temporality)的特点。为了摆脱男性的主导模式,确定女性自己的性身份而又与男性保持“非破坏性关系”(non-destructive relationship),女性要参与到语言和意象表达的话语中,与母亲及其他女性建立一种“跨主体性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⑦肖沃特(Showalter)指出,女性在读作品时常常被迫认同男性经历和视野,因为男性经历被当作人类的普遍经历。费特里(Fetterley)也认为,女性读者经常被迫将自己的经历排除在外,认同一个与自己成为对立面的自我。(Culler:43-64)
⑧克里斯蒂瓦的“符号界”(the semiotic)源于拉康的“想象界”(the imaginary),并置于拉康的“象征界”或男性语言之前。(Kristeva:191)她关注前意识的子宫作为不可命名的“母体空间”(matrix space),用这一空间去“质疑历史、身份和语言的线性时间”。(Zerilli:116)换言之,克里斯蒂瓦试图用女性身体空间作为女性话语(herstory)去颠覆男性历史话语(history)。但是,泽力利更看重波伏娃(Beauvoir)提出的进入男性“象征界”的女性理论,为女性争得话语权,而不是像克里斯蒂瓦的理论那样将女性锁闭在母亲身体空间的“寂静”之中,因此而失去语言和话语权。(Zerilli:113-14)这一观点与伊瑞格瑞的“非破坏性”见解如出一辙。
⑨另外,男性对处女的欲望和恐惧交错的复杂心理被德里达看成是解构二元对立的很好的例子,即处女膜介于“女性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也因此介于欲望和满足之间”,(Derrida:212-13)模糊了内部与外部、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对立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