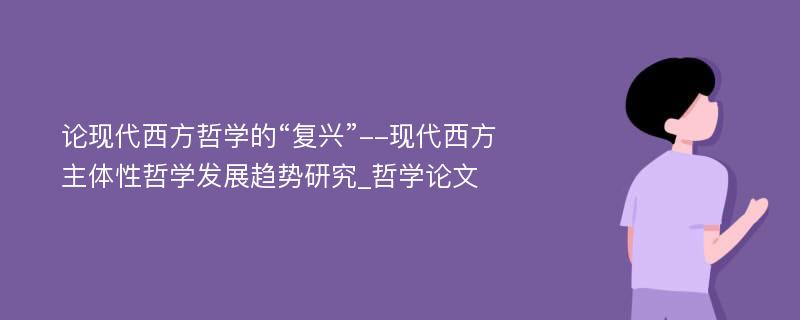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返老还童”——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返老还童论文,主体性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6X(2001)05-0090-06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现代西方哲学或现代西方主体性学说向何处去,成了国内外哲学学术讨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的根本目标在于:从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出发,对现当代西方哲学或现当代西方主体性学说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向“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演进作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富于历史感的阐释,并在回应萨特“马克思主义乃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观点中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史演进或历史转换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作出一点说明。
"Mar"和"clax"语义发生学的人学意义
宗教学的奠基人、东方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在阐述宗教观念形成的“历史道路”时,从语义发生学的角度,曾对印度古代语言中的"Mar"和"clax"两词作过极其认真的考察。现在看来,他的这一考察不仅对我们历史地和深层次地探究宗教的本质、起源和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我们历史地和深层次地探究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本质、起源和未来发展走势也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缪勒的考察,Mar的语义演进大体经历了如下7个阶段:
(1)仅仅和行为有关:当古代印度人作某些最简单的行为,如打击、摩擦、砍切时,总有某些“不自觉”的发音相伴随。这些发音最初仅仅是和行动相关。例如Mar的发音,总是伴随着磨光石头或擦亮武器等摩擦行为而出现的。而且当时完全是“无意”的:既不指说话者,也不指其他任何事物。
(2)同主体意识相关:然而,不久之后,Mar这个音,就变得有所指了,即指某位父亲要去工作,要去摩擦制作某种石制武器的动作。
(3)具有“指令”意义:后来,该词的发音带有确定无误的重音,并伴之以特定的手势,于是就更为明确地表明其含义是父亲告诉孩子们,在他去工作时,大家不要无所事事。
(4)用于“交谈”的“共同语汇”:Mar不仅作为一种指令,而且作为交谈的共同语汇,有了“让我们工作吧!”的意义。
(5)不仅意指行动,而且有区别地涉及到“不同的行为对象”:如果必须把有待磨光的石头从一地移到另一地,从海边移至山洞,Mar这个词不仅足以表示那些聚在一起、被磨平或变得锋利的石头,而且也用来指那些用来切削、磨平、磨削的石头。
(6)区别主体和客体:把Mar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分别意指“让我们磨制石头”和“用石头去磨”。最简单和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改变重音和改变语调。另一种办法是用指示性的符号,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代词根”,通过把“代词根”和Mar这类语音结合起来,从而把“这里磨”(指磨东西的人)和“那里磨”(指被磨的东西)区别开来。
(7)从以语音表达感知发展到以语音表达概念:Mar还超越“工作者”和“被工作者”这两个观念,在人的思想中提升出“工作”的行为观念,从而把行为的主体与行为的客体或结果区别开来。
从Mar的语义发生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几个重大的人类学意义:(1)行动在先。亦即知觉先于概念,行动先于知觉。(2)活动意识在先。亦即先有活动意识(即仅仅同活动相关),尔后才有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3)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意识和群体意识。如缪勒所强调指出的:Mar“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仅仅供一个人使用的词,而是一个为共同从事某种活动的许多人共同使用的词”(注: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讲演集》,纽约,AMS出版社1976年版,第189页。)。换言之,“实践活动”、“活动意识”与“社会意识”当为人类文化或人学的三个中心概念或中心范畴。
对于Mar语义发生学中透露出来的这些人类学意义,缪勒在讨论“语法的性”的问题时作了更明确的发挥。他指出,雅利安语的“最古老”的词都是“无性别之分”的。例如,当时,“爸爸”不是阳性词,“妈妈”也不是阴性词,“对河流、山岭、树木、苍天的最古老名词,也都没有任何语法性别的外部标志。”“然而,虽然没有任何性的标志,但所有的古代名词都表示活动。”缪勒还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名称都意指某种主动的东西。”他举例说,如果clax(足跟)意指“踢者”,那么石头也可称作clax。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之命名。如果脚踢了石头,也就是石头踢了脚,它们都是clax。在《吠陀》中,Vi指“鸟”、“飞者”,也指“箭”;Yudh指“战士”,也指“武器”,还指“战斗”。由此看来,至少在缪勒的眼里,原初的未经理性分析过滤了的主客浑然一体的生存活动不仅构成了人的意识的起源和根据,而且还构成了原始人类意识的全部内容。(注: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讲演集》,纽约,AMS出版社1976年版,第195~196页。)
逻辑思维的傲慢与僭越
应该说,缪勒对人类精神在其原初阶段以未经理性分析过滤了的主客体浑然一体的生存活动为其起源、根据和全部内容的历史特征的说明或解释,并非什么信口雌黄,而是有其比较充分的根据的,不仅有其语义发生学的缘由,而且也同许多人类学家的发现不谋而合。社会学的鼻祖奥古斯特·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曾提出了一个颇为著名的人学公式:“不应当从人出发来给人类下定义,相反的,应当从人类出发来给人下定义。”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不仅在其《原始思维》中提出了“集体表象”、“互渗律”和“原逻辑”(或“前逻辑”)概念,把原始人的思维界定为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而且在其《作者致俄文版的序》中还相当明确地指出:“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页。)应当说,列维—布留尔在该序的结尾所作的这样一种强调,对于人类,无论是现代西方人,还是现代中国人,意义特别重大。因为,人类在其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所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之一,便是把“原逻辑思维”尘封到了“人类学博物馆”,使“逻辑思维”成了人类唯一的思维范式,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活动变成了一种“无根”的“支离破碎”的东西。
诚然,逻辑思维在推进人类文明,促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中,确实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便孳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狂妄和傲慢,不仅把自己看作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把自己看作人类思维的唯一形式,不仅把自己看作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母,而且把自己看作完全自足自主的东西。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的这种狂妄与傲慢,从其产生之日起,可以说就遭到了人们的批评和抵制。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曾提出过关于“非存在”的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至近代,休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可以说是给了逻辑思维以致命一击。他的《人类理解研究》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一篇讨伐逻辑思维狂妄和僭越的战斗檄文。不仅如此,他甚至把“我自己”也还原成“这个或那个特殊的知觉”。此后,康德的理性批判活动及其对“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的划界,虽然在形式上较之休谟有所缓和,但他对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或“先验心灵论”)、“理性神学”(或“先验神学”)以及“理性宇宙论”(或“先验宇宙论”)的打击力度似乎并不逊于休谟。但是,哲学怀疑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挫败逻辑思维的僭越势头,反而促使其向前走得更远。
因为正是在休谟和康德之后,我们看到了逻辑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即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在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发现了罗素的《逻辑和知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另一方面,我们在哲学人本主义的现代发展中发现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如果说罗素在他的《逻辑和知识》以及其他有关著作中鲜明地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著名口号,开始把逻辑问题提升为哲学的根本问题;那么,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便更进了一步,把逻辑分析等同于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完全把哲学变成了一种“语言批判”“活动”。而且,也正是他们这些原创性思想的推动,促成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由实证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向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转变。卡尔纳普之所以被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在于他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年)和《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年)典型地表达了这一转变。至于蒯因,虽然有人因为他在1951年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而把他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异端,但是真正说来,把逻辑主义运用到“形而上学”领域,从而把它提升为一项哲学原则的恰恰是这位哈佛教授。这一点,仅仅从他的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注:其主要著作有《符号逻辑系统》(1934年),《数理逻辑》(1940年),《基本逻辑》(1941年),《逻辑方法》(1950年),《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年),《词与对象》(1960年),《集合论及其逻辑》(1963年),《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1969年),《逻辑哲学》(1970年)。)
至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对于人本主义哲学的规范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诚然,对于胡塞尔本人来说,《逻辑研究》只是其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过渡。然而,对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发展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却不是他的先验现象学,反倒是它在《逻辑研究》中依据逻辑主义阐述的描述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主义”尽管偏离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尽管对胡塞尔的“本质”观念作了重大“修正”,但毕竟是在“修正”过的胡塞尔的描述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毕竟是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而海德格尔对描述现象学的“修正”,对胡塞尔现象学从“观念论”的解放,对人类经验本质结构的着力澄明,以及对“被抛在世”和“筹划”概念的系统阐释,一如德·布尔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又“构成”了以萨特和梅劳—庞蒂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的“理论起点”。(注: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文版前言”第3页。)
现代人类精神的“归根”意向
中国古代大哲人老子曾经深刻地指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又说:“反者道之动。”(注:《道德经》第55、40章。)这差不多可以看作事物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现在,既然逻辑思维经科学主义思潮和哲学人本主义思潮推向极致,则它便势必走向反面,并因此而促成现代人类精神“归根”意识的萌生或“前逻辑思维”的苏醒:一方面促成了“群体意识”的苏醒,另一方面又促成了“社会实践意识”的苏醒。现代西方哲学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向“历史主义”或“对话主义”的历史演进无疑是这一“回归”或“苏醒”的一个突出表现。
众所周知,逻辑经验主义(逻辑主义)虽然于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哲坛上一度独领风骚,但是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很快就让位于“历史主义”。波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向正处于极盛时期的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挑战。他把自己的科学哲学称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宣布它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什么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而是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即“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注:参阅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库恩则在“历史主义”的旗帜下,不仅反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逻辑”,而且还进而反对波普的“知识的逻辑”。他之所以要向任何形式的逻辑主义宣战,乃是因为,在他看来,科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同科学史以及“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排除科学史和社会学的方法论都是不可能对科学发展作出恰当的解说的。我们知道,库恩的“科学发展的模式”的根本目标和重大意义正在于用科学之“常规”形态与“革命”形态的互存互动的“历史”来解说科学理论(“范式”)的“历史”的发展。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锋芒所向也是直指逻辑主义的孤立的“先验个体”的。库恩在其《基本的紧张状态》一书中鲜明地指出:“传统的科学方法讨论一向寻求这样的规则的集合,它将允许任何遵守规则的个人产生可靠的知识。相反,我一向坚持的却是:虽然科学是由个人来研究的,它却本质上是集体的产物,不提及产生它的那些集体,它的特殊的效力和它怎样发展起来的方式都将不会被理解。”(注:转引自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而且,在库恩看来,离开了他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他的“范式”概念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对于库恩来说,所谓“范式”不是别的,无非是“一个科学家集团的一切共同的信念”。(注:转引自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这就把逻辑主义的两个根本缺陷——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先验主义——极其鲜明地揭示出来,从而为在同科学历史(乃至科学实验活动)和科学群体(乃至人类社会)的关联中探讨科学发展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科学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能。这是库恩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作出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诚然,库恩之后,还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如汉森、图尔明、费耶阿本德、萨普、夏皮尔以及布鲁斯、巴恩斯、埃奇、默顿等,对逻辑主义思潮作了批判和抵制,对科学哲学走上注重“群体意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非逻辑思维”或“前逻辑思维”的“回归之路”作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但是,无论如何,在库恩那里,科学哲学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业已形成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上述运动虽然有其外在动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内在矛盾或内在困境酿成的。我们知道,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思想虽说有两个:“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但归根到底在于它的“证实原则”。因为“意义标准”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证实原则”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逻辑主义的内在矛盾或内在悖论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首先是“意义标准”的证实问题,如果“意义标准”能够“证实”,则它便不再成其为“意义标准”了。其次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的“证实”问题。波普之提出“证伪主义”,其根本宗旨正在于化解逻辑实证主义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处境。但是,正如“证实主义”不能解决全称命题的“真理性”一样,“证伪主义”也不足以解决特称命题的“真理性”。而库恩的历史主义、萨普和夏皮尔的新历史主义以及布鲁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无一不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救治良方的形象出现的。
与科学主义思潮的上述哲学运动相平行,当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也经历了一个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到“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演进过程。如所周知,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形态)的重要支柱,形成了气势极其磅礴、影响甚为深广的所谓“现象学运动”,但是到20世纪下半叶,情况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胡塞尔的现象学虽说依然有其生命力,但却越来越受到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挑战。我们知道,胡塞尔的先验主义或逻辑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之把“先验自我”(“先验主体”)放到“制高点”,在于它之强调“自我中心主义”。而对胡塞尔的这些中心观念的批判,换言之,对胡塞尔封闭性的“个我”的消解,恰恰构成了后来形形色色的“对话哲学”或“历史主义”的“理论生长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反对自我独白、强调你—我对话和你—我关系的哲学。正如库恩的一项重大功绩在于把“科学历史”引进科学知识的发展模式一样,伽达默尔的一项重大功绩也正在于把“历史意识”引进了哲学的解释模式中。而伽达默尔的基于“历史意识”的哲学解释模式要突出和强调的也无非是两个东西:一方面是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因而“永远不能”如胡塞尔所说的“在自身的知识中达到领悟”),另一方面是个我同他我的内在相关性,或解释主体的“处境性”。离开了解释主体与解释对象“之间”、文本与当下“之间”、处于解释状态中的你与我“之间”的张力关系,任何解释都是无从发生的。(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强调:“整个‘之间’便正是解释学的真正位置。”)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对抗中,当代西方思想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同,它要处理的中心问题,并不是一般的意识结构问题,而是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拯救问题,特别是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分化”问题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他同(卢卡奇和阿多诺的)“意识哲学”的决裂,从方法论上讲,也是同胡塞尔的先验主义或逻辑主义的决裂。因为他的这一决裂意味着从“先验主体”走向“社会化主体”,从“孤独主体”走向“交往主体”,从着眼于人的“主体性”走向着眼于人的“主体间性”。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上述从逻辑主义到“对话哲学”或“历史主义”的运动,归根到底也是由其内蕴的无从消解的矛盾酿成的。为了消解西方近代主体性学说的经验主义色彩,为了把逻辑主义的内在性原则贯彻到底,当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也就在所难免地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先验主义)和极端的个体主义。(注:参阅段德智《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前景》,载《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这样,现代西方的主体性学说也就在所难免地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困境,遭遇到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难题,如“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中的)先验自我的二元对峙”以及“对‘他我’的确认”等等。(注:参阅段德智《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前景》,载《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无庸讳言,胡塞尔现象学的后继者,如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领悟到胡塞尔的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的理论困境,并为摆脱这一困境作出过种种积极的尝试。例如,既然在他们看来,传统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陷入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自我与他我、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与认识可能性的二元对立,最根本的乃在于他仅仅从认识论的立场上来审视人的主体性问题,那么他们超越前人的决定性一步便是走出认识论进入本体论。海德格尔不仅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本体论”,而且称作“基本本体论”。他的“基本本体论”的基本范畴是“此在”,而“此在”的基本规定性则是“在世”与“能在”。既然如此,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换言之,“此在”与“世界”、观念与现实也就在“此在”的存在方式和筹划过程中自然地统一起来了。萨特虽然区分了“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但他既然把人的意识宣布为虚无,则意识对“自在存在”(物)的依存性和统一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都非但没有成功地解决西方主体性思想中“自我”与“他我”的关系问题,反而使二者的关系更趋紧张。海德格尔虽然也讲“共在”或“人们”,但他却把“共在”(人们)理解为一种与“此在”相对立的“非本真的存在”。萨特虽然力图超越“唯我论的障碍”,承认“他人的存在”,承认作为共同活动“整体”的“我们”,但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表达了“他人即是地狱”的观点。这说明不从根本上摆脱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的理论束缚,是不可能妥贴地解决“自我”与“他我”、此在与共在、“自为存在”与“他人存在”的关系的。伽达默尔的对话式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示
既然我们在前面两个部分依次解说了逻辑思维在近现代哲学中的傲慢和僭越以及现当代西方哲学或现当代西方主体性思想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到“对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历史演进,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历史演进”,这一“演进”是一种暂时的文化现象呢,还是具有某种比较恒久的价值或根本的意义?谁能保证这一“演进”不是一种“喧嚣一时的新闻”呢?
这一问题由于我们是当代人,由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局中人”,就变得愈发尖锐了。但是,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我们毕竟有诸多对付主观主义的方法或武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无疑属于这一类型的方法或武器。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被称作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历史的长流虽然总是挟着隆隆涛声和泛着阳光的浪花,但历史本身却是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我们虽然拥有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三种时间概念——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但只有依据长时段概念,我们才能窥到历史底部的沉默之海,达到历史的内在底蕴和真实本质。正是出于对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理论的认同,我们才在本文的开头对人类精神作了一番“考古学”研究。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使我们看到了现当代西方哲学或现当代西方主体性学说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向“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恒久性意义和价值,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体悟到了“前逻辑思维”并非完全过去了思维方式,人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人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乃至首要的内容。
我们的上述观点不仅可以从人类精神的“文化考古”中得到支持,而且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佐证。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现当代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这些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例如把它简单地与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或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等等量齐观。因为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始终如一地把人的社会性或群体性,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放在人学中的首位,以之为其社会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特别地注重或强调人类逻辑思维与“前逻辑思维”的互存互动或辩证统一。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秘密的话,我们不妨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根本秘密。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佐证时,我们不妨回到萨特曾经强调过的一个话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问题。我们知道,萨特在195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对于一种方法的探求》里对此谈得很精彩。他写道:“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象刚刚才开始发展。他还十分严正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一切“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无非只是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中去,重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罢了。18年后,萨特在其《七十岁自画像》这篇近乎“盖棺论定”的“自叙”中依然坚定地重申了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对萨特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究竟作何理解呢?马克思主义既是它所在时代的产物,它就势必内蕴着许多属于该时代的特定的内容,它就势必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哲学体系一样,内蕴有许多对于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来说将要不断过时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哲学体系,它虽置身于理性时代或逻辑思维独霸天下的时代,却能独具慧眼,看到并注重人的“前逻辑思维”,从而突出强调人的社会性或群体性,突出强调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存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了它的特殊的魅力,使之获得了其他哲学体系往往或缺的内容,并因此而在一定意义上赢得了超越其所在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如萨特所说,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出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当然,当我们对萨特的上述论断作出上述解释时,这丝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惟一正确的哲学,也丝毫不意味着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都将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变态。西方哲学将依然保持其多元发展的势态,马克思主义将依然是未来哲学诸多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但是如果我们说,在新的世纪里,世界各哲学流派将在注重人的社会性或群体性,注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或者说,在注重人的“前逻辑思维”方面,取得更多的共识,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果我们可以对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主体性学说的未来发展作出一些预测的话,我们不妨把现代哲学或现代西方主体性学说的这样一种“返老还童”或“正本清源”作为我们的一项假说。
标签:哲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现象学论文; 逻辑思维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逻辑研究论文; 胡塞尔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