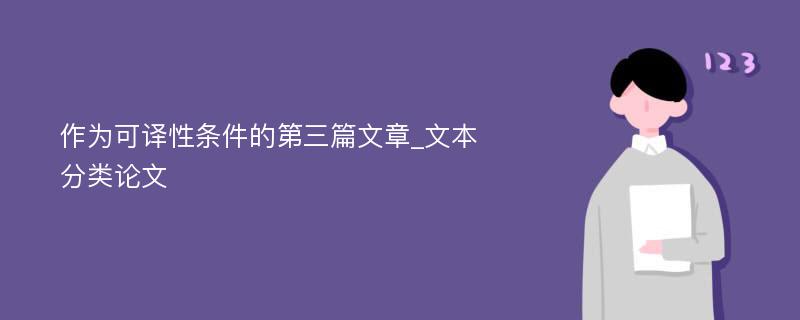
作为“可翻译性”条件的“第三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从哲学的进路考察翻译问题,但它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困境:在 人们印象中,“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个哲学话题。传统翻译研究通常只注重谈论具体的 翻译技术,或者满足于伸张某种翻译伦理,这种基于经验或信念的、体现着强烈规范诉 求的思想活动很难成为体现着彻底反思或追问诉求的哲学活动。因此,对翻译进行哲学 讨论的首要问题是: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
在我看来,要使翻译成为哲学问题,先要拒斥翻译研究中的“自然态度”。(注:“自 然态度”是借自胡塞尔的概念。胡塞尔指出,自然态度是“从自然生活中的人的角度去 思考”,它是“一种先于一切‘理论’的纯粹描述”。换句话说,自然态度是我们在非 反省、非理论的生活中自然获得的各种见解的总和。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 念》第一卷的“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胡塞尔强调悬搁关于世界的“自然态度”是从 事纯粹现象学思考的重要前提。)上述翻译技术或翻译伦理研究就是这种“自然态度” 的必然产物。翻译技术理论关心的是:在“原本/译本”这个二项式中,译本采用何种 语言工艺学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翻译伦理的问题则是,译本诉诸怎样的伦理 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它们很少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原本/译本”这个二项式 中的间隔符号“/”对我们的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缺乏此种追问,传统翻译研究会 自然地假定,“译本/原本”中的符号“/”体现着原本对译本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用 哲学的概括就是“原本中心论”。
一旦涉及“原本中心论”,我们就不难看出“翻译”在哲学研究中的价值。在中文里 ,“原本”是个歧义词——它既指“原始文本”,也包含“原原本本”的含义。它是源 头、是根本、是真相,是人的思想一向寻求的最终家园。我们在哲学活动中总会在三个 向度上碰到“原本”:
其一,在传统哲学领域,作为人的表象和概念之完满根据的“原本”(无论它被表征为 本体、实在、最终根据还是真理)是哲学形而上学的论述起点和终点。(注:“原本中心 假定”是哲学上符合论的基础,按照罗蒂的描述,它关注的是一种“在那儿的实在或真 理”(the reality or truth out there),它在时间、历史或主体表象之外。)
其二,在“文本流传”领域,每个被视为线性意义的传统都有其“原本”。它是原初 的“经”,是历史回溯意识的对象,是在传统发展中不断被复制性传递的硬核,是该共 同体中的人们自我认同的根据。(注:“文本流传”意义上的原本通常是“经”。按照 中国古人的看法,“经为本,传为译”。我在“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一文 曾专门从“文本流传”的翻译角度讨论等级性的“经-传”体制。该文刊载于《云南大 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其三,在“文本流通”领域,被选中的外语文本也是“原本”。(注:“文本流通”是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术语。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我在《开放时代》2002年第6 期的文章:“处于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中的文本流通”。我通常把它与“文本流传”概 念对比使用。)相对于上述“复制性传递”,它是“复制性移植”的对象。传统翻译理 论研究的大多是这种意义上的“原本”。
上述三个“原本”构成了三种知识形态的根基,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知识形态视为三 种翻译类型。在这里,“原本中心论”是“可翻译性”观念(translatability)的一个 共同前提。而所谓“可翻译性”,在认识论上就是所谓“可认识性”、“可再现或可把 握性”;在语言学上则意味着文本转换的语言条件;在解释学上则意味着“可理解性” 。
“原本中心论”有多种变体,其中之一就是对“第三文本”的承诺:即文本1可以转换 为文本2,当且仅当两者都以一个作为“第三文本”的原本为根据。本文的任务就是攫 取20世纪若干西方思想家的论述,考察这种“第三文本”承诺以及相关批评。
一、第三文本·上帝之眼
一般认为,“翻译”是译本对原本的模仿。但“模仿”本身就是个歧义概念。大体说 来,存在着两种模仿概念。一类是完全复制性模仿,在逻辑学中,它指示那种体现着彻 底同一性理想的“重言式”表达(tautology),如A = A。而在非逻辑领域中,一个文本 的物理性复制,一个文本的心理复制(如在传统教育中强调的“背诵”),(注:在笔者 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陈立胜先生曾专门讨论过“经典背诵”的意义。“背诵”的特征 是把“原本”以“原原本本”的方式在内心中完全复制下来,使背诵者成为原本的载体 。在任何传统型教育中,“背诵”都是“原本”持存的一种重要方式。利科在分析“神 话”时曾经指出:“在背诵的意义上,神话的力量在某一特殊语境下会重新恢复。在这 里,文本只是文本,阅读照样存在于文本之中。”参见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 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也可以被视为非逻辑意义的完全性复制 。与之相比,另外一类可称为再现式模仿(representation),在这里,模仿物以自己特 有的方式来表现被模仿物,但它并不能全等于被模仿物,它与被模仿物之间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不可还原或消解的距离。柏拉图在论及Mしμησιζ(英文译名为mimesis,即模仿)时曾提到这种模仿的两种形态。在《智者篇》最后,他讨论了一个人对他人姿态和行为的模仿(counterfeit)。(注:参见《智者篇》,267A,载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柏拉图对话集》),E.Hamilton等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015页。在这里,counterfeit主要表示“假冒式的模仿”,柏拉图因此 称这种模仿为mimicry,即“拟态性模仿”。)这里所说的“模仿”可以被称为“拟态性 复制”,英文多为imitation。此外,他还提到,绘画和雕塑是对外部事物的“形”的 模仿,这种“模仿”可以被称为“拟形性复制”。无论是哪一种复制,它们都可以被视 为文本B对文本A的再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再现式模仿中,译本B虽然可能是对原本A的 非常“逼真地”再现,但它并不全等于原本。对比完全复制性模仿的表达公式A = A, 再现式模仿可以记作:B≈A。
初看起来,A = A与B≈A之间存在着模仿程度上的差异,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模仿系列 ,那么二者之间就可能显示出实质性差异。在完全复制性模仿中,原本与诸摹本之间存 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原本 = 摹本 1 = 摹本 2 = 摹本 3…… = 摹本n,所以摹本n = 原本。而再现性模仿之间则往往存在着以下关系:原本 ≈ 摹本1 ≈ 摹本2 ≈ 摹本3 ……,但摹本n(可能)≠原本!
由此可见,在完全复制性模仿中,诸文本之间存在着逻辑上或经验上的“完全保真性 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y)。而在再现性模仿中,诸文本之间从乐观的意义上说存在 着近似性的“逼真关系”,而从非乐观的意义上,则存在着一种德里达所说的“差异的 播撒”(dissemination of differences)关系。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和《智者篇》所谈到的“三张床”的隐喻,就已经揭示 了再现性模仿的“差异播撒”特性。所谓“三张床”是指:由神创造的床的“原型”; 由工匠根据这个“型”而制造的各种具体的“床”;由艺术家对工匠的“床”的描摹。 在这里,艺术家是与神的原型隔了两重距离的“模仿者”,即他是对“型”(第一重创 造)的影子(第二重创造)的模仿者。(注:《理想国》,597E。)
对完全复制性模仿与再现性模仿的区别并非多余。它们可以分别用来刻划哲学思想史 中的“理想”与“现实”。就理想而言,完全复制性模仿一直是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终极 性认识目标,它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发现真理”、“解释实在”。但从思想史的现实来 看,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中生存的思想家对于“实在”都提供着自己的“摹本”,这些 摹本之间从乐观的意义上仅存在着“近似的关系”。更为复杂的是,如果把思想史中的 那些经典文献作为“原本”,由于“时间间距”和基于不同自然语言的“空间间距”的 存在,关于这些经典文献的不同解释性或翻译性文本之间必定存在着“差异播撒性”关 系。
因此,对哲学文本(如哲学概念或哲学理论)的翻译研究,就是要彰显出哲学的同一性 诉求与哲学文本的“持存”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蕴涵着以下两个重要结 论:
其一,哲学概念在理想上是寻求一种“保真性的”认识或论证逻辑,以使其结论具有 普遍有效性。
其二,但哲学概念——即使是最严格的哲学概念论证——是栖身于特定时代、特定自 然语言的“语词世界”之中的。“语词世界”与特定生活世界、经验世界的密切关系使 任何哲学文本的“持存”都必须由翻译来支撑,而“差异的播撒”正是“翻译”这桩事 情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一向蔑视日常“语词世界”的存在,以为它与哲学思想的纯 粹性格格不入。哲学概念自身应当是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是不因翻译的存在而有所改 变的。即使考虑到哲学文本的“翻译”问题,它也往往强调“可翻译性”概念,强调这 个概念所依据的“原本中心论”承诺。这种承诺,在20世纪西方思想中常常采用一种可 称之为“第三文本”的论证模式:即存在着某一原本A和译本B,B是对A的翻译,当且仅 当它们共有一个“第三文本”M。这个“第三原本”在W·本亚明那里被称为“纯粹语言 ”(pure language)、“真语言”(true language)或“语言总体”(language as a
whole);在索绪尔、乔姆斯基、E·奈达和F·威尔那里则被视为“语言的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of language)。“纯粹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它是“原本”和“译本 ”所共有的“第三文本”;而所谓“深层结构”在“语际翻译”中不仅是指一种语言内 部的深层结构,而且是以理论语言的方式揭示和描述出的“原本”和“译本”的共有结 构,所以我们不妨也把它视为“第三文本”。
显然,在这里,“第三文本”变成了一个新的“原本”。它很像柏拉图在“三张床” 的例子中所说的那个“作为型或相的床的观念”。要达到这样一个“第三文本”式的“ 原本”,我们就需要“第三只眼”,R·罗蒂称它为“上帝之眼”。(注:“第三只眼” 的说法引自Robert Kirk,Translation Determined,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 187页。后面会谈到,Kirk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在翻译理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 即存在着这样一只眼睛,它既能看清母语,也可以看清译语,并且可以对二者的关系作 出判断。这只全能的眼睛也就是R.罗蒂在《真理与进步》一书中所提到的“上帝之眼” 。参见杨玉成所译该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它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了 解“文本A”,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了解“文本B”,并且可以判断A、B两文本在何种情 况下等值或不等值。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亚明的“纯粹语言”概念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层结构 ”中所蕴涵的“第三文本”观念,并引出奎因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质疑。
二、W·本亚明的“纯粹语言”观念
1989年,美国学者安德鲁·本亚明发表了著作《翻译与哲学的本质》,该书从哲学史 的角度系统论列了柏拉图、塞内卡、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戴维森、德里达等人关于翻 译与哲学的思想。而其中第四章则专门贡献给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德国犹太裔思想 家W·本亚明。(注:Walter Benjamin,1892年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在文学评论、美 学、诗歌翻译和大众文化批判等领域卓有建树。年轻时,受法兰克福“自由犹太人读书 之家”(马丁·布伯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的影响,对犹太神秘思想有着浓厚兴趣。他在 一封信中曾提到,“我一直是按照一种神学方式来研究和思考的,这种方式相信犹太教 法典所传授的每一段经文都包含49种含义”。语见单世联所译《法兰克福学派史》(马 丁·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由于他与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思想家具 有相同的犹太身份,由于他30年代以后对马克思著作发生了兴趣,因此,与法兰克福学 派中人关系密切。但他最终没有加入法兰克福研究所。1940年,在从巴黎向西班牙逃亡 途中绝望自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思想史中,W·本亚明一向有两个形象:一个是 作为阿多诺的密友、30年代后开始靠近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W·本亚明,他这 个时期的作品以《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最为著名;而另一个则是在20年代初期 眈弱于犹太教神秘思想(Kabbalah)的W·本亚明。在这个时期,他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其代表作之一是1923年出版的《译者的使命》。
本文十分关注《译者的使命》中提到的“纯粹语言”概念。但在此之外,我们注意到 其中的一系列概念直到今天读来还有着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在该文开篇,W·本亚明就 指出了“翻译”与绘画、诗歌的一个重要区别:
诗并非为读者而作,绘画并非为收藏家而作,交响乐也不是为听众而作,但翻译则似 乎是为那些不懂原文的读者而作的。这是它与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人们以重 复的方式“说同样的事”的唯一重要理由。……既然如此,翻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作品 “样式”(mode):为理解这一样式,人们必须回到原本。因为只有原本包含着制约翻译 及其可翻译性(translatability)的基本法则。(注:参见“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Illuminations,edited by Hannah Arendt,Harcourt,Brace & world Ltd.,1968,第69页。)
在提出“可翻译性”观念之后,W·本亚明并没有立刻进入“可翻译性”是如何可能的 问题。他将笔锋一转问到:这种“可翻译性”对原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
如果翻译是一种样式,可翻译性就必须是某些作品的本质特性。……由于可翻译性, 一些作品便与对它的翻译有了一重密切关系。……如果说生命在其自身展现时并无重要 性可言,那么翻译对原本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代表的不是原本的“现世生命”(life of the text),而是原本的“来世”(after-life of the text)。……换句话说,一个文 本的重要性不是出自它的自然或本质(nature),而是出于它的历史。(注:参见“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Illuminations,edited by Hannah Arendt,Harcourt,
Brace & world Ltd.,1968,第71页。)
基于这个认识,W·本亚明提出“原本是在其常变常新的过程中、在其春花般的怒放中 获得其生命的”。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原本只有在afterlife(来世)中获得其life(生 命)”的辩证理解在W·本亚明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在其另一篇经典论文《故事叙述者》 中,他以同样的方式将“信息”和“故事”区别开来:
信息的价值在保留其新鲜性的那个瞬间消失后便不再“幸存”(survival)。它只活在 那个瞬间,完全依附于那个瞬间,并要不失时机地在那个瞬间展示自己。但故事则不同 ,它不会立刻把自己释放殆尽,而是将其力量保留和积聚起来,使其在很长时间之后还 在不断地释放。(注:参见Story-teller,参见“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Illuminations,edited by Hannah Arendt,Harcourt,Brace & world Ltd.,1968,第90 页。这种把“信息”与“故事”区别开来的思想具有丰富的蕴涵:它一方面反对把文本 翻译简单视为“语义搬运”的狭隘语言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对今天这个“信息时代” 进行批判的先声。它是对解释学“作品的生命即作品意义的持存”这一观念的深刻表述 。)
显然,“故事”(story)只有在“故事的讲述”(story-telling)中才能得到幸存,而 信息则往往在进入讲述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幸存”(survival)和“死亡”(death )成为后来德里达谈论“原本/译本”关系时的核心主题之一。
“原本在其来世中才获得其生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能够具有来世的作 品才是具有永恒生命的作品。因此,“可翻译性”成为嫁接“原本”和“译本”,并最 终将“原本—译本”( = 文本的生命和文本的来世)与永恒的生命嫁接起来的桥梁。在 这里,W·本亚明展开了他的“纯粹语言”概念。他认为,翻译,尤其是可翻译性,提 示着原本中那个永恒的内容。而正是这种内容表现出原语与译语的“亲缘关系”(
kinship)。这种亲缘关系不仅是说译语与原语之间存在着可模仿的“相似关系”(
similarity),(注:A·本亚明指出:“W·本亚明引入‘亲缘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消除 那种在模仿领域中对语言的理解方式。”参见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Routledge Inc.,1989,第92页。)毋宁说,这种相似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它们都是一种“纯粹语言”的碎片:
一个有待于粘合起来的花瓶的各个碎片不需要彼此相似,但它们必须哪怕是在最微小 的细节上都彼此匹配。同样,一个译本不需要将原本的意义简单收集起来,它们必须在 细节上与原本意谓形态美妙地对应起来,从而使人们辨认出原本和译本都是一个更加伟 大的语言的片段(fragments of a greater language),正如那个花瓶的碎片一样。(注 :A·本亚明指出:“W·本亚明引入‘亲缘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那种在模仿领域中 对语言的理解方式。”参见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Routledge
Inc.,1989,第78页。)
本亚明所使用的“花瓶”或“破碎的马赛克”的隐喻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比如,英国当代著名学者乔治·斯坦纳在其关于翻译问题的巨著《巴别塔之后》中就 曾描述了这样一种信念:
从婆罗门的智慧到凯尔特乃至北非的传说,几乎所有语言学神话都一致相信(上帝的) 源始语言破裂为72个——或者是72的公倍数——碎片。它们真的就是原初的碎片吗?如 果这一点得到证实,人们通过辛勤的语词或句法的研究,就可以从它们之中发现伊甸园 中那失落的语言,发现那被荣耀的上帝打碎而均匀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语言的遗留物。对 失落语言的重构犹如复原一块破碎的马赛克,它将使人们回到亚当时期的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如果人可以打破由分散的和被污染的语言(它们犹如被摧毁 的巴别塔的碎片)所筑成的囚笼,他们就能再度洞悉实在的内部机密。他们将知道他们 所说出的真理。此外,他们与其他人类的隔绝,他们之被放逐于暗昧不明的语言,就可 以从此结束。世界语(Esperanto)这个名字就明确表达着一个自古而来的、人们强烈追 求的希望。(注:参见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Oxford Press in New York,1998,第三版(其第一版发表在1975年),第6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W·本亚明称这个更伟大的语言为“纯粹语言”、“最高语言”(supreme language)、 “真语言”(true language)或“语言总体”(language as a whole)。自然语言的真理 一向是“破碎大道”。而W·本亚明所确定的翻译的使命,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道通 为一”。
总之,翻译的重要性在于显示出这样一个语言本体论事实,the original certainly do not reach its entirety(原本自身当然没有达到其完整性),(注:参见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Oxford Press in New York,1998,第三版(其第一版发表在1975 年),第7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所以它是“有待的”。这种有待性表明,它只有通 过翻译才能获得其完整性——“翻译指向作为总体的语言”。而使翻译成为可能的条件 恰好在于,原本和译本是一个更大的完整性存在的部分。因此,翻译的任务就不仅是再 现某一具体原本,而且与这一具体原本来再现、粘合或展现那个整体,我们将它称为“ 第三文本”意义上的“原本”。
三、作为“第三原本”的深层语言结构
不论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承诺“神圣语法”的潜在情结,但在不同语言 现象背后寻找一种逻辑结构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取向。因此,破译一种语言就是破译出 它的结构,这一点在语言学实践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乔治·珍在《文字与书写:思想 的符号》中谈到西方古文字学者文屈斯(Michael Ventris)破译克里特岛线形文字B的贡 献时说到:
文屈斯(1922—1956)善于从古文字符号令人迷惑的各种形式中看出一个基本模式,并 准确地辨认出其中稳定的要素,从而揭示所有符号背后的隐秘结构。总而言之,他的天 赋即在于能够从表面的混乱中发现秩序。事实上,文屈斯的这种天赋,正是所有伟大的 古文字学者的共同特质。(注:参见Georges Jean所著《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 曹锦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由于这种成功,人们很自然地相信,自然语言可以还原为一种理论语言或语言理论, 具体的生活语言可以是理论的衍生物。这一点在所谓“深层结构”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 的展示。这种理论假定,具体的语言使用是表层的,而理论解释是深层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深层结构”理论都假定着“第三文本”。我们知道,索绪尔是在 一种“语内背景”下谈论“语言”的。那里只存在着“语言”(langue)和“言语”(
parole)这样一种二项区别:
但语言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 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 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看来,言语活动是多方 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越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和社会的 领域。相反,言语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 给它以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做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了一种自然的秩序。( 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文版,第30页。)
归纳起来,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言语中系统的、规约的、社会的、语义的方面,言 语则体现着语言中语境的、语用的、个别的方面。(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文版,第29—31页。)索绪尔的区别意识对后来的结构语言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布拉格学派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对音位与语音进行区别,其中,音位是语言中形式化的 语音差异系统,而语音则代表着该系统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使用。此外,分析哲学对命 题与语句的区别也灌注了这种意识。当然,“深层结构”的说法流行起来,与乔姆斯基 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有关。
乔姆斯基虽然对索绪尔那种机械论的语言观不满意,但却接受了语言/言语的分类模式 ,提出使语言生成能力/语言行为二分的理论。从认识与描写的顺序来说,这种生成能 力包含三个部分:(注:参见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和第15页。)
首先是语句的表层结构,即人们诉诸语言行为而使用的任意一个语句,它在语言学上 被称为“表层语符列”(surface strings),这是“语音输入部分”,也就是“语音解 释部分”。然而,一些语音输入完全相同的语词或语句可能表达着完全不同的意思,用 乔姆斯基最喜欢使用的两个例子:
语句:They are flying planes
这个句子可能导致歧义理解:
其一,They/are/flying planes(它们是正在飞行的飞机)
其二,They/are flying/planes(他们正在驾驶飞机)
语词:bachelor
这个词包含着“未婚男人”、“骑士”、“学士学位”、“海豹”以及“未交配的雄 兽”等多种语义。
显然,我们之所以能够从上述语句或语词中看出差异,是对它们进行不同语法和语义 范畴分析的结果。从语法上说,对语句除可以作“名词短语”(NP)和“动词短语”(VP) 的一般分割外,还可以进一步将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按照语义范畴和次范畴(
categorical subcomponents)进行再度分割。分割过程就是给每个被分割单位加上语法 标记(如“名词”或“动词”)、语义标记(如该名词属于“人”、“动物”还是“无生 命物”,等等)。以上整个操作过程就是所谓“转换”。
最后,所得出的经过分割和标记的基本词组系列构成了一个词或句子的基础部分,也 叫“深层结构”,它澄清了表层“基本语符列”的语义内涵。比如上述句子在经过不同 分割和标记后就可消除歧义理解;上述语词经过这一过程也就会展现出多种“语义读入 ”(semantic reading)。因此,对应于表层语言是“语音输入部分”这一说法,深层结 构是“语义输入部分”,它为表层结构提供准确的“语义解释”。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对这个过程概括说:
句法部分的基础是一个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生成着一套高度约束性的基础语符列,每 个基础语符列具有一种相关的基础词组标记,这些标记构成了深层结构的基本单位。我 将假设这一基础规则不会导致任何歧义。……作为语言每个句子基础的是基础词组标志 序列,每个基础词组标记由句法部分的基础生成,我将把这个序列称为句子的基础。… …生成语法的句法部分除了其基础外还包含转换性层次上的次规则要素(
transformational subcomponent),它关注的是从其基础生成句子,生成其表层结构。 (注:参见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译本,第16页。另参见该书第139页 -142页。重号为笔者所加。)
应当指出的是,在乔姆斯基那里,描述的过程是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而说明的过 程则是从深层到表层。后一顺序也适合于说明儿童习得语言能力的过程。此外,从效果 史来看,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结构分析细节只对专业语言学家才有意义,而从其传播来说 ,它有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对“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区别以及使两者联系起来的“转换”概念触 动了许多学者的想象。
第二,乔姆斯基的分析是以英语和他所了解的个别语言为原型、在某一同质语言共同 体中进行的。他很少涉及“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不同自然语言 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成转换语法问题。
但他的分析模式显然对“语际翻译”领域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 就是E·奈达。有趣的是,奈达本人从不承认他是从乔姆斯基那里接受的“深层语言” 观念。他曾举例证明早在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理论结构》(1957年)以前5年,他就已经 创制了这个理论。他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到:
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问世之前,奈达就已经在注经学(exegesis)的若干问题研 究中采用了实质性的深层结构理论。在一篇题为“圣经学研究中的全新方法论”的文章 中,他探讨了从复杂的表层结构回归转换(back-transformation)到一个基础层面(
underlying level)的问题,而这些基础要素包括客体、事件、抽象语词和关系。(注: 转引自E.Gen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outledge Inc.,1993,第44 页。)
本文不想研判“深层结构”理论的专利究竟属于谁的问题,而是要说,这个观念对于 那些旨在说明“可翻译性”的理论来说是一个注定了的思想走向。不过,奈达真正应当 强调的是,与乔姆斯基相比,他的独特贡献是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意味着不同语 言的结构对应和转换。在《走向翻译科学》第四章中,奈达专门在“核心语句和转换” 的题目下指出:
在对诸结构语言的多样性所具有的各种理论可能性进行比较后,人们发现一些惊人的 相似,它们尤其包括(1)不同语言内都存在着相当相似的硬核结构(core structures), 其他结构都是通过变换、替代、增加或删除等方式从它衍生出来的;(2)在最简结构层 面上,不同语言的语词在形式类别(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和基本的转换功能类别( 对象、事件、抽象和关联)上存在着高度的对应。
按照奈达的说法,对一个语言的翻译,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其语法和经验层面的深层结 构的过程,它需要经历以下三个步骤:
(1)将原本还原为其结构的最简要素和语义上最为自明的核心成分,(2)在结构性的简 单层面将原语中的语义转换到接受者的语言,(3)在受体语言中生成在风格上和语义上 的对应表达。(注:以上两段引文均见E.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J.
Brill Press,Leiden,Netherlands,1964,第68页。)
当然,寻找对应表述是一个动态过程(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的这个观念在德国 学者W·威尔斯那里得到了共鸣。他认为(1)一种普遍语言包含着语言A和语言B共有的语 法形式和经验硬核;(2)通过一个动态的解释学过程,语言A的深层结构可以转换为语言 B的深层结构;(3)语言B中的深层结构通过一种转换规则可以生成其各种表面结构;(4) 这些表面结构是由各种文本形式来表现的。(注:参见Wolfram Wilss: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Tuebingen:Gunter Narr Press,1982,第116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深层结构”理论的宗旨是要在自然语句背后找到另外一个 精确的“理论语句”。在“语际翻译”中,这就意味着要在两个以上的语言背后找到它 们所共有的“语言结构”以及该结构要素所承载的共同经验,这个“共同的深层语言结 构”也就是我们说的诸文本、诸语言背后的“原本”。它既是“可翻译性”得以实现的 语言条件,也是使翻译得到描述的理论前提。
四、奎因的“翻译手册悖论”与翻译的“三角关系争论”
在W·本亚明那里,作为“第三文本”的“纯粹语言”为“可翻译性”信念提供了一个 合目的性证明;而在奈达那里,“深层结构”理论为证明“可翻译性”信念提供了语法 的和语义规则的根据。然而,“第三文本”的说明模式并非无懈可击。它有以下几个问 题:
第一,“第三文本”模式过于关注在共时性结构中的“语义”问题,但翻译本身就包 含着一种“历时性”的含义,它很难照搬一种固定不变的语义,而是使这语义进入“变 ”的过程。所以,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专门提到用拉丁文natura翻译希腊文 的physis是造成“存在的遗忘”的重要原因。
第二,语义不是独立物,它必须依附于“什么”而生存。它所依附的是活的语言。语 言在其生存中不仅总在“说什么”,同时一向体现为“以什么方式说”:以诗的方式说 ,以哲学的方式说和以数学公式的方式说,具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果单单把“语义解释 ”作为翻译的核心,就要对语言进行“逻辑剥离”和“概念处理”,(注:参见A·本亚 明: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第11页。)而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 学乃至“深层结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在那里,不同层次的语法和语义范畴和次范畴 框架构成了理论语句(即“基础语符列”)的形成条件。它在向表层语言提供精确语义解 释的同时,忽略了表层结构语言固有的生命性差异。如何处理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成为 这种“第三文本”观念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三,更应该指出的是,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理论假定是在一种“同质语言”(
homo-lan-guage)中进行的。它假定,“深层结构”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在一种语言内部 消解“表层语言”中的歧义性,达到精确的语义解释。而奈达虽然自诩将这种理论成功 地运用于“语际翻译”,但实际上还缺乏对这样的问题的反省:
1、我们如何可以证明一种“深层结构”语言可以在同等有效性上既适用于自然语言A ,又适用于自然语言B?尤其在两种相距遥远的语言之间,从语言A派生出的语法、语义 范畴框架是否可以无条件地运用于另一语言B?在这种运用中是否包含着在概念和范畴上 对语言B的粗暴改写?这正是目前批判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注:翻译暴力不是本论文 的主题,但我们可以特别参照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爱德华·塞义德的“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 ”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2、对以逻辑概念为基础的不同语言表达,我们可以合法地谈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而 对栖身于具体语言表达——如语词——中的概念来说,我们是否只能谈论它们的“相似 性”乃至“差异性”?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使我们超越“第三文本”对作为“表层语言 ”的诸文本的“过度决定论”(over-determinism)——也就是说,不光看到理论语句使 不同的自然语言表达形成“对等性”的可能,还会看到具体表达使栖身于其中的理论语 句获得差异性的事实。
正是在这一点上,奎因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概念显示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1960年,奎因出版了重要著作《语词与对象》,其中第 二章提出的“极端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注:参见E.Quine,“Meaning and
Translation”,第一节和第七节,载Word and Object,MIT Press,1960。Radical
translation一词在中文中往往被译为“彻底翻译”或“根本翻译”,这两种译法都容 易导致误解,因为下文的论述表明,奎因的意思恰恰是要证明“彻底翻译”的不可能性 。)这一思想实验包含着对“翻译不确定性”的精彩论述。他认为,确定一个语词的内 涵并非轻而易举的活动。在翻译语境下,一个语词如何能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应表达— —即synonymy(同义名)——是受制于经验观察的复杂性、人类语言使用的不确定性和超 经验的理论所具有的整体效果等诸因素影响的。该论文在7节论述中提供了大量经典讨 论,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1)翻译通常被认为是某一语言中的语词或句子在另一语言中寻找同义名或同义语句(
word-to-word,sentence-to-sentence translation)的过程。但仅仅谈论两种同源语言 之间的翻译,如从作为低地德语的弗里西亚语(Frisian)向英语的翻译,或谈论相近文 化传统之间的翻译,如从匈牙利语向英语的翻译,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不同语 言中的语词或语句似乎是一个同一性命题或意义(即本文所说的“第三文本”)的多样性 体现。在这里,语句意义的确定、同义名的选择似乎是不成为问题的。奎因认为,为克 服这种错觉,最好设计一种理想实验,即考虑从一个从未接触的土著语言向英语的翻译 情况。这个理想实验被奎因命名为“极端翻译”。
(2)“极端翻译”还假设了另外一种情形,即我们在未知土著人那里只能观察到一些偶 发语句(occasion sentence),而不是静态语句(standing sentence)。要了解这些偶发 语句的含义,我们就必须对土著人使用该语句时的各种刺激性条件进行观察,以确定该 语句的含义。但假设一个土著人指着一只奔跑的白兔叫出gavagai的声音,我们并不能 由其支持性证据(supporting evidence)确定这个词意味的是兔子?兔子身体的一部分? 还是指兔子身上的颜色?或者它的运动,等等。由此,“翻译的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问题显现出来。
(3)从这种理想实验出发,奎因讨论了观察语句如何受到某种概念图式的影响问题(第 三节)、真值确定之难的问题(第五节)。他特别指出,一些语言中的语词可能很难在另 一语言中找到对应物,比如英语中的“中微子”一词就很难为土著语言所翻译。
奎因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讨论不仅引出了经验观察在确定语义方面的不确定性问 题,而且最终导向了关于语词的“相对本体论”断定。由于该文在语言哲学领域中的颠 覆性影响,奎因所假想的那个gavagai成为后来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宠物”。“极端翻 译”实验启发了后人的想象。大卫·刘易斯后来就曾以“极端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为题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在奎因的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两个基本假定:
其一,“极端翻译”发生在母语(在奎因那里指英语)与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之间。在 这里,不存在上帝的“第三只眼”,即它既充分了解母语,还充分了解另外一种语言, 因此才有关于Gavagai的含义的不确定理解。当然,在现实中,我们尽可以假定存在着 某类双语人才,他对两种语言(bilingual)有同等程度的了解。但即使这样,我们还会 面临下一个限定。
其二,翻译所处理的不仅是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同一性”问题,而更主要的是语词和 语词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奎因的著作被命名为《语词与对象》,而不是“概念与对象 ”。这里显示出奎因的一个重要贡献:他通过对“同义名”的讨论,将“同一性”问题 降低到语词的精确性水平上来考察。(注:“For Quine,the problem of
synonymy---equating identity with semantic exactness---extended beyond the
laws of Logic.”语见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第15页。)
由后一限定,奎因在《意义与翻译》中还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翻译手册”(
translation manua)的实验:
借以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可以以不同方式来编制,它们都与那个所 译语言的总体兼容,但这些手册之间却是不兼容的。在它们对一个语言的某一语句的相 关翻译中,它们可以在数不清的地方以各种方式对所译语句给出多种句子,这些句子之 间存在着确定的、无论是如何松散的等值性。(注:参见World and Object,英文版, 第27页。)
显然,两个“翻译手册”在可以“等值地”翻译一个原语的同时,它们之间却可能出 现“不等值”,这种状况在逻辑概念水平上是难以想象的,但在“语词”水平上却是不 难理解的。正是针对这个“翻译手册悖论”,罗伯特·科克概括出所谓关于翻译的“三 角关系争论”(the triangle argument):针对某一外语原语句X,译语手册A可以给出 翻译语句Y,译语手册B可以给出翻译语句Z。这两者对外语原语句X都相容,但语句Y和Z 之间则不同。这成为一个问题。此外,这个问题还可以在三种语言之间出现,即外语( 譬如说德语)原语句A被译为第一译语(如英语)B,又被译为第二译语(如汉语)C,后两个 译语与原语句都兼容,但后两个语句之间不兼容,或至少仍存在多种翻译的可能性。( 注:参见Robert Kirk,Translation Determined,Oxford Press,1986,第187页。)
所谓“三角关系争论”展示的是这样一个领域,解释就是“再命名”(re-naming)。它 所要求的是用“同义名”来定义和展开“原名”的含义。但在自然语言中,一个“原名 ”并非只有一个对应的“同义名”;在“语际翻译”中,一个“原名”更可能会有许多 “同义名”的选择可能。而这里所谓“同义”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得到界定的,那些充 当“同义名”的语词还可能携带着其他内容。翻译者在选择“同义名”时还可能会有其 他非语义性考虑,它可以被概括为“修辞学考虑”。因此,语言的“形象因素”(
figurative factors)讨论不仅只在纯文学中才有意义,它在任何自然语言的翻译中都 是普遍存在的。
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可以引出关于不同理论的“术语系统”(terminology)、 范式(paradigm)或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是否可以转换、关于语言的真值条件 等多种问题的讨论,这是库恩、戴维森和布兰顿等当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在 此不拟展开。本文只限于从奎因的论述展开他的思想的怀疑论态度。这种怀疑根源于他 把“语词”推到了关注中心。“语词”和“语词”虽然可以依据“第三文本”而获得“ 相似性”,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差异性。所以从“语词”来看待翻译,必 然会引出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乃至“不可翻译性”的讨论,而一旦从“翻译的不确 定性”或“不可翻译性”的角度来反观传统哲学关于普遍性概念的诉求,我们就会发现 ,翻译使哲学成为了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