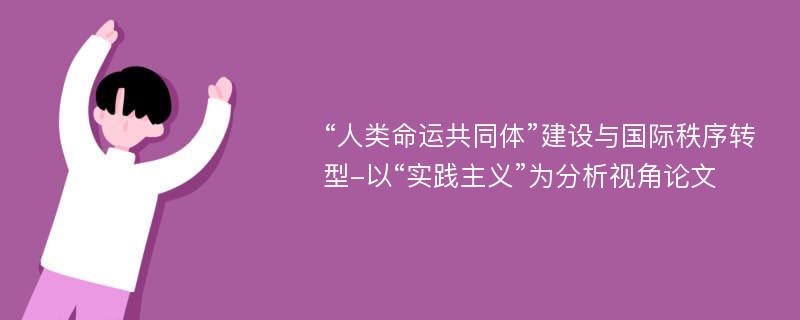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国际秩序转型
——以“实践主义”为分析视角
郭 楚,姚 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它反映了崛起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这个秩序的核心思想是共同安全、合作共赢与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行动上突出了“对话协商”、“共建共享”这一强调国家能动性、强调实践本体的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破解了现有秩序的静态结构主义、表象的偏见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等特征。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实践主义
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最重要的特征是美西方领导下的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当下的国际秩序建立在美西方的权力基础之上,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也体现着美西方的价值理念。然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这些新问题、新情况都要求国际社会要提供新思想、新视角,并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进行修补、调整和变革,从而适应新的形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下关于中国外交的重要思想和话语体系,同时它也是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即建设一种“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国际秩序。建设“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以实践为导向和本位的过程,“对话协商”、“共建共享”是其构建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这一“实践转向”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静态结构主义、表象的偏见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既能为全球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又能对中国在打造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实践过程中赋予合法性。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
(一)当前国际秩序主要是根源于西方体系的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并没有体现非西方世界历史实践及其文明元素和特征
当前的国际秩序发源于西方历史及其实践,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经历了文艺复习、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形成和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欧洲内部,各国合作、结盟、备战、签约、割地等相互交织、竞相上演,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军事实力不断提升,并不断向外扩展,西欧体系逐渐拓展到全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进行的商业战争”。[1]当前的国际秩序因而也就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在物质领域,当前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来源于美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观念领域,当前国际秩序所反映出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规范和制度来源于欧美的国际关系历史及其实践,充满了大量的西方特征及其文明元素。其他非西方国家、文明体系的历史、话语和实践被完全忽略和边缘化。比如“国际体系”概念就是一个例子,该概念被诠释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以来的无政府状态,而东方的等级制度、天下体系等其他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类型被完全忽略和漠视了。[2]因此,这种仅仅反映西方历史的 “国际秩序”概念不能说是普世的,它掩盖了地区秩序间的差异,忽略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实践及其不同行为根源逻辑,并强调和强化了西方的历史价值和实践。
(二)来源于西方国际实践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其价值倾向和问题偏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是指现实的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规律,使自己的行动自觉遵循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它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自觉能动性;合目的性是指人由于认识和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把理想客体变成现实。”[3]因此,所有理论都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目的性的特征,即服务于理论提出者的重大关切。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目的是解决战后西方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主要目的是维护西方主导的(主要是美国)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各种国际社会关系,并使这个体系有效、顺畅运转。[4]秦亚青也指出,理论都是有目的性的(那怕是更多表现为无意识的服务功能),因为研究人员会受到所处时代时空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理论必然具有阶级性和价值倾向)。比如,二战后的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权,在它的土壤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必然是如何维持霸权及其治下的和平,而不会是研究如何崛起和改革现存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样地,拉美国家必然不会研究如何维持世界霸权,相反地,在它的土壤上产生了边缘的非西方依附于中心的西方的依附论。[4]203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社会科学中绝对普适性的、没有体现任何时空内里作用于表象的理论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抑或反过来说,受特定时空影响的无意识的研究人员所提出的理论是反映了一定的“目的性”的,而这个“目的性”的理论在它所处的时空中还同时是“合规律性”的一定范围内的科学理论。因此,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构建原创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则反映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思想品质。
(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话语权本质上具有维护以美为首的西方阵营霸权的功能
在现实国家间互动中,外交概念和口号是一种话语权的体现。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主导话语霸权,中国仍处在弱势地位。[5]比如,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老是抱怨我国的外交话语难懂,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等中国提出的概念和说法或模棱两可,或空洞无物。但是,美国官方和学界提出的一些说法和概念如 “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共同进化”(coevolution)就更好理解、更加言之有物么?其实不然,概念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美国并不想让中美关系的定义权转移到中方手中。[6]
要以长江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恢复为目标,以重要生境、生物资源保护与恢复为抓手,针对不同区域水生态面临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保护修复方案,扎实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长江源区重在加强保护管理,避免或减少人类活动干预,维持高原河湖的自然生态状况;金沙江重中之重是加强水电开发和保护工作的协调性,在干支流寻求建立流水生境保护河段;长江上游重点是加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促进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长江中下游首要的是实施江湖生物通道恢复,其次是实施生态调度,并在加强渔业资源保护管理的基础上实施重要经济鱼类的人工增殖放流。
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义”视角
随着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未来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可能统一于西方的普遍主义,将会充满更多的非西方元素。而中国崛起作为21世纪初国际事务中的头等态势,已经引起了霸权国的高度重视和焦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战略是要削弱美国在亚洲进而在世界的霸权。[7]还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精英日益强硬,[8]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加有围堵和遏制含义的战略。[9]总之,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10]凸显了美决策精英对华不满情绪有所提升。[11]
面对国际体系的压力和霸权国施加的压力,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传达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外界关系的思想理念,即中国拒绝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象性偏见”和“二元对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物质秩序(经济合作、政治军事安全合作),也是一个观念秩序(一种多元主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思想)。在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国际秩序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安全”、“合作共赢”思想展示的是一种和平发展战略,凸显了中国尊重他者的合理安全诉求;伙伴关系战略则展示了中国探索和实践二元对立的“同盟安全”之外的新安全观的外交努力。[12]
(一)“实践主义”的基本内涵
实践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始于历史上的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约翰·杜威、马丁·海德格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米歇尔·福柯等;20世纪下半叶,乔治·赫伯特·米德、欧文·戈夫曼、皮埃尔·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进一步推动了实践主义的发展。[13]他们的观点远非一致,但他们都重视“实践”的本体优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绝对本体”的批判,代之以实践这一人的存在方式为视角,完成了哲学中的“实践转向”。[14]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地融入到国际体系和参与到国际实践中,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实践理论逐步在中国引起了重视。总之,“实践转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现在于,“实践”这个核心概念取代了权力、制度和观念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概念。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主义”认为,实践是在一定结构中有主体、有规律、重复发生的行动,是有意义的、适当绩效行为的实施(competent performances),它的特征是:第一,实践统一了物质和理念,即实践不是“冥思苦想”,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直接介入世界”做事情;第二,实践统一了个体性(individual)和结构性(structural),即实践在结构中发生,又受到结构约束和框定,但也同时作用于结构,实践是建构、维持和解构结构的中介;第三,实践依赖于“背景性知识”。[15]背景性知识是一种含蓄的、无以明言的知识。[16]
(二)实践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政策意义
当中国物质实力增长速度较快,从而在客观物质上可能对既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时,中国就应当用实际行动来缓解体系压力。如主动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等,实际上中国一直都在做: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坚决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但这是与他国共商共建的,而不是单独服务于中国的需要;提出“亲诚惠容”、正确的“义利观”等合作共赢理念;表示出乐见他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等。
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在外交和安全战略领域,中国超越了传统的同盟安全外交,坚定践行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战略,在周边和全球积极开展伙伴关系建设实践。通过实践“同盟安全”之外的新安全观,中国推进协作、共同的安全,而不是“找敌人”的同盟安全。这是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
具体到国际关系中,实践理论为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完善提供了动力。从实践本体角度而言,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各种国际实践的集合。实践主义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操作性上,也有其优势,那就是:聚焦主导性实践,深化主导性实践的合作性质,做大主导性实践;缩小对抗性质的实践,淡化其竞争性质。
另外,一些理论在语境和逻辑上存在“扣帽子”和“贴标签”的问题和偏见,如将实力增长的后发国家视为“崛起国”,其特征一般是先验地被认定为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秩序的动荡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实力增长,“修正主义国家”是需要受到约束和监督的。另外,后发国家需要“被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需要被“社会化”,需要“内化”和接受既有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否则就不被视为正常的一员。进一步地,即便完全“融入”了所谓的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先发国家仍占有主导权和话语权,后来者必须严格按照这些话语权和主导权所设计的规范和惯例行事,否则相关行为就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道义性。
2.实践主义的“背景性知识”行为逻辑在理论上突破了“表象性知识”的行为逻辑,从而超越了普世主义,提倡多元主义,为后来者的行动和话语提供了合法空间。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动逻辑由“表象性知识”驱使,表象性知识一般是理性的、抽象的,它认为行动是经过理性思考和衡量的。[21]实践主义则认为行动的根源由“背景性知识”决定的,是弱意识的、含蓄的、自发形成的,背景知识孕育于行动者所处的背景、环境和长期历史实践经验,而不同空间(地区、国家等等)中的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又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22]因此,不同行为体的行为逻辑也是多元的,多元的理论合理性就得到凸显,普遍主义的观念也自然站不住脚。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国际秩序转型统一于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一)从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层面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彻底颠覆和替代,而是对其进行渐进式调整、改良和补充,是新旧秩序间的良性互动和对接,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合题
作为中国外交实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方案,旨在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的调整和调适。现代国际体系概念起源于欧洲,发展到今天逐步扩大到全球,但仍为美欧主导。如前所述,我们发现当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理论存在 “表象性偏见”和“二元对立”的叙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往往试图将其的地方、局部的政治经验推广成为普遍的、全球的标准和榜样,并力推使其成为普世性的法则。[23]“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合作、协商和对话,着眼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实践背景和现实条件,而非动辄用普世主义来垄断标准和话语,并在现实中以此为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实践理论的多元性特征,即它不是要取代既有秩序和主流理论,而是要“服务”于他们,促进沟通、补充和完善,实现范式间的对话。[24]“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是“另起炉灶”。
如果说起源于西方的国际体系走向全球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有其一定根源性的话,那么当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体系成为现实的时候,融入其他的文明元素和特征并对现有秩序进行调整则也是必然要求。[25]一个多文明多元的世界需要一种包容共生的规范和秩序。
企业想要在低碳发展和绿色经济中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体系、组织和机制,要把握低碳经济的实质和核心,以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系统变革作为基本路径和基本手段,在把握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将现代化的管理观念和组织体系引入到管理工作的实际,做到在基层层面和重点环节的管理创新和机制调整,通过高效率、高质量的管理工作和相关机制建设为企业成长和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在经贸领域,中国倡导渐进性的、兼顾发展中国家舒适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经贸合作实践,同时也积极参加更加开放包容的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这体现了与美国之前推动的所谓“高标准”、“21世纪”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完全不同的理念。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其先发优势来强行统一贸易标准,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标准,故意忽视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这是普遍主义和“表象性知识”偏见在国际经贸秩序中的反映。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否定TPP和TTIP的价值,而是认为在当前不能简单地推广到所有国家,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从本质上看,美欧在经贸领域的这些现实操作和行为根本上旨在维护霸权国的贸易规则制定权。甚至某些当权者如果认为这些规则不能立即为其带来好处时,就对之弃而不用。比如,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TPP态度的大转折就可见一斑。
由于至今没有治愈该病的药物,疫苗成了抵抗阿尔茨海默病的惟一希望。10月初,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阿尔茨海默病大会上,专家们宣布阿尔茨海默病疫苗将首次开始进行人体试验。这标志着使用疫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设想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中国需要从两方面处理好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一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中要准确分析和把握现有秩序的合理方面及其主导者的行为逻辑。如果当下的国际秩序仍是以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象性知识”逻辑主导的话,为了构建一种更好的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即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尤其是与世界霸主美国良性互动,就要给予背景知识——即行动的逻辑以开放性。对中国来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中,首先应科学和理性分析当下国际秩序的特点、合理方面和对中国的有利部分,并充分利用其来发展自身。其次要充分把握好秩序主导国——美国的特征和风格,深挖其背景性知识,从而深化对其行为根源和行为逻辑的理解。最后才能科学评估美国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资源、决心和意志。
最后在Synopsys公司的Design Compiler平台采用TSMC 65 nm CMOS工艺库对接收端同步系统进行了综合,得到各方面指标如表2所示。
(二)从结构和施动者关系的角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兼顾国际秩序的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中国的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
实践本位作为广义本体论,统一了物质与观念、行动者与结构,因而超越了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局限。实践论尤其强调结构变化的原因,那就是实践使然。从实践主义角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是一个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渐进塑造,即中国发挥其施动性作用于国际结构。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不是中国的国强必霸和主导秩序,但是实践主义的品质决定了其必然充满大量中国元素和中华特征。在背景性知识的行为逻辑这一理念驱使下,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将致力于调和现有秩序和新秩序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施动者对结构和秩序进行再建构。
1.实践主义突破了主客二分和二元对立,聚焦于实践这个本体,确立了“改造世界”的哲学观。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根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单向结构的理论,它们没有解释结构在时间中的运行。[17]实践哲学则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8]实践主义重视结构的变化过程,即变化产生于日常生活中——即实践中。[19]吉登斯突破了二元论,提出二元性,阐释了结构与实践(也是过程)的关系,即结构是实践得以产生的场域,但也是反复实践所建构的结果。[20]因此,实践理论解释了事物“何以为此”的原因,即某种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是如何被建构和解构的,答案是通过实践达成。
在提供公共产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现状,中国实践引领“亚投行”的建设,设立丝路基金,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做出了贡献。[26]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交通、联通、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推动有关国家间的合作共赢,稳定了国际和地区局势。
健全并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使得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序快速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完成的效率,有利于企业的进步与发展。另外,健全并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蓬勃发展。
二是中国要清晰和坚定地向国际社会及其秩序主导国传达自己的行动逻辑,从而破解被动应答的状态,争取行动合法性和话语权。在实践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实践行为 (及其提出的各种外交概念)的逻辑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理性的作用,但也是自发的、含蓄的、无以言明的。中国的外交风格、外交特色及其行动的逻辑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这不是处心积虑地对霸权的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文化扩张的追求。① 约翰·鲁杰(John Ruggie)就曾指出,二战后,国际体系里美国霸权中的“美国”因素与其“霸权”因素同样重要,即美国的行为逻辑既包括工具理性主义的因素,也体现了其国家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历史、文化等要素。See 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Vol.46(3):561-598. 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就不应被纳入更多的含义分析,并拒绝被主流理论的“国强必霸”、“制度挑战”、“文明冲突”等逻辑来理解。
中国既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又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在实践主义思想那里得到了对立统一。实践主义关于行为根源的论述侧重于行为发起的原因,即那就是背景性知识,而不是理性思考。但这不意味着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行为体不按理性要求行事。因此,当实践行为自发产生后,正常的行为体也会按照理性原则行事。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捍卫“一中政策”、维护祖国主权领土完整这一行为逻辑更多地是来自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实践,中国及其人民自发地、潜意识地、无需反复思考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不可分割,中国会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而采取任何最坚决、自发的行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会认识到祖国统一在理性主义范畴上也符合其物质利益(如对经济、人口、资源、战略地位等因素的考虑)。但行为的根源更多地来自于文化观念、历史经历和实践经验,并非是简单的利益算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个伟大实践中,中国通过反复和一以贯之的外交实践,既清晰向国际社会划定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又明确表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做到了两者的统一,从而避免被动应答的状态。
四、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兼顾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续繁荣,破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二元对立范式,是中国与世界、理想与现实、物质与观念的辩证统一。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中要把握好当下国际秩序中的具体实践问题、分歧和矛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提出解决办法。这也体现了实践论实事求是的品质,以由易到难、逐案解决的方式,探索国家间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新的利益平衡点。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27]实践主义的过程性和能动性,既要求中国要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也要审时度势,平衡目标与手段。
1.4统计学方法用SPSS17.0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s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塑造孕育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实践主义赋予了主体(即人或国家)以能动性和建构性,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和过程性等品质,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动态实践,这个秩序的最终形态和特征充满各种可能性。[28]国际秩序是渐进改良和转型,抑或动荡和冲突不断;守成国和崛起国是继续走上轮回对抗的老路,抑或是超越轮回、走向“共同进化”,这一切结果都将取决于实践中的互动。[29]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沈阳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的患者。本研究纳入的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标准[9]:有不同程度的结核中毒症状;胸部CT提示胸腔积液征象;胸水生化及常规检查显示为渗出性炎症;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胸腔积液等;患者年龄在16~55岁之间,无严重心、肝、肾等疾病,胸水在中等量以上且发病在两周内住院患者,无变态反应性疾病。按以上标准选择渗出性结核性胸膜炎病人108例,其中男性60例,女性48例。把上述病人分为实验组54例,对照组54例。两组病人年龄、性别、胸水量均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为初治。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0-861.
[2][加]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10-15.
[3]宋德孝.科学发展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之哲学分析[J].求是,2008(2):29-31.
[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2.
[5]周敏凯.加强国际关系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话语权的理论思考[J].国际观察,2012(6):1-7.
[6]徐进.为什么抱怨中国外交难懂的总是西方人?[EB/OL].(2015-5-21) [2018-12-12]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2594.
[7]Robert D.Blackwill. “China’s Strategy for Asia:Maximize Power,Replace America”[EB/OL]. (2016-5-26)[2018-12-12]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strategy-asiamaximize-power-replace-america-16359.
[8]See Aaron L.Friedberg.The Sources of Chinese Conduct:Explaining Beijing’s Assertiveness [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4,Vol.37(4):133-150.
[9]See 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J].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5,Vol.57(3):89-110.
[10]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J].现代国际关系,2016(1):19-28.
[11]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J].美国研究,2016(4):9-36.
[12]郭楚,徐进.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J].国际安全研究,2016(6):22-46.
[13][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M].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14.
[14]刘龙根.论“实践转向”的意义及其对语言问题研究的启迪[J].学术交流,2004(11):152-156.
[15][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M].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18.
[16]John 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M].New York:Free Press,1995:1-10.
[17][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1.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19]See Andreas Reckwitz.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Vol.5(2):243-263.
[20]李红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J].哲学动态,2004(11):7-13.
[21]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181-198.
[22]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181-198.
[23]苏长和.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26-39.
[24][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M].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
[25]王鸿刚.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J].现代国际关系,2016(12):1-14.
[26]涂永红,王家庆.亚投行: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J].理论视野,2015(4):62-64,73.
[27]杜尚泽,吴刚.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1-18.
[28]秦亚青.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10.
[29]See Roxanne Lynn Doty.Aporia: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7,Vol.3(3):365-392.
On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Practicalism”
Guo Chu,Yao Zhu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 100091)
【Abstract】 As a Chinese plan for global governance,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mprov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voice,"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flects the China'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The core idea of the order is common security,winwin cooperation,and harmony in differenc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ighlights the means of"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and"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which emphasizes the state's initiative and the practice ontology.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embodiment of"practicalism"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 is not a complete subversion of the existing order,but a gradual reform and adjustment,for it has solved the static structuralism of the existing order,broke the prejudice of appearance and the world view of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tortuous,iterative and long-term practice process which unified in the diplomatic practice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nternational order;practicalism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01(2019)02-0123-06
【收稿日期】 2019-02-23
【作者简介】 郭楚(1985-),男,广西柳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政治、中国外交;姚竹(1982-)女,黑龙江双鸭山人,国际关系学院党委行政办公室,硕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
(责任编辑:丁忠甫)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实践主义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论文; 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