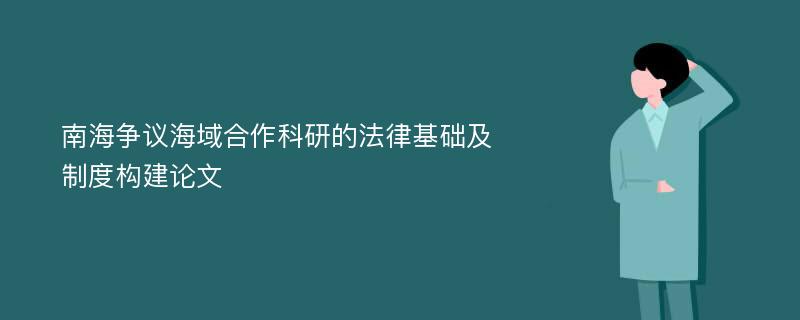
南海争议海域合作科研的法律基础及制度构建
王 宇 张晏瑲
[内容提要 ]当前虽然南海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引起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的消极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周边各国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以增强各国间的信任。南海争议海域中存在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情况,三者均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各种方式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以及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海洋科研合作是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其在实践中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针对以合作方式进行海洋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方式加以解决。
[关 键 词 ]南海 争议海域 海洋科学研究 法律基础 制度构建
南海争端因南海周边各国不同的权利主张呈现出不同类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生效和国际习惯法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各国依据国际法善意地提出海洋主张导致权利重叠而形成的争议区域,应当被认定为争议海域的范围。[注] 在争端尚未解决时,将各国依据国际法提出的海洋主张推定为善意。 而对于因岛礁主权争端产生的海域划界争端而形成的争议区域则不应被认定为争议海域。在南海问题上,首先,我国可以提出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已经通过先发现、先使用、先管理的方式先占取得了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其次,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相关国家曾经承认过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注] 参见傅崐成、李敬昌:《南海若干国际法律问题》,《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7期,第9—11页。 再次,从实际情况出发,各国对已经控制的岛屿及其周围海域通常持有较强硬的态度,即使将其划定为争议海域,各国合作的可能性也极小。
因此,本文将南海争议海域的范围界定为:主张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我国主张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与他国所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相重叠的海域。在争议海域划界尚需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对争议海域的了解,保持争议海域的活力成为重点,海洋科研作为以和平为目的和为增进全人类利益的海洋活动,可以预见将受到青睐。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人类对海洋利用的增强,十九大有关“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皆包含了提高科技用海、强化海洋科学研究的意涵。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海洋科研活动是其他海洋活动的基础,更体现在海洋科研是实现海洋善治的前提。
根据相关实验证明,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是和温度有关的,所处环境温度的升高会对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损害。所以,在日常的使用时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检修。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海洋科研对象的全球性、多学科性和高投入性等特点[注] 参见高婧如:《南海海洋科研区域性合作的现实困境、制度缺陷及机制构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28页。 ,决定了海洋科研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而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低政治敏感度,使该领域得以成为在争议海域建设海洋国际合作的先行领域。各国在争议海域对海洋科学研究合作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一方面,争议海域的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将会对消除各方分歧、缓解地区局势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争议海域针对海洋科学研究问题提出共同解决方案对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科学研究和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南海周边各国的海洋科研合作逐步加强,但通常以框架性或原则性的政策文件为依据,例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海洋科技合作协议》等等,对各方约束力较低。因此,在争议海域内构建有约束力的海洋科研合作法律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对海洋科研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南海争议海域内海洋科研的三种模式,即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分别分析其实施的法律基础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发现海洋科研合作是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基础比较薄弱;最后,通过借鉴其他海域海洋科研的合作模式,提出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框架。
一、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界定
目前,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并没有一个权威且统一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领域,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的列举;另一方面,各国因国家科研实力及综合能力的不同对海洋科研中应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无法对其定义达成一致意见。本部分首先对《公约》及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进行分析;其次,提出在不断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最后,认定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FMA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干预后FMA评分明显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1。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海洋科研相关国际组织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界定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本文认为,争议方单方面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有关地震勘探的海洋科学研究已经被国际司法机构认可。对于其他类型的海洋科学研究,可以参照圭亚那/苏里南案中的标准,以是否会造成“永久的物理性损害”为标准判断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义务,在不违反该义务的前提下,争议方可以行使《公约》中赋予的权利。因此,“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是《公约》和国际裁判规则作出的对争议方在争议海域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活动权利的限制,也是相关国家可以单方面行使何种程度的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依据。
根据过往文献对《公约》中有关海洋科研内涵的研究可以发现,《公约》对海洋科学研究的界定包括以下内容:(1)强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的和平目的和增进全人类利益的目的;[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46条。 (2)海洋科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而《公约》并没有对如何确定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性质或类型提出指导性的标准;[注] 参见邵津:《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研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64—65页。 (3)海洋科学研究不包括测量活动,但《公约》并未对这两者的含义进行区别界定。[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多处将“研究活动”与“测量活动”相区别,包括:第19条2(j)、第21条1(g)、第40条、第54条。
目前,通常认为《公约》作为“平衡政治和法律利益”的协定是“高度妥协的产物”,其中有关海洋科研的规定需要双边和区域性法治来具体实施。[注] 参见姜皇池:《论海洋科学研究之国际法规范》,《台大法学论坛》1999年第4期,第127页;冯寿波:《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科研”条款的解释和效力》,《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21页。 因此,下文通过考察区域性海洋科研组织中的规定尝试解决《公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2.《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公约》
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旨在北太平洋及邻近海域促进和协调海洋科学研究。《北太平洋科学组织公约》(Convention for a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第三条在阐述本组织的宗旨时规定:“促进和协调海洋科学研究,包括但不仅限于海洋环境以及海陆、海气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他在全球天气与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海洋所有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海洋的利用及其资源,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以提高对“有关区域”及其生物资源的科学认识。”[注] 《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公约》第三条第一款。 该公约于1992年3月对我国生效。
实例中每块太阳能电池板额定输出电压为50V,串联后每组额定输出电压为300 V.如图6(a)(b)为采用该霍尔传感器结果,(c)(d)为未使用结果图.二者比对分析充分体现该检测系统采用霍尔传感器对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高、波动范围小.同时经由CAN总线将数据结果几乎无延时地上传至上位机,可以实时观测电压、电流数据.而(c)(d)地延时就很长.进一步采用单片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知每一个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并对每块太阳能板进行编号,可以清楚地了解光伏发电系统每个电池板的工作状态.
3.《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Agreement 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是北极理事会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由北极国家签署,加强并促进北极国家间的科学合作进程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区域性协定。[注] 参见白佳玉、王琳祥:《北极理事会科学合作新规则的法律解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42页。 该协定第一条规定:“‘科学活动’是指通过科学研究,监测和评估促进对北极的了解的努力。这些活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和实施科学研究项目和计划、探险、观测、监测举措、调查、建模和评估;培训人员;规划、组织和执行科学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会议;收集、处理、分析和分享科学数据、想法、结果、方法、经验以及传统和本地知识;制定抽样方法和协议;准备出版物(preparing publications);开发、实施和使用研究维护物流和研究基础设施。”[注]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第一条。
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第三方,是指未在南海争议海域提出权利主张的国家,通常为海洋科研实力及经济实力强国。这些国家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为《公约》中有关海洋科学研究部分的规定,沿海国有关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规定,以及与争议海域内国家签订的合作协定。
《公约》第十三部分第二节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原则。第123条规定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应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未能达成划界协议之前,要求有关各国具有谅解和合作的精神。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是政府间职能自治组织,也是联合国系统中负责海洋研究、观测和服务及能力建设的专门职能机构。[注]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第十届国际科学大会召开》,国家海洋局网站,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4/t20170417_55596.html[2018-12-29]。 中国及除文莱外的南海声索国均为其会员国。[注] 参见《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会员国名单》,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SC/pdf/IOC_MemberStates_Jan2018.pdf[2019-01-05]。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其出版的《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中对海洋科学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本报告中所述的海洋科学包括与海洋研究相关的所有研究学科: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水文学、卫生和社会科学,以及工程、人文科学和有关人与海洋关系的多学科研究。海洋科学力图了解复杂、规模不一的社会—生态系统和服务,需要观察数据和多学科、协作性的研究。”[注]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巴黎:教科文组织出版,2017年,第3页。
5.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CES)聚焦于北大西洋、欧洲附近海域和北极,致力于改善海洋生态系统并为实现海洋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该组织并未对其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内容作出明确界定,但根据其“保护和修复海洋的健康和生产力”[注] ICES Strategic Plan 2014-2018,http://www.ices.dk/explore-us/Documents/Strategic%20plan/ISP.pdf[2018-12-29].战略计划及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可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研究的主题涉及海洋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系统进程和动态,生态系统观察和评估,环境变化、水产养殖和渔业以及社会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二)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
通过上述公约和组织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对“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多采用以规定海洋科研机构要实现的目的为基础并采用不完全列举的方法。通过完善和加强海洋科研组织内会员国合作制度的设计,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通常采用广义解释并进行比较模糊的处理。
随着海洋科学研究在实践中的发展以及《公约》在实践中的运用,《公约》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了如下问题:(1)《公约》虽然在体系上将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分离,但在技术手段、成果运用等方面却很难区分;[注] 参见张海文:《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与军事测量的冲突问题》,载《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1—1612页。 (2)各法律文件均未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活动进行规定,一般认为军事测量活动属于军事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若军事测量船或军事侦察船是为了“和平目的”和“造福全人类”进行的海上测量活动,沿海国是否有权利以这种行为属于海洋科学研究为由行使管辖权?不无疑问。
综上,《公约》作为综合性的海洋领域的国际法规则,为取得多数国家的共识,仅对海洋科学研究作出框架性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具体实施科学研究计划的各科研组织多根据本组织设立的宗旨,明确其所进行的海洋科研活动的具体内容。本文认为,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根据其研究目的可以包含多项内容。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1)海洋科研活动和测量活动在实践中已密不可分,而且各科研组织在进行海洋科研时也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况,即某一个科研国在另一沿海国附近海域进行测量活动时是否需要沿海国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国和沿海国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通常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海洋科学研究内涵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同的解释。在国际合作制度、技术转移制度及相关制度设计更加完善的情况下,即使不同国家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含测量活动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当测量活动与科研活动难以区分时,在目前的科研实践背景下,应当将测量活动纳入海洋科研的范畴,以体现对沿海国的保护。(2)对于军事测量活动,即使声称以“和平目的”和“为全人类的利益”,在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完全达到和平共处,仍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甚至局部海上军事对抗和战争的国际背景下[注] 参见张海文:《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与军事测量的冲突问题》,载《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1页。 ,军事测量活动的“和平目的”很难被证明,而军事活动的完全自由也很难为多数国家接受。因此,本文认为,军事测量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进行军事测量活动的权利作为《公约》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禁止的剩余权利,应当通过考虑沿海国利益和整个人类国际社会的利益进一步平衡协调[注] 参见周忠海:《论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第175—176页。 ,这类活动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二、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是指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行为得以实现和对相关各方产生拘束力的法律根据。如前文所述,本文认定的南海争议海域,包括主张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我国主张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与他国所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相重叠的海域。在该范围内,通过考察国际法、国际司法判例、国际习惯法、区域性的合作协定、国内法及相关政策等方面,本部分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分别对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进行讨论:(1)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2)争议海域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3)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一)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从《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规定[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3款、第83条第3款。 中可以推断出,即使对存在争议的海域也不应当扼杀该区域被利用的水平,应当通过各种方法保持该区域的活力。《公约》第56条和第246条规定了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有管辖权,并可以规定、准许和进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因此,本文认为,即使是在争议海域,因争议一方在该海域内可以提出善意的主张,原则上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只是因为争议海域的特殊性,该权利在实际行使的过程中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
1.法律层面对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权利的限制
根据《公约》第74条第3款、第83条第3款的规定,争议海域内各国在尚未划定海域界线期间,不得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该规定是对争议海域内有关国家进行海洋活动的限制,该限制也同样适用于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以下将结合国际判例和学者学说对该规定进行分析,明确相关国家在从事不同类型的海洋科学研究中应遵守的义务,进一步明确相关国家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基础。
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机制的法律基础构建,主要涉及该协定的适用范围、海洋科研的定义和具体制度等三方面内容。下面通过借鉴其他海域的合作经验,分别针对合作协定构建中的各个问题进行分析。
在“圭亚那/苏里南仲裁案”和“加纳/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中,仲裁庭和国际海洋法庭分别对《公约》第83条第3款后半段作出解释。“圭亚那/苏里南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单方面的地震勘探,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性改变,同时给出四种可能违反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达成义务的情况”[注] Guyana/ Suriname, 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17 September 2007, para. 467, 470, 481:They are: activities of the kind that lead to a permanent physical change;unilateral activity that might affect the other party rights in a permanent manner;activities having a permanent physical impact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and activities that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902[2018-12-29]. ,甚至进一步指出造成海洋环境的物理性改变也不一定导致难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加纳/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认为,应当整体解读第83条的规定,即将“谅解和合作精神”和“尽一切努力”考虑到“不危害和阻碍最终协议达成的义务”中。值得注意的是,白珍铉法官在个别意见中提出的“对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一义务的评估应在两国关系的框架下考虑和平衡以下的关联因素,即:活动类型、性质、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注] 参见张新军:《划界前争议水域油气开发的国家责任问题——以加纳/科特迪瓦海域划界案为素材》,《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31页。 。本案最终认定虽然单方的地震学勘探和石油开发等活动可能“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但是,同时考虑经济和环境因素的情况下,特别法庭没有禁止其已经存在的勘探和开发活动。有学者认为,特别法庭这样的决定,可能会被推断为:单方的地震勘探和开发活动在海洋划界尚未确定的过程中是被允许的。[注] See Yoshifumi Tanaka:“Unilater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Disputed Areas: A Note on the Ghana/ Cote d’Ivoire ^ Order of 25 April 2015 before the Special Chamber of ITLOS”,Ocean Dev . & Int ′l L . Vol.46, 2015, p.324, https://doi.org/10.1080/00908320.2015.1089743[2018-12-29].上述两案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禁止在争议海域的单方面海洋科研活动,前案中将“是否造成永久的物理性损害”作为主要判断因素,后案中将“经济和环境”等情况作为考虑因素。
有学者认为,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在满足:(1)取得研究国本国同意,即不需要通知或经过争议海域其他国家的同意;(2)该研究不会对海洋环境或海床造成任何“物理性改变”的条件下就没有违反“不危害和阻碍最终协议达成”的义务。[注]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port on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under Articles 74(3)and 83(3)of UNCLOS in respect of Undelimited Maritime Areas , para. 98, https://www.biicl.org/documents/1192_report_on_the_obligations_of_states_under_articles_743_and_833_of_unclos_in_respect_of_undelimited_maritime_areas.pdf?showdocument=1[2018-12-19]. 根据上述案例和学说可以推断出,在争议海域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应遵循的“不得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义务的内容虽有变化,但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解释路径。
《公约》于1994年生效以来得到了普遍接受,中国及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均为《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公约》中并没有包含海洋科学研究的明确定义,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的海洋政策提出有利于本国的海洋科研范围,因涉及沿岸国行使管辖权的方式,该争议在专属经济区内尤为突出。[注] 参见邵津:《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研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60—64页。
2.政治原因导致的权利减损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和义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经过国际司法机构解释适用。但是,在实践中,单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往往会由于国际政治、外交等原因而难以实现。
争议方单方面在争议海域内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可能会引起其他方面强烈的反应,从而导致单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无法进行。有学者认为,《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规定的“不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应该基于政治和外交因素,例如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绝对具体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注] 同上。 一国出于缓和地区局势的考虑,有必要告知另一方。这给单方活动的国家施加了通知的义务,导致了根据《公约》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权利的减损。例如,1992年开始,菲律宾单方面邀请外国石油公司对礼乐滩开展地球物理调查,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注] 参见张丽娜:《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6页。 2010年8月,越南反对中国派出地震勘测船在西沙群岛进行地震勘测。[注] See Ramses Amer: “China,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and Dispute Management”,Oce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w , Vol. 45,2014, p. 21.此类事件在南海争议海域比较频繁。
(二)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合作原则
新系统利用开关磁阻电机和SRD控制系统固有特性,通过特有的制动方式,有效实现(2min内)紧急情况下电机呈线性状态快速制动,从而带动双辊筒停止运转,确保设备能够快速停机,提升了设备制动的快速性和准确性,同时减少了原有的抱闸线圈带来的机械磨损,显著提升了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系数。
从上述各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约》多处规定体现出南海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应秉持合作原则。有学者认为,“合作原则是共同开发的理论基础”[注] 萧建国:《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合作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使国家对共同开发负有一般性的合作义务。[注] 参见何秋竺:《争议区域石油资源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2010年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第29页。 该理论可以类推适用到共同海洋科研领域。有学者则认为,合作原则很难说构成了一项一般国际法规则。[注] 参见张辉:《中国周边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基础问题研究》,《武大国际法评论》2013年第1期,第48页。 即使合作义务确实在当事国之间存在,合作的义务更多地强调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即其不会对相关方的合作结果产生强制性的要求。本文认为,合作原则虽然无法对国家间共同海洋科研的结果产生拘束力,但因其对各国行为的约束性且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应当将其认定为共同海洋科研法律基础中的理论基础。
2.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
《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均规定:“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该条的表述相对模糊,国际司法机构和学者对该条的解释和适用也存在不同的标准。
2.5.6 包膜穿孔与外渗的处理 轻度的包膜穿孔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灌洗液外渗,无需特殊处理。如发生严重的交通性穿孔,因灌洗液大量进入膀胱周围间隙及后腹膜间隙,会导致大量的冲洗液吸收。如及时发现且渗液不多,应尽快结束手术并于术后应用利尿剂,一般可自行恢复;如渗液较多且有严重的腹膜刺激征时,应行耻骨上置管引流。
“尽一切努力”强调一国的行为义务;“实质性”强调该临时安排的可行性;“临时安排”是一种不得妨害最后界限划定的过渡性的措施,包括积极利用争议海域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海上危机管控等领域[注] 参见叶泉:《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的国际法义务》,《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01页。 ,或者暂停争议海域内的活动。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低敏感领域,因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较为常见。该条规定中没有对临时安排的具体内容,即结果层面的国家义务作出规定,而是将该权利留给争议海域国家进行具体安排。有学者对“尽一切努力”和“实质性”作出进一步解读,认为根据国际实践,“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要求当事国实际上承担“善意谈判”的义务[注] Yoshifumi Tanaka: “Unilater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Disputed Areas: A Note on the Ghana/ Cote d’Ivoire ^ Order of 25 April 2015 before the Special Chamber of ITLOS”, Ocean Dev . & Int ′l L , Vol. 46,2015, p. 324, https://doi.org/10.1080/00908320.2015.1089743[2018-12-29],para. 316.该文认为,“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可以解释为善意原则,各国需要善意地进行协商,但没有达成协议的义务。叶泉:《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的国际法义务》,《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00—101页。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port on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under Articles 74(3)and 83(3)of UNCLOS in respect of Undelimited Maritime Areas , https://www.biicl.org/documents/1192_report_on_the_obligations_of_states_under_articles_743_and_833_of_unclos_in_respect_of_undelimited_maritime_areas.pdf?showdocument=1[2018-12-19]。该报告中通过对国际法院所做案例的援引,认为第74和第83条适用的谈判必须是善意的。并尽力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间合作机制[注] 参见叶泉:《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的国际法义务》,《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00—103页。 ,简单的立法并不能满足实质性的要求,实质性的临时安排通常包括两种形式:临时的海域划界和划定共同管理区域。[注]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port on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under Articles 74(3)and 83(3)of UNCLOS in respect of Undelimited Maritime Areas , https://www.biicl.org/documents/1192_report_on_the_obligations_of_states_under_articles_743_and_833_of_unclos_in_respect_of_undelimited_maritime_areas.pdf?showdocument=1, para. 50-51[2018-12-19].
在加纳/科特迪瓦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在原告方没有先提出要达成“临时安排”的合作意向时,被告方没有主动达成“临时安排”,这种情况下并不违反“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的义务。[注] 参见张新军:《划界前争议水域油气开发的国家责任问题——以加纳/科特迪瓦海域划界案为素材》,《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30页。 在圭亚那/苏里南案中,仲裁庭认定,争议双方均违反了《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临时安排”的义务。仲裁庭认为,苏里南在面对圭亚那的单方活动时采取了一种强硬态度,而不是试图在理解与合作的环境下与圭亚那解决问题。同时,圭亚那仅通过媒体公示的方式让苏里南参与开发和勘探活动的讨论,同样违反了《公约》的规定。仲裁庭指出“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包括:(1)把官方的和详细的活动计划提交苏里南一方;(2)与苏里南寻找从事相关活动的合作机会;(3)给苏里南提供分享勘探的成果,并且给苏里南监视这些活动的机会;(4)向苏里南提供分享从勘探活动获得的所有财政收入的途径。[注] Guyana/ Suriname, 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17 September 2007, para. 477,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902 [2018-12-29].
本文认为,“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的规定,是对争议海域内相关国家施加的行为义务,即该规定是对各国在争议海域内的相关活动在行为层面产生拘束力的法律根据。临时安排以合作进行海洋活动最能体现善意和对海洋资源和知识的有效利用,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因其低敏感度和致力于人类共同利益属于临时安排中的优先选择。因此,该规定可以视为共同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基础。虽然没有对具体实施内容的规定,但是很多争议海域内的国家合作将该条款列在合作协议的序言之中[注] 例如,尼日利亚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2001年为建立共同开发海域签订合作协议(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ão Tomé e Príncipe on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Petroleum and Other Resources, in respect of Area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Two States (signed 21 February 2001;entered into force 16 January 2003)),在其序言中提到该条规定。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协议(Timor Sea Treaty (signed 20 May 2002, entered into force 2 April 2003))在序言和第二条中有关于该条的规定。 ,国际司法判例中也对认定和为遵守该规定各国应尽的义务进行阐释。由此可见,该规定是争议海域内国家做出临时安排(合作的形式或者停滞的形式)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是共同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基础。
3.南海争议海域内区域性及双边合作协定
争议海域内区域性及双边合作协定,是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具体实施的法律基础。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区域性及双边协定对参与制定的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同时,在第三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为其设置权利和义务。下文将搜集南海争议海域内现存的有关共同海洋科学研究的区域性及双边合作协定,并考察其中的具体制度规定及实施情况,为后文提出解决中国南海共同海洋科研的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1)南海声索国共同签署的文件及参与的科研合作项目
(3)只要我们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1991年)
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文件原则上同意推动海洋合作的五个发展方向,即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注] 参见蔡鹏鸿:《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页。 2017年5月1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在贵阳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同年8月5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2018年8月2日,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王毅指出:“中国已安排最先进的海洋救助船,并配备专业搜救队伍赴南沙值班待命,可在各国传播需要时第一时间提供海事救助服务。未来,中国还将陆续向地区国家提供科研和气象等国际公益服务。”[注] 参见《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04/18/43351167_775682765.shtml [2018-12-29]。
此外,南海权利声索国均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2014年8月在厦门举行的APEC第四届海洋部长会议中通过《厦门宣言》,强调在“海洋科技与创新”领域建立更全面的、可持续的、包容的和互利的伙伴关系,提出推动联合海洋科学研究及知识共享;加强在海洋减灾和灾害应对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促进研究人员交流等具体要求。[注] 参见《第四届APEC海洋部长会议厦门宣言——构建亚太海洋合作新型伙伴关系》,国家海洋局网站,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408/t20140828_33551.html[2018-12-29]。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法律效力。因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不管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是“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中,海洋科学研究的合作发展都被视为一个重点发展领域,未来“南海行为准则”中有关海洋科研合作的条款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科研合作的重要法律基础。
老巴也拄着拐上前帮助阿东,想要抓住阿里,不料却被阿里一掌推到墙角。拐棍甩到了一边,老巴险些摔倒。阿东吼道:“你怎么可以推爸爸!”
再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分委会于1990年成立,致力于促进和协调国际海洋科学、海洋服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加强各国的海洋科研能力、促进各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为推动本地区海洋科技合作,我国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单位牵头实施了一系列地区合作项目,包括西太平洋海洋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项目、季风爆发监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项目、河流沉积对南海的供给作用项目、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的影响项目、南海海啸预警培训项目。[注] 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11中国海洋年鉴》,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461—462页。 这些项目对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实质性科技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最后,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由印尼于1990年首先在东盟成员国内部发起。主要目标是在南海地区与会各方之间创造积极的气氛,推进合作与协调。研讨会决定执行的项目包括:中方牵头执行的“南海海洋数据库与网络建设”项目;印尼牵头执行的“气候变化对南海海平面上升影响的研究”项目,同时设立特别基金以支持科研项目的进行。[注] 参见大卫·L. 范登瓦格、武海灯等:《南海与北极的区域合作:值得借鉴的经验?》,《清华法学评论》2012年第2辑,第9页。 我国代表积极参与该研讨会进程,落实研讨会项目,充分显示了我国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推进地区合作的诚意和努力。但由于该研讨会为非政府间非正式会议,缺乏对各国行为的约束力。
列宁在生命垂危之际,以口授的方式留下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书信。这些文章和书信作为列宁最后的政治交代,构成了列宁的“政治遗嘱”。学者们曾从多种视角对列宁的“政治遗嘱”进行解读,但鲜有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探讨列宁“政治遗嘱”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列宁作为俄共(布)的“顶层设计师”,在逝世前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许多要求和期许,其中蕴含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可以为当前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通过上述合作机制可以看出,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多通过宣言的形式确定各方合作意向,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虽然已经实施了一些具体的科研合作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容易出现执行不力、缺乏资金和人员,以及参与方积极性不强等情况。[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一直面临着资金不足和人员短缺的困难,其中西太分委会也存在执行力不强、缺乏吸引力以及资金和人力上的局限。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09中国海洋年鉴》,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482—483页。
(2)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双边合作协定
根据《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我国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低敏感海洋领域国际合作取得了诸多务实成果。在海洋科研合作领域,通过签署合作协定、实施合作项目、设立合作基金等方式,增强了政治互信,也提高了我国及周边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和观测预报水平。在第一期五年计划执行完毕后,我国于2016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旨在继续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合作,提升对海洋变化规律的科学认知,其提出的五个发展方向,更加注重双边、多边、区域和国际海洋科研领域的合作。[注] 五大发展方向为:(1)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双、多边海洋合作机制,推动海上合作项目的实施,继续拓展与主要海洋国家的合作,建立广泛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2)以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联合调查、联合研究、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等为主要形式,鼓励涉海机构之间和科研人员之间针对《框架计划》所确定的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和交流;(3)支持双边、多边联合建立并运行研究中心或实验室、联合运行科学考察船、联合支持建立并运行区域海洋观测系统、预警报系统,以及海洋信息共享平台,鼓励联合开展技术集成和应用;(4)深化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的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国际计划开展与《框架计划》密切相关的活动,鼓励中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组织或国际计划框架下联合发起并实施合作项目;(5)利用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提供面向参加《框架计划》合作国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奖学金,支持开展专业培训和博士后研究与实践。
目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海洋科研合作最为丰富,签订了包括《中国国家海洋局与印尼海洋与渔业部关于海洋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共同发展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的安排》、中—印尼海洋中心“科技合作备忘录”等合作协定。同时,“南海—印尼海水交换观测”(中、印尼、美)、“南海—印尼海水交换及对鱼类季节性洄游的影响” 、“印尼爪哇沿岸上升流的潜标观测” 、“纳土纳岛海洋观测站项目”等合作项目也有序进行。
中国与越南签订了《关于开展北部湾海洋及岛屿环境综合管理合作研究的协定》《中越海上海浪与风暴潮预报合作研究》等合作协定,成立了中越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组,这都将进一步有利于南海的合作与发展。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海洋科技合作协议》是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海洋科技合作协定。[注] 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10中国海洋年鉴》,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414页。 两国还定期举行中马海洋科技合作联委会,确定中马海洋科技合作计划。中国与菲律宾通过专家组会议也启动了一些科研合作项目。[注] 包括赤潮对比研究、南海台风风暴潮的分析及预报、海洋环境污染容量研究等合作项目。 中国与文莱签订《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但在海洋科研领域还没有具体的合作协定。此外,中国与台湾地区通过研讨会的形式,确定了未来海洋科技合作的愿景。[注] 2010年3月27日至4月3日,首届海峡两岸论坛在台北召开,双方对未来海洋科技与管理方面的合作表达了高度的兴趣,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未来两岸海洋领域相关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11中国海洋年鉴》,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467页。
通过以上列举,南海海域双边合作和区域性海洋科学研究合作有以下特点:其一,不管是双边合作还是区域性合作机制均未明确具体的合作海域,通常指出为南海某海域及周边海域,无法得知某些具体合作项目中是否涉及争议海域;其二,双方及区域性的合作通常通过框架协定、专家组会议、研讨会及相互间的出访活动确定合作项目或者达成合作意向,对合作方的约束力较低,缺乏机制化建设;其三,尚未形成区域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作协定。
4.南海声索国国内立法
国家立法可以作为争议海域内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对本国科研组织签订合作协定,进行合作科研行为具有约束力。中国有关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制度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之中。其中的同意制度、审查程序、监督制度等,是我国参与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样,南海争议海域其他声索国在进行海洋科研合作时,也需要遵守本国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例如,越南《海洋法》第36条,规定了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同意制度及需要遵守的相关规定。[注] 越南《海洋法》第36条,海洋科学研究:“1.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科学研究的外国船舶、组织、个人必须持有越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保证越南科学家能够参与,并且必须向越南方面提供各种资料、原始标本和各种相关的科研成果。2.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科学研究时,船舶、组织、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1)具有和平目的;(2)使用相应的、符合越南法律和相关国际法规定的方式和设备从事科研活动;(3)对依照越南法律和相关国际法规定在海上从事的各种合法活动不能造成妨碍;(4)越南国家有权参与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且有权分享从这些科研、考察活动中获得的各种资料、原始标本,使用和开发各项科研成果。” 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法》第四部分专门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的相关制度,包括同意制度及马来西亚对此科研享有参与权与监督权。菲律宾也已设立大量涉及海洋科学研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并明确了各个机构需要遵循的规定。[注] See Rogelio Cabrera Camaya,“The Consent Regime for Marine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hilippines”,Ocean L . &Pol ′y Series , Vol.4,2000,pp.23-31.
国内立法作为南海争议海域共同海洋科研必不可少的法律依据,可能会导致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是:各国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行政管理制度极可能导致申请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尤其当涉及争议海域时各国均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导致更加复杂的审批程序。
民主,从制度上而言就是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和机制,基础是利益表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基于利益表达的民主业已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是推动民主的强大动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培养了一种强大的惰性力量,它使得人们片面的义务意识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它可以压过人们民主参与的任何欲望,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精神大山。这种惰性力量就是专制与愚昧。
(三)第三方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4.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第三方的参与在为争议海域海洋科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在未与争议海域内相关国家达成合作协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1)争议海域各沿海国对第三方海洋科研的监管可能会出现各国争夺管辖权的情况,也可能存在管辖权的漏洞。[注] 参见薛桂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由此可能对沿海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2)若第三方仅征求争议海域内某一国的同意,则构成对该国在争议海域内权利的承认,从而可能影响后续海洋划界,激化争议海域内的矛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争议海域内争议海域权利主张国有权进行单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但可能因为受到较大的政治阻挠而无法进行。争议方在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研合作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支持,而合作的模式也是第三方参与争议海域内海洋科研的最佳方式。目前在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合作机制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对各国合作的实质性法律约束比较薄弱。下文将通过借鉴其他海域内海洋科研合作经验,设计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合作协定。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的顺利、持续进行。
三、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机制的法律构建
《公约》第十三部分中包括“与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前期的地震勘探活动可以归于该类海洋科学研究。在国际司法判例中,“爱琴海大陆架案”中认为,临时性的勘探活动,例如地震勘探(其中包括小型爆炸),不会对海床、底土以及自然资源造成物理损害的危险,所以国际法院没有支持希腊提出的“在国际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前,未经另一方当事国同意,禁止在争议区域内的大陆架上实施任何勘探活动或者科学研究”的请求。[注]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Interim Protection, Order of 11 September 1976, I.C.J. Reports 1976, para 30-33, 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62/062-19760911-ORD-01-00-EN.pdf[2018-12-29].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国际法院并不禁止在争议海域内单方面进行与非生物资源勘探有关的海洋科学研究,同时对该科学研究的程度进行了界定,即“不会对海床、底土以及自然资源造成物理损害的危险”。该界定对随后生效的《公约》中“不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内涵界定有重要意义。
(一)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
南海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构建,包括对适用的地域范围的界定和对适用的成员范围的界定。地域范围的确定:因南海涉及较多的争议方,争议海域的范围应当通过涉及争议的两国间或多国间分别谈判分别划定。在此基础上确定该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时还应当考虑两点因素:(1)南海争议海域的各国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国内政策及域外因素的影响导致谈判难以进行;(2)因海洋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为获取全面的海洋科研成果需要对争议海域及相关海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考虑到以上两点因素后,可以对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进行适当模糊化的处理,以促进协定的达成。通过考察《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有学者指出,因北极国家存在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区域,外大陆架界限也未予明确,因此该协定对海洋科研适用的地域范围进行模糊化处理。[注] 参见白佳玉、王琳祥:《北极理事会科学合作新规则的法律解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42—43页。
在该协定附件1中表述为适用该协定的海域范围包括“……地区及相邻海域”,同时规定“本协定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任何海洋权利的存在或划定或根据国际法划定国家之间的任何边界” 。[注]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附件1。 在确定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规定,通过模糊化的处理一方面在确保不损害各方利益的情况下推动谈判的进行,另一方面也符合海洋科研自身的特点。
对于成员范围的确定,本文认为,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应当将所有南海权利主张方纳入,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在此范围内各国通过协商确定相关海域内具体的海洋科研制度。该成员范围的确定是吸取《日本和韩国关于共同开发邻接两国的大陆架南部的协定》的教训,日本与韩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签署了该协定,但由于东海大陆架属于中国主权权利范围,在此区域建立“日韩共同开发区”是对中国主权权利的严重侵犯,因而该协定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注] 参见张丽娜:《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9页。 由于南海争议海域涉及不同国家、多个国家间的多种争议,因此为了保证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合法性,也为了提高谈判效率,应当将南海争议海域内各声索方纳入该协定。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内各方海洋科研合作水平和各方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相对限制域外国家的参与可以防止将区域问题国际化。
(二)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界定
如同前文所述,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借鉴其他海洋科研组织的规范模式,以海洋科研的目的为依据确定其范围。其目的应包括,为和平目的和全人类的利益。在南海争议海域应当补充更加具体的内容,包括:为缓解南海紧张局势,促进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对海洋的了解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以此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
更有一个企业借助电商模式积极地拥抱终端市场,他们组建自己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甚至“割肉”舍弃部分原有渠道,下沉终端,与有实力的种植平台对接、合作,将产品、技术、服务有效结合形成合力。这种合作模式,在我国当下的农村市场中极具生命力和活力。正如全国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所言:“服务是农资行业永恒的主题,只不过随着农业新形势的发展,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在发生变化。重新构架服务模式需要整个行业付诸实践和努力。”
(三)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的具体制度构建
南海争议海域各权利主张国均为《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当符合《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应协调各国涉外海洋科研制度,形成适合于本地区的海洋科研制度。下面通过介绍各个地区海洋科研合作的制度安排,为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具体制度构建提供思路。
中日针对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通过协商签署协定规定了“争议海域海洋科研提前通知”制度,包括应当提前两个月进行通知、通知研究机构的名称和科研船舶名称、研究目的和内容、科研时间和区域等方面。[注] See Zou Keyuan, “Govern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Ocean Dev . & Int ′l L .Vol.34, 2003, p.18.日本和韩国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注] Atsuko Kanehar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Waters Where Claim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Overlap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Japanese Ann .Int ′l L . Vol.49, 2006, pp.98-122.该制度的设立,是在双方低层次的合作基础上进行的,不具有长期性,也不能体现双方为共同利益实现对争议海域的研究,各方进行海洋科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对争议海域的权利主张。在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制度安排中应当摒弃该制度,采取一种更加深入的合作模式。在此前提下,《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更值得借鉴。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对科学活动的制度安排做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1)各缔约方根据《公约》的规定协助处理海洋科学研究的申请,此规定对同意制度在区域性海域的适用方法提供了思路;(2)为符合国际法的参与者进入相关区域提供便利,为人员、设备和材料的进出提供便利,为参与者提供研究、运输和储存基础设施和后勤服务的便利条件。本协定从各方面规定了对符合条件的参与方应当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3)加强与促进与非缔约方的合作,并与非缔约方合作采取与本协定所属措施相一致的措施;(4)缔约方应酌情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程序和政策,保护和公平分配知识产权,并促进有关科学信息的获取;(5)为各个教育水平的学生和科学家提供教育、职业发展和培训的机会,鼓励参与者利用传统和当地知识并与有传统和当地知识的人员进行沟通和合作;(6)规定了缔约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与本协定的适用或解释有关的任何争端。[注] 参见《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第3—9、15、17条。
本文认为,在构建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时,可以借鉴《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的具体制度安排,以解决目前在南海海洋科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南海海洋科研合作中有关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因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导致各方的合作协定多集中在框架性或原则性层面,缺乏进入具体项目的途径;在执行具体海洋科研项目时因合作协定的约束力不强,经常出现项目停滞的情况;第三方参与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存在较大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协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缔约方及第三方申请海洋科学研究时面临的“同意制度”。该协定可以借鉴《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协助处理研究国申请”的做法。具体来说,各国可以派代表组成委员会协助处理海洋科研申请,同时,该协定可以统一规定各国处理申请的时间,防止因行政程序导致时间的浪费。其次,对于之前已经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该协定中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规定尽可能提供保障海洋科研顺利进行的便利条件。再次,完善科研成果的公开系统,通过建立网络数据库等方式保障各国获取相关信息。最后,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争端的机制。
李波:拍照“模特”,最著名的是花石头的那位老人,他每天带着狗,在景区溜达,看见摄影师来了就随地坐下,抽着旱烟坐那里等着。拍完照给钱也可以,不给也可以。
五、结 语
南海问题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域外大国的不断干预,南海局势也呈现出复杂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我国在争议海域虽不断释放出牵头南海区域合作的信号,但各国间的合作仍然障碍重重。因此,为增进各国间信任的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以和平目的和增进全人类利益的海洋科研合作需要进一步得到南海周边各国的重视。
根据《公约》及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可知,争议相关国有权在争议海域内单方面进行不造成物理性改变的海洋科研活动,但该活动通常会受到其他争议相关国家的阻碍,甚至被域外国家利用而遭受国际社会谴责。因此,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活动虽然可以作为对该海域享有相关权利和管辖权的证据,但并不是保证争议海域利用价值和缓解区域紧张局势的最优方案。《公约》鼓励各国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在搁置各国争议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认识,分享相关的智力成果,促进各国的科研水平。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基础并不完善,除了《公约》中规定的“合作原则”和“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对争议相关国的行为义务作出规定外,各国间及区域性的合作通常为原则性或框架性的合作安排,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导致南海争议海域的海洋科研合作无法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经常因为一国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停滞。
余额宝就其产品来说,是一只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是所有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最低、收益最稳定的投资品种,具有高流动性和安性好等特点。其主要投资对象为现金、银行定期存单、银行大额存单、债券、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等。虽然货币基金的风险很小,但是并非没有风险。与银行账户存款不同,货币基金没有任何存款保险为其提供担保,一旦投资出错、市场利率发生急剧变动或者基金出现巨额赎回,货币基金都可能会跌破面值。这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并非绝对不可能。
该研究通过对28个红小豆品种在佳木斯地区的适应性进行调查研究。筛选出佳木斯地区红小豆适宜品种,对其株高、分枝数、单株荚数、单荚粒数、百粒重、生育期及产量等主要数量性状进行变异分析、相关分析及主成分分析,明确了红小豆育种改良单株选择数量性状之间的遗传关系,为该地区红小豆育种改良株系筛选与鉴定提供了技术参考。
因此,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的海洋科研合作安排,设计出适合于南海争议海域的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其中包括注重对申请国的协助、为研究国提供便利、完善对域外国家参与科研合作的制度、知识产权共享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海洋科研合作协定,将有利于保证争议海域内海洋科研的稳定性,从而加强南海各国间的信任程度,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和南海局势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作者简介 ]王宇,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张晏瑲,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2-0054-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权发展模式及海洋法制完善研究”(编号:17ZDA145)
[责任编辑:李聆群]
标签:南海论文; 争议海域论文; 海洋科学研究论文; 法律基础论文; 制度构建论文; 山东大学法学院论文;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