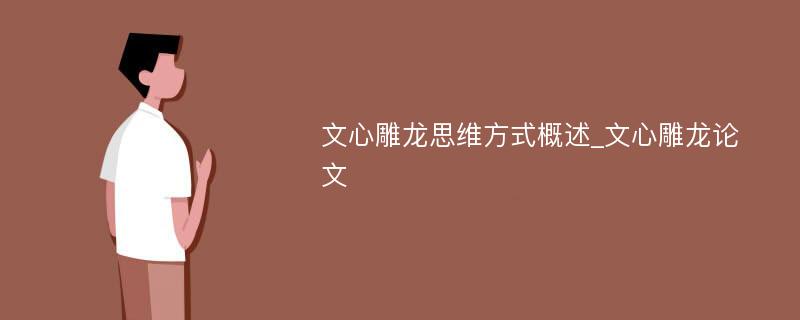
《文心雕龙》思维方式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一部著作的理论体系是与其写作目的及采用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刘勰著《文心雕龙》的终极目的,决非单纯针对现实的不良文风,而是要穷究“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探究“人文”的古今变化,以追寻和阐明“为文之用心”的文章和文学问题的根本原理,以此作为《文心雕龙》的中心课题。以“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两部分为例,说明刘勰以上述目标为中心课题,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取象寓理”和“直观体悟”的形象思维、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交错互补为多元复合体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思考文章和文学问题,从而构造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文心雕龙 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 奉常处变 形象直观形式逻辑
一定的思维方式,既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方法论原则,又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积淀,具有民族特色。而一定的表述方式,又是受一定的思维方式所支配的。因此弄清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必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此书中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之义蕴。故暂且提出此论纲,以作引玉之砖。
《易传》中的《系辞传》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因此我们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民族,远在先秦时代,就早已由《易》文化奠定了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型的非形式逻辑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它是由“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取象寓理”的形象思维、“得意忘象”的直观思维,这样四种具体思维方式既互补又关联而组合成的多元复合体。其主干和核心,则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其优点则是注重辩证逻辑,即注重对事物进行动态考察,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系统性以及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这个见解颇中西方人之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在。但是,中国在魏晋时期,通过注解和论述《周易》等“三玄”著作而兴起的玄学,大盛于世,注重形式逻辑的印度佛学,也源源流入中土,且与长于思辨的玄学相结合,因而,由《易》文化所奠定的这种只注重辩证逻辑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得到了新的拓展和系统化。降至刘勰生活的宋、齐、梁时期,又形成了儒学、玄学、佛学融合而并存的思潮,并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勰即是深受其影响而在思想上和思维方式的结构上,兼综儒学、玄学、佛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文论家(但他只是在知识学问上长于佛理,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至于临死前一年皈依佛门,则是由于“奉时骋绩”的抱负幻灭而不得已)。这表现在:他既遵奉儒家经书中所讲的道理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以下只注篇名),赞誉儒家经学大师郑玄给《三礼》作的注释为:“要约明畅,可为法式”;又以此评语同样地称赞玄学家王弼以“寄言出意”方法注解《周易》而作《周易注》,且还称赞王弼的《易略例》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均见《论说》)。王弼为玄学的创始人,他依“寄言出意”解《周易》,奠定了汉代经学转为长于思辨的魏晋玄学之理论基石。刘勰如此称赞王弼的《周易注》及《易略例》,确乎是欣赏玄学的思辨哲学智慧。而且,他在《文心雕龙》中,还直接援引了《周易》的许多思想资料,来作为阐述或阐明文学理论问题的理论依据。并认为“《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孔子读它时,“韦编三绝”,实为“哲人之骊渊也”(《宗经》)。《文心雕龙》的篇次结构,也是以《周易》的“大衍之数”作依据的。另一方面,刘勰在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编定佛经,博通经论,又受到了印度佛学“因明学”即形式逻辑学的影响。另外,他还在评论玄学家论辩“有”与“无”问题的论文时,赞扬般若学者僧肇论析此问题的论文,比玄学家的论文,要高明得多,认为其论析方法能“动极神源”(见《论说》)。而般若学是富于抽象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的。因此,我认为:刘勰既继承了《易》文化所尊定而后又有所发展的以辨证法为主体的经验型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又受到了玄学理论思辨智慧和佛学重形式逻辑之“因明学”的影响。从而,为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结构,开拓创新了一种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取象寓理”和“直观体悟”的形象思维、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交错互补为多元复合体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思考文章和文学问题,从而构造出了一个“体大虑周”的文章学和文学理论的体系,而“勒为成书之初祖”的《文心雕龙》。
一部著作的理论体系,与其写作目的和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刘勰在《序志》中说他著《文心雕龙》的起因和目的,一是自晋宋以来,一些作家片面追求言词的华美新奇,败坏了文章的标准体裁风格,使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越来越远地背离正道,所以要著此书来“正末归本”。二是前代的文论著作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很少看到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根本原理;有些著作虽间或提出了一些泛泛而谈构思立意的好意见,但都“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要著此书来对文章和文学问题的根本原理,进行“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而且,在刘勰看来,不追寻到在“叶”和“澜”背后的文章和文学问题的根本原理,不阐明这些根本原理,就不能纠正不良文风而达到“正末归本”。所以,刘勰著《文心雕龙》的终极目的,决非单纯针对现实的不良文风,而是要追寻和阐明文章和文学问题的根本原理。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能达到此目的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远祖素来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既有联系又和谐一致的整体、系统,认为宇宙天地、万物发生、人事规律、时间空间,都似乎具有相互牵制而影响着的密切关系。由《易》文化所奠定而后又有所发展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正是以远祖的这种观念为致思的起点和途径,把宇宙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作一个既相关联统一,又有条不紊、生生不已、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去认识和思考;而其思维的目的,则是“究天人之际”。“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方式,把宇宙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当作变中有常、周而复始的循环去认识和思考;其思维的目的,乃是“通古今之变”。而刘勰著《文心雕龙》所要达到的上述终极目的,也就是要在文章和文学问题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即要穷究“天文”与“人文”的关系,通晓“人文”的古今变化,以追寻到“为文之用心”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根本原理。这使得刘勰既把穷究“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探究“人文”的古今变化,以追寻此原理,作为《文心雕龙》的中心课题,又必然以“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相交错的思维方式,还补之以形象直观思维和形式逻辑思维两种思维方式,来对此课题作全面而综合的思考。而且围绕此课题,安排出既能展示思考此课题的思路线索,又能提示思考所得理论成果之逻辑联系的五十篇论文的篇次及组织结构。《文心》全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文之枢纽”的总论、“论文叙笔”的体裁论、“割情析采”的创作方法论、“崇替于《时序》”和“褒贬于才略”等篇章为一组的文学发展论、批评鉴赏论。最后则将作为序言的《序志》放在全书末尾作结。刘勰以上述四种思维方式交错为多元体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上述中心课题,而追寻到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根本原理,以及由这根本原理和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而组成的理论体系,也就内在于这四大部分既前后联贯,每个部分论文的篇次及其理论内涵又都排列得至有伦序和逻辑联系的组主结构之中。下面拟暂以“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两部分为例来说明。
首先,在作为“文之枢纽”的总论的五篇论文中,《原道》、《征圣》、《宗经》居于核心地位,并构成三位一体岛逻辑联系;《正纬》、《薄骚》,则与前三篇构成一种确立和维护“原道”、“征圣”、“宗经”居于核心地位的逻辑联系。而首篇《原道》一开端就以由穷究“人文”与“天文”关系而得来的抽象的艺术哲学命题,作为这总论乃至全书理论体系之逻辑结构的出发点。这抽象的艺术哲学命题是用设问的方式提出的,即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个设问中的“文”,指的是狭义的“人文”,即指文章和它的文采;而所谓的“德”,即如《释名·释言语》所说:“德,得也,得事宜也”;又《淮南子·缪称训》说:“德者,性之所扶也”。所以,这里的“德”,乃指文章和文章的文采是得之于“自然之道”的属性。而全句的意思则是以设问的方式,既肯定文章和它的文采作为从“自然之道”所得来的属性,是非常普遍而盛大的;又确认文章和它的文采是同天地一起产生的。显然,这是由穷究“人文”与“天文”关系而得来的抽象的艺术哲学命题。它既揭示出了文章和文采都本原于“自然之道”,又赞扬了文章和文采的普遍性,并把它们提到了与天地同生并存的高度。如果只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去穷究上述关系,而没有抽象思辨的演绎,刘勰不可能得出如此抽象的艺术哲学命题。惟其是关于“人文”与“天文”关系的这么一个甚为抽象的命题。所以他在提出这命题之后,就接着依据《易传》强调天、地、人三才整体关系的思维模式,以直观类推的形象思维方式,由阐明这个命题出发,论证了自天地形成,便有天地本身的文采,作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的人类,发为言语,自然更有文采鲜明的文章,旁及一切动物、植物以及云霞泉石等等,都有胜过人工雕饰的文采。这些文采,都是由“自然之道”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内在的自然规律,是产生文章和文采的本原。刘勰还通过论述人类文章的起源与发展进程,说明了从伏牺所画八卦到孔子集大成的《六经》,都是效法“自然之道”所生天地之文采而创制的。他由此而推论出一个结论:圣人“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神理”,即“自然之道”。根据这个结论,他指出“自然之道”、圣人、文章三者的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实质上的涵义是:“自然之道”和“研神理而设教”的政治伦理之道,都依靠圣人而留存在有文采的文章中;圣人又通过有文采的文章,来阐明按照“自然之道”所建立的政治伦理之道。而《原道》篇末引用《周易》的话:“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强调圣人的文辞所以能发生鼓动天下的巨大作用,是由于“道之文”,即由于圣人的文章具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又含有效法“自然之道”所制定的政治伦理道德原则的内容,点明了从穷究“人文”与“天文”关系中,所得出的“自然之道”是文章和文采本原的主题。
正由于文章和文采的本原是“自然之道”,所以写作文章和论述文章,都必须从推究文章的本原是“自然之道”出发,即“本乎道”;又由于“道沿圣以垂文”,“圣人之心,合乎自然”(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3页),所以,写作文章和论述文章,都必须验证于圣人,效法他们,即“师乎圣”;还由于圣人效法“自然之道”而创制出的经书,是后世各种文章体制的渊源,所以,写作文章和论述文章,都必须尊奉经书,即“体乎经”。这就是“文之枢纽”的总论中最根本的思想逻辑。它清晰地表明:“原道”、“征圣”、“宗经”,既在这总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又有着三位一体的逻辑联系。而“自然之道”则是这种逻辑联系的理论基础,也就是统帅《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总观点。正是从这个总观点出发,《征圣》中指出圣人由于能够全面观察整个自然界,掌握“自然之道”的奥秘来写文章,故其文章不但创造出了详细、简略、显豁、含蓄的不同表现方法,而且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灵活运用这四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做到“衔华佩实”,即既有雅正而充实的内容,又有文采华美的语言形式,完全贯彻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写作根本法则;另一方面,《宗经》中又指出经书由于能够取法于天地,容纳着体现“自然之道”的深刻内容,所以,“文能宗经”,就能使文章具有以下六个优点: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由此可见,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中,确实通过穷究“人文”与“天文”的关系,而追寻到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根本原理,就是文章和它的文采本原于“自然之道”而形成的这六条标准和“衔华佩实”的原则,以及“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最高准则。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说:“舍人论文,首重自然”,又说《宗经》“六义之说,实乃通夫众体,文之枢纽,信在斯矣。”这是阐明了上述刘勰所追寻到的根本原理的精辟之见。
至于《正纬》、《辨骚》与前三篇构成维护“原道”、“征圣”、“宗经”居于核心地位的逻辑联系之出发点与归结点,则也都是文章和它的文采本原于“自然之道”这个“舍人论文,首重自然”的根本原理。《正纬》首段就充分肯定圣人讲河图、洛书是效法“自然之道”或叫“神道”的说法,只是后世出现了喜好假托荒诞不经的传说,而造作了纬书和谶纬。而刘勰“宗经”的目的,是要树立起本原于“自然之道”的上述六条标准,当然必须匡正纬书的虚假荒谬,反对谶纬诬圣乱经。但他又指出:至于伏牺、神农、轩辕等的最早传说和名山大川等故事,“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于经典,而有助文章”。《序志》中说:“酌乎纬”,主张在匡正纬书虚假荒谬的前提下,酌取纬书中有助于文章写作的精华。这既规定了汲取纬书中养料的指导原则,又维护了《宗经》中所树立起本原于“自然之道”的上述六条标准的纯洁性和神圣地位。《辨骚》中,一方面,肯定了《楚辞》是承接《诗经》而兴起的奇文,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产生了“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则正确地辨析出了《楚辞》与经书的同异,积极地评价了它的艺术特色与成就,并针对后代作家受它影响的各种不同情况,明确指出效法《楚辞》进行创作的原则应该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就是说,要在以经书之一的《诗经》作为准则的驾驭之下,有控制地去酌取《楚辞》中的奇异想象,但不失去它的纯正;吸取它的华丽辞藻,但不失去其情感的真实。《序志》中还提出“变乎骚”,主张在文学的发展变化上,要参考《楚辞》。这既正确地阐明了坚持尊奉经书的纯正文风与艺术上创新求变的关系,又规定了对待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指导思想:即以经书的纯正文风驾驭文学作品所发生的变化与创新,去“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纯正和真实,也就是自然,即保持事物的素朴和真实的状态。所以,《辨骚》列为“文之枢纽”的总论,也还是强调艺术上的创新求变和文采上的华美艳丽都应该首重自然。
其次,刘勰在二十篇“论文叙笔”的体裁论中,对三十四种文章体裁的论述,都是按这样四项程序进行的:第一“原始以表末”,即推究体裁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第二“释名以彰义”,即解释体裁的名称,显示出它的意义;第三“选文以定篇”,即选出代表作品,确定作为论述的篇章,第四项“敷理以举统”,即阐述写作道理,举出它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也就是说明它的标准体裁风格。前三项都是为最后一项服务的。所以,考察和通晓“人文”的古今变化,以追寻到和揭示出各种文章体裁的标准体裁风格,是《文心》体裁论的主旨。试举三个例证,以见全豹。
1、《明诗》在对诗歌进行了“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原始以表末”的论述之后,总括地说: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这段话中的前四句是说,广泛地观赏和考察了各代诗歌,就可以明白诗歌创作情况的古今变化规律;然后归纳列举出各代诗歌的异同,也就可以明白诗歌创作原则的要领了。这正表明《文心》体裁论的中心课题,是考察“人文”的古今变化,以使“纲领之要可明”。而“纲领之要”,即指文章体裁的体制规格,也就是文章体裁的标准体裁风格。这里则是指诗歌的标准体裁风格,是作诗的要领。为探究此课题,刘勰以“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方式,又从对诗歌风格美的审美感受中,去细细品味和考察从先秦直到晋宋四言和五言诗体的创作风貌的变化,从而认为《古诗十九首》质朴而不粗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丽典雅,建安之作“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但“晋世群才”,走向略为俘浅绮丽的道路,“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到刘宋初期则变而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新诗风,越来越趋向华辞丽藻的“绮靡”风格,并从而揭示出四言诗体的正宗体裁风格,是以典雅温润为本;五言诗是由四言诗演变而成的变体,其体裁风格便以清新华丽为主,用以指导诗歌创作回归到《征圣》所说“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的道路上去。
2、《诠赋》的末段说: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这“大体”即指对体裁风格的根本要求。刘勰以“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方式,考究从先秦到晋宋具有代表性的辞赋作品风格的变化,认为宋玉“发巧谈,实始淫丽”,但班固等八人的赋或“明绚以雅赡”,或“迅发以宏富”,或“构深玮之风”。“然逐末之俦”专门讲求文辞的艳丽,以致造成了“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恶果。因此,他要通过阐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的创作原理,揭示出赋的标准体裁风格,是雅正的内容与华丽的文辞相结合。这也是要使辞赋创作回归到“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的道路。
3、《论耸》中考察了说辞体裁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情况之后说:
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钧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
这不但说明了说辞的标准体裁风格的特点在于内容的忠诚和信实,辞语的敏锐;而且批驳了陆机所谓说辞的特点在于文辞光彩鲜明而用诡诈欺骗的说法。可见,刘勰对游说之士进谋献说的“游说之辞”,也要求做到“衔华佩实”。
前已述及,“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方式,把宇宙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当作变中有常、周而复始的循环去认识和思考。刘勰以这种思维方式,去考察“人文”的古今变化,必然对文章体裁等问题得出了变中有常的结论。首先,他认为,源于“五经”的种种文章体裁,在长期写作过程中,都分别形成了恒常不变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表现为标准的体裁风格。而作者则应按照每种文章体裁的标准体裁风格,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去写自己所选择的某种体裁的文章,不要背离标准的体裁风格。这才是在懂得了各种体裁的写作要领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既依据体裁风格的共同标准和共同特色,又发挥自己的才能、个性,写出有个人风格特色的文章作品。例如,《明诗》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拟其清,景阳振其丽。”又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诗有恒常不变的体栽格式和风格,诗人的思想感情,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框框,只能随着自己的才性,选择适合自己天分的某种标准体裁风格的诗体,创作出有自己风格特色的诗歌。这个纲领性的结论在第三部分的《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中,作出了专题论述。例如《定势》篇的“定”,指确定;“势”则有两层涵义:一指文章体裁的姿势,也就是指体裁风格;二指决定体裁风格的趋势。所谓“定势”,就是确定每种文章固定而标准的体裁风格,顺着决定体裁风格的趋势去写作。刘勰在此篇中,将二十二种重要文章体裁的体裁姿势,归纳为六类固定而标准的体裁风格:章、表、奏、议应“典雅”;赋、颂、歌、诗应“清新华丽”;符、檄、书、移应“明确决断”;史、论、序、注应“切实扼要”;箴、铭、碑、议应“弘大精深”;连珠、七辞应“巧妙华艳。”他认为,晋宋以后的一些作家厌弃这些固定而标准的体裁风格,逐奇失正,失体成怪,“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为纠正这种逐奇失正的错误趋势,所以要“定势”,即要确定每种体裁固定而标准的体裁风格,顺着它的趋势,做到“执正以驭奇”而达到“正未归本”。其次,刘勰认为,从上古到南朝刘宋九代文风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质朴到华丽,而商周两代既华丽又典雅,最具有恒常不变的典范性;楚汉以后,则华丽过分,以致到刘宋初年,形成了追求怪诞新奇的不良文风。而造成这不良文风的原因,则是由于一些作家忽视借鉴华丽典雅的古代作品。因此,要矫正不良之风,就必须“还宗经诰”,以经书既华丽又典雅的文风为榜样,既会通前人的成就,又适应文风由质朴到华丽的总趋势,使文章取得质朴和华丽相统一、典雅和通俗相统一的文风,将继承“常则”的典范文风与趋时“变易”结合起来(见《通变》)。
总的来说,刘勰确乎是以穷究“人文”与“天文”的关系和通晓“人文”的古今变化,追寻“为文之用心”的原理作为中心课题,并用上述几种思维方式,思考这课题。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当整个世界观皆据此唯一原则来解释时,——这就叫做哲学系统。”我以为,刘勰则皆据他以上述几种思维方式思考这中心课题所得上面说的那些“首重自然”的总原则,既去由下而上地从文章作品审美鉴赏的具体感受中,系统地总结“为文之用心”的创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概括,又去由上而下地剖析和阐述所作理论概括,并以根本原理统帅其剖析和阐述,从而,构建出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先哲,素来是把用“天人合一”整体思维和“奉常处变”循环思维等思维方式,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作为学致道目标的。明乎此,庶几可以“还原”《文心》理论体系的本来面目,并从而探求到其中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论之义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