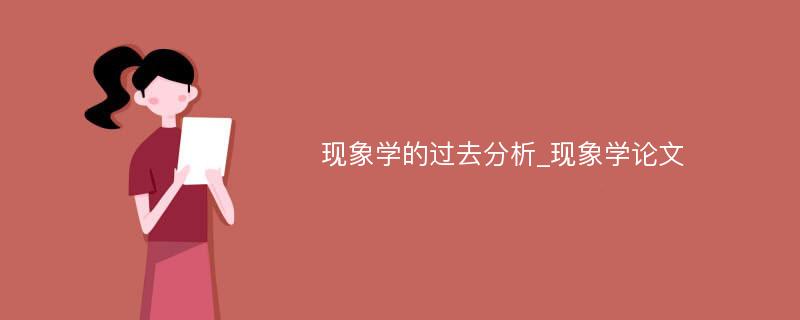
分析现象学的过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2-0022-06
一、引言
斯皮尔伯格在几个地方都提到,20世纪哲学仍然可以区分为几个形态明晰的运动(虽然它们在某个时期有过交叠),如现象学运动、实证主义运动、实用主义运动等[1,2]。诚然,我们还可以将此运动的清单列得更长,例如存在主义运动、诠释学运动及后现代运动等。然而,如果要用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形态来概述20世纪的哲学运动的话,我们就会选择休伊默的说法:“20世纪哲学史可以很好地由两个哲学运动之间的对立来定性,即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这个总体性区分无疑是“合适的,因为这两个运动都肇始于该世纪的开端,而大多数二战后的哲学立场都根源于其中之一。而且,这两个运动没有太多的关联,除了少数的例外”[3](P151)。
诚然如此,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形态,20世纪哲学无疑就是英美分析哲学运动和欧洲大陆现象学运动的主流时代,而其他哲学运动都多少可以说是融入了这两大哲学运动。在分析哲学中,虽然我们在早期还可以发现实用主义传统,但这个传统最终融入了分析哲学而成为分析哲学运动一个新阶段(逻辑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先是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然后是与英国经验主义融合为逻辑经验主义(罗素和摩尔为代表),并以逻辑实证主义的面目盛行(维也纳学派),最后到达美国而成为逻辑实用主义(以蒯因为肇始)。现象学运动也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胡塞尔现象学时期、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时期和现在的综合时期[4](P483);虽然欧洲大陆早期也可以发现诠释学的某些孤独的开创性人物(例如施莱马赫),但最终还是融入了广义的现象学运动(通过伽达默尔和利科)。
作为两个学术文化的社会学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交流甚少,并各自诋毁。但是,198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由于分析哲学传统中心灵哲学研究的兴起,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学理关系已经持续地成为哲学界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发展。
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正在形成。这一新的学术形态现在被越来越多地冠名为“分析现象学”(Analytic Phenomenology),一个原本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使用过但意义十分不同的术语[5](P92)。
然而,尽管已经出现“分析现象学”这一术语,但是决不意味着它已经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术语,事实上,目前尚没有人对这一术语作出令人满意的语义说明。流行于这些用法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可以包括如下三种含义:分析哲学运用于现象学,即现象学的分析化;现象学运用于分析哲学,主要是某些心灵哲学家的观点和立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关联性研究。
应该说,最后一种理解是目前关于这一术语的主流意见,在这种理解中,分析现象学其实只是连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一种桥梁形态,并且,由于它的比较研究的意味,就更多地像一种哲学史的学术形态。然而,如果“分析现象学”仅做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它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正如我们下一节要阐明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初期的相互启发是广泛的。
诚然,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毕竟是两个形态已经明确的哲学运动,将它们的初期都看作是分析现象学形态,显然是不符合哲学史的。因此,我们宁愿使用“过去”一词来表述这种互动,同时将现在的“分析现象学”看作是对这种互动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过去”也将延伸到考虑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后期的分裂。
这里的“过去”一词多少使我们想起20世纪初艾宾浩斯对心理学的评价:“心理学有着悠久的过去,却只有相当短暂的历史”(1908年,《心理学纲要》)。艾宾浩斯对早期心理学的评价无疑能够类比地适应于我们对分析现象学的评价,事实上,这才正是我们使用“过去”一词所要真正表达的东西。
二、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早期互动
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分界线上观察20世纪哲学的发展,仿佛置身于中世纪,一方面是分析哲学烦琐的逻辑论证,而另一方面则是现象学运动后期充满隐喻的修辞学启示。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倒是可以发现20世纪哲学的中世纪痕迹:罗素推崇奥卡姆剃刀,布伦塔诺推崇中世纪关于意识活动中的“内存在”,而诠释学则起源于施莱马赫关于圣经的诠释方法的研究。很显然,这些后来成为各自哲学运动之精神领袖的哲学家们,无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使用的方法与启蒙时代的哲学都甚为疏远。
如果怀着这样一种对20世纪哲学之具有“同源性”的最初印象去观察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学术形态的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分裂程度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广泛,或者远没有其社会学形态(两大哲学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广泛。事实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最初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和交流,即使是在它们分道扬镳的时期,也持续存在着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正面关注,虽然那种关注一直处于哲学主流的边缘。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互动研究的分析现象学,其过去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历史一样长。
就现象学而言,在胡塞尔成为布伦塔诺的学生之前,他由数学转向哲学的决定性影响来自于分析哲学的先驱人物波尔扎诺(Bolzano,1783-1848)和弗雷格(Frege,1848-1925)。这一时期,胡塞尔几乎全部阅读了弗雷格已经发表的论著[6],并在1890年代与他进行长期的通信交流,发表东西;弗雷格后来还为胡塞尔的第一本书《算术哲学》写了一个批评性的评论[6-7]。在这个评论中,弗雷格指出胡塞尔的逻辑哲学是心理主义的,并断言这个方案是没有出路的[3](P151)。
正如现象学者默汉蒂指出的,对于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来说,“胡塞尔和弗雷格几乎属于同一哲学世界”[8](P16)。而分析哲学家达米特也指出过,对1903年的德国哲学学生来说,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形象如果“不管他们旨趣上的某种歧异,必定不是作为两位深刻对立的思想家,而是在定位上相当明显地接近”[3](P151),[9](P26)。
对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比较研究表明,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多得多,在许多方面,胡塞尔几乎就是弗雷格的现象学的广义化版本。根据弗莱斯达尔的看法[7,10],弗雷格关于语言的逻辑图式是:名称(符号)—意义—指称(意谓),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图式是:意向式(Noesis)—意向象(Noema)—对象。胡塞尔的意向象正如其本人所说的,是一种广义化的“意义”,即在经验或意识活动中被把握或理解到的关于对象的内容。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意向式看作是弗雷格的函项,那么意向象对意向式的“充实”不过就是函项被满足。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中也可以看到弗雷格的影子。作为胡塞尔现象学基本方法的现象学还原,其要旨就是对对象的“悬置”,即加括号,而这种还原是为了获得意义,即意向象。胡塞尔的这种“加括号”的说法,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弗雷格关于谓词作为一个未满足的函数的说法:在弗雷格那里,谓词是一个其主词被括号空出的不完整句子;而一个弗雷格式的句子,其合法的主词是一个指称着对象的专名。这就是说,胡塞尔的悬置对象的方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弗雷格关于谓词(概念)说明的启发。如果这种启发具有实质性而不只是类比性的意义的话,那么,在一个事态中悬置了对象之后的意向象实际上就是把握与对象相关的谓词的意义,即把握弗雷格所谓的概念——诚然,胡塞尔是警惕“概念”这个曾经具有心理主义意味的术语的,但是,可以放心的是,弗雷格恰恰是在清除了其中的心理主义意味之后使用这个术语的——很显然,胡塞尔的这种警惕也是受到了弗雷格的影响的。
事实上,在1920年代以前,现象学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广泛的,甚至维也纳学派还曾经将胡塞尔作为象摩尔和罗素一样的精神领袖。
在弗雷格之后,早期分析哲学关于世界和语言的基本单位看法中,具有三个不同的“原子”形态:摩尔的思想对象论(通过他所谓的“绝对孤立法”试图将认识世界的思想对象或质素[quality]减到最少,例如思想对象“美”可以由“善”来定义),罗素的实体对象论(通过摹状词理论这把“奥卡姆剃刀”将世界的实体对象减到最少)和维特根斯坦的事态(句子)论。
作为分析哲学奠基之父的摩尔和罗素,都曾经明确地受到过现象学的影响,尤其是摩尔,其受到的正面影响更为深刻,而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意味最为浓厚,但却完全是自发的。
通过斯多特(Stout),摩尔曾经深受布伦塔诺的现象学思想的影响,1903年,他为后者的思想写过一个评论,名为“布伦塔诺书评:对错知识的起源”。后来(1909-1910年间),通过梅索(Messer),摩尔也间接地受到胡塞尔思想的影响,他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存在不同的精神活动,猜想、判断、害怕、希望、欲望、喜欢、厌恶,它们处于三种类型之中:认知行为、情感行为和意志行为,他甚至主张:“情感和意志的每一行为都‘奠基’在指向同一对象的认知活动上”;博义斯(Boyce)曾经指出,“摩尔钦羡《逻辑研究》”[11]。
我们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并不是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只是在完成书稿之后才发现他的观点与布伦塔诺的接近程度大于任何其他哲学家,而是他写作该书(在1898年三一学院的讲义《伦理学要素》基础上修改而成)时就已经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伦理学原理》与《伦理学要素》的章节比较中看出来。而我们也已经指出,他的“内在本性”(intrinsic nature)实际上就对应于胡塞尔的“本质”。笔者也已经发现,关于“自然主义谬误”的表述,摩尔与胡塞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自然主义谬误乃是将思想对象(或质,quality)或本质化约为物理对象或心理对象的谬误[12]。关于摩尔所使用的“开放问题论证”和“绝对孤立法”的现象学意味,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加以详细论述。
在罗素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在《知识论》(1913)中,罗素声称,存在着不同的精神活动,判断、感觉、意愿和欲望,不同类型的精神活动是不同认知关系中的事件,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形式;而在《关于我们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和“逻辑原子主义”(1917/1918)中,罗素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念[11]。1918年,当罗素被投入监狱时,他就是带着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进去的,他曾经打算为《心灵》杂志写一个关于该书的评论,但遗憾的是,这个意向后来并没有被充实[3](P152)。
有趣的是,胡塞尔和罗素不约而同地埋怨弗雷格错误的使用了Bedeutung(意谓)一词,罗素径直将这一术语翻译为“指称”(denotation),而胡塞尔则建议直接使用“对象”(Gegenstand)。
然而,罗素最早对现象学阵营的关注是他对梅农“对象论”的反驳。梅农认为虚构的对象(例如“金山”、“圆方”)在认识论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关于它们的某些陈述可以是真的,例如“圆方是圆的”。罗素指责梅农违背了矛盾律[13](P49-68)。梅农由此与罗素1904-1920年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之后,罗素的态度由早先的反对(1903年)逐渐转变为同情(1913年)[14],后来(1918年),罗素不再指责迈农违背矛盾律,而只是指责他缺乏逻辑研究所必需的“健全实在感”[15],[16](P159)。
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关于意向象的观点)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具有某种同一性,即都属于关于指称的描述理论的范畴——诚然,胡塞尔没有指称理论,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原初经验的完全意向象看作是指称“词组”的话,那么它就是诸谓词意向象的复合。不同的,在这里,胡塞尔采取的是簇摹状词的方案,而罗素使用“有且只有一个”这样的形式规则来化约定冠词(the)的独断性。另外,罗素关于摹状词的“初现”和“再现”(primary & secondary occurence)的区分也会使人想到胡塞尔关于“呈现”(presentation)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区分,它们都涉及语境的模糊性或隐晦性问题[17]。
诚然,人们也还可以从罗素的“亲知”(acquantance)和“述知”(description)的区分中看到现象学的东西,不过,当我们如此看待罗素时,时刻要记住,罗素的经验论立场及其方法论比摩尔要距离现象学更远。
在摩尔和罗素之后,“牛津学派”(所谓“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旗手赖尔也对胡塞尔的思想着迷,他的动词逻辑以及对心灵状态(如感觉、信念和意志)的逻辑分析深刻烙上胡塞尔的痕迹,事实上,他对心灵的分析主要关注于现象学的“意向式”方面,而他自己也自称其《心的概念》是现象学的[18]。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一直保留着现象学的旨趣,从摩尔开始,直到奥斯汀的“言说行为”(speech-act,即言说作为一种意向式)。奥斯汀明确宣称他的研究是“语言现象学”而不是分析哲学名义下的“语言哲学”[19](P8-12)。而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发展了“言说行为”理论,主要关注意向性问题,在《意向性》一书中,他明确了自己的方案与布伦塔诺和梅农的批判性继承关系[20](P13)。
胡塞尔对早期维也纳小组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作为小组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卡尔纳普参加过胡塞尔1924年(258期)的讨论班,他在《世界的逻辑结构》中的“构造”(constitution)与胡塞尔的“构造”观念被认为有着强烈的联系[3](P152)。卡尔纳普的“构造”显示了深刻现象学旨趣,他自己称之为现象主义(他拒绝作为本体论的现象主义):首先将“我”的经验看作直接的原初经验,由此构造物理对象,最后通过物理对象构造他人经验。他明确承认“我们的系统与胡塞尔作为目标提出来的‘经验数学’和梅农的对象理论亦有共同点。”[21](P7)。
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道扬镳
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分裂开始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时期,一开始是石里克和胡塞尔的争论,而加深这种分裂并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的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石里克与胡塞尔的所谓争论就整个过程而言,似乎更可以看作是石里克对胡塞尔的单方面的攻击。这场争论肇始于1918年石里克在《一般认识论》中对胡塞尔的评论,这个评论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石里克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是一种特别类型的直观或一种关于特别类型的对象或本质的直观,而这些对象或本质不是通常的心理学直观(觉知)”[22]。1921年,胡塞尔在《逻辑哲学》第二版的前言中反驳了这种理解,认为石里克完全误解了自己,否认现象学直观是一种特别的区别于日常精神状态的直观;胡塞尔的反驳更多地是修辞性的,而且用语尖刻。石里克在1925年再版《一般认识论》时删除了这个段落,并且认为现象学是一门基于本质直观的科学,而这种直观有别于通常基于个别感官的经验直观。然而,他却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中作出了回应,说他删除上述段落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的反对,他承认他关于现象学直观不是一个真实的精神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本质直观是区别于经验直观的这个结论[22,23]。公允地讲,石里克的结论是符合胡塞尔本人的主张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通论》中都强调本质直观不是个别直观,即不是石里克所说的基于个别感官的经验直观。
至此,胡塞尔不再关注石里克的工作,而石里克却继续攻击胡塞尔[3](P152)。对英美分析哲学影响最大的是石里克1930年的论文“存在先天事实吗?”。在石里克看来,一个命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不存在先天综合命题,而现象学命题却是关于事实本身的先天综合命题。在这篇论文中,石里克试图表明,所谓的现象学命题其实是分析的或重言式的,是逻辑的真,而不是事实的真。石里克的论证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1)诸如这样的命题“一件衣服不能够同时是红色的并且是绿色的”,在日常语言中是不正常的使用(除非以修辞的方式出现);这就表明,这样的句子对出于交流事实信息之目的的正常用法来说是有区别的,而且是不重要的,就像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不太使用不传达交流信息的分析命题一样。(2)现象学命题不像事实性命题,而像重言式命题,即它们的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关于红色并且是绿色的衣服之存在的断言是不可理解的,没有任何可能的证据能够使我们确信它的真值。石里克的意思是,现象学命题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旦我们理解了一个现象学命题也是知道了它的真,而否认其真则是背离其术语的可理解性的。因此,对石里克来说,现象学命题只能是关于一个术语的概念结构的真,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真[24]。
石里克的这篇论文于1949年翻译为英文并收录于费格尔和塞拉斯主编的《分析哲学读本》,成为英美哲学家的必读书,影响整个新的一代英美分析哲学家[23]。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更深更广的分裂来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一些原来对现象学保持兴趣的分析哲学家认为海德格尔背离了胡塞尔,而这种背离导致了许多分析哲学家(包括原来保持兴趣的那些人)对现象学的怀疑。赖尔1929年曾经在《心灵》杂志发表了一个对《存在与时间》的长篇书评(达29页),开篇就指出,“这是一本十分艰涩和重要的著作,标志着对现象学方法应用的一个大的进展——虽然我可以立即说,我疑心这个进展是一个走向灾难的进展。”[25]。
诚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卡尔纳普对1930年代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在其论文“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中,卡尔纳普将海德格尔关于“无”的存在主义分析看作是一种坏形而上学的例子[3](P152)。
卡尔纳普从“什么是形而上学”一文中摘录了海德格尔的段落加以分析,这个分析表明,海德格尔对“无”的说明拙劣地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句法。海德格尔的句子“只有有——再就无了……这个无本身无着”与句子“屋子外面的雨在雨(下)着”看上去有类似的结构,如果我们将“屋子”类比“有”,而“雨”类比“无”的话。然而,这种类比是不符合句法的,因为“无”并不是一个存在着的对象,也没有一个相应的过程,它既不能作为句子合法主语(根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一个指称任何对象的词是不能作为句子的合法主语的),也不可能动词化作为谓语。当然,为了使得反驳不那么浅薄,卡尔纳普也揣测了“无”的其他含义,例如与“烦”相联系的情绪结构,但是这种揣测可以为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明所拒斥——海德格尔本人是拒绝以逻辑学的矛盾律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更明确的分析参见穆尼茨的《当代分析哲学》[26](P297-300))。
这篇论文后来收入艾也尔所编的《逻辑实证主义》一书,而艾也尔本人在《二十世纪哲学》中也以相同的论调了批评了海德格尔对“无”的理解。作为维也纳小组的英国代表,艾也尔的著作对战后英语国家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不过,即使在这个交恶的时期,也仍然有一个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人始终关注着现象学,他就是考夫曼(Felix Kaufmann)。考夫曼是维也纳小组活跃的非正式成员(当时是一个石油公司的经理),但他同时也是胡塞尔的信徒,1920年就开始与其交往,并很频繁。考夫曼1938年移民美国,虽然他此时已经失去对现象学的兴趣而转向杜威的实用主义,但他仍然在1940年发表了“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的论文,作为对胡塞尔的纪念。在该文中,他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逻辑经验主义误解了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和他的明证性概念,把它们当作伴随经验活动的感觉及其材料,而不是使得对象知觉成为可能的内容,从而错误地将胡塞尔当作柏拉图主义者。第二,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作出了批评,经验主义者将感官经验看作是不可分析的,实际上就主张了一种他们所反对的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
可以说,考夫曼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的第一人。然而,在分析哲学与现象深深的裂痕中,考夫曼的工作长期淹没于文献的海洋中。
四、结语:走向“分析现象学”
在考察了分析现象学的过去之后,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既然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它们诞生之初存在着广泛的互动,那么,为什么在它们的后期又存在着深远的分裂呢?
一种说法是风格问题,人们现在通常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这样的词语来表示两类不同的哲学风格。然而这是一个不得要领的答案,事实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故乡都在德国。
似乎也可以用政治或战争来说明这种分裂,二战的影响使得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如卡尔纳普移居北美,而现象学的领袖人物则几乎都留在了欧洲大陆。当然,人们还可以用地域、思维偏好等因素来说明,如德国哲学对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的偏好、英美哲学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传统的偏好等。
然而,这些说明几乎全部都不是就哲学本身来说明的;而且,它们无法说明的是,既然存在这样的差别,为什么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在初期却存在着如此广泛的互动,难道在那一时期就不存在这些差异吗?或者,这些差异被其他外在的原因所抑制?
与其说上述说明是理由,倒不如说它们只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因果关系对于理由来说,是偶然的、外在的,这样的因素可能影响哲学的一时的发展,但最终会被消除。哲学的基本任务是说理,是一项高度理智性的事业,我们很难相信哲学的分裂会出于外在的因果作用而不是基于内在的理由。
如果寻求内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在分裂部分阐述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色彩曾经是这种分裂的根源。然而,这样也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当蒯因在1950年代之后重新转向关注形而上学的时候,恰恰这种分裂继续深化呢?我们需要求助于弥合裂痕的外在时间吗?
一个合理的答案当然必须考虑外在的原因和内在的理由,以及连接它们之间的东西。我们承认,虽然哲学本身是高度理智化的事业,但哲学毕竟是哲学家的事业,风格、政治和地域都可能对哲学产生外在的暂时性的影响。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分裂的内在理由是它们基本立场的分歧,而外在原因加深了这一分歧并导致它们长期无法弥合。不过,我们还必须增加一个更重要的连接两者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教育或学术活动的原因,哲学教育或哲学学术活动的分裂导致了两个学派的显著社会学形态,并形成各自稳定的传统。
如果我们的说明是合理的,那么,作为说理事业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就最终是会相互融合的。其实,考夫曼早在前述的“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一文中就已经作出了这种预测: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并非不相容,而是在各层次上互补的;“如果经验主义坚持追求其目标,即科学分析的方法,那么,这些造成现象学反思之出发点的困难必定也会涌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迟早转向现象学[3](P154-158)。
事实正是如此,当对时代问题之回答的理智需求压倒外在原因导致的隔阂时,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最终在心灵哲学中导致了融合。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融合的力量很复杂,这里简单地区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美国本土哲学家受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影响而对现象学保持的兴趣。齐硕姆就是这种情形。他早年就读哈佛大学时就深受来访的摩尔和罗素的影响,从而对布伦塔诺和梅农发生兴趣——事实上,作为一位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两个领域多产的哲学家,齐硕姆一生都没有离开对这两位现象学者的理论的发展,他的方法论是摩尔-布伦塔诺(价值论)和梅农-刘易斯(知识论)的混合。(2)年轻的现象学者来到美国,并最终对分析哲学发生兴趣。弗莱斯达尔和默汉蒂就是这样的学者。弗莱斯达尔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后跟随蒯因研究逻辑哲学,其博士论文的最初动机就是从现象学的立场发展出一套比蒯因更好的逻辑系统。默汉蒂作为印裔哲学家曾经获得哥廷根博士学位,在美国最初的成果就是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比较研究,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从现象学的角度关注心灵哲学。(3)心灵哲学中的现象学立场,如德雷弗斯和塞尔。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家,前者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激烈地反对人工智能的立场,而后者作为日常语言学派奥斯汀的学生则发展了布伦塔诺和梅农的观点以批评人工智能理论,并且因为“中文屋”的思想实验而声名卓著。
应该说,分析现象学的中坚力量在第二类,他们明确了“分析现象学”这个术语,但是第三类研究目前最有哲学影响力,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对现象学的兴趣,第一类则人数众多(这得益于齐硕姆培养学生的能力,他一生培养了59名博士,在他去世前是美国人文类排名第三多的研究生指导者),但是他们的现象学立场并不明确,掩映于对知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分析中。
关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融合过程将是一个长长的故事,限于篇幅,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加以介绍。
收稿日期:2010-01-05
标签:现象学论文; 罗素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胡塞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逻辑研究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