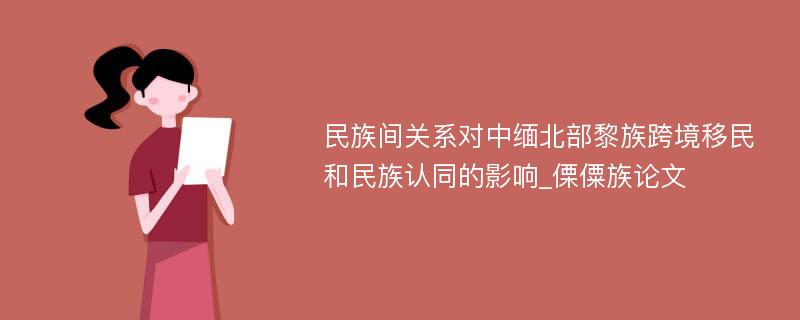
族际关系对中缅北界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民族认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傈僳族论文,对中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缅北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5-0080-06
傈僳族作为跨界民族,有着一般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的同时,又有其特殊性。内在因素是因其自身游猎游耕的生计方式而主动寻找经济资源;外在因素中主要是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而导致其被迫迁徙他乡异国。尤其是因民族关系所导致的民族迁徙的历史,与居处不同国家后形成的新的民族关系的现实双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着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
一、元代,傈僳族先民与丽江路八种蛮“参错而居”
元代傈僳族先民主要居住于“东有丽水,西有兰沧,南接大理,北距吐蕃”的丽江路范围内。① 主要是延续唐代南诏统一战争之后的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栗粟两姓蛮”迁居金沙江铁桥四境的分布格局,[1](P28-30)但已形成一定的聚居区。
据《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丽江路军民宣抚司》记载,迁徙到北胜府的施蛮因其故地在剑寻赕而称“剑羌”者,到宋代大理时因高大惠镇守该地,而与白蛮有了接触。而曾“立施州”,说明施蛮人口已达到一定规模。“施蛮本乌蛮种族”,[2](P150)在唐代,施蛮文化上就与白蛮族属已有差异;元代因二者所处政治地位不同,也将加速二者间的“认不同”心理,由此加速对其内部文化的认同心理。
《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还载:“顺州,在丽江之东,俗名牛赕。昔顺蛮种居剑、共川。唐贞元间,南诏异牟寻破之,徙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等川。其酋成斗族渐盛,自为一部,迁于牛赕。至十三世孙孙自瞠犹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内附。至元十五年,改牛赕为顺州。”至大理国时以顺州之顺蛮以一个“部”的身份隶属于大理而与白蛮有了关系,到元代内附于元代中央王朝。“顺蛮本乌蛮种类”,[2](P151)顺州因为唐代顺蛮迁徙于此而改称顺州,可知顺蛮数量较多,或者说已成为其地主体民族,因而能够长期延续发展“自为一部”,其认同心理应该比较明显。
《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又载:“兰州,在澜沧水之东。……唐为卢鹿蛮部。至段氏时,直兰溪郡,隶大理。”唐代的“卢鹿蛮部”在大理国时被大理国所设兰溪郡所控制,与白蛮发生联系。“卢鹿蛮”也即为“卢蛮”,元《混一方舆胜览·金齿诸路·潞江》曰:“俗名怒江,出潞蛮。”怒江“即自潞蛮地界流入,潞蛮即卢蛮同音异写,而卢蛮亦即栗粟也”。[3](P846)这部分发展脉络较清楚,即在南诏兼并战争中,有傈僳与怒先民西迁兰州,因本乌蛮种而以“卢鹿蛮”称之。② 称其为“部”,应该人口并不少,因而也有发展其民族认同心理的传统文化基础。《元史》同条目还记载:“兰州……元宪宗四年内附,隶察罕章管民官。至元十二年,改兰州。”“卢蛮”在元代隶属于丽江路军民官管辖,又与磨些(纳西族)发生联系。顾炎武《肇域志·云南志》记载:“蒙阁罗凤尝徙善阐杨城堡张、杨、李、赵、向、间、任七姓戍守之(兰州),以丽水节度领制之。”南诏时期善阐杨城堡(昆明)的具有汉姓的内地移民镇守兰州,兰州的“卢鹿蛮”就处于民族传统文化与汉、磨些、白蛮多重文化场景当中,在“我者”与“他者”的文化对比中,必然促发对自身文化更为强烈的认同心理。可见,民族认同一方面是基于内部文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基于与他族文化的差异性。
而且,不惟兰州,整个丽江路范围内的“卢蛮”也处于多重文化场景之中,而出现了统一的族称。《元一统志》曰: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故称一族”。丽江路范围之内,众多族群“参错而居”,相互间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就在所难免,由此基于族群内部文化一致性而来的族群认同,以及与其他族群之间文化差异性而来的“认不同”心理同时存在,这为傈僳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再则,从元代史志中出现的统一族称“卢蛮”来看,尽管在对北胜州、顺州的纪录中还有“施蛮”与“顺蛮”称呼,但《元一统志》中却无,只是作为将“施蛮”与“顺蛮”作为区域性支系群体的称呼,显然并未将与磨些蛮、白蛮并列,而与其并列的是此“卢蛮”。“卢蛮”族称的出现,如是自称,说明其外部文化特征与内部文化特征的一致性都比较明显,因而已发展成为拥有并分享共同文化的同一族群的雏形;如是他称,至少说明其外部文化特征在记录者看来是较为相近的,这也应该是其认同基础之一。
二、明代,在木氏土司纳西与吐蕃战争中傈僳的疏离
明代丽江麽些(纳西)木氏土司辖境在延续元代丽江路辖地范围基础上,有明显拓展。而其领地拓展与其境内民族关系息息相关,表现之一是其境内傈僳也被拖进民族战争当中,其结果使傈僳聚居地空间发生巨大位移。
“维西县范围包括金沙江流域奔子栏一带,所以维西县占据着金沙江、澜沧江上游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代是丽江木氏土司与吐蕃势力争夺地”。[4](P416)维西在明代是傈僳族先民“栗粟”聚居地之一,其北部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吐蕃,其南部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麽些。尚处于狩猎与采集经济阶段的栗粟,其“登山捷若猿猱”,“利刀毒弩”的生产能力极强,在战争中可转化为极强的山地作战能力,并被同一区域的麽些木氏土司所利用,成为其“诚心报国”旗号下与吐蕃争战的马前卒。[5](P19)约从景泰二年(1451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636年)近两百年持续战争中,傈僳与吐蕃,自始至终是战场上敌对的双方,战争使二者间的文化差异性更加凸显。傈僳与木氏土司为首的麽些,在战争初期立场、目标一致,即联合抵抗吐蕃贵族南下侵扰,但冲锋陷阵在前的傈僳伤亡极大而被迫迁徙以避战祸;后在木氏土司以移民屯垦推进方式排挤吐蕃势力中,傈僳故地也被占领而被迫迁徙他方。木氏土司的移民政策,在屠杀吐蕃民众的同时,对其区域内的傈僳也有影响而使其不得不向西远徙。
今天维西塔城其宗、腊普居民以“木”姓与“和”姓纳西为主,根据当地口述家族史,其祖先均是明代木土司与古宗(吐蕃)打仗时迁徙来的,木姓以管理者、和姓以下层士兵与农奴的身份,各司其职镇守与生产,而将吐蕃势力排挤出去。而傈僳的地位比之“和姓”麽些更低,受木氏土司盘剥。丽江塔城洛固村和姓老活佛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该村寨有傈僳居住,后来藏族与木土司打仗打了很久,藏族与吐蕃轮流占领这里,傈僳就迁走了。今天怒江傈僳族括氏(荞氏族)的口述历史也反映了明代傈僳与麽些、吐蕃之间的关系:“据说很早以前,傈僳人住在金沙江边,那时藏人很强悍,丽江的‘木天王’(木氏土司)害怕他们,遂挑动木必扒去打。木必扒上了木天王的当,领着兵杀死了不少藏族。等藏族的增援队伍到了后,木天王撒手不管,寡不敌众,木必扒只好带领弟兄们和老小开始逃跑。一边跑一边和追来的藏族打。……木必扒打了胜仗,趁势爬过碧罗雪山,征服了怒族。”[6](P5)到怒江后,又以射箭试武艺而折服了木天王派来怒江收门户钱的代表,就提出要求:“什么我都不要,把你们剩下的汤水给我喝一口就行了。”[6](P6)木必扒成了木氏土司在怒江流域的代理人,怒江傈僳与木氏土司就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木必扒是荞氏族的首领,故又称为括木必(比),是傈僳族众多口述史中屡屡提到的一个英雄人物,实际上是众多傈僳民族迁徙传说中的“箭垛式”人物。这个传说不唯在荞氏族中长期流传,甚至成了怒江傈僳族以及迁居缅甸、泰国傈僳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可见木氏土司与吐蕃战争已铭刻于其历史记忆中。由此可知民族战争对于民族认同感的激发作用。战争中,敌对双方因对彼此间政治上的冲突有强烈的感受,因而有可能有意放大其文化差异性。因此,傈僳逃避战争向西迁徙,就是一个与统治民族在心理上“疏离”的过程,而大规模西迁行为及其后所积淀的历史记忆,则不断强化着其内部认同心理。
傈僳迁徙到澜沧江、怒江流域之后,在与早就生息于此的其他民族(族群)的接触中更显示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仅从与其同源的该区域“卢蛮”来看,因长期封闭于澜沧江、怒江峡谷而导致的文化封闭性,与从金沙江流域接受了更多的汉文化与麽些文化影响的这部分“卢蛮”后裔“栗粟”相比较,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明显。而且,因傈僳人多势众,作战能力强,在生产生活适应性上占据优势,到怒江后又从木氏土司手中获得了对怒江其他民族的管理权,这就有可能有意彰显其作为强势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从而强化其内部的文化认同与对其他族群的文化区分。总之,傈僳大规模迁徙怒江后,在统治怒江“卢蛮”后裔怒、勒墨人(白族支系)、白衣(即摆夷、傣族)“成为被统治民族”过程中,[1](P123)不断加速与增强着内部文化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不断加速与增强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发展趋势,从中进一步强化了其民族认同心理。
三、清代,在反抗异族统治中傈僳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后,维西傈僳并没有摆脱异族统治,只是统治者由丽江木氏变成维西麽些土司。这与维西险要军事位置与清代中国西南改土归流大趋势有关。
陈宗海《丽江府志略》载:雍正七年(1929年),“以其(维西)为云南西北门户,乃分隶鹤庆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设兵,于旧头目七人,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四,分治其地,而约束于通判”。在元代维西地带磨些与“卢蛮”“参错而居”;明代麽些木氏土司与吐蕃战争中,又将大量的麽些人口迁徙于此驻军与耕种,麽些在区域政治地位上、经济上、人口方面都占优势;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都不得不依靠、扶持麽些“旧头目”为千总、把总,继续对维西地经营管理。从此,维西傈僳就处于维西麽些土司与清朝官兵的双重统治之下,并与其产生矛盾冲突。终于在嘉庆七年(1802)酿成为时两年的恒乍绷起义,《滇系》载:“力些藤鲊(乍绷)知医药,所治病即愈,只博酒食,却钱币,诸夷咸亲爱。驻防某千总赫以邪教,得赂方止,已非一次。继之者大有所欲,诱而系之空室。于是夷众愤怒,持械劫之去。驻防以作乱报,维西协付将即令千总以兵五十征,拒捕反斗,伤兵十余人,并杀千总,史遂未可已。”该史料一方面说明栗粟的“占卜疾病”、“打鼓念经”宗教巫医之术已成为其文化特征之一,而且成为集体动员的力量。在纳西象形文字中把栗粟族称记录为“竹签打卦”之人;③ 另一方面由此激起的民族起义,以及被土司武装与总督觉罗琅玕联合镇压的残酷之举,对傈僳影响甚大。“这次事件后,大批傈僳族被迫渡过澜沧江、越过怒山(碧罗雪山)山脉,迁居到怒江两岸居住,一部分继续往西迁徙到中缅未定界。二十世纪初期,部分傈僳族又逐渐向西迁至密支那一带。另一部分傈僳族往南沿高黎贡山山脉迁至腾冲、保山及德宏地区,并继续往南发展,达于耿马、镇康及阿瓦山区”。[7](P2)可见清代傈僳分布格局变化中,傈僳与区域内其他民族关系紧张是使其遍布三江流域的主要原因之一。麽些土司与清朝军队的残酷镇压,强化了傈僳与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反而有助于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而使民族认同感更为强烈。
清代后期,傈僳族与异族统治者的矛盾转移到了怒江流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泸水称杆傈僳族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而镇压起义“有功”的白族、彝族头人被朝廷赐封土司职务,傈僳与区域内其他族群关系的紧张程度有增无减,迫使其继续往南、往西迁徙。至今,怒江、缅甸的傈僳中还留存有其祖先居住丽江、维西的历史记忆;而在缅甸、腾冲、德宏等地傈僳中还拼接上了“故乡石月亮”(在怒江峡谷)的历史记忆。民族起源与迁徙的历史记忆,应该是民族认同心理的一种反映,在经世累代的传承中不断强化着内部认同。其中,傈僳族与统治民族关系紧张所造成的隔阂,成了其民族内部认同的强化剂,深深地铭刻于每个傈僳人的头脑中,成为口述记忆文本,不断地固化着其民族认同感。
四、民国时期,多重压迫下傈僳与统治民族的隔阂
民国以后,导致傈僳搬迁到中缅未定界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异族土司的剥削。“由于长期的统治剥削,生产得不到发展,百姓生活十分痛苦……不敢反抗,只有消极的逃避,所以常常发生严重的迁移现象。如登埂土司境的老百姓迁往百多里外的片马”。[6](P246)“全泸水以该区(老窝)的负担最重,所以老百姓都要求划归碧江管,有的已迫不及待自动搬到碧江或未定界去了”。[6](P241)
同时,国民政府“开辟”怒江也导致一部分傈僳逃难到未定界居住。“自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等处设置设治局后,汉人来傈僳社区者日益众多。殖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④“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李根源委派……任(宗熙)、景(绍武)两员率拓边队八十多至丽江,分路并进。……该地土人,聚众顽抗,不愿归顺,并以弓弩、毒箭伤官兵。后来终以弓箭敌不过枪炮,才投降归服。从此以各队震慑两地(上帕、知子罗)改为行政区域”。④终于通过武力手段将统治绳索强加在怒江各族人民身上。“那时老百姓的负担相当重,每户要缴粮二斗,缴纳各种经费(包括党部、设治局的经费和兵役费等),每户半开八元,其中仅兵役费就是半开8角至1元。每换一个局长或乡长,每户要送二、三元的礼品,另外每户还要给他们三、四元的养家费。各种苛捐杂税加在一起,每年每户平均要缴十五、六元半开。当时老百姓忍受不了,跑到未定界,据说有五、六十户,约二百四、五十人”。[6](P54)
因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引起的傈僳反抗事件屡屡发生,也导致傈僳西迁缅甸。“过去国民党派到福贡的官,对地方没有一点建树,只是剥削一点就走了,然后又换来一个,人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史国英任福贡设治局长,一个案子要罚款几十两,并加重其他税款。另外他兼做生意,无钱买的让你赊,限期付款。到期不能付款的,就被拉到县府扣押追缴,人民为此而出卖田地、儿女的很多,激起了公愤”,[6](P12)傈僳人拿起弓弩、大刀,打进衙门杀死了史国英夫妇,和他的师爷、舅老爷、伙夫等九人。[6](P10)国民党调集常备军和陆军官兵一千六百多人,对起义者与无辜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使得福贡县的傈僳族百姓700多户六千多人背井离乡,逃往缅甸。⑤
此外,傈僳与“汉商”的矛盾隔阂也很深,不堪汉商剥削西迁缅甸的傈僳也不少。“知子罗行政委员董建芳(鹤庆人)就任时带来鹤庆汉商刘子明、刘显清二人,官商合资在知子罗开设‘天宝号’,卖布、煮酒、卖盐。本来一升包谷可以煮六碗酒,但是‘天宝号’只卖给一碗。喜欢吃酒的傈僳族人民,每年被‘天宝号’剥削去的包谷,不知有多少斤”。[7](P4)一些“汉商”常常凭借国民党势力,甚至有些人还担任了国民党的基层官员。如张连逵任国民党福贡设治局的检察委员,李恒丰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些亦商亦官的“汉商”用煮酒、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等方式,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他们大多空手而到这里,有的不久即成为富户。“此间所称之汉商,实际包括有其他职务而以经商为副业的在内”。④ 维西人李恒丰,汉族,原是进来福贡给人做帮工的,后来用薪水做本钱到兰坪县营盘街买来盐,在福贡高价出售,然后用换来的粮食煮酒、做豆腐、喂猪卖,进行不等价交换。利润越滚越大,积存了的钱又用来放高利贷,朱米都村傈僳族村民何阿珍因还不起高利贷无法生活,逃往密支那后不久即死去。⑥ 怒江汉商中如李恒丰这样发迹者并不少,当然如何阿珍这样被逼逃往缅甸的也不少。
军事镇压、政治统治、经济盘剥,使“傈僳对外来人之态度一般言之为畏惧疑忌,盖傈僳因常受汉人之压榨剥削,故认汉人多数为凶狠刁狡”。④ 而“汉人中实际有一部分属么些(纳西族)与民家(白族)人,但彼等自认为汉人,一般人亦以汉人称之”。⑥ 因此,民国时期傈僳族与所谓汉人的关系,也包括与纳西族、白族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汉人是被优待的,不纳政费,不应夫役。和设治局有关系的汉人,设治局还可以给他们派民夫。傈僳、怒族、勒墨都不敢得罪汉人”。[6](P10)“驻傈僳社区之汉军,以及贸易边地之汉商,多系奸诈之徒,自私自利,盘剥傈民,欺之侮之,用种种伎俩而凌辱之,蹂躏之,戏弄之,俾傈民无以自容,无以自忍,无以自耐,饱受着诸多不平条件所压迫。是以傈僳自由之天赋,似有被汉人夺去,竞相谓曰:‘汉人没有好的,乌鸦没有白的。’对于汉人之印象,有如是只恶劣焉”。④ 显然,“汉人”进入怒江,不但使傈僳与其文化差异性凸显出来,而且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加深了心理隔阂,使傈僳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这过程中,傈僳族西迁中缅北界未定界事件屡见不鲜。
五、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下的傈僳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1949年,怒江地区和平解放,傈僳族摆脱了异族土司与国民党设治局的统治,也结束了异族商人剥削的历史,尽管因历史上长期不平等民族关系的阴影一度存在,也因1958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曾经错误执行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的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傈僳人西迁缅甸。但是共产党执行、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中国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主流,傈僳族对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而皆有切身感受:首先是傈僳族成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有着同等的民族生存与发展权利;其次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在中国云南,除了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之外,在各地傈僳族聚居区成立了傈僳族乡,傈僳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惠;第三,傈僳族作为跨界民族,大多居住在边境地区,因而还受到兴边富民等特殊优惠政策。
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促使傈僳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和强化,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傈僳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对自身的权利给予了更多关注与诉求。这在一些傈僳族精英身上较为突出。他们在自身努力与共产党培养之下,在政府、学界、经济等层面为傈僳族赢得地位与声誉,也在傈僳民族凝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怒江州原副州长和金玉自己筹资拍摄了傈僳族第一部电影《怒江魂》,鼓励缅甸傈僳学会会长撰写缅甸傈僳族史;原州长邱三益退休之后,自筹资金在怒江开办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吸收大量傈僳族劳动力,其中有来自缅甸的傈僳族民工;保山市政协主席胡应舒长期积极扶持帮助傈僳族青年求学成才,同时在研究傈僳族历史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还亲自带着傈僳徽章、电视机、电脑等前往密支那,赠送给缅甸傈僳学会;云南傈僳族学会会长鲁建飚积极致力于傈僳学的创建发展,邀请缅甸傈僳学会参加2009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傈僳族文化专题会议。他们来自不同的傈僳居住地,共同的特点是其关注视野已经超越了地方、区域的范围,而放到整个傈僳族层面上,甚至包括缅甸傈僳族。于是,傈僳族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就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傈僳族范围之内,同时也影响到了国外的傈僳族当中。而他们作为民族精英,被中国各地、被中国与缅甸的傈僳族所共同认可。
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对于作为民族标记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于拥有与分享共同文化的群体的认同,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阔时节、刀杆节,还有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故乡石月亮(在怒江峡谷,傈僳族有附着于石月亮的兄妹成婚、民族繁衍的创世神话);另一方面是对于“傈僳族”身份价值的认同,即共产党的民族优惠政策,使得傈僳族在自治地方拥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基于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原因,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并由此来标明其民族身份而加以维护利益权利。福贡县腊乌行政村在历史上为怒族聚居地,近代以后人口构成发生变化,1949年以后,傈僳族成为本村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与怒族、独龙族“变为”傈僳族有关。这种“变”,一是外界认为本村是典型的傈僳族村子,政府部门登记户口时不加以调查就把一些怒族、独龙族填写成傈僳族;二是村子里傈僳族占多数,怒族、独龙族受傈僳族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显性和隐形的民族“边界”都越来越模糊,于是越来越多的怒族和独龙族对外也称自己是傈僳族;三是填写傈僳族,意味着是民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其民族身份在政治、经济资本兑换过程中的“含金量”相对高。因此,在共产党民族政策下的傈僳族认同感,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是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利益意义的民族认同感。于是,各地傈僳族,特别是一部分民族精英以服饰、节日、族徽等等来有意彰显其民族性。
六、作为迁徙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1949年前后,面对历史巨变,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阴影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蛊惑造谣,曾使得一部分对共产党心怀疑惧的傈僳人逃往缅甸。美国牧师马道民说:“共产党是魔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共妻,不准教民信教。见了老人就杀害,抓着小孩就用石碓舂死。”[8](P1098)就有不少傈僳人跟随外国传教士跑到中缅未定界——葡萄、江心坡一带。如贡山有242户傈僳族跟随法国传教士莫尔士搬到未定界去居住。[6](P27)福贡县神召会一部分傈僳族跟随马道民跑到独龙江,再继续迁到缅甸境内。[6](P29)在密支那调查发现,大约一半以上的傈僳族居民迁徙到缅甸仅有三至四代的历史,大约七、八十年的时间,也造成了缅甸傈僳族人口数持续增长。在缅甸,主要从中缅北界到密支那,傈僳族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相同的族源、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以基督教堂为核心的一个个傈僳族社区中浓厚的傈僳族文化氛围就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具体体现。
缅甸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致迟在元代,傈僳先民“卢蛮”就已迁徙居住于怒江以西地区,明清时期不断有傈僳迁入此地。更多的傈僳主要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剧烈变迁及大规模政治运动期间和其后大规模迁入缅甸的,迁徙人口规模较大,使其比较容易保留其传统文化。傈僳族迁徙缅甸之后,长期与缅甸北部地区的缅族、克钦族、阿昌族、掸族、德昂族、怒族、独龙族等相处,经历了一个从依附缅甸主体民族到与其疏离的过程。从语言方面看,学会克钦语与缅语,是傈僳族在缅甸北部生存的第一技能,因此,缅甸克钦邦的傈僳族大都会讲克钦语与缅语;从基督教信仰看,傈僳族在迁入之初,教会势力尚小时,依从西方传教士的建议,参加了克钦族的教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傈僳族教徒人数、教堂和神学院数量都达到一定规模之时,就从克钦教会中分离出来。这是密支那傈僳族与周围民族关系中的生存调适。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族群之间的整合与分离。与同样迁徙自中国怒江地区的怒族与独龙族,傈僳族又以“老大”的包容之心,形成一种民族认同与区域相同并存的现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迁自中国的独龙族因与缅甸日旺人同族源的关系,而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怒族则更明显,虽然曾一度自称“傈僳”或“傈僳一怒”,把自己融入傈僳族当中(目前缅甸傈僳学会中还有一位怒族担任副会长),但是缅甸怒族已经开始着手成立怒族学会,并想通过创制怒族文字等来显示自己的民族性。对此,缅甸傈僳族学会会长阿此说:傈僳与怒族是一家,在中国一样,在缅甸也一样,我们傈僳族要团结,跟怒族、独龙族也要团结。这是同源异流民族的区域认同与族缘认同相互交织的表现。
无论是缅甸傈僳族与克钦族、缅族关系的变化,还是傈僳族与怒族、独龙族的关系,都有移民身份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生存需要,使得缅甸傈僳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调适着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笔者去缅甸调查期间,尤其在傈僳族聚居的密支那众多傈僳村子,深深感受到缅甸傈僳族强烈的民族认同,不仅体现在缅甸傈僳族内部,同样体现在对来自中国的傈僳族同胞上。大多数傈僳族敢于身无分文就迁徙缅甸,这与“老移民”同胞对于“新移民”的接纳关心有关。刚到缅甸,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也可以生存,因为可以借(还不起就成变相地要)房子、借粮食、借地、借钱,在傈僳族社区里傈僳族所受到的扶持帮助,大多是来自本民族同胞。更重要的是傈僳族在缅甸定居下来后,首先要靠本民族头人为其担保,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缅甸国籍这也同样需要同胞相帮。可以说,每一个傈僳人从移民身份到缅甸人身份的转变中,从逃难而来到在缅甸谋生立足、发展,都在傈僳族社区里实现,从中每一个傈僳族个体都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深的依赖,无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作为移民的民族历史记忆的扩散过程,傈僳族关于来自怒江石月亮的历史记忆,不仅在迁徙自怒江的傈僳族中传承,甚至在迁自腾冲、德宏、临沧等地的傈僳族中也广为传播。民族历史记忆的扩散过程,本身就是民族意识越来越一致、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往自然资源丰富而山高皇帝远的中缅边界地区迁徙,是历史上傈僳族寻找经济资源与区域内民族关系紧张双重因素下的生存选择。自明代以来,傈僳族先民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关系和地位对傈僳族民族认同感的演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傈僳族大规模迁徙缅甸等国之后,因其特殊的民族关系,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调适,并出现相应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体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之下的民族意识有一定差异的缅甸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即其民族凝聚力、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更为强烈。主要是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以及所在国家民族政策皆对其民族意识产生着重要影响。总的说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导致傈僳族跨界分布的原因之一,而傈僳族跨界分布的格局又激发、强化了其超区域、超国界的民族认同感。
收稿日期:2010-07-16
注释:
① 赵万里校缉引.寰宇通志[M]一一三引:元一统志·丽江路[M].(P94)
② 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第35页:“蒙夔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
③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M].成都:西南民族学院,1986.P1
④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M].成都:西南民族学院,1986.P9、15、168、147.
⑤ 史富相.傈僳族迁居缅甸的历史:福贡政协文史编辑室.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M],1995.P94.
⑥ 保维德纂修.上帕沿边志(民国二十年抄本):怒江州志办公室.怒江旧志(内部刊印)[M],1998.P135、P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