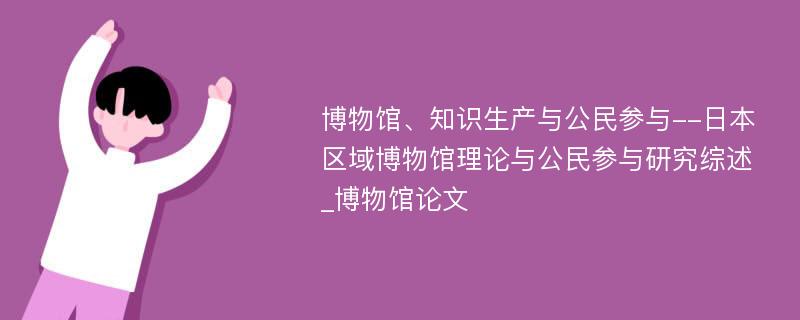
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市民参加——日本地域博物馆论与市民参加型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物馆论文,市民论文,日本论文,地域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6-039-045 前言: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市民参加 如何强化博物馆作为公共场域、公共论坛的角色,乃是今日博物馆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增进博物馆与公众,包括利用者(Visitor)、观众(Audience)或相关社群(Community)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具体的做法如改善博物馆的可及性,留意博物馆相关社群的多样性与需求,①甚至开放博物馆过程的公共参与,例如为展示诠释加入观众意见,与相关社群共同规划展览或教育活动,或者如公募市民参加博物馆评议会等等。换言之,在增进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的课题上,目前的相关研究指出,博物馆可以/应该改善其管理与观众服务,提高博物馆对多元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相关议题的关注,并在做为博物馆专业职能象征的展示与教育之操作上尝试新的技术,让公众得以参与博物馆的知识生产或相关事务的决策过程。 有关于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巴瑞特提出更基进(Radical)的意见,②将博物馆的知识性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以及博物馆研究员(Curator)的角色与职责带入相关论述。巴瑞特指出,搜藏、研究、展示与教育等知识性功能,乃是博物馆做为一个公众文化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担负这些工作的博物馆研究员,既是博物馆知识生产的核心,也是与观众接触的接口。过去将博物馆生产知识、发挥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职责的核心聚焦在博物馆研究员身上,但是博物馆这种机构更具有扮演这种角色的潜能,这个观念将可重新建构博物馆研究员的角色、职责、甚至涉及专业培育的方法论。过去,研究员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权威,是博物馆内的全知者,因此反而成为公众参与博物馆的屏障。然而,面对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性课题,研究员也应该扮演“协助者”(Facilitator)或“适当的参与者”(Appropriate participant),甚至让非专业者加入知识生产的团队,以助博物馆有关知识生产的实践(Curatorial practice),增强博物馆做为公共场域的意义。[1] 有关非专业者加入博物馆知识生产的实践,巴瑞特(Barrett)引用克瑞普(Kreps)提出的“适用博物馆学”(Appropriate museology)概念,认为典范型的博物馆专业职能应该发展出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能涵纳地方知识与资源的运作方法,以使博物馆更能符合特定的地方与社群需求。例如,博物馆应重视地方既有的、传统的对象照护与知识生产的方法,并与博物馆专业机制整合,为地方社群建立参与博物馆实践的渠道,除了能提高社群对博物馆的兴趣,亦有助博物馆发挥协助照护地方上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的功能。[2] 日本1970年代以降地方博物馆实施的市民参加型调查,为博物馆知识生产过程的公众参与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实践方法。所谓的市民参加型调查,其基本型态是由多数非专业的居民参与博物馆有关地方的调查活动,目前所见案例调查主题以地方的自然与生态居多。调查成果除了为博物馆增加标本搜藏,累积解读地域生态的第一手资料,也被运用到博物馆展示之中,成为有关地方环境与生态教育的内容,而实地调查的经验也成为市民认识地方自然、关注地方环境保全课题的发端。 从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的角度来看,市民参加型调查的实施模式有两个重要的特色。与克瑞普研究的印度尼西亚案例相反,日本的博物馆学艺员③为研究、搜藏等专业职能的运作发展出非专业的公众也能参与、对知识建构有所贡献的机制。市民参加型调查的队伍由专业者与非专业者共同组成,调查的架构与方法的规划,以及数据的整理与解读,需要高度专业知识;调查所需规模,如果没有多数居民参与则无法完成,而地方居民的参加,也提升了共同调查活动的地方环境教育意义。 此外,更重要的是,市民参加型调查的实施,乃是受到日本地方博物馆治理观的影响。日本的地域博物馆论指出,从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立场出发,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公共意义)在于以彻底的地方研究为基础,确保居民学习的权利,并与地方居民建立伙伴关系,协助居民面对地方课题。此论述兴起于1960年代,虽经衍释与补充,然其核心观念一直延续至今。④ 为了理解日本地方博物馆市民参加型调查实施的背景、运用方法与意义,本文梳理日本战后的地域博物馆论述,对地方博物馆治理的影响,以及市民参加型调查几种不同的实施模式,最后检视这种独特的地方博物馆实践对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课题的启发。 一、日本战后地方博物馆论述 在日本,认为地方的博物馆应有独特的使命与经营哲学的想法,到了1960年代末才出现。在此之前,所谓的“地方博物馆”,或是从设立者的角度,指由地方公部门设立的博物馆,而其型态几乎都是以既有国立博物馆的缩小版来想象;或是从搜藏的性质,指搜集保管地方乡土资料的博物馆,经常被称为“乡土博物馆”。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地方”,或者是相对于国家或中央的行政单位,或者是一种狭义的乡土概念。[3] 战后由于地域主义思维的启蒙,日本经济与社会体制逐步走向地方分权,地方的治理注重地方意识、认同与自立,所谓的地方,才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各自独特历史、自然、产业、人文的真实存在,特别是1970年代以降日益显著。日本地方公部门设立的博物馆即在此背景下蓬勃兴起,被视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媒介之一,与地方发展计划关系密切。[4] 对地方博物馆的治理提出明确主张的,始于1960年代,以日本的博物馆法(1951年成立)所提示的社会教育机构性格为根本,从博物馆与地方的关系,提出搜藏、研究与教育之应有的方针,主张博物馆应着重地方的搜藏与研究,促进并保障地域居民的学习权,总合复数领域的博物馆更能符合地方的需求等。1980年代,伊藤寿郎(1947-1991)提出“第三世代博物馆论”与“地域博物馆论”,成为日本地方博物馆的理想,对于日后地方博物馆的论述与行动有一定的影响。[3] 伊藤的“第三世代博物馆论”,从历史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角度提示博物馆社会定位与功能的转变。伊藤将博物馆的发展分为三个世代:第一世代的博物馆以搜藏、保管具有稀少价值的数据(宝物)为使命;第二世代博物馆搜藏的类型开始多样化,而以数据的公开为使命;第三世代的博物馆则是基于地方社会的需求而运作,并以市民的参与与体验为经营轴心。伊藤指出:这三种世代的博物馆虽然是前后出现,但今日呈现并存的现象。[5]141-154 “地域博物馆论”则从博物馆与所在地方的关系,提示新的博物馆治理哲学,主要论点有二:第一,主张以往运用通论式的科学方法来搜集与诠释地方资料的做法,应该转向以地方课题为轴心,总合地运用科学方法来发现地方数据的价值。第二,不同于以往把市民当作观众,是博物馆启蒙对象的观念,主张市民应为认识、解决地域课题的主体,而博物馆则应运用其各种功能来培育这样的精神。也就是说,“地域博物馆”是一个以地域课题为主轴,透过博物馆的搜藏、研究、展示、教育等活动,引领地方居民认识、发现地方,甚至解决地方课题的场所。伊藤认为地域博物馆论逆转了以往博物馆经营的方法论,乃是一个基进而有革命意味的理论。 伊藤等有关地方博物馆的论述可说是日本在地博物馆学的代表。比起战前博物馆作为创设近代国家、移植西方国家制度一环的国家论述,以及战后依附地方发展计划的地方论述,地域博物馆论乃是地方博物馆的在地实践、反省与展望的总合,反映了日本地方博物馆独特的地域观、治理哲学与方法论。如果对照欧美以生态博物馆论、小区博物馆论为地方型博物馆论述的核心,伊藤的论述则是针对搜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并俱的地方中小型博物馆,着重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性格,并特别强调专业博物馆学艺员的重要性。伊藤将县市立博物馆视为论述的主要对象,也可以说是日本战后普设县市立博物馆现象的反映。 从博物馆治理的角度来看,伊藤寿郎有关博物馆与地方连结的主张,有几个重要的方法论:一、地方博物馆应该参与地方社会文化建构工作。地方博物馆不是自成体系、自我完结的知识库,博物馆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现问题与对应问题的手段。二、博物馆与地方居民不但关系密切,更应该发展出对等的伙伴关系。三、博物馆应该透过其独特的专业功能(搜藏、研究、展示、教育)之运用,来实践上述两个目标,因此,具有专业训练的博物馆学艺员有其重要性。 从日本博物馆史来看,以伊藤为代表的地域博物馆论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目前针对伊藤博物馆论影响之深入研究还有限,总体来看,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地方博物馆关注的知识内涵,从以科学方法为核心生产的通则性科学知识,转向以地方田野为基础的地方科学知识,并讲求运用不同科学领域的方法论,例如,自然史博物馆从自然史知识转向关注环境与生态,并注重自然与人文的关联性。 二、地域博物馆论之博物馆与市民 在伊藤的地域博物馆论中,市民与博物馆关系的建构是地域博物馆论的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方法论。伊藤想象地方博物馆所面对的不是一般而没有个别性的观众,而是在地方生活、具有高度自主意识,与博物馆有共同连带关系的市民,市民的参与也是地域博物馆理念实现的必要条件。 伊藤有关市民与博物馆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三个面向:⑤ 一是博物馆与市民学习。市民不是博物馆启蒙的对象。博物馆应保障市民学习的权利,协助市民进行自我教育,成为面对地域课题的主体。二是博物馆与市民参加、体验。市民主体的参加与体验是博物馆经营的主轴,博物馆除了应提供市民主体参加博物馆活动的场域,并提供不同阶段持续学习的机会,也应逐步累积市民学习的成果,再公开还原给地方。三是博物馆与市民运动:博物馆应该与地方市民团体有所连结合作,但是与市民运动之间的关联应该限定在教育性的面向,市民运动的主题不能直接成为博物馆的课题,而应转化为适合博物馆对应的课题,予以协助。 伊藤有关博物馆与市民关系的论述,乃是受到数个地方博物馆实践的启发,并以教育学者海后宗臣(1901—1987)的教育论为基础总合而成。伊藤引用海后宗臣将近代教育分为“知识者养成型”以及“生活者养成型”两种教育观,指出既有的博物馆采取第一种,而地方博物馆应该采用第二种。“知识者养成型”教育观乃是近代国民教育的目标,透过教科书的编辑,提供所有国民相同的教育内容,以教导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的知识为主。“生活者养成型”教育观从生活之中发现教育课题,教育的内容具体而有地方性,也应该在地域的实际生活中进行学习。教育方法则重视学习者自我学习、思考、表现能力的培育,学习内容只是培育这种能力的媒介。[5]160-162。 伊藤有关博物馆与市民的主张,可以视为地方博物馆教育方法论,包括市民做为学习者的性格、教育活动的规划方针以及地方社会资源的运用方针等。不过,有关市民的参加与体验,由于强调博物馆应开放市民主体性参与博物馆事务,其实已经超越了教育论的范畴,涉及博物馆治理的课题,在此市民的角色也超越了向来辅助性质的博物馆志工定位,可以说是地域博物馆论中最基进的主张。 三、市民参加型调查与博物馆 由非专业者的市民参与博物馆有关地方的调查研究工作,常见的型态如协助研究员进行标本或数据整理等,分担研究工作中需要大量而反复性劳力的部分,或者将研究型的田野调查活动规划为单次性教育活动,带领市民/参加者一同走访地方田野。日本地方博物馆所发展出的市民参加型调查,可说是日本地方博物馆实践中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新博物馆技术⑥,也是最能彰显地域博物馆论精神者。 在日本,大规模生物调查的实施可追溯至1960年代,当时由于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带来重大社会问题,相关计划希望通过生物调查来掌握环境污染的实态,但这类调查需要一定专业训练,非人人可以参加。一般市民参与的大规模生物调查首见1971年兵库县,民间社团“自然保护协会”为了促进居民关心生活周遭环境问题,开始尝试规划一种让一般市民也可参加的环境生物调查模式。⑦ 1970年代后半以降,在环境省厅局行政系统、地方博物馆与民间社团的推动下,市民参加型生物调查逐渐成为日本环境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博物馆规划执行的市民参加型活动,调查结果更为细致,由于与博物馆研究、搜藏、展示、教育机能的整合,环境教育的意义或者有关地方公共意识的启蒙,也得到较好的成绩。此外,环境行政系统所推动的主要是“指标生物调查”类型,而博物馆规划推动者较为多元化。从进行的方式、条件和意义来看,可大分为三种类型:指标生物调查型、地方自然志建构型以及总合环境教育型。以下就三个类型的代表案例加以分析,包括博物馆治理方针、调查活动的实施方式、成果与影响。 (一)指标生物调查型 指标生物调查,或者称为环境指标种调查,是市民参加型调查最普遍的类型,指通过对某个特定条件敏感的生物为媒介,藉由对该生物生息状况的调查间接掌握环境的变化,该生物则称为指标生物。[6]此种调查原是为了掌握公害污染状况而实施,调查的实施或资料解读都需高度专业知识,之后在指针生物的选定或调查结果的判读,发展出适合大多数非专业者进行的模式,转化为适于市民环境教育的手段。 指标生物调查转化之所以具有环境教育意义,除了这是一种学习自然知识的方法,更在于通过自然生物的观察,体会人与环境的密切性。因此,市民参加型调查所选定的指标生物,并不是用来掌握复杂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是藉以理解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市民参加型调查指标生物的选定原则如下:可以做为理解环境变化的指标,例如都市化、外来种侵入状况等;在人类生活周遭生息而且具有亲近感的生物;容易发现、种类判别也较为简易的生物;可以由非专业者进行调查,而且调查活动对其生息不会有太大影响。[7]博物馆的实施案例,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者为平冢市博物馆。伊藤寿朗指出,1976年开馆的平冢市博物馆是日本第一个在博物馆条例中明列研究田野范围的地方博物馆,第4条第1项指出:“收集、保管、展示有关相模川流域的自然与文化之实物、标本、模写、模型、文献、图表、照片、幻灯片等博物馆数据”,明确博物馆研究对象,打破行政区划之界限,打破人文与自然领域的界限,开启总合型地域博物馆之先例。[5]95-98 (二)地方自然志建构型 以地方自然志建构为目标的市民参加型调查以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为代表,该馆也是启发伊藤的案例之一。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设立于1952年,确定以追求学术价值与成绩为目标,并发展出博物馆研究者与市民共同进行地方自然志调查、标本收集的特殊模式,今日不但建立140万件具相当规模的地方自然标本收藏,也以自然史业余研究者的重要据点而闻名。近年,博物馆的定位从“自然史研究”正式变更为“地方的自然志信息中心”。[8] 1960年代,第二任馆长千地万造强调博物馆建立学术价值的重要性:“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从地方的自然与身边周遭的现象出发,是地方自然史博物馆的原则”、“长年累积所建立的搜藏,必然在分类学、地方的生物志与地质志上建立学术研究的价值与贡献,如此博物馆不只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而是一个在地方研究上不可或缺的设施,如此才能稳固博物馆的地位”。[8]1970年代,博物馆学艺员日浦勇提出“彻底的地方主义”之概念,认为地方博物馆的出路就在对于“地方”的彻底研究与展示。日浦勇鼓励博物馆学艺员建立自己的同好社团,认为应该以专业标准来带领社团的活动,藉此培育业余者成为独立的研究者,未来可以协助学艺员的研究与数据整理工作,也可以增加地方自然史的研究人力。[9] 由学艺员领军的同好社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自然观察与标本制作。该馆学艺员认为,学习如何采集与制作标本是导引市民仔细观察、纪录自然的手段,也是深入体验、学习地方生态的方法,在地居民透过标本的观察制作学习地方自然,也是生物多样性管理上重要的一环。博物馆称这些参与自然观察与标本制作的业余者为“市民科学者”。[10] (三)总合环境教育型 总合环境教育型调查的模式以指针生物型调查为基础,但是相关调查延展到人与社会的变化,因此在环境教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最著名案例是滋贺县立琵琶湖博物馆(1996年开馆)所实施的“大家的萤火虫调查计划”。该馆以“人与环境”、“人文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关怀,以成为引导居民走入地方田野、关注地方环境保全课题的媒介,创造地方上人与人交流契机的平台为目标。⑧ 承继第三世代博物馆论的理念,琵琶湖博物馆提出,观众不应该只停留在“观看”的阶段,而应该成为博物馆活动的主体,因此将博物馆“观众”称为“利用者”,并标榜成为“以利用者为主体的博物馆”、“由馆员与利用者共同进行研究、展示与教育交流活动”的“参加型博物馆”。该馆为“参加型博物馆”提出细腻的主张:1.博物馆对于所有年龄、阶层与兴趣的利用者,都能提供适当的对应并使获得满足感。2.博物馆能提供、或协助规划由利用者为主体、表达自己意见的活动。例如为参加型调查成果举办发表会或出版,日常的博物馆活动,也为利用者规划能直接表达意见或参与的机制,甚至协助居民组成同好会或社团,持续地进行相关活动。3.博物馆能够规划进阶型活动,以带领居民一步步持续相关活动。[11] 各种参加型调查活动中,“大家的萤火虫调查计划”突破向来类似计划的格局,结合人文与自然两方,具有高度总合环境教育意义,也唤起居民的环境行动。1989年起由滋贺县琵琶湖研究所发起,乃是为了掌握水环境变化的计划之一,之后地方社团“水与文化研究會”⑨以及琵琶湖博物館结成团队,持续推动十年、共計3500人参加。“大家的萤火虫调查计划”的参加者除了观察萤火虫的出现状况之外,还包括观察地、日期、时间、天候等,特别是有关观察地点之水量、垃圾分布、护岸方式以及周遭建物与照明状况等,透过辅助表格将观察结果纪录或绘图下来。持续进行十年后,从历年来萤火虫的生息变化,观察环境的变化等,解读出萤火虫生息与地方气候、环境与社会变化的影响。⑩ 这项计划执行十年发现,地方居民与环境连带感提高了,家庭的共同话题、近邻的交流也增多了,已经被淡忘的往昔生活景象又重新回到人们的交谈中。此外,为了保护萤火虫的生活环境,也出现居民团体的环境保全行动。(11)因为参加者除了藉由调查了解生态环境,透过萤火虫也仿佛看到了自己于生态中的处境,因此对自我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关于环境问题,专家进行的专业调查与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地域居民环境意识的唤醒,为保护活动奠定社会基础,同样重要。市民参加型调查,希望透过参加者的实际体验,强化环境与生态学习,也是一种为地方上不同背景的居民建立相互交流与沟通管理的设计。世代住于此地的人、新迁入的人、行政人员与专家、从商与务农等等,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利益立场都不同,为了共同的环境保全问题,必需建立共识。琵琶湖博物馆将参加这类调查活动的市民称为“业余科学家”,调查所得成果称为“生活知”。从生活者的观点来呈现环境课题,也成为琵琶湖博物馆进行环境研究与展示的理论根据。(12) 四、结语 日本的地域博物馆论与治理观可以说与巴瑞特在公共性议题上强调博物馆知识生产重要性,以及博物馆应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等论点一致。日本的地域博物馆论从社会教育的立场出发,强调博物馆的公共价值在于有关地方的知识之建构以及确保居民学习权,而博物馆的研究工作正是实践两者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个理念也影响了博物馆研究员专业发展与市民(公众)关系的方向:地方博物馆的研究不应是通则性的科学,而应是以地方田野为基础,为地方建构实证的、科学的知识,博物馆研究员应与市民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博物馆的不同功能协助市民成为面对地方课题的主体。 有关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日本地方博物馆所实施的市民参加型调查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式:当面对有关地方生态、人文与民俗之知识建构,博物馆研究员有可能为专业者生产知识的方法,发展出一种可以涵纳地方居民参与的模式,不但可以推动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参与地方田野的经验更成为居民关注地方的契机,特别在有关地方的公共性议题,例如环境问题,其影响更具意义。 不论何种模式,从公共性角度观之,非专业者参与博物馆知识生产的过程,关键在于共同生产的知识应该具有其独特意义与价值,更应有助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性意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整合或开放而已。日本地方博物馆市民参加型调查的实践并不是专业调查的简易版。对博物馆来说,这些大规模的、实证的地方科学知识建构,市民的参加不可或缺;对市民来说,由专业者带领的地方田野观察经验,甚至成为地方知识生产团队之一员,是促发地方学习以及关怀地方课题,更是建立地方连带感的契机;对地方来说,这个实践建立了有关生态、环境等的地方田野知识,在相关问题上能成为与行政或专家说法抗衡的实证资料。 在日本的案例中,我们也看到建立方法论与创新机制,对于兼顾博物馆专业与公众参与的实践之重要性。几个地方博物馆为市民参加准备了不同的途径:如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着重以同好会的形式培育可以独立作业的业余科学家,协助博物馆的研究、标本搜集制作工作,也增加了地方研究的人力资源;而滋贺县立琵琶湖博物馆则强调应通过参加型调查的形式,将居民对于生活周遭的经验与感知转化、建构为地方科学知识,也提出细腻的方法论与机制,以实践其“参加型博物馆”的理念。 此外,日本的案例也提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博物馆面对的公共性课题可能因区域性文化社会脉络而有所差异。日本的研究者指出,日本有关博物馆与地域社会课题的思维和欧美不同:欧美博物馆强调如何对应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地域社会中各个不同个人的需求,而日本的地方博物馆则面对地方的所有居民,强调如何培育具有地方意识与地方关怀的居民,并关注如何通过博物馆活动使得居民有所改变。[12]日本地域博物馆论提出的公共性课题,设定为居民学习权的保障,关注地方公共课题意识的培育,以及扎根地方的知识建构等,这除了与日本博物馆法中博物馆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有关,也与日本战后走向地方分权、强调地方意识的背景密切相关。博物馆之公共性课题,不只是管理与服务、强化社会意识与创新专业操作模式的问题,更不能靠某些实践模式的套用来达成。如何在各自的文化社会脉络中找出公共性课题的核心,以此为中心发展创新机制,应该是博物馆面对公共性议题挑战的第一课。 注释: ①参见:Sandell,R.“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1998.17(4):401-408.及Fleming,D.“Positioning the Museum for Social Inclusion”.In Sandell,R.(ed.),Museums,Society,Inequality.London:Routledge,2002.pp.213-224. ②在台湾,“Radical”一词有译为“激进”,有译为“基进”,笔者择后者强调“根本的、从根基的改变”之义。 ③“学艺员”是日本指博物馆内负责研究、搜藏、展示等研究性质工作者,相当于西方所说的“Curator”。 ④水嶋英治、栗原憲司,公立ミュ一ジアムの存在理由,2009。http://www.bunkanken.com/lib_cul/vol33/01/p1.html(浏览日期:2011年1月15日) ⑤三点分别参见:伊藤壽郎著《市民のなかの博物館》第159-160.132、142、153、123-124页。 ⑥此为原琵琶湖博物馆学艺员布谷知夫先生的意见,2011年3月12日笔者通过电子信箱询问相关问题所得回复之一。其实,市民参与环境调查的模式并非日本原创,但博物馆藉之发展成符应其治理观的技术,的确是日本地方博物馆独特的实践。 ⑦脇田健一“参加型調査と博物館の役割:堀田満氏に聞く,瓦(琵琶湖博物館(仮称)開設準備室ニュ一ス)”,1994年。http://www.lbm.go.jp/publish/kawara/kawara3.htm(浏览日期:2011年2月8日)。 ⑧参见该馆官方网站有关“基本理念”说明:http://www.lbm.go.jp/active/about_us/idea.html(浏览日期:2011年2月13日)。 ⑨水与文化研究会于1989年由滋贺县内有志者结成的地方社团,第一任代表为滋贺县立大学教授高谷好一,其后由嘉田由纪子续任。嘉田由纪子1982年到1996年任职琵琶湖研究所,1997年起担任琵琶湖博物馆学艺员,也是这两个机构与民间社团紧密合作的关键人物之一。嘉田由纪子于2006年当选滋贺县知事,并连选连任,是日本目前唯一一位博物馆研究员出任地方首长的例子。参见水与文化研究会官网http://koayu.eri.co.jp/Mizubun/(浏览日期:2011年2月5日);以及水と文化研究会編《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琵琶湖地域のホタルと身近な水環境調査》,东京都:新曜社,2000年。 ⑩参见:水と文化研究会編《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琵琶湖地域のホタルと身近な水環境調査》,第10-27页。 (11)水と文化研究会編《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琵琶湖地域のホタルと身近な水環境調査》,第45-133页。 (12)参见:嘉田由纪子“住民参加による环境调査の理念と実践:生活现场での环境认识とCommunication”,《日本科学教育学会研究会研究报告》1990.4(5):41-46。布谷知夫“身近な課題から始める環境教育”,《日本生態学会誌》2006.56:158-165。畑田彩“博物館と生態学(6):博物館学芸員と地域住民による自然環境保全活動”,《日本生態学会誌》2007.57:443-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