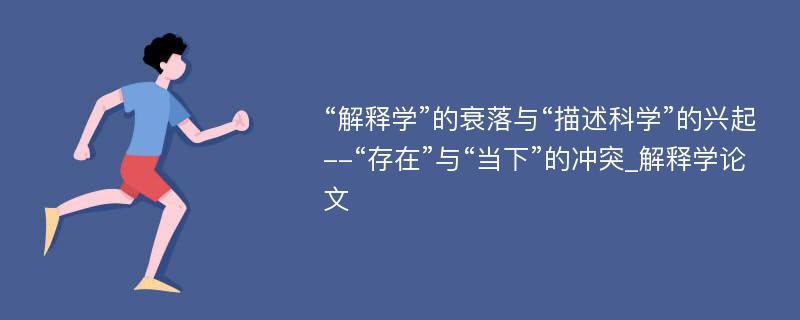
“解释学”的没落与“描述学”的兴起——“既成”与“当下瞬间”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冲突论文,瞬间论文,既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充分理解“解释”这个术语本身,我们得回到它的前提及其相关术语。解释的前提是理解,被理解的叫含义或意义。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解释”已经意味着进入哲学,“从来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马克思语)。怎么解释呢?用语言。传统上,我们往往从意识或概念领域接近解释学问题,但事实上,解释学涉及的是词语或语言本身的问题,或者说,解释学是语言学的嫡亲。
把意识或概念问题还原为词语或语言问题,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趋势,解释学也不例外。但解释学的初衷暴露出它总体上还停留在近代启蒙运动所开辟的形而上学水平上。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其试图建立“解释”的科学方法、模式,强调在对话中的共同基础即“被理解”的可能性。总之,“理解的可能性”是在对话或接触文本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种共识。就像我们坐在一起开解释学会议,最起码我们要听懂对方在说什么,这是我们继续讨论的基础,而全部努力似乎应该朝向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对方。
一
问题的焦点在于,就“理解”而言,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语言?语言究竟是理解的桥梁还是障碍?解释学事先设定了理解的可能性,这既是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也是一种固执的意志。这意志符合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它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它在理论上的缺憾,在于排除了真正的时间性。只要引进时间维度,我们就不难发现,“理解”只能发生在理解过程之中,而不能发生在理解活动之前。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理解”换成“沉浸”或者“沉醉”,意思就更清楚了,因为凡是发生“理解”的地方,往往要发生语言活动。可是,当你沉醉的时候,却几乎不发生语言活动。当一切解释、理解等语言行为发生时,这些行为不是在沉醉之前就是之后,即发生语言的同时,意味着你已经不沉醉了。如果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在沉醉发生时伴随有理解活动,那么它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非语言的理解活动,近似于无意识的直觉,这就是本文所谓“描述”。
为什么说理解不可以发生在理解活动之前或者之后呢?因为这就等于你跳出时间之外说时间。你是一个时间之外的旁观者,而不是处于时间之中活生生的生命。换句话说,你被机械生硬地割裂在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僵死的空间位置。这也是语言本身的天然缺憾——语言本身与绵延的生命是脱节的。一个概念或命题、一个词语或句子,都意味着“已经发生”的行为、既成的行为,而不是当下瞬间正在发生的行为。这个形而上学的缺憾,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因为似乎在进行普遍怀疑和推论之前,关于“我”、“思”、“在”究竟是什么意思,笛卡尔早就知道了,而批评笛卡尔的经验论哲学家们也从没有想到在这一点上做出反驳,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与笛卡尔完全一致。同样道理,我们不可以在理解活动之前,就已经切割好解释学的术语,也就是一种广义上的二分法,区分解释者的主观意向与文本的客观意义。我们不可以在脱离时间的意义上谈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融合。至于对笛卡尔的反驳,我们可以想到赫拉克利特的著名箴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人设定为哲学家或解释学家,而那条河象征着处于时间过程的生命本身。当这个人不是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生命诞生时,他已经在这条河里了,而当他后来作为哲学家想对这条河说点什么时,他说的就是另一条河了。
当我们把“既成”的概念或理解作为出发点时,麻烦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在用某个瞬间的判断代替在它之后的所有判断,也就是用瞬间代替永恒。我们将时间做了空间化的处理,并且在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假定每个瞬间的性质都是同样的,就像钟表上的分秒一样。这样,时间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就像一条河。它在哲学上的表现,见于巴门尼德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个伟大的命题,也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
说语言的性质是空间的,是指在抽象意义上,语言意味着确定性、位置、间隔。语言是对视觉空间的深化,是超视觉的。形而上学沉思就靠概念或语言实现了这种看不见的视觉,也就是德里达说的蘸着白墨水写的“白色的神话”。(Derrida,p.213)这种形而上学变相意义上的“视觉”却反过来瞧不起真正的视觉图像,因为图像不确定、难以把握。这种歧视使人们渐渐忘记了形而上学的视觉来源,或柏拉图那个著名的关于洞穴与阳光的比喻。与此同时,这种抽象的视觉异化为一种抽象的听觉,因为西方语言是拼音文字,不出声的默读也否认不了字母与意义之间建立起来的直接而抽象的关系。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基础上的哲学不可能不是观念论、概念论、理念论的。甚至可以说,西方的宗教、科学、音乐都与此有关并因而不同于东方。文字是传达信息的载体或媒介——但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媒介只是可以过河拆桥的表达外部信息的工具,而是说媒介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意义,就像通过小说或电影所表达的《红楼梦》,是根本不同的《红楼梦》,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拼音文字意味着观念论,而汉语或象形的表意文字则意味着象征与类比,这两种媒介自身就天然地携带着不同性质的信息。如果让哲学说汉语,即使是在说西方哲学,也意味着它是一种不断走神的哲学。
当语言用“准确的”理解代替印象时,语言所遗漏的是活生生的生命。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象形文字因其象征性而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它成为活的语言。相比之下,严谨、精确、特别在意立场的拼音文字却成为僵化的、死的语言。① 汉语有一双内在的眼睛,它就像能看见自身的目光一样,有一种寄生与自爱的效果,它把不一样的因素感应为一样的。天人合一的“一”不同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一”:后者的基础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前者把反映当成感应,好像镜子里的“我”其实不是我,而是陌生的它。就像古希腊神话人物美少年纳瑟斯爱上水中自己的倒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以感受为特征的理解;就像评价汉语好文章有风骨,风骨就像时间一样,是看不见的,它也像时间一样,是构成我们生命的骨架。由于拼音文字的理解是观念性的,最终将形成没有感性色彩的纯粹理解或纯粹理性。拼音文字是脱离了“原始思维”或象形思维的文字,就好像终于有一天那个自恋的美少年意识到那清澈河水中的倒影就是自己本人的“照片”,于是,就开始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历史。他从此由自恋异化为自大,觉得作为人自己高于一切植物和动物。大写的“人”是衡量万物存在与否的尺度,这是人道主义所暗含的特权思想:它要与天地与人奋斗!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这当然不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传统。“天人合一”的意思绝非人就是天,而是说在所有感应过程中,人并不高于事物:人既不高于植物和动物,也不高于周围自然环境,就像我们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看见的那样。
人是怎么觉醒的呢?沉醉不等于觉醒,因为在沉醉时人不知道,而在觉醒时,人知道。人知道了什么呢?从根本上说,人知道自己会死,而动物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尊严在于“知道”。所谓思想,就是意味着“知道”。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知道”换成“理解”或者“解释”,意思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思想、理解、解释——这些词语本身是不可能被解构(“解构”本身也是一种理解)的,它们构成人的骨架,人在它们就在。但是,我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什么叫“‘解释学’的没落”呢?因为这里的“解释学”特指对“解释”做出一种特定理解的学说,而我对这个学说或者它的方法,持一种批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愿望只是“活着”,那意味着他已经死了,因为人活着的意思绝非生物机体含义上的行尸走肉,而是指精神或者自由——人从知道自己会死的思想中获得了根本自由,从此人有能力区别实际的生命与可能的生命。这就使我们的身体打上了文明的烙印。
“会思考”指的是活的思考。就独立的个体而言,在运动变化的思考过程中思考,要远远胜过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奋勇前进式的思考。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一定如何”,这个思考模式是西方的,它僵直而死板。当下的中国学术文化界,经常以中国化了的西方思维模式反对西方价值观,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和东方文明传统。这是一种悲哀。我宁可把中国文明传统描述为沉湎于生活本身:中国人所谓“知道”,就是在这些沉湎中领悟,寻找机缘。它是一种精神,散漫任性而没有超越、没有远虑的生活态度。超越的态度是冒险而脱离实际的态度,其中孕育着宗教、科学、现代政治制度等等,它还培养起西方式的沉思,就像笛卡尔那样。我们一定要抛开西方式的概念思维,对中国的“道”或形而上学做一种感悟性理解。
只要是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某些共同因素。我这里指构成人骨架的因素(比如人性、语言、时间),这就与“解释学”的初衷相冲突。也就是说,所谓“解释”和“理解”应该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是瞬间完成的,就像男女在相貌上一见钟情一样,是一种下意识的直接反应;又像写文章,好文章绝不是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沉醉文字之中酣畅淋漓的效果(而当你想着如何才能写好时,你肯定写不好,因为想写好的愿望对能写好的能力不但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还会妨碍写好)。
我有一个比喻,不考虑绵延或时间因素的“解释学”,就像天文学里的“地心说”,它虽然承认解释角度的差异,但解释者自己是不动的,而被解释的东西要围绕着解释者自恋式的想法旋转。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限,我们“转换”解释者的状态,使他不再是生活世界的旁观者,而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使他处于运动或绵延状态,即他一开始就在赫拉克利特那条河里,也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在沉醉中理解,使沉醉和理解两个过程合二为一,从而实现一种“理解”问题上的革命,因为传统上沉醉与理解在时间上是脱节的,理解者总是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使沉醉和理解两个过程合二为一”的理解,是极其迅速的瞬间理解。懂就懂,象划过夜空的闪电;不懂就不懂。在这个过程中,光有“理解的良好愿望”和艰苦卓绝的意志是没有用的,“先验”是没有用的。“理解”成为在当下瞬间急剧变化的东西,因为任何瞬间都没有特权,或者说人生的每个时刻都是平等的。瞬间与瞬间的性质不同,任意瞬间都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它起源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偶然念头,而不要去追溯什么深刻的思想动机。
我这里“极其迅速的瞬间理解”中的“理解”,并不会在某个瞬间定格,而是流畅的、快乐的、无意识的。绵延状态中的“理解”不时改变着姿态,处于出神状态。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样的“理解”似乎是“非理解”,因为它完全破坏了习惯上对“理解”这个词的理解。在习惯上,生活状态与思想状态是隔开的:你沉醉于物质世界,你在工作但你没有觉醒,因为你不必像思想家那样思想;如果你以思想为职业,你实际做的是解释和理解的工作,你清楚你是在和观念打交道,但你远离生活世界的沉醉。使沉醉和理解两个过程合二为一,就是使习惯上被分裂的东西重新归还给生命本身;返朴归真,使物质的沉醉与精神的沉醉合二为一。就好像云彩、石头、气味、相貌都有精气神,我们爱这些东西就是爱自己。庄子在《知北游》篇中曾认为,道就在瓦砾屎尿之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不隔”(可以在他所谓“隔”的意义上将“沉醉”与“理解”分为两个过程吗?),就是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这就是“赋比兴”中的“兴”,在禅宗中叫“机缘”。“兴”是一种随机的无意识念头,把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
头脑是理解的器官,它使我们冷静;心灵才是沉醉的器官,它连接着我们的心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精神与物质彼此不分。就此而言,它与西方文化之间是隔离的。汉语说“精神”,是一种不排除物质因素的微妙精神,就像说一个人有精神,和他的相貌有关,不是“活的肉身”意义上的相貌,而是指精神气质,就像透过一个人的笔迹和文章可以洞察这个人的个性一样。
二
那么,我所谓“描述学”是怎样一幅情景呢?消解关于“对象”的意识,变对象为一个虚无。萨特说,“一切意识,正如胡塞尔所说,都是对某事物的意识。这意味着占据超验对象位置的与意识无关,或者说构成‘内容’的不是意识。”(Sartre,p.17)这意味着意识不再至上,意识不再高于事物。我们面对的所谓“现象”既不是外部的也不是内部的,而是一个等待我们去添满的虚无。这很像是自恋过程的原意,即古希腊那个美少年爱上了自己在河水中的倒影——这个道理与笛卡尔的沉思不同,因为“我思故我在”中的“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与“思”完全是一个东西,但那水中的倒影却不是这个美少年。于是“意识本身成为不能朝向自身的意识”。(ibid)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不是反思的,而是异化的。我们来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胡塞尔的“一切意识,都是对某事物的意识”:其中都有“意向性”,但前者是朝向自身的,后者却朝向不同于自身的别的东西。这里所谓意向,就是直接面对的方向(英语用for,法语用de)。我们完全不必为“思”而在,不必只有反思的一生。事实上,说“我行动故我存在”更符合实际情形。完全不必费笛卡尔那番周折。那番周折所需要的是概念,而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只是意识与行为的直接材料。所谓“描述学”所描述的,正是这些“直接材料”,它们只是一些事实而已。
就是说,所有的意识都是“非意识”,一切存在都是不同于自身的东西,这里已经静悄悄地引入了时间因素。就像在思中我们并不是在死板地专注,而总是出神。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自然而然”。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中断,就像当我们“知道”某件事时,同时就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某件事情”,这是一种共鸣的效果,只是多数人没有朝这个方向想。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跳出局外的过程。用现象学术语来说,就是意识总是朝向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用批评“我思故我在”的道理,也可以批评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因为它还是局限于“内在”而没有超越,忽略了时间因素,因为事实上,“存在”或“被感知”的东西,不是一个停顿下来已经被完成的行为。
“我思故我在”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对象性思维——它们都把文字当成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没有把文字当成表达思想的骨架。骨架不同于工具就在于,骨架是组成人自身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文字,而且时间与在时间中的沉醉,都是构成人骨架的因素。一旦你从这个骨架中跳出来,持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就像你想从时间中跳出来说“时间是什么”一样,这时你马上就会处于一种不真实状态。这里有个对待文字的态度问题,文字既可以是妨碍沉醉的,也可以是构成沉醉的。如果你让文字为“解释学”服务,那就是在妨碍沉醉;如果你以“描述”的态度使用文字,文字就构成了你生命的骨架,就是说,你处于沉醉状态。其实,处于沉醉状态与处于时间状态,是处于同一种状态的不同说法。那么,究竟怎样才是以“描述”的态度使用文字呢?就是面临陌生的局外状态,一切都不是现成的,一切都不是已经计划好的。以“描述”的态度使用文字,就是放弃“生活还是讲述”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态度。放弃日复一日安排好了的呆板生活,就像描述绝不是照着念事先写好的稿子一样——于是,我们遭遇“奇遇”。如果奇遇也是上述构成生命骨架的因素,那么我们每天的生命都会充满芬芳。文字的描述态度同时意味着我们要谨慎使用判断句,因为判断意味着绵延着的时间被拦腰切断,并且凝固成一个词语或概念。描述性文字是好奇、沉醉、出神、奇异的文字,很像是奇遇——是处于“正在进行”的文字,而非人为地利用概念或判断强行跳出时间之河的文字。我们只需要体验这些奇遇的细节,而对海德格尔所谓“平庸的时间”中的场面,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当然,这样的态度又与现象学还原连接起来。
上述“描述的文字”制造的陌生效果或奇遇效果,与时间箭头有关,即时间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意思,并非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而是说时间在投骰子,并不朝着一个方向——从过去和现在无法推断将来的东西,“描述的文字”就是描画匪夷所思的未来。在这里,预测性等于零,选择是莫名其妙的,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只是在选择;没有什么正确的判断,只是在判断;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只是在留恋。但这里的选择、判断、留恋,是指解释性文字而非描述性文字的特征。解释性文字从现在反推过去,属于“事后诸葛亮”;描述性文字永远面临未来,即使它正在描述一件过去的事情,也不过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未来事件,这就是我们正在写的句子。传统上,哲学家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是认为语言从来就担负着解释的功能。柏格森诉诸生命在时间中的绵延并且不相信语言,理由就在于语言自身的单位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是僵化的而非流动的。如果按照这样的语言解释世界,也必将是一个摆脱了生命绵延的僵死的世界:“我们一定得通过词语才能表达,那么我们的思想总具有空间性质。换句话说,语言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之间,如同在物质对象之间一样,树立种种同样明晰而准确的区别,产生同样的无连续性。”(Bergson,p.1)当柏格森用文字破除这种具有空间性质的解释学文字的时候,他的文字是描述性的。这种文字具有哲学与文学的双重属性,它不仅是关于美的文字,而且自身就是美的文字。
“描述性的文字”是出神状态的文字,任何事实都可以生生变化不息(兴),思想极其活泼。用禅宗的术语,那“兴”起思想的来头,就是机缘。“机”是飞跃性的,超因果性的。而所谓理论,常常意味着遵从因果规律性。“因果性”并非创造,而是重复。“兴”和“机”的任意性与飞跃性之特点,表明它们不仅是活泼的,而且是创造性的、生动变化的。“机”更是艺术的,我感慨于清代画家石涛的“一画之法”。他的描述正是以上“描述性的文字”的生动记录,其作品的“千古风流独绝”正是应了“机”。所谓“机会”,有“机”才有“会”。与“机会”连接的是石破天惊。所有的遇都是巧遇。写好文章也是这样,并非写出作者事先想要表达的念头,而是写出作者即刻想到的东西或者此刻还不知道的东西。这样的写作,相当于文字正处于生成状态,在写的过程中渐渐觉醒,生出秩序与逻辑。这样的文章因其一气呵成,显得漂亮与自然。那么,文字究竟是怎么“生出来的”,并在“圣人”笔下“随写随明白起来”?这正是“正在描述性的文字”之谜,连“圣人”自己都不知道。但笔下正在或就要发生的事情,是激烈新鲜的,像是精神上的高难动作,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唯一的、绝对的、无可替换的感受。
“描述性的文字”是遭遇险绝的文字,是初出茅庐的纯粹状态。比如当一个人非常出色并感到周围人都平庸时,我们说这种自豪感本身就是平庸的;相反,如果这个出色的人为自己的出色而对众人深感羞愧和不好意思,我们就说他遭遇了心情的险境,因为它稀少。这样的心情相当含蓄微妙。当我们去玩味这样的心情(相当于上述“知道‘知道’”),“险绝”就魔术般地化为幸福。它是无意中开出的花朵,“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行”。
解释学要求一种对话式的语言结构。这是一种假设的对话,对话双方(即写文章时,作者潜在假定了一个对话者)始终围绕着“什么是”做一问一答式的周旋。但是,处于描述状态的语言,却始终处于未回答状态。描述之妙,在于使我们不断进入思考的过程,而不是回答得头头是道。问题始终比回答更为重要。没有什么老师,问题都是自己悟出来的。总之,解释学的倾向,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赋”这种文体,而“描述学”则相当于“兴”,好像把思想流转于诗一样的境界。当代法国哲学家与文学家用非常隐晦的语言,不过描述了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这传统就在《诗经》中,那一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大意是说,如果人家问你看见新娘子了吗?你竟然呆头呆脑地回了一句“桃花”!这样的写作手法,就属于“兴”。为什么呢?因为“桃之夭夭”与“之子于归”之间毫无解释学意义上的关系,属于没有关系的关系,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关系。这也是“机”,瞬间灵机一动之“机”,转瞬即逝之“机”,属于那种“异在”或“缘在”的东西。这才是海德格尔的Dasein的意思。所谓“从天上掉下来”,就是“没有的有”、一种越界或“多余”的东西,比“想”(这个“想”,是解释学意义上的)还多的“想”(这个“想”,是描述学意义上的),是笔下从零开始活脱脱发出来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书写者自己在初下笔时尚不知道。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有精气神,也就是我所谓“描述性的语言”。它使文章有生命,像活生生的人之情绪与性情,而非人的雕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使语言成为构成我们生命的骨架,并且避免了“解释学”的命运。文如其人,我们以这样方式陶醉于文,也可以如此方式沉醉于生活本身,使我们从此忘记钟表的指针,就像古人本来是饿了才吃饭,自从发明了钟表,人类就死板地按照钟点去吃饭了。“饿了才吃饭”的感觉是香喷喷的,这也属于我说的广义上的陶醉;按照钟点等外部条件去吃饭的人,无意中使自己变成了“被吃饭”的死板机器。
描述性语言所使用的文字,貌似若即若离(参见以下郑板桥说“石涛画兰不似兰,盖其化也”),像萨特所谓“我存在于我所不在的地方”(Sartre,p.152)。所有这些,都等于在语言中引入了时间因素,使得语言生动活泼,绝处逢生。好思想不在理论里,而在诗或诗一样的语言里。诗是语言的姿态。象形文字之“象”不仅是画画一样的初级形状,更是姿态,有姿有态才“别有摇曳风姿”。(这也像中国古代文论中评价好文章有“风骨”。“风骨”是被体会出来的,而不是肉眼看出来的;或者叫风格、个性。更微妙的,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文章的风格本身也分皮毛和骨髓,因此才有“学杜得其皮”的说法。[《钱锺书散文》,第401页])“象”是虚的(用萨特的存在哲学术语叫“虚无”),靠体悟才呈现;“形”却是实的存在,可以肉眼看见。美人是“形”,由此“兴”起的桃花则是“象”;反过来也可以说,眼前的桃花是“形”,由此兴起的美人则是“象”。由桃花过渡到美人或者从美人过渡到桃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这里所谓“无中生有”,并不是指世界上原本没有桃花与美人,而是说从前人们没有在二者之间约定某种关联。通俗地说,想到了才有,没想到就没有,而所谓“想到”,就是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这里,桃花与美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同于索绪尔所谓词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说到张三就绝对不能同时意味着李四),而桃花与美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灵活多变,是任意的。
由上观之,所有的绘画作品都可以谓之“象”,而非形。“形”属于“知识论”,“象”属于“兴”,由领悟而来。如果以“求象”的态度“格物”,其结果将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致知”,而是艺术意义上的直觉。形是可灭的,因为它只在脑子里;象是不灭的,因为它刻在灵魂。描述性语言所使用的文字,又像是石子在河水里以变化的节奏跳跃而去,激起一连串绝不会相同的波圈水纹。运气是怎么来的?去寻那与你不相干的人或事物,当机立断,于是你就交上了缘分。两个不投缘的熟人在一起将体会到尴尬;肉眼看不见尴尬,但那尴尬是实在的。就像好文章透露出的言外之音,正是这些与气质有关的因素促使我们滋生爱意。在这里,存在即虚无——但是,萨特这种概念性表达方式很笨拙,无奈他是西方哲学家。同样的境界,画家石涛这个“苦瓜和尚”早就领悟到了。本文的开头,我说语言的解释学倾向已经开始衰落,现象学、当代法国哲学以及已经到来的“媒介即信息”之读图时代,将开辟一个文明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语言的主要功能将从“解释”转变为“描述”。描述不是解释,描述只关照对各种事实的感悟,而不是对事实之是非的判断——它从万物之“形”中抽取出“象”。如上所述,“象”是抽象的形,是神似而非事物之照片。郑板桥说“石涛画兰不似兰,盖其化也;板桥画兰酷似兰,犹未化也。盖将以吾之似,学古人之不似,嘻,难言亦”。(转引自石涛,第223页)这里的“不似”或者“化”,我领悟为神似,即“兴”与“象”的意境(耐人寻味的是,不能把这里的“化”、“兴”、“象”理解为“概念”)。石涛所谓“一画之法”,就是建立在“兴”与“象”基础之上的无法之法。“无法”乃全神贯注、自然而然之意。顺着精神生命的节奏,别开生面而滋生的“法”,就是西方哲学术语所谓“结构”。“结”什么“构”啊?多么笨拙的表达!在此必须把“结构”化为“兴”与“象”。为什么古文言的单字比现代汉语的复合词更精妙呢?因为单字与单字的衔接更加灵活机动,而复合词或概念则体大笨拙。笔巧在于心巧,“动之以旋,润之以转”。(石涛,第3页)画万物如此一以贯之,其旋律与节奏犹如生命之呼吸,或如上述生命之骨架也——这才叫“一画之法”。关键是屏住气息别让沉醉停下来,凡停顿都意味着重描或临摹,就变成“板桥画兰酷似兰”的照片了。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只是死板地用“河水”和“绵延”寓意变化,然石涛几乎全用单字的动作行为描述“一画之法”:“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截断横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同上)这些都是“兴”或者“象”。我们说“领悟”或“直觉”,石涛则说“参”、“测”、“度”、“审”、“识”——这些与笔端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即将发生新世界的过程。它与我以上所谓好文章要写得“摇曳风姿”遥相呼应,构成了形状拓扑学意义上的相似——例如石涛对大海与山峦的形状相似的描绘:“海有洪流,山有潜伏……海潮如峰,海汐如岭,此海自居于山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笔一墨之风流也。”(同上,第51页)这样的画已经是诗中意了,也就是我所谓变成了描述的语言。风动乃在于心动,即使风没有动,已然成为心的元素。这些都是从性情中来,是中国古人绝不陌生的感受。
注释:
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一定要从复兴汉语开始,恢复汉语的形而上之韵味。复兴国故,就是复兴民族的内在生命,就像让一个窒息而濒临死亡的人重新呼吸。从学术上讲,这也是我们与欧美学界得以“抗衡”和比肩的学术大道。与晚清乾嘉学派的实证倾向不同,现在需要的是涌现一批汉语写作的思想大师,就像莎士比亚对英国、歌德对德国的作用一样。我这里的意思是说,思想和语言是一回事,而不是去利用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