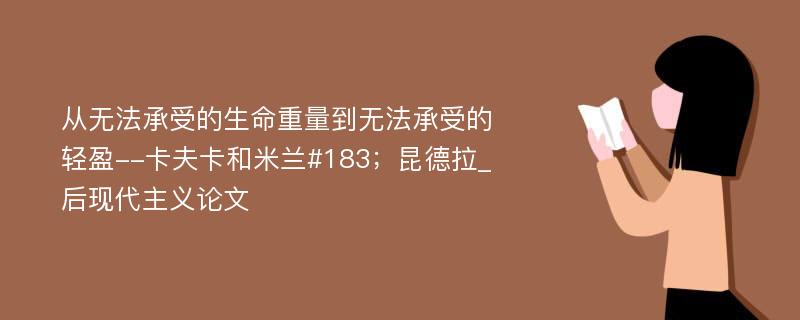
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卡夫卡与米兰#183;昆德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兰论文,生命中论文,之重论文,不能承受论文,卡夫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夫卡和昆德拉这两位布拉格作家,均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引起世人瞩目。卡夫卡以其生命的沉重,营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梦魇世界;昆德拉则以生存的智慧和幽默,透视了现代工业社会里的芸芸众生。两人气质不同,风格相异,却共同基于对人性的根本洞察,对存在的深层思索。本文拟从其各自主人公的基本姿态——沉重与轻松出发,略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及作者价值取向的异同。
一、轻与重
在欧洲文学史上,一直有推崇沉重的传统:以沉重为不幸的同时,也以沉重为崇高。希腊悲剧中人与命运的冲突是其光辉范例:人在抗争命运中体现人的伟大和庄严,尽管抗争总以悲剧告终;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疑问在人文主义的自信中透露生存的晦暗不明;加缪则以西西弗斯承担荒诞的勇气宣称:“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承担命运的豪情到卡夫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生的不堪承受,人甚至异化为丑陋的甲虫。到了昆德拉,一反欧洲传统的沉重主题,他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轻松。昆德拉从而以对“轻”范畴的探究,展现人的存在境况,将对人的探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卡夫卡作品的寒冷与沉重,使他鲜明地区别于其它现代派作家。卡夫卡认为一本好书应该是一把劈开心灵寒冷的斧子,以此创作观出发,卡夫卡试图在作品中提供一种可能的意义。对意义的追问构成了他创作的主题之一:寻求。随着幕布的揭开,苏醒开始了,寻求与逃避、申诉与判决也开始了,而结局已蕴含在幕布揭开时的第一个情节中,其它情节的展开只不过是一步步加深不安和绝望,因此寻求过程总是伴随着难耐的沉重。这类寻求的沉重明显体现在其长篇《诉讼》和《城堡》中。
《诉讼》中的约瑟夫·K是一家银行的襄理, 一天早晨突然被捕。从此一切看似普通的事物都显出其不寻常的意义,K 就此踏上申诉的旋转轨道。有意味的是,法庭是设在阴暗的阁楼上,审判过程变成K 慷慨陈辞的过程,而法官的判决书亦不过是黄色读物。同样有意味的是, K被告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一般规则,案子全是事先已经判好了的。”〔1〕我们以前倾向于认为这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 然而这只能是种表层的意义,满足于这一表层意义将会导向一系列的误读。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现实,一种人类走向迷途的景观。K 的申诉终归失败,最后象条狗一样被人杀死,而且也终究不可得知自己犯了什么罪。K 就无从摆脱吗?然而,“在法的门前”这则寓言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上帝的法庭是,你来,他就让你来;你去,它就让你去。”K 试图尽快洗清罪孽,就主动去寻求法庭和正义,结果只是加速死亡。一场诉讼类似一件死缓。
如果说约瑟夫·K总在寻求法律、公理、正义, 总在为自己的清白辩护,而“城堡”土地测量员K则是寻求进入城堡的道路, 以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正常人,在进入一个反常的异己的社会时,就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城堡就在前面的山岗上,但是可望而不可即。K充分利用一切机会、 尽最大的力量对抗重重阻挠——密密层层的等级、僵死的官僚机构、他人的拖累,直到最后他既没有进入城堡,也未见到城堡官员克拉姆。这种寻找往往导致对自我的无限流放,而流放的结果只能是个体的毁灭。卡夫卡更多地是在超验领域进行活动。他也批判现实社会,但至多是一种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恰好是一种普遍隐喻的折射。卡夫卡一系列的寻求和申诉又似乎只是在内部完成的:犯的罪只是内心的,刽子手和法官也是内心的产物,寻找的艰难只是内心一系列障碍的阻碍,小说主人公的死亡也是卡夫卡内心对自己的宣判,一种左冲右突不得出路的被迫宣告。“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首先是他意识到外在现实已是一只有魔力的笼子,你只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再也无可摆脱;《变形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因为卡夫卡“我在自己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其主人公无一例外或衰竭而死或被杀死,只因为卡夫卡早已洞悉“目的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而最好的路乃是“放弃吧!放弃吧!”;其主人公无一例外寻求失败,是因为卡夫卡深知“草怎么能从中间生长?”。然而卡夫卡终究未丧失所有希望,他终究看到一束光线:《在法的门前》的K 临死时终于看到只为自己设置的大门内透出一束光线;《诉讼》中约瑟夫·K 被杀死前发现远处一扇窗突然打开,灯火通明。然而卡夫卡更多地却是描写寒冷而阴郁的死亡以及永远的飘泊:《乡村医生》里乡村医生“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再看《猎人胡格拉斯》中猎人“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有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2〕
如果说卡夫卡的主人公总在与不可知的力量作斗争,感到难以承受的沉重,而昆德拉的主人公则是时常置身于一个失重的世界,体验不能承受的轻。
轻是在事物失去意义、反叛失去对象、行动失去目标、存在失去依据之时的一种感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外科医生托马斯经历了轻与重的二难抉择。
在遇见特丽莎之前,托马斯是个性爱领域里的唐璜。他充分体验性友谊的自由甜美,并且希望不受任何限制地领悟存在的自由即“轻”,而不愿体验必然、责任、嫉妒这些沉重因素。然而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坎坷、夫妻间的冲突之后,他重新认识到“重”的东西的价值,同时体验到轻的虚幻。最重要的是,托马斯最终发现占据他诗情记忆的唯有特丽莎一人。“轻”终于让位于“重”。轻有什么意义呢?不过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地球在宇宙中就是孤独的。因此,作者并不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灵与肉的冲突导致的“轻”在特丽莎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产生特丽莎的情景残酷地揭示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3〕特丽莎母亲的世界里心灵与肉体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只有肉体,没有灵魂。既然所有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也就不会有神圣、神秘、羞耻和崇高。特丽莎期待摆脱这一世界,对母亲世界的敏感使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自卑,同时滋生对灵魂之美的强烈向往。特丽莎从母亲的世界逃出,又进入托马斯的世界。托马斯的世界是个只关注性友谊而不涉及情感领域的世界,所以才有特丽莎如下的梦境:托马斯的情人们被迫绕水池行走,并且高声歌唱,谁不唱就会被击落水中。就是说人人必须遵从同一的律令,让自己只还原为肉体。因此,母亲的世界与托马斯的世界都不过是肉体的巨大集中营。它以取消个性也取消灵魂的轻使只重灵魂的特丽莎因肉体的拖累而不堪承受。特丽莎为了保持灵魂的重量而尽力逃避母亲的世界,却终于发现“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对她而言,没有灵魂的交融而只有身体的性爱是不可理喻的。灵与肉的片刻分离是在与某工程师的片时交往中。她的灵魂很清醒地注视着自己的肉体作为纯粹的女性肉体怎样被陌生人亵渎。她目睹肉体背叛灵魂,灵与肉分离这一实验的结果只是痛苦及至分裂。
如果说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生活奏出一部轻与重渐趋和谐的乐曲,那么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轻与重旋律却以前者的不告而别戛然中止。
弗兰茨是个心中充满理想、神圣这些概念的知识分子,萨宾娜则来自高度集权的捷克,对所谓的革命和个性自由有痛切体验。弗兰茨要进入的正是萨宾娜要逃避的,弗兰茨要建构的恰是萨宾娜要消解的。萨宾娜的一再背叛终于使她无可背叛:“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只有虚空,这无边的虚空恰是最难承受的。
昆德拉以其对“轻”的思考,揭开了人类另一重生活真实,逼使人们去反思、去权衡、去探索。“轻”一方面带来生活的轻盈甜美,背叛的快乐,另一方面又只是数量的一次次重复,是留不下痕迹的,这是“轻”带给人的二重感觉。那么体验沉重的人就幸福吗?为什么特丽莎总是觉得晕眩?她以痛苦使托马斯放弃性友谊不同样是一种软弱吗?至于弗兰茨,为什么他总在担心萨宾娜的离弃,而后者真的这么做时不也是对他的软弱幼稚失望至极的了断吗?
因此,昆德拉并不单纯地在轻与重之间作出抉择,他只力图揭示生存的真实与虚妄,并在真实与虚妄之间对人类进行轻轻的揶揄。
卡夫卡的认真执拗,使他的主人公永远在寻求、在申诉、在飘泊,永远置身于沉重与疲惫之中不能自拔。在轻与重之间,卡夫卡几乎对前者视而不见,而记重占据绝对地位。“受难是这个世界上人与积极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系”,他也的确把自己的一生押到对所谓积极事物的寻找中。
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造成卡夫卡和昆德拉主人公“重”和“轻”的原因,除了作者个性、时代背景之外,还与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相关。如果按照通常的划分方法,在批判现实主义之后,西方文学主流经历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二者的分期约在本世纪50年代。作这类粗略的划分,当然不可能绝对正确,而且给作者标以某某“主义”的标签在文学史上曾经屡屡引起评论界与作者的拒斥。然而把卡夫卡和昆德拉置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与此相应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上对于理解两位作家思想还是十分有益的。
从个性看,卡夫卡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众所周知,他赢弱、胆怯、敏感、忧虑重重,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是个蛮横、喜怒无常之人,这使得卡夫卡有着深重的失败感、负罪感和内疚感。这种消极意识使现实中的卡夫卡在学生时代就确信自己无法通过考试;在职业选择上“我并不指望会找到什么避风港,在这方面,我早就放弃了一切希望”;在婚姻问题上,由情感上的向往到行动上的逃避。卡夫卡终其一生,尽管尝试如父亲所期望所勉励的强壮、健康、功成名就,然而由于天性的羞怯脆弱,更由于父亲的粗暴教育方式,他成为一个体弱内向病态的人。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昆德拉知道得太多。只知他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同时知道他热情信仰过共产主义并经历过二战、苏联入侵捷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1975年移居法国。相比之下,昆德拉是个正常和健康的人,他也自认为倾向享乐主义者。只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用他的笔触摸到人类心灵最深处的奥秘,他同时也用他的笔点醒了人类在历史舞台上演的种种荒谬剧。”〔4〕
从时代背景看,卡夫卡处于资本主义由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作主导而至全面危机的时代。经济危机、世界大战、排犹浪潮、价值崩溃等使人感到外界现实是不可把握的,人是渺小无力的人,人已沦落到甲虫、毛猿、犀牛的地位,彼此之间隔膜深重。整个现代主义旗帜下,尽管流派众多、手法各异,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当时的作家们普遍承受的是焦虑、不安、绝望和沉重。
除对强权政治的批判外,昆德拉感受的主要是后工业社会里的危机:大众传播造成的文化急剧商业化、世俗化;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深度模式的消解;人沦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等等。因此昆德拉在作品中更多地批判人性的脆弱、荒谬以及普遍的媚俗——“在现今的社会组织中,只有媚俗才有社会生存理由。”
从卡夫卡和昆德拉的主人公来看,前者在屈辱地感觉到非人化之时,还是确信人类的主体地位,而后者则拒绝主体与客体的思考,乐于作技术社会的商品媒介;前者意识到现实的荒谬、黑暗、窒息,并坚持“向最后一道尘世的边界发出突击”,后者则既丧失了外在的对峙力量,也丧失了对外界的改造力量;前者超越个人的狭獈经验,对宇宙、人生作许多形而上的思考,后者则根本拒绝乌托邦梦想;前者是对新的价值规则的重建,后者则是对一切价值规则的消解;前者有一种精英意识,后者则满足于个体的狭獈经验。
如果说描写后工业社会的不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如果说后工业社会里一切文化现象都可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不可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文学,那么昆德拉能否称得上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家呢?
从形式来看,昆德拉作品的确有某些后现代特征:
自我揭示虚构:昆德拉不同于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对世界的模仿或表现,他把人物的虚构过程干脆直接呈现给我们: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想象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恰如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变来,恰如维纳斯诞生于海浪之中,阿格尼丝是从游泳池边那个六十岁女人向救生员挥手致意的动作中蹦出来的,而那个女人的五官特征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忘。当时,那动作唤起我对往昔的一种无法解释的深切怀念,这怀念产生了我称之为阿格尼丝的女人。”(《不朽》)
小说由卡夫卡式的把内心推向外部并从中感受到巨大幸福转化为昆德拉式的冷静(或抒情)操作,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审美距离。然而,昆德拉也有大段的激情议论,而非取消深度、取消意义、取消判断,即非“零度写作”。
反讽: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站在几千年文学传统的阴影下,感觉无法写出莎士比亚似的崇高巨著,那么他们创新的形式之一就是反讽。昆德拉小说也时常把前人作品、历史人物、意识形态等作为反讽对象。
拼贴:无关事件的相互组合。事件相互独立,因此任何事件都是平面的,目的在于取消深度,使事件只停留于语言层面。昆德拉也搞拼贴,目的却是在多重时空关系中,呈出人世的可笑、荒谬或悲剧性质,并在呈现中加强批判力量。
随意性:同作为形式的实验,卡夫卡充分运用变形、隐喻、象征等手法来表现主题,昆德拉则以四重奏、变奏曲等形式,明快清澈,带有后现代的自由无度、无选择技法等色彩。
以上我们是从作品的外观特征来看昆德拉小说,从作者的价值取向来看却迥异于后现代主义作家。
按照哈桑的观点,除一系列外在特征外,后现代主义有两个核心构成原则,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6〕不确定性是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是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而昆德拉尽管认为生活中充满悖论,但作品总是围绕中心进行;他也消解某些伪价值,如所谓的个人主义、革命,但基本意图却是建构性的,是对健全人性、政治、生活方式的一种肯定和建构。从内在性(适应而非超越)而言,昆德拉恰是反内在性的。他关注人的精神、价值、真理和超越。在这两点上,昆德拉鲜明地区别于任何后现代主义作家。然而与卡夫卡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坚持人类主体性同时,能认识到人类的能力限度、个体的能力限度(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和历史的悖谬,所以他能够幽默而从容地展现人生、安度人生。卡夫卡则是那类试图超越必然、超越无限的人,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人的傲慢就在于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6〕
如果说卡夫卡永远守在窗前等待皇帝信差的到来,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嘲笑皇帝存在的神话,满足于形而下的享乐,而昆德拉既不相信皇帝存在,又要求人类为皇帝的缺席自己负责;如果说卡夫卡总在试图超越本能,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意味着依据本能,昆德拉既承认生命本能,又要求超越本能;如果说卡夫卡甚至通过扼杀本能同时扼杀现世生命来实现超越,后现代主义者则根本认为深度和超越实乃虚妄,昆德拉则认为卡夫卡对我们是一笔宝贵遗产,同时认为超越的确是有限度的,自虐是不足取的。
笔者无意亦无力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异同,只想指出:在工业社会——现代主义的背景上,卡夫卡作为沉重、焦虑、幽暗的一员融入广大的现代主义作家群体中,在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上,昆德拉却以轻快、清新、明晰、诗意的笔触独立于一片无序、平面、冲动、耗尽之纷繁景观之外。
三、超验之光与田园梦
已有评论家指出,卡夫卡的作品可归结为两大主题:寻求主题和动物主题,昆德拉则自称自己的作品有两大主题:政治和性。其实两人作品尽管存在巨大差异,前提都基于人的主题。
卡夫卡的寻求主题构成其作品最激动人心的部份。寻求当然是人的寻求。从卡夫卡本人来看,“我在斗争,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动物主题则是直接将人置于动物层面,体现人的纯粹的超越表象的存在。而昆德拉在经历过苏联入侵捷克这一历史事件后,不能不关注政治,然而无论是描述政治或历史事件还是描写性爱,他都基于对人性的关注。在性与政治这两个浓缩的舞台上,最容易集中展示人物内心的善与恶、轻与重、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就卡夫卡的《判决》和《诉讼》而言,都是主人公被诉有罪,前者的宣判者是父亲,后者的宣判者是法庭。如果结合卡夫卡《给父亲的信》中关于他置身之世界的三种划分,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卡夫卡创作这类作品的外在契机。盖奥尔格为什么会有罪?首先是父亲因他的私自订婚、“好吃懒做”等不成理的理由视他为异己,甚至隐藏着父辈因不甘退出舞台而憎恨子辈的集体无意识。其次是卡夫卡这个善良得近乎圣徒一样的人,为自己在社会角色中的无能而内疚、而自觉有罪,这是一种生命的罪。“对我们来说,存在着两类真理,分别由‘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为代表,也就是能动原则的真理以及静态原则的真理。根据前者,‘善’有别于‘恶’,而后者既不知有‘善’,也不知有‘恶’,仅仅就是‘善’的本身。”〔7〕父亲坚持的就是第一类真理, 一种文明社会里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阶段真理,它以善与恶的明确区分来压制“生命之树”为代表的真理,而后者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永恒真理,是只能依靠直觉、体验来达到的。然而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比较两类真理,却会发现,前者是生机勃勃的,后者是怯懦不堪的;前者是一往无前的,后者是进退维谷的。尽管长远来看,“第一类真理就在第二类真理的光芒之中黯然消失。”在卡夫卡看来,有价值之物总是有光芒的,然而这光芒只有心中有光的人才能偶然瞥见。所以在一种可能性上(屈从于第一类真理)他痛快地解决了自己,另一种可能性上(坚持第二种真理)他绝对不放弃寻求。约瑟夫·K能够不辞辛苦, 都基于他相信以第二种真来看,自己是无罪的。直到他被以知识之树为代表的真理扼杀,直到屠刀“在心脏里转了一下”之前,他才看见远处的灯光和某人伸出的双臂。这光线已不代表尘世的救赎,只能是他确信这世界的未来或另一种世界一定有光,他才发出那么热切的询问和呼唤。其中“法的门前”寓言中的光线,好似一种内视,一种幻觉,在幻觉中,沙漠里干渴濒临死亡的人瞥见绿洲。
卡夫卡的内疚和负罪感可以趋向极端,如《饥饿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只能绝食来维持艺术,“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象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对精神食物、真理的执着达到这样的程度:一旦寻找不到它们就弃绝尘世食物,似乎以此为代价能达到绝粹的自己,似乎封闭所有的感官真的能达到精神的狂喜。这里我们发现卡夫卡寻求主题的倾向之一:等待姿态。这种等待到《一条狗的研究》有了结果。〔8〕这条早早就发现与狗类生活“存在着一条小小裂缝”的狗,这条“心中充满对伟大事物的预感”从而“对一切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纯粹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求驱使着向前行进”的狗,终于跑进了一个超验的领域,或者说他把超验的“芳香、亮光、音乐和空中之狗”召到了尘世。音乐四面八方向它涌来,“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响着一种清晰、威严、持续不变的、来自遥远却始终如一的声音。”这轰鸣是世上万事万物的整合,每一粒沙、每一片云、每一个生者和死者都有生命、都有声音,所有天籁和人声汇聚起来形成始终如一的声音,形成绝对的存在本身。这存在是一切的本原,一切追问的答案,这存在如同太阳,不可直视,只能感觉。所以这条狗会被乐声搅得拚命挣扎、痛苦不堪。这种存在老子称为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9〕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是不可定义的和“自明”的。 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存在则分明属于“不可说”的。
卡夫卡不会放弃追问。关于空中之狗(即艺术和艺术家)的意义、生存方式就是这一追问的取向之一。空中之狗不可为自然科学作贡献,因为后者是一种物理性的东西,“的确,科学在前进,这是不可阻挡的,……但这有什么可以称赞的呢?就如同称赞谁的年龄一年年增大从而愈来愈快地接近死亡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可憎的过程,我看不到一丝值得称道之处。”科学通过土地能给人们带来尘世的食物,这是尘世之狗所必需的。然而空中之狗只能依赖空中的食物,尘世之狗通过咒语、歌舞也能得到空中的食物。所以广义的科学应包括朝空中进行的“低语、跳跃和舞蹈。”在此意义上,空中之狗的确对科学有着巨大贡献。而呼唤空中食物的最好方式是绝食,因为在对尘世食物的品味中,尘世之狗是无法坚持追问的。
在作为一条年轻的狗时,它常常焦虑,常常发问,责怪同类的麻木与冷漠。卡夫卡也常常批判人类的无理性、怯懦、油滑和漫不经心,就如同《城堡》中的助手、《诉讼》中的同事和《乡村医生》中围观者一类,“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它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10〕当成熟一些时,这条狗就只通过绝食来验证获取空中食物的可能。而卡夫卡“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在你面前扭动。”〔11〕这种静听、内视是否已是对人类的背叛?不,他只是走得太远,但还未走出人类的理解范围:如卡夫卡认定“美只存在于被告身上”(拯救只存在于被告身上);狗类对这条作绝食实验的狗充满求助;耗子家族对耗子歌唱家约瑟芬充满敬意等。因此,他不是背叛人类,而是在用全部身心寻找一条可能的道路。
当祖先已走上一条迷途,使得我们今天在“已被别人搞得乌烟瘴气的世界里”除了沉默地承受之外还有别的出路吗?批判社会、批判人类都是次要的,因为你能拿出拯救的方案吗?你能说出哪怕是局部的真理吗?卡夫卡反复追问,最后倾向内求。人们渴望自由,而自由必须清洁心灵,必须通过个体的内视来达到。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体验,也很容易得出卡夫卡寻找上帝救赎的结论,然而从卡夫卡日记和传记中得知他对宗教非常冷淡,他只把目光投向人本身,这并非一个形而上的怪圈。
昆德拉否认了善与恶在生活中的明确区分,这点与卡夫卡如出一辙。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悖论,这些悖论及其由此引发的议论构成其作品最耐读的部份。他尖锐的批判锋芒指向强权政治,指向人性的异化,指向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媚俗。他绝非一个持“零度写作”的作家,一个中止判断的作家,一个取消意义深度的作家。
昆德拉批判强权,指出强权要剥夺的是人对语言、祖国和传统的记忆。对殖民地的侵占重要的不是占领土地,而是侵占人们的意识,是大规模的洗脑活动。这种洗脑以天真和欢笑的外观惑人,暴露个体的隐私于公众,从而抹杀个体,消灭个性。这种强权不只限于政治,它广泛地体现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在母亲及顾客的肆意挖苦嘲笑中,特丽莎不能保持灵魂安宁,托马斯的不忠行为亦不能使她灵魂安宁。灵与肉、轻与重的失衡终于和谐于田园牧歌。苹果树、狗、牧场与乳牛这类意象是如此温暖、宁静,以致使昆德拉对人类的文明、对人于万物的统治地位产生怀疑。以“卡列宁的微笑”为题,展示了乡村单调生活的透明、纯粹、幸福一面。人类的真正幸福,不可缺少大自然的温情微笑,更不可扼杀这种微笑。
集中营意象不仅来自于他人对个体孤独的强行打破,也来自于一个充塞着“复制”文化的社会。《不朽》中一本杂志集中展示二百多张人脸:一个面具充斥的世界,人们却在那里狂欢。在一个个性丧失、诗意无存、噪音充斥的世界,还有人竭力表现个性:无限出书的冲动(给人们意识增加更大负荷)或者去掉摩托车消音器以让人们注意其存在。神性的光辉早被工业的烟尘所吞没,温情的眷恋已让位于机械的肉体享乐,个性和自由已泛滥成普遍的无个性无自由。阿格尼丝试图保持自我,只得想象手举一枝蓝色勿忘我在街道穿行。一枝蓝花,大自然的赠予,是窒息中唯一的清晰气流,五光十色的物品背后唯一的生命。阿格尼丝临终拒绝丈夫的吻别与父亲临死前销毁属于自己的一切具有同样含义:拒绝媚俗。阿格尼丝和父亲,在歌德著名的短诗中获得默契、美和沉静:
群山之颠,
一片静谧,
所有的树顶,
你听不见,
一声叹息。
林中鸟儿无语。
只等着,很快地
你也休息。
在倾听自然、返回自然中他们终于发现了生命的美、喜悦和安详。
《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聚会目的却是永远的告别。心理学家雅库布象一颗执着的冷眼,洞察到历史和人类的悖谬,他试图向这一切告别之时却听任自己成了事实上的杀人者。
悲剧在于:他本可以避免对方之死,潜意识中却渴望验证另一重自我:人类的投毒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可以在对别人死亡的预感中品味隽永。透露出他对人世的否定。聚会结束了,他以清醒之眼抚摸祖国,看到无辜的孩子在重复他的生活。沉痛的感觉一出现,即被别一种明察代替:世上的孩子都是复制品,是斯克雷托医生试管的产物。没有沉痛,只有淡漠。
告别的沉痛之处在于:人只能有一个祖国。人类只有一个家园,能到何处去泥?可能的倾向只是美的追求:一种精神的东西,一种闪耀于宇宙每一片叶子之上的光采和呼喊,一种灵魂的极致。昆德拉对自然与美的关注,不是逃避社会,而是基于重建健康人性,与马尔库塞“新感性”学说如出一辙。
卡夫卡发现超验之光芒,昆德拉则倾向田园牧歌。他们在对生存提问的同时,也对生存提供着可能的答案。
关于人类的未来,许多哲人作过设想或表示过忧虑。胡塞尔曾作过欧洲危机的著名演讲,海德格尔曾描述过科技世界诸神逃离的景观:世界之夜已达夜半。卡夫卡深入到人类形而上学迷误和科技迷误的起点,昆德拉则深入到历史深层及人性深层。在后现代文化泛滥的今天,倾听哲人们的痛苦反省,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摆脱危机的方法?
注释:
〔1〕《诉讼》第62页,〔奥〕卡夫卡著,孙坤荣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第269页,孙坤荣选编,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9页,〔捷〕米兰·昆德拉著, 韩少功等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
〔4〕转引自《二十世纪艺术精神》第417页,黄卓越、叶廷芳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序言第32页,王岳川、 尚水主编,北大出版社,1992年版。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6页,〔美〕丹尼尔·贝尔著, 赵一凡等译,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
〔7〕转引自《论卡夫卡》第689页,叶廷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8〕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见《世界文学》1993年4期。
〔10〕老子《道德经》二十一章。
〔9〕〔10〕《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5、129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卡夫卡论文; 城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