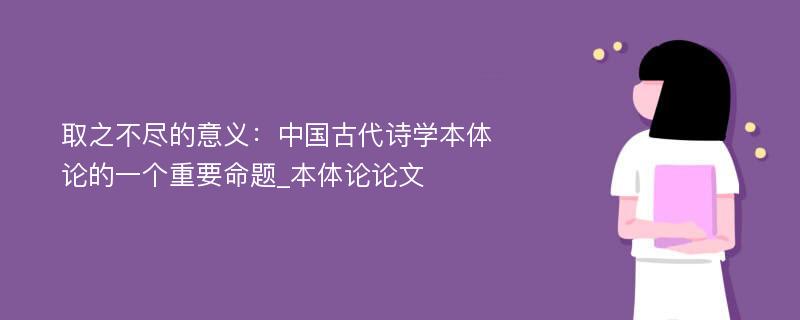
“言不尽意”: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的重要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不尽意论文,本体论论文,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里,“言意”是其重要范畴,从“言意之辨”出发,“意”是诗所追求表现的本体,而“言”则是为表意服务的,“言不尽意”因此而成为诗本体命题。它既抓住了诗美的特质,又开发了“意在言外”的美学疆域,使诗的艺术内涵和诗学的理论内涵得到丰富和提升。
关键词 古代诗学 言意之辨 言不尽意 诗学意义 本体命题
一 定位:“言意”说作为诗本体命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对此肯定有加,尤其是现代主义文艺批评把语言升格为文学本体,也就是文学等同于语言,文学规律等同于语法规则……认为,任何作品的情节,总是在“叙述的组合”中生成的,甚至认为一篇作品就是一个句子,具有“句子性质”。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问题牵涉到文学本体的理解,是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在中国古典诗学里便没有现代理论这么复杂,这么偏激,它们也极度推崇语言的作用,但从不将它作为诗本体,而是作为诗本体的存在形式,从而对诗美特质作出了独特的表述。
在古典诗学中,对于“言”的重视,完全不亚于今人。早在先秦时代,以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代表,就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的作用。历代诗学家重视有加,以至于出现了“苦吟”、“一字师”、“以一字计工拙”的现象。创作者从炼句到炼字,像自动旋拧的发条越拧越紧。语言成了成就诗人的沃土,也成了诗人的重负。清初诗人钱澄之在《诗说赠魏丹石》中曾说:“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求其雄,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用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意之所需也。”“一字之间”足以显示诗人之才华,也足以耗尽诗人之才华,足见重视语言之程度。
然而,中国古人从不把语言作为诗本体,比较起来,语言只是诗本体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手段。同古人论“兴”,论“情景交融”一样,古人论“言”亦和“意”联系起来,在二元对立统一中确立“言”的合适地位。在“兴”中,古代诗学认为真正的诗美是将本体的情兴具象化,物态化,其可视见的生动的具象与物态则不是诗本体,诗本体依然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兴”;在“情景交融”说中,古代诗学进一步具体地去探讨情兴具象化、物态化的内在构成,从而揭示诗美特质。同样,在“言意”中,古代诗学从形式表现角度探寻诗的美学特质,认为能视听的语言形式也不是诗本体。诗以形式为美,但诗不止于形式,还有一个大于形式而又因形式而欲显的深层的本初的东西,它才是诗本体。这样,“言意”说的诗学框架在古人那里就得到构建。“言意”与“兴”,与“情景交融”三位一体,共同构成诗的美学特征的系统组因,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显示诗的美学特质,体现出东方诗学博大而独特的艺术精神。
二 言意之辨:“言意”作为诗本体命题的建构
诗(广义的文学作品)的构成从载体表现角度来说,也可沿袭王国维“二原质”说法,是“言”与“意”的组合。“言”指以语言为特征的表现形式,“意”指支配诗并因之获得表现的内在意蕴。二者可解为表里,又不可截然切分,是血肉相联的整体。机械唯物论对此的把握总是偏失于“言”与“意”的割裂,而追求“会意”、“会心”兼以道家玄奥为哲学基础的中国古代诗学,不仅巧妙地作出“言意之辨”而且在辨析中融注了博大而精深的东方诗学的艺术精神。“言意”作为诗美特质命题是因“言意之辨”而建构成的。
早在《周易》,就在哲学领域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易传·系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从哲学角度讲,一般的东西,可以通过逻辑的推理去破解,而创造性的思维、复杂的心理,则是逻辑推理所不能把握的。尤其是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缺乏精密的认识工具和表现手段,得“天下之理”而又“言不尽意”的矛盾被突现出来。
《易传》以其玄奥的哲学思辨为言意之辨奠定基调,到了道家那里,“言意”便被纳入“道”的思辨框架。在他们看来,“道”是事物的本体,至大至美,不可言说。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道”的最高层次和一般层次都是语言所不及的,“言之所不能论”,只“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在“道”的最低层次,“言”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而且,“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当获得了“意”后,语言这一工具也被弃置不顾了。
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影响一切精神文明的思想背景。哲学上的“言不尽意”是诗学上的“言不尽意”的衍化源。到了魏晋时期,便引发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言意之辨”,推进了诗学上的“言意”说的建立。
荀粲以非常激进的态度,有力地揭露了在“天下之理”面前哲学家“言不尽意”的窘态,但又将“言不尽意”绝对化,导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淖。
年青的哲学家王弼则极力以调和的方式来推进“言不尽意”的理解阐释,论证了“言不尽意”而利用“象”可以尽意,进一步将道家“得意忘言”观点明朗化、具象化:“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明象》)王弼在这里以其强力的思辩强化了“言不尽意”的命题,同时他调和地将“象”作为“言”、“意”之间的中介,也是富有迷人意义的。
这场争辨的基本观点未脱出“言不尽意”、“言可尽意”的基本框架;重要的是,王弼的观点对诗学产生了更大的直接的影响。以至于欧阳建等竭力证明“言可尽意”似乎说得更有道理,也没有冲淡中国诗学“言意”(“言不尽意”)范畴的提出。
促成诗学“言意”观出台的还有中国佛教哲学的影响。佛道乐于对“言”与“意”的分辨,认为“言”无法“尽意”。认为佛道是超越一切语言文字的:“一切法实性……出名字语言道。”语言一出,“道”就断了,故主张“不立文字”,“心心相传”。其如慧能传教四十年,只万余言《坛经》传世,且由别人记录整理的。
从道家哲学都到佛教哲学从哲学角度辨析了“言”、“意”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哲学命题,对中国诗学的“言意”观肯定要产生强烈影响。当然佛教与道家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未必尽合艺术思维,有的观点也过于粗疏绝对,不无可追问修正之处。不过,作为一种高级哲学思维是颇具启示性的。加之,中国古典诗学一开始就定位在表现主义上,其拍合极为细密。
故而到唐代,由与佛道有缘的皎然、司空图诸君正式创辟了中国诗学的“言意”说。
皎然在其著名的《诗式》中借对诗人作品的品评总结指出:“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这里把包罗万象神秘的“道”移化为文学作品的情性,化用恰适,其思维方式与佛道惊人拍合,而又从根本上抓住了艺术的特质。到晚唐诗僧司空图更是按佛道的“句样”,移化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
一个“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一个“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包容了精深而玄奥的艺术辩证法,使中国古代诗学的“言意论”命题高度成熟。南宋时期的严羽“以禅论诗”,对皎然、司空图的命题进行阐发,他从“旨冥句中”、“意在象外”的崭新视角,切入“言意”命题,承传弘扬了中国古代诗学的“言意”论。
本来,哲学上的“言不尽意”在魏晋时的文论大师那里就已经得到密切关注,梁代刘勰认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技”(《文心雕龙·夸饰》),“言不尽意,圣人所难”(《文心雕龙·序志》)。晋人陆机早就提出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的问题。但他们此时还主要是科学地观察分析了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现象,他们的工作也主要是在研究“言不尽意”和“言能尽意”双方意见后,从“言不尽意”的矛盾存在出发,去寻求“言能尽意”的境界。这是很好的创作论。而唐宋时的三位诗僧则是以佛道思维为基础分析理解“言不尽意”。这样,“言不尽意”就成了艺术思维的问题,也就是艺术本体问题,即不是面对现象想办法找寻出路,而是从现象溯源深进,归纳艺术本性。这就切合和把握住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质。故从诗学本体论来说,三位诗僧的表述更为自觉,更具有命题意义。
尔后,代有传人,将“言不尽意”推向广泛性的创作与欣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和诗学理论的发展。如明人沈际飞从作品分析盛赞“言不尽意”,方以智从欣赏角度看待言与意,要求“越浮言”、“超文字”,断言“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字。”(《文章薪火》)清代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指出:“诗不可以言语求,当观其意。”“善论文者,贵作者之意指,而不拘于形貌也。”
无论哲学,更无论诗文,讲超越语言,“去言”、“忘言”,从原生的意义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思想感情要交流,而且通过文字交流,而没有“文字”怎么可能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师们又一再表达“言不尽意”,要“去言”、“忘言”呢?诚如“言意之辨”中的“言尽意”论者所辨,如去言,所谓的“言不尽意”观点本身也无法表达出来。
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语言。把语言单独作为一个封闭系统去看,可以说它具有极为玄妙的表意性,任何玄妙的道理都可以表示出来。诗人作家不是通过语言去表情达意,成为艺术大师的吗?作家诗人本身就是语言艺术家。这是不可怀疑的。而当我们从诗本体论角度,即诗究竟以什么为本、究竟表现什么的角度去看待语言,就瞬然间建起了一个异常复杂庞大的艺术系统。诗创作主体、客体、诗本文、诗接受体皆和谐统一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语言就退居到另外的地位去了。比较起来,诗表现的就不是“言”了,而是那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完的包容巨大语境的“意”,而诗要表现的就是它,有了它,诗才美,语言也才跟着而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古人才说“文以意为主”,其词采章句只是一种“兵卫”(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曹丕语)。
从诗美的特质来说,正是如此。中国古诗学从情兴的具象化、物态化到情与景(即心与物)内在构成再到一个美妙的“意”怎样造型的角度,系统地思考与建构诗美特质。换句话说,诗美是应从它的怎样表现的全面角度来认识和表述的。我认为,“言意论”是以“言”不能尽“意”——诗不是以表现“言”为指归的含义而成为诗学本体论命题的。我们可以从语言角度去张扬它的艺术功能,但完全不能丢掉从“意”与“言”的本体角度去更高层次地探讨艺术本体问题。
皎然、司空图及严羽三位大师既通诗之三昧,更领悟佛道玄奥,故造成了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式,而这正与东方艺术精神沟通无间,故他们的论述更加引人注目,值得玩索研究。
基于上述理解,中国古代诗学的“言意”论从表现主义的土壤里植根生长,得佛道玄学的营养滋润,其生态不仅鲜活灿然,而且内涵丰富,包孕无穷,有不同于西方诗学的绝妙处。
三 言不尽意:诗美特质的强化表述
由“言意之辨”而重“意”轻“言”,这是中国古典诗学独特的“言意论”,或独特的发展轨迹。表面上看,古典诗学把“言”的作用降得很低,而实际上则如前所述,是回避了“言”的自足封闭系统而纳入到诗美创造表现的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诗本体,不至于把受本体支配的形于外的言语形式当成了艺术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言不尽意”是对诗美特质的强化表述。
从诗的创造表现来说,诗人所要极力展示表现的是那内心深处躁动不羁、浑沌无边的情兴世界本体,语言是诗人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借用或者说创造的一种载体。本体和载体之间是不重合的,甚至是矛盾的,因此,诗人常常陷于“言不尽意”的困境中,导致内心世界得不到完整再现的“语言痛苦”。古往今来,这种痛苦与文学家同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家是在这种困境与痛苦中诞生成长的。“言不尽意”就是这种痛苦与困境的表现。然而,且不说文学家要寻求解脱痛苦与困境的路径,即使这种痛苦困境存在,文学家也仍然不为困境所困,不为痛苦所痛,而能从观念上表现出对内在“意”的完善的心理自足。从老子、庄子再到魏晋“言意之辨”的“言不尽意”坚持者们都是充满着这种把握本体的自信的。本体之“意”对他们来说,神圣、原创而博大无际,而表现它们的语言本身则是形而下的可历练的技巧。
由此看来,“言”、“意”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包容了哲学的内涵与心理学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既有“言”、“意”本身的,也是作为接受者的心理认识的。因此,古典诗学“言意”说作为古典诗学命题是异常重要的。
首先,从诗创造表现的大系统定位上,“言不尽意”体现了古典诗学的“重内容”的本体观。
诗美首先是内容,与内容相比较,一切都是形式。就其地位而言,内容是其表现本体,而形式是其支配的表现手段和材料;就其生成而言,也是内容为本,它先于形式并决定形式。南朝大理论家刘勰就深刻地把握到这一点,指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是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当把古代诗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时,我们强烈感到,古代诗论家对诗本体性的东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魏文帝曹丕指出:“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语),宋代诗论家陈师道对此说作了生动的张扬。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表述:“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他也重意轻言。金人王若虚指出:“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滹南诗话》卷一)清代诗论家袁枚则以“主人”、“奴婢”作比(《续诗品·崇意》),在他看来,“意”生于人心,而“言自手出”(《随园诗话补遗》卷四)。清代诗论家厉志从创作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讲“作诗务在足意,意不足,诗可以不作”(《白华山人诗说》卷一),他以此观点衡诗,新意迭出,慑服人心。他说“每读古乐府之佳者,皆有无限深意在内,发而为文,千古不朽。后世徒以时流之笔仗,描绘古词之肤末,读之总不动人心目,由其少真意也”(《白华山人诗说》卷一)。
重视“意”而将“言”放在形而下层次的论述不胜枚举。概观之,他们所说的“意”是个模糊的概念,其实质内容包括了具体的诗本体:审美意象。因是相对“言”等形式因素而言,故“意”显得宽泛朦胧,包括了诗本体的全部内涵。“一本所系”,可派生出很多对关系,如意与词、意与法、意与格、意与气……显而易见,意与言的关系只属于这个层次里的一对关系,难怪把“意”与“言”作为诗本体命题时,“意”是那样的重要和具有不可超越、不可回避的支配力。古代诗学重内容的诗本体观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其次,从诗本体的涵纳上,“言不尽意”表现出古典诗学对无限美的追求与自信。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而美也是如此。有额定的浅表的美,也有动态的无限的美,而诗追求后者。美是无限的,但表现的手段——语言,无论怎样具有表现力,也是有限的,它与人的思维是非重合非一致的,语言以其难以摆脱的有限性,阻碍着思维走向更大的世界。故古人宣称“言不尽意”,“言”是不能完全传达主体的本体之意的,明确地让世人明了语言的局限掩盖阻滞不了内心情性的富有与绵长。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古人宣称“言不尽意”,是向世人昭示有一个比语言表现更大的“意”在,诗作也不是以表现语言为指归,同时也是征服、超越语言走向无限美的豪迈宣言。
《奥义书》说过一段有深意的话:“当一个人看不到别的,听不到别的,体会不到别的时候,那就是无限。”古代诗学的“言不尽意”就是对这一玄机的领悟与布达。诗人运用“言”来传达“意”,但由于语言天生的比要表达的本体情兴有限,故诗人要求接受者超越语言,以语言为媒介又无视语言去“直寻”那内在之意的无限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曲诗学的“言不尽意”表达了对无限美的情醒意识。
最后,从诗美的生成与接受上,“言不尽意”扣合了诗美的复合性美学特质。
诗美是复合的美。从“言意”的诗美范畴来说,二者要造成终极的复合的美,而二者与这一特质的关系是不等的,尤其是二者之间甚至有矛盾冲突,有极明显的错位。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属于理性范畴,在人的心理机制中,人的语言沿着理性的线路通行流布而诸如情感意绪领域却不敢涉足。照弗洛依德的观点看,人的心理几乎是一片无意识的汪洋大海,理性的意识只是时而溅出的浪花,或偶尔露出来的沙屿。情感意绪在哪里?毫无疑问,融汇在无意识的汪洋大海里。语言不能涉足这无意识的海洋,本身就是一种缺陷与矛盾,情感意绪又是构成诗“意”的最根本的基因,言语根本上回避与它的联系和对它的表现,只能导致诗的破产。
诗“意”处于人的心理的无意识大海,其特性何在呢?既然心灵大海是无意识的,那就说明它是一片浑沌,是多样的聚合,“意”生成其中,天生带有了母体的“复合”特性。用现代心理学观点分析,诗之“意”也是复合的,甚至是多元复合的,其情感属于“混合情感”。而正因此,诗美出焉。
复合的“意”需要复合的手段来表现,而语言则是非复合的,与复合的“意”很难对应。所以大诗人陶渊明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复合的“真意”使单相的“语言”难以分“辨”对应表达。不独陶渊明君,得诗之道者都有如斯体验与感受。对于这种现象,椿是说“言”太无能,而是说“意”太博大而复杂微妙,“言”的出路在于突破困境,将有限的手段以无限地运用,运用语言的机杼,借用读者肌联想∥想象等心理合力去粒求还原“意”之深厚与博大,把恼其原质美。
诗“意”作为诗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蹈,它是主体与客体与受体“合力”熔铸的,在它里面涵纳了哲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与心理学的全部内涵,具有全息性特征。
从创作来说,要炼意、蓄意,要有心灵之博大浑厚。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原诗》)叶燮也以此观点衡断诗人,认为“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昆弟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原诗》)。叶燮推崇李白、杜甫及苏轼,无不是赞美其心灵之博大厚重。心灵博大厚重而能显发为厚重之言语作品,正如清代诗论家方恒泰所说:“根行深厚人,要他作浅薄事,说浅薄话,势必不肯;根行浅薄人,要他行深厚事,说深厚话,亦断不能。”(《橡坪诗话》卷十一)清代诗论家吴乔指出:“诗之难处在深厚,厚更难于深。”(《围炉诗话》卷四)诗的难处在于深沉与厚实,而厚实比深沉更难做到。厚实就是“意”的多元复合,富有蕴含,具有全息特征。创作追求“意”的厚实,是意厚为美的诗美性征的体现,而意厚为美又是因为“意”的复合特质所致。总而言之,意之谓美,乃因为具有复合的全息性。而创作上一对有意味的矛盾就出来了:诗人作家极力追求“意”的深厚博大,而“意”愈深厚愈博大,与“言”原生的表现功能的有限性矛盾也就更尖锐更突出。诚如清诗论家沈德潜所指出的:“情到极深,每说不出。”(《说诗晬语》)西方诗人、美学家曾用“折磨”、“缠斗”、“挣扎”一类极形象极感性的语言表明了“意”与“言”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好的表“意”之“言”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找不到适意的语言会毁掉一个可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人。
从诗的接受角度看,古人一再指出:“只有意会,不可言宣。”不能用语言对等翻译。换句话说,欣赏者接受诗本体的切入不是“言”对“言”的转换与接受,既需忘诗作之“言”,更要忘本身之“言”。一句话,言不尽意,只能从把握“意”入手,才能窥其堂奥,领略其美。可以说,这是古代诗学接受论主流。皎然《诗式》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刘禹锡《赠别君素上人诗引》:“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证也,犹暗人之享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于言,以闻于耳也。”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龚自珍《学诗诗》:“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游潜《梦蕉诗话》云:“学诗浑如学参禅,妙处难于口舌传。”黄子云《野鸿诗的》:“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宣。”
所有这些妙语精论,都说明“意”与“言”的不对等,不是一般地说“意”不可以“言”表达,而实实在在是说“意”含蕴丰富,具有复合性特点而无法完整直接转换。如果“意”是单值的,那么“言”之有什么难呢?
基于如此理解,我们便看到“言不尽意”非常准确抓住了“意”的复合性与“言”的单值性的矛盾关系,从而超越了它,深层地扣合了诗美特质。创作上是如此,从接受来看,依然是这样。如果将“意”与“言”平列,那就舍本逐末,把诗美降到了单值的语言美上。
四 意在“言外”:“言意”作为诗本体论的诗学意义
将“言”、“意”加以分辨,并概括出“言不尽意”,是古代诗学诗本体认识的关键环节。说“言不尽意”,是不让“言”冲淡“意”的诗本体位置。就其本身看,它成功地维护了“诗意”作为诗美核心本体的地位,而从整个心理诗学发展来看,它起到了推动诗学深化美化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能把“言不尽意”置于诗本体论外。
“意”作为诗人所要传达的内核或本体性东西,它依赖于“言”,又不止于“言”,“言”的达“意”功能是有限的。既重视“言”,又超越“言”,于是有了“言外”的美学疆域。
为解决“言不尽意”问题,早在先秦就提出“立象以尽意”,以“象”作为“尽意”的媒介,语言不能尽意,以“象”为中介来接近传达“意”的造型。这是很见智慧的。然而更深刻的是,古代诗学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开掘内涵,建构体系,认为“言”所造之“象”仍不能尽意。因为从“言”的角度只能把握象内之象,而不能显尽象外之象;只能显出意内之意,不能显尽意外之意。“象外”、“意外”实质都属于“言外”,是古代诗学从“言”出发辟出的言外世界。
“象外”,是说所造之象,有显层与潜在深层之别。显层可以语言解,而潜在的深层则出于言外,非语言能解。刘禹锡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董氏武陵集记》);司空图认为:诗“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品·雄浑》);沈德潜以陶渊明诗作论:“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唐诗别裁集·凡例》)。如此论述甚多,尤其是中国画艺日渐成熟以后,“象外”求象是中国画的一种高格要求,为画论所强调推崇,有力地影响了中国诗学“象外”理论的成熟。诗论将画论融通类比,画论所强调能画得就的东西只是画中所实际描述的形象,而画之精旨则在这些实际形象之外;诗论也认为诗所显于外的实际的表述的形象是其表,最根本的东西恰恰不是这形象。诗论家黄子云是这样解释的:“情志者,诗之根柢也;景物者,诗之枝叶也。根柢,本也;枝叶,末也。”(《野鸿诗的》)他将诗以本与末相分,认为“言”所表现的是枝叶,“本”在不显山露水的深处。通观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命题,它的这种思维方式及其内在含义是不难理解、也不难明白的。诗作为一种艺术也就表现在这种探幽揽胜、“一山放过一山拦”的神秘性中。试想,如果理性化的语言已作为一种终极的达意方式,怎会还有如此令人神往的探索呢?古代诗学又怎会定位到这样高的学科之位?!
再看“意外”。与“象”相似,古人又直接从“言”、“意”关系立论,认为“言”所直接诉说之“意”不是本意,更不是终极之意,而还有言外之意。殷罭在《河岳英灵集》,计论好诗说:“佳句辄来,唯论意表”;元人刘将孙感叹作诗:“今天山川草木,风烟云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识,其入于吾语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于意外焉”(《养吾斋集·如禅集序》);彭辂又从作诗角度表达类似的看法:“善诗者,……其言在意外。”(《诗集自序》)从“意外”来论诗意,也是令人玩味的。
关于“意”及“象”的本身内涵及审美心理含蕴都是异常浑厚的。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什么离开语言走得这么远,这么多精彩的命题都置“语言”于不顾。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非心理的单值的物是可描述出本真内涵,甚至可对等揭出其绝对内含的,而复杂者莫过于人心,一旦心物融合,则就很难单值地将其说清道明。语言是诗人形式造型的唯一手段,然而这一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又是如此无力,这不分明表示出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化倾向吗?它把文学作为人学,诗是人心的产物,人心如此之复杂微妙,“言”的地位受制于心理本性,其研究也应从心学的角度切入。当我们视角一换,自然茅塞顿开,发现出广袤的世界。因此,“言不尽意”说的提出,不仅没有因暂时忽视“言”的功能而阻碍诗学的发展进程,反而有力地推进了古代诗学的发展进程,是它促使诗学定位于心学,是它促使人们不浅尝辄止、不走到艺术宫殿的门口便误以为领略了美妙风光而止步,没有因爱“椟”而还“珠”。当我们去具体探寻语言的妙用时,仍然觉得作为诗本体论的“言意”命题具有战略性意义:没有“言不尽意”的深刻揭示,诗就不会有今天的艺术风采,诗学也不会有如今的学术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