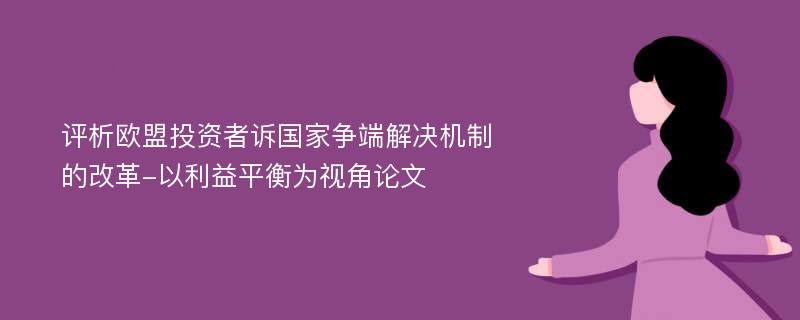
评析欧盟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
——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李荻凡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摘 要: 投资者诉国家争端机制因其引发的正当性危机饱受争议,欧盟近年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以投资仲裁为核心的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欧盟在对ISDS机制的改革中,试图通过加入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条约实体条款、规范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ISDS机制的透明度规则等加重对国家权益保护的措施,平衡ISDS机制中已经失衡的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但其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如对于国家规制权的保护范围并未明确、投资法庭缺乏便利性、国家的“回归”或将改变机制性质等。
关键词: 国际投资协定;ISDS机制;利益平衡
以投资仲裁为核心的ISDS机制,为保障投资协定中实体条款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一种中立的、去政治化的投资争端解决 方案。这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运行良好,但近十几年来,随着投资仲裁案件的剧增,一些裁决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批评,有学者主张这是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1]正当性危机在ISDS机制中的体现主要包括裁决不一致和缺乏可预测性、透明度的缺失等,其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东道国公共利益和规制权被忽略,引起东道国的规制寒颤(regulatory chilling),由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国际商事仲裁的色彩,使得该机制本身很难自我完善解决其合法性危机问题,必须进行改革,国际社会为此纷纷提出改革建议。欧盟作为ISDS机制的主要利用者之一,对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如在投资章节强调国家规制权、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增强ISDS机制的透明度等。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创建于德国斯图加特,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密封件供应商。自1879年建立至今,其在汽车零部件贸易和生产领域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目前,爱尔铃克铃尔总部位于德国代廷根,旗下18家合资及全资子公司分布于欧洲、亚洲及北美,为汽车制造企业提供隔热罩、发动机汽缸垫及其他密封件等产品。
一 欧盟对ISDS机制进行改革的原因
自《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华盛顿公约》)签署以来,由投资者发起的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国际投资仲裁,成为投资者解决投资争端的首选。[2]
以课外科技活动为载体的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高校某一部门的职责,也不是单一部门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高校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保证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开展的广度和深度,真正使学生受惠,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人才。
但随着国际投资实践的不断发展,国际投资协定的高度自由化,以仲裁程序解决公法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出现了正当性危机,引发了严重的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失衡。
(一)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
学生的生活数据信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象。如果我们想从这些复杂的数据关系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便可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技术对其进行处理使得这些数据信息更为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在可视化的过程中,数据将会变得更具备可塑性、可行性,最终更加人性化。由此帮助用户完善自己的日常生活,提高用户的生活质量。
国家规制权(right to regulate)源自国内法,指一国在领土范围内对其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管制自由。[7]其作为国际投资法视角下的特定概念,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权威解释。从国际法的视角,规制权的渊源为国内法,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并无需贸易或投资协定的授权。
为改变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失衡的现状,欧盟对ISDS机制进行了颠覆式的改革,包括采取了在投资章节规定国家规制权、通过构建投资法庭制度限制仲裁庭自由裁量权来解决ISDS机制因其浓重的国际商事仲裁色彩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增强ISDS机制的透明度来提高东道国国民对于其国家公共利益相关的国际投资仲裁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二)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失衡
自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生效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根据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来主张权利,使得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成为投资者向东道国索赔的重要法律依据。赋予投资者各种权利,对东道国的权利及投资者在东道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未有涉及,导致了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失衡,而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国际投资仲裁,因投资仲裁庭裁量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际投资协定,也将失衡带入了裁决中。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最初是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工具,直至上个世纪末,投资协定仍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与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间签订,发达国家旨在通过投资协定保护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其宗旨和目的是促进和保护投资。因此协定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核心,将维护东道国权益的问题置于一边。[3]
一方面,随着国际关系逐渐法律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也从政治色彩浓郁的外交保护模式走向了“去政治化”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模式。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受到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将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关系定位于平等的商事主体,即侧重保护私人的权益又要求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本身保密性高、还实行一裁终局及将司法干预减到最小。另一方面,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通常涉及的不仅仅是私有财产,还关涉东道国公众的利益,国际投资仲裁将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被管理与管理的公法关系,等同于了平等的商事关系,无疑弱化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并且,实践中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多是由东道国为实施公共管理职能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往往涉及到了东道国主权及其在劳工、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等重大利益领域的实现。
二 欧盟ISDS机制改革中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规定
国际投资协定在程序条款上偏向保护投资者、仲裁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上仲裁程序本身的不透明,让国际投资仲裁不管是机制本身还是其仲裁裁决的效力都不足以服众,从而形成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正当性危机。[5]
(一)在实体规则中加入国家规制权
实体规则是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主要依据,要改善目前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失衡的现状,就不能仅对程序规则进行改革,是以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建议文本中,欧盟第一次将国家规制权写进投资协定正文,即在文本的第2节第2条规定“本章节中的条款不得影响东道国在其领土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实现合理政策目标的规制权力”。而在EUVFTA第1章第13bis节第1条中也规定了“本章节的条款不得在缔约国领土内影响其合理政策,如为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以及道德,维护公共秩序及消费者保护或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提升及保护”,与TTIP建议文本中关于国家规制权的规定一脉相承。《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CETA)中虽然没有在投资章节明确规定出东道国权益,但序言中规定了缔约方的规制权,且在投资章节中规定了一系列现代化条款,以平衡投资者权益与东道国国家公共利益规制权之间的关系。
国家为保护本国公共利益而拥有的权力应该被尊重,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也不能例外。欧盟将这一理念贯彻到了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改变了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的法律依据本身仅规定投资者权利和东道国义务,而忽略投资者的义务与东道国的权益。
(二)规范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
2.1 肺部H-E染色和PaO2 结果(图1、表1)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损伤后4 h和12 h,治疗组炎症程度明显下降,PaO2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ISDS机制本身对于透明度问题的规定较少,欧盟对于ISDS机制改革中的透明度规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信息公开。CETA将《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UNCITRAL透明度规则》)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纳入了条款中,且对应当公开的文件进行了列举,包括磋商请求、请求被申请人决定的通知、被申请人决定的通知、同意协调的协议、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通知、对仲裁员异议的决定、合并仲裁请求、证据清单中涉及的物证等,EUSFTA在其附件8中也对应对公开的文件进行了列明,范围小于CETA,但授予了仲裁庭可以自行决定公开其他的司法文件。TTIP建议文本纳入了《UNCITRAL透明度规则》详细规定的文件公开,并在此基础上还规定了附加义务,扩大了文件公开的范围。EUVFTA有关透明度的规定中,在TTIP建议文本的基础上,规定了与透明度相关的文件都应该被公之于众(may be made publicly available)。(2)审理公开。CETA对公开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即如果没有当事双方提出申请,则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TTIP建议文本和EUVFTA中也对公开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
为保证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不会偏向于保护投资者,欧盟在ISDS机制的改革中,增设了对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和规范的内容,主要包括:(1)规范仲裁庭的组成。欧盟的投资法庭致力于改变ISDS机制中饱受诟病的仲裁员选任临时性,减小原来投资者对于仲裁员有极大的选择权,从而加大引发不公正裁决的可能性。(2)保证仲裁员的公正性与独立性。传统的ISDS机制采用的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框架,仲裁员来源的多样化和非专职性,使得仲裁员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饱受质疑。在TTIP建议文本和EUVFTA中,欧盟尝试着建立的投资法庭制度(the investment court system,ICS)要求法庭成员必须具备确定无疑的独立性(independent beyond doubt),EUVFTA的第4章第12条第14款中也作出了相同规定。(3)设立新的解释机制。欧盟希望通过效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常设委员会,给予成员国更多的条约解释权,以缔约国有权对仲裁庭的条约解释提出意见,且仲裁庭必须将其放入考量,以保障国家的规制权不会受到损害。
(三)完善透明度规则
此外,在CETA中规定,非争端缔约方可以针对条约解释向仲裁庭提出意见,对于非争端缔约方对于条约解释所提出的意见,仲裁庭必须接收。争端缔约双方也可以共同对条约进行解释,这种方式作出解释对仲裁庭产生法律约束力。
欧盟还在投资法庭制度透明度要求的内容中,加入了接受法庭之友的意见及第三方的介入,如在TTIP建议文本中规定“允许任何可以证明与案件有直接利益相关的自然人、法人作为第三方参与程序中,获取争议双方所有文件,并有权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面陈述和在听证会中进行口头陈述”。允许第三方参与投资冲裁无疑能够更好地保证投资仲裁裁决的公正性,更好地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避免损害东道国的公共利益。
三 欧盟ISDS机制改革中对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的不足
国际投资发展至今,已从资金的单向流动转为了多样化,许多国家已不再是单一的资本输出国或资本输入国,而是两者兼具。身份的转变,对ISDS机制的需求也从仅为投资者提供保护与便利,但忽视对东道国权益的保护,变为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应该对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程序进行适当限制,才能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6]欧盟对ISDS机制进行的改革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限定国家规制权的范围
国际投资仲裁源于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庭的组成具有临时性,由争议双方逐案挑选仲裁员,但国际投资仲裁又有别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双方当事人都有权主动提起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庭传统上多是由律师和处理商事仲裁案件的仲裁员组成。一方面,仲裁员的双重身份极易形成“旋转门现象”,另一方面,《华盛顿公约》中,虽然对仲裁员小组进行了规定,即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能力,尤其是法律方面的能力,但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员具备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知识。投资法学家沃德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共同体“事实上接管了国际投资仲裁,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新型商事仲裁业务加以运作”,但它们“几乎不能理解针对国家实施和运用规则与对待那些国际商界老手们之间达成的交易是大不同的”[4]。
式中:xw,yw分别为终端执行器x轴和y轴坐标;L1和L2为机械手连杆长度;Ox和Oy分别为第1个关节x轴和y轴方向的偏移量.
欧盟的ISDS机制改革,虽然体现了对国家规制权的重视,如明确了协定条款不能影响东道国在领土范围内为实现合理政策目标而行使的规制权力。但对于国家规制权所涉及的具体范围并没有明确,例如EUVFTA中列举了公共健康、安全、环境、道德、维护公共秩序、消费者保护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提升这些领域,即使以“合理政策”作为前提,其解释的范围仍然十分宽泛。将国家规制权写进投资协定中,但未对其进行明晰的界定,一方面仍然留给了投资仲裁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仲裁庭依旧可以对国家规制权进行有偏向性的解读。另一方面,极有可能出现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频繁使用“国家规制权”来回应其对投资者造成损害的行为,使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有悖于ISDS机制保护投资者的初衷。
(二)投资法庭缺乏便利性
欧盟在对投资法庭的组成设计中,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法庭成员都由缔约国选任,ISDS机制的初衷在于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去政治化,虽然ISDS机制所解决的争端涉及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但其要解决的依旧是经济活动所引发的争端,仲裁庭从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员变为了固定仲裁庭组成,让原本灵活、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机制变为了单一的法院制度。上诉机制虽然可以减小裁决的不一致性,但延长了案件审理时间,让案件更昂贵,加重了争端双方的经济负担。
(三)国家的“回归”或将改变机制性质
欧盟在CETA和《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The European Unio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EUSFTA)中,不仅赋予了争端缔约方共同解释的权利,还允许非争端缔约方针对条约解释对仲裁庭提出意见,其中争端缔约方的解释对仲裁庭产生约束力,而非争端缔约方提出的条约解释意见,仲裁庭必须接收。这样的规定将国家重新拉回了国际投资仲裁的舞台,根据缔约方所给出的条约解释意见而作出的决定不再是法律决定,而是政治决定。
ISDS机制的出现,是因为外交保护式争端解决方式与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方式都是由投资者母国出面解决投资争端,无法避免对国家利益的充分考量,一旦投资者利益的考量值小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值时,投资者的利益很可能被牺牲掉,这样一来,投资者不仅面临着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较量,还需要面对与投资者母国的利益较量。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政治化争端解决方式,才有了ISDS机制,以此一方面实现了投资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另一方面也排除了投资者母国对投资者的影响与干涉。
欧盟ISDS机制改革中为维护东道国的利益,加强了东道国对于条约解释的参与,但是否会出现东道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参与条约解释,而投资者母国权衡利弊后,并不愿意为了私人投资者出面进行条约解释,这样利益的天平又倾向了东道国?在条约解释中赋予了国家较大的解释权后,是否相当于将“去政治化”的ISDS机制变为了“政治化”的ISDS机制?
(3)日本农业移民研究。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以农业移民为主体,因此对农业移民的研究是重点研究内容。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有日本移民侵略时期东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变化及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影响;日本移民初期农业试点移民的过程和结局;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农村社会结构的殖民地化研究。
结 语
在ISDS机制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失衡,ISDS机制下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失衡原因主要包括国际投资协定忽视东道国权利、国际投资仲裁庭倾向保护投资者和其以充满私法色彩的仲裁程序解决公法问题。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失衡,要么使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将违背ISDS机制“去政治化”的初衷,使ISDS机制从利益失衡到再平衡,是ISDS机制改革的核心。欧盟在对ISDS机制进行改革中,将解决因机制的商事仲裁特征而引发的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失衡现状放在了重要位置,通过在投资条约中明确国家规制权、规范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ISDS机制中的透明度规则等措施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虽然其改革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尚未明确协定中保护的国家规制权范围、投资法庭缺乏便利性和国家的“回归”或将改变机制性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并将更加推动全球范围内对ISDS机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Susan D.Franck.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J].Fordham law Review,2005,(73):1521-1625.
[2]邓婷婷.中欧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欧盟投资法庭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7,(4):99-111.
[3]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1,(4):123-143.
[4]陈安,蔡从燕.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5.
[5]廖凡.妥协与平衡:TPP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6-8.
[6]张庆麟,郑彦君.晚近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新发展[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2):70-81.
中图分类号: D9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19)03-0103-03
收稿日期: 2018-1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及中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7CFX0 83)。
作者简介: 李荻凡(1993-),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责任编校:呙艳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