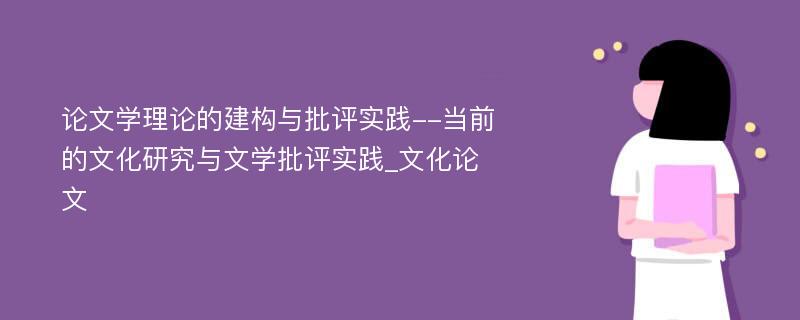
“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文化研究与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笔谈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文化研究再做经院式的谱系分析,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方法或研究范畴,在文艺、文化研究领域的普遍应用业已成为事实。只要我们翻开文艺杂志、打开与文化、文艺相关的网站、回顾一下我们近年来读过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在文学讨论会上使用的话语、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的视角,这个事实便无可质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正是源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对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实践的不同看法,在近一个时期得以集中地讨论。普遍的焦虑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审美批评是否还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论批评的民族性如何坚持或体现;文艺理论的边界如何确定,它是否还有自身知识的质的规定性;等等。
文化研究的普遍应用和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以“知识的方式”表达的两种文化和学术心态:是坚持传统的学科界限,发展以“审美”知识为主的文艺学,还是打破学科界限,以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知识整合,批评并参与当下的文化和文艺生产。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学术心态及其批评实践,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尖锐的学术冲突,这里并不存在等级、权力、取代和支配关系。而恰恰是学术研究向着多元化、多种可能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表征。我们应当承认,在大学的教育体制中,传统的文艺学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无可撼动的学科,它不仅被列入本科教学的主干课程,而且是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学科。虽然不断有对这个学科的质疑和批判,但因其树大根深而巍然耸立。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法和范畴,因其学科界限一直难以确定而莫衷一是,它蓬勃发展又歧义丛生,规模宏大又界限模糊。但它对新的文化语境中出现或产生的新问题的有效阐释和有力批判,使这一批评方法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和对象,而且也使文化、文艺研究者有了参与当下文化和文学生产的可能和契机。
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这一变化不只是物资生活的巨大丰盈、社会财富的急速增长,同时,还有在社会生活表层遮蔽不深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巨大变化。“消费文化”的兴起,不仅拉动了这个时代的巨变,同时也是改变或操纵我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隐形之手。当“消费”成为这个时代关键词的时候,它也无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艺生产的形态和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方式在过去虽然并非独一无二,但它延续的时间之长,制度之坚固,即便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因此,自80年代起,对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开放和自由的吁求,几乎是所有文艺家的共同心声。但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我们初始遭遇了有限度的开放和自由的时候,不期而遇的却是出人意料的“与狼共舞”,中国成了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丰富的文化实验场,除了国家主义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外,各种消费文化在市场霸权、商业主义和剩余价值的控制下粉墨登场。“消费文化”构筑了当下中国的超级文化帝国。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批判过的“文化工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姗姗来迟却气势汹汹。我们还难以解释这一文化逻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中国发达地区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是大有关系的。无可怀疑,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远程通讯空前发达的今天,麦克卢汉概括的“地球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天涯若比邻”虽然是电子幻觉,但全球在经济、商业领域、在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关联愈益紧密化,“与国际接轨”已成为社会流行语,即便在文化艺术领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和覆盖渗透,也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无论强势文化或弱势文化,都对全球化的趋势在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批判全球化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指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资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孕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伊氏所批判的显然不只是英国或欧洲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他所批判的还包括美国想象的“全球化”或文化同质化。西方的知识左翼批判全球化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对强势文化的自我检讨和批判。但我们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更多听到的还是对强势文化愤懑的抱怨或激进的指责,在全球性的“文化之战”中,我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弱势的文化地位和心态,也使我们失去了对自己文化检讨的耐心乃至愿望。
事实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知识左翼对“文化工业”、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到全球化的批判或检讨,是文化研究的起源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是他们关注的最基本的主题之一,他们的成就令人难忘。“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和艺术史方面最大胆的概述、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最精确的评价、从这一状况下的解放可能包含的要求与允诺的全部意义都要归功于他们。”(注: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他们发动的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浪潮,经由伯明翰学派和欧美文化研究“转向”的推动,至今方兴未艾。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启蒙话语受挫之后确实曾一度“失语”,但他们自我期待中的国家民族关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时,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和“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几乎同时如期而至,这对彷徨焦虑和目标迷茫的知识界来说恰逢其时。因此,表面上看,文化研究在中国是一种“外来话语”,是西方理论旅行的一个“驿站”,但就本质意义而言,它却接续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介入,是这一阶层挥之不去的思想情结,而文化研究恰恰提供了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批判的视角。
另一方面,文化语境和文艺生产的历史性变化,也使传统的“审美”批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仅电视剧、广告、大众传媒、酒吧、美容院、影楼、选美大赛、T型舞台、MTV、卡拉OK、人体彩绘等大众文化及其场景,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严肃文艺”创作,如小说、戏剧、诗歌、美术等精英文艺,“美感”为“快感”所置换和替代的趋势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的电影当然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分析,比如画面、音乐、服饰、场景等,但是,作为商业电影,他的成功从来就不是美学的成功,而是和巨额投资、媒体炒作和商业运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只要我们考察一下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官场文化”、知识分子小说、留学生文学、“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后”的写作,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可资谈论的话题,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性的,比如性爱、女性心理、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新的“零余者和多余人”、跨国文化和漂流心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不同时间等,对这些现象的批评和研究,以“审美”批评的角度来匡正和抱怨已无济于事,而文化研究却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其做出有效的阐释和批判。并不是说批评家非要选择文化研究作为武器,而是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状况,使文化研究有了用武之地。极端地说,90年代以来,如果没有文化研究的介入,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批评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我们也看到,对审美批评回归的普遍愿望当下正在经历,但是,具有悖论意义的是,一方面,“现代艺术中的那些超美学的观点似乎已经使人们对它完全失去了信任,并且在新的后现代的支配下,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和混杂物充塞着消费社会。而老的美学传统已几乎不能拿出足够的理论储备来解释这些新作品,因为这些新作品吸纳了新的交流手段和控制论技术。同时,对于过去的现代主义的‘进步’这个概念——导向新的技术发现和新的形式创新的目的——的怀疑使艺术进化论的时代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给传统的审美特性、关于自然与艺术经验、关于作品作为超越实践与科学领域的自主性等等问题的分析带来极大的未定性,如同我们时代的艺术接受、消费(或许甚至生产)正在经历某些根本的变异一样,使旧的范式变得互不相关或至少成为昨日黄花。”(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性中的形象转变》,见《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我们不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但是,我们遭遇的现代性,却使我们遇到了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同样的文化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文化阐释,是过去审美批评不曾遇到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审美批评在新的语境下的尴尬和有限性。在审美批评保有高贵气质的时代,艺术是一个超越商业化的领域,它有力量颠覆或抗衡与商业主义的联姻,即便在阿多诺的时代,他也试图在有限的领域内(如音乐),以美学的模式积极建构和创造新的批判文本。但是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徒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具有原创性源泉的原因。”(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性中的形象转变》,见《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131页。)
在“快感”文化的挤压下,传统的审美文化、严肃文化和更具消费性的文化混杂地重叠在一起,可供审美批评的范畴正在缩小。严肃文化虽然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从来也没有占据过中心地位,但在“快感”文化、中产阶级趣味和吞噬消费一切的大众文化喧嚣的声浪中,包括文学在内的严肃文化的边缘化,其形势越来越严峻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有人惊呼: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有繁荣的时期。这就赋予了黑格尔的箴言另外的涵义(或者也可能是同样的涵义):艺术属于过去,“总而言之,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对我们来说,艺术属于,而且永远都属于过去。”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内,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这一点黑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于其中,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①这一说法可能有些耸人听闻或过于悲观。起码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并没有、也决不会“成为过去”。事实上,大学的文学史编写及教学,所沿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社会批评或历史、美学的方法。在文学评论杂志上,用审美批评撰写的评论文章,仍然大量的存在。而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恰恰是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警觉和检讨:当下的中国文化,“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色彩绚丽、线条清晰的图画,不如说为我们设置了一处镜城:诸多彼此相向而立的文化镜像——诸多既定的、合法的、或落地生根或刚刚‘登陆’的命名与话语系统,以及诸多充分自然化、合法化的文化想象——相互叠加、彼此映照,造成了某种幻影憧憬的镜城景观。简单化的尝试,间或成为命名花朵所覆盖的危险陷阱”②。有的文化研究学者甚至直接提出“文化研究向何处去?”认为今日的文化研究已经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它涵盖面甚广,从古老的传统学科到新近的政治运动,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逐渐转化为劣势。文化研究对文化的定义如此广泛,就连霍尔也承认缺乏足够的专门化术语决定什么不是“文化”。文化研究这种“居无定所”的状况,决定了它是“一个毫无安全感的孤儿,在绝望地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③。这些警觉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位论者最后断言:也许,文化研究可能会消失在文学研究之中,今天从事文化研究的风云人物,许多都是文学专业出身;而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文化研究最早是来自于文学研究,那么,回到文学研究之中,或许是它最好的归宿。④文化研究学者事实上已在考虑文化研究未来的出路。问题是文化研究不是需要退回文学领域,作为一种方法或视角,它已经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即便未来文化研究需要一个界限分明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一种“遗产”或训练,它仍然不会被轻易删除或了无痕迹。
文化研究的利弊同时存在,大概也正因为它的“不成熟”,才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盎然兴趣。另一方面,这一歧义丛生的领域,无意间却也起到了学科整合或打通学科壁垒的作用。在学院体制内,学科划分过于精细,界限过于分明,已经暴露了未被言明的明显缺陷,跨越学科界限一步,学者就会言不及义甚至一无所知。这种学科壁垒造成的知识隔膜,反过来又带来了画地为牢的学科职业化心态。“术业专攻”使今天的学者更像一个“知识工人”。现代工业革命分工细密给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得以纠正。文化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不仅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革命,同时它也是学者职业“自救”的有效途径。文学等学科的交互效应模糊了过去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科学技术主义霸权强加给人文学科的精细分工,使人文学者在处理当下问题时,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和视野。因此,无论西方文化研究的前景如何,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应该是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
责任编辑注:此笔谈共有四篇文章,本刊转载了其中两篇。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艺术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