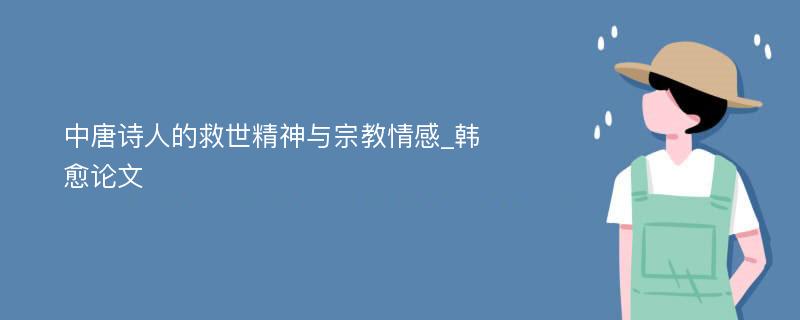
中唐诗人的济世精神和宗教情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情绪论文,宗教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唐的概念有宽泛和狭隘的划分方法,本文的中唐是指唐德宗贞元年间到穆宗长庆末年这一阶段(785~824),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一个新进进士集团在一系列的政治变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政治变革的同时,哲学文学变革的思潮也随之而来,使唐代诗坛再度繁盛。这一时期的诗坛的创作,充满着强列的济世精神,显然是和士阶层的救弊热情有关。人们通常把这一现象看作儒学传统以及儒学重新振兴的结果,而把士人政治变革失败以后,与释、道人士的交往,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举动。从而只注意到诗人们在诗歌创作技巧方面以及诗歌风格上接受宗教影响而得到发展,忽视了诗人们的济世精神与宗教情绪有互补的一面,同时也忽视了诗人们对佛学的中国化以及释、道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本文希望通过中唐一部分著名诗人的宗教情绪以及宗教态度,来研究这个复杂而有趣的现象。
一
研究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并且寻求它们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许多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出现,除了自身的发展因素以外,还有哲学思想的变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风俗的变化等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有时这类因素甚至可能左右文坛,因为中国的诗歌的创作主体——士阶层自汉代开始,始终与政治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曾经考察韩愈的新儒学与元和诗坛的关系。发现新乐府的创作、古文创作以及新儒学的提倡,几乎产生于同时,三者同是中唐儒学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拙作《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文学遗产》1993,6)新儒学的出现,与唐代士人的济世精神有关,那么,济世精神和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情绪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显然,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论述过这类问题,但是,个案并不足以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情况,而且我们也很难把一个诗人的思想构成说成“早年是属于道教,中年属于儒教,晚年属于佛教”,因为你不能清楚地划分,某人某个时期的思想中只有一种思想成分,当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唐代诗人有皈依宗教的趋势。事实上有许多人既同僧人交友,又与道士为伍,而他自己始终以儒者自居。
众所周知,宗教在唐代的发展,似乎有一个百花齐放的现象。以佛教为例,自唐高祖及太宗起,至武后而大光,除武宗等少数帝王外,大都有信佛的记载。此外,佛教本身在唐代的发展,也是一个兴盛的时代,所谓“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兴”(注: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此外,道教在唐代则有了空前的地位,因有老子与李唐王朝同姓的传说,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八年(625)下诏宣布了“道教第一, 儒教第二,佛教第三”的原则,奠定了唐代“三教论衡”以及“三教归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派别,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和矛盾是正常的。在唐代,儒、道、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势力有所消涨,但总的说来,基本上处于和平共处的局面。
信奉者的宽容首先表现在统治者的兴趣上,三教论衡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三教论衡最早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唐代自高祖起就有此类活动。经太宗、高宗、玄宗历朝,遂成常制。据目前能看到的有关三教论衡的记载,这些当着皇帝的面,儒者与和尚、道士们的互相攻讦,大多以趋同而告终。三教论衡以趋同为结局的传统大约也从南北朝开始,《北周书·韦夐传》说,“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辩其优劣。以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乃著〈三教序〉奏之。”后来唐太宗幸国子学,亲临设奠,引道士、沙门、博士,相与驳难,并曾下诏曰:“朕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注:见《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这些材料说明,三教的辩论,根本目的在于求同,这个同,便是“同归于善”。
有关三教论衡的全过程,今天已经无法见到详细的资料,各家诘难的问题以及答辩也仅存零零星星的片段。如《新唐书·艺文志》载孙思邈有《会三教论》一卷,《宋史·艺文志》载陆龟蒙有《三教论》一卷等,如今本集均不见载。中唐以后,三教论衡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取悦于皇帝的形式:据《新唐书·徐岱传》记载,“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诏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所以,到了懿宗咸通中,已有优人演戏来讽刺这种情况(注:高择《群居解颐》,参见任二北《唐戏弄·剧录》所引。)。
白居易集中有《三教论衡》一篇,记叙作者与“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清宫赐紫道上杨弘元”的问对。序言中盛赞释、道两家的学问,指出因“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可惜作者略去了僧、道两家答对的内容,而仅保存了作者自己一方(儒教)的答对,因此,僧、道的答对不得而知。但从白氏所提供的论辩题目和论辩排场来推测,似乎是一种依次宣讲、互通学问的过程。如义休法师所问的“《毛诗》的六义”、“《论语》的四科”,白居易所问的《维摩经》中“芥子纳须弥”的理解,以及道家《黄庭经》中有关“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可想而知,参加论衡的儒道释三方人士除了熟读自家的经典,还要大量阅读其它二教的各种书籍,正如白居易在论衡时所说的那样:“居易窃览道经,初知玄理。”不然的话,这般论衡,无论是真正的辩论还是演戏,都是无法进行的。
如果说,统治者为三教的共存提供了政治基础,那么,一场又一场的三教论衡客观上促使士阶层中更多的人士广泛地接触佛、道两教,寻其异而求其同。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试想,在大量研读释、道两家著作之后的儒士,能没有一点想法吗?三教的“同归于善”,表现出一种宗教的宽容性,最终成为儒士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其它宗教的基础。
二
严格地说,儒学并不属于宗教,但它的确又是一种生存哲学,是千余年来中国士阶层立言立身的哲学。韩愈所谓的道统就是这样一种令士人自觉遵循的处世哲学。中国的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自孔子起,便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特征和性格,对社会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关怀,成为人类社会某些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种终身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便来自于儒学学说的道德观和政治理想。说到底,也可算作一种宗教情绪的反映。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义,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注:《论语·里仁》、《论语·泰伯》。)这里的“道”,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所负担的关怀和责任,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来体现的一种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维系体系。因为儒家的理想是希望先建立一种文化的、道德的秩序,然后通过这种文化的、道德的秩序去建立政治的法律的秩序。由于士阶层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己本身“道统”的传承去实施,还必须通过某种中介如政治势力或政治集团,把文化道德秩序变为政治法律秩序,这就决定了士阶层必须通过被政治势力或政治集团所“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既要有“笃信善学,守死善道”的毅力,又要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骨气。也就是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是在逆境之中自觉地维护文化、道德的秩序,在这一点上,“儒教”要求信奉者超越个人利益的限度比起其它宗教来要严格得多。在现实社会里,士阶层往往会处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而儒家本身也不可能有任何缓冲和通融的办法。因为儒教从来都是一元化的世界。
中唐诗人们的济世精神首先来自于士阶层的这种儒家传统特征和性格,自贞元年间起,政治变革和文化的变革不断交替着进行,但每一次的变革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先是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被贬为阳山令,然后是永贞事变后王叔文集团中的刘禹锡、柳宗元,再者是元和时期的元稹、白居易……,古文制诰以及新题乐府诗的创作至长庆以后也掩旗息鼓,这些诗人也都与佛、道两家有点关系,但最终未脱离儒家的立场。
白居易集中有律诗《读老子》、《读庄子》、《读禅经》等作品,均为大和八年(834)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所作(注: 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二。)。此时白氏和释氏已过从甚密,但诗中仍能见出他那种儒家的价值尺度。
如果说,三教论衡时,白氏只是为了应付形式或互通学问而对僧、道发出质询,那么,上述的三首诗歌则是诗人与释、道价值观念的真正分歧。作为本质上仍是儒家的白居易即使到了晚年,即使时时念叨“尤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却被山僧戏相问,一时改业意如何”,仍然不能悟出佛门“空”的道理。开成五年(840), 又有《自戏三绝句》。诗中心与身的一问一答,表现了作者表面的平静而内心的极不平静。不断地强调自己已是心闲,因心闲而身闲,恰好应了白居易嘲讽老子《道德经》的那句话:“言者不知知者默”。
对于晚年半官半隐的生活,白居易始终是站在一个儒家的立场上来表述的,这说明他只是在现实生活面前用一种开通的方式接受现实。读经也罢,坐禅也罢,不过是儒家“独善其身”的一种变换形式而已。用释、道比较适意的生活观以及生活方式来冲淡“独善其身”中严于律己的成分。同是写于开成三年的两首诗(注: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四。),便表现了作者的这一心路。
由此可见,作为儒家,儒学为体,而其它宗教则为“用”。无论他的思想体系中吸收了多少释、道成分,除了化解、融合,便是在不违背“儒教”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将释、道化为己用。这样,中唐的诗人们,不论宗教倾向如何,他们的人生观始终是入世的。
三
儒学能“治世”,而佛学能“治心”,这在唐以前就被意识到了。如南朝宋时人宗炳就说过“依周孔以养民,味佛法以背神”(注:《明佛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二十七)》。)。因此,“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便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共识。
三教论衡到三教归一,对士阶层来说,是一个不断调整儒学与释、道关系,将释、道为己所用的过程。从士阶层的信仰需要、生活方式的需要出发,佛教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宗派——禅宗来适应这种需要,可见唐人强烈的实用主义及现实主义。
如前所述,三教论衡要“同归于善”,而“善”又恰好是与儒学济世精神及济世理论最近的结合点。刘禹锡在《袁州萍乡县杨崎山故广禅师碑》(注:《刘禹锡集》卷四。)中指出:
“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有水火异气,成味亦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起因业,故劫浊而益尊。自白马东来而人知象教,佛衣始传而人知心法。弘以权实,示其摄修。味真实者,既清静以观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迁善;厚于求者,植因以觊福;于若者证业以销冤,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生死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
刘禹锡的这段话,实用的意味就很浓,说出了以释家理论补充儒家的“罕言性命”的需要,并提出各取所需的用法,但最终仍归结为有助于教化,这是典型的儒家立场。按照刘禹锡的理解,在济世的宗旨上,儒、释是相通的,只是济世的途径及方式不同。如果以此推论,儒家的兼济,便可以更宽泛一些,身为达官时自然要兼济,而隐退之时也可以“兼济”,只是方式有所改变而已。例如儒家的施善,根本目的仍在于现世,而不仅局限于后世的福报。白居易集中有《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其一云: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经。夜州通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谙施慈悲与后人。
此诗作于会昌四年(844),白氏已七十三岁,诗前有序云:
“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会昌四年,……经营开凿……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
儒家对人类以及对社会的关怀是现世的关怀,所谓的济世,也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这是儒教与释、道的本质区别。白居易开凿八节滩,不光是佛家慈悲为怀的意义,而是希望身殁心存,永远能造逼于后人。他强调并不要求来世的福报,体现的正是儒家超越个人利益的济世精神。但是这种力所能及的“兼济”,也证实了佛教思想的“阴助”。
中唐士人的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做法,还体现在现世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渴望健康长寿而炼丹服丹;与僧人的交往,有时是为了求医治病。刘禹锡集中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注:《刘禹锡集》卷二十九。)
又有《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
“劳动诸闲者,同来问病夫。添炉捣鸡舌,洒水净龙须。身是芭蕉喻,行须邛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注:《刘禹锡集》卷二十二。)
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调节、宣泄压抑的需要。这在中唐诗人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许多士人在谪贬以后,与僧、道过从甚密,研读经书,多半是出于排遣孤独、压抑的心理需要。
唐人的实用主义同时也深深地渗透到释、道两教之中,长期于儒者交往,僧、道也大量阅读儒家经典,习做诗歌,曾涌现出不少著名诗僧、如灵彻、皎然、道标等。甚至儒教中的伦理观也为僧人所接受,如柳宗元的《送元嵩师序》(注:《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九。)提到的元嵩,便是一个恪守孝道的僧人。
四
中唐士阶层的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最大成功是新儒学的建立。新儒学的开创之功不能不追溯到韩愈和李翱。新儒学触及性命的问题,李翱认为,因传统的儒学“不足以穷性命之道”,所以,人们便依赖于庄、列、老、释来解决生命的起源和归宿的问题(注:见李翱《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这个看法与刘禹锡的佛教“阴助教化”的论点很接近,可见,新儒学的理论借鉴佛学的理论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此外,李翱的理论中也引用了《易经》,从他现在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到作者与当时道教著名人士的交往:
“紫宵仙客下三山,因救生灵到世间。龟鹤计年承甲子,冰霜为质驻童颜。韬藏修咎传真箓,变化荣枯试小还。从此便教尘骨贵,九宵云路愿追攀。”
——《赠毛仙翁》(注:《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九。)
李翱的《复性书》与韩愈的性三品的根本不同,就是他涉及了“性命之源”这个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李翱的发展,使初创的新儒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他的“复性”说,正是吸收了佛教的学说才得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后人评价说“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提到韩愈的性三品的便要提到韩愈的排佛。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十分极端的,与中唐士人宗教倾向截然不同的例子。但如果我们从中唐士人的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文化心态来理解,便会发现,韩愈现象并不是单一的,就韩愈本人的宗教情绪来说,也不是仅用“排佛”二字概括得了的。
有唐一代,最大的一次排佛、毁佛事件发生在武宗的会昌年间。在此之前,便是韩愈的谏迎佛骨。宪宗元和十四年(819 )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韩愈为此上表劝阻,言辞激烈,宪宗大怒,于是便有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结局。韩愈并没能阻止迎佛骨的仪式,但却因此而名声大震。这两次排佛,前一次没有结果,而后一次有了结果,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状态和经济承受能力。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僧尼不事生产,却又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产业,这种状况沿至文宗大和年间,文宗便有了去佛的想法(注:杜枚《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文宗皇帝尝语辛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崐人,今加兵、佛,……其问吾民尤困于佛。),至武宗毁佛时,经济上的不堪负担已作为主要的原因写进了诏书(注:见《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
“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工木之功,夺人力为金宝之饰……且一夫不出,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至也。”
韩愈反对迎佛骨的举动,并没有从经济的角度提出来。或者说,宪宗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尚未恶劣到武宗时期的无法维持。也许这也是导致韩愈上疏失败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中唐的士人要重新振兴儒学,目的仍在于建立一个文化的道德的秩序,这个思想体系是韩愈在《原道》中已经形成的。因此,他的《论佛骨表》(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强调的重点是有关“伤风败俗”的社会影响。他的《送灵师》(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诗,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由此可见,韩愈排佛的依据,一是要建立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三教并存;二是担心礼佛的形式蛊惑人心,妨碍对儒教的信仰;三是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这三个方面,韩愈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强调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秩序,这是因为韩愈希望以此来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因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鲜明的反宗教情绪。但仅仅就反佛而言,以经济上的原因上表反佛的在韩愈之前有十数人(注: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而不满释道礼拜形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后世儒家赞誉韩愈反佛举动不在于反佛本身,而在于他直言敢谏。这恰恰又是一个以儒学为体的立场的证明。
既然中唐的士人以儒学为体,释道为用,那么,他们对释、道二家在一定程度上总会持有保留。例如禅宗特别是南禅在士人中盛行的一个原因,便是唐代士人不拘泥礼拜的形式。刘禹锡《佛衣铭》(注:《刘禹锡集》卷四。)中所说的“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贵”,就是指士阶层与普通民众在信仰礼拜形式上的区别。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韩愈的反宗教情绪是因为强调儒学为体而表现得突出一些。中唐士人的宗教倾向则因释道为用而表现得突出一些,韩愈与中唐的士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尖锐的对立。中唐士人有以儒学为用体的立场,而韩愈同样也有以释道为用的事例。
《唐宋诗醇》在韩愈《送灵师》诗后评论道:“退之辟佛,却频作赠浮屠诗,……其所以称浮屠者,皆彼法之所戒。良以不拘彼法,乃始近于吾途,且欲人其人而已。并未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这就是说,儒、释、道三家在遇到原则性问题时,界限很分明;但日常交往时,脑子里“守戒”的那根弦并不都绷得那么紧,而是作为普通人,那么,韩愈反佛归反佛,作诗归作诗,不是很正常吗?《唐宋诗醇》的作者看来很能理解唐代士人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必为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大惊小怪了。
历史上韩愈的反宗教情绪始终被理解成为一种非常绝对化的情绪。宋儒甚至怀疑《与大颠书》是伪作,直到朱熹才做了比较可信的分析(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
同样,关于韩愈服用丹药的事,后代也有许多人认为有损于韩愈的形象而为之开脱。但韩愈在《李于(一作干)墓志铭》(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中记载了自己曾受吉州司马孟简所赠的“秘药一器”,而这一器“不死之药”多半属于丹药之类。
韩愈以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运作,还表现在他的诗歌作品广泛地吸收寺庙壁画的艺术营养,从而形成独特的奇险风格。这一点,已有学者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唐诗坛的艺术多元化以及诗人观念价值、思想方法的复杂性,来源于中唐的社会变革、中唐哲学思想的演化等多种因素。中唐诗歌里,既有反映士人济世理想和世途挫折的作品,又有反映释道思想及隐世生活的篇章,仅仅将此解释为诗人的“消极表现”未免过于简单。就中唐士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其中一个层面就是传统的儒学与佛教、道教的矛盾和调和。三教的并存,首先取决于统治者的“儒教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的实用主义指导思想,使三教并存获得了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而三教的“同归于善”又成为士阶层在儒学为体的基础上容纳释道的思想基础。儒、释、道在士人的实际生活中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导致中唐的士人采用了儒学为体、释道为用的实用主义生存方式,成为三教并存的社会基础。同时,释、道教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新儒学向心性学的方向发展,并支持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直觉型的审美方法。释、道教中的适意的生活观还为儒教“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行为方式拓宽了界面。
标签:韩愈论文; 儒家论文; 白居易论文; 国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刘禹锡集论文; 读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