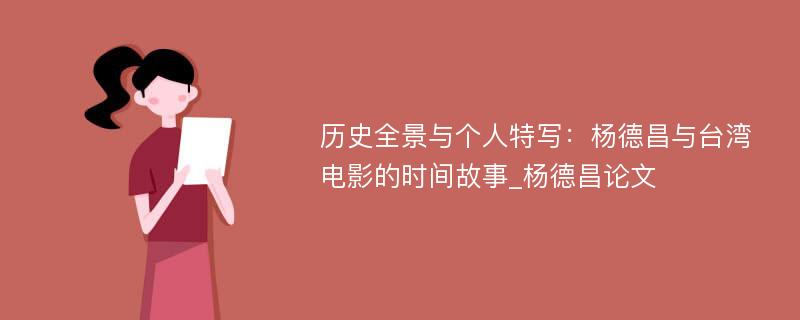
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景论文,特写论文,光阴论文,个体论文,台湾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华语电影如百花盛放的今天,台湾“新电影”已如远去的明日黄花日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今年夏天,“台湾新电影”的主将杨德昌导演的溘然辞世则使人们的目光暂且驻足、回望,缅怀这样一位孤独而执著的电影作者、缅怀台湾电影史中那段静美而真诚的光阴故事。
“都市文化思辨者”、“知性思辨家”、“台湾新电影的旗手”等是人们冠以导演杨德昌的称号,作为台湾的第二代导演和“新电影”的代表人物,杨德昌在台湾电影中的确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地位,尽管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他的影片所呈现出的叙事特征、镜语风格、精神气质、题材类型、表现形式以及深刻内涵则是颇为值得反复解读的。也正是这些风格与特征,一方面构成了台湾“新电影”的艺术品格与创作风貌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对此前的台湾电影中可供吸纳的艺术主张和创作经验的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并且,“新电影运动”初期所迅速形成的艺术追求也影响了新电影后期及后新电影时代台湾大多数艺术电影的叙事风格。由此,作为台湾电影导演坐标系中的重要一员,杨德昌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个体,而是台湾电影成长中一个起着承前启后、书写历史的关键人物。此刻,当我们旧事重提,反观杨德昌的创作时,特写式地将其作品在眼前中一一闪回可以算作是纪念的方式之一,不过,若能身置历史的时光隧道全景式地扫描杨德昌之于“新电影”以及整个台湾电影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或许会得到不同于以往的发现。本文的写作目的正基于此。
杨德昌与“新电影运动”
台湾“新电影运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源于当时台湾电影逐渐沦落的大环境。一方面,日趋格调低下的功夫片和言情片被大多数观众厌弃;另一方面,当时的电影市场已经完全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在创作能力和经济能力皆低下之时,起用新人成为解决当务之急的最好办法。1982年8月28日,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四位新人以合作的形式共同执导拍摄的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在台湾联映,标志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滥觞。此后,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张毅、王童、万仁、陈坤厚、吴念真、朱天文、小野等一大批青年人以编剧、导演的身份投入到新电影的创作中,《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看海的日子》、《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玉卿嫂》、《我爱玛莉》等作品也相继诞生,并成为台湾“新电影”的重要代表作品。其中,以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且皆获得国际影坛的认可。
台湾“新电影”的参与者们虽没有制定过统一的创作纲领,但却不约而同地拥有较为一致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追求。整体来看,“新电影”的作品在题材上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作品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这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① 很多作品充满了对台湾现状与历史的反思。而且,新电影的许多作品(如《恋恋风尘》、《小毕的故事》等)都选择了将成长记忆作为创作题材。“新电影”在剧作结构和内容上较少注重戏剧性和情节性,而是偏爱散文化的结构方式,追求朴素、清新、自然的写实风格。此外,“新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表现方式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探索与实践。它借鉴欧洲现代电影中惯用的长镜头、景深镜头、跳接等摄影技巧和剪辑手法,形成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美学特征。
作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杨德昌的导演手法及其作品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可看做是新电影整体创作特征的有力例证。当我们把这些由旁观者高度提炼、归纳的艺术特征带入由杨德昌构建的鲜活、流动的影像世界后,我们会发现,支撑这些共性特征的恰又是那些有着鲜明杨氏印迹的、个性化的元素,诸如主题、思想、人物、景致、语言……
台北故事:写实镜语下的人与城市
对城市这个人类生存空间的描绘是杨德昌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表征。同为“新电影运动”的主将与旗手,侯孝贤钟情于对乡土情怀的书写,而杨德昌则始终将视线投向令他熟悉又陌生的繁华城市,用影像记录着它的变迁。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来替台北市画肖像。我要探寻台北这些年来发生变化的方式,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台北市民的。”
六七十年代是台湾社会变化的一个阶段,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到了80年代初,台湾社会由小农经济时代转型为机器大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有力的冲击,并导致传统的裂变。而这一过程刚好又是杨德昌这些新电影的作者们身体成长、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作为这一变革社会中的一分子,杨德昌用影像转述了自己的所见,表达了对这一社会变革及其引发的现代人的种种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的思考和态度。
从其处女作《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便开始了对城市的关注,表达现代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世界的空虚这一主题上。之后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Ⅸ独立时代》、《麻将》和《一一》都延续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这一主题,显示出杨德昌对于台湾中产阶级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高度的关注及长期的思索。从《海滩的一天》到《一一》,杨德昌在对人物速写式的描绘中,仿佛完成了一次从二人近景拉开至多人全景的运镜过程。在《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独立时代》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分辨出主要角色、核心人物,到了《独立时代》、《麻将》,片中人物就开始以群像式的样貌出现了,因为导演想要言说的主题并非只负载于一两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代表了不同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物又集合为当下社会现代人的基本表征。他的最后一部影片《一一》依然以台湾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为切入点,围绕台北一户中产阶级家庭展开情节,构架更加宏大。杨德昌说:“家庭这个单位中的每个人物都处于不同年龄,这使我很容易来探求一些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影片中的人物近乎代言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人群,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成员就如同抽样调查中的不同样本,既共时地体现了各自生命阶段的苦恼和困惑,又历时地串连起整个生命过程的情感状态。
在杨德昌的7部长片中,从所描述的社会时代来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其他作品都表现了当下社会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而这一部则讲述了60年代灿烂阳光下的残酷青春。事实上,描述时代的不同丝毫没有影响导演对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的传达、对残酷社会现实的批判。杨德昌曾经说“我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所见解。若你只说好话,不说难听话,不会让我感到你有思想,你有思想的话一定是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双面。”有人认为,杨德昌对城市现代生存方式的批判态度经历了从冷峻到温情的转变,这种判断或许依据于影片中人物的身份、生存环境以及最终的走向、结局。在未找到相应的导演访谈作为注脚的情况下,笔者不敢随便附和这一说法。尽管在其最后一部作品《一一》中没有出现血腥的画面(“胖子”杀人的画面被导演以电子游戏的画面处理了),不过,“胖子”的杀人依旧是令人叹息的青少年犯罪,而且在影片结尾处,管洋洋在婆婆追悼会上的“悼词”似乎更是令人心悸,导演借儿童幼小的身躯、稚嫩的言语道出了自身对生命的态度与感知。在这样一个平静的画面下所蕴含的力量与冲击要比杀人流血来得更为强大、震撼。因此,或许我们不能仅从表面上便认定导演的批判态度发生了变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杨德昌所关注的人群是广泛的,他有可能是某个高级写字楼的白领,也有可能是街头小混混,城市中的普通人、边缘人皆是他言说的对象,毕竟他们都是高度物质化进程中精神状态极度失落的人。
杨德昌为自己所隶属的城市记录下历史的存在和人性的真实。与其说他将城市与人作为了创作素材,不如说他是在为台北用影像书写一段历史。而如此忠实、执著地表现一个城市的电影作者不要说在台湾,就是在内地、香港,乃至世界恐怕都是鲜见的。
光阴故事:冷峻目光里的成长记忆
“新电影”许多作品都将个体对成长的记忆/回忆作为影片的题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新电影剧作者成长的二三十年,正是台湾政治、社会、经济变化最巨的时期,自传式的成长回忆,不但展现台湾电影史上未曾有过的现实笔触,也代表着多种角度寻求台湾身份认定的努力”。② 《冬冬的假期》就是根据编剧朱天文的散文改编的,其间充满了作者零散的个人化回忆。《恋恋风尘》是编剧吴念真的个人记忆,取材的内容多半都是他自身切实的生活经验。而《童年往事》则源自导演侯孝贤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这一点他在影片开始的旁白就有所点明。事实上,任何一个创作者都不可避免地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以往生活的痕迹,对于杨德昌来说亦是如此,只是他很少以自己的某段经历作为素材,而是将那些生活中的感受、习惯零散地隐藏到影片的角落里,自我观赏。例如,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表现开放空间的镜头,一个小学生在书摊买漫画书,小四入画后,小学生因怕小四离开,当小四遇到小明,追问她事情的时候随即改变了运动的方向,镜头跟随两人而移动,小学生此时又再次入画,向老板买漫画书。这个买漫画书的小学生或许很像当年一到星期四清晨就到街角的杂货店,排队等着租阅《漫画大王》的杨德昌。因此,当我们津津乐道于那个常被引为范例的空间段落时,或许杨德昌更会被画面中时隐时现的小男孩所感动。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作品中较为著名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以童年记忆为素材的作品。这部影片也并非杨德昌自己的真实经历,而是根据他所在的学校发生的一起真实的少年杀人事件改编的。中学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别恋而将其杀害,也因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少年犯。这件事情对杨德昌有着极大的触动,因此,当他有能力用影像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一部真正称得上表现残酷青春的影片便诞生了。影片中,杨德昌表现的并非少年杀人这一事件本身,而是以其编织的诸多情节深刻地阐明了造成这一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同时,他也在小四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很多个人的影子,例如他的家庭成员构成、学习情况、在学校与老师的关系等都与杨德昌本人的情况相似,甚至校名也用的是母校的名字“建中”。
与“新电影运动”中其他描写成长的影片相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显得最为悲凉、最为刺痛人心。在其他的以成长记忆为题材的影片中,或多或少会洋溢着一些年少的简单和美好,即使是那些伤痛也无非是成长本该付出的并不致命的代价。而在混迹着形形色色青少年的牯岭街,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灿烂的阳光,尽管影片的英文名恰恰为“A Brighter summer Day”,这仿佛也成为影片的又一个隐喻。
直至今日,谈及青春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依旧是堪称经典的一部,它不仅是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作,也是华语电影的重要作品。很多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深受这部影片的影响,也尝试将自己的青春体验融入作品之中。至于这些作品的成就能否与此片相提并论不是这里要强调的,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仅就这一部影片来衡量杨德昌在华语乃至世界影坛的地位都是不为过的。
对写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新电影运动”诞生的电影作者,杨德昌的创作在引领了新电影的诸种艺术追求、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方式的同时,也继承了台湾电影固有且特有的主题诉求,并以崭新的形式将其加以呈现。
二战以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相继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写实主义电影浪潮。从1963年开始在台湾兴起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就是受该浪潮的影响。台湾“新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是对“健康写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
1963年,龚弘就任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提出了“健康写实主义”的主张。在此创作路线的号召下,台湾第一代导演李行、白景瑞等人创作了一批较优秀的作品。但“由政治所认定的‘健康’,往往会对社会‘写实’的深度及其认识价值形成一定程度的削弱或损伤”,③ 因此,写实电影并非完全而彻底的“写实”。由于受台湾当时电影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那时候的“健康写实主义”影片大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1、背景大多设置在台湾某农村、渔港等地,以农业、渔业的生产为题材;
2、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女演员的装扮上往往带着不协调的城市妆;
3、健康写实摆脱不了“宣政”的任务;
4、健康写实电影的结局往往是善良、正义的一方战胜感化了邪恶的一方,或者是大团圆式的结局。④
无论如何,伴随着60年代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早期的写实主义影片,如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等叫好又叫座,还是促进了台湾电影的发展,“国片起飞”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汇。在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后,由于政策、经济、海外市场、观众的观赏兴趣以及电视新媒体的出现等多方面的原因,台湾电影逐渐面临瓶颈。如前文所述,也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电影”应运而生。
“新电影”的美学特征之一便是以静观和间离的镜头去表现现实生活。这恐怕还要归因于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新电影作者的巨大影响。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精神之父安德烈·巴赞认为,唯有冷眼旁观的镜头才能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⑤ “新电影运动”的作者们对写实风格的追求正是为了“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作为“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果说侯孝贤更着意于对乡村、小镇的描绘,从而形成带有水墨画般的诗化风格的话,那么杨德昌对城市的复写则更像是拍照,既不掩饰也不修饰,并且一个思辨者的审视目光仿佛永远相伴。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到《恐怖分子》中酷爱摄影的小强,一个拿着相机到处游走,为台北这个城市进行记录的青年,或许这里真的有作者的影子在里面。
认为杨德昌对城市的关注始于其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已无争议。不过,在1980年,杨德昌帮助好朋友余为政创作《一九五零年的冬天》的时候,他在编剧上强烈的社会触角点和对人物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兴趣已经隐约可见了。这一主题以及独特的出发点和触角,也一直是后来杨德昌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使他后来的作品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观察角度,而这正是70年代台湾电影最为欠缺的一种人文观点。
杨德昌的电影有着论文式的结构与冷峻的思辨。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电影作者,在直面台湾社会高度物质化扭曲下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不满足于仅仅再现现代人生活中的种种苦恼,而是要进一步探讨导致现代人苦恼的深层原因。纵观杨德昌的影片,我们发现,都市生活的复杂和虚伪、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缺乏真情实感的交流、人与他人甚至自身的疏离与隔膜、没有值得信仰的东西、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个体不加约束的物欲等都是导致现代人痛苦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影片中借剧中人之口道出了很多颇为值得玩味的“至理名言”,例如,《光阴的故事·指望》中,男孩说:“我以为学会以后,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会骑了,却又不知道去哪里。”《麻将》中的红鱼对伦伦讲“不要动感情,要动脑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独立时代》中男作家指出,有些人“连自己都懒得去了解”,片中的一位创意设计师说:“在现在这个社会,谈感情是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感情已经是一种廉价的借口了,装得比真的还像。”在《一一》中,男主角NJ说:“诚意可以装,老实可以装,交朋友可以装,做生意可以装,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一一》中婷婷对婆婆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得不一样呢?”每个人看似随意说出的话,都值得观众深思、自省。同时,他也借剧中人之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仿佛为现代人的精神顽疾开出的一剂药方,例如,《麻将》中红鱼的父亲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都是金钱买不到的”;《独立时代》中司机对男作家说:“活得好好的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一一》的最后一个镜头里,洋洋对着婆婆的遗像说:“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现在看来,杨德昌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镜头道出了他对电影的诉求与渴望、态度与理解。
结语
尽管“台湾新电影”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并获得国际认可的同时,票房成绩却不那么理想,到了1986年,新电影在数量上直线下降,台湾媒体也越来越多“倾向香港、检讨台湾”的呼声。到了1987年,新电影的导演已遭到片商的普遍拒绝。1987年1月24日,《中国时报》发表了詹宏志起草,杨德昌、侯孝贤、张毅、万仁、柯一正等53位电影人签名的《民国76年台湾电影宣言》,承认“电影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商业活动”,但也宣称“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另一种电影”即“那些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电影”。“宣言”成为台湾电影走向没落、宣布终结的标志。当年签署宣言的导演们对电影的坚持,或许变成了迂腐的笑柄;媒体和影评人也把台湾电影日渐式微的责任归咎于“艺术导演”的身上。侯孝贤曾不得已地自嘲说:“台湾电影就是我和杨德昌搞死的。”这种无奈的自嘲是令人心生悲凉的。作为杨德昌的好朋友、赖声川导演的夫人丁乃竺曾经说:“杨德昌在电影上有很多委屈,有一次他说,其实就是我们太在意电影了,希望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着行人,我就在想,你们究竟想看什么电影呢?他们可能不在乎,但是我们在乎。”“杨德昌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们真的是拿命在创作的人。’”
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杨德昌以及以他和侯孝贤等人为代表所引领的“新电影运动”呢?如杨德昌所言“所有的事情都有双面”,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新电影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及影响力。可以说,国际影坛对台湾电影的认识与关注便是从“新电影运动”开始的。这其中便有杨德昌的贡献,他的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获得第28届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青梅竹马》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恐怖分子》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等;《一一》获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新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台湾新电影”当初能够脱颖而出、形成一定的气候,恰恰就是因为新电影初期的一些影片不仅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从而赢得了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支持,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倘若没有较强的观赏性,新电影或许早就胎死腹中了。而新电影后来的式微,正是因为一味地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却忽略了影片的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观赏性和商业性。这一点与“从一开始就认同商业机制,拥抱商业美学”(黄建业语)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大相径庭。当然,我们绝不可以武断地说新电影的导演心中没有观众,前面丁乃竺的一番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问题就在于导演的思想与观众的接受能力能否达到统一、导演想要传达的思想是否过于深刻或是自我。郑洞天在9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电影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来自当前观众层的素质水准。而新电影创作者则看重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以期引导观众通过看电影来思考现实人生,因此对观众就影片的读解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况且,新电影中的部分作品的确因其主题与表现形式而略显晦涩。综合多种因素,新电影走向衰落也是一种必然。
杨德昌的影片数量不多,但是作品本身却留给我们太多值得阐释的东西,他为台湾电影的新格局和新类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的只言片语就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艺术贡献而言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笔者写作期间,欣闻正在进行的釜山电影节将亚洲电影人奖特别颁给了已故去的杨德昌导演,以纪念其为世界电影发展做出的努力。这大概可以看做是亚洲的电影人们对这位真诚而执著的电影思辨者的再次缅怀以及由衷的致敬吧。
注释:
① 焦雄屏《台湾新电影的历史及文化价值》,《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黄式宪《中华影坛双子星座:谢晋和李行》,王海洲主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④ 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⑤ 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标签:杨德昌论文; 台湾论文;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论文; 电影节论文; 独立时代论文; 侯孝贤论文; 麻将论文; 青梅竹马论文; 恐怖分子论文; 新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