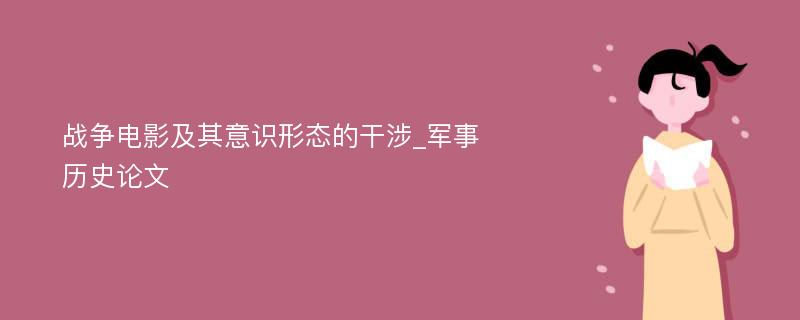
干涉战争电影及其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战争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2)04-0022-09
干涉战争是有关战争的新概念,表现这一战争的影片属于类型电影中的战争片,但却明显不同于一般的战争片,本文试图通过对于这一类影片的分析读解来把握这类影片的特殊之处,并揭示其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什么是干涉战争
一般来说,干涉是指大国、强国对于小国、弱国的武装干涉。在冷战时期,小国的战争一般都有大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子,或者也可以说,许多小国之间的、小国之内的战争就是大国挑起的。不过在冷战结束之后,干涉往往是指大国对于小国国内所发生的种族灭绝或者恐怖主义事件的武装干预,因此也被某些人称为人道主义干涉。按照惠勒的说法:“美国于1992年12月在索马里的干涉行动潜移默化地建立了冷战之后国际社会上一种进行合法化人道主义干涉行为的新标准。这似乎意味着在脱出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禁锢后,西方国家政府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在这里他们将会为了拯救外国人的危难而将士兵们派出到远离故土的地方执行军事任务。”[1]184因此,出于人道和反恐的目的、合法(联合国授权)或不合法地对他国进行武装干预被称为干涉战争。对于冷战之后国际战争的性质,亨廷顿有一个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这是文化差异和地域霸权的争夺所引发的战争。他说:“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2]105这个解释显然比冠冕堂皇的人道主义更为深刻,它揭示出了大国的文化认同并非理性和公正的思考,文化价值观的背后往往潜伏着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在我们看来,人道主义干涉或反恐这样的说法尽管在表述上有一定的新意,但并不能掩盖大国自身的利益往往是干涉的实际出发点这一事实,只不过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抗衡改换成了人道主义这样的在表面上更具普世意味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罢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西方政治家需要这样的宣传来蛊惑民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野心的缘故。尽管不能否认小国中确实有非人道的残酷事件发生,但这并不能在理论上构成他国武装干涉的理由,正如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屠杀和后来在关塔纳摩和阿布格莱布虐囚的非人道不能成为武装干涉美国的理由一样。大国、强国如果能够人道地不将武器出售或“援助”给前南斯拉夫的各民族,那里的种族杀戮也许就不可能发生,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道主义干涉也就没有实行的必要。可见人道主义的说辞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我们还是欢迎这样的表现在电影中出现,因为丑恶现实毕竟在梦幻中受到了抵制和批判。
二、干涉战争电影的特点
干涉战争电影表现的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这些战争大致集中在非洲、中东和巴尔干,这些战争影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无宏大战争场面
所谓干涉战争主要是指大国、强国对那些发生种族屠杀的小国的干涉,这样的干涉战争是一种不对称、不匹配,在实力和装备上都不在一个水准上的战争,有的书上干脆称其为“‘小鸡’对抗‘老鹰’的非对称战争”,[3]因此在干涉战争影片中一般看不到大规模的军队对抗或作战,这与一般表现战争的类型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在干涉战争影片中最多只能看到一方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展示,如美国电影《深入敌后》(Behind Enemy Lines,2001)、《新海豹突击队》(Seal Team VI Journey into Darkness,2009)等,表现了航母和飞机,当飞机从航母上起飞的时候,确实能够看到非常壮观的场面。不过大部分影片所反映的军事对抗都是小规模的,甚至是业余水准的。即便是那些展示了大型武器的影片,如《深入敌后》和《新海豹突击队》,其所表现的战争冲突也是小规模的。尽管在《深入敌后》中有导弹袭击飞机的战斗场面,但影片主要表现的是被击落的美军飞机驾驶员如何在敌后躲避敌人的追杀,最后被营救的故事。《新海豹突击队》表现的是海湾战争中一支为美军轰炸机指示目标的深入敌后的小分队,他们的任务主要不是战斗,而是不让敌人觉察,只是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与敌人交手。至于像《锅盖头》(Jarhead,2005)这样从正面表现海湾战争的影片,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美国军队,但却自始至终没有同敌人照面,更没有战斗的场面。还有像《哈迪塞镇之战》(Battle for Haditha,2007)这样表现伊拉克战争的影片,美军的对手仅是一些安放炸弹的业余反抗者,他们打了就跑,美军找不到还击的目标,结果把平民当成了杀戮的对象。
(二)倒霉的英雄
一般来说,战争电影总少不了要塑造战争英雄,英雄们在战场上展示英雄业绩、克敌制胜,但是在表现干涉战争的战争片中,其英雄人物的塑造总是与各种各样的不幸交织在一起,以致使英雄人物的面貌大打折扣。
比如根据史实拍摄的美国电影《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2),是一部反映美国干涉索马里的战争片。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饥荒,非洲索马里政府倒台,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战乱,其中由艾迪德领导的民兵不但抢劫联合国援救灾民的粮食,还打死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美军决心将艾迪德绳之以法,在得到了艾迪德将在巴卡拉召集高层领导人会议的消息后,美军计划派出精干小分队进行劫持,直升机先将部队运到会议地点,占领建筑物,俘虏人质,然后从地面用装甲军车将人质和部队运走。但是行动在实施中碰到了麻烦,不断有受伤的战士需要营救,营救的直升机先后有两架被击落,又需要营救,如此恶性循环。影片表现了两名特种部队的狙击手自愿前去救援被击落的直升机驾驶员,结果受到了当地民兵的猛烈攻击,尽管他们英勇抵抗,结果却是双双战死。美国2000年拍摄的影片《生死豪情》(Courage under Fire),表现了一位美军上校对一位在伊拉克战死的直升机女驾驶员的调查。这位名叫海伦·华顿的女性上尉,不仅在战场上机智勇敢,用直升机携带的燃油烧毁了敌军的坦克,而且在坠机后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坚决地阻止了部下动摇想要投降或者逃跑的行为,但她自己却被部下开枪打伤。当救援部队到达时,身负重伤的华顿上尉冷静地指挥部下有序撤退,自己则用一支M16步枪掩护,上了直升机的士兵因为害怕被告发,告诉指挥官说华顿上尉已经阵亡,结果直升机飞走了,轰炸机向战场投下了燃烧弹,把那里烧成了一片火海。在美国电影《太阳泪》(Tears of the Sun,2003)中,华尔士中尉接到任务,要从尼日利亚叛军占领的地区接出一位女医生,这位女医生执意要带着她的病人一起上路,结果直升机上坐不下,只能让妇女和孩子先上,剩下的人在丛林中逃生,华尔士发现无法摆脱敌人的追踪,怀疑队伍中有人给追兵发了消息。结果果然查到了,这个间谍居然还得到了其他人的默认和庇护,原来这些非洲难民对前来营救的美国兵毫无信任感,美国人曾经杀死过他们的亲人,华尔士中尉必须面对他所救助的对象完全不顾自身安危却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尴尬。尽管影片的结尾华尔士和他的战士们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这些难民,并最终赢得了他们的感激和信任,但华尔士本人身负重伤,他的部队几近全军覆没。即便是在像《新海豹突击队》这样显然是得到美国军方支持的主旋律电影中,影片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麦菲还是命运不佳,他带领5名战士从海上潜入伊拉克,为美军飞机指示攻击目标,特别是那些生产毒气的工厂,为进攻部队扫清道路。当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伊拉克军队的集结地,并呼叫飞机前来轰炸的时候,一名伊拉克儿童发现了他们,并惊慌呼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麦菲开枪打中了他。尽管极力营救,这名儿童还是死了。小队最后摆脱敌人的追击,回到航母,小队中多人负伤,指挥官麦菲伤重而死。
倒霉的英雄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干涉战争所面对的不是敌我分明的战场,而是极其复杂的情况,干涉的本身有时并不能得到被援助国人民的认可,英雄也不能仅凭勇敢来解决问题。
(三)变态的士兵
士兵在战争中的变态的表现在一些著名的越战片中便已经出现了,如《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这样的影片。在干涉战争电影中,对于士兵变态和疯狂的描写比越战片更进一步,不仅揭示了战争使人疯狂,还从人的本性角度对此加以反思和探讨。
美国在2007年制作的两部影片《第四战队》(The Four Horsemen)和《勇敢者的国度》(Home of the Brave)中,均出现了从伊拉克战场回国之后无法适应环境的士兵群像:他们有的无法与家人相处;有的无法从战友的死亡和自责中解脱,以致铤而走险与警察持枪对峙,最后被打死;有的则选择重回伊拉克战场。这看起来是一种无法解释的行为,在战场上拼死作战,是为了能够活着回家,但回到家中却又要重返战场。在《勇敢者的国度》中给出了当事人的解释,这是影片结尾男主人公重返伊拉克时的画外音:“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无法理解我再次从军,这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知道,但是我必须回来,我和乔丹都不想死,我们第一次到战场时,还不知道面临什么,或许这个国家的领袖也不清楚将走向何方,或许民众不想我们来这儿,或者整件事情是个错误,即使这样,我也不能苟且偷生,别人作战时我却躲在后方,我觉得重返战场与他们并肩作战是个正确的决定。当兵是很不容易的,不仅仅对我们来说很难,对那些我们身后的人来说也不容易,爸爸妈妈,女朋友,孩子,丈夫和老婆,但是我这样做的话,大家就能够快点与家人团聚。我希望你们能够认同,这是我最好的生活方式,这里有我的战友,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不是为什么信念而战,但我感到,如果我不来就对不起乔丹和加马尔,还有那些和我并肩作战牺牲的朋友,对不起他们比回不了家更难受,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这么做,我知道你们爱我。我回来了,回到这里我知道如何做得更好。我会尽快回到你们的身边,请为我祈祷。”从这段冗长的解释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男主人公重返前线的动机是因为在国内有自我认同的障碍,前线能够使他更好地找到自我。但这样的解释毕竟显得牵强,因为他没有说出自我认同障碍是哪些具体的事物,是什么样的自身角色不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认同。关于这一点,《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2008)讲得比较直白,影片的一开始字幕便引用《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赫奇斯的话:“战斗的狂飙突击是一种瘾,强效而致命,因为战争本身是种毒品。”影片主人公詹姆斯是位拆弹员,曾经成功拆除过八百多枚炸弹,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在伊拉克的拆弹战斗中遭遇集群炸弹、电子引爆装置、遥控引爆装置、自杀式人体炸弹、狙击手的袭击,可谓九死一生,终于能够回家。影片的结尾,詹姆斯抛妻别子,重又回到伊拉克战场。战争被描写成了某些美国人的欲望,只不过在许多的场合,这种欲望被抹上了爱国的色彩。
究竟是什么欲望让回国的战士重返战场?仅仅使用上瘾一词显然还是抽象,每一个战士都是战争中具体行为的实施者,他的行为便指称着他们的欲望。一些影片毫不犹豫地展示了战争中人变得残忍而冷血,如英国电影《该隐的记号》(The Mark of Cain,2007)表现了英国士兵集体虐囚的丑闻,这一行为不但有下级军官的参与,而且得到了更高级别指挥官的默许。美国电影《哈迪塞镇之战》则表现了美国士兵因为遭到炸弹的袭击,迁怒于附近的居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杀死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行为还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只是因为美国报刊上公布了这一事件,当事人才受到调查。美国在2007年制作的影片《决战伊拉谷》(In the Valley of Elah)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片,影片表现了一位父亲因为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儿子被人杀死并肢解焚烧而参与了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不仅吸毒,而且经常残忍地戏弄受伤的俘虏,把手指探进伤口然后问疼不疼,并因此而得了一个医生的外号。除此之外,他还曾开车故意撞死过伊拉克小孩,事故发生后,他停车拍照然后扬长而去。而杀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平日与他一起残忍对待他人的战友,起因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口角,杀人对于这些士兵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如同日常的作业一般,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波斯湾阴谋》(Redacted,2008)更是把美国士兵强奸15岁伊拉克少女以及屠杀她们全家的事实作为了影片表现的主题,由此我们看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堕落、扭曲和残忍。
(四)看不到胜利的结局
由于干涉战争本身往往不是一种需要战胜敌人的战争,即便是像伊拉克战争那样需要打败敌人,其主要的战争表现也不在战场上,因为战争的不对称往往使战争很快就打完了,主要的战争是在多国部队占领伊拉克之后,因此表现干涉战争的影片往往没有一个完美的胜利结局。
如前面提到的《黑鹰坠落》,结局是被围困在城市中的美军终于等到了援兵,得以回到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敌人当然是阴谋没有得逞,但是这些敌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勇敢者的国度》、《拆弹部队》这些影片,主人公重又回到了战场,战争似乎没完没了。《深入敌后》、《新海豹突击队》这些影片尽管在结尾处有表现敌人被痛宰的画面,但主要还是主人公逃脱了敌人的追杀,而不是战胜了这些敌人。在有关干涉战争的电影中,有一部名为《绿色地带》(Green Zone,2010)的美国电影值得一提,这部影片试图将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归咎于美国政客的黑幕,从而将影片的结局从战争的胜利扭向了政治的黑暗。
《绿色地带》讲述的是美军在2003年刚刚占领巴格达不久,出动大批部队搜寻伊拉克人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米勒准尉带领的85小队在执行任务中屡屡扑空,情报所说的生物化学武器制造厂竟然是生产厕所洁具的工厂,仓库中鸟粪堆积,已经多年没有人去了。米勒质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他的上司让他不要多嘴。米勒与中情局的一位官员配合,想要通过伊拉克军人来稳定目前伊拉克混乱的局面。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位名叫拉维的伊拉克将军,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米勒:将军,我知道你跟一名美国官员在战前几星期有联络,我知道你准备告诉他们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一切。
拉维:什么计划?……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官员,我们在91年后已拆除了所有东西。
米勒:他跟我们的政府说,你确认那个计划仍在生效,他以你之名捏造事实,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拉维:有人去查证他所说的吗?没有。米勒先生,你们政府想听谎话,他们想萨达姆下台,于是他们就做了他们要做的事。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你有事要跟我说?
米勒:将军,如果你跟我走,华盛顿依然会有人跟你合作,依然有人会明白我们需要伊拉克军队去维持这地方的安宁。
拉维:那你们政府为何要解散我们的军队,使我们成为罪犯?为何要逐步分化伊拉克?为什么?……我冒生命危险告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真相,他们说:“讲出真相,你便可以在新的伊拉克得一席位。”但我现在得到什么,米勒先生,一副牌?
就在米勒劝说拉维投诚的时候,美军的特种部队赶到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死拉维。拉维最后被杀,米勒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向媒体公开。
三、干涉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
由于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被认定为是意识形态之战,干涉战争是冷战之后出现的战争模式,因此干涉战争似乎有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不过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基于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为数不少,只不过“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不在,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2]230这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并非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只是将过去的主义意识改换成了今天的种族或文化意识。这样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意识形态势必反映到电影之中。
(一)干涉非洲
在影片《黑鹰坠落》中,一位中士小队长在谈到黑人的时候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尊敬他们。……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教育和未来。我只是觉得我们有两个选择:帮助他们,或是眼睁睁看着他们自相残杀。……我是来改善世界的。”这是在表述美国人干涉的动机,在经历一场苦战之后,这位中士这样说道:“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那是在我们被派来之前,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去打别人的仗?你自以为是英雄吗?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的答案是:不,我不想当英雄,没有人想当英雄,只是有时候时势造英雄。”这就认定了美国人在索马里是救人的英雄。不过,影片毕竟是在2002年拍摄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美国人自命为救人出苦海的英雄,但并没有得到被救援者的认同。惠勒指出,美军在索马里试图抓捕艾迪德的做法缺乏文化敏感度,“因为在索马里的传统习惯里,他们对杀戮者采取严厉手段,并且赋予集体处理此事的最大优先权。这种缺乏文化敏感度的进一步的例子就是,在索马里社会里对人最严重的侮辱行为是给别人看你的鞋子。当美国直升机在摩加迪沙进行低空侦察飞行及打击行动时,索马里人能看到飞机上脸往下看的美国士兵们的靴子,这让索马里人不可能对美国产生好的印象”。[1]222美国人在非洲其实是在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我们看到影片中被美军杀死的非洲人都被处理成凶残的暴徒,他们似乎毫无理由地攻击美国士兵,文化的隔阂使美国人只能创作出或接受这样的非洲人的形象。
在另外一部名为《烈血的规条》(Rules of Engagement,2000)的美国影片中,一名美军上校在也门美国大使馆执行任务时,因为部下有三人伤亡,他下令向使馆外抗议的人群开枪,结果包括妇孺在内共打死83人,打伤一百多人,被以妨碍和平、行为不当和谋杀三条罪状告上法庭,最后仅被认定妨碍和平,另外两条罪名不能成立。影片中的也门人同样被表现得富有攻击性,而且,在美国人看来,只要美国人受到了伤害,不论多少加之于对方的伤害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二)干涉伊拉克
有关干涉伊拉克的战争电影,我们前面提到了《新海豹突击队》,在这部电影中,美军指挥官麦菲为了完成任务不得已射击了一个儿童。这其实可以看成是整个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隐喻。在这些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高科技武器,对伊拉克狂轰滥炸,伤及了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包括我国的大使馆),德里达认为“其残暴程度不亚于人们所说的‘9·11’事件”。[4]在电影中,西方军队这样的行为被集中在了美军小分队指挥官麦菲的身上,为了使美军的形象显得完美,影片特别把麦菲的家庭作为了表现的内容,在麦菲上战场之前,儿子刚刚因为车祸死亡,他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因此射击儿童对于他来说尤其困难,但是为了“大义”,他还是做了。用海豹突击队一位战士的话来说:“这是抉择,士官长说,意义很简单,一个小男孩的鲜血能换来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性命,一个人的死可让其他人活下去,这只是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没有名字,没有墓碑,没有纪念。”这样的说法看起来似乎能够解释战争中伤及无辜的问题,并且使这样的伤亡具有了积极的、肯定的价值。但是,这样的说法似乎早有耳闻,在1969年制作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影片《雷玛根大桥》(The Bridge at Remagen)中,当一位司令官命令士兵冲上布满炸药的大桥时,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逻辑推理,他对下级军官说:“这是战略,少校,占领那座桥将可缩短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一百人,但可拯救一万人,甚至五万人,这是改变历史的大好机会。所以少校,你必须马上令部下行动,现在,少校!”这部影片在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那些近乎去送死的一百个美国士兵来说,战争又意味着什么?显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将军的正义是一种相对于个人外部的规定性,这种正义如果不是士兵自愿的选择,那么就毫无价值,正如巴恩斯所指出的:“不管社会是多么的自由和开明,总会有一些罪恶的残余。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人总是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而生活的。然而,这里并不存在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人类进行加减乘除的算术。”[5]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用少数人的牺牲来置换多数人幸福的计算方法,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是不容剥夺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对待人的生命不能使用简单的算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他来说就是其全部,只有不尊重生命的人才会进行如此冷漠的算计。因此,在表现伊拉克战争的电影中使用这种陈旧的伦理观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漠视他人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人的价值相对于美军的胜利来说更为低下。
(三)干涉科索沃
众所周知,前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在西方的极力支持下完成的,德国首先支持了克罗地亚的独立,然后所有西方国家紧随其后,因此,在前南斯拉夫,执政的塞尔维亚人成为了西方的众矢之的。
在一部法国拍摄的影片《危机密布》(Harrison’s Flowers,2000)中,通过一群摄影记者在前南地区的所见所闻,把塞尔维亚的军队描写成了屠杀妇女、儿童和无辜平民的恶魔,由于是通过影片中人物的感受和见闻来表现,尽管没有对战争进行正面的描写,却更具有艺术的真实感。影片回避了西方国家(包括法国)对于克罗地亚独立的支持,只是通过剧中人物突兀地告诉观众,“1991年11月18日,世界又恢复了宁静”。这个时间正是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并开始大量获得西方援助的时间。事实上,世界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宁静,“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数十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2]259我们看到,这部拍摄于2000年的影片,对于西方世界为克罗地亚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对其实施“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不置一词,保持了与其所在国家一致的立场和完全谈不上公正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美国电影《深入敌后》也是如此,影片的故事以塞尔维亚军队追杀美国飞行员为主线,之所以要追杀他,是因为他在侦察飞行中拍下了塞尔维亚军队屠杀平民的证据。影片中的塞尔维亚人被表现得极端丑恶,不但雇佣监狱中的罪犯进行杀人的勾当,而且还对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普通百姓进行血腥的屠杀。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当时西方媒体对科索沃报道具有严重的倾向性,这样一种倾向性的由来完全是因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信奉伊斯兰教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则得到了伊斯兰教世界各国以及西方各国的支持。在我看来,北约东扩的野心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偏执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塞尔维亚人形象在西方电影中的改变得益于2004年3月科索沃地区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当时的科索沃已经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骚乱导致近千人死伤,该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到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攻击,维和部队和警察也遭到了攻击,150辆国际组织的车辆被毁,120人受伤,[6]这使西方人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似乎是为了维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而来到巴尔干的,或者说是他们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救出了塞尔维亚人的统治,没料到却遭到了如此恩将仇报的对待。从此之后,西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不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变成了恶魔。如意大利拍摄的影片《塞尔维亚维和军》(Radio West fm.97,2004),不但表现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暴民烧毁塞尔维亚人的住房,还塑造了一名说塞尔维亚语的少女,她被强奸后被迫留在阿尔巴尼亚人的家中,以致她不择手段地要跟随意大利士兵离开。为了迫使她留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甚至用杀死她的孩子相威胁,最后是意大利士兵杀死了那个邪恶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英勇地从枪林弹雨中救出了婴儿。利用儿童来做文章具有明显的宣传意味,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杀婴的形象,很容易使人想起海湾战争前夕美国媒体宣传的伊拉克人丢弃科威特医院中婴儿任其死亡的故事(事后证明这只是杜撰)。[7]在德国电影《触摸和平》(Snipers Valley,2007)中,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同样是魔鬼的化身,他们不仅以曾与纳粹军队并肩作战为荣,甚至还煽动民族仇恨,教唆青少年狙击塞尔维亚人。在这部影片中,塞尔维亚人被描写成既是受害者,也是曾经的杀人者。影片表现出了一种对种族仇恨无法释怀的悲观,似乎只有在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仇恨的种子才能被逐渐消解。
对于类型电影中战争片的研究,干涉战争电影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除了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电影的类型元素——暴力上之外,更要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电影中战争暴力的含义有所变更,它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刺激,同时还包含了大量政治文化的潜在话语,影片中所呈现的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平理想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不着边际。因此,对于干涉战争电影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史实的考察,离不开对潜在政治或文化话语的揭示,否则便会堕入权力话语的陷阱,不知不觉地丧失中立的、相对客观的立场。相对于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来说,干涉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意味要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正义的概念在现实的干涉战争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往往难以被人们认同。但是,在电影中正义却是一定要被完整建构的,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会不遗余力地标榜这一立场的正义性。比如德国人拍摄的影片《触摸和平》,表现的似乎是德国维和部队在维护科索沃的和平,年轻的德国士兵秉持着正义的理念竭力抚平那里的民族仇恨和阻止血仇报复,但实际情况却是,因为德国带头支持了前南斯拉夫的分裂,所以引发了那里一系列的战争和民族仇恨。倘不触及外国势力干涉这个大前提,没有国际化介入这个语境,人们会把影片中的科索沃各民族人民看成是好战的非理性之徒,而把德国人看成是天使,而电影的表述恰恰是忽略国家政治立场这一前提的。因此,对于干涉战争电影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对于影片文本的讨论之中,一定需要揭示出战争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背景,尽管电影研究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少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使电影观众有可能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人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