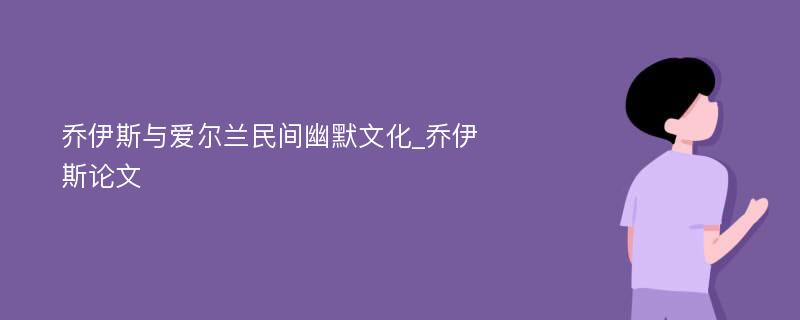
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诙谐论文,民间论文,文化论文,乔伊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2年,乔伊斯见到了叶芝,尽管当时的叶芝还没有写出他后期那些传世的诗歌,但早已有了显赫的诗名。为了慑服态度倨傲的乔伊斯,叶芝拿出了自己当时最新也是最得意的理论——他后来成为世界大师,与这一理论是分不开的——即民间文学比艺术家们以前追求的纯美的文学更有生命力。叶芝对乔伊斯说:“艺术家,当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以那些与他一样精雕细琢的艺术家为榜样后,就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他变得极其个性化,同时也在追求彻底完美的过程中,最终变得贫瘠。相反,民间想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没有观念的形象。民间故事无视道德法则和日常法规,它们是一系列的图片,就像孩子们在火中看到的那些图案一样。你注意这两种创造,艺术家的创造和民间创造,前者源自城市文明,后者存在于乡村生活的形式之中。……民间生活和乡村生活属于自然,丰饶多产;艺术生活和城市生活则属于精神,如果不与自然结合,就会变得贫瘠不育。 ”(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03.)如果是十几年后,这段话应该能够打动乔伊斯,但那时乔伊斯信奉的是易卜生反群氓的思想,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愚昧冲动、没有主见的“乌合之众”,在一年前自费出版的文章《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第一句话就声称,“如果不厌恶大众,一个人就不可能热爱真理或善;艺术家虽然可以利用民众,却与民众保持距离。”(注:Richard Ellmann,James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9.)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称爱尔兰为欧洲最落后的民族,“落后”一词他用的是“belated”, 这个词直译是“来得太迟的”。如果把城市比作现代文明的门槛的话,乡村正是一种“来得太迟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被乔伊斯称为乌合之众的爱尔兰民族,倒正是叶芝所提倡的民间生活的体现。
一
爱尔兰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的民族,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文化。与英国相比,爱尔兰的中古文化发展得更早,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宗教德鲁伊教,出现了爱尔兰世俗文化的传承者“菲利”诗人——主要担负传播民间口头文学的责任。此外像由“康城十字架”代表的黄金和青铜工艺,由卡舍耳的科马克教堂和克朗弗特残留的废寺门廊代表的建筑风格,以及至今伫立在土阿姆和莫纳斯特博伊斯的石头十字架等,都显示着爱尔兰当时突出的文化成就。
但由于从11世纪起英格兰人就开始了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对爱尔兰文化实行殖民压制,用英格兰文化取代爱尔兰文化,因此使处于幼年时期的爱尔兰文化后来的发展举步维艰,“几百年来都被判处了死刑”(注:Don L.F.Nilsen,Humor in Irish Literature:A Reference Guide,London:Greenwood Press,1996,p.3.)。就爱尔兰自己的民族文化来说,在20世纪爱尔兰文化复兴之前,它一直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化阶段,换句话说,爱尔兰不仅民间传说和民间歌谣到20世纪初仍然传唱不衰,是爱尔兰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而且爱尔兰的民间故事表现出很强的说、唱、听的特征,此外,爱尔兰一直存在着传播民间故事的社会群体和“深厚的口头、民间传统”(注:Thomas Bartlett,ed.,Irish Studies:A General Introduction,Dublin: Gill andMacmillan,1988,p.89.),这保证了爱尔兰民间文化的繁荣,并使口头文学这种古老的传播方式和创作方式在爱尔兰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爱尔兰民间口头文学最活跃的地方是在爱尔兰的酒吧,“爱尔兰的酒吧闲谈和书面创作产生了异常众多的‘说故事人’, ……爱尔兰书面文学中的故事与在酒吧中创作和讲述的故事有着相同的叙述结构。”(注:Don L.F. Nilsen, Humor in Irish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London:Greenwood Press,1996,p.3.)酒吧在爱尔兰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都柏林的酒吧更是都柏林男性聚会的主要场所,都柏林人在饮酒时的饶舌善辩、口若悬河也是有名的,这在许多都柏林游记中都有反映。爱尔兰人酒吧饶舌的主要内容,除了像其它国家的酒吧那样传播各种传说逸闻外,最具特色的是充满爱尔兰民间智慧的笑话、幽默和文字游戏,“没有什么庄重的东西不能用来打趣,没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能用来嘲讽……娱乐和政治、美酒和女人、欠债和决斗都成为玩笑的内容,而且没有任何避讳,却又包含着对世界的晓悟和对人心的洞察。”(注:Thomas and Valerie Pakenham, Dublin:A Traveler's Companion,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1988,p.320.)在这样的场合中,“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年龄或尊严, 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职位太高或身份显赫而不加入这场狂欢的热潮。”(注:Thomas and Valerie Pakenham,Dublin:A Traveler's Companion,London:Constable & Company Ltd.,1988,p.320.)这段引文描述的虽然是爱尔兰总督府的一次晚宴,但我们把它与《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描写的都柏林医科大学生的聚会及都柏林酒吧的聚饮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们都有着都柏林酒吧特有的狂欢气氛——一种不分你我、充满了粗俗谐噱的群体宴乐。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就是一个酒吧娱乐的高手,说学逗唱无一不通,在都柏林小有名气,当然,他也是一个有名的酒鬼。在青年乔伊斯的心目中,约翰·乔伊斯那种“纵酒、挥霍、饶舌、唱歌”的生活方式成了都柏林男性社会生活的代表。乔伊斯曾经称“《尤利西斯》中的幽默是他的幽默,书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部书就是他的写照”(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2.), 乔伊斯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由约翰·乔伊斯所体现的都柏林酒吧文化。
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巴赫金提出了“民间诙谐文化”这个概念,并以此来描述拉伯雷作品中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狂欢节文化”。巴赫金在书中详细研究了这种民间诙谐文化,发现它的狂欢和诙谐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娱乐,它也是一种深刻的世界观,是一种和形而上的或“严肃积极”、或禁欲主义、或个人英雄的世界观相对的人生模式,它“同一切自我隔离和自我封闭相对立,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立,同一切与世隔绝和无视大地和身体的重要性的自命不凡相对立”(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李兆林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民间诙谐文化首先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全民文化。在狂欢节的世界里,人的一切等级界限(无论是政治的、血统的、道德的还是精神的、物质的)都消失了,人只作为不分你我的社会群体的一个分子而存在,个体消融在群体之中,仅从群体的价值和生命中获得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此外,民间诙谐文化还突出地表现出世俗的和肉体的特点,筵席和肉体在这一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在民间诙谐文化中得到大量表现,而且一改在正统文化中受贬斥的地位,成为民间诙谐文化的主要内容。民间诙谐文化完全立足于大地、立足于物质现实,它不是无望地追求超越和永恒,而是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变化运动中,从人类整体生生不息的繁衍更迭中获得无尽的生命力。巴赫金认为,正统文化和严肃文化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古板沉闷、贫乏僵化、自以为是,它们“看不到自身的开端、局限与终点,看不到自己那副衰老滑稽的尊容,看不到自己对永恒和不朽的妄想所具有的喜剧性”(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与它们不同, 民间诙谐文化从开放的、未完成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和世界,从交替与更新的角度来看待存在与死亡。这一文化以诙谐为主要特征,因为“诙谐不会创造教条,不可能变为专横;诙谐标志着的不是恐惧,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诙谐与生育行为、诞生、更新、丰收、盈余、吃喝等人民世俗的不朽相联系;最后,诙谐还与未来、与新的将来相联系,并为它扫清道路。”(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民间诙谐文化废黜一切又更新一切, 在本质上是“人民对其集体历史不朽性的生动感受”(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巴赫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民间诙谐文化即狂欢文化所具有的积极价值,而这个文化一千年来却一直遭到排斥。如果说在希腊奥林匹斯众神的欢宴中还有它的影子,那么当基督教文化取得统治地位后,这种文化就被与粗俗堕落划上了等号,被赶出正统道德严肃的历史舞台,只在民间笑话中还可以听到这个文化微弱的声音。爱尔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由于它“落后”(belated)的特点,却使得这种不分等级、 开一切崇高的玩笑、诙谐戏噱的民间文化在爱尔兰酒吧和欢宴中保存下来,成为爱尔兰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在基督教文化的权威话语之下,这种文化在爱尔兰也常常蒙上低贱堕落的色彩,但它强大的生命力却不断吸引着叶芝等优秀的爱尔兰诗人回到它肥沃的民间土壤中来。乔伊斯后期作品较前期表现出更持久和博大的生命力,与他后期作品中包含的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成分密不可分。
二
正如乔伊斯与叶芝的见面所表明的,乔伊斯在创作初期对民间文化、社会群体文化持鄙视态度,把民众称为乌合之众。乔伊斯早年的这种态度除了受当时欧洲兴起的易卜生、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影响及欧洲传统文化中精英思想的影响外,乔伊斯的父亲也起了直接的反面作用。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应该说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颇具口才和表演才能,是常常出现于都柏林酒吧聚饮中的明星。问题是,约翰·乔伊斯后来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生活都消耗在了都柏林酒吧中,为此当尽了家产,也毁了自己的前途,几个孩子不得不像《尤利西斯》中描写的那样到处找饭吃。这样的家庭经历无疑使年轻的乔伊斯对父亲和那种由他父亲体现的都柏林酒吧生活充满了反感。在大学时写的一个断片中,乔伊斯曾这样描写都柏林人,“都柏林人是我在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遇到过的最没有希望、最无用、最善变的无赖民族。难怪英国议会充斥着世界上最啰嗦唠叨的人。都柏林人把时间都花在酒吧、酒馆或妓院的空谈和聚饮上,却从未因双倍的威士忌和自治权而‘发胖’。”(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17.)据艾尔曼记载,有一次约翰·乔伊斯又喝醉酒回来,乔伊斯痛打了父亲,差点让他丧命。
出于对都柏林人空谈和酗酒行为的反感,乔伊斯一直把自己想像为一个卓尔不群的超人,一个超越爱尔兰社会迷宫振翅高飞的天才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的肯定构成了乔伊斯早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都柏林人》中,他对都柏林人的生活和精神都做了一次诊疗式的冷静解剖。在乔伊斯的笔下,都柏林灰暗窒息的画面完全是都柏林人精神“瘫痪”的必然结果。整部《都柏林人》展示了都柏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一丝亮色。
与《都柏林人》在叙述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乔伊斯那时创作的一部没有发表的小说《英雄斯蒂芬》,用一位乔伊斯研究者的话说,乔伊斯“在《英雄斯蒂芬》中把自己塑造得近乎于偶像”(注:Sudney Bolt,A Preface to James Joyce,New York:Longman Inc,1981,p.15.)。《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英雄斯蒂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它淡化了原小说主人公斯蒂芬的“英雄”色彩,不过,即便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也是以闷铁屋中惟一的清醒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小说中,只有斯蒂芬一个人在对爱尔兰传统的宗教、政治、道德乃至艺术观念进行反思,也只有他一个人说得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不少评论者认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乔伊斯作品中构造得最好的一部。的确,就该书的结构与叙述的和谐精致来说,这部小说确实可以为乔伊斯赢得艺术家的称号。但是,与《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却稍显单薄,可以说,如果没有《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社会广度和生命厚度,乔伊斯今天只能与柯林斯、威尔斯这些人并驾齐驱,不可能产生现在这样大的影响。《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缺陷正是叶芝所说的纯艺术不可避免的贫瘠不育的缺陷,斯蒂芬·迪达勒斯这个艺术形象的弱点,也正是巴赫金描述的那种自我隔离、自我封闭、自命不凡的禁欲主义者必然带有的古板沉闷、贫瘠僵化的弱点。总之,乔伊斯早期的作品缺少后期作品那种丰富旺盛的生命力。
乔伊斯后来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尤利西斯》中放弃了继续以斯蒂芬·迪达勒斯为主人公的设想,他对朋友弗兰克·巴金抱怨说,“斯蒂芬的形象缺少变化性。”(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59.)与斯蒂芬相比, 布卢姆这个人物则更有包容性,性格也更丰富,用一个评论家的话说,“布卢姆的‘一切主义’与斯蒂芬的‘虚无’的呼喊正成对照。”(注:Richard Brown,James Joyc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89.)《尤利西斯》的“刻尔吉”一章很典型地说明了布卢姆形象的多变性和丰富性:他既可以像皇帝、主教、市长一样高贵尊严,也可以像奴隶、妓女、男宠一样任人凌辱;他可以是宣传社会革新思想的工人演说家,也可以是被判处绞刑的犹大;作为丈夫,他既能伺候自己妻子的情夫,也能与其他女人调情;作为男人,他既可以成为女性膜拜的对象,也可以被女性鞭打;他像唐璜那样寻花问柳,同时却是一个阳痿的废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能够死去也能够新生,他曾是老者也变成过婴儿。在西方文学史上,很少有其他艺术形象像布卢姆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和可变性,也没有哪个形象可以经历如此大的跨越而不四分五裂。“刻尔吉”一章写的虽然只是布卢姆的幻觉,但是并不让人感到突兀生硬,因为布卢姆白天表现出来的“随着环境而变换自我的能力”(注:James H.Maddox,Joyce's Ulysses and the Assault
upon Characte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 p.41.)已经为这一黑夜狂想曲做了铺垫。可以想像,如果这一情节发生在斯蒂芬身上,则必然会因为形象的不和谐而导致失败。
布卢姆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形象的现实感和社会性,来源于他立足于浑浊但也丰富的物质现实这一特征。布卢姆不像斯蒂芬那样在人群中高举自己的理想,排斥一切不属于理想的东西。布卢姆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基督式的同情与爱,他能敏锐地洞察人性的一切,同时也能对一切抱有同情。他并不昏昧。他能够看出市民们的狭隘和医科大学生们的轻浮,在小说中除了莫利根之外也只有他一个人能与斯蒂芬对话,也只有他有勇气对“市民”的专横予以回击。不过,布卢姆虽然了解人性的种种弱点,却并不像斯蒂芬那样对其他人表示蔑视,在小说中他最常出现的反应是内心中发出基督式的叹息。是爱使他能够尊重女性和弱者,也是爱使他可以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上去理解一切,接受一切。如果说斯蒂芬的主要特征是超越生活,那么布卢姆的特征就是对生活敞开大门。与斯蒂芬所显示的人的自我相对,布卢姆显示的正是人的社会性一面。斯蒂芬的理想形象是造出翅膀、飞上天空的希腊工匠迪达勒斯,而布卢姆的最高理想则是成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布卢姆虽然还多少保留着马群中的黑马、羊群中的山羊的特点,但与斯蒂芬相比,他无疑代表着都柏林的社会生活。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刻尔吉”一章的狂想中,布卢姆的形象都是和其他人、和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乔伊斯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比《尤利西斯》更进了一步,彻底摆脱了斯蒂芬的个人主义,主人公叶尔委克完全融入了群体之中。叶尔委克的简写是HCE, 这个词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断出现,按照乔伊斯的解释,HCE(Here Comes Everybody )即“人人如此”,意味着主人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人(everybody), 总是看上去类似和等于他自己, 并且特别符合任何和所有这样的世界普遍性(universalisation)。”(注:James Joyce,Finnegans Wake,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p.32.)HCE这一“人人”形象表明乔伊斯最终接受了人的社会性,把自我看作人类群体中的一个分子。这一点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主题上也突出地体现出来,正如乔伊斯的研究者们公认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像其它小说那样写一个人或几个人,也不是塑造某个社会集团的“群像”,而是从哲理高度阐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小说中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抽象的,都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乔伊斯后期从斯蒂芬的个人主义向HCE 的群体生命的这个转变过程,用歌德的概念说是一次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在本质上与浮士德从私人书斋走向群众集体劳动是一致的,都是艺术家从纯艺术的世界向民间文化的回归。
有趣的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选择了都柏林一个酒馆老板来做自己的“人人”,用他一家五口的关系来概括人类生活,用他酒馆的景象和酒客来代表人类社会。很显然,乔伊斯的这个选择来自他对都柏林生活的理解。在他的心目中,都柏林酒馆的聚饮狂欢代表着爱尔兰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民众文化。
乔伊斯后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乔伊斯自己性格中遗传自父亲的喜剧成分外,婚后的家庭生活和流亡欧洲大陆的经历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早年,乔伊斯虽然在青年人确立自我的欲望驱使下表现得孤傲不群,但他的性格中一直隐含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喜剧性或者说丑角的一面,并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来,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提到的斯蒂芬模仿酸气十足的校长的才能,不过是乔伊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表演才能极小的一部分,直到成年,乔伊斯还会跳一种四肢着地的“蜘蛛舞”来娱乐宾朋,《尤利西斯》中就曾谈到斯蒂芬一次表演时把腰给扭了。据雅各斯·麦坎顿回忆,乔伊斯曾自称为“爱尔兰小丑”(注:Elliott B. Gose,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Joyce's Ulysses,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p.116.)。在青年时代,乔伊斯用孤傲高深把性格中的这一喜剧因素遮盖了起来。
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诺拉把乔伊斯从早期纯粹的理念和艺术世界带回到日常生活现实,不仅使他通过成为丈夫而接触到家庭和社会现实生活,而且使乔伊斯获得了自信心,从而有勇气展示自己性格中喜剧的那一面。在书信和作品中,乔伊斯总是把诺拉和那些有妻子身份的女性比作大地,认为她们有着大地所具有的深厚、包容和永恒这些特征。这些女性给了她们的丈夫力量和坚韧。乔伊斯把《尤利西斯》定在他和诺拉相识的一天不是没有含义的,这一天诺拉使乔伊斯找到了立足的大地,正像斯蒂芬找到了布卢姆这个父亲。
诺拉使乔伊斯获得现实感,流亡欧洲的生活则使乔伊斯重新审视和评价爱尔兰文化,特别是发现爱尔兰民间文化中积极的那一面。许多年后乔伊斯写道:“有时想到爱尔兰,发现我过去似乎过于苛刻了。(至少在《都柏林人》中)我没有反映出这个城市具有的魅力,自从离开爱尔兰后,除了巴黎,我在其它任何城市都没感受到在都柏林时的那种自在。我没能反映出它的纯朴的狭隘和热情。后一种‘美德’我至今没在欧洲其它地方发现过。我从没公正地对待过它的美,在我的心目中它比我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或意大利所看到的都更具有自然的美。”(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Press,p.231.)乔伊斯离开了爱尔兰,反而更加亲近爱尔兰文化。他后来不仅接受了他父亲那种酒吧生活,声称没有比这样的生活更好的了,而且开始对爱尔兰的诙谐文化发生了兴趣,“一些人在我的住处呆到深夜,谈论爱尔兰的智慧和幽默”(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34.),他们谈得如此之多,以至有一天对乔伊斯的创作从来不感兴趣的诺拉也向乔伊斯要关于爱尔兰智慧和幽默的书看。当然,乔伊斯对爱尔兰诙谐文化的最高礼赞莫过于他在作品中表现爱尔兰的酒吧狂欢,特别是表现出了这种文化的现实魅力,同时,反过来,爱尔兰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赋予了乔伊斯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浑厚感和生命力。
三
爱尔兰的民间诙谐文化除了改变了乔伊斯作品的价值取向,使他从早期的超人价值转向后期的群体价值外,随着作品重心的转变,乔伊斯后期作品的题材、结构和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相比,乔伊斯的后期作品越来越显得“什么也没说”(注:Robert H.Deming,ed.,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Vol.1,London:Routledge 1997,p.22.),越来越缺少黑格尔认为一部作品应有的绝对理念,但同时,他的作品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现实感和生命力,在形式上也越来越复杂多变。
(保加利亚裔)法国女学者克里斯特娃曾经谈到乔伊斯后期作品中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特征,她把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列为典型的“多声部小说”,认为正是这一语言特征赋予了《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不断延展的生命力(注:Alan Roughley,Joyce and
Cr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Press,1978,pp.67-73.)。不过她主要是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来分析乔伊斯作品的结构、叙述这些形式方面的问题的。笔者同意克里斯特娃的观点,不过同时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民间诙谐文化因素远远超出了形式的范围。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斯蒂芬的自我的人与布卢姆的社会的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他们的存在方式直接对应的斯蒂芬的封闭性、排他性和布卢姆的开放性、包容性,而开放性是布卢姆的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独眼巨人”一章中,布卢姆与“市民”的冲突表面看是布卢姆的犹太身份导致的,但从这一章的“市民”叙述模式与布卢姆本人的思维模式看,两个人的叙述/思维模式其实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上,一个是“市民”的狭隘专制的爱尔兰民族沙文主义文化,一个是开放兼容的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两人真正的冲突是文本叙述层面中封闭的文化与开放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一章中布卢姆的胜利也不是简单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开放的价值观念的胜利。罗伯特·舒勒认为,这种价值观念“把我们逐步引导到一种不同于早期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对人的认识之中”(注:Alan Roughley, Joyce and Cr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Press,1978, pp.16.)。
与早期小说相比,乔伊斯的后期小说容纳了许多乔伊斯过去曾排斥的东西,特别是属于现实的物质—肉体层面的东西,这一点在作品使用的语言上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早在《都柏林人》阶段,《都柏林人》就曾经因为书中的“污言秽语”在出版时数次碰壁,不过乔伊斯对此的辩解是这些“污言秽语”是爱尔兰社会本身就有的,如果把这些话删去就会影响爱尔兰人看到自己的丑陋。显然,乔伊斯说这话的时候,对这些“污言秽语”持批判态度,是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来揭示现实的“丑陋”。与后来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都柏林人》的语言其实可以说“干净”得很,乔伊斯后期的作品不仅大量使用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粪便”(注:James Joyce,Finnegans Wake,New York:the Viking Press,p.483.)的语言,而且随着“粪便语言”的增多,乔伊斯在使用这些粪便语言时所持的否定态度也逐渐减少,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已明确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粪便学研究。“刻尔吉”和“潘奈洛佩”两章的语言应该说是《尤利西斯》中最污秽的,然而这两章带给读者的却不是《都柏林人》式的压抑沉闷,反而有着一种狂欢式的放纵和宣泄。
与“粪便”语言相应的是人物形象的物质化、肉体化和肉欲化。《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禁欲和思辩。他曾经被性诱惑过一次,但这次经历反而使他走上了极端的禁欲主义。他“不抽烟,不到市场上去,也从不和女孩子打情骂俏,他从不干这类事,或者说,他妈的什么也不干”。(注: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安知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斯蒂芬“艺术家”式地终日沉浸在纯粹的审美体验之中,他的思想里只有存在、美这些理念化的东西。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的这一特征继续发展,“普洛冬”和“斯鸠利和卡吕布狄”两章体现了斯蒂芬抽象思辩的高峰。詹姆斯·马多克斯认为,正是斯蒂芬这种“排他的书卷气”造成了斯蒂芬这一形象的缺陷,他指出,斯蒂芬的头脑中只有“关于经验的抽象概念,而没有经验本身”(注:James H.Maddox, Joyce's Ulysses and the Assault upon Charact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p.5.)。
布卢姆则正相反,他一大早就美美地吃了一副猪腰子,还洗了一个在当时都柏林人的生活中仍属奢侈的热水澡(值得注意的是,斯蒂芬以几个月不洗澡而著称,并且他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在这一天中,布卢姆除了猪腰子外,还吃下了一客奶酷三明治、一份肝和熏猪肉、一块巧克力、一份咖啡和面包,本来他还买了一只猪爪和一只羊蹄准备晚上享受的,后来扔给了一只不肯离开的狗。他的饮食趣味也绝对谈不上高雅,用小说里的话说,“他吃起下水、有嚼头的胗和炸雌鳕卵来真是津津有味”。至于性,布卢姆与玛莎的书信、与格蒂的意淫、戴绿帽子的隐痛、乃至为自己的妻子与斯蒂芬牵线搭桥,性的母题贯穿于布卢姆一天的活动,“刻尔吉”一章的半夜狂想曲更是充满了性受虐者的欲念。《尤利西斯》全书是在莫莉的性的随想中结束的,这个结尾被认为是“对人体、 对人、 对婚爱和性爱的赞美诗”(注: RichardBrown,James Joyc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95.)。 其后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整部书都是围绕着弗洛伊德式的性欲展开的,人类的历史被从正面阐释为欲的纠葛,甚至对乱伦的的道德批判也减弱了。乔伊斯在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从饮食到性这些肉欲的坦率明朗的态度与拉伯雷在《巨人传》中的态度相当接近,都是民间诙谐文化特有的“物质—肉体下部语言”,在那里,“生育着、吞食着、排泄着的肉体同大自然、同宇宙现象汇合成了一体”。(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4页。 )巴赫金认为,通过这种汇合,人类文化摆脱了严肃文化的有限性和死亡意象,获得了另一种快乐地、自由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其次,在作品的社会广度上,尤其在生活细节的丰满上,乔伊斯的后期作品也有了巨大发展。《尤利西斯》被一些评论者称为史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部作品具有“人间喜剧”式的社会丰富性。《尤利西斯》虽然以两个主人公斯蒂芬和布卢姆的意识活动为主线,但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不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叙述视角主要聚焦在斯蒂芬身上,其他人物起的是背景作用,他们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主人公斯蒂芬的精神发展起了说明或辅助的作用,至于那些与斯蒂芬的精神历程无关的生活琐事则完全被摈弃在作品画面之外。相反,《尤利西斯》的叙述者经常跳出两个主人公的范围,表现社会其他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从第七章“埃奥洛”开始,小说的叙述重心就很少集中在斯蒂芬和布卢姆身上,比如在“太阳神的牛”中,斯蒂芬和布卢姆只是作为医科大学生聚饮团体中的一员出现,其他医科大学生的分量不下于他们两人。“游岩”一章的19个片段中,斯蒂芬和布卢姆总共只占了分量不大的三个片段,而且既不在开头也不在结尾,这一章的表现对象并不是他们两人,而是整个都柏林社会群体。在《尤利西斯》中,作为背景的人物走到了舞台中央,与传统主人公式的人物一起,不分等级、不分轻重的共同表演。群体取代了主人公/英雄,普天同庆的狂欢取代了主人公的孤芳自赏。
由于从社会的层面来理解人,关注人类社会的现实物质生活,乔伊斯的后期作品获得了与前期作品不同的历史观和生命观,那就是《芬尼根的守灵夜》所表现的循环的观念。循环的观念直接影响了乔伊斯后期作品的结构模式。从人物的运动轨迹和小说的结构看,斯蒂芬的世界是直线性的,像哥特教堂一样指向上方,而布卢姆和芬尼根的世界则是循环的,像河流一样运转不息。斯蒂芬的迪达勒斯这个姓表明了斯蒂芬与希腊工匠迪达勒斯之间的联系。像迪达勒斯制造了翅膀飞出迷宫一样,斯蒂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追求就是向上飞跃出迷宫一样的社会。斯蒂芬对形而上的思辩和理念世界的沉迷,也正是他用精神的翅膀对物质社会所做的一次迪达勒斯式的向上飞跃。但是乔伊斯知道,迪达勒斯的神话中也包含着伊卡洛斯坠入大海的悲剧,人虽然渴望最大限度地向上超越,但人的本质决定了这种希望的虚幻性。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有一个与伊卡洛斯的故事相对应的片段,那就是斯蒂芬在交给老师的作业中思考人能否通过不断升华而最终接近上帝,在那时,乔伊斯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让斯蒂芬说,人作为人“没有可能愈来愈接近”(注: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安知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直线向上的观念与人的物质存在发生矛盾,其结果就是斯蒂芬在《尤利西斯》中陷入虚无主义的迷惘之中,非但不能向上,反而丧失了发展的可能。
《尤利西斯》虽然不像《芬尼根的守灵夜》那样明确地建立在循环的历史观之上,但从活动轨迹来说,布卢姆的运动却是循环的。他像斯蒂芬一样早晨从往处出发,由于某个人侵者而不得不到处流浪,但到小说的结尾,他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第17章中的一段话点明了布卢姆的循环性和再生性,“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依稀听见了召唤他回去的声音。于是,就有点儿不大情愿地、在恒星的强制下服从了。……不知怎么一来,他再生了,并重新出现在仙后星座的‘德尔塔’上空。在无限世纪的漫游之后,成为一个从异邦返回的复仇者、秉公惩戒歹徒者、怀着阴暗心情的十字军战士、醒了的沉睡者。”与斯蒂芬不同,布卢姆的价值是“入世”的,他的思绪总是从周围的具体现实出发,最终回到现实中。由于可以无限地循环,布卢姆便具有了巨大的可变性,他可以在“刻尔吉”中经历荣誉的巅峰,也可以经历耻辱的深谷,他可以成为女性,也可以变成襁褓中的孩童,而且最终,他仍然会回到自己,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迷失。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且不说它本身就是对维科的“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复归”这一循环历史观的阐释,“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首爱尔兰民谣叙述的也是一个叫芬尼根的泥瓦匠在守灵夜的酗酒狂欢中死而复活的故事。至于小说的主人公HCE,更是集合了爱尔兰传说中的巨人、 爱尔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芬·麦考尔、威灵顿、20世纪都柏林的一个酒店老板等不同历史时代的形象,体现了人类的再生。在循环的历史观中,生命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再生。显然,生活在20世纪的乔伊斯不可能相信人死后还会复活,否则他也就不必像艾尔曼记载的那样害怕死亡了。生命不断循环的再生观念只有从群体的角度来理解才是可能的。通过对人的群体性的体认,通过与人类群体相结合,乔伊斯终于摆脱了斯蒂芬的纯理念世界的“不妊”,获得了民间文化所具有的不朽的生命力。
正如叶芝所说的,民间文化的形象虽然是“没有观念”的,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民间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表现了某种深刻的理念或道德。从表面看,民间文化的主题像艾尔曼评价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司空见惯”(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但是, 民间文化却具有抽象观念所不具有的另一种深刻性,在巴赫金看来,这种深刻性要远远超过那些理念与思辩,那就是在物质—肉体下部的狂欢中所包含的无限的丰富性和不朽的生命力。正是这一深刻性赋予了乔伊斯的作品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
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主要从形式来分析民间诙谐文化,如广场语言、节庆形象、筵席、怪诞的人体以及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等。如果叶芝对民间创作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应该是形式而不是主题才是民间文化的主要表达手段。拉伯雷的《巨人传》现在引起人们兴趣的也是它的形式而不是人文主义思想。拉伯雷的语言不仅是粗鄙的,也充斥着许多“从人民生活深处吸取来的‘处女词’”(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 )和各种外来词的组合,此外,《巨人传》中还有大段大段我们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常见的那种没有意义的聒噪和纯粹的语言游戏。巴赫金指出,拉伯雷的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如果放在传统的文学标准和规范中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在民间文化中,拉伯雷式的“怪诞”却比比皆是,由此巴赫金提出,民间文化的这些形式是与民间文化的自由性、开放性、生成性和欢乐的气息直接相连的,“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把拉伯雷式的语言游戏推到了极致:俯拾皆是的新词,大量的双关语、头韵,长达数页的没有意义的罗列,十几种语言的交融……显然,表意已经不是乔伊斯主要追求的东西。乔伊斯的这些语言游戏让研究者们伤透了脑筋,但只要我们看一下爱尔兰人的酒吧饶舌,就会发现这种语言游戏对于乔伊斯父亲一辈的酒吧高手来说,不过是一道家常小菜。在《乔伊斯传》中,艾尔曼记录下乔伊斯的弟弟和朋友们所做的几个文字游戏,其形式与《芬尼根的守灵夜》十分相似,也是用谐音、头韵、双关、绰号来取得效果,也是编造多意的新词。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拉斯曾经提出,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用的一些“新词”实际是他发明的。在爱尔兰的民谣中,这类新词和饶舌话也非常多,乔伊斯在作品中也采用或模仿过这些爱尔兰民谣。语言游戏和创造新词是爱尔兰民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乔伊斯对爱尔兰酒吧语言的运用不仅使他的后期作品具有了明显的诙谐文化的外表,而且也使他的后期作品取得了比前期作品更大的革新功能。大多数乔伊斯研究者都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角度来分析乔伊斯后期作品的颠覆性,其实乔伊斯本人对这些多少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向来不感兴趣。事实是,当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本身的欢乐和自由特征、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吸引了乔伊斯,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这个文化的语言后,乔伊斯的作品便获得了民间诙谐文化所具有的再生的生命力。
正如叶芝所说,早期一心想进入正统艺术殿堂的乔伊斯由于把自己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片面地追求纯粹的理念和美,反而变得贫瘠。严肃带来了沉重和死亡。相反,由于立足于大地之上,融入社会群体之中,乔伊斯在超越早期创作的同时也得到了永生。与个体的精致相比,群体的狂欢也许缺乏高雅与美,但却充满勃勃生机。与斯蒂芬相比,布卢姆和芬尼根的世界可能过于普通,但这个普通的生存价值却正是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通过《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物质—肉体的喜剧世界,乔伊斯的作品终于达到了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