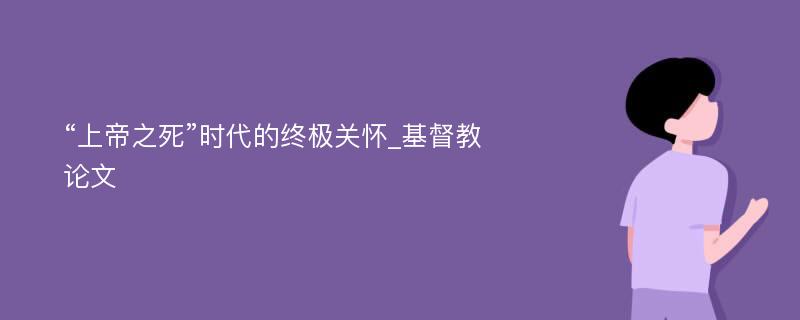
“上帝之死”时代的终极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上帝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8)04-0005-05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坚持不邂地追求着幸福,永恒的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的,而实现这一终极目的则是对人类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的找寻和追求。在人类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也随之加快,然而,在这个以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世俗化社会,无论自然科学如何发展,人类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终极关怀,即人类自身存在的根据、存在的确证。因此,在现代社会,如何追寻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和终极关怀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新教神学界内出现的激进世俗神学家或“上帝之死”派神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独特的见解,他们主张重建基督教同现代社会的关系,在人类已经成熟,“上帝”已经死亡的时代,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来看,基督教道德价值观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把人的幸福引向了彼岸世界,牺牲了人的世俗幸福。激进世俗神学家或“上帝之死”派神学家们认为基督徒惟一应当关注的对象不是“彼岸世界”或者“来世生活”,而是此世,人们应该追求作为“此世的超越性”之典范的耶稣的形象,号召世人效法基督,从而追寻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笔者认为,对激进世俗神学家关于“上帝之死”阐释的研究,对于今天完全生活在世俗化社会中的我们或许有着某种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上帝之死”
世俗是指人类的现世生活。世俗化代表了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现代社会,其表现就是人们不再受教会和封闭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控制,摆脱了那种超自然的神圣存在的束缚,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放到现世而不是来世。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马丁·路德对释罪教义的抵制开始,新教徒便开始更加关注现世,关注人类活动对现世的影响。激进世俗神学家加布里尔·瓦哈尼安认为,新教徒的信仰与世俗是分不开的。圣经观中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反思加强了对世俗价值的真正肯定。圣经没有截然一分为二地描述人对上帝的责任和人在现世的生活。这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并没有在宗教与世俗之间遭遇根本的分裂。可以说人类生活的宗教和世俗两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人类对上帝的神圣责任和在现世的世俗生活从表面上来看虽然对立为两极,而其实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的平衡。韦伯曾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1](P155) 于是,在世俗化的今天,在尼采宣告了上帝死亡,在人类不遗余力地解构各种各样的权威,否定终极价值,否定任何“永恒”或“神圣”的东西之时,瓦哈尼安认为,此时对“上帝之死”的谈论绝非要抛弃上帝信仰,而是要在摆脱偶像崇拜、涤除人们的庸俗和对上帝的歪曲之后,在现世找到那真正的、活生生的上帝。正如瓦哈尼安在其《没有偶像的等待》一书中所指出的:“谈论‘上帝之死’意味着: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领域,活着的上帝的实在在于他是独立于文化思想和其它一些试图使他具体化的团体之外的。‘上帝之死’表明基督教文化的终结,而且尤其是试图同化另一个上帝的终结。另一个上帝是在我们的宗教和普遍的偶像崇拜中活着的上帝,是一个绝望的漫画。这表明,人类作为一种宗教性的动物,正在探索一个新的上帝观,一种新的态度,一种与它一致的模式;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就要到来。当新的宗教信仰从已死上帝空无的坟墓中升起、出现时,一个新的纪元就开始了。”[2](P231)
在犹太—基督教的宇宙观中只有两个基本的实在: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上帝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不同于他的创造物的完全者。尽管人格的上帝观对此提出了挑战,但上帝与人类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上帝不是理想的人,他的神性也不被人类所分有,但他总是通过他的创造物表现出来。在传统的圣经信仰中,上帝,人、自然构成了以神本思想为基础的框架。上帝是至高的绝对者,上帝之外没有上帝;人在上帝之下,但由于人有神的形象,因此高于自然,所以可以管理自然;然而人不是上帝,不能征服自然;由于人与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们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在圣经思想中,上帝不是人直接可以达到的智慧或道德原则,他是人类实在的源泉和终点。信仰圣经的人强烈地相信存在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指引着人类和历史的发展。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传统的圣经信仰已经是不可理解的。在科学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下,人类逐渐崇尚以人为本的思想,否定神本思想。人的地位随着自然的地位一起上升,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获得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进而改造社会、支配他人的信心,上帝已不再是人类的必需。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道德伦理的演变,人们发现无需借助上帝,科学和伦理就可以解释人类和宇宙。人类开始将自己的终极关怀寄托在理性、科学等世俗价值之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甚至认为人类的理性无所不能并主宰一切,科学和理性可以解释一切神圣的领域。这对传统基督教思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从传统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宗教之间没有真正的冲突。科学与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冲突只有在对其中任何一个的本质产生误解的时候才会产生。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是一个自足的、自治的实体,不需要外在的原则来解释它的运行和意义,而且人类对宇宙的知识虽然是相对的,但仍然比对那位绝对者“上帝”更加确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基督教的思想家和神学家接受了世界是不依赖于上帝而自我存在的思想,开始主张宇宙的本质意义似乎是可证的,但同时他们希望上帝是其最终的解释。在此,上帝逐渐成为物质世界的附属物,一个机械的神(deus ex machina)。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和证明的只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没有发现任何对上帝直接可证的责任,人类自身创造和救赎这个世界。自从人类开始独自行使对物质世界的最高主宰权,其就开始独自赋予宇宙以意义。
但“上帝之死”并没有使现代人更轻松,他们仍然无助和迷失方向。人们对自我的追求并没有完全达到,仍然需要寻找自我。人类仍然处在同一起点,惟一不同的是对意义的追求是在无神论的而不是有神论的支持下进行。现代道德伦理标准已完全人类中心化,假定上帝作为必要的道德的认证已经毫无意义。现代人在原罪与犯罪上拒绝接受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而是建立了一种以人类的内在纯洁为基础的完全清白的道德标准。因此,人类在与他自身直接相关的环境中追寻其存在的意义,拒绝接受任何超验的意义。从人类在现世存在的具体情形来看,上帝已死。
二、信仰问题
在尼采喊出了人类的现状即“上帝死了”之后,他关注的是当上帝死亡之后怎样成为一个人,他把上帝从一个自足的宇宙和依靠自我的人文主义的体系中排除在外,认为人类存在的问题是独立于上帝问题之外的。瓦哈尼安同意尼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他认为这并不影响信仰的存在,如他所言:“说上帝死了或是主张人与上帝之间有无限本质的差别意味着不仅从人到上帝没有任何阶梯可以到达,而且上帝和人之间也没有物质的同一性,因此,人类存在的问题就是独立于上帝问题之外的。即使是科学,无论是什么假说,都无法证明这一与上帝的假说,即使是存在主义也没有可能证实上帝和人的同一性。人类的现实性并没有根本地妨碍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克尔凯郭尔仍然是一名基督徒——而且以古代的信条为基础: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3](P210-211)
所以,在瓦哈尼安看来,虽然人类在饱和了无神论和人类中心论的人文主义的文化背景下,陷入了信仰危机,但信仰不会消失,也不可避免。德国思想家西美尔曾断言:“现代人不再信仰传统的宗教,但现代人又仍然需要宗教。”[4](P25) 从本质上来讲,信仰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可以证明的或完全清楚的。它代表了主观真理和客观现实的结合。他认为:“信仰以不压倒任何一方为前提,试图调和主观和客观,主观真理和客观实在,自我与世界。信仰试图调和实存的两个领域——位格的和非位格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但并不使它们成为一体。它试图以一种综合的表述,或是作为极端的集中,以及在完全与相对,普遍与特殊,世界与自我的张力中来定义人类。”[3](P165)
瓦哈尼安认为,造成现代宗教信仰危机的根源是虚伪的宗教信仰观。当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只是一种偶像崇拜或是迷信,是对传统圣经信仰的曲解,信仰已经完全成为形式上的信仰,毫无意义可言。现代信仰危机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它也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被充分地表现。法国著名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小说《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通过其主角一个乡村教士,象征性地描绘出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瘫痪。贝尔纳诺斯的教士反对贫瘠的和空洞的基督教形式,逐渐地开始揭示一切都是恩典。最后他必须承认基督教已不再影响生活,而且将来也不会。贝尔纳诺斯的教士和现代人正在寻求一种更人文的和充实的存在观念。在贝尔纳诺斯那里,上帝在世界的空缺是显然的,基督教应该为这个空缺负责。这样,如果一个人想信仰上帝,或是想从衰落和瓦解中拯救西方文化,他必须反对基督教。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权利与荣耀》一书中牧师对酒精的上瘾和对一个私生子的培养,象征了基督教无力为这个世界的生命提供一个所需的内在推动力。牧师所代表的信仰已经是在毁灭的边缘,因为它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现代的需要。最后,格林的牧师也揭示出:在他不再穿着牧师的服装时,一切都是恩典。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严肃地质疑了基督教以信仰为基础的存在价值,即相信有一个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上帝。有人认为,剧中的“戈多”是一个缩小了的上帝的漫画,人类愚蠢地在心里认为好像没了这个偶像人类就无法生存,其实完全相反。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上帝已经仅仅是一个情感的出路,戈多只存在于人类的幻想中。阿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J.B.① 反映了萨特式的人文主义。麦克利什宣称,如果上帝存在,人类就不能忍受不是那个上帝。对J.B.来说“上帝就是道”;他代表了所有一切好的事物。但最终J.B.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由于人类的清白和上帝的存在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上帝,如果他是上帝,就不是“善”,而如果他是“善”,就不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生命是他自己的选择。人类是“自我”的独自拥有者。而为什么人类却像科林斯王一样,总是试图想证明上帝?如果人类所要的就是爱,为什么还要追寻上帝?对于J.B.和处于后基督教的人们来说,已经没有公义或神圣的爱,所有的只是人类的爱。对此,瓦哈尼安写道:“在圣经的神话里,约伯无法理解痛苦和罪恶,因为对他来说,上帝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J.B.,或是后基督教的人们无法理解罪恶和痛苦,因为上帝并不真正地存在,除了从神学上来讲。对他来说,只有“爱”是存在的,而且不管是痛苦,不义,死亡,或是上帝,当爱被自由地给予时,爱是存在的。”[3](P128)
所以,在基督徒信仰上帝,认为一切都是恩典之时,现代人认为一切都是恩典乃是因为上帝已经死了。瓦哈尼安认为在他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内在的恩典,它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即人类生活的最终意义来源于存在主义原则下的恩典。他说:“现代人是基督教和无神论的继承者。他们既同意基督教一切都是恩典的观念,又同意无神论上帝死了的观点。他们的论证是:一切都是恩典;因此上帝死了。因为生命如果是毫无意义的,就应该没有上帝。但是如果它有意义——而且也应该有,否则就会自相矛盾——它是在存在的恩典的某种德行中才有意义;因此上帝不存在。如果一切都是恩典,那么上帝是死的。或者由于上帝死了,一切才是恩典。”[3](P106-107)
三、“上帝之死”与文化
基督教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的,然而现代人的思想已经从超验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现代世界是对文化和神学变革的继承,如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教会对文化控制的终结,美国革命带来的则是神学对文化控制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世俗团体逐渐为自己罩上神圣的光辉,人们利用自己的权利废除了上帝与人救赎的合约。上帝也逐渐被认为是人的最高本质。所以在19世纪中叶,费尔巴哈看到神学已经成为人类学,于是声称,上帝已经成为人的最高、最纯的本质属性。现时代,人们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所以从对基督教对人的理解和现代世界对人的普遍理解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一个激进转变。在基督教思想体系中,在圣保罗的教导下,人类是在认识上帝之中认识自我,在寻找上帝之中发现自我,人类与世界的关联来自于上帝这一超验的中保。而在现代人的思想中这一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认为:今天的世界用它直接的和内在的实在为人类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境况。上帝与人认识自我的过程不再相关。事实上,上帝存在与否已无法提供解决人类的困境的任何办法。因此,今天人们所相信的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你就不需要再寻找上帝。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人失去了对宗教的热情,不再关注宗教问题。
在现代人看来,上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附属品,因为基督教在形成之后,就侵占了人类存在中本应自然地属于文化领域的那部分,它已经把信仰转变为一种文化的形式。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在他的《审判的文明》中提出今天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西方社会中净化基督教;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也认为基督教是与西方文化共命运的,而现代人需要在基督教信仰和无信仰之间作出选择;基督教思想家艾略特(T.S.Eliot)在他的《基督教社会的理念》中,认为现代人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形成新的基督教文化,另一种是选择接受无宗教信仰。然而,瓦哈尼安认为,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生,如果不依靠于给定的理性、社会和文化的条件,这种信仰是无法存在或具有任何确定性的。换言之,一个给定的宗教只会在某一确定的文化环境中才有其超越的效力。当基督教不再与某一特定文化相关联,它就不再具有普遍性。目前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已经衰落,世俗化的教条代替了传统基督教教义。现代的文化发展方向与基督教发展方向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现代社会中对人和世界超验的、神话的和神圣的观念已经被存在主义的、科学的和世俗的观念所取代。现代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后基督教时代,对于他们来说上帝是无关紧要的,他已经死了。所以,瓦哈尼安认为,“上帝之死”并不是指上帝自身已经死去,而是人类宗教——文化信仰中的上帝死去了。
瓦哈尼安在一篇名为《超越上帝之死》的文章中曾解释说,“上帝之死”是一个文化事件,从这个文化事件,现代人认识到从基督教时代向后基督教时代的转变。从文化角度来讲,曾有一个基督教时代,但现在一个激进的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世界的神圣意义消失了,人类的存在丧失了其超验的领域。讽刺地讲,基督教产生了现在看起来是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但从“上帝之死”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现代人的新的思维方式已使他们不能接受基督教福音。现时代激进存在主义完全弥漫于现代人的心理,并使人们得出结论:基督教对现时代已经无关而且毫无意义。当前的信仰危机错综复杂,因为现代人在宗教和科学上都已醒悟。宗教的醒悟在于当前“上帝之死”的现象,科学的醒悟在于由于人类科学创造而带来的灵魂与肉体的毁灭的威胁。瓦哈尼安认为,目前所需要的不是神学上的宗教改革,而是一场文化的变革。人类使世界不再神圣,但却忘记最终的文化模式是一个神圣世界的模式。因此,目前需要一个文化的转型来使事物恢复其适当的面貌。
四、超越“上帝之死”
瓦哈尼安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应该认识到:上帝的实在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世界观就其本身而言能使对上帝的信仰无效,所以,上帝的实在是独立于他所控制的文化体系之外的,正如卡尔·巴特的观点,即我们的思想与上帝的实在之间是断裂的,上帝总是完全的他。现实之中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基督教的真理与人类生存之经验的真理相结合,因为基督教神学不依赖于任何单一的哲学体系和世界观,它有其自身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领域。因此,解决当代宗教危机,寻求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可行模式,是人们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瓦哈尼安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的革命和通基督学(Christosophy)才能改变“上帝之死”的危机。通基督学的核心就是对待现实的最好办法是将现实的无上帝状态看作是对信仰上帝的有效选择,然而正是如此,通基督学其实是一种向现代无神论世界观的妥协,并且瓦哈尼安没有说明怎样进行文化的革命来建立一种新的上帝观,所以,他所提出的建议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代的信仰危机。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都有求知的欲望。在现代都市化的、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在这个充满压力与危机的现代世界中,人们仍一直在努力探索人类存在的最终意义。然而,人类理性认识愈深入,人类愈是发现理性本身的局限,正如康德所言,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所以理性局限之外的认识空间也许就只能由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予以填补。因此,如何达到人类从古到今一直在无止境地寻求的真理、至善,或许只有在真正阐明了上帝的本质、人的本质、信仰的本质之后,才能达到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解决现代人们的困惑与不安、失落与彷徨,满足现代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希望与期待。
[收稿日期]2008-05-11
注释:
① J.B.是美国诗人阿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所写的戏剧中的人物,此剧于1958年获普利策戏剧奖,它利用圣经的和现代的事件对约伯记进行了讽刺性的解释。剧中,J.B.是一个虔诚的、富裕的、仁慈的商人,也就是现代的约伯。上帝受到撒旦的挑唆,对他进行敲诈。J.B.失去了他的一切——他的存款、孩子、健康和名誉。虽然他非常生气,但他并不报怨上帝。上帝就像在约伯记中质问约伯一样,质问J.B.,J.B.立刻屈倒臣服表示忏悔,他重新获得了以前所拥有的一切。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后一幕中,J.B.最终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他总结到,上帝不会仁慈地帮助人类,上帝那里没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