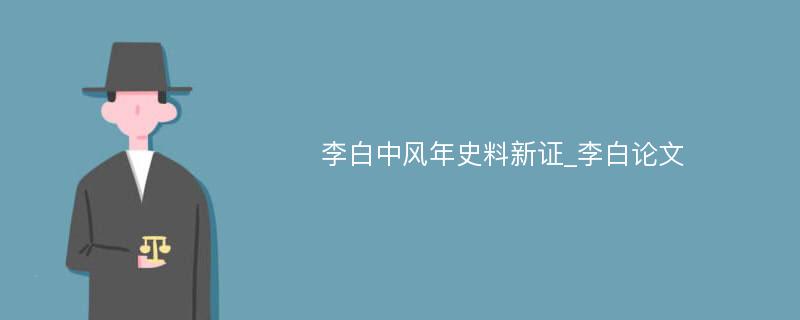
李白卒年史料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K8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51-06
关于李白生卒年,自宋以后历代学人都依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来作推论。《序》说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疾亟”,论者遂谓李白卒于当年;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1],遂从宝应元年逆推李白生年为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①。根据此说,李白在其父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之前就已经出生了,于是李白的出生地和籍贯都出现了问题(不是蜀中而是西域,即中亚碎叶或条支)②;《李白集》中宝应元年以后诗文的真伪也有了疑问[2]。但是此说又与李阳冰《序》以及其他唐人(诸如魏颢、刘传白、范传正等)所作碑序的记载相矛盾,故难成定论。古今学人对此深表怀疑,又提出了各种“新说”。或相信李白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卒于宝应元年(762年),终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广德二年(764年),享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广德元年(763年),享年63岁;或以为生于神龙二年(706年)、卒于大历二年(767年),享年62岁等等[3]。可惜诸人士由于占有史料并不充分,为了证成新说,都或多或少地疑误或篡改唐人文献,如谓李华《墓志》为伪托,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的记载不可信;又如谓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为伪作,因其中说至德二载(清人误定)李白“年五十有七”不可靠。虽然花样翻新,新论日出,但却谬误丛生,此牵彼掣,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李白生卒年(包括出生地和籍贯以及许多诗文的系年和真伪)问题,自今悬而未决,仍有探讨的必要。
笔者近从五代、宋初人引录唐人文献资料,表明李白并不卒于宝应元年,也不卒于广德元年或二年,因为新出资料记载李白至迟在大历初年仍然活在人世。由于本则史料反映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对重新认识李白生卒年大有裨益,这里谨将其原文先披露出来,并对其可信度略作考证,以为引玉之砖。
历来学人考证李白的生卒年,依据的资料只有李阳冰《草堂集序》,但是据我们所知,有关李白生活下限的记载,至少有六家③,而以李士训《记异》所载最为真实,表明迟至“大历初”李白尚与李士训、李阳冰等人传诵《古文孝经》,从前说他卒于宝应元年(或广德元年或二年)当然都是错误的。
一、《记异》所载大历出土《古文孝经》真伪之审察
据唐人李士训《记异》记载: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④
为了证明这则史料的可靠性,首先必须对李士训其人、《记异》其书,以及大历出土《古文孝经》其事,进行系统证明。
(一)《记异》及相关文献的审察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李士训是与李白同姓的、半耕半读的书生,其他事迹已经无考。《记异》一书也不见于历代书目著录,详情也不可得知。只有《太平广记》卷461《高嶷》、《天后》二条,似出自其书。《高嶷》记渤海高嶷惑于“鸡魅”之事;《天后》记唐文明年间“天下进雌鸡变雄”预兆武则天“正位”之事,两则的出处都注“出《纪异》”[4]。“纪”与“记”常通用,《纪异》疑即《记异》。可见其书北宋尚存,故郭忠恕、李昉等得以称引。根据《广记》所录,《记异》的内容乃杂记异闻,有些流于志怪小说,故为“专记异事”的《太平广记》采录。对此,难免有人会对以之佐证李白生活下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这里笔者将深入探讨《记异》所载大历出土《古文孝经》一事的可信度,以破此疑。
《记异》虽已失传,但引录李士训《记异》的郭忠恕《汗简》却是一部严肃可信的学术著作,其作者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
郭忠恕(730—977年)本末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卷21《郭忠恕画赞并叙》、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3和《宋史》卷442。郭忠恕是五代、北宋间人,曾仕后汉,并历后周,终于北宋。郭《图画见闻志》传注:“忠恕尤精字学,宋元宪尝手校忠恕《佩觹》三篇,宝玩之。”[5]《宋史》本传称:忠恕“尤工篆、籀”,“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艺文志》著录:“郭忠恕《佩觹》三卷,又《汗简集》七卷。”[6] 其人精通群经,崇尚古学,尤善古文字,《汗简》、《佩觹》皆其代表作。《汗简集》即《汗简》,以其集先秦以下古文篆隶字形而成,故称《汗简集》。《汗简》乃现存唐宋最早的古文字形工具书,“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由于其书“所征七十一家存于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7] 今传《汗简》有两种版本:一本三卷,卷各分上下,另有《目录》一卷⑤;一本七卷,正文六卷,第七卷即《目录叙略》,郑珍《汗简笺正》本即此。《目录略叙》历叙其所依据的“古文”、“篆”、“籀”资料71家,李士训发现的“绢素《古文孝经》”即其一种。《汗简》将其作为“古文”著录,凡录七字,出处皆注为“古孝经”。
李士训这段文字,不仅见于郭忠恕的《汗简》,与郭同时代的句中正《三字孝经序》也有称引,所录之文相去无几:
臣耽玩篆隶,习以性成。(中略)乃得旧传《古文孝经》(自注:陆氏《释文》云:“旧有《古文孝经》”;《开元实录》:刘子玄云:“《古孝经》出孔壁,其语详正,无俟商榷。”又李士训《记异》曰:“大历初,霸上耕,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与今文小异,旨义无别),以诸家所传古文,比类会同。依开元中刘子玄、司马贞考详今文十八章,小有异同,亦以不取。约秦、许(慎)、斯(李斯)、蔡(邕)篆文及汉、魏刻石隶字,相配而成(笔者按:谓《三字孝经》)。⑥
句中正(929—1002年)字坦然,益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自孟蜀归宋。精字学,太宗时献八体书,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徐铉等“重修许慎《说文》”,《宋史》与李建中同卷,称其“(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咸平五年即1002年,其生当为929年。句作《三字孝经》即据22章“旧传《古文孝经》”与其他篆、隶“相配而成”,他是见到过《古文孝经》实物的。清郑珍《汗简笺正》说句氏《三字孝经》乃“中正自集奇古文为之,在郭氏后,又非渭上(当为“灞上”——引者,详下)本。”这一怀疑是没有必要的。《宋史》本传:句中正在孟蜀时曾参与校刻《蜀石经》,对儒学文献是熟悉的。北宋时,又“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坐。问所书几许时,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句氏生年(929年)与郭忠恕(约930年)同时(甚或稍早),他完全有可能与郭氏一样见到过李士训大历初发现的《古文孝经》。句氏《三字孝经自序》[8] 也引用李氏《记异》,惜过于简略。尽管如此,他是与郭忠恕同时引用《记异》的学者,足证郭氏所引非出虚构。
清朱彝尊《经义考》、倪涛《六艺之一录》、王琦《李太白集注》附录也有转引,这里不再一一转录。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于灞上“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白授李阳冰”的事,广为五代、宋初及后世法书、经籍著录之家所称引。其中清人皆系转录,固无足多;而五代、宋初郭忠恕、句中正所言,则是实见其书,其所称言无异精金美玉,洵可宝贵。这则史料明白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年)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其传授给了李阳冰。李白不卒于四年前的宝应元年(抑或两、三年前的广德元年和二年)的事实,就不言自明了。
(二)大历出土《古文孝经》之审察
李士训《记异》所载《古文孝经》的发现,是经学史上十分重大的事件,可惜未获得历代学人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审察此一事件的真实与否,即可考见《记异》记事是否准确,亦可旁证其“初传李太白”的记载是否可信。
《记异》说:“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与汉儒刘向、桓谭、班固等人所言《古文孝经》情形吻合。
《汉书·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又于《孝经类小序》注引桓谭《新语》:“《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⑦ 只不过,班氏、桓氏等人所言乃“孔壁古文”,其书已随“孔安国《传》”的失传而亡于梁末;隋世新出本又疑为刘炫伪造(隋时“诸儒”及唐代学者司马贞俱疑之)[9]。22章的《古文孝经》之以古文字形行于世者,实有赖于大历初年的这次重要发现。
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古文四声韵序》对《古文孝经》的此次出土亦有所记载,却与李士训的记载有一定出入:夏称《古文孝经》出自项羽妾墓:“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耕者所获。”[10] 夏竦这里提出了两个《古文孝经》的来源,一是项羽妾墓、一是渭上耕者所获。有的学人以为这与李士训灞上得《古文孝经》是一回事,以为李氏所获乃项羽妾墓出土,为秦汉之间旧物。但是我们根据傅奕《老子解序》关于项羽妾墓出土古文献的记载可以得知,该墓是在北齐武平五年(574年)重见天日的,且记载出土文献中有《老子》而非《孝经》;地点是在彭城,而不在灞上也不在渭上。有人将傅奕、李士训的两条资料合起来,说项羽妾墓出土的既有《老子》又有《孝经》,也缺乏依据,可能皆为李士训灞上出土《古文孝经》之误传。
李阳冰从李白处接受了《古文孝经》,经过研习,“尽通其法”,一方面将其书“上皇太子”(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氏家传鸿宝,传与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愈《科斗书后记》有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中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中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11]
王应麟《玉海》对此事也有记载:“李阳冰子服之,贞元中授韩愈,以其家《科斗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后以归归登。其后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再乞观之。张籍令贺拔恕写之。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经》。”[12] 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在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如前所述,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都有传授,郭忠恕首次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七例);句中正又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字孝经》;李建中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13]。夏竦称赞说:“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古文四声韵序》)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这些也都章章在目,有案可考。特别是夏书所录404例《古孝经》字形,与桓谭所谓《古孝经》与《今孝经》“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巧合如此。
宋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⑧,还手书其文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⑨。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历考其分章起讫、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大历出土《古文孝经》在禁中秘府的收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所“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14]。
换言之,作为《记异》作者的李士训,躬身耕于灞上,竟意外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其本身就不得不惊为一件异事和幸事。而作者将其以奇闻杂记载于书中,也是无可厚非的。
笔者费墨颇多,援引旁证,旨在证实李士训《记异》所载“大历初”发现《古文孝经》实有其事。而《古文孝经》在后代的流传授受过程又那样地清晰无隐。这些都说明《记异》所记“异事”是有真实的历史内容的。同时载有“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传授序列也不应有问题,是实属可信的。
二、《记异》与其他唐人碑序可以互证
李士训《记异》为我们昭示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按理,研究李白的生卒年就应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可惜前人或以李士训《记异》是小说志怪不足征信,忽略其中反映的历史事实,王琦《李太白集注》将其归入《附录·外纪》“书法类”,而在《李太白年谱》中只字不提,即是证明。可是当我们将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生活下限,与其他唐人记载李白生平的历史文献相对照,就会发现彼此实可互相吻合,毫无矛盾扞格之处。
据陈振孙、赵希弁等人书录所载,《李白集》自北宋以来就载有唐人所作的“两序”、“四碑”: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⑩。李阳冰《序》作于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之时,资料得之李白“枕上授简”。李华与李白同时,互有诗文赠答(11),其作《墓志》当受托于李白子伯禽。范传正虽与李白“甲子相悬”,但其父范伦与李白“有《浔阳夜宴》诗”唱和,范、李二氏有“通家之旧”。刘全白年辈稍晚,自谓“幼则以诗为君(李白)所知”,李白生平亦得之亲闻。魏颢与李白同时,曾于“广陵见之(李白)”,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曾“尽出其文,命颢为集”。裴敬乃李白师从学剑之“裴将军”(裴曼)的族曾孙,敬“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四过青山,两发涂口”,得李白诗文多篇,裕闻李白故实(12)。这些作者所作的碑、序本该是考证李白生平及生卒年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裴敬撰《墓碑》未言李白生卒及籍贯,是个例外),可惜前人却一意曲解、怀疑原文,反而从中引出了错误的结论。
李华《墓志》序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路)[终]歌》而卒。悲夫”!根据李华提供的李白享年,再结合李士训《记异》所载李白生活下限,从大历初年(766年)上推62年,则得李白的生年即唐中宗神龙初年(705年)。这与李阳冰、范传正所言完全吻合:
(李白先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指李白——引者)。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号。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即李树——引者)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李阳冰、范传正俱说李白之父(即李客)“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公元705年)从远窜之地“条支”(或“碎叶”)潜逃回来,客居蜀中(或称“广汉”,唐时彰明县属广汉郡),恢复李姓,才生李白。假令李白生于神龙初其父归蜀之时,下数62年,也正好是大历初年(766年)。李阳冰《集序》、李华《墓志》、范传正《新墓碑》与李士训《记异》四条材料如此契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李阳冰《草堂集序》得于李白的枕上口授,自然真实可信;李华《墓志》又系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不会有误;李士训《记异》所录更是当事人记亲历事,也是道地的实录;范传正撰《新墓碑》系李白孙女“搜于箧中得公(李白)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改撰而成,亦非耳食传闻者可比!四者都是原始材料,没有造伪嫌疑,因此才能如此互相印证,彼此契合。因此我们说,李白的正确生卒年应该据此定为约705年—约766年,而不是其他。
李白既然生于李客“神龙初”归蜀之后,其出生地和籍贯自然就非蜀中莫属了。正因为如此,魏颢作《李翰林集序》明确地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又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刘全白作《李君碣记》亦直称:“君名白,广汉人。”都视李白为“蜀人”(或“广汉人”),将其出生地点毫不含糊地定在蜀中。易言之,既然李白一家定居于蜀是在其父“神龙初”从流放地逃归以后,则李白之生不得早于神龙初年亦可知矣。
由于李阳冰以一代书法大家为世人所重,他那篇一唱三叹、情辞并茂的为李白所作的《草堂集序》也随《李白集》而广为天下所传诵。李士训则名不见经传,他关于大历初得《古文孝经》以传李白的记载,又有些神神怪怪富有传奇色彩,除了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对此略有所闻外,研究文学甚至研究历史的都对其比较忽略。故世人徒知李白有宝应元年“疾亟”之事,却不知有“大历初”与李士训、李阳冰传诵《古文孝经》的事。李阳冰所记“宝应元年十一月”成了人们习见的李白生活之下限。人们错误理解李阳冰《序》所说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为死卒,将李阳冰作序之年当成李白的逝世之年。以此误解为基础,再根据李华“年六十有二”之说,将李白生年定在神龙前五年即长安元年(701年)。这就是传统所谓“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一说的由来。
可是,此说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载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白)”的事实明显矛盾,于是王琦将两处的“神龙”都改为“神功”(697年)(13),不惜擅改古文以从己说,当然是不可取的。有人又依据李白生于长安元年立论,认为李客归蜀时李白已经五岁,于是又弄出李白不生于蜀而生于“西域”(或“中亚碎叶”、“条支”)等说。又有人因相信李白宝应元年已卒,遂谓李白宝应以后诗文为伪托(如《草书歌行》等)。由于传统所定李白生卒年有误,李白许多自叙其年的诗文(如《为宋中丞自荐表》等),也统统被系错了年代。至于因此而将李白诗文的创作背景、作品本事、主题思想弄错了的,更是不在少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皆因李白生卒年之误定,遂使有关李白行止事迹之研究统统都出了问题!
我们认为,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得《古文孝经》实有其事;所载“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也真实可信。这则史料非同于一般志怪小说,它真实反映了大历年间《古文孝经》出土和传授的历史,既是我们研究经学史的枕中鸿宝,也是我们考证李白生平特别是生卒年的重要资料。它关于李白“大历初”(766年)仍在人世的真切记录,为我们印证和坐实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新墓碑》关于李客“神龙之始”归蜀后而生李白、李华《墓志》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魏颢《翰林集序》称李白“身既生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可靠而重要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纠正前人以篡改、误解古书来推定李白生卒年的错误做法,通过它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印证,考证出李白准确的生卒年代(约705年—约766年)。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对李白出生地即籍贯、诗文系年、诗文背景及本事、交游及履历,甚至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真伪问题,等等,重新通盘进行思考,以开创李白研究之新局面。
注释:
①清王琦《李太白年谱》:“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李太白全集注》(中华书局,1977年)卷35《附录》。后之学者多从此说,时下各类文学史和李白研究专著、辞书亦多从之。
②李宜申《李白的籍贯和生地》(1926年5月10日《晨报副刊》)首倡李白“生于西域说”,陈寅恪《李太白氏族疑问》(《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从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又提出“中亚碎叶说”,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周春生《李白与碎叶》(《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俱从之。
③关于对除李士训《记异》外的五则文献的征引及考证,参见舒大刚《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102页。
④见郭忠恕《汗简》(郑珍《汗简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广雅书局本,上海书店,1994年)卷7《目录叙略》。
⑤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汗简》,《总目提要》称有《目录叙略》一卷,实则有《目录》而无《叙略》。
⑥宋朱长文《墨池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引。又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库本)卷269亦引,文字有残缺。
⑦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又《太平御览》卷608引桓谭语作“《古孝经》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今异者四百余字”(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同),“十”下盖脱“二”字。
⑧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今已与唐玄宗注《孝经》合编,收入《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等丛书中。参见舒大刚《今传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合编本”之时代与编者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
⑨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1,影印道光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雍正《四川通志》,卷26,清刊本,等书著录,并参见舒大刚《试论范祖禹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⑩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李翰林集》三十卷,(中略)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中略)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郡斋读书志》卷5下)亦云:“《李翰林文集》三十卷(略),希弁所藏三十卷,(中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
(11)李白《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复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足繁忧”一诗,见《文苑英华》卷343),本集题作《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兹从郁贤浩说(见《李白大辞典》197页“李华”条)。
(12)上引俱出诸家碑、序。详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31《附录》各文。
(13)清王琦《李太白年谱》:“长安元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志》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标签:李白论文; 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草堂集序论文; 李阳冰论文; 孝经论文; 宋史论文; 古文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甲骨文论文; 金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