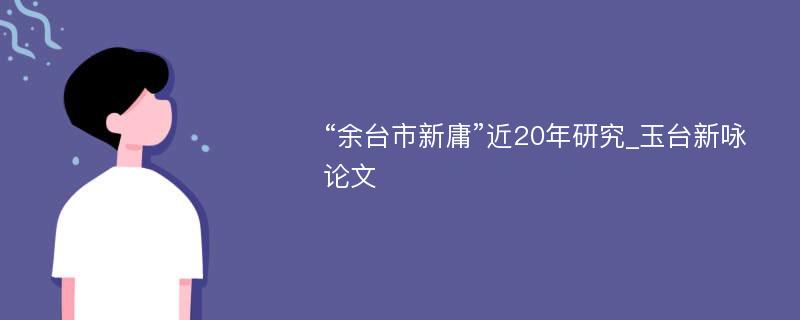
近20年《玉台新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玉台新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8444 (2001)02—0225—05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诗歌总集,主要收集了齐梁时代的一些宫体诗。清代以前,由于儒学以及封建礼教、文化背景等影响,多数学者认为《玉台新咏》是一部淫秽之书,糜乱之作,对其评价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冲破了研究《玉台新咏》的桎梏,研究者们写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文章,给予了《玉台新咏》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对于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给予总结和反思,对《玉台新咏》的进一步研究,也许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
对《玉台新咏》成书时间的考证,牵扯到对该书整体的研究,不少研究者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日本学者兴膳宏在《〈玉台新咏〉成书考》一文中将《法宝联壁序》中萧绎、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等六人的排列顺序与《玉台新咏》卷七、卷八作者的排列顺序作了比较,其结论是:排列顺序一致,并且按职位高低来排列,这些人在《法宝联壁序》成文时还活着,从而考证出《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六年(534年)[1](P.329)。 沈玉成赞同兴膳宏的观点,并积极地加以肯定,他说:“《玉台新咏》编定于中大通五、六年间,至少我个人认为可成铁案。”[2 ]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周禾在《论〈玉台新咏〉的编纂》一文中分析了梁代的政治形势,认定《玉台新咏》的编纂时间应在大同中(大同5年前后,亦即539年前后),其下限为大同七年(541年)12月[3]。隽雪艳认为,“《玉台新咏》大概成书于梁简文帝即位之前,元帝尚为湘东王的时候。因为书中只有明人妄增部分称简文帝、元帝,而其余卷第都称简文帝萧纲为皇太子,称元帝萧绎为湘东王。”[4]据考证,萧纲即位在550年,萧绎为湘东王时是514年,《玉台新咏》成书时间在514年—550年之间, 时间跨度太长。穆克宏指出:“《玉台新咏》当编成于公元542年前后, 有人认为《玉台新咏》编成约在531年前后,显然是不准确的。”[5]对于《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刘跃进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证。他指出:“《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六年,也有许多疑惑难以索解。最明显的问题是,这一年,徐陵年仅28岁,当时许多文坛宿将都还活跃一时,他的父辈徐摛、庾肩吾等还在世,他据何而选录当时人的作品?再说,选本收录活人的作品,目前尚未找到六朝的成例。据此《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更应该给予重新考定。”[6]
二、《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
关于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的动机,古人有下列几种看法:唐代的李康成认为是为备讽览而作,“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总集类》《玉台新咏》条引)较李康成之后的刘肃认为是张大宫体,他在《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称:“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清朝的朱彝尊认为“寓有微意”,他指出:“徐陵少仕于梁,为昭明诸臣后进,不敢明言其非,乃别著一书,列枚乘姓名,还之作者,殆有微意焉”,“昭明优礼儒臣,容其作伪”。清代的梁启超认为是宣扬诗体,他说:“《新咏》为孝穆承梁简文帝意所编,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缘情绮靡之作是也。”[7](P.551)对古人的观点,近人多有不同的看法。主要依据徐陵《玉台新咏》里的论述:居住在深宫中的女子,长日无聊,所以“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皋苏,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瞑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沈玉成认为,《玉台新咏》“是为后宫妇女编选的一部读本”[2]。周禾认为, 《玉台新咏》一书是为萧纲的东宫妃嫔们“备讽览”而编,同时他又强调,从《玉台新咏》这一书名也可考见徐陵的编纂目的。他认为:“徐陵身为萧纲东宫的宫官,取‘玉台’一词绝不会是指萧衍的后宫。由此更可知,徐陵取‘玉台’就是指东宫妃嫔们居住游乐的地方。‘新咏’即新的诗集,以别于旧。”[3 ]许云和在《南朝宫教与〈玉台新咏〉》一文中分析了南朝宫教的具体情形,认为《玉台新咏》“是一部备后宫讽览的诗集,也即一部宫教读本”[8]。 章必功在《玉台体》一文中认为:“《玉台新咏》顾名思义即‘后宫新咏’”,“乃是徐陵为宫廷妇女提供的一部可资悦目赏心的诗歌读本。其性质,是服务于萧梁宫廷文化娱乐生活的工具,是萧梁宫廷文学的产物”,“是一本宣传‘艳歌’,推广宫体‘艳歌’的范本。因此而立的玉台体,质而言之,即是一种专门‘言情’的诗体。”[9]
三、《玉台新咏》的编纂标准
齐梁宫体诗绝大部分都收集在《玉台新咏》这部诗集里,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明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二中指出:“《玉台》但辑闺房一体。”清纪容舒在《玉台新咏考异》中说:“按此书之例,非词关闺闼者不收。”这是古人对《玉台新咏》一书编纂标准的看法。近来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穆克宏认为,《玉台新咏》的编撰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标准,他说:“徐陵的概括是不准确的,胡应麟和纪容舒的判断也是片面的。因为《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有不少非‘艳歌’,不是‘但辑闺房一体’,更不是‘非词关闺闼者不收。’还是评选《六朝文》的许梿说得好,他说:‘是书所录为梁以前诗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韵一卷。虽皆绮丽之作,尚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艳斥之。或以为选录多闺阁之诗,则是未睹本书,而妄为拟议者矣。’可谓力排众议,道出了事实的真相。”[5]周建渝阐述了《玉台新咏》的编撰艺术标准, 认为在《玉台新咏》选诗之艺术标准上,“‘清文’‘新制’是其鲜明的特色”。他进一步指出:“无参于雅颂”“靡滥于风人”的思想标准和“清文”“新制”的艺术标准既与《玉台新咏》入选的作品相符合,又与“近世之所竟”的文学潮流相一致[10]。也有研究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玉台新咏》的编撰标准,指出:“魏晋南北朝由于汉王朝的瓦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不仅儒家思想的统治受到冲击,而且出现了先秦之后第二度的百家争鸣与思想解放,理论思维十分活跃,是一个文学和美学比较自觉的时代。《玉台新咏》以‘抒情’、‘感人’‘娱己’为标准的编选思想正是这种时代特征的折射。”(栾晓平,《山东社会科学》,1988,2)
《玉台新咏》的编纂者是徐陵,指导者是萧纲,这两人的编撰指导思想是否一致呢?沈玉成认为,“事涉后宫,没有皇帝或太子的命令、指示,一位文学侍从之臣决不可能去编这样性质的书。刘肃说萧纲令徐陵撰集此书‘以大其体’,多少接触到了事情的深层目的。所谓‘以大其体’,可以作两种意义的理解,即扩大宫体诗的影响或范围。”[2]栾晓平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说:“徐陵在萧纲的旨意下,在既定的范围之内选诗,其目的并非完全是为宫体诗‘艳诗’溯源,证明其发源于古诗,合乎于风雅之道,所辑诗作也并非以‘宫体’为其唯一标准,而是兼顾文学思想,文化的系统和以妇女为主题的编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玉台新咏》的产生,萧纲的旨意是次要的,编选者的主观精神则是主要的。”
四、对《玉台新咏》的评价
《玉台新咏》收集了齐梁时期大量的宫体诗,而宫体诗的声誉又不佳,故历代对《玉台新咏》的评价也不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玉台新咏》,既看到其不足,指出确有少数恶劣不足道的诗,同时也给予《玉台新咏》以正确的评价,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一)编选体例在文学观上前进了一步。金克木在《〈玉台新咏〉三问》一文中指出:“《玉台新咏》却在预定的内容主题范围之内选诗,由‘古诗’、乐府诗起,大体照时代排。卷三到东晋,卷四至卷六已到梁朝,卷七才专选梁武帝萧衍等帝王的诗,卷八选梁朝诸臣的诗。卷九是七言诗,兼收四言,六言,杂言。卷十是五言绝句。仍大体照时代先后排列。很明显这是有文学史和文体史眼光的排列顺序。”“他编选的诗的程序系统显出了诗的发展路线:乐府诗—拟乐府诗—古体诗—今体诗(宫体诗)—杂言—七言诗(歌谣)—五言绝句(歌谣)。”“全书提供了文体,文学思想以至文化的系统排列资料。这是历史发展的本来系统,但如果编者毫无见地,就不会这样收录。”[11]穆克宏认为,“《文选》不选录生存者的作品,而《玉台新咏》五、六、七、八这四卷所选都是当时文士的诗歌,这种做法不同一般,也是比较大胆的。”[5]
(二)《玉台新咏》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不但在当时没有先例,就是在以后几百年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也非常少见。金克木认为,对待妇女的态度,“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内容。《玉台新咏》正是这点上集中了我国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止的诗中的妇女表现,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这书不是只表现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思想,反而包含为妇女申述怨恨的思想。”[11]周建渝认为,《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妇女爱情诗歌专集的前例,为后世同类诗集导乎先路,这自然有其进步的作用”[10]。历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如《孔雀东南飞》等,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三)可以用《玉台新咏》校订其它古籍。《玉台新咏》成书在梁朝,当时编者能够见到的古书,后来有许多已散失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它来校订其它古籍。《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一》曾指出:“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又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作汉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魏文帝作,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无名氏,据此知为枚乘作。《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亦无名氏,据此知为蔡邕作。其有资考证者亦不一。”穆克宏、周建渝均持有这种观点。另外,王仲镛在《徐庾文学评议》一文中认为,“由于有了《玉台新咏》作为《文选》的补充,使我们对汉朝的诗歌发展,得睹其全貌”[12],进一步强调了《玉台新咏》的考证作用。
(四)《玉台新咏》因其独特的风格和内容,后人将其称为“玉台体”,对古典诗歌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章必功认为:“玉台体具有宫体诗的一般优点,诸如描摹物色的逼肖,遣词造句的新颖,对仗的逐渐工整,音韵的日趋和谐等。”“玉台体中有一类取材娼妓的诗歌,这类诗兴于南朝民间,梁代文人学而拟之,原是玩东施效颦的游戏,但经过玉台体的张扬,促进了后代文人对娼妓生活题材的注意和开拓”,后人“正式起用‘绝句’的名称并成为诗歌的一种体裁,则始于《玉台新咏》”[9]。周建渝认为, “《玉台新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西汉诗歌到梁代‘宫体诗’这六百年间我国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此时期诗歌语言由古朴渐尚华丽,且渐重对偶,用事,声韵渐趋和谐,五言诗体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七言诗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0]
(五)在描写女子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玉台新咏》800多首诗篇,都是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 这本身就是对妇女的重视。其中,许多关于妇女‘颜色,衣服,心灵,舞姿’等的描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美的一种赞赏,是编撰者的先进妇女观的表现。”(姚晓柏,《湖湘论坛》,1996,2)
栾晓平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玉台新咏》对妇女的歌咏,一是对女性的赞美,不只限于歌舞、体态、才情等的赞美,有的表现了女性人格的尊严,赞美了坚贞不屈的女性。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二是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如《上山采蘼芜》;三是对重男轻女观念的捐弃,如左思的《娇女诗》;四是对爱情的赞美,内容上有情深意笃、浓情蜜意的情爱,有离别愁绪、悱恻缠绵的相思,也有恋情阻隔、幽锁深闺的忧怨等。
歌咏爱情是《玉台新咏》一个重要方面。周禾在《试论〈玉台新咏〉的思想价值》一文中指出:“《玉台新咏》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所收录的爱情诗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这些诗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面貌,而且具有较强的人民性。”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首先,《玉台新咏》中的爱情诗反映了古代恋人们细微、复杂而强烈的种种思绪”,“其次,婚姻和家庭是爱情生活的重要内容,《玉台新咏》所收爱情诗也反映了当时这方面的各种情形”,“另外,《玉台新咏》中还有一些专门描写妇女容貌、情态的诗,这些诗虽然有的带有色情成分,但是也有写得较健康的。”[13]
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玉台新咏》,是研究方法的新突破。祝菊贤的《论〈玉台新咏〉的女性化审美特征》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认为,“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价值,这是多情而又生活封闭的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特征。《玉台新咏》正是‘爱’的主题的集大成。”“生命的全部价值回归、维系于绵绵情爱,男性开放的情感世界也逐渐靠近女性封闭的情感世界。这是女性化审美心理对《玉台新咏》中诗歌审美情感的重要影响。”从描写的内容看,作者指出:“‘爱’的象征就是‘春’,《玉台新咏》女性化审美特征的表现之二便是充溢了诗歌中多姿多彩的春天的意象。”“《玉台新咏》女性化审美心理的另一表现是诗集中大量出现以风花雪月与闺帏之物构成的诗歌意象。另外,《玉台新咏》中诗人酷爱写夜与月的意象。诗人对象征女性的夜与月具有特殊的兴趣。”[14]作者还从意象和语言形式方面论述了《玉台新咏》的女性化的审美趣味。
金克木指出:“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些以妇女为主题的诗的两重性。表层是妇女,深层是文人,因为两者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处境和心情类似。”[11]姚晓柏也指出《玉台新咏》中“以美女的不幸针砭时弊,比喻怀才不遇、忧国伤时的遭遇”。如何看待这种性别角色的游移和反串?王玫在《宫体诗现象的女性主义诠释》一文中指出:“宫体诗人时而以局外人的眼光窥视描绘女性的一举一动,时而在诗中自充女性角色,抒发伤春迟暮相思之类的感慨。作者在男性与女性角色之间反复游移、反串,获得某种满足,将女性作为梦幻偶像,进入女性特有的自足状态的本能需要,使他们试图一体兼具两性。如果用卡米拉的话说,男女性别角色的游移和反串不仅是人们深层的心理需要,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卡米拉的解释是,‘外化’是男人的宿命,男人总需要某种外在的东西,需要一个‘他者’,才能使自己完善起来。男人成为艺术家,便可进入女性特有的自足状态。由此她得出一个结论:艺术是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结合,是阴阳的调和,所以艺术也是雌雄同体。”[15]王文虽然论述的是宫体诗,但从中也可窥见《玉台新咏》中性别角色游移和反串的意义。
(六)近年来研究者们给予《玉台新咏》应有的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玉台新咏》存在的糟粕和不足。隽雪艳指出:“《玉台新咏》比其他诗文总集更集中地收录了一批轻靡、艳丽的作品,其作者主要是以梁简文帝为代表的梁宫体诗人。他们醉心于描绘女性的容颜、服饰、体态、舞姿以及寝室的枕、席、衾、帐等等,感情极不健康,趣味比较低下。”[4]栾晓平指出:“《玉台新咏》艺术上也有许多不足, 如有的诗歌偏重于形式的铺张,形式游离内容,有的则故弄玄虚,操险执惊,也有的卖弄才情,做文字游戏。”
重新认识和评价《玉台新咏》是一项复杂而严谨的工作。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念体系随时间、地域、社会、阶级、阶层、群体而不同,一些认识也不同。同时,《玉台新咏》本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以两性情爱作为生命主要价值和讴歌对象的“玉台”文化与老庄道家文化的清静无为、归根反本之间的关系等等,还有待于文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地研究。
收稿日期:200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