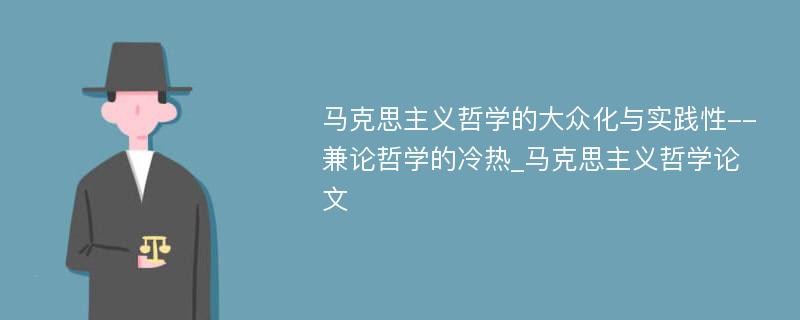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与实践性——兼谈哲学的冷与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一部分青年人中的所谓信仰危机,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淡主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理解,不感兴趣,甚至拒斥。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怀有某种忧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是有益的,但用以总结的哲学原则应该是正确的,否则很可能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一、应该面对群众,宣传群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宣传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多次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如此。“学习哲学,终身受益。”是陈云同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言。江泽民同志曾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学习哲学,最近又提倡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尽管如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青年一代所掌握,还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宣传和教育过程。
意识形态领域正如经济建设领域一样也是充满曲折的,其中在宣传和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确有许多教训。例如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学哲学热潮,其用意是好的,是为了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但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而且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处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成果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偏颇。这些都是应该认真总结、切实改正的。但把“君临一切”“指挥一切”作为教训,很容易使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面对群众,也不应处于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面对群众、宣传群众,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历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他们的思想对人类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的信仰者和研究者人数不多。全世界有多少黑格尔主义者?一百、二百就了不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由少数人的哲学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像对待德国古典哲学那样来对待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是忘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面对群众,宣传群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时就确定了的原则。他们非常重视向工人宣传自己的理论,决不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而采取蔑视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突出地表现在它与人们的实际活动、与各门科学研究活动的联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用”中才表明它是“有用”的。割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的联系,把它从实际活动和科研活动中排挤出去,就是把它变为无用之物,最多是一种“偶像”。
我们决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认识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出解决一切问题的结论,责任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自己的无知。认为一切结论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申出来,这是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它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来源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意志论;“文革”中打倒一切、否定传统,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等等,更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不能把过错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
我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应该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青年一代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很值得赞扬的。不过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强调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端正思想路线,证明此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做到“指挥一切”,否则何必拨乱反正呢?
其实,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造成的错误,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和“形象”。马克思说过一段话,用在此处特别贴切。他说:“就好像汽锅爆炸(结果使一些乘客血肉横飞)这种个别情形不能成为反对力学的理由一样,某些人不能消化最新的哲学并因这种消化不良而死亡的情形,也不能成为反对哲学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4页)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倡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决不是相反。
无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是冷一些。但不能认为“今天哲学的冷遇便是‘发烧’后所表现出的虚弱。”任何一个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接触过学生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至少有三点是起作用的。第一,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很不够。它没有着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着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教条地停留在一般原理的照本宣科上,使学习者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功能,从而大大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第二,就业问题是决定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专业的选择并不完全代表兴趣,而更多出于毕业后的考虑。热门专业,收入高,就业容易,对学生们有很大吸引力。第三,更重要的原因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到严重挫折,使马克思主义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我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一定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放光辉。
二、应该面对现实,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决定她必须面对群众,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教育我们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决定她必须面对实际,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中关系最为重大的改革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改革。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但决不是什么浅层次的问题。从哲学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决不是什么“赶时髦”。如果置关系到12亿人口命运和前途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于不顾,而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专注研究什么“人的形而上学本质”之类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哲学主张我很难赞同。
康德和黑格尔不研究商品经济,不能成为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哲学问题的根据。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都始终停留在思辨哲学的领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页)而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纯哲学领域,而是由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从而突破了思辨哲学的传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巨著《资本论》,既是经济著作又是哲学著作。谁都不敢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降低了哲学的品格。依我看,在当今中国,谁要是像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写出《资本论》那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谁就是有真正贡献的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它不能成为我们今天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的样板。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使其整个体系处在概念的范畴的阴影王国之中。马克思曾经批判过它的这个缺点:“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充分吸取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但不能沿着它的足迹前进,像它那样面对概念、范畴,精心构筑自己的体系,而是要面对现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面对现实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面对客观存在着的重大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科学,没有对问题的思考就不需要哲学。“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所谓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就是指它捕捉住时代的普遍的、重大的问题,从时代高度,把人们在实践中和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凝集在哲学思想之中。
哲学问题来自时代的实际生活,即特定时代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重复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来自人的抽象本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所谓“形而上”,把“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说成是处理人作为经济动物和人作为形而上学动物的矛盾,实在高深莫测,令人如坠五里雾中。
人和人的本质问题当然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不能把哲学对象归结为人与人的本性,特别是归结为对人自身抽象本性的研究。正如迁出神庙抛到荒野的神像不再是神而是木偶一样,脱离社会及其环境的人不再是人,而是两足动物。人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己的质的规定性的。马克思说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了奴隶制,就没有奴隶主与奴隶;离开了封建庄园制,就没有领主与农奴;离开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没有资产者与无产者。所谓人自身所固有的本性,除了通过遗传获得的生物特性外全都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即使是人的生物特性也经过社会的再铸造,不能归结为动物本能。
正因为哲学中的问题不是植根于人的抽象本性,而是来源于时代,正因为问题和考察问题的方式都是依赖于时代的,因此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哲学的时代性,表现在不同时代所着力探讨的哲学问题不同。例如在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中,自然哲学处于支配地位,着力于世界本质的探讨;中世纪由于宗教和教会的统治,哲学致力于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论证;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许多大哲学家如洛克、康德等致力于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研究;同时由于对社会认识的要求,历史哲学也悄然兴起。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哲学的中心,分析哲学则致力于语言和逻辑的研究。哲学对时代的依赖性,对于每个民族而言则表现为民族性。由于阶级对立是进入奴隶制以来时代的重要内容,哲学还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哲学代表人物着力探讨的哲学问题不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
哲学不可能是超功利主义的。虽然哲学由于它自身的特点,往往觉得它与利益无关,是在纯概念王国中驰骋,其实并非如此。哲学是以哲学方式实现它的功利主义,即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恩格斯说:“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0页)在德国古典哲学那“迂腐晦涩”、“笨拙枯燥”的语句背后,恩格斯都看到了“隐藏着”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是隐蔽的功利主义,是不承认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公开地、鲜明地倡导革命功利主义原则,把自己看成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宣布哲学的目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相结合的。恩格斯说过:“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在取得政权之后,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不能叫狭隘功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既是功利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自身就包含革命功利主义,即包含对无产阶级和人类根本利益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利主义”,不仅在于它为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服务,而且表现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锐利的认识武器。各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中获得“效益”。
事情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哲学境遇越来越困难,是由于狭隘功利主义造成的。在我看来,刚好相反。如果我们哲学工作者关注现实,写出《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如果我们哲学工作者能真正实现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经验,提供新的哲学方法,而不是停留在重复一般原理上,或者进入虚无缥缈的哲学太空,我看感兴趣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困境,走出低谷的道路,是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我们要有人专门从事所谓纯哲学的研究,即研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但这种研究也必须结合人们实践中和科研中提出的问题,观点要真、结论要新,而不是年复一年地重复基本原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另一方面,也要有人在应用中求发展,结合研究各门具体科学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当然应该淡泊名利,潜心学问,耐得住寂寞,但不能走历史上某些哲学家的道路,即远离闹市、隐居农村、隔绝人世、背对现实的哲学道路。在当代,这做不到,也不能做。恩格斯曾经为隐居乡村而限制了自己哲学思维的费尔巴哈感叹不已。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开这种处方实在不妥。
三、要正确把握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我们遵循的哲学原则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沉湎于对人的抽象本质的哲学思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决不能归结为人的本性是“形而上”,动物的本性是“形而下”;人的本性是“追求理想”,动物的本性是“追求功利”。这种说法令人困惑难解。
人的需要当然不同于动物。人的需要有其生理基础,但人的需要既不能仅仅归结为生理结构,也不能归结于人的所谓形而上学本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求的内容不断丰富。为什么人们“在吃好、穿好的同时,还要看演出、听音乐、外出旅游呢?”这当然不是由于人的“超功利的”“形而上学本性”,而是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引起的需求层次的变化。现代人和原始人,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富人和穷人的需求的内容和层次的差异性,离开了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从人的所谓超功利的本性中是得不到科学说明的。
人与人的关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社会关系;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关系。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某种自然关系,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但这已经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关系。因此,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人与动物的区别决不能离开这个基点。为什么“人比禽兽还要野蛮一千倍、一万倍”呢?为什么某些动物之间的斗争最多是单个的或成群的撕咬,而人却“发明越来越先进的武器成百成万地杀人”呢?把这归之于人对自己“思维能力”和“文明”的“误用”,归之于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不能认为是合适的解答。
在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斗争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各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以及革命时期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决战;另一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同被侵略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深刻的根源是物质利益,阶级斗争的核心是阶级利益,国际战争的根源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主要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没有利益冲突就不会有大规模的相互“残杀”。即使以文化冲突、宗教信仰冲突形式出现的战争,深层次的东西仍然是物质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利益问题是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进行过无数次国内战争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大规模地相互残杀,这决不是理性的迷误,而是私有制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当前,人们可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决不能消除一切战争。事实上,世界上战争不断。决不可以认为只要考虑到人的“超功利的理想的要求”,不考虑“功利的方面”,向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发出呼吁,就可以制止或消灭人类的相互残杀,这是不可能的。
同样,从人的所谓超功利的“形而上学”本性出发,也无法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的出路。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人在客观世界中处于双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中,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页)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考虑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撇开另一方面。不能离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从人的本性而不是从生产方式中探求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有点偏离。
动物与环境的所谓平衡是不值得羡慕的。因为这种平衡的主导方面是自然,通过自然选择使不适宜环境的生物品种灭绝或迫使它变化。这种“平衡”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对它们自己而言,代价是巨大的,是“残酷”的。当然,人类实践活动造成的结果有时确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这决不是说,如果排除人为因素,它们就是没有矛盾的“极乐世界”。
人类的发展也如此。人类社会早期决不是人与自然平衡的时代。当时人类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人对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动物般依赖之中。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为自然创造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自然环境。尽管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它不可能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但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生态环境恶化。资本主义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建立的相对平衡。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从对自然界的改造中受到日益增多的惩罚,最终导致引人注目的生态危机。这个原因并不在于人类“没有考虑到超功利的理想的要求”,而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对巨大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运用的目的和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相反,只要运用得当,它为克服生态危机、改善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的、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化不能归结为人性问题。克服这种危机的动力,也不能指靠超功利的理想,相反,恰好是来自最大的功利主义,即来自人类对自己生存还是毁灭的自觉认识。
科学家同哲学家有相似之处。对于科学家而言,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责任。有幸而从事科学研究,进入科学殿堂,这表明了他承担的社会义务。对于我们国家的哲学工作者也应该这样要求。哲学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思辨,而应该看作是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提高民族素质和思维水平服务。我深信,尽管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但繁荣我国的哲学事业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