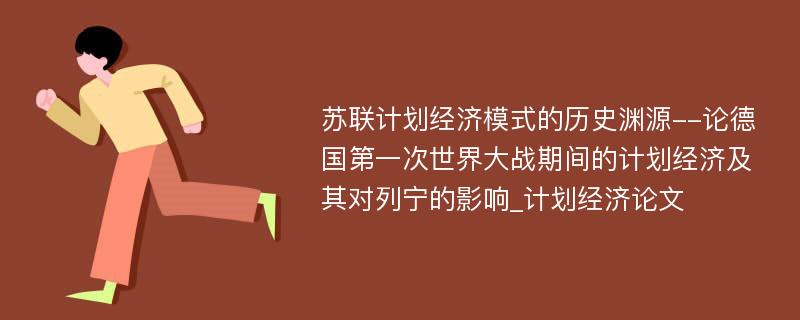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经济论文,苏联论文,德国论文,列宁论文,原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3—0064—07
在目前关于高度集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照抄照搬;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反映。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都忽视了两个具体的重要环节,一是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二是“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历史上第一个“被隔绝的战时计划资本主义经济”[1](P415)。这两个环节相互结合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分化,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开始现实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
“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历史条件地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1893年5月,恩格斯在与一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2](PP628—629) 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试图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最终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对于19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在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理解上形成分歧。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3](p210)。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化,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跟着出现了分化。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4](p567) 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开始向自由主义偏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计划问题上的细微变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两种状态,经济上,社会主义是“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主义”[5](p145、p200)。由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修正主义”的理解,包括“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在内的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开始变形,只要是“为社会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至于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社会生产是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核心,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过时了。相反,“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上的增长”,其中包括工人“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6](P318、P358)。在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学派的理论逻辑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开始向抽象的“社会性”偏斜。比较而言,考茨基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地设想过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需要充分的社会化和计划,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考茨基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二是认为货币经济不会很快消失,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在更好的替代品被发现之前是必不可少的[7](pp365—366)。考茨基的存在着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形,那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二者却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党纲在表述未来社会的经济蓝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经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们。”[8](P36) 1906年,列宁第一次把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概括为“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使用:“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9](p124)“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坚持并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经典设想,但这一时期列宁关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是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实践意义。这正如布哈林后来所说的,革命前“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问题”[10](p63)。但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历史和政治信念无疑已经植入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了,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理论上一个鲜明的特征。但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却是“完全独特的、使西欧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陌生的特征”[11](p61)。
二、“一战”期间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如果说,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还是隐性的,那么,在面对“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战时计划经济时,这一认识上的分化就开始显性化和进一步扩大。
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走上了一条国家主导下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高度资本集中和垄断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政治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工业化道路。在这种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支撑下,“一战”期间的德国很快就建立起了同一时期的英法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完备的战时计划经济。
1914年8月8日,德国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前者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后者下属59个军需公司,专门管理征集和分配各种工业原料,把重要原料和货物优先给予垄断组织。“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分配稀缺原材料方面便需要研究出一套系统性的优先顺序的标准,从而迫使人们要有某种程度的先行思考,也就是要对未来的消费结构作出某种计划性的安排。”[12](p270) 除了对生产需求的计划外,由于战争造成的普遍饥荒①,德国先后建立起了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帝国谷物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这样就把人们基本的消费需求也纳入了政府计划管理的轨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计划机构。对此列宁曾高度评价说,德国“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13](p254)。
战时德国能够把基本生产和消费逐渐纳入计划管理之中,其“经济基础”在于对企业和劳动力的政府管制。1915年,德国通过了一个卡特尔化法律,进一步促进了战时德国主要工业经济垄断组织的发展,强化了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的手段。1916年德国颁布了《兴登堡纲领》,规定劳动力不能随意流动,一切工业生产必须首先服从军事需要,从而为战时计划机构的运转提供了必需的前提条件。对企业和劳动力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已经使经济发展脱离开了市场利润的导向,转而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生产。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战时经济一样,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最初也是出于战时的临时需要,但是在这种需要中最终发展出国家控制经济的一种新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确立起了政府对经济的支配作用,使经济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意志。由此,德国战时计划经济最终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发展特征,成为国家管制下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源地。虽然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但战时德国的计划经济却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出现了分化,因此在面对“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战时计划经济时,他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考茨基坚持否认这里面有任何可以向社会主义引申的因素。1918年3月,考茨基在一篇探讨过渡经济的文章中认为,过渡时期有两种意义,一是从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过渡,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对考茨基来说,能提上日程的只是第一种意义上的过渡经济,“从理论上探讨第二种意义即较复杂意义上的过渡经济,目前还为时过早,尽管它对于我们西欧来说也可能不久就具有实践的意义”[14](p251)。1919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鲍威尔也在一篇论著中否认在战时经济的基础上有进行计划经济尝试的可能:“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长,对民主制度可能是一种危险。”[11](p76) 但对列宁来说,问题却截然不同,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经济桥梁。霍布斯鲍姆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15](p65) 其实这不是“多少师法”的问题,在20世纪初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出现分化的背景下,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扩大这种分化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联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开始把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选择结合在一起。
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首先,支撑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共保存了1915—1916年间的20本笔记和其他一些札记,从这些材料的题目上看,直接与德国经济有关的大约是23份,而直接与英国有关的大约是9份,法国是7份,美国是6份,俄国为5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表明了反映德国经济发展的材料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同样,如果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主要材料进行统计,可以看到,在该书最重要的前五部分中(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列宁引用的反映德国经济和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观点的材料大约是33处,而同样的数字美国大约为11处,英国大约为4处,法国大约为6处。这同样说明,反映德国经济的材料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是其他材料无法相比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直接就是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当然在列宁看来,德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特殊性,“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16](p336)。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这种材料状况,一方面如同列宁本人所说的,是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与大战开始后列宁心目中的一个深层疑问有关,即如何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战争中对国际主义的背叛。英国历史学家多纳德·萨苏认为,当时“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号召工人进行普遍罢工来反对战争,那么,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将不会采取如此好战的立场”[17](p29)。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来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成为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超额垄断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16](p416)。因此“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18](p74)。在列宁看来,这就是大战开始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深层原因。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把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提升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带上了鲜明的德国特殊历史背景的烙印。
其次,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直接的体制参照。列宁在很多情况下把对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程度的论证,放置到对德国战时经济的审视上。“在德国,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由一个机构领导6600万人的经济生活,由一个机构组织6600万人的国民经济。”[18](p249) 列宁对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认识中,蕴含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受饥饿和战争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18](pp348—349) 在列宁看来,包括德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不自觉地实行了“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13](p53)。这些措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出来的一条历史道路。因此,列宁激烈地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试图把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的观点。里塞尔在1910年出版的《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德国生产和银行业的集中状况,但里塞尔并不认为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他说:“社会主义者所预测的集中运动的另一个后果,即最终将导致他们所希望的和应当在‘未来的国家’内实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后果,在德国并没有实现,今后也未必能实现。”列宁把里塞尔称作“资产阶级的白痴”,因为“单是德意志银行就有945亿马克的周转额,它与一个由12家银行构成的集团有联系,支配着十亿马克的资本,它吞并了52家银行,在德国有116个分行、存款部及其他机构,——在120家工商业公司的监事会中占有席位,等等。这还不是社会化!!!!!!”[19](pp401—402)。罗伯特·伯夫曼也在1915年出版的《战争是不是使我们接近社会主义?》一书中反对关于战争促进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战时实行的税收、垄断、面包配给制,所有这一切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外。对于伯夫曼的这一观点,列宁认为这“都是些庸俗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道理”[19](p837)。根据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蓝本,十月革命前列宁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突显出了俄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参照,这种参照点主要聚集在强迫辛迪加化,普遍的劳动义务制与国家对经济的监督和调节这几个方面。
1917年9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针对在实现了银行国有化和辛迪加国有化后未来的经济组织管理问题,列宁写道:“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13](p251) 对于劳动力的问题,列宁则认为:“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13](p267) 在大战形成的条件下,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带有活生生历史内容的问题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从对国民经济“反动官僚的调节”向“革命民主的调节”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因此,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从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13](p199、p202)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反驳“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国家政权”的责难中再次强调:“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如果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新的国家组织,“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13](p300、p297)。显然,在列宁对国家集中行动作用的强调中鲜明,地体现出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中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对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②。
归纳前面的论述,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影响,即列宁不是从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般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高度来理解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战时计划经济的建立,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熟到可以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根据,由此列宁把德国和俄国比喻为“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13](p526)。其次是体制意义上的影响,在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中体现出来的以国家力量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蓝图设计提供了直接的体制性依据。列宁以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为原型,描绘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设想[20](pp107—111),无论从后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中,这一设想的支撑作用都很明显。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具有历史原点性的制度影响。
三、正确认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历史原点的理论意义
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分化的理论背景下看,完全有理由把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看作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正确认识这一“历史原点”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到后来的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再到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历史逻辑的体制运动,因此,决不能仅从经典文本来解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如同计划经济的确立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过程一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也是一个具有自身内在历史和逻辑自恰性的完整制度变迁过程。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非历史的文本性认识,会直接导致对市场经济改革的非历史主义理解。
第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这一思想尽管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原初的思想背景,但无论在历史还是逻辑上它却都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直接原点,因此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衰落中走向改革,并不能证实这一思想的无效性。实质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并不是矛盾的。
第三,从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的双重影响来看,不管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计划经济中政治内涵的比重远远大于经济内涵,这一点在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可以说,它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在的本质性特点。苏东国家在长期的经济改革中正是忽视了这一特点,导致改革成为一种内卷化的周期运动,即体制效率的下降推动着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谋取经济效率的技术性工具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但市场经济本身却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当市场经济在扩展的过程中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冲击时,在集权性旧体制的反压下,市场化的改革也就停止了,“从而使得体制在其权力结构发生微小变化的情况下获得了稳定”[21](p199)。长期的周期性改革使改革的效益递减,改革的成本递增,改革的空间缩小,最终苏东国家丧失了领导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能力。这表明,对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政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能够走多远,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能够走多远。
注释:
① 1914—1918年间,德国共有75万人饿死(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仅1918年死于饥饿、疾病的德国人就有293000人(Stephen J.Lee,Imperial German,1871—1918,p.111.)
② 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与这一时期列宁对国家消亡的理解形成了明显的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含义出现了多重性。关于这一点可参Ralph Miliband,Lenin'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in Jeremy Jennings(ed.),Soci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2,Routledge,2003.
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帝国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