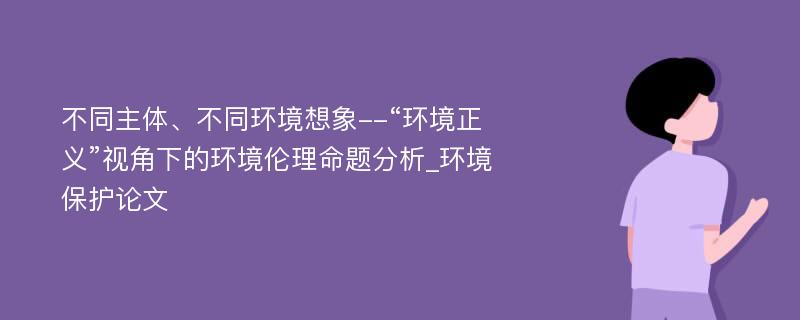
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命题论文,伦理论文,视角论文,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环境正义”:作为环境伦理命题的现实分析视角
当代环境伦理发轫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反思环境危机根源、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文化思潮。80年代,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干的环境伦理围绕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阐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伦理研究开始呈现出某种停滞的状态:在理论上各执一言、争执不下;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尽管形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伦理自身过分追求言说的自由和境界的高远而“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李培超语),是导致环境伦理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到了90年代,环境伦理对于环境危机给民众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全面恶化问题的忽视,使得它受到环境保护实践中一些现实问题的挑战,其中以由于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引起的“环境不平等”(environmental unequal)问题最为突出,并直接引发了“环境正义”运动。
所谓“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指人类社会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时,各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注:“环境正义”一词最初被使用时的含义与“种际正义”的含义相同,例如Peter S.Wenz的Environmental Justi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一书,主要探讨的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原则的可能性。而自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爆发之后,“环境正义”一词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原则”的含义渐渐被“种际正义”所代替,而让位于“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本文主要使用“环境正义”一词的后一个含义。)这一思想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中,针对美国因环境因素而引发的社会不正义问题,特别是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问题而提出的。由于“环境正义”思想所强调的环境利益在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分配问题,正是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要理论基础的环境保护实践长期缺乏关注的领域,所以一经产生,不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成为反对环境保护中的不平等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
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在1991年10月草拟的17项环境正义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环境正义”的基本信念。根据这些基本原则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正义”不仅涵盖了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而和谐地对待到各种消除政治经济不平等的要求与行动的广泛环境议题,并且在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在强调人们应该消除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的同时,肯定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生存及自决权也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向度。也就是说,“环境正义”一方面关怀被人类破坏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更认为,强势族群和团体能够几乎毫无阻力地对弱势者进行迫害是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
“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和“环境正义”的一些重要的思想,从现实的角度为我们今天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对当代环境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当代环境伦理仅仅强调种际正义,代际正义不同,“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与当代环境伦理强调集中讨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不同,“环境正义”更关注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当代环境伦理将环境保护实践聚焦于自然不同,“环境正义”将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作为当前最需要保护的重点;与以当代环境伦理为指导的西方主流环境保护实践单纯强调保护自然不同,“环境正义”强调在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破坏在这种环境下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人们的生存;与当代环境伦理以西方世界观作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不同,“环境正义”主张透过不同的思想资源对环境危机进行评价。
本文将通过“环境正义”的视角,对当代环境伦理作为主要目标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进行尝试性分析,对这一惯见的表述给出不同的解释。
二、有差异的主体
1.“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环境正义”对环境伦理全称命题的分析
在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的各种论述中,经常出现“人类”、“我们”这样的全称名词,它们往往作为不可分隔的整体概念被使用。当代环境伦理正是要站在人类这个类主体的角度上,对以往的价值观念展开自省、批判和前瞻。但是,面对当今的环境危机,人类真的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主体吗?持“环境正义”观念的人对此提出质疑。面对环境伦理中无差别主体的表述,“环境正义”提出:“谁是‘人类’?谁是‘我们’?”
“环境正义”认为,环境伦理所强调的环境危机后果的普遍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正确的。现实的问题是破坏环境的人往往并不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样,掠夺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强势人群也往往并不需要担负生态危机与自然反扑的后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担负)。环境破坏的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或群体的头上。以污染为例,尽管在环境伦理的理解中,污染问题是超越地区和国家界限的,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社会废弃物如垃圾、废料等,并不是平均地散布在所有人的生活领域中,而是遵循两种最常见方式——方便原则和最小抵抗路径原则被处理。“方便原则”是指废弃物制造者将废弃物任意地排放、丢弃,让这些废弃物的生态后果由地区、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对象来承担。而“最小抵抗路径”原则是指废弃物的制造者将废弃物丢弃在特定的地点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领域。这些最小抵抗的特定地点,一般而言便是偏远地区,包括地理位置上的以及文化位置上的偏远地区;而特定人群,则常常是各种弱势族群和贫穷社区。这些废弃物、尤其是有毒废弃物(有时甚至是核废料),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活、生存环境,更影响了当地人的健康与生活。(参见Bullard,p.4)正是基于后一种原则进行的有毒废料处理方式,引发了瓦伦县抗议,并成为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导火线。可以说,社会中强势者在对自然和弱势者进行着双重的压迫。
“环境正义”提出,虽然利用自然是人们普遍的生存方式,但是对自然的利用却在目的上存在着维持生存和攫取财富的根本不同,即存在着满足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和基于欲望的需要的不同。环境伦理将人类视为不可分隔的整体,而无视不同种族、地域、性别、阶级等因素的不同需要。其结果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多数人继续消耗全球大量资源与能源来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们仍必须以危害生态的消极方式来达到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正如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伐木工所说的那样:“我知道继续砍伐树木可能会导致地球的毁灭。但是如果我停止砍树,我可能明天就会饿死。”
“环境正义”还指出,环境伦理强调的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更多地表现为强势国家、地域或群体的利益。在当今社会现实之下,将人类特别是当代人视为不可分整体的做法,将会藉由“共同的需求与命运”、“共同的目标”的名义,掩盖或忽视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及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对抗性,使环境保护成为一句美丽的空话或一种不公正的暴行。
另外,从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角度看,单纯强调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也掩盖了当代环境危机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生态扩张的结果这一事实,淡化了其对解决环境危机和补偿对欠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损失这些问题上应该承担的义务。实际上,无论是1993年召开的里约会议,还是1999年召开的京都会议,我们都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提出自己环境保护主张(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全球变暖)的同时,极尽所能地将欠发达国家歪曲丑化为导致环境恶化的首犯,从而逃避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或补偿。
基于此,“环境正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对于所有人的环境问题。“所谓的环境问题,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影响,这当中,一部分人是受害者,但也存在着一部分受益的人。”(洪大用,第242页)环境伦理在使用这些单一、全称名词的同时,实际上谋取了与他们有差异的种族、阶层或性别团体的代表权,使之被湮没在无差别主体的抽象论述之中。正是出于对这一举动的严厉批评,台湾学者纪骏杰指出:“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第141页)。 一个埃塞俄比亚或印度的穷人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未来绝对是不一样的:对前者而言,他的未来可能仅仅是下一餐或明天的粮食在哪里。此时,我们不得不问:“环境伦理代表的是谁的声音?是衣食无忧者的闲适无着的感叹,还是衣不果腹生计难维者的愤懑?是为可持续发展辩护,还是为可持续的不发展执言?”(李培超,第160页)
2.环境保护运动主体的差异性
那么,环境伦理是该从虚拟的“人类”出发,还是应从现实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出发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呢?
基于环境问题对不同主体产生影响的差异性,有研究者对社会中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权力关系可以区分为四个不同的权力范畴:首先是居于最强势地位的、追求经济高度增长、提出对自然进行合理有效利用的第一主流论述;其次是相对于前者较为弱势、从价值观念的深层根源反省生态危机的第一边缘论述,也可称之为第二主流论述,因为相较于偏僻边缘地区的居民,环境保护论述的社会影响力是比较强势的;第三则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发生冲突时无力申诉、亦无力改变现状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居民,他们是最不被重视也是最没有影响力的一群,所以称之为第二边缘论述;最后,在人类中心的构架中处于最最被压迫底层的非人类、无法发言的其他物种与环境则处在第三边缘。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作为整体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具体为第一主流与环境的关系,第二主流与环境的关系,第二边缘与环境的关系。(参见连志展,第10-11页)9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为这种分析提供了生动的图解。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面对来自两方面的阻力:“明智的利用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它们与环境保护主义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处于第一主流的“明智的利用运动”代表着美国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受到环境保护直接影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处于第二主流的环境保护主义则具有明显的白人中产阶级色彩;而环境正义运动则是代表处于第二边缘的美国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和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参见侯文蕙,第5-8页)
而如果将当代环境伦理论述放在这一交错的关系中来分析,可以看到,环境伦理的论述基本上是以非人类自然及其生态系统的代言人自居,然后再进入人类社会和第一主流群体、第二边缘群体二者进行互动。当环境伦理的论述者在高举着生命平等或生物共同体的大旗反抗第一主流群体反环境保护的论述时,他们和第二边缘群体的关系将最终影响环境保护结果的成败。因此,当代环境伦理是与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合作,共同抵制反环境保护主义?还是环境正义运动与反环境保护主义的“明智的利用运动”合作,成为环境伦理所支持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阻力?能否成功地解决环境问题或许就取决于这种选择。因此,环境伦理到底将自己置于何种位置,值得慎重思考。
三、不一样的环境“想象”
在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的论述中,环境被定位为自然环境(或称之为生态环境),它包括非人类的生物、非人类的自然物以及由它们共同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当代环境伦理对环境或自然的这种定位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西方科学和文化传统对环境(自然)的论述建构的结果。本文将从现代生态学和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对当代环境伦理中环境(自然)想象的建构进行尝试性分析。
1.“科学之眼”:现代生态学与环境伦理的自然想象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认知体系为人们描绘出不同的自然图景,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想象。而构成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对于自然的理解和想象基础的,是现代生态学透过“科学之眼”对自然的认知。随着人们对现代生态学知识的广泛接受,现代生态学以生态系统的形式对自然的展现,被公认为是一种科学地认识世界的方式。“在科学的论述之中,我们相信了一种‘纯净的凝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也因为这样的‘纯净’,使得科学的凝视得以建立对‘真实’的权威性,并压抑了其他的‘杂音’与想象,形成了一种‘沉默’的状态,而科学的凝视则成了惟一观看世界的‘正确’方式。”(福柯,第21页)
当代环境伦理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于自然的现代生态学想象之上。最早将生态学中“有机”整体的自然想象运用于环境伦理建构的是利奥波德。他将自然比喻为由不同的生命器官组成的机能性整体,指出:“至少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器官的零部件或动作协调的器官整体,其中每一部分都有确定的功能”(利奥波德,第42页)。他使用了现代生态学中生物共同体的概念并将之扩展至“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大地”。他认为,“大地并不仅仅是土壤,而是能量在土壤、植物和动物所构成的循环中流动的源泉。食物链是引导能量向上的通道,死亡和衰败则使它回到土壤。”(同上,1997年,第204页)可以说,利奥波德正是透过现代生态学的“科学之眼”完成了对自然的想象,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大地共同体的范畴,由此建构了一种维护自然整体性和完美秩序的“大地伦理”。
可见,现代生态学的论述在西方环境伦理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基于科学理性的自然观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西方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事实上,正如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所差异一样,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也存在着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一个当代美国白人中产者和一个土著人对自然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事实上,那些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许从未在土著居民的观念中出现过。
“环境正义”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以现代生态学知识中无人的“自然”概念作为对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基本命题中的“自然”的理解,实际上忽视了在不同文化中“非理性”的人对“自然”的不同的想象的存在,忽视了现实中一些社会文化下与人和谐存在的“自然”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权利上对其他自然想象的禁止。这种以抽象、疏离的“自然”来代替不同社会文化中具体的、活生生的自然的方式,可能正是当今环境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2.寻归荒野: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与环境伦理的自然想象
除了现代生态学之外,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是影响当代环境伦理的自然想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浪漫主义者眼中,充满活力和整体性的自然成为与工业文明相对立的质朴世界的象征,成为诗意人生的象征,成为他们执意追求的道德理想的象征。美国先验主义文学家爱默生认为,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不仅可以是“以简单的直觉观看自然的形体”而产生的美,而且更是从人们的理智活动出发来发现和探究自然之美,以及大自然通过与道德的关联而产生的完美无缺的美。(参见爱默生,第4页)反过来审视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浪漫主义思想中对自然的想象,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超验主义的精神气质,渗透在其思想和论述之中。
此外,浪漫主义思想与美国的拓荒历史相结合,使美国拓荒者的后代——白人中产阶级产生了对于自然的一种独特的“想象”,即荒野“想象”。
在当代环境伦理中,荒野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概念。它既指真实的受人类干扰最小或未受干扰的纯然的自然,也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的象征。最先提出荒野价值的美国思想家梭罗认为,荒野中蕴藏着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生机与活力。对于他而言,“希望与未来不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镇中,而在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抖着的沼泽里”,所以他主张“在荒野中,保留着一个世界”。(转引自程虹,第119页)而污染严重、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以及由此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上的荒原客观上强化了人们对自然的荒野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想象中的“‘荒野,虽然是个名词,却起到了一种形容词的作用。在特定的地点,它会在某人的心中产生一种心境或情感”(同上,第28页)。
罗尔斯顿在论证哲学为何要走向荒野时,将自己对环境的想象进行了如下划分:“有三类环境——城市、农村与荒野,提供了三种人类的追求——文化、农业与自然。所有三种追求都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应该从事的;而且所有三种环境也都是我们的福祉所必需的。”很显然,在他看来,荒野与当代环境伦理所要保护的自然之间是紧密相连的。罗尔斯顿还认为,城市环境是我们的“生境”,是文化的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地方;“乡村环境”则是指被人工驯化、用于支撑人类生活的自然,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与自然遭遇的地方”,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地方”。这两者都是人类所需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环境就是荒野”。(罗尔斯顿,第41-43页)这反映了当代环境伦理对自然(环境)的界定。
总之,无论是在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中,还是在美国人的荒野文化之中,自然都被看作是与人类、与社会截然不同的存在,而原始的、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自然才是它们共同的追求。而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自然(环境)对于处于弱势的国家、地区和群体来说,首先意味着生活和生存。而当代环境伦理由于受到浪漫主义文化传统对自然想象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是置身于“环境”之外的,它所表现出的过分追求意境高远而脱离现实的特点,具有了某种“中产阶级的偏见”(侯文蕙语)。
3.不同的环境想象:作为生活的自然和作为生存的自然
可以说,现代生态学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客观化的科学的姿态排除了其他自然想象的可能,将人们对自然的想象凝固化。浪漫主义文化则是以一种超验的态度和直观的方式,剥离了自然与生活、生存之间的联系,将自然看作是某种精神追求的象征,在客观上贬低和丑化了那些出于现实生活和生存的需要对于自然的现实理解。而无论是超然的想象还是超验的想象,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各种文化、不同人群对自然的不同理解。正如梭罗对于自然的想象是基于瓦尔登湖展开的,美国对于荒野的想象则是基于它的独特历史展开的,任何关于自然(环境)的想象都是基于某一地理位置、某一文化传统的想象。“如果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无法拥有精神上的支撑点。”(程虹,第15页)而在现实世界中,无论从地理分布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除了当代环境伦理所认可的作为精神追求的自然以外,还存在着作为生活的自然和作为生存的自然。
在1991年召开的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上,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就阐述了与西方主流环境伦理论述不同的环境观:“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转引自侯文蕙,第7页)这一见解反映了生活在美国下层的、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群体对于环境的想象。相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森林、荒野等属于白人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事务而言,他们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条件。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生活自身的全部。
第三、第四世界的土著人也具有与当代主流环境伦理不同的自然想象。他们说,“土地和森林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生命本身,对于我们的社区有一种整体的、精神的价值。它们是我们作为濒危人群的社会、文化、精神、经济和政治生存的基础。”("Charter of lndigenous-Tribal Peoples of the Tropical Forests")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与自然紧密联系的,自然往往是他们取得生活必需品的直接场所,因此,自然是这些土著人赖以生存的“居所”。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们与自然是一体的、和谐的,并不存在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经历过的人与自然的所谓对立,另一方面他们如果被剥夺了这种生产方式,等待他们的将是生存的危机。
基于以上的理由,环境正义“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还将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包含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关注不同主体对环境认识的不同和需要的不同。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当代环境伦理的自然观因其是建构性的,因而有其固有的狭隘性,只代表了一些人的利益和追求。不幸的是,这些建构起来的、基于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关于环境的想象,在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伦理中被赋予了普遍的意义,并且在环境伦理被普遍承认为价值“正确”的今天,抹煞了关于环境的其他想象的存在理由和真理诉求。
四、结语
透过“环境正义”视角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当代环境伦理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至少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方面,它藉由普遍的环境危机,用“人类”、“我们”这样的全称名词取得了有不同现实需求的群体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以抽象的“类”主体掩盖了现实世界中以及环境保护运动中主体的多样性,遮蔽了现实生活中有差异的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它所体现的西方科学和文化背景之下以现代生态学作为其知识基础、秉承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精神气质的某些阶层对环境的理解,将纯然的自然看作是对于环境的客观的、惟一正确的想象,并且往往在精神象征的意义上把握自然的含义,从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那些从生活的和生存的角度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忽视了不同群体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不同的环境诉求。而如果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用抽象的人类和抽象的自然代替环境保护运动中多样的主体和不同的诉求对象,那么必然导致当代环境伦理及其实践无法看到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模式,使环境保护实践有落入人与自然二分的片面保护的危险。
可以说,这一命题的缺陷对于当代环境伦理而言是带有根本性的。它既是当代环境伦理缺乏对现实关注的原因,也是当代环境伦理缺乏对现实关注的结果。正是这一抽象化、普遍化的缺陷,使得环境伦理将环境问题这样一个极具社会现实性的问题局限在道德形上的层面,使环境伦理缺乏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敏感,无法把握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中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缓解这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因此,通过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这一环境伦理基本命题进行的基于“环境正义”视角的分析,我们对当代环境伦理的发展报以如下的期许: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对于所有人的一般的环境问题,只存在不同地区和人群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生活和生存所面对的具体不同的环境问题。当代环境伦理要重塑现实情怀,就必须转变被抽象的“人类”概念遮蔽的视线,认识到现实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使环境伦理不至于在高呼保护环境的同时,却无视发生在身边的由于“环境不公正”造成的某些人群的生活和生存危机。其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统一的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以西方环境伦理为主体的当代环境视野中的纯然的“自然”,实际上是强调超然的现代生态学和强调超验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以及一些西方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当代环境伦理要想真正理解自然(环境),就必须摒弃西方视角和特定阶层的偏见,了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下人们对环境的不同想象,将作为生活自身的自然和作为生存自然的自然也纳入到环境伦理的视野。此外,由于存在着利益主体的差异和对环境“想象”的不同,所以在不同地理、历史、文化条件下存在着不同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因此,当代环境伦理及其指导的环境保护实践应该避免将所有现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将所有人都看作是自然的他者,将一些本是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生存方式评价为对自然的破坏,进入人与自然分离的保护的误区。
总之,当代环境伦理要想实现其为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可靠的道德基础与伦理支持这一根本目标,就有必要扩大其理论视野,夯实其现实基础,积极调整自身来对现实做出适时的回应;就必须认识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不仅要有对共同道德理想的勾画,还要顾及道德实践的现实可能,使其真正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生命力。从某种角度来看,“环境正义”所表现的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关注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正是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