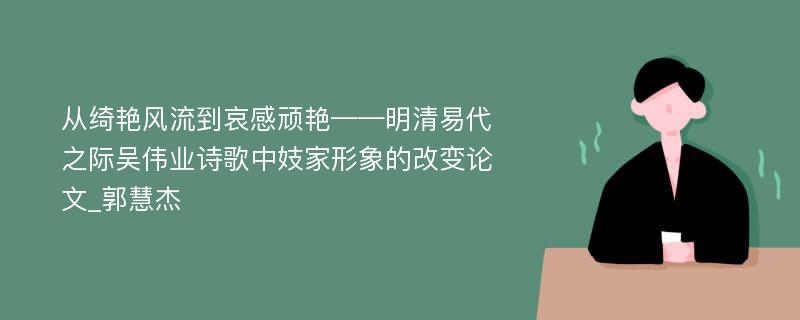
云南民族大学 郭慧杰
摘要: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以独特的“梅村体”叙事诗饮誉文坛,受晚明社会思潮影响,以妓家入诗成为吴伟业诗歌中常见题材。但明亡前受时代风气与个人经历的影响,妓家题材多绮艳风流,而到易代之际,妓家题材亦随鼎革之痛而沧桑。可见同样是以妓家入诗,因时代之不同与诗人心态的变迁,诗歌意蕴与妓家形象大不相同。
关键词:吴伟业;明清易代;妓家题材
明清易代之际,诗人吴伟业身经鼎革而诗风为之苍凉,以独特的“梅村体”叙事诗名冠 “江左三大家”之首。尤其是以《圆圆曲》为代表的长篇歌行体多以人物系兴亡,“存史”之余更以情韵为胜。这既是吴伟业借圆圆身世有感而发,也是诗人亲历鼎革之际的种种惨痛,对人事兴亡有了更深的体悟。以秦淮名妓的遭际叙说兴亡,并非吴伟业的独创,但无疑为吴伟业的创作增添了一抹凄艳绮丽的色彩。以妓家入诗,在其明亡之前的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赠妓郎圆》、《偶成》二首,及模仿齐梁乐府所作的《子夜》群歌都可视作吴伟业早期妓家之作的代表。在这些诗中,妓家的形象多轻浮靡丽,与历经沧桑变故后的《圆圆曲》相比,无论是在对女性的认识还是诗歌内涵方面皆不及后者哀艳婉转、寄寓良多。大致来说,吴伟业的艳情之作多作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左右,而《圆圆曲》等歌行体产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前后。朝代的更替使诗人饱经患难多舛,同时也使他的创作更为真挚哀婉,并以一系列成就极高的“梅村体”叙事诗饮誉文坛,奠定了明清之际最重要诗人之地位。
一
晚明素有狎妓之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士子们大多风流倜傥。教坊妓馆们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爱好,特意培养了一批色艺皆佳的名妓,这些名妓不仅情趣上较为高雅脱俗,而且多精通琴棋书画。以才学闻名的吴伟业跻身名士之列自然深受当时风气的熏染。故在明亡之前,吴伟业也曾有过诗酒风流的岁月,并留下了若干狎妓生活的艳情之作。其中有赠送妓家的《赠妓郎圆》:
清靴窄袖柘枝装,舞罢斜身倚玉床。
认的是侬偏问姓,笑侬花底唤诸郎。
此诗以男性的视角去观赏妓女郎圆的娇媚与体态美,充斥着浓浓的脂粉气与轻佻之态。
另有《偶成》二首,亦是留恋青楼之作:
其一:好把娥眉斗远山,细蝉金凤绿云鬓。画堤无限垂垂柳,输与楼头谢阿蛮。
其二:海棠花发两三枝,燕子呢喃春雨时。恰似栏杆妖欲醉,当年人说杜红儿。
全诗以静态写妓家的美,风格上也较清丽芊绵,但缺憾在于景多于情,妓家的形象是泛泛而模糊的。诗人用大量的景物烘托妓家的美,但过于纯粹而理性的观赏态度使我们无法具体感知她们的音容笑貌,更无法从中体味诗人内心深层的情感。
除上所列,《子夜歌十三首》也是吴伟业早年艳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以仿齐梁民歌写就的艳体诗,以咏与妓家的欢好为主要内容,表现缠绵的儿女私情。在风格上,上承六朝民歌的绮艳,而新增了明末的纵欲色彩。现以其中二首为例:
其一:欢是南山云,半作北山雨。不比熏炉香,缠绵入怀里。
其五:双缠五色缕,与欢相连爱。尚有婉转丝,织成合欢带。
《子夜》群歌的出现与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主义有关,廖可斌认为:“明末文学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的开端,可以从复社、几社的形成算起。”[1]这次复古运动是明末士人试图力挽危澜的又一次努力,在内容上包括了向儒学的复归及对古诗文的推崇。复社创始人张溥对六朝文学极为推重,而作为复社骨干,又是张溥及门弟子的吴伟业自然深受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子夜歌十三首》在语言上极力模仿六朝民歌,善用双关与谐音,但艳情成分较多,读来并无六朝民歌的感人。“欲”的成分过于彰显,反而掩盖了“情”的质朴。但这些艳情诗却体现了吴伟业对于女性题材的擅长,他以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去体味两性的欢好与情欲的沉醉,语言、情态间都极为靡丽。正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评论:“梅村诗本以‘香奁体’入手, 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 辄千娇百媚, 妖艳动人。”[2]
若要考订早期妓家之作出现的背景,不得不考虑诗人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政治处境与心态。徐江先生认为,以崇祯十三年为界,梅村早期的政治活动与心态有所不同。[3]自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至崇祯十二年(1639)是吴伟业在政治上的进取期,诗人力图有所作为而行为较为谨慎;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因多涉党争,渐觉仕途险恶,而萌生退隐之心,故于崇祯十四年(1641)以母病归辞,隐居家乡。而明亡前的妓家之作正产生于诗人归隐的背景之下。如果说刚入仕途而循规蹈矩的吴伟业行为不得不有所束敛的话,那么之后渐渐远离政治的吴伟业便越来越染有风流放荡的文人习气,而仕途的失意更使他沉溺于青楼歌舞,心系儿女情长。
另一方面,自北宋起就以蓬勃之势踊跃发展的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到明后期更以新的经济形态改变着士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在思想界,从王阳明首倡心学、到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这股明中叶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不仅肯定人的合理欲望与享受,而且极大促进了士人们精神的解放与自我意识的提升,而明末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又促进了社会上奢侈享乐的盛行。故吴伟业早期的妓家之作可说是个人灰心仕途与风流而开放的社会风气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
当吴伟业在明末度过了几年风流放荡的生涯以后,崇祯十七年(1644)的申甲国变彻底改变了整个明王朝及吴伟业同时的许多士人的命运。明亡后杜门不出、以遗民自居的吴伟业是致力于以一代诗史照兴亡,曾经萦绕在诗人心中的儿女私情终被易代之痛与亡国之思替代。以妓家入诗的题材得以延续,但沧海桑田大变故激荡起的风云气、悲怆情,洗涤、冲刷去了明亡前浮艳的脂粉气、轻薄气。[4] 情欲的成分褪去,对女性命运的关照得以凸显。妓家不再作为赏玩的对象入诗,而是承载了兴亡之叹与诗人的沧桑之感。《圆圆曲》正是易代之际妓家之作的最具代表者。
秦淮名妓陈圆圆因与明末将领吴三桂的分合情事,而在风月变幻的明清之际占有一席特殊地位。“冲冠一怒为红颜”虽不免带有文人叙事的感性成分,但无可否认,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夺回陈圆圆的史实一举把陈圆圆置于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从此“一代红妆照汗青”成了人们对这位名妓最为绮艳的遐想。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诗人用婉转又富诗意的语言描述圆圆的身世与美丽,这样一位貌美而多情的女子,其命运必有引人关注之处。故接着以大段的笔墨叙述她在盛名之下的种种波折: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晳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从被豪家强载到遇合吴三桂,再到二人被迫分离而被李自成部下掳去,在这一系列的周转中陈圆圆始终是被动态的。辗转于权贵之手,却“明眸皓齿无人惜”,只能在孤独与无奈之中“等取将军油臂车”。“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吴三桂的出现仿佛让一切有了美好的开始,虽然中途历经磨难,但幸未被辜负,并终因吴三桂的英雄之举而得以盼来“无边春色来天地”。
《圆圆曲》把宏大的历史叙事依托于儿女情长,但诗人的立意并非单纯歌颂爱情。诗中的陈圆圆虽也有对爱情的憧憬与幻想,但吴三桂显然对于她改变命运的意义更大。她所日夜期盼的正是:“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从而彻底摆脱“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的不幸命运。
关于吴三桂的形象历来多有争议,刘剑先生认为吴三桂在《圆圆曲》中是集英雄和叛徒的双重想象。[5]他首先是一位多情的英雄,他的多情不仅表现在初见陈圆圆时的心动:“白晳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也表现在心爱之人被重新夺回之后的极度宠爱:“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作为一位守关将领,吴三桂无疑有着极强的军事才能,能够从起义军手中顺利夺回陈圆圆,也要得益于“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更重要的是,吴三桂深知自己在明末复杂局势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多方政权中的摇摆态度,正是为了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与最大化地实现自身价值。无论是为了陈圆圆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全家白骨成灰土”是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诗人对吴三桂怀有较复杂的情感,几乎同时掺杂了讽刺、同情与哀叹。他虽为明朝叛将,但在乱世之中仍不失英雄本色,况且“冲冠一怒为红颜”并非人人有这样的魄力与勇气,他的降清更一举而扭转了乾坤,奠定了大清几百年的基业。
《圆圆曲》的叙事终结于吴三桂的云南封侯,陈圆圆随之荣华尊宠。但全诗却以一种惆怅空幻的基调结尾: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诗人先是以西施喻圆圆貌美,后又以西施喻其结局,虽是叙说“时事”而带有沧桑的历史感。《圆圆曲》的感人之处正在于真实而富有情感地记录了身处历史巨变中的人有着怎样的动荡悲欢,而这种悲欢又是由怎样的不可预料的外力带来的。吴伟业深知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不仅发生在当下,同时也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循环往复。从这一点来讲,吴伟业晚期的叙事诗已经超越了“诗史”的范畴,从根本上表达了一种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珍惜。
虽然英雄、美人、功名、荣宠最终都将沦为一场空,但人生的际遇让他们不得不走上历史的舞台,走向既定的悲剧命运。而吴伟业把这种悲剧归结于 “当时只受声名累”。陈圆圆色艺俱佳的声名让她饱受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的辗转之苦;吴三桂作为镇守三海关的将领,“鼎湖当日弃人间”的动乱局势不仅让他的抉择事关历史的走向,也让他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身败名裂。
“当时只受声名累”也正说到了吴伟业的痛处。《圆圆曲》创作于清顺治八年(1651),此时申甲国变的剧痛已经褪去,诗人所面临的是日益艰难的现实处境与政治压力。吴伟业在江南士子中极大的声名与威望,让他虽为遗民而常怀惴惴之心。“虑祸”在吴伟业的人生抉择中占有重要因素,他在明末激烈的党争中主动退隐;在明亡时虽未殉国,但也不愿如钱谦益般率众归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及至顺治十年(1653)不顾友人反对违心仕清,莫不出于个人福祸的考虑。但身处易代之际,祸福并不由己,他在遗民中的巨大声望终使他无法逃脱清廷的招揽而在余生怀有失节之痛。关于他的仕清,吴迪昌先生有较为客观的表述:“吴伟业的性格中有懦弱和首鼠两端的缺憾,这是导致他失节的一个因素,而缙坤士大夫的虚荣好名,特别是热衷于政治派别活动的那种名心未除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基因。”[6]可见除了哀叹“为声名所累”外,他无疑也希望抓住一丝声名所带来的机遇,只不过亲历了易代与兴亡,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诸事皆空的幻灭感。
三
朱庭珍《筱园诗话》曾评价吴伟业:“吴梅村祭酒诗,入手不过一艳才耳。迨国变后诸作,缠绵徘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7]虽以“入手一艳才”来概括吴伟业早期诗作未免有失偏颇,但若放在明亡前妓家题材的创作上还是合适的。而同样是以妓家入诗,明亡以后,因朝代不同与诗人心态的变迁,诗歌意蕴与妓家形象也大不相同,不仅由单纯的儿女私情走向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且在后期的妓家之作中显然承载了诗人更多的心曲。
注释:
[1]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2] 赵翼:《甄北诗话》卷九 ,《清诗话续编》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290页
[3] 徐江:《论吴梅村早期诗歌风格——兼考其早期作品编年》,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
[4] 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5] 刘剑:《无言历史,有恨人生——<圆圆曲>人物形象的另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9年第6期
[6] 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7]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 ,《清诗话续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2355页
参考文献:
[1] 严迪昌. 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 刘剑.无言历史,有恨人生——《圆圆曲》人物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名作欣赏.2009年第6期
[4] 何锐珏.《圆圆曲》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慧杰(1989.10——):女,26岁,汉族,籍贯河南商水县,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论文作者:郭慧杰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6
标签:诗人论文; 崇祯论文; 梅村论文; 明末论文; 之作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论文; 兴亡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7月论文;
